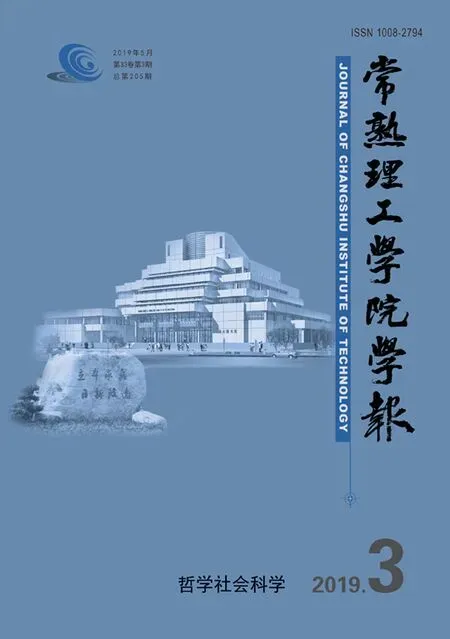权利粘性、“三苏同城”与“强富美高”
——泛长三角区域内江苏空间生产权利审视
2019-03-21王新建王梦哲
王新建,王梦哲
(淮阴师范学院 a.马克思主义学院;b.淮安发展研究院,江苏 淮安 223001)
一、 问题的提出
“三苏”是指江苏域内传统意义上的苏南、苏中和苏北。从空间地理分界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三苏”泾渭分明且难以通联,早已成为“三苏壁垒”。江苏省委 2017年 5月提出“1+3”重点功能区战略设想①参见《“1+3”重点功能区战略正式提出,重塑江苏发展优势》,《新华日报》2018年1月5日第4版。“1+3”的“1”,即扬子江城市群;“3”即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济区、徐州淮海经济区。这是推进江苏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其中,扬子江城市群侧重集群发展、融合发展,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沿海地区主攻现代海洋经济,是潜在增长极;江淮生态经济区重在打造生态竞争力;徐州通过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拓展江苏发展纵深。各大功能区域板块各有侧重,从而在更高层次上统筹区域发展,重塑江苏发展优势,提升江苏未来竞争力。,从理念层面打破了“三苏壁垒”,这一被学界称之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手笔”,让人们终于敢于想象“三苏壁垒”可望打破的前景。而这种打破的前提,只能是高铁时代“三苏同城”的实现,即依托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把从最南端的苏州到最北端的连云港这450~460公里的距离连接起来,实现“三苏”所有城市间的“一日交流圈”[1],即2~2.5小时的同城化生活圈。
然而,不消说多年来人们不敢想象“三苏同城”,就是在“1+3”战略提出一年多以来,学界至今对“三苏同城”依然保持着“坚定的缄默”。我们的问题是:仅有“1+3”战略能否破除“三苏壁垒”?“1+3”战略靠什么打破“三苏壁垒”?是目前学界都认为的市场吗?然市场又靠什么建立起来?显然在高铁时代,没有高铁驱动的“三苏同城”空间变革的实现,遑论江苏域内整体市场的建立,“1+3”战略也只能永远在人们的“设想”之中。那么,又是什么令哪怕仅仅是观念和概念层面上的“三苏同城”难产呢?这便关涉到本文所要讨论的当代空间批判理论中空间生产的权利粘性问题。
本文将依据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在陈忠“空间生产的权利粘性”[2]理论视域下,进行讨论。
二、 空间生产的权利粘性与“三苏壁垒”
当代空间批判理论昭示,空间生产早已上升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发动机和重要衡量标尺。空间批判理论家爱德华·苏贾指出,空间性乃“社会生活的真正本源”[3]。当代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大卫·哈维也指出,“压缩时间”和“突破空间”将成为人们用来不断取得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主要手段;社会时空在较根本的层面制约着人类社会实践的范围、规模和水平,并决定着社会实践的路向和手段[4]。
理论上的“强调”固然丰满,而现实却又是那么骨感。由于各种主观、客观或历史、现实等原因,一些地域在社会时空的功能呈现上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空间的生产和变革总是受到权利粘性的严重制约。上述“三苏壁垒”便是如此。
“权利粘性,就是由于权利的过度个体化或区块化、区域化、国家化,由于微观、区域或体系主体对自身权利、利益的理性或非理性坚持,也由于国家宏观制度对权利确认与设置的片面化、刚性化,不同层面的权利主体围绕空间、物品、财富等权利对象所形成的一种相互纠缠、胶着、无法改变与推进的状态。”[2]陈忠先生还强调在这种相互胶着、扭结的空间生产权利粘性状况下,行为主体的行动可能丧失,主体权利也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以此审视,江苏在空间生产上所反映出的权利粘性,至今在学界和政界的讨论中还处于无涉状态。
截至2017年底,我国高铁已达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2/3,“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形成。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和高铁时代时空距离的缩短带来的便利,使以前在人们心目中朦胧存在的空间权利问题凸显出来。对处于空间权利弱势的苏北、苏中的人们来说,一方面,在出差、旅游等域外出行活动中深切地感受到时空压缩带来的诸多便捷和先进;而另一方面,在回到域内时,又痛感空间权利的弱势和固化给自己带来的诸多不便和落后。“三苏壁垒”表征的正是这样一种空间权利的弱势和固化,即江苏域内空间生产上的权利粘性。而且随着泛长三角域内浙皖两省高铁出行的便利,苏北、苏中的人们这种被固化的心理意识便愈加强化,对空间权利粘性的无奈也愈加凸显。一如马克思指出,在周围都是小房屋的时候,一座房子再小也能满足要求。但若在附近耸立起高大的宫殿,这座小房子便缩成了茅舍的模样,“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5]
2008年,国家推出由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一市三省组成的泛长三角超级经济区决策。上海作为泛长三角同城化的“极核区”[6],自然是泛长三角这只大雁的头部,居于“引领”和“带头”地位。于是,浙江、江苏便成为大雁的两翼,安徽东部则居于大雁的身躯位置,安徽西部便是大雁的尾巴。有比较才有鉴分,十年筚路蓝缕高歌猛进,以GDP为主要标尺的发展成就让长三角北翼的江苏实实在在地走在了全国前列,但高铁建设却躺在2011年6月开通的京沪高铁线上睡起了大觉。目前,南翼的浙江除海上的舟山市没有开通直达上海的高铁之外,其余所有地级市均开通了直达上海的高铁,而且用时均不超过同城化“一日交流圈”的3小时门槛。浙江经济发达或不足为据。那么安徽呢?安徽最西北端的淮北至上海已通高铁近两年,距上海约630公里的空间距离用时也仅3.5小时稍多;安徽西部的六安、安庆通达上海的高铁均超十个班次,用时也只有3~4小时;处于大雁尾巴尖的亳州,是安徽目前尚未开通高铁的最后一座地级市,2019年底也将开通直达上海和杭州的高铁线路。
北翼的江苏呢?北翼翼尖即最西北端的徐州倚靠京沪高铁西线已与上海通联7年多,用时最长3小时稍多,最短2.4小时;最东北端的连云港目前有两个班次的“K”字头列车通达上海。除此之外,余下苏中、苏北的6座城市即宿迁、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和南通至今无火车通达上海,更不消说高铁和动车了。虽不能说“地无寸铁”,但转车绕圈抵达上海的无奈,是身处苏北、苏中之外的人们感受不到的。而这6座城市所在区域面积却占江苏全域面积的2/3。即便在占江苏全域面积3/4的苏北和苏中域内通联,也是车次寥寥,犹如蜗行。更令人惊诧的是,作为地级市的宿迁,其市区竟也没有火车停靠站。我们也知道,目前连淮扬镇、徐宿盐淮等高铁线路正在加紧施工。可等到通车之日,保守估计,怕也要晚于泛长三角域内的浙皖两省5~7年。
《2016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报告》指出,随着国家拓展区域发展新格局战略的实施以及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推进,2015年长三角立体交通网络得到进一步优化,区域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网络逐步完善[7]。必须指出,这里的“逐步完善”,却是撇开苏北乃至苏中的“逐步完善”。不论从江苏域内还是从泛长三角超级经济区整体乃至国家战略层面看,这种撇开都是极其偏颇的。泛长三角经济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被誉为国家第一区域经济板块,又被称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在国家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全国转型升级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8]。区域竞争力的培育,国家区域总体战略的实施,包括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等等,都要求加快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和一体化发展。而上述撇开,已经对泛长三角乃至国家层面区域协调发展的脚步形成羁绊态势,对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的东部要率先发展起来的决策实施造成延滞效应。
三、 以“三苏同城”破解“三苏壁垒”权利粘性,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奠定空间变革的根本支撑平台
江苏域内空间生产的权利粘性最根本的表征或后果,不仅是“三苏壁垒”,还有江苏在未来的十多年内,将被牢牢地锁定在“国情面相”之上,即占江苏全域3/4空间地理面积的苏北、苏中大地,将继续延续着“苏北(苏中)之相”的悲催。所谓“国情面相”,是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省份的江苏,其在南北差距方面与国家层面的东西差距酷似孪生,即在“面相”上与国情相像。我们难以想象,但却不得不承认,15年前就提出“两个率先”的江苏与极核区上海的通联竟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越近越发展”“越远越落后”的窠臼,仿佛经济增长的扩散势能因“长途跋涉”而变得“筋疲力尽”似的[9]。现象背后隐匿着本质,即便是这种势能好似筋疲力尽的假象,也是域内空间权利粘性这一本质的反映。一言以蔽之,要彻底消除“国情面相”这一横亘在江苏经济社会一切发展目标、战略决策的实现面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唯有倚赖“三苏壁垒”空间结构上权利粘性的消除。而其最根本的消除路径和手段,就是苏北、苏中和苏南在高铁时空压缩的空间变革中实现“三苏同城”。“三苏同城”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更是必然的。高铁时代的“三苏同城”,能够最大限度地销蚀目前江苏在空间权利上的粘性状态和垄断局面,为江苏空间权利的合理化变革指出了不容他顾的路径和手段。以“三苏同城”破解“三苏壁垒”的权利粘性,推进空间生产、空间权利的合理化,保持空间生产的可持续性以最终消除“国情面相”,已经成为关乎江苏、泛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乃至国家区域发展整体规划和布局健康持续推进的基础性工作和战略性抉择。
现代空间批判理论认为,空间生产、空间权利的合理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最主要的标志。这种合理化,就是“人在把握各层面复杂关系的基础上,自觉营建能够统筹复杂关系的制度、知识、行为方式。”[2]对现代社会而言,没有个体、社会、国家三层主体的总体和谐和相互关系的合理化,也就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化,自然也不会有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走向“强富美高”的道路上,江苏必须自觉地推进空间变革、空间权利的合理化与和谐化,自觉地从苏北苏中的跨越发展目标、江苏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目标、泛长三角超级经济区这一国家区域发展目标乃至国家区域发展整体布局等多层发展目标之间有机关联的视角,以辨证施治、综合调适的高标准要求,致力于解决空间权利配置中长期“淤积”的老问题和遭遇到的新问题,以实现对区域内外空间生产制度、空间生产文明和空间生产心理等方面的弹性建设。
第一、致力于空间生产制度的弹性建设。多年来国家层面、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江苏域内空间生产制度的过于刚性化,对江苏空间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钳制效应。自江苏在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两个率先”以来,无论是苏北、苏中身为“个体”层面的权利粘性,江苏域内身为“区域”层面的权利粘性,还是泛长三角身为“整体”层面的权利粘性,乃至国家层面的制度粘性,都体现出一种难以随时代发展而调整的制度刚性,其集中表现,就是作为“个体”层面的苏北、苏中的“被忘却”“被淡化”。无论如何,在“两个率先”提出多年,尤其在京沪高铁通车多年来,在浙皖两省快马加鞭建设高铁的同时,苏北、苏中在与苏南乃至“极核区”上海通联上几近原地踏步,这充分说明空间制度设置上对“个体”的“忘却”。比如作为未来苏北同城化“极核区”的淮安,因被这种制度刚性所制约,也只能耗费巨资在兴建100多年前老上海“版本”的轻轨电车和绕城高架上“自说自话”,却难以突破在空间生产上“被忘却”的制度刚性。其最鲜明的表征,便是淮安在与南京的通联上至今竟然“地无寸铁”。这种被制度刚性所制约的“自说自话”,在苏北多个城市均有突出表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青岛途经连云港到盐城的高铁线路,竟先于江苏域内徐宿盐淮高铁在2018年年底开通了。按说在体现国家战略的京沪高铁开通后,江苏包括泛长三角整体应该能够深刻体会到高铁给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力,并在南北通联的高铁线路建设上乘势而上。可令人费解的是,江苏一直在做“睡觉”状,泛长三角整体也好似“淡忘”了北翼这“半边翅膀”。笔者认可“空间差异的客观存在及其多样性,决定了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非均衡性”[10],这是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但在高铁时代,在迈向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时代,怎么还能在制度设计上延续着忽视“空间母体”重要性的惯性,以致失却最能发现问题的批判视野,“一任历史决定论遮挡着视线,无法走进空间崛起的现代生活世界”[3]呢?学界早在2012年便指出:泛长三角域内缺乏专门机构统筹协调,各地政策和法律多以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出发点,难以形成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受制于各种制度因素的影响而一直无法取得关键性的进展[11]。这是具有深刻性的对症评论,只是这种评论所指出的症结,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并确定了协调机制之后,也没有对泛长三角形成些许鞭策之效。只有打破上述制度上的刚性,致力于合理化的、富有弹性的空间制度建设,才能顺利实现“三苏同城”美好愿景。
第二、致力于空间生产文明的弹性建设。对空间生产文明的理解,20世纪末逐渐走向成熟的西方新区域主义理论可作他山之石。建立在治理理论基础上的新区域主义,主张区域内地方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和市场主体共同构成治理主体及其组织形态,共同制定治理理念和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它将城市群治理看作是多种政策相关主体之间谈判的过程,而不是通过科层制或竞争而推进的过程,其要点之一便是“国家-市场-社会”构成的多元行为主体[9]。以此反观我们当下的“区域治理”,可以看出落后地区其主体性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曾几何时,我们一度顺应历史的必然,让有条件先富起来的地域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强力推动而先富起来,并指认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沿海或条件好的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又要求它们拿出更多力量带动后发地区发展。这便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是一种政府通过推行非均衡战略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但目前的问题是,一些地区在受益和发达后并未能及时地对后发地区进行补偿性或带动性帮助,却在以效率为取向的政府运作模式的惯性推动下,进一步淋漓尽致且充分地发挥着其市场主体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应有”行为,使收入差距快速扩大且分化加剧[12]。学界所揭示的这种倾向,江苏在空间的功能性、利益性、道德性等层面的综合施治方面同样存在。江苏对“国情面相”的“固守”,“苏北(苏中)之相”的悲催,便是上述倾向性的注脚。易言之,国家整体层面存在的倾向,作为沿海大省和经济发展排头兵的江苏也同样存在。我们实在不该忘记,当初宣布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还有“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更伟大的政策和目标紧跟其后。当下,历史的脚步已走到了我国“要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13]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恰好处于中国方兴未艾的高铁时代,是党的十九大号召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转向效应和高铁驱动的时空压缩效应双效叠加的时代节点之下,综合运用行政、市场、道德等手段对下一步的江苏空间生产进行辨证施治,不断提升空间生产的文明弹性,从而更健康顺利地走向“三苏同城”,这是与上述制度弹性一样不可规避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
第三、致力于空间生产心理的弹性建设。“中国人对空间的理解,历来有综合性、杂糅性,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在思想深处也始终把空间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归依与基本构成”,即“把空间作为同自然融合为一体的主体性存在的一部分来认识”“把空间同主体、家族的延续、国家、利益、道德,乃至所有的非理性层面相联。”[2]对空间的这种理解,具体表征于苏北、苏中的人们不仅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更期盼拥抱“南方”。百度词条对“苏北”“苏中”的介绍是:苏北位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沿海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地势以平原为主,拥有广袤的苏北平原,辖江临海,扼淮控湖,经济繁荣,交通发达;苏中东抵黄海,南接长江,与上海、苏南地区隔岸相望,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江苏省经济发展最快地区之一。尽管这些介绍明显是一半写实一半多具溢美和渴盼的“期许”,但却令人神往。从目前的状况看,长期条块分割致苏北、苏中与苏南近在咫尺却成天涯般遥远。淮安与省会南京作为文件上的挂钩城市,却长期钩而不连;除徐州之外的苏北和苏中7座城市,多年来延续着在“普铁绕圈”和“转车一天”的无奈中与苏南和极核区上海的交往;而正在施工的连淮扬镇高铁线路,或将使以淮安为中心的苏北以“高铁绕圈”的形式在高铁时代延续着与省会南京的绕圈交往;多年来渴盼的“连淮宁直线高铁”,概念的提出令人神往,而施工却迟迟不见。前述苏北、苏中只能“自说自话”的状况,反映的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争取,更是一种渴盼。那么,苏北和苏中的人们在空间的社会心理图景上的期冀,在高铁时代“三苏同城”美好愿景的导引下如何实现呢?约翰·罗尔斯指出:应“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14]鉴此并充分考虑到空间权利粘性的消除,在江苏空间生产和变革的过程中,理应充分理解苏北、苏中的人们空间心理上的特殊性,致力于营建充分考虑这种特殊性的、更为合理的空间文明样态——“三苏同城”。同时在“1+3”重点功能区战略设想的实施过程中,亦应充分考虑到苏北、苏中在作为生态功能区建设上对江苏、泛长三角整体乃至国家层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巨大生态贡献,聚焦和致力于传统三大板块在差异发展、协调发展、融合发展基础上的,能够反映富有弹性的空间生产心理建设的补偿性发展和一体化发展。这样的空间心理弹性考量,才能凸显现代文明与发展效应,该是江苏空间生产和变革的题中本有之义。
四、 结语
当下早已成为显学的空间批判理论,“实为现代文明发展所造就”。它绝非“某些思想家或学者出于灵感而偶然的创设,而无可辩驳地与人类现代化运动息息相关。”[15]作为当代主体权利重要内容的空间权利,其大小及合理化程度的高低正是衡量这种现代文明和现代化水平的最主要的尺规。多年前提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江苏,理应在空间变革的道路上,对域内空间权利的合理化给予足够的在意和重视。试想,不消除江苏域内空间生产和变革的权利粘性,学界上述在介绍苏北、苏中时那多具溢美和渴盼的“期许”,如何变成人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笔者在这里很想把“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更改为“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把“经济增长极”更改为“与苏南实现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极”,其间所要表达的,便是倚借对权利粘性的消除而走向“三苏同城”,继而迈向习总书记殷殷期待的“强富美高”新江苏。舍之,遑言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