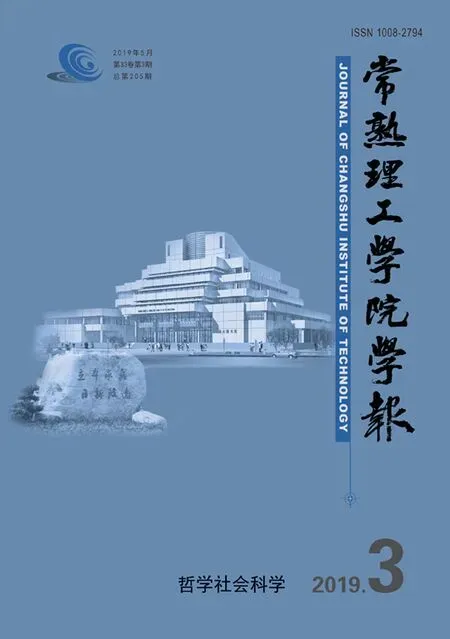北方书曲艺人的拜师行为与职业资格
——基于清末及民国相关资料的考察
2019-03-21陈雪冰
陈雪冰
(内蒙古察右前旗旗委办,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 012200)
一、 “拜师”的重要性
至少在1949年以前,北方书曲艺人①为避繁琐,如不特别说明,则本文所谓“书曲艺人”“旧时艺人”等,都是指1949年前即开始作艺的北方书曲艺人。都极看重师承。业界要求凡从业者必须有师父。评书大家连阔如说:
凡是江湖人,不论是干哪行儿,都得有师父。没有师父是没有家门的,到哪里亦是吃不开的……就以说评书的这行儿说吧……不论是谁,若想入这行儿,都得先找个人介绍,拜个说书的为师:先下帖请人,在饭庄内定下酒席;磕头拜师父、递门生帖;得将同行有门户的先生们请了来,先磕头、吃饭。大家亦受了他的头啦,亦吃了他的酒菜啦,同行的先进之人才承认这行里有他这么个人。然后学好了能力,不论是上书馆献艺,或往市场搁明地、拉场子说书,才没人拦挡。[1]85
无师承者,行话谓之“海青”或“海青腿”。理论上讲,“海青”没有从业资格,不得以此挣钱谋利,分业内人士的一杯羹。如果没有从业资格而强行下海挣钱,业内人士有权破坏其演出,行话谓之“踢买卖”或“横买卖”,手段之一是“携家伙”,即业内人士通过一定方式将“海青”的道具拿走,以取消其表演资格。对此连阔如曾有记述:
就以说评书的艺人说吧,他要是没有家门、没拜过师父,若是说书挣了钱,必有同行的艺人携他的家伙。携家伙的事儿是:同行的艺人迈步走进场内,用桌上放的手巾把醒木盖上,扇子横在手巾上,然后瞧这说书的怎么办。如若说书的人不懂得这些事儿,他就把东西物件连所有的钱一并拿走,不准说书的再说书了。[1]46
除了“携家伙”,还有其他手段。连阔如记载过这样一个实例:
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位松先生……他就没认师父、没拜门户。到馆子说书,颇有叫座的魔力,一班听众无不赞成。他要是干长了这行,可坐头把交椅。不料同行的人说他没有门户、没有师父,警告开书馆的掌柜:如若用他,全体人员都不进这书馆。“黏箔”(管开书茶馆的人,调侃儿叫“黏箔”)们就不敢得罪大众,居然没人敢用。那位先生亦有志气,弃了这行不干了,另谋他业啦。[1]85-86
连先生对上述行为的实质说得很透,即“海青”遭排挤打击的真正原因,是“说书挣了钱”。基于类似的考量,艺人同样会为难与排挤挣钱能力强、收入丰厚的同行,只是手段有别。也就是说,不论对内还是对外,只要是分享同一块蛋糕者,其间的打压不可避免。“携家伙”等行为与“维护行规”实无关系,其目的是将挣钱能力强、收入丰厚的从业者驱逐出市场,以抢占市场份额,保障自身利益。“没认师父、没拜门户”只是一个发起攻击的借口而已。但既有成例,后来者自然乐得踵武与效仿。于是原来的借口,逐渐成为业内的“规矩”。
理论上讲,“海青”因为没师父而被同行责难,则只需拜个师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下海挣钱了。“携家伙”之类的做法实不能真正阻止有能力的“外行”分一杯羹,反徒结怨恨。那么,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呢?
第一,从“海青”的角度讲,并不是所有的“海青”都有拜师下海的机会与勇气。首先,出于种种原因,不是所有的“海青”都有师可拜,如连阔如就提到“海青”范友德因年岁大而无师可拜[1]86;其次,旧时代的艺人社会地位底下,被目为“下九流”,甚至是“下三滥”,即使普通平民也多看不起此业中人。所以,在一部分“海青”看来,喜爱并研究此道、玩票并借此谋利是一回事,当真拜师下海是另一回事。玩票,毕竟是在“玩”,还算是局外人,自己与旁观者所持的态度都是游戏的、宽容的;一旦拜师,便成了此道中人——这一般被认为是“丢人现眼”“玷污祖宗”,甚至是“身染下流”。民国时的评书大家常杰淼在其巨著《雍正剑侠图》开篇的定场诗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情绪:“何人引我染风尘?荏苒韶光年旬五!衣冠颠倒辱为荣,放浪形骸玷曾祖。都门赤子不堪言,风流乞丐甜中苦”[2]尽管他当时已在天津得享大名,收入颇丰,而且“口似悬河若水流,心同宝鉴如案牍。文惊四座吾说评,点缀八方皆仰俯”,但依旧认为自己是个“辱为荣”“玷曾祖”的“风流乞丐”。所以,拜师,其实是横亘在内外行之间的一条红线,可以阻挡一些“海青”进入业内。
第二,从“携家伙”者的角度来说,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成本却不甚高。通过“携家伙”,他至少可以“把东西物件,连所有的钱一并拿走”,这其实就是“讹诈”。另外,旧时书曲艺人多游走于各地各书馆卖艺,演满一定时间后,艺人往往会换另一处演出场地;而“海青”寻师、拜师必然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携家伙”者只要将眼前这个有力的竞争对手赶走,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己的收入就能保证甚至提高。等对方拜师回来,也许自己早已离开这个书馆了,甚至自己与他再也不会见面了。
第三,一个从业者是否拜师,对个人来说,也许意义不大;但对这个行业来说,却有一定的意义。旧时,江湖艺人之间有互帮互助的传统:有师门的江湖艺人肩负着无偿帮助同道度过时艰的义务,也享有在困难时无偿接受同道帮助的待遇。“海青”无须遵守这一传统,却分享了本行业的一杯羹。显然,为本行业增加一个成员,总比增加一个只得利不奉献的局外人要好得多。
综上可见,“凡从业者必须有师父”的行规,实质上是江湖艺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设的一道藩篱。拜师,是削平藩篱的手段之一。
二、 拜师的仪轨
按行规,拜师须经过一定的仪式,对拜师仪轨的记载,所在多有;实际操作中,却并不一定完全按规矩进行,需视师徒双方的个人意愿、私人关系、经济状况、实际处境等而定。简单者,双方只消口头约定,便算确立师徒关系,只要自此后双方都对外公开承认此师徒关系即可;繁杂者,则要大摆筵席,广邀业内外宾朋耆老,磕头拜师、立下字据等等。孙桐枝藏《说书艺人师徒谱》记载:
收徒拜师,先由师父下帖请本门的师伯、师叔、师兄弟们,少数外门前辈,举办酒席。一切仪式皆有一定的规矩:内设神座,立神牌,上写“供奉祖师爷周庄王之位”;正当中摆供桌一面,香炉供品;在“周庄王”牌下,写上书曲故去的老前辈名单。到焚香行礼之时,公推一位年高居长者主持仪式,分辈分大小上香磕头,每进行一项都唱念祝词。礼毕之后,新徒弟跪向师父,头顶门单,门单上写:年月日,某省县人,年龄,“愿投某师门下,学说书曲,以谋衣食。某某在祖师爷驾前叩禀,倘有负心,听凭师父论处。对师父师母生养死葬。介绍人保师、保师兄、立业人具押手印”。其师与本门人共同讨论给徒弟取个名字,写在门单(也叫关书、文书)上。然后新徒弟逐一磕头,门里门外彼此祝贺。行拜师入门之礼至为隆重。
待几年后艺成,徒弟必须先谢师父,也摆酒席,叫“入摆知”。是日,为师者赠徒弟扇子、醒木、手帕,并将书曲界的规矩、行话暗语传授给徒弟,从此徒弟闯荡江湖。[3]
现对此仪轨中的几个要点分析如下:
(一)祖师
对书曲艺人祖师的记述较多,但纷乱复杂、互有歧异,就连业内人士对本行祖师究竟是谁、何以奉其为祖等问题,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车王府藏鼓词《左传春秋》中说:“众公,说书乃是当初周庄王爷所留”[4];《唐河曲艺志》记载:“曲艺艺人供奉自己的祖师,称作敬神。三弦书艺人敬三皇爷(天皇、地皇、人皇);坠子艺人敬丘祖(丘处机);评词艺人敬何真人;鼓词艺人敬庄王爷,也敬孔子;莲花落艺人敬范丹”[5];《桐柏县曲艺志》则说:“莲花闹敬育国家……评词、大调曲不敬神”[6]。可见,仅河南一省之中的说法便有矛盾处,若再旁及北方其他地区,就更缴绕难明了。但总体来说,北方书曲艺人所奉的祖师,大致以黄河为界:河北及受河北影响巨大的东北,多奉周庄王;山西、陕西一带,多奉三皇;河南、安徽、山东多奉丘处机。李乔先生的专著《行业神崇拜》中对此有详尽的梳理,因其罗列的资料已经非常周备,故不再赘述。
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祖师”是本行业的开辟者。其实,所谓“祖师”,并不一定是该行业的第一个从业者,但一定是所有从业者中影响最著的那个。而每个行业中杰出且有名的人往往不止一个,所以,业内所奉的祖师往往也不止一个。天津的评书老艺人张枢润说:“说书人供奉的三位祖师爷是孔夫子、周庄王(传说就是周朝第五代君王,名姬佗)和文昌公(或称文昌帝君)。评书门里为什么把这三位奉为祖师爷,师父没有解释过。而评书艺人在收徒、举行‘拜门’仪式的时候,一定要给三位祖师爷上供、烧香,新入门的徒弟也一定要给三位祖师爷叩头”[7]。
以上内容至少反映出两点:
第一,对艺人而言,“祖师”只是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即依“敬天法祖”的传统,“祖师”一定要有,至于是谁,则不那么重要。行业祖师往往不是考证出来的,而是议定出来的。通过寻检历史与传说,找到一个可以和本行业产生联系的人或神,由业内多数人接受后,将其尊为本行业之祖;同时,这个偶像必须要有名、有影响力,其与本行业关系的紧密程度则不那么重要。比如铁匠奉太上老君为祖师,居然是因为“太上老君有八卦炉的传说使之成为铁匠的祖师”[8]。如果历史与传说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偶像,那也不妨编造一段故事,以塑造出一个偶像。对业内而言,“祖师”除了接受例行的香火供奉外,唯一的作用就是给予艺人一点“因为我的祖师很高贵,所以我和我的行业不低贱”的精神安慰。
第二,各书曲门类所奉的祖师本有不同,但不同书曲门类奉同一祖师的现实,也许正说明艺人之间、各书曲门类之间会有交互影响。一个艺人同时从事几个书曲门类的表演,奉祖师之时,往往选择彼时彼地影响较大的那个祖师;而本不奉此祖的书曲门类,也因其他书曲门类的影响,转奉此祖。连本业的“祖师”都可以乱认,更说明,对艺人而言,“祖师”其实没那么重要。
(二)门单
门单,也称关书、文书、门生帖、海底、拜师帖等。今有连阔如《江湖丛谈》、孙桐枝藏《说书艺人师徒谱》、芦柏祥《拜师帖》、龚国强的《曲艺拜师帖溯源》等相关资料存世。
严格地说,拜师帖分为两种,《相声民俗调查》中说:
师父同意收徒后,徒弟要先写折子,也叫帖,即确立师徒关系的字据。帖又分红帖和白帖两种,红帖多是中途带艺投师或者家境较宽裕,自供食宿,只是学艺而已。写好“×××经×××介绍拜××为师……”等;家境贫困,从小学徒,只能在师父家吃住的要写白帖,帖上写着:“×××学徒×年,立字为据,其间天灾病业,投河觅井,两家各自由命;不遵师训,打死勿论。如本人中途不学或逃跑,需按日赔偿师父食宿费”,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张卖身契。[9]写下这样一份字据的目的,主要是防备日后可能出现因师徒反目而产生纠葛。
拜师帖中除了要注明师徒及见证人名姓、徒弟艺名、年月日等要素外,尚需讲明本门源流、本支的传承谱系、师徒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如《曲艺拜师帖溯源》中所收的拜师帖里明确写道:“情愿拜李永名下为徒,学艺守体、四海交游。如有截艺,老师一面承当;若有违命、欺师欺友、扣窑抓相、勾挂捧搂、非蒙即盗、不听训教,愿打愿罚、察清问明,送到当堂,一律问罪”[10];《说书艺人师徒谱》中也说道:“愿投某师门下,学说书曲,以谋衣食。某某在祖师爷驾前叩禀,倘有负心,听凭师父论处;对师父师母生养死葬”[2]322。
旧时道德将师徒关系与“天地君亲”并列为五伦之一。五伦,都处在“父”地位;五伦下的每个人都处在“子”地位。所以,师徒间形成的是一种类血缘的伦理关系。对徒弟而言,师父处于家长的地位,与徒弟生父享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利。这种关系推而广之,不断衍生:一师之徒为师兄弟、师父之师兄弟为师叔伯、师父之师为师爷、己之徒为师父之徒孙。由此,将所有从业者编织成一个带有浓厚家族意味的类血缘的共同体,其中的每一要素都能与世俗家族一一对应:整个行业即是一个大家族,祖师即始祖,各门户即家族宗支,所有从业者在这棵家族树上都有自己的伦理地位。没有师父,就是没有父亲,在家族中就没有自己的位置,自然就不是本家族中人,也就不是业内人士——这就是“拜师”形上层面的重要性所在,所以连阔如说:“没有师父是没有家门的,到哪里亦是吃不开的”[1]85。但须指出的是,我们也不应过分强调这种形上意义的重要性,因为对大多数从业者而言,只有能带来实际利益的,才是重要的。
正是基于拜师的诉求和这种伦理关系,师徒关系中,对师父的要求至少有两点:一是“传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艺”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某些徒弟也许并无学艺诉求,某些师父也许也不愿传艺于徒弟,但既称“拜师”,如不写上“学艺”二字,总嫌离题。二是不论师父是否传艺,都对徒弟负有荫蔽、教训之责。这其实是基于世俗中父亲的责任而提出的要求。而弟子不论是否向其师学艺,都必须孝养其师。这首先是基于世俗中儿子的责任而提出的要求;其次,旧时书曲业中普遍认为,通过拜师,弟子从师父处起码获得了从业资格,甚至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本事,这是师父对弟子的“恩”,弟子自然需要按照规则,以“生养死葬”的方式“报恩”。
(三)艺名与门户
徒弟拜师后,师父要赐以艺名。河南、山东、安徽一带,由于多尊奉丘处机为祖师,故也将艺名称为“道号”“法号”。这一名号通常有固定格式:“本姓+本门字辈+后缀名”,如单田芳,家名传忠,由其师李庆海赐名“田芳”,“田”是门户中他这一辈的排字,“芳”是后缀名。可见,艺名有两大基本用途:一是标示门户;二是标示行辈。
书曲界所说的“门户”有两种用法:一是指称书曲门类,如评书门、大鼓门等;二是指同一书曲门类中的支派,如河北书曲界通常认为鼓曲分梅、青(清)、胡、赵四大门户,评书分柯、赵、洪、屠四门。
至少从今日及今日所能溯及的历史来看,实在看不出各门户之间有何实质分别。也许在门户产生的那个时间,各门户在某些方面确有分别,但随着时迁事异,其间的差异逐渐泯灭了;也或许只是名为“梅、青、胡、赵”的四人在当时弟子众多,自然而然就被认为是四个独立的支系。
今日,各门户的分别恐怕只能体现在“艺名”上了。这是因为艺名中各门户所用的排字是不同的,比如西河大鼓梅家门排“春、德、庆、田、祥”,另一支排“长、树、华、荣、成”;竹板书门排“万、福、来、临、贺”;西河大鼓清家门排“起、连、增、景、祥”;北京评书排“德、致、傑、阔、增”;东北评书排“悦、庆、桐、浩”等。
尽管诸家所用的排字有重合者,但只要稍加确认,就很容易确定其所属门户及行辈:同一门户,前一字的行辈高于后一字;不同门户间,梅家门“庆”“长”、清家门“起”、竹板书门“来”、北京评书“阔”、东北评书“桐”为平辈,余者自可类推。
“艺名”是艺人行艺时所用之名,目的是便于观众识记,以提高艺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所以往往易识易记、幽默诙谐,甚至有哗众取宠的意味。古者如黄幡绰、敬新磨、郭门高、罗衣轻等;近者如常宝堃艺名“小蘑菇”、骆玉笙艺名“小彩舞”、马瑞河艺名“马三疯子”等。有的艺人因久用艺名,本名反而失落无考了。“艺名”的产生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由艺人自己选命,如张英杰之艺名“盖叫天”就是自己选定的;二是先由广大受众约定俗成地叫响后,才被艺人接受的,如上所举“小蘑菇”“马三疯子”等皆是如此。
但师父所赐的那个名号,显然不具备这种特质。因为对受众而言,这个名号并不见得易识易记;而且由于其固定格式,在同姓同字辈的情况下,单靠后缀名来区分,辨识度显然不会很高,比如王振山、王振芳与王振元,李庆海、李庆溪、李庆洋与李庆魁等,其名相似,辨识度显然不如王振山的艺名“一人团”、王振元的艺名“老毛贲”高;再如马轸元、孔轸清等所用的“轸”字算不上是常用字,这样的名字就更谈不到“哗众取宠”了。而且,如果这个名字是“艺名”的话,一定要在行艺时使用才有意义。但实际情况是,有不少艺人行艺时并不用这个名字,而别有艺名,如张士权行艺时用“二狗熊”、常宝堃用“小蘑菇”等等。另有部分艺人则舍师父所赐的名号不用,而用家名,如西河泰斗赵玉峰,行艺时用家名“玉峰”,而不用艺名“福元”;天津西河名家田荫亭,行艺时用家名“荫亭”,而不用艺名“起微”。
以上种种,不能不令人怀疑:将师父赋予的那个名号称作“艺名”是否确切。换句话说,师父赋予的那个名号的原始功用或目的是否是供行艺时使用,是值得怀疑的。笔者认为,这个名号的原始功用也许不是为了行艺,应该只是参加某一组织后,依照组织规则赋予的一个组织内的代号,正如现在会给学生编定学号以便管理一样,这也许只是面对同一问题而产生的同一种处理方式。
综上可见,对拜师者而言,“拜师”实质上相当于向某一组织缴纳投名状,而师父则相当于介绍人与保人。拜师者通过“拜师”的形式获得组织接纳,使自己迅速与组织中其他成员形成较为松散的类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从而得以享受组织带来的福利。尽管依照组织规则,拜师者也须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很难衡量成本与收益孰轻孰重,但对走江湖讨生活的艺人而言,个人的力量毕竟渺小,有个组织可以依赖,总比单打独斗强得多——至少也能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对收徒者而言,收徒也好,传艺也罢,都算是一种投资,接受弟子的孝养,就是在收回投资得益。正如连阔如指出的:“作师父的算全始全终教成了个徒弟,自己亦有名有利”[1]49。所谓“名”者,有人愿意拜自己为师,本身就是对自己的肯定。若是徒弟能响大名,做师父的当然颜面有光。所谓“利”者,由于徒弟对师父有“生养死葬”之责,师父的花销、养老都有指望。
三、 从业资格的授与受
局外人很容易想当然地将“拜师”的第一义误认为“技艺的授受”,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拜师”的所有内蕴中没有“技艺授受”一项,而是强调这不是“拜师”的第一义。
“拜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赋予拜师者从业资格,技艺的授受反在其次。作此论断的根据是:书曲界强调“凡从业者必须有师父”,却从不曾要求“授受技艺必须拜师”;海青挣钱谋利会遭到业内人士的责难,但从未有业内人士责难外行学艺或艺传外行,反而多有内外行共同切磋技艺的美谈。可见,拜师是从业者入行必须履行的手续,却非授受技艺的必备条件。之所以必须履行这道手续,是因为拜师是获得从业资格的唯一途径。很多并无学艺诉求的人仍要拜师,目的就是取得从业资格。
今日,欲从事某行业,往往须首先取得从业资格;而从业资格的取得,必须通过由法律认证并赋予相关权利的机构的一定形式的测试。与此相似,旧时书曲艺人行艺,亦需获得从业资格。只不过,此从业资格是由艺人组织内部赋予并承认的,通过拜师便可自然取得,不需考试。这就是连阔如所谓的“经过这番手续之后,新入道的徒弟,在评书界算有其人了”[1]85的真正涵义。至于该人是否有能力从事本行业,则是另一码事了。
仔细分析起来,书曲行业的从业资格具有显著的排血缘传承和普适性。
所谓“排血缘传承”,是指拜师者所选的师父,必须是无血缘关系的外人——如果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看,这种要求是极为特别的。
传统上,中国人最重视血缘传承,即“父传子受”:父亲从事某行业,儿子就天然具有从事该行业的资格。如果皇帝也算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大到天下的授受,小到手艺的传承,莫不如是。但直至今日,北方书曲界都不承认这种血缘传承,他们的规则是:纵然某人的父祖数代都是行里人,只要他没有拜师,就不算行里人。马三立在《艺海飘萍录》中说:“那年头,卖艺的规矩很多,要想说相声挣碗饭吃,必须磕头拜师,同时必须加入班社,才算正式的相声艺人。不然的话,哪怕你一家子、几辈子都说相声,也不许你干”[11]。
这种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为何没有遵从被普遍奉行的“血缘传承”传统?艺人们对此也多不明所以,以致众说纷纭,尚无信说。由于资料阙如,任何一种看似有理的假说都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只好存疑。
今日,从业资格的有效范围是被明确并严格划定的。理论上讲,书曲艺人通过拜某一艺术门类的师父获得的从业资格,也只被允许从事该艺术门类的工作,而不许越界。但实际中,从业资格的有效范围却并没有被限制得如此死板,拜了此门的师父却从事别门艺术者并不鲜见。如孙桐枝的师父杨庆凯属东北评书门,孙桐枝却主要从事东北大鼓的表演;再如山东快书大家杨立德的师父是大鼓门的傅泰臣,傅泰臣长期以演说评书为主。
这种现象的成因有:一是该人已有技艺或另有获得技艺的渠道,没有投师学艺的需求,只是不欲挑战行规惯例,不得不拜个师父。因缘际会,拜到了其他门户的师父。既有师父,便算有了光明正大的从业资格,也就不再较真。如孙桐枝拜师前已能唱东北大鼓,但未曾拜师,不好名正言顺行艺,遂拜评书艺人杨庆凯为师。二是艺人的趋利性,即在某时某地见从事某艺获利更丰时,只要有此能力,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又不可能临时现拜一位此行的师父,在利益的诱惑下,也就顾不得行规了。
不论哪种情况,本质上都是由于一切行规的产生与执行都以艺人们最基本也最核心的诉求为最终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挣钱”:对绝大多数艺人而言,作艺的最大目的就是挣钱谋利。这就决定了艺人的趋利性,当规矩影响到利益时,艺人便会有意无意地变通或突破既有的行规,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业内人士见他既为同道,又有师父,就算在业内有了一定的人脉,若无较大利益冲突,谁愿撕破脸面较真?同时,同行不免有样学样,也可以享受这种变通与突破带来的好处。
四、 行规的破与立
关于拜师,书曲界还有“徒不二师”的行规,即理论上不允许艺人在同一门艺术上拜两个师父。而欲再拜其他艺术门类的艺人为师,则不在限制之中。但假如其师同时从事多种艺术门类,通常也不许徒弟再拜相应艺术门类的师父。这种行规对所有相关人员都有利:对师父而言,假如徒弟另投别师,岂不是说明本师很无能,师父颜面何存?对徒弟而言,由于他需对师父承担一定的义务,“转益多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给自己找了一堆需要负责的“爹”,成本太高。对其他艺人而言,若收已有师门之人为徒,则势必要开罪于该人先前的那个师父,艺人最讲究“和为贵”,所以他们通常不愿徒招此怨。另外,由于师徒之间具有类父子式的伦理关系,所以业界舆论多鄙夷转投别师的行为。故此,通常不会出现“一徒二师”的情况。
尽管“徒不二师”的行规被艺人们很好地坚持了下来,但也并非没有例外,比如连阔如就是先拜李杰恩为师,后又拜张诚斌为师[12]。这也算是对行规的一种突破。
既然行规是有弹性的、可变通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不论欲拜的师父是否健在,只要其徒愿意代师父收此人为徒,那么该人就算拜师成功,业内也须认可,行话谓之“代拉师弟”。如孙桐枝拜杨庆凯,即由杨之徒李桐年代拉师弟;马志明由侯宝林代拉拜朱阔泉。由此更进一步:如欲拜之师已故,经其家人或徒弟同意,拜师者给师父的坟或遗像磕了头,也算拜入师门。如西河名家王再堂就是通过拜坟认马三疯子为师的[13]。由此途径而拜入师门者,却又并非全是为了获得从业资格:有的是出于攀附盛名;有的是出于对师父艺术的崇拜;有的则是出于行辈的考虑。更大尺度突破行规的事例是,“海青”下海不但被业界承认,还自立了门户:
屠万顺……他没有拜师学艺,没有家门,同行的人欺负他,要携他的家伙,他在桌子底下放一把刀,准备打架。后来告到衙门,惊动宫廷。嘉庆四年,侯皇后传赐另立门户,屠万顺为外门头一代……拉老柯家开小青门(柯、屠一家),收徒为五亮。[2]320
此记述恐有夸大成分,但屠万顺以暴力手段简单粗暴地解决了问题,并自立门户的故事可能是真的。这反映出,对江湖艺人而言,权力与拳头,要比江湖规则现实得多。对此,连阔如曾记载:
生意人携家伙的事儿,在我国旧制时代之先,是常有的事,不算新鲜。一入民国时代,因而改变,这种事可就看不见了。如若再有人携家伙,没有门户的人喊来警察和他打官司,携不成人的家伙,反倒法院能判他个诈财的罪名。[1]46
可见,在面对现实时,被艺人强调的师承及从业资格,有时已经不再是艺人下海挣钱的必备条件了:没有师承的“海青”,同样可以下海挣钱,也可以被同行接纳。连阔如记载过这样一个实例:
不料在光绪年间,还真有一位海青腿儿。这说书的海青腿名叫范友德……范友德亦愿意拜个师父,只是评书界里没有人收他。不是他品行不好,是因为胡子都白啦,年岁太大了。收他为徒,那师傅得八十多岁,在那时候找不出八十多岁的老说书的。若有人收他做徒弟,晚辈人亦有五十多岁的,平空跑出个年岁相仿的师叔谁亦不干。后来评书界的人们因为他入门的事儿不大好办,大家商议好不用叫他入门啦,算是海青腿吧。[1]86
连阔如说:“可是江湖的老合,许有海青腿,可不准海青腿收徒弟。他既没有师父、没有门户,传了徒弟算哪门的人哪?谁花钱请客拜师父,亦是为有门户,好吃得开、出来做艺没有拦挡,谁给海青腿磕头啊!”但现实毕竟复杂得多,于是连阔如接着说道:“唯有范友德这个海青腿儿,他就收了个徒弟,名叫陈纪义,并且评书界人还承认了陈纪义算是评书界的人”[1]86。另据金受申先生说,旧时说“聊斋”的张智兰就是海青下海[14],他也收了徒弟,就是天津评书名宿陈士和。书曲界认为海青的徒弟不是海青,因为既称“徒弟”,必有师门。
五、 拜师与学艺
既谈“拜师”,就一定不能不谈“学艺”,尽管“拜师”与“学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很多人拜师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从业资格,而无学艺的诉求。那么,拜师而不学艺,其艺自何来?首先,较为普遍的情形是,旧时艺人多是世守其业,父母、亲故都是业内人士,技艺可以自给自足,拜师只是遵从习俗而已。其次,书曲艺术中的很多门类,其实并没有艺人对外宣传的那样难以掌握,不少有天赋者在拜师以前便颇有心得,不须在师父处空耗时日。连阔如说:
自从清末光、宣时代,说评书的收徒弟,多为“询局”(笔者按:曲艺行话,即观众)的下海。从前听书的人们,都是有闲阶级……总是八旗的子弟居多……若是记性好的人,听个几年评书,怎么也能听会了一套两套的。赶上时代改变,旗人的钱粮没有喽,受生计所迫,投个门户,拜个师父,下海就要挣钱养家。书是早就听会了,何必再虚耗一二年的光阴,再跟师父“听活儿”呀![1]47
于是,拜师,便仅仅成为获取从业资格的手段,而非学艺之起点。
旧时的学艺方式是:首先,现场观摩师父演出,即“听活儿”;听会后,由师父加以点拨,然后上场实践演出。所以,那些“听会了”便下海挣钱的人,其实只是缺了师父指点的环节。于是很多业内人士强调这一环节的重要性:许多技艺看似平常,其实内含奥妙,不由师父指点,单凭视听与模仿,很难得其精髓,是学不到真东西的。其实不仅是书曲艺术,任何行业都是如此,而且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此特点越明显。但具体到艺人,这种说法就似是而非了,因为上述说法强调的是师父的指点对掌握技艺精髓的重要性,但绝大多数艺人关注的却不是对艺术的掌握,而是挣钱。现实中,艺人的挣钱能力与其技艺水平并不成正相关,即艺术不成熟,甚至很低劣者偏能成大名、挣大钱的情形屡见不鲜;艺术水准很高却一生业绩惨淡的艺人,亦不乏其例。所以,对艺人而言,掌不掌握技艺精髓,并没有那么重要。
另一方面,艺术的很多奥妙之处,难以言传,学艺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天分,艺术大家尤其如此,而非有什么“秘籍”“秘方”;再加上旧时师徒双方的文化水平大都有限,纵然有什么幽微妙法,师父能不能通过“言传身教”赋予弟子,徒弟能不能接受并化于己身,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即便有师父的指点,也不能确保教学质量与效果。这正是许多艺术大家没能教出同样水准徒弟的原因。如果单靠“视听”就可以掌握基本技艺并能下海挣钱,则显然可知此人很有天分与灵性,所以即便他一时未能掌握技艺精髓,但随着揣摩与实践,未必不能有所会心——至少也不影响挣钱。所以连阔如说:“据江湖中的老前辈说,越是海青腿儿的人,越有能力”[1]85。
六、 结语
对旧时江湖艺人的行为与思想的理解,一定不可以蹈空与僵化,必须从江湖艺人的生存环境与最根本的诉求入手进行解读,方能得其真。对以卖艺谋生的江湖艺人而言,挣钱才是最紧要、最核心的诉求。业内的一切规矩,都要以这个诉求为最终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凡与此诉求相悖的行规,无不可以被变通或打破。同时,由于这些规矩只是业内的行规,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更不受法律的支持与保护,所以其约束力并没有艺人说得那么大。它只能对那些不愿生事、愿意遵从者有效;对不愿遵从者,则不过徒具仪文而已。
总之,规矩的破与立、守与废,并不取决于行业传统与艺人们的信念,而是取决于艺人要面对的现实成本与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艺人往往既维护与执行着既有的行规,又在不断地变通与打破着规矩。而那些变通与打破规矩的行为,又成为后来者踵武的成例与规矩。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旧社会江湖艺人的那一套规则也被画上了一个休止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书曲艺人的拜师活动又逐渐多了起来。然而,今日之拜师,不论是师徒双方的诉求,还是业内对此的认知,都与此前迥乎异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