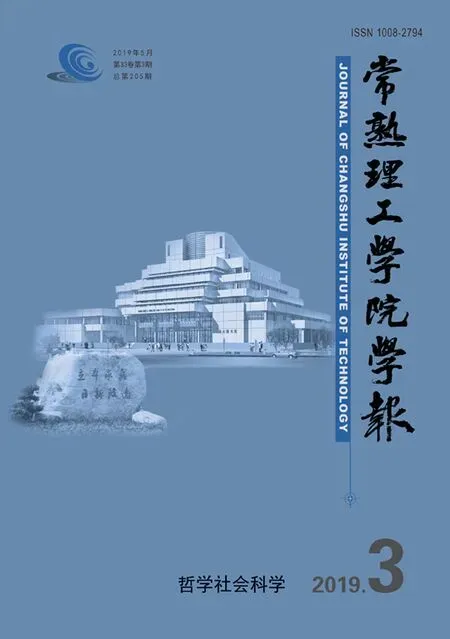相声中四种主要幽默技法的失谐理论分析
2019-03-21鲍震培
鲍震培,张 鹏
(1.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2.内蒙古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22)
一、 幽默的失谐理论
幽默是一种主观情绪体验,通常能够使人发笑或者产生愉悦感。探讨幽默产生原理的理论主要有三种:优势理论、释放理论、失谐理论。
优势理论由柏拉图最先提出,是最早尝试解释幽默和笑的理论。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该理论的原理是:使我们发笑的原因是对他人的比较和判断,这种判断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其他方面都强调自己的优越性,看到自己比别人具有优势而产生的愉悦感[1]。但优势理论所阐释的幽默多是不友善的,任何促进这种幽默的行为都是不适当的[2]。
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中解释了释放理论的原理[3]。他认为笑和幽默是对心理能量积累的反应,人们可通过倾向性笑话或与性有关的笑话对压力进行缓解,使其得到宣泄,进而让人产生愉悦感。
本文重点探讨的失谐理论,又称不一致理论或乖讹-消解理论。“乖讹”一词在汉语中的含义是差错、不协调、不正常。Mcghee也认为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是违背常规的,不协调的,则这种联系就是乖讹的[4]。这正体现出失谐理论解释幽默的要点所在,即人们根据背景信息做出的预期与实际结果存在不协调,这种不协调造成的认知失谐引起人心理上的幽默感受。哲学家最先从乖讹的角度研究幽默。康德提出“笑产生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成乌有”[5]。叔本华的幽默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可笑的事物引起了人们思维中的预期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人们才会感到好笑”[6]。可见,哲学观点认为失谐理论的关键在于“期待的落空”。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论》一书中提出,人们的常规思维是追求认知的协调,人们具有认知和谐一致的心理需要。一旦感觉到认知的不协调、不一致,人们就会有强烈的认知失谐感,并且会进行自我调适以达到新的认知平衡。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注重幽默的认知状态和对幽默的心理加工过程。Suls于1972年针对幽默心理加工的特点提出了乖讹-消解理论的双阶段模式(incongruity-resolution theory)[7]。该理论认为幽默是由两个阶段组成:期待与实际间的乖讹的探测阶段和乖讹的消解阶段。Attardo于1994年又提出了三阶段模式:铺垫-乖讹-消解模式(Setup-Incongruity-Resolution model)[8]。 现 代 心理学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揭示了该理论的认知神经机制[9-10]。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的有关研究显示,在乖讹的探测阶段和乖讹的消解阶段,幽默材料均会引起波幅更大的脑电波。
Warren和Mcgraw认为单靠“不协调”这一标准并不能区别幽默与非幽默[11]。的确,诸多文献中过多强调乖讹,却不注重能够产生幽默效果的乖讹的条件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以经典传统相声《大保镖》[12]片段为例分析幽默产生的失谐理论原理:
甲:刀、枪、剑、戟、斧、钺、钩、钗、鞭、锏、锤、抓、镗、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儿的,带尖儿的,带韧儿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儿的,带锁链的。我是样样——
乙:精通?
甲:稀松。
逗哏流利的贯口和捧哏的“精通”二字使观众产生了“样样精通”的心理预期,而实际信息却是“样样稀松”,这就产生了认知失谐,具有了幽默效果。但如果将与前文有关联的“稀松”换成与前文无关的“好吃”“模糊”等词汇,同样会产生认知上的不协调,但只能给人以不适的困惑感,而不是幽默感。因此,笔者给出了失谐理论更合理的描述:心理预期与实际信息之间存在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乖讹产生了幽默的认知体验,而后对认知失谐的消解过程产生了幽默的情绪体验。
失谐理论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广告等领域[13-16],也都体现出幽默是由于认知失谐而引起的这一理论特点。Morreall认为失谐理论是最具说服力的幽默理论[17]。虽然不是所有的幽默都能用失谐理论来解释,但符合失谐理论的幽默都是典型且容易被人接受的幽默。幽默的感受和识别需要一种不协调的感觉,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和认可[2]。
二、 相声主要幽默技法及失谐理论分析
相声是中国传统曲艺的瑰宝,是笑的艺术,更是中华语言文化的艺术。相声是以笑为武器来揭露矛盾,塑造人物,评价生活的[18]。相声通常充满幽默与滑稽,相声中“抖包袱”的过程就是通过语言将幽默传达给观众,使其产生认知失谐的过程。相声大师侯宝林认为幽默是因矛盾产生,是人的主观意识、想法和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在瞬间中的感觉。没有矛盾就没有笑话。侯宝林所说的“主观意识、想法和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本质就是人认知上的不协调。漫画家方成认为幽默是一种奇巧之术,能够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使人理解、使人发笑并且感受幽默[19];他还指出了幽默与滑稽的区别,认为幽默是充满智慧、使人感到意外的,而滑稽是有意而为,故意逗乐,略有做作,并且具有可重复性的。从失谐理论角度来讲,幽默的背景信息和实际结果存在差异,能够引起人的认知失谐;而滑稽多数并不引起认知失谐。相声的“包袱”是否能“响”,关键在于创造的“包袱”能否引起人们适当的认知失谐。汪景寿提出制造“包袱”的技法有语音和词汇的利用,方言土语的运用,古语、成语、歇后语等语言成分以及夸张的作用[20]。彭友明从认知语境的词汇、逻辑、百科知识信息方面分析了认知语境原型在相声创作中的运用,解释了相声“包袱”的认知语言学原理[21]。
笔者以失谐理论为依据,分析相声中创造“包袱”的七种幽默技法。这几种幽默技法并非各自独立,它们通常相互融合,一个“包袱”上可以体现多种技法。其中主要幽默技法包括语音、语义、逻辑、修辞四种(据此主要幽默技法创作出的“包袱”基本符合失谐理论,将在下面进行详细分析)。另外三种技法是语气语境、情节设计、滑稽与重复。语气和语境的运用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侯宝林介绍马季和姜昆时说:“这两位大家都熟悉吧?一个是我的徒弟(马季),一个是他的徒弟(姜昆),下面的话就由他们说去吧”,观众听后发出会心的笑。幽默语气的运用可以产生幽默的韵味。2001年在马三立从艺80周年晚会上,马三立见舞台周围摆放着花,说“这鲜花多香啊,这是真花。纸花咱不要,那是花圈。”在座观众闻言皆笑。若换个语境则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情节设计通常是带有剧情的作品的主干,通过情节展示矛盾巧合、组织“包袱”。在侯宝林的《夜行记》[22]中,有一个被该相声剧情中的主角撞到药铺里的老头儿,在看到该主角撞汽车后再次出现时说道“噢,你呀!又跑这儿玩命来啦?你打算把汽车也弄药铺里头去?”这样巧妙的情节设计能够给观众以更多的趣味。滑稽的语气和动作在现场表演中大量运用,效果甚好。重复可以使观众的心理期待得到满足,如马三立的《十点钟开始》中“从晚上十点钟开始”“同志,您说我行吗?”等经典台词的重复,使观众心中形成预期,所以,当台词再次出现时,观众会不约而同地随声附和。
(一)语音技法的失谐理论分析
语音类的幽默技法是将语音的变化运用在“包袱”中,通过语音变化使“包袱”的结果与观众的预期之间产生差异,引起认知失谐。该类技法包含谐音(同音)、象声、方言、音韵等,其中谐音和方言最为典型。
1.谐音
传统相声《歪批三国》片段:
乙:赵云卖什么呀?
甲:赵云卖黏糕嘛!
……
甲:《天水关》这出戏,姜维在校场一传令,那句【流水版】,就把赵云卖黏糕给唱出来啦。
……
甲:(唱)“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丧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卖)年(黏)高(糕)。”他老卖黏糕!
该“包袱”中“老卖黏糕”与“老迈年高”谐音,前文的信息使观众产生赵云卖黏糕的心理预期,而唱词中的“老迈年高”指的是赵云年事已高。通过谐音的使用将年事已高解释成经常卖黏糕,给人造成认知失谐,产生幽默的效果。
2.方言
通常相声的表演使用普通话,偶有使用方言的。相声术语中“怯口”或“倒口”指的就是方言的使用。相声《找堂会》中逗哏使用方言,给人以认知上的差异,形成饶有趣味的诙谐幽默感。相声《钓鱼》中使用天津方言,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钓鱼》中多处用到“哏儿”一词,类似的这些天津方言中特有的方言词汇和发音与人们常规认知不一致,使人产生认知失谐的幽默感觉。
(二)语义技法的失谐理论分析
语义类技法是通过语义的变化,如词义歪讲、一词多义、反义等手段来制造包袱,语义的变化可以带来认知失谐,从而产生幽默效果。
1.词义歪讲
相声《讲帝号》是词义歪讲的典型作品,对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十个皇帝的年号均用词义歪讲的手法来制造“包袱”,其片段如下:
乙:“乾隆”哪?
甲:“乾隆”那还不好讲吗?乾隆吗?皇上不是有钱吗?
乙:那“隆”哪?
甲:大概他是聋子。
乙:这是有钱的聋子。
“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寓意“天道昌隆”;而在该“包袱”中解释成“钱聋”——有钱的聋子。这一解释偏离了人们的常规思维,引起认知失谐,给人以幽默的感觉。
2.一词多义
相声《白事会》中用一系列的词汇描述捧哏的父亲去世了,如“归西”“下世”“入土”等。其中用到“没了”一词:
乙:他呀,没啦。
甲:找找!
乙:找?
甲:那么大东西没了就没啦?
乙:东西?
甲:找找。
“没了”一词既有人去世了之意,又有东西丢了之意。此处本是指捧哏父亲去世;而逗哏理解成了捧哏他爸爸丢了,需要找一找。观众知道此处“没了”的本意,却意外听到“丢了,找找”的意思,由此形成认知上的失谐,体验到了其中的幽默。
(三)逻辑技法的失谐理论分析
逻辑是事物或人的思维的常规规律。不论逻辑是否合乎情理,违反常规的逻辑必然给人以认知上的冲突。这种认知冲突如果符合“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则可以产生幽默效果。
1.合理逻辑
相声《夜行记》片段:
甲: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
甲:买旧的。
乙:那能骑吗?
甲:啊,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乙:骑得过儿
甲: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乙:好嘛,这车要散啦![22]49
前文给出的铺垫是“花钱不多,车还可以”,结果是都快散架了。“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具有现实可能性,合乎情理,是一个合理的反常逻辑;但这个合理逻辑却是意料之外的,给人以认知失谐和幽默感。
2.不合理逻辑
相声《醉酒》片段:
甲:拿出一个手电筒来,往桌上一放,一按电门,不是出现一个光柱吗?
乙:是呀。
甲:你听这话醉了没有?“你说你没醉。来,你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乙:啊?
甲:那能爬上去吗?
乙:是醉了。
甲:那个还不含糊呢。“这算了什么,你别来这套,我懂,我爬上去呀?我爬到半道儿,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呀?!”[22]136
该片段情节中有两个醉酒者,其中一人拿出手电,让另一人爬手电光柱,此处为第一个不合理逻辑;另一人还十分“机智”,担心自己爬上光柱,对方关电门使光柱消失,自己会掉下来,此处为第二个不合理逻辑。两处逻辑错误均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属于不合理的反常逻辑。这样“三翻四抖”的铺陈,将不合理逻辑逐步推进,使得认知失谐程度增大,当然,引起的幽默体验也就越强烈。
(四)修辞技法的失谐理论分析
修辞手法在相声的创作中广泛运用。如《对春联》等“子母哏”的相声作品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充分体现。常用的修辞手法还有比拟(拟人或拟物)、比喻、夸张、排比、设问、双关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能够提升相声的文学韵味,使其更具文学性、艺术性、欣赏性。下面将对夸张和比喻这两个最符合失谐理论的修辞技法进行举例分析。
1.夸张
夸张的修辞手法在相声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泛的应用。相声《卖布头》①选自《侯宝林相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23-424页。至于“亚赛过”一词,可能是根据表演时唱段里的内容直接音译过来的,或者是方言的用语习惯。片段:
甲:“它怎么那么白呀,它气死头场雪,不让二场霜,亚赛过复兴的洋白面哩吧。……”
……
甲:“怎么那么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亚赛过唐朝的黑敬德哩吧,在东山送过炭,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了,它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外号叫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不怕洗,它不怕淋,它不怕晒呀,任凭你怎么洗,它不掉色呀!”
该片段描述卖布头的商贩夸大自己所售布匹的颜色,白布的白色堪比雪和霜,赛过洋白面。黑布的黑色胜过历史上三位肤色黝黑的名将:张飞,李逵,尉迟恭;它比煤炭都黑,并且怎么洗也不掉色。此处夸张的运用使得人们的认知失谐变得具体可感,达到良好的幽默效果。
2.比喻
传统相声《八扇屏》片段:
甲: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乙:比什么呀?
甲:你好比面茶锅里煮皮球。
乙:此话怎讲?
甲:我说你混蛋,你还有肚子气!
……
甲:好比面茶锅里煮灯泡,我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火儿。
……
甲:你好比面茶锅里煮茄子,简直混蛋大紫包。
……
甲:面茶锅里煮铁球,混蛋到底带砸锅。
《八扇屏》中这一系列比喻的“包袱”已经在相声的改革与净化中被摒弃或改进,但这并不影响“包袱”自身具有的幽默效果。当观众听到“你也好有一比”的时候心里开始有预期,而后风趣的比喻及解释让人意想不到,构成认知失谐,产生幽默。
三、 失谐理论对相声创作的启示
失谐理论能够解释大多数幽默的产生原理,是具有较强普适性的幽默理论。失谐理论为相声制造“包袱”提供了心理学上的理论依据,相声的创作者可以据此进行创作。(1)认知失谐的程度决定了“包袱”的幽默效果。如前文所述,“包袱”给人带来的认知失谐要在适当的程度内才能够具有良好的幽默效果。若认知失谐的程度过大,则会给人以思维过于跳跃的困惑和不解;若认知失谐程度过小,则人们不会感觉到强烈的幽默感,“包袱”就不够“响”。“包袱”的创造要把握好认知失谐的适当程度,而这个适当程度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2)认知失谐所在情境、认知失谐的内容决定了“包袱”的时效性和普适性。“包袱”的时效性是一个作品生命力的关键。相声《牙粉袋》讽刺了日伪时期,日伪政府实行“治安强化运动”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四块大洋才能够买到一袋牙粉袋大小的洋白面[23]。使用牙粉袋作为“底包袱”,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具有良好的效果,而在现在牙粉早已被牙膏替代,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牙粉袋是何物,其给年轻人造成的认知失谐过大,因而这个“包袱”失去了原有的幽默“功力”。“包袱”的普适性同样如此。相声在京津起源发展,其中很多“包袱”具有当地特色,如方言词汇或者地理名词等。这些“包袱”在其他地方演出,当地观众的认知范围内若没有相应经验,就不会产生幽默效果。面对不同的观众群体也要注意“包袱”的内容,不仅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更应该因观众制宜,即“入乡问俗,把点开活”。《吃元宵》中“十字头上添一撇儿,我吃一千”这类的“包袱”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所以这个作品不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任何观众都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总之,相声的创作中既要制造出符合时代特点,适宜具体情境,顺应观众需求的“包袱”;又要有普适性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袱”,这样的作品才能够历久弥新、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