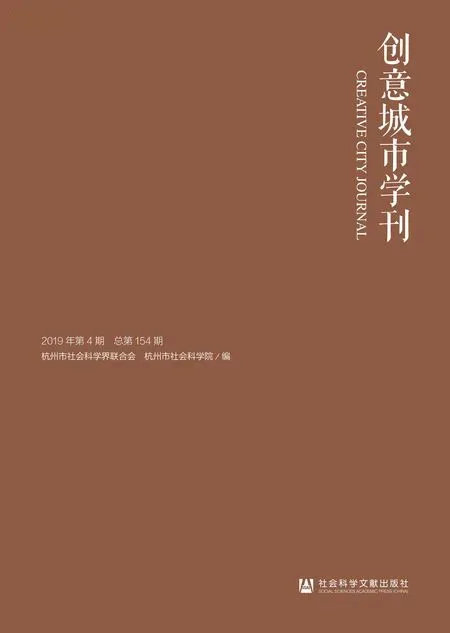在引进与创新之间*
——竺可桢的治校之道探讨
2019-03-20卢美艳
卢美艳
提 要: 竺可桢1936 年临危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经过短短13 年, 使一所地方院校一跃成为国内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这固然离不开浙江大学师生员工的群策群力, 但作为校长的竺可桢厥功至伟。 竺可桢曾留洋于美国哈佛大学, 并深受艾略特与洛厄尔两位校长的影响。 他掌浙大后积极引进哈佛大学的先进大学理念, 并根据本土实践加以改革和创新, 塑造了以“求是” 精神为核心的独具一格的大学文化, 从而促成浙江大学迅速崛起。
竺可桢(1890 ~1974) 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与教育家。 他1890 年出生于浙江绍兴, 1910 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 1913 年考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其时哈佛大学的校长为阿尔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 1856 ~1943)。
查尔斯·W·艾略特(Charles W. Eliot, 1834 ~1926) 校长是洛厄尔校长的前任, 1869 年开始执掌哈佛大学。 在任期的四十年内, 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推行选课制、 广罗优秀师资等举措, 帮助哈佛大学完成从学院制向现代大学的转型, 并使哈佛大学从“偏安一隅的传统学院发展成为世界顶尖大学”[1]。 艾略特不仅是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也是哈佛大学最伟大的校长之一。 洛厄尔1909 年接任哈佛大学校长, 他通过完善选课制、 推行导师制等措施, 使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教学质量进一步获得提升, 并成功把哈佛打造成一个教师热爱教学、 学生追求卓越、 学习热情高涨的高等学府[2]。
竺可桢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 哈佛大学艾略特和洛厄尔两位校长对他的影响颇深。 前者主要是大学的功能、 大学的培养目标等大学理念和教师选聘制度举措[3],后者主要是“博雅” “精专” 并重的课程体系设置和导师制方面[4]。 艾略特虽然已于1909 年退休, 但家尚住在剑桥, “时时出来演讲”[5], 竺可桢对他的大学理念可谓是耳濡目染。 竺可桢1936 年临危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 根据中国的实际, 以哈佛大学为“标准” 与“偶像”, 对艾略特的大学教育理念进行吸收和改造; 对洛厄尔的导师制等举措进行积极引进和改良, 并着力培养学生学会自我教育和追求卓越, 从而使浙江大学即便处在不断西迁、 颠沛流离的困境, 依然异军突起, 一跃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6]。 对于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与洛厄尔的大学理念,竺可桢如何洋为中用、 推陈出新? 他的这些举措对于当今“双一流” 的建设又有何启迪?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 “教育不是灌输头脑而是点燃心火”。 而要点燃心火, 培育具有共同核心追求的大学文化至关重要。 竺可桢根据大学的使命和中国的具体实际, 确立“领袖人才” 为大学培养目标, 塑造以“求是” 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 这些举措对我国当前一流大学的建设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大学使命与“求是” 精神培育
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 它是“时代的表现, 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7]。 正因如此, 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 承担着连接历史与未来、 把握当下、 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作用。 作为其头号舵手的大学校长如何勾勒蓝图、 清晰定位大学的功能与培养目标, 往往对其所掌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1. “蕲求真理、 培养领袖人才” 的大学使命
关于大学的使命, 竺可桢主要从大学功能与大学的培养目标两方面进行过阐述。首先, 关于大学功能, 竺可桢认为, 大学应该是“承先启后, 以精研学术, 而且不忘致用试行为国效劳”[8]; 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 除了“精研学术、 蕲求真理”的大学首要使命, 与艾略特校长一样, 竺可桢也很看重大学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服务功能[9]。
竺可桢指出, 毕业生的培养应重视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今后大学应该和中央各部院、 省政府、 市政府通力合作, 以免闭门造车之弊”[10]。 不仅如此, 竺可桢还根据中国当时饱受战争威胁的实际, 提出“大学是社会之光, 不应随波逐流”, 大学亦是“海上之灯塔, 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因此他认为, 大学应承担弘扬道德、 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11]。 事实上, 浙大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在竺可桢的领导下, 浙大每到一地, 都为当地的文化、 教育、 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其影响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清晰可见。”[12]
其次, 关于大学的培养目标, 竺可桢认同艾略特校长的大学应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的国家领袖人才的理念[13]。 他认为, “培育良好公民, 作中流砥柱, 社会领袖”是大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竺可桢掌校的20 世纪30 年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大学教育越来越转向“注重实用科学”。 但他认为, “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 理应并重”[14]。 大学教育的目标, 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 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 能担当大任, 主持风会, 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为了切实落实“领袖人才” 的培养目标, 竺可桢1936 年与浙大师生第一次见面时, 就对同学们提出了具体要求, 希望他们加强学业、 道德、 体格各方面的修养,特别是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 除了学业方面须注意学习方法和研究能力、 反省精神的习得之外, 竺可桢同时强调, 德育、 体育和美育也不可偏废。 德育方面, 竺可桢倡导“训教合一”, 教师以身作则来对学生的品行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 体育方面, 则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予毕业, 还特意聘请了著名的舒鸿老师, 自己也每日体育锻炼, 以身示范。 1940 年西迁遵义时, 虽然经费紧张, 但浙大还特意为学生修建了400 米跑道的大运动场[15]。 美育方面, 竺可桢聘请了著名画家丰子恺教授为学生开设艺术欣赏课, 聘请了声乐家沈思岩教授开设音乐欣赏课等, 让浙大学子即使身处困境, 也能时刻享受艺术的熏陶。
2. “只顾是非, 不计利害” 的“求是” 精神
清晰的大学功能定位与明确的大学培养目标就像启明星, 代表了一所大学的发展愿景。 而要实现这个愿景, 则需要精神内核的指引、 行为文化的熏陶和切实制度的保障, 其中第一项尤为关键。
1936 年, 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日益迫近, 在这时局动荡的关头, 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深受其扰。 为了躲避战乱, 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 历经艰难困苦, 一次次西迁, 尽最大可能保持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在这过程中, 他成功营造了以“求是” 精神为核心的浙大文化。 竺可桢1938 年提出以“求是” 为浙大校训, 通过一次次演讲, 他从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 的传统与哈佛大学校训“faith of truth” 的不约而同出发, 帮助学生明了所谓“求是” 即“只顾是非, 不计利害”;而求是的路径在于“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竺可桢求学时, 或许受到艾略特校长不计名利的科学精神[16](scientific spirit)的启发, 不过, 作为一名科学家, 他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 中国应先“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17], 即“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 的“科学精神”。
为了能让年轻的浙大学子养成“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 的科学精神, 竺可桢通过一次次校园演讲, 旁征博引, 谈古论今, 循循善诱。 从领袖人才必须具有“明辨是非、 静观得失、 缜密思虑、 不肯盲从” 的习惯, 到历史传承, 即一脉相传的浙大的传统—— “肯牺牲肯吃苦” 的风气与“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8]; 从殷殷期望毕业生能“但知是非、 不计利害”, 并负起责任, 慎思明辨, “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 而在于努力去干”[19], 到明确浙大的校训——求是精神, 强调“只顾是非、 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大毕业生应具有的”[20]责任。 这些演讲如春风化雨一般, 让“求是” 精神悄然浸润到浙大师生的心田。
不仅如此, 竺可桢还把培养目标与“求是” 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整合。 他指出,领袖者, 因其能知众人所未知, 为众人所不敢为。 因此, 作为“未来的领袖人才”,必须具有清醒而理智的头脑, 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 深思远虑、 不肯盲从的习惯。 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 有吃苦耐劳、 牺牲自己、 努力为公的精神, 从而能“培植真正之学问技术, 将来贡献国家”[21], 无负国家作育与社会期望, 把拯救中华民族、 拯救我们的祖国作为共同使命。
由此可见, 竺可桢提出“求是” 精神, 不光是吸收了艾略特“scientific spirit”的理念和求是高等学堂的浙大传统, 也是他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和当时所处环境的进一步创新。 20 世纪30 年代末40 年代初的中国, 由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为了保全自己, 一部分国人失去民族气节, 只顾利害, 不顾是非。 竺可桢提出“求是” 精神, 正是针对此种现象有感而发。 因为只有发扬“求是” 精神, 才能把浙大学子培养成“公忠坚毅, 能担当大任, 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22], 才能扭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随着竺可桢和众多师生的努力, 即使在战乱频繁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浙大的“求是” 精神也早已是春风化雨, 日夜践行。 这一点, 浙大的学子最有体会。 在回忆浙大龙泉分校时, 学生写道, 课堂上, 对同学提出的疑难问题, 有的老师除了当场解答外, 有时还会补充说: “很抱歉, 现在我只能作这样简单的回答, 不能使你满意, 课后我查一下有关书籍资料, 下次再给你作解答。” 对于学生的实验报告,要求也非常严格。 老师看得非常仔细, 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写错了也不会放过; 若是有较大的错误, 就必须重做实验[23]。
二 导师制与行为文化营造
大学中良好的人际关系, 特别是融洽的师生关系, 集中体现了大学的行为文化。在这一点上, 竺可桢大力推行的导师制功不可没。
1936 年, 竺可桢刚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 对当时“教而不训” 的教学状况十分不满。 他指出, 哈佛大学要求导师“有指导学生行为之任务”[24]的做法十分值得浙江大学借鉴, 认为“行导师制更易见效”[25]。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读书时, 曾受惠于导师制, 因此他对母校的导师制推崇有加。哈佛大学的导师制主要在洛厄尔校长时期得到完善与推广, 它是对选课制的一种重要补充, 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不过, 根据中国当时“教而不训” 的实际, 竺可桢对洛厄尔的导师制进行了改良。 他推行的导师制不仅仅在于课程和学习指导, 甚至也不在于单纯的改善师生关系,而是在于, “本训教合一之精神, 提高学术兴趣, 辅导课外活动, 以培养高尚道德”[26]。
1937 年, 在临安西天目山, 浙江大学开始试行酝酿许久的导师制。 同年10 月,浙大抵建德后也实行导师制, 并对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 随着浙大的一再西迁, 竺可桢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导师制加以改革与完善, 直到1946 年, 浙江大学奉教育部令, 停止导师制[27]。
洛厄尔校长认为, 理想的教育是达成学生“门门博通、 某门精通” 的目标。 对此, 竺可桢深表认同。 他指出, 浙大培养的学生应是“各方平均发展, 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 又能各具专长, 俾成全才”[28]。 为实现这样的办学理想, 竺可桢对原来的学分制进行了改革, 并参照哈佛大学在实施学分制中的做法, 提倡通过严格的考试来促进学生追求学术荣誉, 通过课程的分组及必修方法保证学生学习知识的系统性。 他要求学生选课时, 在人文学科中及自然学科中, 以各选至少9 学分为原则;主系学分至少40 学分, 辅系学分至少24 学分。 因个别需要, 辅系科目, 可不限于一系, 但须各有关联, 经系主任与院长之认可[29]。 这些规定, 可以有效避免学生选课时的盲目性与取巧性, 保证了学生学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从而保证学生的“专精” 与“博通”。
导师制促成了浙江大学即使身处困境, 学生依然刻苦求学的良好学风。 同时,这一时期的师生关系极其融洽, 有时像是亲人一般。 当然, 无论是导师制的成效,还是学风的养成, 都离不开优秀的师资。 竺可桢认为, “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 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 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 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30]。 以数学系为例, 当时浙大高年级数学系的学生须选定研究方向, 并和全体教师一起轮流报告论文。 苏步青教授和陈建功教授要求非常严厉, 如果报告不令人满意,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 都会被当众批评甚至训斥。 所以,每次报告, 无论师生都会精心准备, 也因此愈加受益匪浅。 两位教授既有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面, 更有对学生的学业倍加呵护、 精心培育的一面。 如他们对于学生的投稿论文不仅一一审阅, 而且逐篇批改。 正因如此, 当时的数学系后来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浙大学派”[31]。
师生融洽、 教授云集的浙江大学, 很快成为考生争相报考的高等学府。 1946 年浙江大学招生时, “预计此次以浙大为第一志愿者当有5000 人, 而所取名额不过400 人, 则是12 人中取1 人而已”[32]。
三 完备有效的大学制度保障
浙江大学西迁时期, 条件非常艰苦。 竺可桢与其团队通过建立一套完备而有效的大学制度, 从教师聘用、 学生培养、 学术风气各方面保证了一切活动井然有序地展开。 因此即使屡次被迫西迁, 浙江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也从未中断, 有效地保障了学生的求学和成材。
1. 保证优秀教授人选的师资聘用制度
竺可桢上任伊始, 就一再强调教授的重要性。 竺可桢认同艾略特校长“教师是办学第一要素” 的观点, 他提出,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 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 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 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竺可桢明确表示: “决将竭诚尽力, 豁然大公, 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 以充实本校的教授。”[33]
为了保证有优良的师资, 竺可桢上任之前就开始谋划教授人选, 并作为条件之一向政府部门郑重提出: “校长有用人全权, 不受政党之干涉。”[34]竺可桢为了浙江大学拥有更好的师资, 四处搜罗专家学者。 苏步青教授说: “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 只要有好教师, 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 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 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35]如为聘请国学大师马一浮, 竺可桢曾三顾茅庐, 却无功而返。 马一浮后来主动表示愿意来校时, 竺可桢不计前嫌, 立即派专人将其迎至校中。 竺可桢不仅四处聘请人才, 对已有人才也是呵护备至。 如1940 年初浙大刚到遵义, 竺可桢便马上安排苏步青回去接家眷, 并由学校提供全部经费。“这样的校长, 他把教授真当作宝贝, 我们当教授的怎能不受感动啊!”[36]
竺可桢聘请教师的标准是: “只要学问精湛, 热衷于教育事业, 皆兼容并蓄,不拘一格。”[37]为了壮大浙大的师资队伍, 他把知名学者胡刚复、 王琎、 孟宪承、 梅光迪、 蔡堡等教授从别处辛苦请来; 积极回聘因不满前任校长郭任远独断专横作风而愤然辞职的蔡邦华、 吴耕民、 梁希、 张绍忠、 何增禄、 束星北等教授。 他非常重视对年轻教师的任用, 认为“要发展一个大学, 最重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38]。如任美锷、 谈家桢和卢鹤绂教授受聘时, 分别只有27 岁、 28 岁和31 岁。 另外, 本校的优秀毕业生也积极留用, 如程开甲、 朱祖祥、 姚鑫、 陈述彭、 胡济民、 谷超豪等。 竺可桢对于“校中用人, 素不管党派如何”[39]。 当时, 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一般很难为国立大学录用, 但竺可桢唯才是举, 聘请了燕京大学毕业的谈家桢、 谭其骧和沪江大学的涂长望等人。 竺可桢海纳百川、 招贤纳士在教育界有口皆碑, 当时社会上曾流行一句话: “为竺可桢而来。”
2. “教授治校” 制度
关于治校的核心理念, 竺可桢充分吸收本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精华, 既本土化又国际化; 既教授治校又保持学府与政府的平衡, 以保证充足的治校经费。
竺可桢主张校务公开和教授治校。 浙大最高权力机构为校务会议, 由校长、 各院长、 总务长、 训导长以及大多数教授代表组成[40], 教授代表每年通过民主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各种专门委员会由教授担任负责人, 分任经费预算、 章则修订、 图书设备、 招生、 训育、 福利等各种具体事务。 竺可桢经常通过开座谈会、 个别交谈等形式听取教师的意见, 以改进工作[41]。 王琎曾回忆说, 浙大的教授不仅担任领导职务, 而且在新生录取工作、 教授的聘任和提拔、 学术课题的选择和评估、 研究经费的申报等具体事务中, 都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42]。
3. 一年级基础课的教授上课制度和本科生参与科研制度
竺可桢作为一名科学家, 深知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1927 年他就指出, 要“取消学术上的不平等”, 科学“是追寻真理的唯一途径”[43]。 为了和世界列国相抗衡,不能不脚踏实地地去研究。 他认为, 作为重要学术机构的大学, 自然须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同时, 竺可桢认为, 蕲求真理这项大学的重要使命, 也要求师生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达成蕲求真理的目标, 要求学生须具备扎实的基本功。 因此, 竺可桢非常重视一年级的基础课教学。 西迁遵义期间, 在湄潭永兴专门设立浙大一年级分部,特意为此聘请了不少博学笃行的名教授前来担任基础课的教学工作, “如朱福炘的‘普通物理’, 钱宝琮先生的‘数学’, 储润科先生的‘化学’”[44], 再如孟宪承教授的“教育概论” 和蔡堡教授的“普通生物” 等。 当时浙大一年级的基础课教师, 可谓是群星璀璨, 教授云集。
浙江大学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基本功, 对高年级学生更提出了较高的学术要求。 当时的浙江大学科研风气浓厚, “陋屋之下, 浙大师生专心‘精研学术’” 的画面随处可见。 如数学系就要求学生读完三年级就要选定一个研究方向, 并和全体教师一起轮流报告论文; 学生也经常向国外投稿论文, 1940 年毕业的白正国就曾在国外发表数篇数学论文[45]。 学生勤学苦读, 教师也不例外, 即使已是功成名就的大教授也相互学习问答, 孜孜不倦。 “如束星北教授讲授‘相对论’, 听课的一般是研究生、 讲师、 助教, 但荣获日本国家博士的苏步青教授也坐在最前面听课”[46], 并且笔记记得密密麻麻。 “教师们从系主任起, 除了上课外, 其余的时间都在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 学术空气十分浓厚。”[47]正是这些身处困境, 却心无旁骛, 一心向学向教的浙大师生, 使“求是” 之风愈加兴盛。
四 结语
竺可桢掌浙大之后, 对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与洛厄尔的大学理念积极加以引进,并根据本土实践进行改良; 通过以“求是” 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的营造, 促成了浙江大学浓厚的勤学苦读之风。 1944 年, 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参观浙大后, 对浙江大学评价甚高, 称“浙江大学是与昆明的著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齐名的学术机构, 可能在中国的大学中排名最高”[48]。
竺可桢在浙大13 年, 学校从文理工三院, 发展到七院[49], 共计培养3000 多名高级人才。 他们有的是科技界的精英, 有的担任高等院校管理者等[50], 真正成为社会各界的领袖。 以农学院为例, 1940 ~1946 年在湘潭毕业的学生, 有本科生418人、 研究生13 人。 他们中有的成了专家、 教授, 有的担任了大学校长, 有的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他们基础扎实、 知识面广, 能吃苦耐劳, 做事勤恳负责, 一丝不苟,在社会上很有声誉[51]。 “1945 年, 英美奖学金留学生共录取176 名, 其中浙江大学获奖者19 名, 比例不可谓不高。 这足以证明当时浙江大学的教学水平及抗日战争时期教学不辍的优秀智力和‘求是’ 精神。”[52]
竺可桢治校时, 没有却步于学校当时经费不足、 校址一迁再迁的发展困境, 他以远大的目光和宏阔的胸襟, 大力打造大学的精神内核——以“求是” 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 其关键内容为: 大学应时刻不忘蕲求真理的使命, 教研并重以达成知识传承的使命, 同时注重社会影响与社会服务的间接功能; 大学的培养目标应结合时代背景和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 师资选聘, 须才华与品格兼备, 无门户之分, 兼容并蓄; 严格大学的入学标准; 推行导师制来保证“训教合一”; 改革学分制和选用教研俱佳的教授担任基础课教学, 以保证学生文理兼修, 力求“专精与博通”等。 这些高瞻远瞩、 独具匠心的举措, 使当时的浙江大学迅速崛起, 名扬国内外。对于当今高等教育的“双一流” 建设, 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美〕 亨利·詹姆斯: 《查尔斯·W·艾略特传——他缔造了哈佛》, 朱建讯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第1 页。
[2] Morison S. E. ,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 - 1936), The Bele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3] 刘正伟、 卢美艳: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大学理念的接受与改造》, 《高等教育研究》 2018年第9 期。
[4] 刘正伟、 卢美艳: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导师制的引进及实践》,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6 期。
[5] 《竺可桢全集》 (第4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89 页。
[6] Needham J. , “Science in Kweichow and Kuangsi,” Nature, 1945, 156 (496).
[7] 〔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 徐辉、 陈晓菲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第1 页。
[8]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333 页。
[9] 刘正伟、 卢美艳: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大学理念的接受与改造》, 《高等教育研究》 2018年第9 期。
[10]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352 页。
[11] 《竺可桢日记》 (第2 册), 人民出版社, 1984, 第838 ~840 页。
[12]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14 页。
[13] 刘正伟、 卢美艳: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大学理念的接受与改造》, 《高等教育研究》 2018年第9 期。
[14]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640 页。
[15] 姚庭华: 《竺可桢体育思想研究》,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第245 页。
[16] 刘正伟、 卢美艳: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大学理念的接受与改造》, 《高等教育研究》 2018年第9 期。
[17] 竺可桢: 《厉害与是非》, 《科学》 第19 卷第11 期, 1935 年。
[18]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371 页。
[19] 《竺可桢日记》 (第1 册), 人民出版社, 1984, 第120 页。
[20] 《竺可桢全集》 (第9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第444 页。
[21]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451 页。
[22]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455 页。
[23] 许高渝: 《从求是书院到新浙大——记述和回忆》,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7, 第114 ~115 页。
[24] 《竺可桢全集》 (第6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 第67 页。
[25] 竺可桢: 《竺校长答词》,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第250 期, 1936 年。
[26] 《训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第27 期, 1936 年。
[27] 刘正伟、 卢美艳: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导师制的引进及实践》,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6 期。
[28] 《国立浙江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记录》,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第250 期, 1936 年。
[29] 《第三次校务会议记录》,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第254 期, 1936 年。
[30]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334 页。
[31] 许高渝: 《从求是书院到新浙大——记述和回忆》,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7, 第98 页。
[32] 《竺可桢日记》 (第1 册), 人民出版社, 1984, 第960 页。
[33]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335 页。
[34] 张彬: 《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第48 页。
[35] 苏步青: 《怀念竺可桢先生》,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第302 页。
[36] 苏步青: 《与竺可桢校长共事13 年》, 《一代宗师竺可桢》,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第4 ~5 页。
[37] 张彬: 《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第53 ~57 页。
[38] 《竺可桢日记》 (第2 册), 人民出版社, 1984, 第1120 页。
[39] 《竺可桢日记》 (第2 册), 人民出版社, 1984, 第1045 页。
[40] 竺可桢: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 第67 期, 1948 年。
[41] 张彬: 《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第247 ~248 页。
[42] 王琎: 《竺可桢师资队伍建设的思想》, 《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思想研讨会” 论文选集》,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第87 ~89 页。
[43] 《竺可桢全集》 (第1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571 页。
[44] 钱永红: 《求是忆念录: 浙江大学百廿校庆老校友文选》,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第124 页。
[45] 许高渝: 《从求是书院到新浙大——记述和回忆》,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7, 第99 页。
[46] 钱永红: 《求是忆念录: 浙江大学百廿校庆老校友文选》,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第138 页。
[47] 许高渝: 《从求是书院到新浙大——记述和回忆》,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7, 第102 页。
[48] 李约瑟、 李大斐: 《中国科学(摄影集)》, 1945 年。 中译稿参见《李约瑟游记》,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第346 页。
[49] 《竺可桢全集》 (第2 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第689 页。
[50] 张彬: 《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第303 ~326 页。
[51] 许高渝: 《从求是书院到新浙大——记述和回忆》,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7, 第104 页。
[52] 钱永红: 《求是忆念录: 浙江大学百廿校庆老校友文选》,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第1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