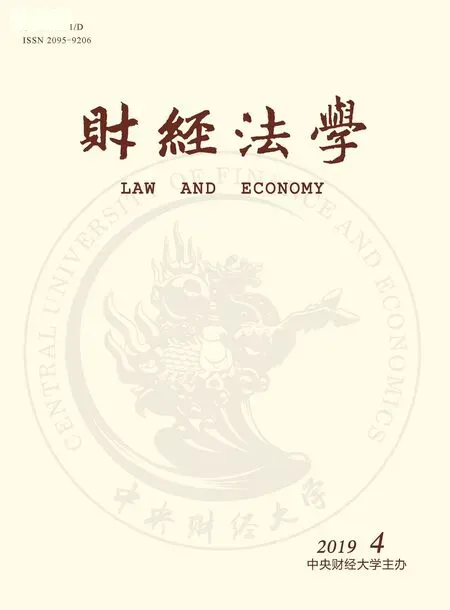产业发展与立法典范的变迁
——从“裁判立法”到“赋能立法”
2019-03-20廖义铭
廖义铭
内容提要:产业发展的动能取决于民众的信心,而民众的信心,则由市场上各种被交易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与价格的相符与否所决定。法律对于市场上价值取向的确定、交易安全的保障及行为人相互调适能力的提升,有关键的影响力。然而,在产业发展的不同情势中,不同的立法典范,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归纳当前立法,大概可总结为两种不同的典范:一是以裁判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为核心的“裁判立法”;二是以赋予当事人遵守法规范的精神为目标的“赋能立法”。在产业处于亟需发展、加值或转型的地区或社会,仅着重于争议发生后公正的裁判或课责的“裁判立法”,较无助于该地区民众对产业之信心的建立或提升。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设计以及法律人功能的发挥,来使人们更愿意自主地进行自我调适与学习,提升自己的生产或服务于市场上的价值,从而建立或提升民众的信心。
一、引 言
产业发展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于任何时代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产业发展一旦停滞,经济活动即逐渐萎缩;而经济活动一旦日益萎缩,人民的基本生存所需便会遭受威胁;而人民的基本生存所需一旦不足,便会产生人口流失或社会动乱,而这乃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也不应接受的悲剧。然而,纵观史册,一个社会的产业能够持续发展并非必然,其必有相应主客观条件的支持,我们曾见在缺乏这些条件时人类历史上许多族群的灭绝、文明的崩坏,令后人无限唏嘘。当然,我们更曾见人类历史上某些地区上的某族群,在某个时代中创造了产业发展上的重要成就,使其族群本身享有比其他族群更优越的生存条件,也为其他族群的生存发展带来可资学习模仿的典范。
“法与发展”乃是法学上一种特殊学问。对于法律与社会或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尚未以自己的经验与所累积的学术能力对全世界法学界做出必要的贡献。[注]参见张英磊:《发展经济学思潮与法制变迁:以台湾公营事业相关法制之变革为例》,载《财经法暨经济法》2010年第23期。关于法律与发展之研究发展概况另参见程骞:《法律赋能: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之新路径》,载《人权研究》2015年第15卷。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各地有许多地方,都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现象。[注]经济衰退泛指2008 年雷曼兄弟证券(Lehman Brothers)、美国保险集团(AIG)、美林公司(Merill Lynch)以及欧美多家银行陆续爆发财务危机,进而使全球经济活动的消费需求与投资大量的减少。然而,在供给与需求方面易出现的工厂关闭、失业率升高、薪资缩减、员工无薪休假和福利的缩减,亦会形成保守之消费形态而使国家整体经济受到消费支出不足的影响,引发更多的厂商之倒闭并出现更多的失业人口。在面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问题时,究竟立法的发展,应如何有助于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法学教育的推行,应如何有助于地方产业动能的提升?这是我们全球法学界所必须共同思索并携手努力的课题。
二、产业发展的条件
任何一个地方或时代的产业要得到发展的能量,都必须有许多主客观条件的配合,而归纳各种主客观条件,可归结为一项最关键的条件,那就是:在该地区,市场上交易的产品或劳力,其所创造之价值与其所能获得之价格,愈能够一致或落差愈小,产业发展的能量愈大;反之亦然。
价格是指消费者为了获取产品所必须支付的金额;[注]See D.I.Hawkins,R.J.Best,K.A.Coney,Consumer Behavior:Implication for Marketing Strategy Revised,Business Publication Inc,1983,p.448.而价值则是指消费者基于所得到和所付出的认知,对产品整体效用的评估。[注]See V.A.Zeithaml,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Quality and Value: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52 Journal of Marketing,2-22(1988).价值更可以进一步定义为:消费者自产品获得的知觉质量(或利益)相对于价格支出所知觉的牺牲二者间的权衡,[注]See K.B.Monroe,Pricing:Making Profitable Decisions,McGraw-Hill,1990.或价格支付所交换的知觉价值。[注]See J C.Anderson,D.C.Jain,P.K.Chintagunta,Customer Value Assessment in Business Markets:A State-of-Practice Study,1 Journal of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ing,3-29(1993).当一个地区在市场上交易的产品或劳力,其价值与价格能够相当一致时,人们便会更愿意在市场上提供劳务或物品,来换取同等价格的金钱,此时,产业发展便得到其最为根本的能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来说,价格与价值一致,也就意味着市场上双方进行交易之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即交易的成本,相当低廉。而交易成本是一种额外并且可避免的社会成本损耗,交易成本越低,对双方交易越有利,社会整体也因此能获得最大福祉,[注]有关新制度经济学上述交易成本论,参见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3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而此福祉便能激发人们在生产与消费上的信心。
信心,是人类活动能量之源,因此,消费者的信心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注]消费者信心,也有人称为消费者情绪,是指消费者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对就业、收入、物价、利率等问题进行综合判断后得出的一种看法和预期。在许多国家,消费者信心的测度被认为是消费总量的必要补充。消费者信心指数(ICS)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是监测经济周期变化不可缺少的依据。然而人们对于生产与消费的信心却并非偶然或轻易即可建立。人们的信心来自于自己所付出的劳力与精神与所能获得的利益,能够取得平衡,甚至于所得能够大于付出,如此信心才能够持续或增强。当然,就个体而言,人们对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之间的衡平得失,乃完全由自己主观界定;然而,就总体而言,在某种环境下,人们较易认定自己的付出与所得能够平衡,而在某种相反的环境下,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前者那种环境,便是人类社会所乐于建构并予以维持的环境;而后者,则多为人们所厌弃。[注]因此,亦有经济学者将发展的定义,由经济发展扩张至全人类的自我实现能力与机会的增进。Amartya Sen在其名著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发展不能只观察所得与财富的增加与分配,而应该以个人自我实现能力的提升为其核心意义。自由与法治不是为了促使利伯维尔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工具,而是利伯维尔场使人得以发挥其创业精神,行使其规划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的必要制度条件。See 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Anchor Books,2000.有利于人们对于自己的付出与收获之比较感到满意的环境,通常具有下列特性。
(一)价值取向明确
在任何环境中,人们若能很轻易而明确地获知某种价值取向,便能够将该价值与其所付出的价格作比较,而决定自己是否愿意继续为留在该环境而付出相当的金钱价格。例如,在一个装潢布置十分高雅而清洁的旅馆中,或食物用料及烹饪非常讲究的餐厅中,人们能够很清楚地得知如此之旅馆或餐厅所要求的价值取向,因此,即使在物价飞涨、所得降低的时代,这种诉诸高级设备及食材的餐饮业,仍能创造出傲人的产值。
(二)交易安全性高
当人们在任何一种环境中,其所付出的劳力或金钱的价格与其所能回收的价值,得以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乃至于可预测性,那么,人们就会自行去衡量应投入多少的劳力或金钱,来取得相当的价值,而这便是交易安全性高的环境。[注]在交易安全性高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较容易取得信任,而人们对于陌生人,较愿意倾向于以信任的态度来对待,一般而言,这样的社会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之基础。学者早已意识到,在人们愿意信任陌生人的社会中,比如日本和美国,社会合作比较容易,并且存在经济上的溢出效应。See Francis Fukuyama,Trust,Free Press,1995;Robert 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相反的,在交易安全性低的环境中,人们无法预测自己所付出的劳力或金钱,能取得多少价值,或是否能与上次一样,获得等同的价值,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即使曾经有过一次交易经验,体认到其所付出的价格与取得的价值能够相当,但也无法保证类似的交易能持续进行,因此,此种环境的产值难以维持或提升。
(三)具有调适功能
不具交易安全性的环境,若能够具有使交易双方或多方彼此相互回馈或自行修正的功能,则此环境亦能够逐渐具有交易安全性,并且达到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的境地。
大部分具有明确而被人接受的价值取向,或具有高度交易安全性的环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多是日积月累逐步发展而成的。但是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有些环境不具有让交易当事人彼此回馈与调适的机会;有些则予以容许,甚或鼓励。前者的环境,便会使交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因无法使其付出的价格与所得的价值得到平衡而离开该环境,此便造成该环境产能的逐渐空洞化;相反的,在容许甚或鼓励的环境中,当事人所付出的价格与其从相对当事人处获得的价值能够在不断反馈、调适与修正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取得平衡,于是在取得平衡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发展的动能,取得平衡后,更能够维持其产能。
三、法律在产业发展中的功能
产业发展,需要价值取向明确、交易安全性高且具有反馈与修正功能的环境,而法律对于这种环境的构成而言,有时候具有正向的功能,有时则产生负面的影响。具正向功能的法律与负面功能的法律,在价值取向的设定、交易安全的保障及反馈与调适功能的设计上,有不同的规范。
(一)价值取向的设定
在价值取向的设定上,法律有时因其明确性与稳定性的特质,而有助于一个环境发展成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环境,有时则因其对环境的功能与特性做了错误或不合时宜的规范,而使该环境的价值取向在此法律规范下难以明确。[注]论者或谓“法律的精确性可减少纠纷处理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促成财富极大和公平正义的手段……,然而精确性使人们易于遵循确有其益处,但也其缺点,……法律过于精确也代表弹性低,在适用于特定个案时,有时将违反公平正义或财富极大的追求”。谢哲胜:《法律经济学基础理论之研究》,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1第4期,第37页。例如,当法律将必须营利才能够维持其生存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规范其营运的模式,不得具有营利的性质,并将其营利行为界定为犯罪,便使得这类组织多半价值取向不明,因此使投入该类组织的人员无法将其所投入的价格与所能获得的价值予以适合的比较,于是这类组织通常不具有永续经营发展的能量。
相反的,法律将某一区域界定为某种特定产业生产、加工的基地,给予该特定产业于该区域中设置厂房相当的租税优惠,便使该区域能够吸纳该特定产业的业者进驻,而特定产业业者进驻该区域后,由于其周遭有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可资合作,又能在较低营运成本下,将自己的产能发挥至极,于是该区域便成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主要基石。
(二)交易安全的保障
交易安全被破坏时,法律提供争议解决的依据,并且对破坏交易安全者予以制裁。因此,法律向来是市场上保障交易安全最重要的工具,尤其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更被视为保障市场上交易安全的唯一良方。
然而,法律却不见得一定能够保障交易安全,在某种情况下,法律会成为交易不安全的保障。例如,在劳动市场中,劳力的提供者与购买者二者之间,同样必须在彼此交易时,价格与价值能够相符,劳力市场才能够永续发展,而如果法律一味地偏向于保障某一方的权利,削弱另一方的议价权,便有可能使劳力市场上劳力的提供者所付出的价值,与其所能够得到的价格,也就是薪资不相符,无论价值或价格的任何一方高于他方,都会使人们愈来愈不愿意在此劳力市场上交易劳力。在此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企业外移或人才流失这两种明显的产业负成长的现象。
(三)调适功能的设计
法律或许无法对市场中的各种产业作正确且明确的界定,也或许无法直接就交易中应有的安全性通过文字性的规范给予直接且强有力的保障,但是法律却有可能设计出某种机制,让市场中的各方当事人,比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更愿意彼此相互反馈与调适。而当市场中的相关当事人之间,能够彼此反馈与调适,有时便能够对交易的安全给予最大的保障,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当事人可以相互沟通与调适的感受,或许就是一个交易环境能够给人的最明确而有实质意义的价值。
四、两种立法典范
法律如何才能促使市场中各种行为者能够维持明确的价值,并且确保交易的安全,同时又能够设计出良好的机制,来让各方当事人能够更愿意相互反馈与调适呢?其关键在于立法时,对于法律的性质与功能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然而,对法律的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却因为不同时代中不同的认知典范而有不同的见解。可归纳出两种对法律性质与功能的认知典范:[注]所谓“典范”(paradigm),系科学史家兼科学哲学家孔恩(Thomas S.Kuhn)所提出的著名概念。“典范”观念虽源自于对自然科学史的探讨,然其后续效应仍广泛地影响了经济学、企业管理、法学、政治、传播、文学等学科,促使各学科对自身后设(meta)的反省。简单地说,典范是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科学家不会去质疑典范是否能成立,他们在典范的指导下进行“解谜”(solving puzzles)的活动。See T.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一是传统的“裁判法学”(legal theory for judgment);二是结合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所发展出的“赋能法学”(legal theory for empowering)。[注]与本文所提“赋能法学”相近的概念,是近年来的“法律赋能”(legal empowerment)这一新兴概念。这是一种“以小区为导向、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其根植于基层的需求和活动,而又能使小区层面的工作对国家法律和制度产生影响。其将公民社会的支持放在首位,因为这通常是增强穷人法律能力和权能的最佳选择。”有关“法律赋能”论,可参见Stephen Golub,Beyond Rule of Law Orthodoxy:The Legal Empowerment Alternativ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3,pp.3-4.两种不同的法学典范,对于立法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及其于社会与经济发展上的功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价值取向不同
传统的裁判法学一般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争议时,作为裁判用以解决争议的依据。因此,裁判立法为社会及市场所设定的主要价值,在于争议双方或多方的当事人能够接受解决争议所做出的裁判。在这种对法律功能的界定下,立法发展的主要内容,便在于如何让人们在争议中做出可为人所接受的裁判,包括裁判的依据、裁判的方法、裁判的程序以及裁判的组织与人事。
而以裁判能为争议当事人所接受为主要目的的立法,其所最崇尚的价值,乃是公平与科学。公平是指在裁判程序中,各方当事人都能拥有相等的时间与机会,来为自己的主张而努力。科学,则是指裁判所依据的各种参考信息,必须尽量能经由科学方法检证,并且为人类共同感官经验所理解与接受。
赋能立法在价值取向上,则强调法律的功能在于赋予当事人必要的能力,来完成公共政策的目标,或实践当事人自身的权益,或于遇有争议时能与争议他方达成协议。因此,以赋予当事人能力为目标的赋能立法,其所必需的价值不在于公平与科学,而在于沟通与学习。因为人类的能力表现为沟通的能力;而沟通能力的提升,必须经由不断地学习。
(二)交易安全保障不同
就交易安全的保障而言,裁判立法的重心在于事后的保障;而赋能立法则着眼于事前的预防。所谓事后的保障,系指当交易安全受到破坏后,通过各种司法或准司法的程序来予以救济,而救济的方法,则是通过公正的裁判者的裁判,要求破坏者提供补偿或予以恢复。为使上述交易安全的事后保障得以实践,裁判立法就交易安全保障的立法,着重于制定出可令裁判者于裁判时引以为据的法条。这些法条多具有“指令-控制”的内涵,也就是文字中明确地规定行为人应遵守的行为指令,用以控制行为人的行为,以及裁判者的裁判取向。
着眼于事前预防的赋能立法,则强调交易安全欲获得保障,其条件在于交易者各方都拥有特定的能力,使交易安全有受到破坏的可能时,行为人本身即有能力来予以防止。此外,赋能立法也认为可以引进更多具有特定能力的行为人的参与,来使原来交易的双方因为加入了新的参与者,而无法恣意破坏交易安全,或在交易安全有受破坏之虞前,即被新加入的参与者阻止。
(三)调适机制不同
关于当事人之间相互的调适,裁判立法强调的是当事人所拥有的平等权与自由,也就是让当事人拥有平等地使用各种形式或非形式的制度,来与他方当事人进行沟通或协商;这些沟通与协商,可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进行。此外,裁判立法也认为由司法机关或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行政机关介入,作为当事人间相互调适的中介,是可信且可行的。例如劳动法规中规定由政府的劳动部门来作为劳资双方遇有争议时的协调机关。
赋能立法则相当重视让当事人具有充分的诱因与能力,以法律上的互动进行双方的协商与调适。赋能立法认为当事人之间的相互调适,其基础在于信任,因此,赋能立法重新检讨裁判立法所建构出的各种决策程序或裁判程序,对其中不利于当事人相互信任感之建立的敌对性程序予以变革,企图通过软化的规范,来降低各种程序中的敌对性。
最后,赋能立法认为,更多人的参与,尤其那些在法律程序上与双方当事人都无敌对关系,但是在该领域却拥有适切的专业能力或利害关系之人的参与,相当有助于提升各方当事人的能力。赋能立法强调当事人的学习,而学习必须有学习的对象与试误的机会,因此,赋能立法在法规范的设计上,强调要善用各种可资行为人学习的信息;并且,在行为人的学习过程中,硬性的指令与控制管制应尽量退出,以给予行为人试错与成长的空间。
五、产业发展需求与立法典范的选择
如前所述,产业发展的条件,在于创造一个生产价值与其市场价格相符的环境。而上述两种不同的立法典范,究竟何者对于创造如此之环境较为有利?这与时代产业环境之变迁及产业发展的需求有关,而在目前全球化的产业发展局势下,产业发展有如下的需求。
(一)提升在地性的价值
在全球化发展下,全球各地产业发展都因全球化而获利,但也因全球化而产生致命风险。全球化的发展,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而这种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现象,便会使富者所创造的价格,逐渐大于其价值,而贫者的生产与劳动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价格,远低于其价值。这种情况若未能改善,任其恶性循环,则许多已经趋贫的地区,将逐渐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边缘地区,且终将破产而成鬼城。
因此,提升在地性的价值,乃是世界各国、各地区产业发展的共同课题。尤其,美国挑起贸易战后,其贸易保护政策可能导致多国反击,因而打乱企业供应链,迫使全球经济提早走向收缩调整期。对于经济学者而言,如何避免重蹈1930年人类“经济大萧条”覆辙,[注]所谓“经济大萧条”,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经济大萧条从美国开始,以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下跌开始,到10月29日发展成为1929年华尔街股灾,并席卷了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人均收入、税收、盈利、价格全面下挫,国际贸易锐减50%,美国失业率飙升到25%,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33%。全世界各主要城市全部遭到重创,特别是依赖重工业的地区。许多国家实际上无法进行工程建设。农产品价格下降约60%,农业受到重击。由于缺乏可替代性,第一产业中的经济作物、采矿、伐木等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有的经济体在3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复苏。成为近期经济发展重要议题。而要避免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再次发生,其唯一的方法,便是积极提升各地的在地价值,使地方的独立经济得以发展,以避免各地工资和收入,受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而普遍落后。
(二)降低非经济性的交易风险
在产业发展走向衰退的地区,通常伴随着较高的交易风险,法律在此地区便特别需要发挥其降低交易风险的功能。然而,在法律欲发挥其降低交易风险的功能时,却有可能反而产生许多非经济性、非市场性的交易风险,例如官僚体系介入生产与市场的交易过程,但却因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借由执行法规范时可裁量的空间,课予行为人各种法律所未规定的义务,造成额外的交易成本。
产业发展低迷的地区,中央或地方政府决策人物通常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而要求官僚体系介入市场经济,以期通过公部门资源的挹注,来振兴产业发展。此种做法在许多地方能够得到良好成效,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奇迹或典范,但却也有可能使产业发展更加恶化。而其主要之差别,就在于官僚体系介入市场经济,经常有其自身的利益,其若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忽略其追求自身利益对市场交易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便很有可能使市场上的行为人产生生产与交易以外的成本负担,而此成本负担在市场交易者必须降本求利的需求下,必然会造成价格升高或价值降低,如此便将加剧市场上物品或劳务的价格与价值不相符的现象。因此,在产业发展低迷的地区,法律规范的设计,应特别留意如何让行为人自身拥有确保交易安全的能力,并且降低官僚体系的介入从而尽量避免造成价值与价格扭曲的问题。
(三)强化中小企业的调适能力
在产业发展衰退的地区,要提升在地性的产业价值,必须仰赖充满弹性与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再发展。对中小企业而言,其经营上的弹性与适应力,乃是其主要竞争力来源。因此,应使中小企业在遇有争议时,更具彼此适应的弹性与能力。中小企业提升自我调适与彼此调适的能力,最主要之阻力,首先即来自于法律规范,例如法律对于中小企业雇用员工的薪资,如同对于大型企业一般,予以硬性的规定,便使中小企业的资方与劳方成为无法彼此调适的敌对双方。
中小企业在市场活动中所贩卖的产品或服务,如果其价值与价格不相符,该企业便会很快被市场所淘汰。相反,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若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其价值与价格又能够相符,则该中小企业便对于该地区的产业发展,能够做出相当的贡献。一个产业发展正值起步或步入衰退的地区,对于中小企业与市场上的其他行为者,包括上下游供货商、顾客,以及员工的调适能力,应特别予以重视。
总结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为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立法取向与法律教育的价值典范应有所调整。对于在地性价值并未特别予以重视,且对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一视同仁的立法典范,应排除其适用。法律制度的设计以及法律价值的推广,应更重视如何运用法律让社会上的各种行为人,能更有意愿学习提升自身的特殊价值,更愿意通过彼此的调适、学习与合作,来强化交易的安全。
传统法学的主流典范在立法上的运用,为本文所谓的“裁判立法”,其立法内容的重心在于对行为人违法与否的裁判;而其于立法方法上,则着重于通过制定法规来限缩有权对违法与否进行裁判之人的裁量空间。这种立法典范,对于社会上各种行为人的公平权利的保障,有其形式上的效用,但是除非有其他来自于宗教、信仰、文化或社会体制的支持,否则对于一个产业正值起步或衰退的社会,并无帮助。甚至,在过度着重事后裁判的立法价值的推衍下,人们容易在遇有重大危害社会及产业发展的事件时,仅强调对于违法或犯罪之人的课责,而忽略使各种行为人拥有学习如何遵循法律的精神或免于犯法的能力。
在产业寻求发展、加值或转型的地区或社会,人们所需求的,不只是争议事后公正的裁判或课责,更是预防争议情事发生的能力。因此,立法上对于法律功能,以及法律人应扮演角色的界定,其意义应不仅在于依据立法者的目标,有效地控制被规范者的行为,以及当遇违法争议时提供公正的裁判,更在于通过法律规范的设计,以及法律人的运用,来使人们有意愿接受立法者所期望的价值,并愿意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与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生产或服务于市场上的价值。这乃是赋能立法的主旨,更是笔者期望持续为赋能立法赋予更充实内容的目标。
六、结 语
产业发展的动能,取决于民众的信心,而民众的信心,则由市场上各种被交易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与价格的相符与否所决定。而市场上产品与劳务的价值与价格要能相符或减少落差,则必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交易安全有所保障,且市场上各种行为人间能够具有相互调适的能力。法律对于市场上价值取向的确定、交易安全的保障及行为人相互调适能力的提升,有其关键的影响力。然而,在产业发展的不同情势中,不同的立法典范,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笔者归纳当前立法,约可总结为两种不同的典范,一是以裁判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为核心的“裁判立法”;二则是以赋予当事人遵守法规范精神为目标的“赋能立法”。
在产业处于亟需发展、加值或转型的地区或社会,仅着重于争议事后公正的裁判或课责的“裁判立法”,较无助于该地区民众对产业的信心的建立或提升。因为民众的信心,必须要通过法律规范的设计,以及法律人功能的发挥,来使人们更愿意自主地进行自我调适与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生产或服务于市场上的价值。而这乃是赋能立法的主旨,更是笔者期望实现的在立法教育上形塑创新思维以符合全球性经济衰退阶段的产业发展现实需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