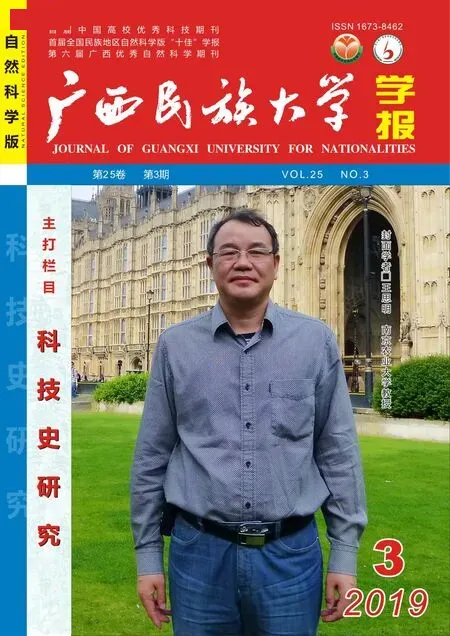“算术”和“数术”*
——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两条进路
2019-03-18周瀚光
周瀚光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中国数学史研究开展到现在,应该有条件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路径做一个宏观的分析和把握了.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数学在其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两条具有不同特点的路径:一条是“算术”的路径,一条是“数术”的路径.所谓“算术”,顾名思义,就是计算技术和算法系统,它以解决国计民生中的具体数学问题为目的,涉及田亩、测望、工程、营建、赋役以及商品交换、度量换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所谓“数术”,则主要讨论较为抽象的数理,其中不仅包括了基本的数学理论问题,甚至还涉及更加广泛的领域,如用“数”去范围天地、化成万物,去把握并预测万物发展和人生命运.①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数术”一词具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不同的含义.广义的“数术”,数学家秦九韶的说法,数理和算术相关的内容,同时也包括了星占、形法(后世演变为风水)等与数学无关的方术(术数).一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数术略”之“数术”.中义的“数术”,特指仅与纯粹数学相关的内容而不包括其他与数学无关的方术,其含义大致与秦九韶《数术大略》(即《数书九章》)书名中的“数术”一词相当.狭义的“数术”,则专指纯粹数学(即中义的“数术”概念)中与“算术”(即计算技术)相对而不同的内容,大致与《数术记遗》书名中的“数术”一词相近.本文所说的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两条路径之一的“数术”,就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的,专指中国古代数学中与“算术”(计算技术)相对而不同的数理思想及其他内容.按照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说法,数学具有“大”和“小”两方面的功能:“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书九章序》).这里“经世务、类万物”的“小”者,就是“算术”的功能;而“通神明、顺性命”的“大”者,则是“数术”的功能.从两者的表现形式和书面语言来看,“算术”一般采用实际生活中应用问题的形式,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问——答——术——草”这样一种较为规范的书写程式;而“数术”则多采用注释、陈述、推理、论证等不拘一格的书写形式,并且往往喜欢引用《周易》或其他传统经典中的概念和词句.从两者的数学家群体来看,“算术”家以朝廷的行政官员为多,而“数术”家则更多地来自民间,其中一部分具有天文历法的背景,另一部分则具有道教或隐士的背景.这两条路径从中国数学一开始发源后,就沿着各自的方向并按照不同的特点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期间经过了分分合合,各展所长,互相交融,互相补充,最终汇成了中国数学史精彩纷呈的绚丽景象.大致说来,当“算术”和“数术”这两条发展路径合流而融汇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中国传统数学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也由此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一)
中国传统数学发端于伏羲画八卦的《周易》,这是历代数学家的共识,而《周易》正是算术和数术的共同起源.《汉书·律历志》说:“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刘徽《九章算术注序》一开头就说:“昔在包牺(即伏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这里的“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出自《周易·系辞下》,所说的“通神明”和“类万物”正是后来秦九韶区别数学大小两种功能的出典.这说明中国数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蕴含了“通神明”(数术)和“类万物”(算术)两方面的内容,存在着算术和数术两种潜在的发展进路.所谓“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中的“九九之术”,是用来“类万物”的乘法口诀和四则运算,是算术;而“六爻之变”则是用来“通神明”的测算之术,是数术;中间用一个“合”字把它们连接起来,说明算术和数术一开始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算术是为数术服务的.
时间稍晚一点的黄帝也是中国数学的鼻祖之一.《数术记遗》中说:“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这是说黄帝发明并确立了数的记法和用法.又传说黄帝的老师大挠发明用天干和地支来记年、记月和记日,黄帝时的隶首作数,倕发明了画圆和画方的规矩,等等.所以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序》在肯定了伏羲氏对数学的始作之功后,接着便说:“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这说明在刘徽的思想里,黄帝的数学功绩是继承了《周易》的数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神而化之、引而伸之”的发展.
大约在西周初年周公的时候,算术开始从数术中分化出来并独立地向前发展了.周公制礼,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和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六艺”,其中之一便是“九数”,而这就是最早的国立“算术”学科.秦九韶《数书九章序》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说:“按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这说明周公时确立的“九数”,即是后来《九章算术》的滥觞,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算术”这一发展进路的重要标志.
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儒家和法家等有志于国计民生的学派继承了数学发展中的“算术”这一传统.儒家创始人孔子年轻时就很懂算术,后来更把包含算术在内的“六艺”作为他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培养出了曾参、冉求等一些精通数学的人才.枚乘《七发》说:“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说明在西汉人的眼中,孟子也是很擅长于计算的.法家的《管子》把“计数”列为其治国的七大法则(“七法”)之一,以为“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管子·七法》).现存的《管子》一书中,保存了先秦时期的许多“九九”口诀、分数运算等原始数学资料.李悝在《法经·尽地力之教》一文中,通过加减乘除九步四则运算,逐一列出了当时农村一家五口的正常收支情况,并且把这一运算过程详细地记录在文章里面.除了诸子学派之外,还有一些专门的数学家继承并发展了“算术”这一传统,例如秦简《数》的作者和汉简《算数书》的作者等.
与此同时,数学发展的另一条路径——“数术”,也在独立地向前进展.春秋末年的《老子》曾说:“善数者不用筹策”,这说明当时确实有一些数学形式是无关筹策,无关计算的.①刘徽《九章算术注》卷五说:“数而求穷之者,谓以情推,不用筹算.”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老子》的话并非虚言.就我们现在所知的与计算技巧迥然相异的数学形式,首推战国时后期墨家的《墨经》中所蕴含的理论数学萌芽.《墨经》运用其所掌握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一系列数学概念如圆、方、平、直、厚、端、兼、体、盈、损、穷、倍等,用判断和命题的形式给出了科学的定义,从而开创了中国数学史上理论几何学研究的先河.同时又用推理和论证的形式,探讨了“位值制”计数法、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一些基本的数学原理.同时期的名家则提出了“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一系列涉及“无穷”的数学悖论.
除了上述理论数学的内容外,中国古代的“数术”中还包括了与天文历法相关的数学内容.由于天文历算在中国古代具有“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以及“通神明、顺性命”的功能,因此将其归于“数术”是理所当然的.班固在编撰《汉书·艺文志》时,即将“历谱”置于“数术”略之下.他解释“历谱”说:“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此圣人知命之术也.”[1]这种“通神明、顺性命”的“大”功能与纯粹计算技术的“小”功能显然不同,所以在《周礼》“九数”的算术传统中是不被包括的,在后来继承这一传统而编撰成书的《九章算术》中也付诸阙如.
“算术”和“数术”这两条不同的数学进路发展到汉代,各自出现了自己的代表著作.“算术”的代表著作是《九章算术》,而“数术”的代表著作则是《周髀算经》,两者具有较明显的不同特点.《九章算术》是一部由官方编定的实用数学著作,最早的编撰者为汉初的北平侯计相张苍和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周髀算经》则是一部民间口耳相传的数理天文学著作,至今仍不知其作者是谁以及其确切的成书年代.①现在的数学史家一般认为,《周髀算经》是长期积累编撰而成的一部著作,最晚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成书.《九章算术》的内容涉及田亩、测望、工程、营建、赋役以及商品交换、度量换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当时计算技术和算法体系的最高水平.《周髀算经》则阐述了数学方法在测量天地、制订历法中的作用,提出了学习和研究数学的正确方法,论述了勾股圆方的基本知识、测望“日高”的计算方法以及《四分历》的基本数据和有关算法等一系列数学理论问题及与天文历法相关的数学内容.《九章算术》以应用问题的形式引出计算方法(术),每一问题基本上都采用了“问——答——术”这样一种比较规范的表述程式;《周髀算经》则仍然采用传统的叙述和论说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周髀算经》还借周公之口发出“大哉言数”的感叹,体现了其不限于具体计算技术而要去追索数之“大”者的学术旨趣.
(二)
“算术”和“数术”这两条具有不同特色的数学进路各自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和学术契机,又常常会出现一种融汇和合流的景况,而这又往往给传统数学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新的动力.纵观汉代以后数学史的发展,这种“算术”和“数术”融汇合流的景况主要出现了三次,而每次融汇合流的出现,都对传统数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从而使中国数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算术”和“数术”的第一次融汇合流出现在魏晋时期,是由刘徽通过注释《九章算术》而得以完成的.刘徽于正史无传,是一位民间的布衣数学家.从其《注序》中屡屡征引《周易》“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两仪四象精微之气”等话语以及关于“日高”和“日径”等测望计算方法的论述来看,他对于“数术”方面的内容是非常精通的.当他把“数术”的精髓引入“算术”,用他掌握的丰富的“数术”知识来注释《九章算术》这样一部“算术”代表著作时,立刻使《九章算术》的数学水平大大提升了一步.刘徽的这种融汇“算术”和“数术”的注释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刘徽继承了先秦墨家注重逻辑和理论数学的传统,按“审辨名分”的原则对《九章算术》中的许多数学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和准确的定义,又用“析理以辞”的方法对《九章算术》中的许多公式和法则进行了详细论证和逻辑证明,从而奠定了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基础.
(2)刘徽继承了《老子》“大直若屈”和《周髀算经》“圆出于方”的圆方统一思想,及先秦名家和《墨经》关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的无穷分割思想,首创“割圆术”以求取圆面积,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圆周率π=3.14和π=3.1416这两个较为精密的近似数值,从而使中国古代关于圆周率的计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刘徽继承了《周髀算经》中因历算需要而测量“日高”的方法,创立了“重差术”这一相似勾股形的比例算法,并把它推广到测量诸如海岛、远山、深谷等一些极高、极远、目之能及而人不可达的目标,从而弥补了《九章算术》在这一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开创了一个新的数学研究领域.
显然,刘徽的这些工作都是原来数学发展中“数术”这一进路的强项,是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算术”这一进路的弱项,而刘徽通过他对“算术”和“数术”的融汇合流,有效地弥补了原来“算术”进路的不足之处,提升了当时数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从而使刘徽的《九章算术注》成为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高点.
魏晋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在刘徽《九章算术注》的基础上,继续沿着“算术”和“数术”这两条具有不同特点的进路向前发展.到唐代初年,这两条进路出现了第二次的融汇和合流.而这一次的融汇合流,则是以李淳风奉命编定十部算经并以此作为国子监明算科的教科书为代表.
唐初李淳风编定的十部算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和《缉古算经》.这十部算经可以说是汇集了自汉至唐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数学著作,也可以说是涵盖了“算术”和“数术”这两条研究进路的最重要的成果.其中《九章算术》《张丘建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和《缉古算经》这五部著作因其以计算技术为主要内容,大致可归为“算术”类研究成果;而《周髀算经》《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经算术》和《缀术》这五部著作则因其内容既含有计算技术而又不限于计算技术,大致可归为“数术”类研究著作.关于《周髀算经》一书的“数术”性质,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海岛算经》原为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附在卷末的“重差”章,至唐时单独成书.其内容源出于《周髀算经》中因历算需要而测望“日高”的“数术”,经刘徽演化创立为“重差术”(相似勾股形比例算法),并把它推广到测量诸如海岛、远山、深谷等一些目之能及而人不可达的目标.《孙子算经序》说:“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终始;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这种对于数学的极端推崇,明显带有《周易》论数的印迹.《孙子算经序》中又论及数学的目的是“稽群伦之聚散,考二气之降升;推寒暑之迭运,步远近之殊同;观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纵横之长短;采神袛之所在,极成败之符验;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这显然就是秦九韶所说的“通神明、顺性命”的“大”的功能.该书托名孙子,虽不必视为先秦孙子所著,但其中保存有先秦以来兵家或其他学派的思想资料,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其中的“物不知数”一题,开启了后世“一次同余式”理论的研究和“中国剩余定理”的取得,是对世界数学史的重大贡献.这在《孙子算经》的年代,应该是属于“善数者不用筹策”(《老子》)的重要成果.《五经算术》是一部对儒家经典中涉及数字计算的有关内容进行详尽解释的著作,其论题的表述方式与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中“问——答——术”的基本程式完全不同,明显是一部“数术”类的著作.至于《缀术》,虽因其早已佚失而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从其作者祖冲之曾编制《大明历》和唐初国子监明算科规定学习《缀术》一书要长达四年这两个史实来看,推测该书当是一部与天文历算有关的较为深奥的“数术”著作.又据李淳风《隋书·律历志》和《九章算术注释》所述,祖冲之父子曾取得圆周率3.1415926<π<3.1415927及球体积计算方法等重要数学成就,这些应该都是《缀术》一书中的重要内容.与十部算经一起作为唐代国子监明算科教科书的,还有《数术记遗》和《三等数》等数学著作.《数术记遗》以“数术”为名,本身就昭示了其“数术”的性质.该书至南宋时,因《缀术》一书的佚失,而被补列于《算经十书》之中.
唐初,“十部算经”的编定以及当时国子监明算科对各种数学典籍的收集和研究,是中国古代数学自先秦以来的一次大检阅、大合成和大总结,也是“算术”和“数术”这两条发展进路的一次大融汇和大合流.它克服了在此之前数学发展或偏于一隅,或隐于民间,或失之单薄的弱点和不足,使中国古代数学的整体发展迎来了一个丰盛期和繁荣期,并由此而奠定了唐朝作为一个数学大国的历史形象.东西方各国前来学习先进的数学知识和其他知识的遣唐使络绎不绝,而中国当时先进的数学知识则随着这些数学典籍的翻译和传播,流布到了东北亚、东南亚,甚至西方等各个国家.
中国传统数学发展到宋元之际,迎来了“算术”和“数术”这两条进路的第三次融汇合流.这一次的融汇合流是由秦九韶、李冶、朱世杰、杨辉这四位号称“宋元四大家”的一流数学家群体共同完成的,并由此而推动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自述其“早岁侍亲中都,因得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这说明他学习数学的背景,一个是来自于太史的历算,另一个是来自于隐士的“数学”,两者都属于“数术”的范畴.他的《数书九章》一书,又名为《数术》《数术大略》或《数学大略》,也昭示了其数学研究的“数术”渊源.他提出的“大衍求一术”理论,自称源自于《周易》的“蓍卦发微”,并且能解决“古历会积”的历算问题,显然是建立在“数术”这一研究进路上的重大数学成果,并因其给出了一次同余式的一般解法而创立了“中国剩余定理”.李冶的数学工作和研究成果,是其中年以后弃官北渡、隐居山林时才开始并取得的.他写作数学名著《测圆海镜》的动力和基础,完全是因为得到了一部具有道教背景的算书——“洞渊九容”,因爱不释手、日夕玩绎才最终完成的.而所谓“洞渊九容”,其实就是讨论勾股容圆、方圆相缠的“数术”问题.该书最早记载并保留了“天元术”这一中国数学史上的重大成果,被后来的数学史家称为“自古算家之秘术”(清阮元《测圆海镜序》).朱世杰完全是一位民间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在《四元玉鉴》中所创立并阐述的“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也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高点.他在书中的一个旁注中说:“凡习四元者,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也.”这里的“尽性穷神之学”,无疑应归于“通神明、穷性命”的“数术”进路.至于杨辉,他不仅对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中的计算技术非常精通,曾著《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保留并记述了“贾宪三角”等一系列重大数学成果;而且还编撰了《续古摘奇算法》一书,开辟了“纵横图”(即今所谓“幻方”)研究这一组合数学的新领域.纵横图起源于《周易》中的“洛书”和《数术记遗》中的“九宫”,它在杨辉的时代,完全是一种“不用筹策”、与复杂的计算技术关系不大的“数术”.
要而言之,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数学发展高潮的来临,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数学家们继承并发展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卓越的“算术”传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同时又吸取了传统“数术”研究进路中的优秀创新成果,两者融汇相通,共同发力,终于使传统数学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高峰.到了明代以后,一则由于“八股取士”制度的盛行而导致“算术”进路乏人问津,二则由于“数术”进路偏向神秘一隅而少有真正的数学创新,致使传统数学趋于停滞,一蹶不振.明末数学家徐光启一针见血地指出:“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同文算指序》)诚哉斯言.
(三)
以上我们简要地回顾了中国传统数学中“算术”和“数术”这两条进路既各自独立发展又互相融汇合流的历史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关于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认识:
(1)首先应该为中国历史上的“数术”一词正名.广义的“数术”一词,既包括了“算术”(计算技术)和数理,还包括了一些与数学无关的其他方术(“术数”).而中义的“数术”一词,排除了与数学无关的其他方术,完全就是纯粹的数学内容,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代名词.正如中国古代的“儒术”其实就是“儒学”一样,中国古代的“数术”其实也就是“数学”.秦九韶的《数术大略》又称《数学大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狭义的“数术”,则主要是指与“算术”(计算技术)相对而不同的数学理论、与天文历法相关的历算知识以及与计算技术关系不大的其他数学分支(例如纵横术等).
(2)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计算方法及其算法体系,虽然显示了中国古代高超的计算技术和独特的数学风格,但是却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水平.《九章算术》从其成书的时代起,就缺漏了数学理论以及天文历算这一领域的数学成果,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不能完全涵盖各个时代的其他数学成就.如果没有刘徽在《九章算术》原有框架中增添数学理论以及其他“数术”元素,没有宋元数学家取得突破《九章算术》框架的其他重大数学贡献,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光辉将大为逊色.
(3)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起源于广义的“数术”.以后“算术”从“数术”中独立出来,并与狭义的“数术”齐头并进地各自独立发展.在整个传统数学的发展史上,“算术”和“数术”这两条进路曾有过三次大的融汇和合流,第一次是魏晋时期刘徽对《九章算术》的注释,第二次是唐代初期李淳风编定“十部算经”并作为国子监明算科的教科书,第三次则是“宋元四大家”在融汇整合这两条进路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重大数学成果.“算术”和“数术”的每一次融汇合流,都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数学的进步;而两者在宋元时期的第三次大融合,则将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推向了它的最高峰.
鉴于以上这些认识和总结,笔者认为,我们对于中国数学史和中国数学思想史的发展,也许可以采用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框架去理解和概括,以便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