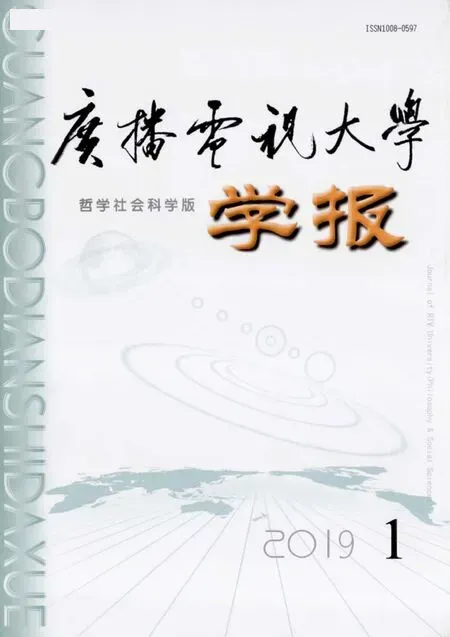论虹影小说与创意写作
2019-03-18厉向君
厉向君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随着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留学欧美的华文女作家形成了第二代女性作家群,随着地球村概念和文化上的全球化态势,使她们在异国他乡少了许多漂泊感,也少了包括生存在内的许多压力。虹影、严歌苓和张翎是当代海外华人女作家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除了这三人,还有在美国的於梨华、聂华苓、查建英、周励、汤婷婷、谭恩美,在英国的林湄,在法国的鲁娃,在瑞士的赵淑侠等,在不同的国度各显身手,群起锐进,在欧美大陆绘出了一片属于华文女性创作的斑斓天空,成为海外华文创作的重要力量。
虹影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诗人,是中国新移民女性文学的代表之一。主要有长篇《孔雀的叫喊》《走出印度》(又名《阿难》)《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K——英国情人》(《K》的改写本)《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绿袖子》《女子有行》等长篇小说。另有《你照亮了我的世界》《53种离别》《小小姑娘》《火狐虹影》《谁怕虹影》《虹影打伞》《鱼教会鱼歌唱》等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虹影通过写作,她不断出走与回归,并借此寻找自己,更是以反映人性的复杂、沉重而闻名,一方面她大胆表现女性的情欲,不断冲破禁忌,另一方面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深深影响着虹影的创作。
下面就虹影的小说与创意写作的联系作一番探讨。
一、“杂语化小说”:创意写作的探索与尝试
创意写作是指以写作为样式、以作品为最终成果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它最初仅仅是指以文学写作为核心的高校写作教育改革,后来泛指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一切面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以及适应文学民主化、文化多元化、传媒技术的更新换代等多种形式的写作以及相应的写作教育。
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一词,最早是1837年爱默生(R.W.Emerson)在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上发表的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提出来的。但这时的“创意写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创意写作理念的诞生。在19世纪20年代初,文学的审美价值受到商业价值的极大冲击,随着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出版业的快速成长,导致文学商业化席卷了整个美国后而产生了创意写作。工坊活动和阅读研讨会成为美国创意写作教学的主要形式。1976年创意写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成立。“创意写作的任务不是培养训练职业作家……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创造性体验的能力。”[1]P123
在欧洲,英国最早引进美国创意写作体系而建立起文学生产机制的国家。英国著名高校东英吉利大学在1970年建立了自己的创意写作系统。
在亚洲,创意写作系统广泛传播,进入韩国、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香港、台湾建立了“写作营”“文艺写作研究队”等。中国大陆创意写作作为新兴学科,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大学等率先招收创意写作方向的学术型硕士、博士和本科生。
现在被称为“全媒体”时代,它的背后仍然暗合了创意写作系统的最初原则:将你所熟悉的材料写成文本,寻找你想要的表达形式。
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者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海外华人的白先勇、严歌苓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虹影曾在国内参加过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的作家班的学习,虽然不能说已学习了创意写作理论和受到创意写作的训练,但从她的小说创作来看,与创意写作有着相当多的关联,应该是当代作家在创意写作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尝试的代表作家之一。
传统小说的写作离不开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特别是情节,要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这是我国传统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人物要有主要人物或典型人物,环境要有典型环境。恩格斯在评论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信中指出“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中的典型人物。”[2]P462恩格斯在这里强调了人物、情节(细节)和环境等要素的重要性。这虽然只是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说的,但基本代表了从古代小说以来的传统小说的写法。
虹影的小说颠覆了传统写作,主要体现在:
第一, 披着“小说”外衣的“自传”。在小说中虹影既是第一叙述者,也是旁观者、目击者、亲历者,小说用了片段性的、拼合的与互不相关的写法,主人公与作者的分离与重叠方式,更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小说中主人公就是作者,但读者不会认为在读一本作者的传记,因为它明明是一本小说,只是有些事情是属实的而非虚构的;同时读者又会认为在读一本传记,因为作者始终在叙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只是用了小说的外衣。
一般来说小说是虚构的,传记是真实的。杨振声就认为“没有一个小说家是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学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象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于主观。”[3]P83与之相反,郁达夫则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是千真万确的。[4]P312一般说的传记、回忆录都是真实性很强的文本。但是,也不尽然,作者自己写自传或回忆录,或者比较亲近的人写传记和回忆录,他能写自己或亲人的劣迹吗?他也会有选择地组织材料而不一定会毫无选择地事事都写,除非具有很大的勇气。如果写的是关系较远的人,可能会比较客观一些。袁良骏曾跟洪子诚说过,他在编丁玲研究资料时,有的材料、文章,丁玲就不让收入,考虑的自然是对自己形象损害的问题[5]P30。舍斯托夫与杨振声的观点刚好相反,他认为,小说比历史更真实,甚至传记亦是如此。“迄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直截了当地讲述自己的真话,甚至部分真话,对于奥古斯丁主教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穆勒的自传、尼采的日记,都可以这样说。”舍斯托夫认为,关于自己的最有价值而又最难的真话,不应该在自传、回忆录中寻找,而应该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比如,《地下室手记》通过斯维德里盖伊洛夫向我们展现活生生的、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果戈里也不是在日记、书信,而是在他们的作品,如《野鸭》《死魂灵》中讲述自己[5]P30-31。虚构的文学(小说)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说话,因此,比传记,比历史更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这才是(小说)真实性的主要原因。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虽然是小说,但更符合舍斯托夫的这一理论,这两部自传体小说的真实性是很强的,也是虹影小说的独特之处。作品中的“我”,即可以看作运用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也可以说就是作者自己。按虹影自己的说法,《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是自传[6]P227,P231,但笔者认为更是小说,因为小说“更能够自由的说话”。
第二,“杂语化小说”尝试。“杂语”是虹影在《大世界中的杂语演出》中提出来的,虹影针对当今中国作家的京味小说、秦腔小说、湘语小说、鸳蝴小说等小说称谓,把自己的《上海魔术师》称为“兰语小说”[7]P337。她说:“我的实验,正是想把现代汉语拉碎了来看”,“这是一本众声喧哗的小说,是各种语调、词汇、风格争夺发言权的场地”,“我试图做一件中国现代作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做的事:杂语化小说”[7]P339。陈思和说,虹影的小说“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各地方言的拼凑,在表达语言的层次上,她超越了作为南方普通话的上海语言的层面,直接将现代汉语(规范普通话)、外来语翻译的白话和传统的江湖语言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杂交实验。……她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她所隆重推出的兰胡儿的语言里,最生动的还是操起了四川的江湖黑话来泼骂。”[8]P345-346梁永安认为,“虹影是最有杂语化潜质的女作家”[9]P358。《上海魔术师》里的人物,各说各的语言:犹太人“所罗门王”说的是《旧约·圣经》的语言;天师班班主“张天师”说的是中国传统江湖语言;所罗门收养的中国孤儿“加里王子”说的是旧上海流行的——洋泾浜英语、市井语、“戏剧腔”以及养父的半外来语;张天师女徒弟兰胡儿说的是“兰语”。所谓“兰语小说”就是指《上海魔术师》里兰胡儿的语言,即虹影的语言。虹影说:“兰胡儿就是我”,“兰语就是我的语言”[7]P338。因此,各种语调、词汇、风格的语言,成了《上海魔术师》众声喧哗的“杂语小说”。“杂语化小说”,可以说是虹影创意写作的探索与尝试。
二、“写你知道的”:虹影小说与创意写作融合
写作本质上是一种交流、沟通、说服活动,以文本为媒介,牵连写作者和接受者两头,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利益、观念的碰撞以及妥协。创意写作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文学写作是创意写作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创意写作不等同于文学写作。我们说的创意写作,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欣赏类阅读文本写作”,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包括故事、小说、诗歌、随笔、游记、传记等。但创意写作还包括非文学,或与文学相关而本身又不是文学形式的有创造性的写作。二是“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这一类不是作为艺术欣赏消费的直接对象,而是创意活动的文字体现,包括出版提案、剧本出售提案、活动策划案等。三是“工具类功能文本写作”,这类写作文本与中国高校传统应用写作、公文写作的对象基本重合。
美国当代学者马克·麦克格尔(Mark McGurl)用“高级多元文化主义”(high cultural pluralism)来概括创意写作的核心特征,那就是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关注。
“写你知道的”是创意写作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虹影小说既是创意写作“欣赏类阅读文本写作”,又是“写你知道的”的典范之作。由于虹影的生活环境和自己的经历,在小说中把自己人生体味和盘托出。虹影小说“写你知道的”主要是:
1.写了“母亲”——一个女性宿命的社会角色
母亲,是历来被歌颂的人物,虹影的小说也不例外。但虹影小说表现对于母亲“爱”的描写是从“恨”的方面来表现的。虹影彻底颠覆了关于母亲叙述的既定话语,呈现了一个人性深渊里的母亲。这个母亲形象,不论是流言蜚语里的坏女人,还是有很多情人,还是坚强地生下婚姻外的孩子,还是晚年的捡垃圾等细节,都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受难,爱,以及尘世的残酷、情欲与道德的波澜。虹影把母亲的历史置于时代里,这既是她个人的史诗,也是时代的史诗[10]P7-8。在当下,我们大多数的文学早已学会用一套娴熟的技术掩去现实的残酷,用中庸的温情遮掩着放弃了对人性弱点与黑暗的开掘,也正因为此,当我们试图从正面表达爱意时,也总是显得虚伪而孱弱。相反,虹影锋利的解剖,勇敢的坦陈,把母亲写得淋漓尽致,惊世骇俗。这是作者因为深挚的爱恋,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世界总还怀有美好的期待。虹影在涉笔与中国当代史密不可分的家族经历时,不回避,不躲藏,从家庭成员复杂的关系入手,坦率而直接地写出了时代,写出了一个城市被长期遮掩的一个残酷的角落。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意图并不止于暴露和控诉,而是专注于幽暗的同时也开掘闪光的人性,专注于曾经的青春所经历的中国式的残酷挣扎与成长,以及更多生命从坚韧充沛走向衰竭与消亡,专注于这些生命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如动植物般生存却进行着人的自我救赎。救赎——不能通向哲学,但至少通过亲情、爱情,达至中国人朴素的宗教感。虽然宗教感中也充满宿命,但这就是人,出身于脏污现实中的人,挣扎求生,作孽而又向善,身行丑陋却心向美好[11]P3-4。虹影描绘了一个坚韧、无私、宽宏大量的女人,但也是一个叛逆的、与男人有多种关系的女人,晚年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被欺负的女人。虹影在书中对母亲的描写是多重的,虹影的感情在爱中痛苦着,她爱母亲,她试图描述母爱。书中描写出复杂的母女感情,多次写到母亲拉着她的小手,牵着她的手,走在磕磕碰碰的路上。
虹影的“苦难的母亲”是个历经磨难和感情丰富的女人。母亲的磊落、承担、宽广,对苦难的承受与自立的个性,使虹影似乎找到了自己反叛的根源,自己起伏不平的男女关系的根源,好像轮回,甚至自己软弱的根源,因为自己跟母亲一样爱过,容忍过。她们都是在男女关系上走过不同一般的路的人,她们都强烈地爱过,也都磊落与宽广;她们对苦难都有敢做敢当的承担和对人世复杂的宽容与理解……母亲和虹影都乐于助人却被世界曲解或误解,她们在精神上达到的是那些对她们加以判断的人不能达到的高度[12]P8-10。
2.写了“性爱”——人的最本质的显露
古往今来关于爱情的描写,尤其是两性的描写,越含蓄越好,令人有联想和想象的余地,但也有喜欢直接宣泄或一览无余的。如郁达夫的性爱描写,茅盾突出女性某部位的描写,叶灵凤的性爱描写等。在直接描写男女做爱和交合方面,无名氏和林语堂是突出的两位,他们的描写不是低级庸俗,污秽不堪,而是美轮美奂,令人陶醉,使人获得美的享受和审美愉悦。前者如《海艳》,后者如《红牡丹》,都反应出作者写作水准和艺术的高超。
虹影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其“性”的大胆描写远远在冯沅君、庐隐、丁玲、苏青之上。特别是《K》《上海王》《孔雀的叫喊》《绿袖子》等里的“性”描写就是例证。《K》里的“林”和朱利安,《上海王》里的筱月桂先是与常力雄,继而与黄佩玉,再是与余其扬,做爱、交合超过郁达夫的描写,可以与林语堂、无名氏媲美。与其他作家的内敛风格不同,虹影小说表现情欲的描写可谓大胆和恣肆,已超过同时代所有作家。
虹影认为,当小说家把性爱写得“欲仙欲死”时,应该受到尊重和理解。小说描写再精彩,也不会有读者诸君做事情时的感觉犀利。试试:划一根火柴烧一下自己的手指,或用利器像不小心时划破皮肉那样,然后你把这种感觉写成文字,这文字绝对写不出那种又烫又痛的切肤之感,除非读者补入自己的经验。性,爱,也一样。[6]P204-205
她还说:作为一个作家,性对我很重要。性在我生活时,就是我的衣服、我的食品、我的亲人和朋友。性在我写作时,就是奇想和激情,是妖术的语言,是我的脸、我的乳房、我的腿、我的眼睛、我的愤怒和疯狂、我的冷静和温柔。即使是我从头到脚裹了长袍,你也能见到我的手,我的全身最性感的部位就是我的手,无论是握着笔或是敲击着电脑键盘,这时刻,我就是《K》中的K,一个能左右生命的符号,一个神州古国的代表,一个他(男人世界,东西方男人世界)注定跨越不了的美[6]P205-206。虹影在这部作品里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自觉与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性别概念:女性必须贞洁,家中兄弟姐妹男女关系都以男人为中心,这个以男人为中心的世界,让人厌恶又让人摆脱不掉,让人同情也让人绝望。因此,虹影的“性”描写,不是具有一般的反封建意义,而是男女在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体现。
3.写了“私生女”——最受非议的“爱”的结晶
一般来说,写自传应该在晚年为好,可虹影在38岁就开始了“自传”的写作。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众所周知,郁达夫写小说是最为扬家丑的,殊不知,虹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她十八岁离家出走的“家史”公布于众。郁达夫的小说毕竟有夸张的成分,而虹影的小说是贴近生活的“原生态”。
私生女(子)在文学作品中不乏案例,但至今还没有哪一部小说把一个“私生子”写得像虹影一样如此令人难忘。
虹影是一个私生女,原名,陈红英,又名陈英,乳名六六;她的养父姓陈,生父姓孙——其实也不姓孙,而是姓李,因为生父是随着母亲改嫁姓孙,所以,虹影姓李才是正统。“虹影”是诗人梁上泉给她取的笔名[13]。虹影认为,一个人姓什么并不重要,一个人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14]P127。就像生活于我,从来都比小说精彩一样,生活对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6]P252。她说:我既不随生父姓,也不随养父姓,跟我自己姓。虹姓在百家姓里面是找不到的,只属于我自己。按作者自己的解释,虹影是指“淫奔他乡”,实际取自《诗经》,言女子有行,应远父母兄弟,而且宜西不宜东[14]P126。
虹影1962年出生于重庆南岸的一个贫民窟里,她是家中老六,唤作六六。在饥荒年代,虹影的父亲驾船在外边,很久没有下落,六个孩子处于饥饿之中,有一个年青人来帮助全家度过困难,母亲与他相爱生下虹影,母亲也因此落下坏女人的名声。虹影说:“这是当地一个人人皆知的秘密,只有我被蒙在鼓里。生来是多余的,母亲顾及大家庭里其他人的感受,不敢爱我;法院规定在成年之前,生父不能与我相见;而养父,对我则有着一种理还乱的复杂情感,始终有距离。没人重视、没人关心,在周围大人和孩子的打骂与欺侮中,我一天天长大。”[15]P24
读初中的时候,虹影就以作文好而出名,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学财会。从那时开始,虹影就写诗、写小说。
18岁的虹影在知道了自己是一个“私生女”后,如五雷轰顶,一气之下,只身离开重庆,南奔北漂,浪迹天涯。1989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后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流浪路上,她结交了大量的作家、诗人、画家。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她不得不拼命写作以获取稿费。曾有一段时间,虹影对诗歌十分狂热痴迷,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作。
虹影认为,爱,是可以忽略一切外在附着物的。所以,虹影后来向比她大20岁的赵毅衡坦白承认自己是一个私生女,读中学时与历史老师有过一段非常的情感经历,被家乡人认为是坏女孩。她还说,中国也有 80年代性解放。“那时,我们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我们开黑灯舞会,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试验各种艺术形式,跳裸体舞。”其坦诚可谓令人震惊。
世人大多会嘲笑“私生子(女)”,殊不知,“私生子(女)”大多都是“爱情”的结晶,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男女相爱的人不能够结合,导致“私生子(女)”在社会生活中备受冷眼和歧视,这是封建社会影响的延续。虹影作为一个“私生女”并非像人们嘲笑的那样低人一等,不仅同样应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且更应该对其关心呵护,因为“私生女”毕竟也是爱的结晶。“私生女”是虹影贡献于文坛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出,“写你知道的”就是写了虹影知道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女”,知道自己的母亲一生是多么的不容易,知道“性爱”的重要和应当受到尊重与理解。小说完全做到了实现一种交流、沟通和说服活动,甚至会与读者的观念发生碰撞及妥协,这就是虹影的小说与创意写作做到了有机融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虹影的小说与创意写作存在着一定联系。在我国,创意写作作为新兴学科正处于初创阶段,虹影的小说还不完全说明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成熟,但既然探讨的脚步已经迈开,相信未来的研究将会不断深入,成果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