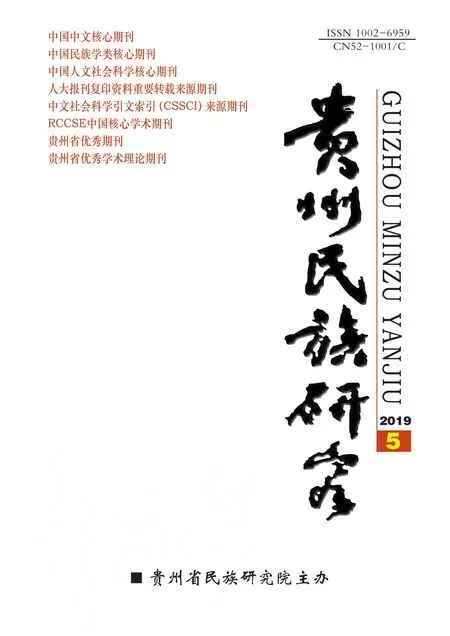基于文化视域下的民族舞蹈探究
2019-03-17高莎
高 莎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舞蹈是民族艺术最深邃的文化表达,是民俗文化跨时空汇聚的活化石[1]。不同于民族建筑艺术的文化写实,不同于民族工艺的抽象推敲,也不同于文学艺术的文化遐想,民族舞蹈艺术是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习俗解读最为活跃的“史书”。一方面,民族舞蹈在自我发展中不断吸收其他艺术文化的精髓,使舞蹈艺术成为民族可视化文化的枢纽。比如:凉山民族风情园雕塑基本以彝族司空见惯的民族舞蹈姿势为主,水族在壁画艺术中除钟情山水自然外,铜鼓舞的人物姿态也是水族壁画艺术颇为钟情的纹样。另一方面,民族舞蹈以独特的本源意蕴和显著的文化定位,逐渐成为民族世俗文化的艺术浓缩。比如:普米族歌舞《拜龙调》通过舞蹈有效地反映了普米族群众朴素自然的生态文化和简易的祭祀文化,虽舞姿简便但文化意蕴深长。此外,民族舞蹈艺术在情境交织的情感领略中难以把握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中庸儒道的线性情感认知上,民族舞蹈的价值内敛是非文化机制所能耦合构筑的。“喜而生悲,因悲而舞”与“悲而喜舞,舞却生哀”的民族舞蹈生成是非文化难以诠释的艺术形态。比如:土家族群众在长辈去世时,视葬礼热闹表示子(孙)孝道,因而《跳丧舞》成为悲而生乐的舞蹈典范,当然,丧事活动中也有悲舞,或以慰藉亡灵、或以歌颂死者,比如:哈尼族舞蹈《莫搓搓》、景颇族舞蹈《戈奔》等,这些民族舞蹈艺术都蕴含着群体祈福消灾的文化心理。由此可见,跨情境与艺术的文化视域才能更确切地审视民族舞蹈真正的魅力所在[2]。
一、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本源追溯
(一)民族舞蹈是劳作行为的艺术化呈现
劳作是群体智慧的艺术映射,是社会文化艺术建构的基本保障。就民族舞蹈艺术的本源而言:劳动是最原始的舞蹈行为符号和艺术转换体。特别是少数民族依山傍水的自然生活环境、采种狩捕的生活形态为劳动行为的舞蹈艺术兴起与转换提供了天然屏障。
首先,劳动行为为舞蹈的肢体变化提供了朴素的参照。群体在劳作之余依据劳动行为和劳动工具不断在艺术化蜕变中成为群体喜闻乐见的舞蹈艺术。比如:曲水藏族群众传统舞蹈《打阿嘎》就是源于砌墙劳作的演变,阿嘎棒(类似北方土砖模子)作为碎土、砌墙工具逐渐成为重要舞蹈道具[3]。其次,民族群众在劳作与娱乐之间的肢体行为的无意缓冲,逐渐成为民族舞蹈艺术衍生的雏形。藏族群众歌舞《砌墙歌》在肢体动作表演中主以腰部、胳膊的动作交替为主,姿势既是蹲姿疲劳的缓解又是劳作闲暇时间的嬉戏之作,舞蹈整体基本与砌墙劳作息息相关。再者,源于朴素田野劳作的行为和得天独厚的劳动场景,为民族舞蹈的起源铸就了原始的气息。一方面,民族群体在田野劳作之际不断将自然万物进行艺术化的抽象临摹,进而在肢体行为的演化当中成为独特的舞蹈形体。比如:南疆哈萨克族群众在高原生活中对飞禽走兽动作不断模仿,成为独特的舞蹈艺术,而以“买力斯”为代表的鹰舞,成为其世俗舞蹈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民族群体在田野劳作中,将劳作的场景与气息潜移默化地延伸到舞蹈艺术当中[4]。比如:延边朝鲜族舞蹈《农乐舞》将典型的庆丰收、勉勤劳作的气息不断纳入舞蹈演绎布局中,使舞蹈本身充满群体独特的劳作仪式与情怀。当然,劳作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源泉,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劳动过程中对自然万物的巧妙模仿也是民族舞蹈的重要起源。
(二)民族舞蹈是民族娱乐行为的艺术体
虽然“乐”难以界定民族舞蹈的艺术性能,但是“娱”却是民族舞蹈不朽的秉性。不管民族舞蹈“娱神”“娱人”的形式的悲喜倒置与否,舞蹈娱乐行为的艺术体本能是民族舞蹈起源的关键。一方面,民族群体能歌善舞的先天性艺术潜能为舞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民族群体个人本位主义品性鲜明,加之群体豪爽的性格,为民族表演行为的舞台扩散注入了人性化的艺术品格,从而使民族舞蹈的娱乐性植入到民族艺术体的脊髓。民族群体体教活动同舞蹈艺术始终融会贯通,舞蹈的娱乐性超乎主题的断然聚集[5]。比如:水族《斗角舞》舞姿动作同水族传统体育活动肢体动作如出一辙,舞蹈在传统体育活动中逐渐扩大了舞蹈娱乐的艺术属性,而朝鲜族《假面舞》将特有的朗诵、音乐、舞蹈集于一体,成为主题鲜明的娱乐艺术体。民族乐舞同轨并体,音乐与舞蹈相生于乐。或取悦于鬼神,如哈尼族铓鼓为圣物,而《铓鼓舞》则是哈尼族群众祭祀神灵,避祸求福的舞蹈。或寄托心愿,如蒙古族传统舞蹈《草原上的热巴》在朴素舞姿乐曲背后传递着蒙古族同胞强烈的故土情怀,表达了他们向往幸福生活的愿望。总之,民族乐舞在娱乐外衣包裹中不断成为一种特定的民族情结。
(三)民族舞蹈是民俗遗风的有机体衍生
舞蹈的视觉直观性与习俗仪式场景的内在诉求基本吻合,民族舞蹈从民族习俗仪式组成中逐渐扩散、独立,是民族舞蹈形成发展的社会动力。首先,类似舞蹈的行为作为民族习俗仪式的重要组成,在舞蹈艺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脱离既定的仪式成为特色鲜明的民族艺术。比如:水族《铜鼓舞》本是源于祭祀活动中的器乐击打行为,在历史演变中成为简便易学的民族舞蹈艺术,而佤族《甩发舞》则源于佤族妇女洗发梳妆习俗,而后发展为姿势优美的舞蹈。其次,在民族民俗活动中传统舞蹈本身作为重要的有机体被不断地传承,成为地域特色鲜明的舞蹈艺术。比如:白族舞蹈《绕三灵》本是祭祀舞蹈,只是随着群体艺术审美的变化而不断艺术化、规范化[6]。再者,在繁杂多元的民俗活动中,独特的民俗行为在群体的艺术抽象过程中不断演变为妇孺皆知的舞蹈艺术。比如:独龙族早期舞蹈“纳目萨”多源于巫师巫术,但随着独龙族群众舞蹈艺术认识水平的提升,其舞蹈逐渐脱离巫术成为群体娱乐活动。总之,民族舞蹈作为民俗文化的“活招牌”,在民俗文化的岁月洗礼中也不断进行着艺术本身的“吸收”与“融合”。但是,民俗文化作为民族舞蹈的生命线和显性主题始终被传承,成为跨区域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元素。
二、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文化定位
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文化定位是构建其文化体系的窗口。从肢体艺术、习俗承载、功能导向的艺术品位审视民族舞蹈的文化定位,理应是艺术、情感、习俗的三维体。从艺术角度而言,民族舞蹈毫无疑问是民族群体最为智慧的艺术瑰宝,是民族群体艺术审美的历史产物。特别是民族舞蹈同养生保健、体育活动、文学艺术的有机衔接,使民族舞蹈的艺术品格,超脱了肢体语言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永存的艺术精神。在民族舞蹈文化的凝聚过程中,服饰文化、音乐文化等先后融汇交织,成为民族艺术文化共同体不可磨灭的灵魂。地域文化、服饰文化则同民族舞蹈艺术毫无保留地衔接。比如:藏族《牦牛舞》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青藏高原、游牧文化、藏域风情和豪爽的藏族儿女。可见,民族舞蹈是一种复合型民间艺术[7]。从情感的维度而言,民族舞蹈通过地域性道具及风格的汇聚,逐渐成为折射群体内心情感的镜子。一方面,民族舞蹈在群体生活的不断融入中成为彰显民族秉性的旗帜。比如:蒙藏地区群体性格豪爽,舞蹈演绎对民族秉性一脉相承。蒙古族《训马舞》热情奔放,将蒙古族同胞热情、爽快的性格诠释得无与伦比。另一方面,民族舞蹈折射着群体别样的情感表露,“喜而生悲,因悲而舞”与“悲而喜舞,舞却生哀”成为其舞蹈艺术情感最为迫切的写实,基于文化视域下的民族舞蹈诚然是艺术情感文化的典范。从习俗的角度而言,民族舞蹈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集合。无论是世俗文化还是宗教文化民族舞蹈均能通过舞蹈的姿态演绎[8]。比如:哈尼族舞蹈《棕扇舞》作为祭祀舞蹈,除舞蹈艺术文化的映射外,还承载着独特的图腾文化,棕榈叶充当白鹇鸟羽翼,而白鹇鸟则是哈尼族吉祥物,反映了哈尼族以白鹇鸟为主的原始图腾崇拜。总之,文化视域下的民族舞蹈是萃取民族文化、构筑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见证,而审视民族舞蹈文化定位是追寻民族舞蹈文化隐含的不二法门。
三、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文化蕴意
以文化视域审视民族舞蹈是其艺术特色和文化点缀的必然结果[9]。一方面,民族舞蹈“悲而起舞”的艺术假象只能以文化维度考量。比如:大理白族群众舞蹈《搭高锅》同土家族《跳丧舞》类同,抛却习俗文化是难以权衡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主旨的。另一方面,不论是早期民族舞蹈的民俗文化承载,还是当前民族舞蹈的文化映射,习俗文化是民族舞蹈永恒的生命力。比如:藏族《螭鼓舞》通过不同环节反映了藏族群体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因此,从民族舞蹈的文化机能剖析,民族舞蹈文化的蕴意是实然文化与应然文化的有机统一。
(一)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应然文化
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应然文化理应包含其艺术本能文化的基本机能、艺术审美文化及艺术所延伸的节庆文化。
民族舞蹈艺术的自我本能文化是其应然文化的基础。民族舞蹈艺术的自我本能文化以舞蹈艺术的显性文化和主题性内在文化为基础,民族舞蹈的显性文化是指艺术主体性文化,而民族舞蹈艺术的主体性文化,则是舞蹈艺术在演绎过程中的艺术要素,是对民族舞蹈艺术要素的单项性文化考量[10]。一方面,民族舞蹈通过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和肢体动作,映射合乎舞蹈艺术衡量的舞蹈文化,即从艺术、服饰、音乐等多维度的评估。比如:哈尼族《棕扇舞》中群体服饰色彩的搭配以白色为主,反映了哈尼族注重冷色调的色彩忌讳文化。另一方面,民族舞蹈以其演绎的动态变化和艺术氛围,映射着舞蹈艺术的主体性文化。比如:鄂伦春族舞蹈《树鸡》具有体育游戏性,反映着鄂伦春族独特的文体文化。这些民族舞蹈的艺术元素中特意塑造“独特的情结”以彰显舞蹈艺术主体性能,或以道具透析、或以服饰突出、或以舞姿示人。总之,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显性文化基本能以文化的可视化符号彰显。
民族舞蹈的主题性内在文化是以舞蹈的本源文化和潜在文化表现为基准,是民族舞蹈应然文化跨艺术性的直接反映。比如:哈尼族《棕扇舞》其本源文化以民族图腾崇拜为主,而大理白族《巫舞》和《花宝花舞》虽舞蹈旋律、节拍颇为神似,但是其内在主题性文化却截然不同,《巫舞》以本主崇拜为主,《花宝花舞》则以小乘佛教为主。此外,民族舞蹈的主题性文化还体现在舞蹈的用途当中,从而蕴含着不同的民族文化机能,大体包含:丧葬文化、婚嫁文化、祭祀文化等,比如:土家族《跳丧舞》其主题性无外乎丧葬文化。
民族舞蹈艺术群体审美文化的聚集是其应然文化的关键。一方面,民族群体对艺术的审美诉求决定了舞蹈表演的基本格局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民族群体的舞蹈审美思维,决定了民族舞蹈艺术发展的基本走向,镶嵌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节庆文化是民族舞蹈应然文化的核心[11],是民族舞蹈赖以发展的基本空间,节庆习俗为民族舞蹈开辟艺术平台的同时也为民族舞蹈注入了文化灵魂。比如:傣族《依拉贺舞》多见于傣历“开门节”,其艺术的改造与文化精髓的植入,均以节日文化的变迁为主。
毋庸置疑,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应然文化是艺术辐射维度中社会文化机能的有机吸纳,洞悉民族舞蹈艺术的应然文化是挖掘舞蹈精粹的必然捷径。
(二)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实然文化
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舞蹈的实然文化则超乎了艺术的本能,成为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凝结的驱动力。首先,民族舞蹈在艺术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将民族习俗文化内化,成为民族文化的“招牌”,特别是民俗舞蹈在岁月的洗礼中成为民族群体文化认同的桥梁。其次,在泛民族化舞蹈和现代民族舞蹈的市场化运行中,以原生态民族文化为精髓的民族舞蹈,成为民族精神文化认同的符号。再者,民族舞蹈作为民族艺术文化的混同,蕴含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机理,在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中,民族舞蹈的实然文化潜移默化地聚焦在艺术的骨骼中,散发着超乎艺术范畴的文化自信。
因此,基于文化视域下审视民族舞蹈艺术,要以舞蹈艺术的实然文化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民族舞蹈的内在文化内涵,这是新时期构筑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诉求。
总之,以文化的维度和艺术广度认知民族舞蹈是挖掘其精髓,洞悉其发展脉络,保持其族群秉性,构筑其原生态艺术精粹的必然切入点[12]。在新时期民族舞蹈的跨区域性商业化运作背景下,以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民族舞蹈的历史记忆,构筑民族舞蹈的文化脊梁是弘扬民族舞蹈艺术的根本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