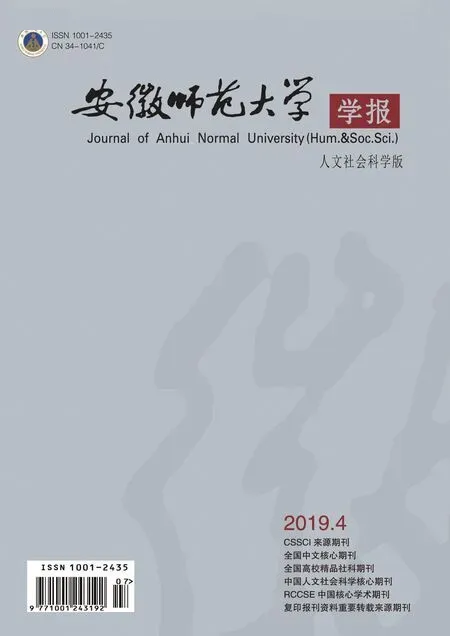论荀子的“解蔽”之方与“治气养心”之术*
2019-03-15匡钊
匡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倾向将荀子所关注的心灵的思知层面上的内容与孟子所言的心灵的先天道德能力对立起来,视为这两位儒者的根本分歧所在,如徐复观便判定:“孟子所把握的心,主要是在心的道德性的一面;而荀子则在心的认识性的一面;这是孟荀的大分水岭。”[1]146牟宗三也有类似的评价:“荀子只认识人之动物性,而于人与禽兽之区以别之真性则不复识。此处虚脱,人性遂成漆黑一团。然荀子毕竟未顺动物性而滚下去以成虚无主义。他于‘动物性之自然’一层外,又见到有高一层者在。此层即心(天君)。故荀子于动物性处翻上来而以心治性。惟其所谓心非孟子‘由心见性’之心。孟子之心乃‘道德的天心’,而荀子于心则只认识其思辨之用,故其心是‘认识的心’,非道德的心也;是智的,非仁义礼智合一之心也。可总之曰以智识心,不以仁识心也。”[2]224这些评价,只看到了荀孟之间的区别,却没有足够强调荀子所言思知与道德实践之间的连续性。前一方面的内容早为人所熟知,而从后一方面来说,无论是荀子对于人思知能力的培养,还是孟子对于人道德能力的发展,均服务于人格塑造和德性养成——更精确地说,荀子给后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更关注理智德性的获得,而孟子则更关注道德德性的获得。[注]儒家对于两类德性的可能区分,相关讨论参见拙文《早期儒家的德目划分》,《哲学研究》2014年第7期。但是作为儒家的荀子,在追求理智德性的时候绝对不会放弃对于道德德性的追求,这正如荀子既有对于心之思知的训练,也有对于“治气养心”的关怀,甚至我们可以从荀子本人的著作中推断,他应该已经看到了上述两种精神修炼技术之间的连续性,行道首先要知道,伦理实践离不开理智的指引。此外值得说明的是,虽然荀子在对于人心的看法方面与孟子存在巨大差异,但如果他从自己心有思知能力的立场再前进一步,如苏格拉底所暗示的那样,主张心灵同样具备某些先天的知识,那么他与孟子之间立场上的差异就会变得非常细微了,先天的道德能力与先天的道德知识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实践上的侧重略有不同而已。当然荀子虽重视心知的能力,但也并未像古希腊人那样给予人的心智过多的信任,而上述可能性也未曾出现在儒家思想中。
一、心何以“知道”
从以上角度来看,在以“养心”为目标的“心术”当中,荀子所看重的,无疑首先乃是心能“知道”与如何“知道”。荀子有言:“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荀子·解蔽》)暂时不考虑“心术之患”的特殊说法,荀子所知之道,当然还是判别是否的标准:“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于知道。”(《荀子·解蔽》)荀子继续主张“人何以知道?”(《荀子·解蔽》)的关键在于“心”,这个有思知能力的人心,因思而“知道”,进而遵循“道”,并据此改变自己的方式便是“伪”:“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荀子还认为人格中美好的品质也是被创造出来的,所谓“善者伪”(《荀子·性恶》),这种显然超出知识意义之上的价值创造首先也取决人心的思知能力。既然人心是一切问题的起点,荀子便有必要对其加以更细致的分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荀子·正名》)这里出现的“性”“情”“虑”,是从三个方面对人心加以总括性的说明,“性”所表征的是心的生命禀赋的基底,在此基底上,心所具有的第一方面内容则是情感、情绪意义上的“情”,而对于“情”的进一步处理,便产生了第二方面,即思知层面上的内容“虑”。荀子认为思虑与情有关,显然与《性自命出》中关于“情思”的种种说法有关。稍后荀子继续将对心的分析扩展到“欲”或者说欲望上面:“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在荀子的这个分析心的观念谱系中,“性”“情”“虑”与“欲”,均不脱离生命禀赋的先天性,比较重要的看法则在于,在这些先天的、价值无涉的内容中,有的任其发展便会导向负面效果——比如“情”与“欲”,而其他的则是引导人趋向“道”的积极因素——比如“虑”。心之思虑,也被荀子称为“征知”:“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荀子·正名》)荀子在这里将“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和“说”“故”都和心联系在一起,利用对后面这些本存在于论辩环节中内容的了解,继续扩张了心之思知能力的范围。
对于拥有上述能力的人心,荀子依然主张其对人身体的支配:“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这个定位近与稷下黄老学之《管子》“四篇”中“心体君位”的思想有关,远与《国语》中“正七体以役心”的说法相先后,而从儒家内容的思想传承来看,则与郭店简书中的内容密切相连。对此荀子在《天论》中也有类似表达:“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统五官,夫是之谓天君。”人心的能思虑的方面,对于人心情、欲的方面还有绝对的控制能力,荀子举生死为例说明了“治乱在于心之所可”的道理:“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荀子·正名》)这里荀子提出的最为重要的观念,便是文中所谓“理”,心的思虑活动,正是因为合乎理才相对于“欲”位于更高的“止之”“使之”的地位。理在荀子这里归并于道的范畴之下,心能“中理”,不外还是心能“知道”的意思。
荀子对于论证活动本身给予高度关注,而这方面内容当然也与心之思知能力密不可分。不但前文涉及的“说”“故”,包括“辨”“辞”之类的内容也都与心灵有关:“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这里暂不对荀子所使用的用来表述论证诸环节的术语加以分辨,重要的是荀子将其视为“心合于道”的标志,这等于是为“知道”设立了可以实际把握的客观标准。荀子对于心之思知层面内容的思考,在儒家学者中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致。
荀子思考中更重要的内容在于心如何“知道”,这对等于获得理智德性的精神修炼,而荀子对这一方面的精神修炼的见解,可以分解为前后两个环节:先“解蔽”,其次达到“大清明”。曾有论者从传统上认识论的角度总结先秦诸子对心的思考:“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的认识论,关注的主要是知识的来源和求知的方法、途径等问题。……人们着重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妨碍正确认识的因素是什么,二是认识主体——‘心’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才能获得正确认识。”[3]105可以说这两方面内容,在荀子的思想中都有明确反映。就“妨碍正确认识的因素”而言,白奚认为在先秦的思想谱系中,哲人们有大量可从此角度加以理解的看法:“在妨碍正确认识的因素(即认识为什么会陷入错误)这个问题上,……如慎到所谓‘建己之患’与‘用智之累’,宋钘所谓‘宥’,庄子所谓‘成心’,《管子》所谓‘过在自用’和‘去智与故’,韩非所谓‘前识’,荀子所谓‘蔽’,《吕氏春秋》所谓‘尤’与‘囿’等。”[3]106专就荀子而言,问题自然便集中在应“解”之“蔽”,也就是荀子所谓:“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对于何以会出现“蔽于一曲”之“患”,徐复观以为是由于“心的认识力之不可信赖”:“《解蔽》篇说‘圣人知心术之患’,术是田间小径,心术是指心向外活动之通路而言。心术之患,正指的是心的认识力之不可信赖。”[1]148这里徐氏将“心术”这个术语所指的对象看窄了,荀子所要说明的,乃是整个精神修炼过程中都可能出现问题,只是这些问题首先会表现在思知当中,也就是怀疑人心有“蔽”。但这些“蔽”,并不意味着人心本身的思知能力并不可靠,对于人身之“君”“主”,荀子实际上并未表现出任何的不信任,甚至随后指此心:“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从上述言论可以推断,在荀子看来,心灵完全是自我做主的,至于影响其正确判断的,并不是心灵本身的天然缺陷,只是由于受到了蒙“蔽”,而这些“蔽”一旦解除,心本身则呈现出“大清明”的状态。
荀子在《解蔽》开篇不久便为我们列举了“为蔽”的十种原因:“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而上述这些原因除“欲”“恶”之外,显然不能被简单归于心灵思知能力的缺陷,更多则与经验上的差异有关,用荀子自己的话说,“蔽”的直接来源就是“万物异”的客观状况,而人心只要面对这些“异”便不免受到负面影响:“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如果我们有能力排除上述妨碍正确思考的因素,那么心便能“知道”,而这也就解决了“如何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问题。有论者以为:“战国中后期的思想家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认识的主体——‘心’上,都认为‘心’处于某种特定的理想状态便能获得最高的修养,也就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如庄子所谓‘心斋’,孟子所谓‘存心’‘养心’,《管子》所谓‘心处其道’‘虚素’,荀子所谓心之‘大清明’‘虚壹而静’等。”[3]107上述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不同性质的“心术”混淆在了一起,抛开庄子、《管子》不谈,孟子所谓“存心”“养心”与荀子所谓“大清明”“虚壹而静”相比,强调的乃是不同类型的精神修炼工夫,前者专注于道德德性的获得,与“气”的修养相关,而后者专注于理智德性的获得,方与“思”的修养相关。
如果说“解蔽”只是荀子眼中与思知有关的精神修炼的第一个环节,那么随后的环节便是心灵在摆脱“蔽”的影响后达到“大清明”或“虚壹而静”的状态,而后一种状态既是对“蔽”的克服,也是对心灵先天能力的呈现。荀子在讨论过种种之“蔽”以及相关的例子之后,从三个方面将这些因素总结为“臧”“两”和“动”:“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荀子·解蔽》)将这三方面负面因素分别加以克服,便达到“虚壹而静”的理想状态:“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荀子·解蔽》)
就荀子所谓“臧”“两”“动”而言,“臧”之所指乃是人心中因原有知识而带来的主观性,而首先只有排除这种主观性使心“虚”才是正确的认识“道”的方式。至于“两”指的则是不同的意见,前面提到的荀子认为“为蔽”的十种原因可归结为一个“异”字,而此“异”实际上也就是所谓“两”:“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荀子·解蔽》)我们的目标便在于,设法避免其相互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让两种不同的意见达到统一之“壹”。最后所谓“动”,指的则是各种幻觉或错误信息的不良影响,设法避免上述错觉而“静”心,对于“求道”而言也是必须的。对于心灵围绕上述三方面所展开的活动,早有杜国庠继郭沫若之后注意到荀子相关思想与以《管子》“四篇”为中心的稷下黄老学之间的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荀子的思想会与稷下黄老学发生联系并不奇怪——稷下学宫的存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具体就其思想关联方面的细节而言,杜国庠曾从传统上认识论的角度详细讨论了荀子所谓的“虚壹而静”。[4]134-157“虚”向来是一个道家的说法,向上很容易回溯到《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的言语,而《管子·心术上》中也有“虚其欲,神将入舍”的说法,杜文认为此“虚”与宋子所讲的“情欲寡少”有关——这大概是受到郭沫若对于《管子》“四篇”作者不太可靠的考证影响的错误结论,不过他却正确指出,与上述思想相对,荀子并不主张单纯的“去欲”,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不以所已臧害其所将受”(《荀子·解蔽》)表示的是对于人心主观性的拒绝。至于“壹”的问题,杜文注意到《管子》“四篇”中所谓的“一意专心”之类的说法重点在于养生,而荀子则与此相反,完全是在思知的意义上主张统一不同的观点,“不以夫一害此一”(《荀子·解蔽》),但却并不了解,荀子所强调的思知上的统一,仍然具有与《管子》相类似的精神修炼意义。同样,杜文也发现对于“静”的看法荀子也大不同于《管子》,《管子》“四篇”旨在以静制动,以静养心,如《管子·内业》所谓:“凡道无所,善心安处,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心能执静,道将自定。”荀子的主张“不以梦剧乱知”(《荀子·解蔽》),却是在提倡一种积极意义上的“静”。总之,杜文认为荀子强调心积极的认识作用,而《管子》“四篇”则完全停留在虚静无为的道家立场上。抛开这种立场上的差异,荀子对于“虚”“壹”“静”的了解,都带有主动消除主观性、统一不同观点和摆脱错觉干扰的积极意义,而他对上述内容的看法却并未停留在传统的认识论层面而与修身有关,这些与思知有关的精神修炼,仍然是以德性的获得、人格的塑造和人自身的改变为目标的。
在荀子看来,如果我们的认知心能达到上述杜绝“臧”“两”“动”之影响的状态,便是达到了“知道”所必须的“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睪睪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夫恶有蔽矣哉!”(《荀子·解蔽》)荀子对于这样的无蔽之“大人”予以了充分的信任,而此等人也因此由普通意义上的“人心”而进于“道心”了。荀子极力赞美内心掌握“道”之精微者,对于这样的人他在《解蔽》的后文还以庄子般的口吻称之为“至人”。当然这样的“至人”绝非翱翔于莫可名状的虚静状态的道家人物,在荀子这里,他仍然是立足于仁德的儒家圣人,虽然此圣人因为对于外在的道的依赖而不免显示出一些“无为”“无强”的道家风格:“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荀子·解蔽》)
二、从养生到修身
荀子虽然最为重视心灵的思知能力与相应的精神修炼,但他却并未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严格来说,这个层次的精神修炼,可能只是荀子所设想的改变自己的努力的起始,而在围绕思知展开的修养之后,还有更进一步的后续工作。除了这些与理智德性的修养有关的“心术”之外,不曾放弃对儒家传统道德德性之追求的荀子,同样考虑到了与道德德性有关的精神修炼技术,即那些与“气”有关的修养方式。对于后一种修养方式的思考,荀子称之为“治气养心”。
在讨论“治气养心”之前,荀子先提出了“修身自名”的问题,并将其与“治气养生”对举,统称之为“扁善之度”:
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在这个“扁善之度”的题目下面,荀子首先对比了两类不同追求的“修身”:一是道家式的,以追求“长生久视”为目标的“治气养生”,这种“修身”的目的与早先的老子一样,重点在于效仿彭祖长久保存肉体生命;一是儒家式的,以追求“礼信”为目标的“修身自名”,这种修身的目标则与先前的孔子一样,重点在于追求德性。荀子将前一种“修身”完全纳入到后一种修身内部,这等于是取消了其独立的地位与意义。
在上述言论中,荀子实际上提出了两个论点。首先指出了修身活动的用意所在,在与“气”有关的修炼活动中,排除了单纯以身体保存为目标的“治气养生”;其次不拘于“心术”范围,对修身活动做出了一个整体的说明,并分析了修身实践展开的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在这里真正强调的乃是被他作为所有修身活动总原则的“礼”,而非作为某一种修身技术或进路的“礼”——荀子这里所谓“礼”,与他所谓“道”是一致的,是后者的具体规范化,覆盖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其意涵超出了早期儒家“为己之学”问题域[5]内礼乐训练进路意义上的“礼”。
荀子在这里指出的修身实践所得以开展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血气、志意、知虑”这样的身体、生命或者说“性”的方面,与“食饮、衣服、居处”有关的个人与公共生活方面,以及与人的容貌姿态等有关的身体训练方面。其中第一方面与道家“养气”意在“长生久视”的传统有关,而后两方面则反映着儒家修身实践的特色,其内容远可回溯到《论语·乡党》中的各种记载,近则与孟子“践形”的说法有关,儒家从来都认为,人的内在德性应该有相应的外在反映。最终的修养原则,可被归结为以礼修身——荀子总结说,礼所代表的内容,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群体,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在荀子上述对于“修身自名”思考中,他首先对身体层面的“养生”有所关照,而这一点或许与他对于直接与生命禀赋相关的“欲”和“情”等方面内容的比较正面的看法有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上述身体层面的项目都是修养的对象,但这方面内容却绝对不是他思考的核心。儒家传统中从来都不重视独立的以肉体生命为对象的“养生”话题,而荀子也不例外,在他的思想里,这方面内容总是被归结到“礼义”的话题之下的:“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荀子·强国》)换言之,对身体层面之“养生”的要求,乃是荀子所强调的儒家所主张的“礼义”的题中应有之意: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荀子·礼论》)
礼义要求我们对于身体层面的“养生”有所关照,而这方面的重点落在不同身份、状态的人应该享受不同的生活待遇上面,至于荀子在谈“扁善之度”的时候,从修身技术角度之所以要关心衣食住行、容貌姿态这样的内容,肯定也与上述考虑有关——礼的具体要求,便包含了对不同的人应该怎样穿衣服、怎样说话行事等方面内容的规定。从这个角度讲,身体层面的“养生”的关键在于“适度”照管身体,否则“养生”的效果便会适得其反。荀子在《乐论》末尾处,便将“养生无度”视为“乱世之征”,他在其他地方还明确说到无度之“纵养”根本就是有害的:
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荀子·正名》)
究上述“养生”的负面效果的缘由,当然是因为上述“纵养”未能遵循礼义,而变得毫无正面意义。至于关乎衣服饮食和容貌姿态的修养,简单地说就是有关活动必须合乎礼义的要求,这些既涉及私人与公共生活,也与身体训练有关的实践,因统一于“礼”而最终归结到人格价值的修养上面去。
荀子在“扁善之度”的话题下面,所关注的最重要内容当然仍是儒家传统的德性寻求与人格塑造,而其对修身实践的概说,从技术上讲则早已超出了“心术”层次的内容,但是无论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运用了什么样的修身技术,对于荀子而言,在早期儒家主张“心术为主”的意义上,心在所言这些修养活动中均不会缺席:
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荀子·正名》)
相反: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养体。局室、芦帘、稿蓐、敝机筵,而可以养形。(《荀子·正名》)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原因便在于相对身体而居于支配地位的“心”。
三、“治气养心”之术与矫正性修炼
既然在“修身自名”的题目下面,无论将牵扯到何种类型与层次的修身技术,“心术为主”的立场也不会受到动摇,那么荀子紧接着在对上述话题进行全局性思考之后,便迅速转向更为专门的精神修炼范围内的“治气养心”之术,便是非常自然的。从论证策略上说,荀子显然是在上下文中将其与前面所谓“治气养生”之术加以对照,并以后者的不完备来凸显前者重要性: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刦之以师友;怠慢剽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荀子·修身》)
但荀子所谈到“治气养心”之术,如将其视为对狭义的、精神修炼意义上的“心术”的一个具体说明,则包含了一些必须加以说明的特殊问题。
荀子所谓“治气养心”涉及对人的心态九个方面的调理,其具体内容大多没有被哲人们详细地考虑到,荀子在这里对于人所可能表现出的骄傲、阴险、粗暴、诡诈、狭隘、卑鄙、懒惰、懈怠和愚蠢顽固均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但如果他的对策同样被视为与气有关的精神修炼技术,那么与以往的儒家思想相比,至少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在于对气这个观念的把握。从荀子本人对“气”的定位来看,他对这个观念把握实际上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似乎视其为春秋时代为人们所了解的“血气”——此“血气”与荀子前面谈到“扁善之度”时所用的“血气”一样,应该是属于身体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从荀子将“血气”与随后言及的一系列精神性内容并列的角度来看,他似乎又将其视为精神性的内容。以往《管子》中曾多次提及“血气”这个观念,它作为驱动生命的自然力量,本停留在质料性质的“气”的水平,如《水地》所谓“水者,地之血气”,而《内业》所谓“四体既正,血气既静”,大概还是表达了这种意义。这种身体意义上的“血气”与气息之气一样,在统一于生命现象的情况下,可以逐步与精神性的活动发生联系,而最终在道家系统内过渡到与心灵密切相关的精气。由此气也被视为精神层面的内容,而相关的修炼,也已经出现在精神修炼的范围内。这一点在《管子》“四篇”所反映的稷下黄老学思想中已经有所表现,而在儒家谱系内,从一开始引入气与相应的修炼思想,所看重的便都是超出身体之上的精神层面上的气——无论《五行》中的“德气”说,还是《孟子》中的“浩然之气”,都应作如此看待。也就是说,在稷下黄老学的某些部分和全部早期儒家的思想当中,血气与精神性的气的区分非常清楚,但在荀子这里,从他对“血气”的前后用法来看,上述区分却显得有些含混。会出现这种状况,或者说荀子坚持讨论“血气”,并将其与种种精神性内容并列,可能与他一贯强调人的生理层面的生命禀赋有关,也可能与他对以往儒家围绕“气”展开的种种言说的“隐约”有所不满有关,但从早期儒家的整体思想状况而言,荀子论气的方式,却反而显得有欠流畅。
第二个区别在于对与气有关的修炼方向的把握。早期儒家以往与精神性的气有关的修炼,清晰地指向道德德性的获得,而这一特色在荀子这里也完全无从寻觅。荀子谈到的“治气养心”的九个方面,包含了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内容在内:其中既有关乎理智德性的成分,如“知虑”“思索”,也有关乎道德德性的成分,如“勇敢”,还提到了诸如“师友”这样的德性典范。如果将这些内容都与气的修炼联系起来,则以往儒家与道德德性有关的修炼指向,便完全不见踪影了。从孔孟之间儒者较早时引入以“内外”为根据的新的德目的分类标准开始,孔子本人确立的对于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划分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而上述划分因被遮蔽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推手,则是孟子。早期儒家发展到荀子这里,上述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之间的划分,可能已经被完全遗忘,而他只是无意识地遵循儒家一贯的在精神修炼领域内的工夫区分,分别谈论着与思知有关的“解蔽”工夫和与气有关的“治气养心”工夫,但对于后一类工夫的特殊针对性却已经没有了了解。值得一提的是,从《荀子》中《解蔽》的文本和《不苟》中关于“诚”的言论来看,推测荀子最重视与“思”有关的精神修炼工夫,并认为这种工夫对其他德性的获得具有毫无疑问的优先性,大约既不违背荀子的本意,也不与上述不同类型德性间的逻辑关系相冲突。更有意思的是,荀子在上述方面与孟子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实际上在并不理解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区分的基础上,仍然都遵循了相应的精神修炼工夫方面的分别,只是前者更强调与“思”有关的工夫,而后者更重视与“气”有关的修养。
第三个区别在于对修养的整体方向的把握,而这个区别甚至并不仅仅局限于“治气养心”的范围之内。以往儒家在讨论与气相关的工夫时,在将气作为德性实现的动力性因素的意义上,对于有关实践的说明总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而荀子这里提到的修炼技术,则完全是从消极的、矫正性的角度着眼。在以往早期儒家的“心术”领域,实际上一向存在一类以消灭精神活动中的不良倾向为目标的修炼,如已经探讨过的《大学》之“正心”、孟子之言“寡欲”和荀子之言“解蔽”都是从这种矫正性的角度出发的精神修炼工夫。这一方向的思考仍然可以回溯至孔子本人,无论“克己”的教导,还是所谓“子绝四”的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都是要我们努力去消除一些有不良倾向的内心活动对人格完善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类型的消极的精神修炼实践,以往似乎被视为相对独立的活动,而未将其与“思”或“气”直接联系起来,到了荀子这里,则不但将其与气的修养相联系,也如前文所未及言明的那样,与思的修养相联系。可能是出于这样的立场,荀子在谈论与气有关修身技术时,并未用如孟子那样的“养气”的说法,而是用了更为严峻的“治气”的说法,这个“治”字,恰与孔子以往所言“克”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矫正性的或者说负的方向思考精神修炼技术,应该说在荀子这里表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他的精神修炼工夫严格来说,都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着眼的。这种思路在早期儒家中的进展,除了前文所涉及的内容之外,还曾经很明显地留露在郭店简书《性自命出》当中: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
简书文本中对于“性”的塑造养成,不但曾运用“养之”“长之”这样建设性的说法,也运用了“逆之”“厉之”这样矫正性的说法。如果说上述正面或负面活动的治理对象还是整个人性,那么在狭义的“心术”范围内,《性自命出》也曾提出过一些批评性的建议:“凡用心之躁者,思为甚。用智之疾者,患为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这些直接针对“用心之躁”“用智之疾”的反思,完全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来荀子对于精神修炼技术的矫正性立场。
在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全幅领域内,上述矫正性的立场也以其他的方式存在,最初《论语·阳货》中便有对孔子所谓“六言六蔽”的记载: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在这里以笼统的方式,从反面说明了“学”对于人格塑造的重要意义,而所称“蔽”,则正与后来荀子相呼应。《性自命出》对于修身实践中“不应有”的行为,除了上文言及的内容之外,还有如下说法:
身欲静而毋□,虑欲渊而毋拔,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壮而毋拔,[心]欲柔齐而泊,喜欲智而亡末,乐欲怿而有志,忧欲俭而毋惛(闷),怒欲盈而毋希,进欲逊而毋巧,退欲循而毋轻,欲皆度而毋伪。
这里“不应有”的行为,不但涉及人心,也与“身”“行”“貌”大有关系。在《尊德义》中,与“应有”的礼乐教化相对比,还提及了一些“不应有”的教学项目:
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教以辩说,则民艺□长贵以忘;教以艺,则民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讦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远礼无亲仁。
这也是主张从整体上将一些被认为起负面因素的内容,从修身的全部活动中排除出去。结合《性自命出》中出现的一个“刚”“柔”的说法:“刚之柱”“柔之约”,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儒家从来就是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提倡修身实践,其中建设性的、积极的、正面的方法乃是“刚”的方法,而矫正性的、消极的、负面的方法,乃是“柔”的方法。从这个角度就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三条进路而言,其中精神修炼与礼乐训练可谓刚柔并济——前者无须多言,而后者则如《论语·乡党》中暗示的那样,既包括对于适当行为的指示,也包括对于不适当行为的禁止;至于经典学习大概是偏于主“刚”的方法——孔子与其后学是绝对不会故意去“攻乎异端”的。
四、创见与传承
对于自己所谈论的“治气养心之术”的具体对策,荀子最终从三个方面加以总结:“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这里第一方面仍然回到荀子将“礼”视为修身总原则的观点上,而第二、三方面内容,实际上讲的是同样的东西,荀子都是在强调学习过程中指导者与榜样的重要性。从孔子开始,早期儒家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人伦关系维度:师生关系,而对于这方面内容荀子表现出极高的重视。对于“得师”的重要性,《荀子·修身》中言之甚明:
君子隆师而亲友;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
至于所谓“一好”,则并不简单就是指“向善”,这里的“好”,仍然与作为指导者和学习榜样的师友有关,荀子有言:“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劝学》)所谓“好其人”,也就是“近其人”:“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荀子·劝学》)在荀子看来,“好人”“近人”甚至比“隆礼”还要重要,而缺少合适的人的指导,即便诗书礼乐这样的修身方式,其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所以荀子才会主张“师者、所以正礼也”,点出指导者与榜样在修身实践中的重要性,或者说师生关系对于德性养成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荀子所谓“一好”,指的应该是专心追随值得并应该追随的榜样的意思。在学习榜样与根本原则的双重作用下,荀子所谓“治气养心”之术才是以改变自己为目标的学习、修身手段,这些技术与荀子所提倡的其他诸如经典学习与礼乐训练一起,构成了他所谓“以美其身”的“君子之学”(《荀子·劝学》),而荀子将其清晰地定位为“古之学者为己”的学习——这无疑是先秦最后的儒家大师对孔子所开辟的反思人之应是以及如何成就这种“应是”的一个有意识的回应,从孔子到荀子,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问题域始终呈现出相对清晰的形象。
继续就心术范围内的修身技术而言,荀子对于先前儒者已经讨论到的某些精神修炼方法也多有涉及,比如在荀子这里,“省”和“诚”的工夫的重要性,可能就仅次于“解蔽”和“治气”。荀子多次强调“自省”或“内省”,如他在《修身》中谈到:“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在《王霸》中荀子还有“内自省”的说法。荀子对于修身工夫意义上的“自省”了解,无疑来自对孔子先行思想的继承,并十分明确且有意识地将其置于“学”或者说“为己之学”的问题域中:
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
这里荀子“博学”而“参省”的说法,正是对孔子讲求“学而思”的一个回应。至于荀子对“诚”的强调,如他“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的判断,则一方面继承了孔孟之间儒者的观点,另一方面则也与自己对与“思”有关的工夫最为关注有关。徐复观早已看出,在荀子这里,“‘诚心守仁’,‘诚心行义’,这是从工夫上以言诚”[1]93,而这种与理智德性的获得相关的工夫,在荀子看来还会进一步产生各种外在的效果,比如显示于容貌、言语之中,体现在父子、君臣的关系之间。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可能存在于荀子和思想反映在郭店简书中的那些一度从历史上失踪的儒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比如荀子还谈到:“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荀子·解蔽》)他将“仁者之思”“圣者之思”与精神修炼方法联系起来的说法,明显与《五行》经部中出现的“仁之思”“圣之思”这类工夫有关,乃是与前述“诚”的工夫同类,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围绕理智德性的获得而展开的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