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本源,重理根脉
——刘醒龙写作的变与常
2019-03-13■
■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刘醒龙的故乡在大别山区,他的作品大体写的是大别山区的景和人,写的大别山区的历史和现在。在《蟠虺》之后,本以为他的创作会别开生面,展示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景致,不再执着于大别山区,不再纠结于村镇的人与事;比如继续写些都市生活、学术故事或考古解密之类的作品——毕竟他在武汉生活了20多年,一直工作在文化圈——正如在神秘的“大别山之谜”系列之后他突然转向了贴近现实的《村支书》和《凤凰琴》等“分享艰难”式作品。虽然转向太急促,让读者缺乏心理准备,但无疑他是充分具备能力的。没想到,《黄冈秘卷》又带我们回到了曾经的村镇,回到了曾经熟悉的人群中。只是这次他走得更远,步伐更大。如果说“大别山之谜”系列立意于寻找原始、蒙昧的文化之根,现实主义系列作品在于展示苍凉、朴素背景下脊梁式人物抵抗磨难的活动,《黄冈秘卷》则旨在为地域黄冈和“我们的父亲”立志、著书,地域特色与文化的传承使作品充溢着空间的广阔与丰盈,历史的绵延与承继。
刘醒龙将其《致雪弗莱》及之后的作品归为第三个阶段的创作,综观其此期的作品,虽然在题材方面差异巨大,但不离其宗:回归本源,从宏观上寻求一套价值理想和道德观念,规范家庭、社会和个人。如果说《致雪弗莱》是探讨人的组织与宗族两种属性和价值观念的对抗,《圣天门口》则是回归历史,回到民间,探讨历史与文化前进的真正力量与价值准则,《天行者》探讨文化传承的真正力量,《蟠虺》回到楚文化的源头,通过曾候乙尊盘的真伪,探讨学术道德与人性伦理,《黄冈秘卷》则再一次回到地方,从地域文化中寻求人格与文化的踪迹。这种回归,表层上是对地域文化的回归,实质是寻找地域文化中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契合点,寻求时代所需要的人物形象与价值观念。
纵览刘醒龙的创作,似乎变化明显,但有些东西始终坚持:对根的追随和对伦常的思考,对故土或故人的感念,只是这种追随和感念在世事人心的变幻与个人成熟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充实与升华。如果说早期作家对世界充满迷惘,如孩童般地面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那么中期则如青年般地面向社会和世事,思考着规则与榜样,那么近期作家则如中年一样地思考着世界秩序、人间伦常,进入了创作与人生的总结收割阶段。
一、反复书写
在刘醒龙此阶段的写作中,一个最为明显的现象是:对此前作品的再次利用。有些情节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有些材料在他的作品多次被运用,有些故事在他的创作谈中多次谈及。当然这种反复书写不能简单认定为重复或自我抄袭。在音乐上,同一曲调的重复与回旋是乐曲惯常的表达方式,它不仅有抵抗时间与空间的艺术效果,更通过重复与回旋来转化与衍生出新的内容。诗歌也是如此,反复不仅在同一首诗歌不同章节出现,在同一组诗歌之中也经常有相同诗句的复现。何况,在音乐和诗歌中,相同内容因轻重、长短和节奏的不同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效果。
在刘醒龙的创作中,既有对前作的扩写、改写,也有同一情节的多次出现。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其2009年“茅奖”作品《天行者》是在其1992年中篇《凤凰琴》基础上的拓展,其它,如2018年出版的《黄冈秘卷》是对20年前《致雪弗莱》的拓展,《痛失》是对《政治课》、《往事温柔》是对《倒挂金勾》的拓展。这几部作品都是在大体因袭前文的基础上所作的扩充与深化,原作只是后作的一个章节。
改写方面,在2005年出版的《圣天门口》中能看到1991年出版的《威风凛凛》的大体故事框架和更早时期作品《牛背脊山》的相关故事片断。《威风凛凛》提供了小镇三方的势力比拼架构,《牛背脊山》提供了抗战与文革时期的奉献与情怨。
其他反复重现的情节,如忧伤的口琴在《凤凰琴》、《清水无香》、《弥天》、《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都一再吹奏,作者在创作谈中也多次提及口琴是其有意设置的乡村文明抵抗城市文明的符号。
和口琴的反复吹奏一样,在创作谈中,刘醒龙也反复提及到他作品中重复部分的用意。他多次谈到爷爷代表的传统文化、奶奶代表的温馨与包容对自己的影响,及不知名诗作《一碗油盐饭》给自己的感动和启示,并在《天行者》和散文集《一滴水有多深》中反复阐释这首诗。在创作谈中,刘醒龙一再提及的另一些重要话题还有已故《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对其作品中“大爱”与“大善”的评述及其作品对高贵、圣洁的自觉追求。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作家对前作的反复书写,对此前记忆的一再提及,正说明作家对这一些情节与记忆的念念不忘,及这些记忆对作家的重要价值。它们如同一片人生富矿,作家无比珍爱,不忍舍弃;反复揣摩,一再挖掘。
这些被反复书写的部分,有写实,也有虚构;同是虚构,虽然在题材上并不一致,故事情节相距甚远,但从其近期(第三阶段)作品观照,总体而言,都是回到历史与地域的乡土(《蟠虺》是回到楚文化)去探讨人体与群体的生存智慧。
二、推陈出新
《天行者》是最为读者熟知的一次对前文本的回归。在《天行者》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接受《京华时报》(2009年7月30日)采访时刘醒龙说:“早在1992年《凤凰琴》在《青年文学》第五期发表后,编辑就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我续写《凤凰琴》,我没有赶那个热潮。这里有我个人性格原因,不喜欢随大流。然而,这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有动手写作的欲望。”在采访中,他说,写《凤凰琴》只是心存感动,而写《天行者》则是心存感恩:当汶川地震摧毁了乡村校舍,夺走了樊晓霞等民办老师的生命后,他看到了乡村教师命运的本质;他要为默默奉献的乡间民族英雄立传,记录他们的历史,传递他们薪火相传的文明之火。这段话既表明了作者长期以来续写前作的愿望,也表明了作者回归此前作品有很多背后的推动因素——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在作家手中,然而,这种回归并非简单重复,而是推陈出新或完全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文本。如果说《凤凰琴》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民办教师的故事,在《天行者》中读者体悟的则是一批、几代民办教师的命运与他们大善、大爱的情怀。
而《圣天门口》则应属回归的经典范例,如果不仔细研读,普通读者很难从中读出文本的承继关系。《威风凛凛》以乡村少年学文的视角记录了教师赵长子、五驼子和金福儿三股乡村势力之间的斗争,通过民间习见的“抖狠”的劣根性探讨了传统文化中恶的根源,而《牛背脊山》则以大学生的视角,揭示了革命时期不同阶层间的恩怨纠葛与革命对山村的破坏。而《圣天门口》则以天门口镇为舞台,以书香门第雪家和勇武凶蛮的杭家的恩怨为主线,通过七十余年的革命进程,叙述了雪、杭两家及社会各阶层间恩怨情仇,借“小地方”和“小人物”的历史写“大历史”,探讨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及社会伦理的合理途径及维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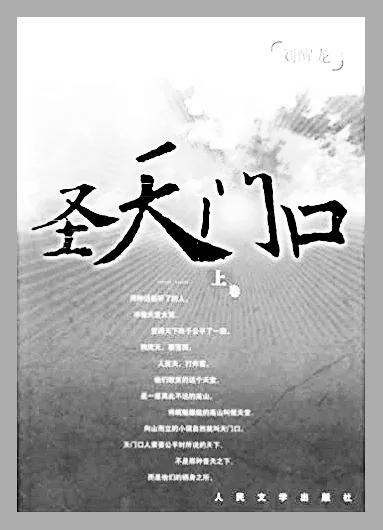
《圣天门口》
相对而言,《黄冈秘卷》对《致雪弗莱》的回归则更加一目了然,但也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本了。《致雪弗莱》通过《组织史》和《刘氏方志》两重文本讲述的是“我们的父亲”,一个黄冈人,一个坚定的老革命在组织与宗族之间的选择与回归,而《黄冈秘卷》则用《黄冈秘卷》这一文本将《组织史》和《刘氏方志》统辖其中,探讨了地域的文化品性和地域对人的规定性。
以上三部都是刘醒龙第三阶段的作品,都属于重拾此前文本的回归式作品,然而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文本上的重拾,而是推陈出新,别开生面的回归。后期文本较前期文本在思想内涵,整体格局上都较前期有大的改进。
同时,这一回归也是叙事地理空间上的回归:重回乡村,重回大别山区。地理空间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情感空间的回归。实际在《黄冈秘卷》之前,刘醒龙的《蟠虺》也被广泛看好,也让读者和评论家认为这会成为他创作上的一个分水领,从此告别大别山,进入另一个题材领域。但没想到《蟠虺》只是作家短暂的一次出门远行。即使在这部关于都市的考古题材作品中,大别山相关的情节也在文中偶有出现;从大的范围而言,《蟠虺》也是对楚文化的一次回归。继而推出的《黄冈秘卷》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回归和情感的回归,在文中和作品的后记里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感恩和朝拜。在题为《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的作品后记中,作者明确表明了为故乡立志,和黄冈所代表的“志”贤良方正的重要性。
再回顾此期刘醒龙的作品,实实在在地都有为地方写志,为人物立传,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理想。《圣天门口》通过小镇从辛亥革命以来70余年的家族和政治纷争,展示了在宏大口号与历史理性演绎中的具体历史样本,这一样本可以称之为大别山区或天门口镇的地方志,在作品中作家以“仁爱”作为治世秘方;《天行者》作者表明了其为民办教师这一无名英雄群体作传的目的,仁爱和责任是他们的行事法则;在《蟠虺》的扉页上,作家标注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的核心句子;而《黄冈秘卷》更是表意鲜明的为黄冈写志,书写地域的文化品性和确立优良的处世风范。
三、层层升华
刘醒龙对故乡大别山区的书写层层累积,反复刻划,一笔比一笔深入,每一阶段都较前一阶段更深情和深刻。在他的三个创作阶段中,虽有部分作品或短暂时期没有或没有直接书写大别山区,但作家很快就实现了叙事和情感的双重回归。总体而言,大别山也从最初的寻根式的景观和传统呈现,升华为人格化的乡土,到第三阶段,大别山成了一种文化和价值的符号和标杆。
在“大别山之谜”时期作者直面故土,直接书写大别山。这一阶段刘醒龙尚未形成清晰的创作方向和目标,他的作品整体体现出对失落的传统文化的找寻和维护,这种过程与其说是家园找寻旅程,毋宁说是一种对传奇的热衷与呼应。在作品中,景物成为核心;对景物的过分重视和对人物的忽视,对描写的热衷与叙事的薄弱都表明这一时期创作思想内涵的不足和逻辑力量的弱势,这种薄弱表明其身份定位与认同的迷茫。作品虽涉及面较广: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青年发展与社会问题、历史与创伤等都有涉及,但并未形成稳定的意图所指。虽然其重要作品“大别山之谜”系列关注是传统文化,但这种关注与其说是自发的内心诉求,不如说是时代思潮的反映;部分作品透露出为古老、怪诞而罔顾故事逻辑的特色,有为文化而文化、为先锋而先锋的趋向;对人物的兴趣明显小于景观,而对景观的兴趣则体现为对荒诞、奇异事与物的传写。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作者关注点多而杂,虽然对传统文化相对较为重视,但这种重视更多地出于跟风和个人的创作风格的营造,作家没有形成固定的人生与文化理想,尽管在多部作品中作家思想相对保守,力倡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批判现代意识现代中的唯利是图和伦理失落,但在另一些作品中,观点会有迥然的差异,甚至在同一部作品中,作家思想都处于来回游移,捉摸不定的状态。如在《河西》中钟华与十三爷两个形象的暧昧价值定位,钟华思想解放,十三爷垄断、专制、迷信;钟华唯利是图,十三爷重视文化伦理,宽厚有加;《鸡笼》中,作者在宿命论和现代意识中莫衷一是;《大水》对传统家族纷争和图腾文化也处于展览与批判之间的暧昧状态。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刘醒龙创作的迷茫期,在广泛关注的基础上,作家希望通过古老文化为切入点,来找寻打开世界和家园的钥匙,因此作家创作了“大别山之谜”系列作品。
20世纪90年代,刘醒龙创作中暧昧的文化找寻随着社会的商业化趋势而表现出更强烈的时代对抗意味,作品中文化精神直接转换成人格精神,诉诸于对理想人格形象的树立与弘扬,直接书写大别山风物改为讲述大别山人的故事。而这种理想人格的承担者则再一次回归到过去,回归到革命浪漫主义时期的父辈英雄人物角色,他们忍辱负重、力挽狂澜,无私且坚定。只是这一理想人格的完成也经历了一番漫长而艰辛的演进历程,从最初国民性批判中被打倒的父辈形象(如《威风凛凛》中的赵长子),到此后舍已为人、忍辱负重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父辈形象(如《村支书》中方建国和《凤凰琴》中余校长),再到身肩道义、默默无闻、润物无声的父辈形象(如《黄昏放牛》中胡长升和《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陈老小),这一长廊式形象谱系书写了“我们的父亲”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却足以成为时代精神楷模的品质。
新世纪以来,刘醒龙在一系列长篇作品中逐渐隐去了父亲的时代性特色和对抗性品格,改以仁爱、包容、贤良、刚毅等终极价值来重新定义其作品核心人物,作品人物形象非限定性指代(如“我们的父亲”、曾本之、民办教师群体、代表革命的法朗西、圣法的梅外婆和雪柠,代表民间暴力的杭九枫(酒疯))和空间形象的开放性特征(如圣天门口、界岭、博物馆和学术圈、黄冈故乡),使作品具有更多的普适性意味和超越性特征,表明作家的创作又一次发生了嬗变与飞跃。在《圣天门口》中,梅外婆和雪柠的包容、温馨与高贵成了抵抗暴力与黑暗的最佳良药,是传播仁慈、抚慰伤痛的最好选择;《天行者》中炼狱般恶劣背景下的不懈奉献是高贵英雄的最好的慰藉,《蟠虺》中曾本之不识时务、坚守良心、维护真理,《黄冈秘卷》中贤良方本的父亲……这些人物及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正是作家所追寻的人类普适性价值和美德,这些价值和美德也正是中国儒家传统美德之集大成,这些作品也正表明作家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回归与重新梳理。
四、审视回归
刘醒龙进入文坛适逢寻根文学盛行,他也以“大别山之谜”系列寻根作品闻名于世。此后寻根热潮散去,现实性作品随商业大潮涌现,他的《村支书》《凤凰琴》等一系列现实感较强的作品也曾弄潮一时;近年,文化考古类的作品频现,他的《圣天门口》《蟠虺》和《黄冈密卷》都可归为此类,他也可谓引领了部分潮流。但从另一角度看,他似乎变之不多,长期立足本乡本士,立足于发掘故乡的人文历史、普通人与事,寻求宣扬某种正面、积极和影响社会、人生的价值准则。但从其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整体考察,其回归寻根,回归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理念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寻根文学时期他的创作更多懵懂与随大流,价值观念波动易变,此期则变得清晰而恒定。这也清晰地展示了其创作的巨大飞跃,但同时也潜藏着某些不足。
首先,作家结构故事,把握叙事的能力浑厚、自如。此方面,《圣天门口》和《黄冈秘卷》可谓典范。《圣天门口》将70多年的历史,将不同势力,迥异的价值观,几十个性格各异,观念不同的人物从容写来;多重文本,多重线索。没有超常功力,无法做到。作品使用了其此前的多部作品中材料,如《威风凛凛》《倒挂金钩》《牛背脊山》《异香》等,但化为无形,着实令人惊叹。而《黄冈秘卷》通过“黄冈秘卷”这一文本的加入,使此前《致雪弗莱》中的立意陡然变得高妙,三重文本的利用使作品格局更加宏大。
其次,作品视野更加阔大,境界更加超迈。从以前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到此期对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对中国革命,甚至人类价值观念的整体探讨,作品更具有史诗品质与超越精神。
但不足也较为明显。首先,经营故事用力不够。《蟠虺》《黄冈秘卷》等都让读者感觉故事性不足的缺憾。其次,教化意味显露。文学无疑有教化功能,但大多润物无声。一般而言,说理意图太过明确会给人有教化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