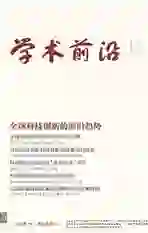科技前沿领域存在“文明冲突”吗?
2019-03-12吕乃基
【摘要】贯穿古今的科技发展主线在20世纪末出现分裂的迹象,金融危机后愈益明显,贸易战,进而技术战,科技发展不再“跨越”和“超越”,而是与文明冲突交互。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理解“分裂”之因。“内在”包括科技本身,特别是“科技黑箱”和马斯洛需求层次提升的影响;“外在”即全球化加剧国际的利益之争,涉及经济、技术和文明层面。利益、科技、产业和价值观可以在不同层面沟通不同文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用”,而且是“体”。科学活动所形成的精神和规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公约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科技前沿 文明冲突 发展路径 科技黑箱 公约数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4.003
人类社会的演化复杂而又曲折,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其原因是各国各民族自然与人文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以及由此发生的彼此间“文明的冲突”。虽然如此,其中依然有一条自古至今,跨越民族和国界,超越文明冲突,清晰可见的主线,那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这条贯穿古今的科技发展主线,在20世纪末出现了某种分裂的迹象,并且在金融危机后日渐明显,科技发展不再“跨越”和“超越”,而是与文明冲突交互。文明冲突干预科技发展路径,科技发展影响文明冲突态势。
由“超越”到“嵌入”
人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譬如根据某某“主义”的划分,但是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充满个案甚至反例,在学术界也难以形成共识。至于远古—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的划分方式,没有内涵,仅以时间划分,几近于同义反复。相对而言,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划分方式,具有较大普遍性。托夫勒的“三次浪潮”也得到普遍认可。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两种划分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对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具有超越性。
科学发展规律。大体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和知识论等四方面理解科学发展规律。本体论有量子阶梯和相关的运动形式两个视角。
先看量子阶梯的视角。近代科学以降,科学家从宏观世界感官所及之对象,如气体等入手,提出原子-分子论。20世纪初至今,科学沿量子阶梯向三个方向发展:向上、向下,以及扩展。向上,指由原子分子—生物大分子—细胞—生命—大脑……,探讨量子阶梯更高的层次,自然界中越来越复杂的存在。向下,在微观上是核与电子、质子中子、夸克,最新的发现是希格斯波色子;同时伴随着宇观尺度的推进,白矮星、中子星、黑洞;微观与宇观共同指向奇点,宇宙起源。
第三个方向是扩展。近现代科学主要是抽象,由现象揭示确定的实体、本质和必然性,20世纪后,注重研究处于不同语境中的对象、主体,以及各种关系,关注演化、非线性、混沌、分裂,不确定已经成为“原理”。
运动形式的视角是基本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意识运动,以及微观和宇观物理运动。基本物理运动包括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之所以“基本”,是因为这些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最为“简单”(其本身还有众多未解之谜),以及为其他所有运动所共有。科学从基本物理运动着手,遂有力学、热学、电磁学,随后由简至繁,逐步进入化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以及量子某某力学、极早期宇宙学等。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实际上包含了科学的所有门类。
还有跨越量子阶梯各个层次,遍及所有运动形式的复杂性科学。
认识论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两条道路”。[1]“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排除主体和语境的影响,直至“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回到“表象”,是“具体的再现”,必然涉及形形色色的语境和不同的主体。上述量子阶梯的第三个方向已经涉及这一点。显然,第二条道路必然涉及复杂性科学。
在价值观层面,近现代科学排除来自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善与美的影响,为科学而科学,求真至上。当代则要求科学从属于社会,从属于善和美。
在知识论视角,第一条道路所得到的“抽象的规定”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超越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可以共享。第二条道路回到现象,必然嵌入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受到特定价值观的选择,是嵌入编码知识。虽然“嵌入”,但由于以非嵌入编码知识为“最大公约数”,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彼此间依然可以相互理解和兼容。
上述四个视角可以归为两个方面:科学活动与科学成果。科学成果固然重要,但毕竟处于“用”的范畴;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是科学活动所培育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这是科学之“体”。
技术发展规律。技术的发展规律与科学发展规律密切相关,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与消费者,在更大范围是与社会的关系(军事技术因其特殊性而不在本文討论之列)。以下从三方面讨论。
其一,人化。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与科学发展规律同步。在工业革命前,机械技术已经在钟表、八音盒等工艺领域得到充分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热机登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角是电机,染料、尿素、诺贝尔炸药,以及20世纪合成材料,属化工技术。20世纪末,生物技术问世,直至现在的人工智能。类似的观点还有“器官投影说”,由四肢、五官到大脑。技术的发展就是朝着人的方向,人工度越来越高,也就是人化的过程。
其二,材料—能量—信息,被称为人类社会三大支柱。远古及古代,石器、青铜、铁器,以材料的进步定义人类的时代;随后是蒸汽、电气与核电,以能源定义;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与之后,电话、广播、电视问世,开启信息时代。
其三,所有的技术产品和过程在消费侧彼此相关兼容,在供给侧前后相继,环环相扣,形成越来越庞大完善的技术—产业体系。材料是载体,能源是动力,信息是沟通与整合的要素。
其四,马斯洛需求层次。如果说上述3点主要涉及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马斯洛需求层次则是技术的目的,关系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供给方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得利润。如果达到某种垄断地位,还将获得对产业链上下游和需求方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支配与控制,而是服务于利润。一旦到这个地步,就会扼杀技术发展的动力,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将打破垄断。
在需求侧,在漫长的岁月里,技术主要满足生存需求,衣食住行。近代以降,两次工业革命体现的是效率和力量。
虽然技术竞争激烈,但目标相对一致,供给方沿袭投入产出比,需求方讲究功能价格比。之所以可以“比”,是因为无论供给还是需求方,参与者在理论上平权,相互之间比拼的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沿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技术的难度不大,进入门槛较低。
综上,直至20世纪中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之前,对于所有人基本上无差别的自然界,科学活动排除个人与社会的干预,科学认识要求达到“抽象的规定”,科学知识非嵌入,以及科学精神和规范,这是科学之所以“超越”的依据。技术“人化”的成果是人的身体,除了大脑之外的器官,满足对于所有人基本上相同的生理需求、效率和力量,竞争者的目标雷同、途径相似。相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多样,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指标清晰而一致,这是技术之所以“超越”的依据。
分裂。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横空出世,在科技的发展途径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些国家因自身特殊的国情而设置防火墙以屏蔽某些网站,但并不排斥科技本身的进展;或者互不信任,如各自运行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这种新的情况在金融危机后,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变得更为明显。美国既拒绝华为5G,也不准特定国家使用本国的科技成果。不仅美国的零部件不能供应华为,还不让华为参加很多国际组织,不能跟大学加强合作。郭台铭认为,未来将有两种5G,中国5G和美国5G。一个市场生产的设备可能与另一个市场的设备互不兼容,迫使各国、各公司在技术贸易战中选边站。两家欧洲电信集团正考虑为东、西半球建立分开的业务部门。
如果说贸易摩擦偏向经济层面,那么技术战就隐隐指向“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进入了相对纯粹的科学领域。美国指责“中国利用了美国科学事业开放性”;一些华人科学家辞职或被解雇;美国限制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签证、科学设备出口审查;不准非嵌入编码知识共享,等等。
倡导开源硬件的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包云岗感叹,[2]虽然每个人都有民族、国家、宗教等多重属性,但“为全人类服务”依然是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终极目标,甚至信仰。但在今天看到的是目标的虚幻,信仰的脆弱。
单一的科技发展路径正在发生分裂,与文明的冲突相间。
分裂之因
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理解“分裂”之因。“内在”包括科技本身的发展和马斯洛需求层次,“外在”指全球化。
内在原因。在科技发展路径上,科学精神和规范依然有效,但科技本身的发展蕴含了分裂的因素。
其一,科学“向上”,进入生命运动与意识运动,技术“人化”,由身体、生理进而大脑、心理。人的身体、生理相似,大脑、心理多样。在国家层面,经济基础处于同样的“电气时代”,社会形态各异。科学的“扩展”涉及形形色色的主体及其所处之语境。
其二,在“第二条道路”上,科学回归表象,嵌入于社会,必然受到各异的制度,多样乃至对立价值观的影响。这两点是科技路径分裂在供给侧的依据。
其三,需求方的需求层次上升。严格说,需求方之需求层次上升并不属于科技本身的发展,但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世界范围,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时期,人的需求由彼此雷同的生理需求进入心理和多样的自我实现的高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小康”。经过40多年的赶超,虽然还有艰巨的扶贫重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精神生活愈益重要。心理层面需求的一大特点是多元。这一点是科技路径分裂在需求侧的依据。
还需要考虑“国家”的需求层次,譬如“富强”,由此会导致相当不同的科技路径。各種文明对个人隐私的考量也有天壤之别。
其四,科技黑箱。[3]科技黑箱可以是软件或按一定程序运行的硬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集成于科技黑箱中,使用者无需知晓,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这里就存在需求方对科技黑箱,也就是供给方的信任,是否侵犯需求方的隐私、留有后门、植入病毒。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满足需求的一端在“人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抵达心理的高度,另一方面是知识链和产业链越来越长,换言之,供给方有可能在链的“沿途”,特别是源头(如操作系统、根服务器)控制需求方。再者,低端产品知识含量少,进入门槛低,复制、仿造、“山寨”即可;随着科技黑箱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制造难度越来越大,难以山寨复制(如芯片)和替代,从而加大供给方对需求方的依赖。这就是所谓“依赖关系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4]
与此同时,科技黑箱越来越黑,供求双方的知识越来越不对称,供给方可以经由科技黑箱,在需求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支配控制需求方(如漏洞、后门)。精神需求看起来很美,但首先要实现包括可替代和透明等安全需求。
由科技黑箱引发的信任危机,给科技路径分裂的客观基础抹上了文明冲突的色彩,反过来加剧科技路径分裂的可能性。
最后,科学与技术的捆绑。科学与技术,技术一侧会更多受到文明冲突的影响,进而参与其间,可能造成某种恶性循环;而科学一侧将一如既往,超越文明的冲突。随着科学与技术日趋一体化,在科学一方必然受到与利益(利润、权力)不可分的技术的捆绑。在“向上”的路径上,譬如医学,是科学还是技术?生命科学中充溢着利益。美国NIH向中国研究者说不。科学实验随时可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技术。科学无国界正在成为往事。
外在原因:全球化。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麦哲伦环球航行,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全球化”。直至20世纪中叶,总体而言呈现三个特点:其一,在时间尺度上,各国差距大,例如可以清晰区分工业国与农业国,不在同一水平上较量;其二,在空间尺度上,世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其三,产业链短,各国的关联不密切。
20世纪末至今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一,各国虽然还有差距,但差距已经没这么大,竞争加剧;其二,回旋余地缩小,各国之间近乎贴身肉搏;其三,全球产业链导致各国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缓解了竞争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纷争,国界似乎也变得模糊。前两点致使各国的生态位窘迫,第三点实际上是各国调整自己的生态位,扬己所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位之争。
在2005年到2006年间的一个论坛上,主持人向当时微软(中国)的负责人提问:“中国什么时候能有像微软那样的企业?”那位负责人纠正主持人说:“中国已经有了,因为微软就是中国企业。”为了攫取中国市场,当时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自称中国企业。[5]然而危机正在酝酿。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其中起沟通整合作用的第三点破裂,导致关系紧张的另两点加剧,在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当选后尤甚。冲突在经济、国家实力,以及所谓“结构性”问题三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经济层面主要是贸易逆差、制造业回流、就业等,相对容易化解;国家实力关系到国际影响、国际地位;结构性问题则涉及深层的制度和价值观。
经济层面的冲突,简单说可以归结为“熵增”。在全球化中,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力要素的价格在全球摊平、趋同;这或许是“地球是平的”一言的最好注解。资本、技术、知识产权等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享受世界工厂的廉价商品之时,劳动力价格也被拉低,说得极端些是享受中国农民工待遇。美国虽然低通胀且资本与精英获利,但整体被拉低,熵增;中国虽然也付出生态和维稳等成本,但整体提升。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先是要中国补偿美国,以减少逆差;继而大幅提高关税,意在切断两国之间的熵流。特朗普的算盘是,虽然美国要付出代价,但中国的损失更大。
打关税牌的贸易摩擦基本上限于经济层面,由中兴到华为的技术封锁上升到国家实力层面,涉及到“修昔底德陷阱”。“断供”等技术封锁超越经济层面,指向国家实力之本。第二层面的潜台词是,国家实力强弱交替背后的文明,这就是第三层面的“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进一步针对中国的立国之本。关键是,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是国家,还是公司?在全球化中,中国的国家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虽然主要是公司作为参与的主体,但贸易逆差显然是在国家层面。特朗普启动301调查,针对华为的措施,也是一再动用国家机器。在中美两个国家的背后,国家利益之争和意识形态差异正在导致科技路径分裂。
任正非在一次访谈中回答英国记者说:“华为不需要与中国政府对话,对话就是上了特朗普的当。特朗普想让中国用一些利益来换取华为生存,中国政府凭什么要把利益给美国来换华为生存呢?所以,我不希望跟中美贸易捆在一起,相信我们会打赢。”[6]
英国脱欧虽非直接起因于贸易摩擦,但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巨大作用清晰可辨,由此必然影响欧洲和英国的科技路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下日韩贸易纷争,背后依然是国家利益。韩国的科技路径或将面临重大变化。
中国这样的大国科技路径的变化将带来世界性的影响。如当年温家宝总理所言,所有的事项一旦乘上13亿,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从科技和客观的角度看,供给,需全球市场消化;需求,对于任何供给方都是挡不住的诱惑;自身拥有“完整产业链”,貌似可以自己玩,而其他所有的科技路径几乎都绕不过去。从文明和主观的角度,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韧性和忍耐力,还要加上当下国人令人罕见的致富欲望。当中国以“举国之力”做一件事,各国或许不得不举世界之力应对。
对此,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就世界而言,没有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如此之大国及其灵活性,欧美为此要求改革WTO,例如美国提出的《一个无差别的WTO——自指定的发展状态导致体制的边缘化》;而中国,也感受到來自世界的前所未有之压力。
科技发展路径之分合
无论是贸易战、技术战,还是“文明冲突”,依然存在着弥合分裂的因素。
经济上的考量。虽然形形色色的个人、公司,乃至国家,需求层次的高低不一,价值观各异;但是对利润的追求普遍适用,“‘利益尤可贵”,这就是资本的逐利本性。
随着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由单纯的招商引资和世界工厂,逐步同时成为投资方和世界市场。在贸易摩擦中,美国两党和朝野难得达成一致,有人表示,绝不相信中国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甚至彻底消除后,美国企业家会为了所谓中美之间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的不同,拒绝到中国卖东西,甘愿看着日本和欧洲的企业在中国市场赚大钱。[7]美国企业无法拒绝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资本和技术的逐利性就会把美国的资本和高科技企业推进中国市场。
虽然如此,中国毕竟不能把牌押在随机的资本逐利性上;再说,资本、公司也受到国家的管辖,譬如联邦快递对华为邮件的处理。曾经认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坏也坏不到哪去”的依据,然而随即发现压舱石“滚来滚去”,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前不久,居然还有人以为,大豆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公约数”。[8]大豆贸易可以沟通两国关系,然而买卖双方都可以轻易替换,故不可能成为纽带,更不可能成为公约数。日韩经贸关系也说明了这一点:类似大豆或半导体的原材料这样特定的贸易关系,绝不是什么公约数,一旦有事,就会沦为政治的工具。
科技发展的融合因素。可以从科技整体、IT的特点,以及产业链等三方面来理解。
(1)科学以往的发展超越文明的冲突,并将继续以一以贯之的规律、精神和规范超越并弥合科技路径的分裂倾向。
其一,科学之“向上”建立在较低阶梯,基本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的基础上,基本物理运动等低级运动形式对于所有人是一样的,从而在本体论上为高层个性化的意识运动奠定共同的地基。
其二,认识论上的“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亦即本体论上科学的“扩展”。“扩展”有其共同的出发点,“第二条道路”始于共同認可的“抽象的规定”。扩展、发散、嵌入、语境,都可以在非嵌入编码知识这一共同的地基上彼此理解与兼容。“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等走过了头。
其三,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所培育的科学精神和规范,这种精神和规范不仅延伸到今日,而且扩展到技术领域,其主要标志是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放源代码,体现了默顿规范中的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科学技术与规范在今日已扩展和提升为自律与包容、协作与创新。科技一体化,原本利益捆绑的技术也会受到科学无私利和知识公有的影响,其典型就是自由软件运动。
其四,一件科技黑箱只能满足人的有限需求,然而人的需求综合且彼此相关,因而必然要求科技黑箱之间彼此兼容,适合更多语境,以及可以配套更新,从而形成技术生态。
(2)IT的特点。开放源代码同时还体现了IT的特点。与其他技术不同,IT显示了以下特点。
其一,由封闭到开放(源)。信息具有渗透性和共享性。前者意为可以从任何事物中提取信息,后者意为不同的事物可以接受同种信息,可以将信息输入到任何事物中去组织其物质、能量等要素。信息的渗透、传输与共享是有条件的,只可能发生于彼此开放的事物之间。所以,开放是由IT的本质所决定了的。
微软一开始胜过一度辉煌的苹果公司,在于其系统的开放,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走向封闭,斥责开放源代码运动及Linux是违背商业规则的“癌瘤”。正是基于开放源代码的精神,Linux将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层提供给用户,“源代码谁都可以看到”。微软的竞争对手通过开放步步壮大。
IBM在研发PC机的过程中没有申请一项专利,将全部技术标准和规范向业界开放,为PC的普及应用创造了条件。由阿帕网到因特网的一步步发展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反过来,封闭走向停滞。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开放是要素、系统从环境中吸取负熵以使自我得到进化的必要前提。国外许多大公司采用了公司间“代码共享”策略,以期获得双赢。自由软件(尤其是Linux)开创市集模型Bazaar的软件开发模式。在成百上千程序员热切而专业的眼中,错误是浅显的,结果是更加高速、健壮和完美的软件。相反,“教堂模型cathedral”开发模式,源程序被锁定在一个保密的小范围内。错误和编程问题狡猾、阴险、隐藏很深,几个月仔细检查,也未必能都挑出来。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完美的版本。[9]
不同主体处于各自独特语境,具有形形色色需求和价值判断,必须开放知识,由此才能吸纳和兼容更多知识,面向更多需求。“开源”,意味着得到更多知识的支撑,能接受更多的审视和批判,因而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技术生态要求开放,容错,不求完美。一项技术对其他技术支持越多,得到其他技术的支持也越多,不仅商品遍及世界,而且在全球范围获取创新要素。相反,工业技术的特点则是封闭、追求完美和不容许错误。
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撼公司易,撼“开源”体系难。[10]与开源体系对垒,几乎等同于与全世界作战,甚至包括自己。要挑战一个成熟的“开源”体系,先要自己成为“开源世界”。[11]
其二,信息技术的“外部性”。IT的应用面越广,用户的效益也越好,对物质资源消耗的比例越小,厂商的利润也越高,这是“赢家通吃”的缘由。互联网的效用与节点的平方成正比。供应链的各方,进而供给方与需求方,经由互联网彼此融合,进而相互赋能。因而在“互联网+”的情况下,最后的“赢家”不是一家公司包打天下,而是众多公司与个人的集成与融合。
任正非在最近谈到,全世界都有很多小公司,特别是欧洲有非常多。如果没有一根线把珍珠串起来做项链,就没法增值。如果我们实施开源,允许珍珠在开源体系中连接起来,就可以把这些珍珠的科学价值分享给全世界人民,放大了商业效果,对英国、欧洲振兴有好处,对全世界振兴都有好处。[12]
中国和英国、欧洲存在的问题是自己没有平台,在创新上都是单个的。鸿蒙开源,是对英国、欧洲创新的支持,对中国创新的支持,对全世界小公司创新的支持。而且鸿蒙有低时延的特征,有可能让人们获得更好的体验。华为就是把珍珠串起来的那根线。
0~1和1~100。0~1和1~100,前者指原始创新,后者指原始创新的商业化,直至“最后一公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始创新与最终应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美国多有原创,中国重在商业化。原创固然重要,如果没有随后的商业化,一来得不到用户的反馈,未来发展方向不明,二来缺少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支持。中美如果在0~1和1~100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共享的契约关系,在这一环节携起手来,有望部分改善眼下科技路径的分裂倾向。
这一点可以说是经济与科技的结合。
有必要指出,同样是“1~100”,实际上有所不同。关于两套“5G”和两个市场,大致是爱立信与发达国家市场,以及华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主要是中国市场。就市场的影响而言,有质与量两个因素,“量”是购买力。仅就人口而言,后者居多,但经济实力显然发达国家领先,因而可能迭代更新的周期短,反过来对爱立信的支撑就更大。
相比之下,“质”的影响更为重要,具体指消费者的体验和对供给方的反馈。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体验显然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其一,在西方个人本位的语境中,消费者具有较强维权意识,容不得商家说了算;其中还有一个特殊性,即重视个人隐私。其二,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位于较高层次,反馈多在精神层面,故而具有多样性,易于发生随机涨落,成为创新的源泉。
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其一,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较弱,保护隐私的意愿不强烈,商家可以更多自行其是。其二,在需求层次上位于较低层次,具有更大的同一性,缺失随机和非线性,加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易于发生“近亲繁殖”。
发达国家固然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庞大市场,而发展中国家更离不開发达国家规则严谨、需求高端、多样和变化的市场。
什么是公约数。究竟什么是中国、美国与世界,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公约数?其一,利益。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即使在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内,英国因利益分歧脱欧。特朗普当选,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回归利益,随后一次次的退群更是赤裸裸唯利是图。大豆或半导体材料等特定贸易,因为可替代和存在众多竞争者,也不可能是公约数。但是考虑到另一些情况,中国发起的亚投行,G7中五国参与,利益均沾。“一带一路”建设,随着“第三方参与”,发达国家的立场软化。这就意味着,广义而不限于经济的利益,在一定场合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的公约数。不仅如此,利益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其典型是比尔·盖茨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立场,同样具有众多拥趸。
其二,合规。[13]从反腐败专项合规扩展到包括竞争规则合规(反垄断),金融规则合规(反洗钱),贸易规则合规(遵守出口管制以及经济制裁之规),以及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合规等全面合规。合规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必须跨越的门槛,成为企业重要的软实力。放大到国家层面,同样需要“合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提出“与国际接轨”,加入WTO后遵循相关的规则。
利益可以出卖,出尔反尔,只适合于特定场合;规则高于利益,在空间上普遍适用,在时间上适用于整个有效期。规则是国际关系的公约数。然而在客观上,规则总有漏洞,在主观上,总有人钻漏洞,或破坏规则,“扛着小锄挖墙脚”。[14]有必要建立更高层次的公约数。
针对前文述及的“开源”,业内人士认为,一个完整开源“生态”的建立,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还涉及到历史、文化、法律甚至价值观。建立“开源世界”,需要更好的技术积累和法律保护机制,更开放的包容体系,对原创知识产权的虔诚尊重,更长时间的文明沉淀,在价值观上成为“世界中心”。本文写作中,欣闻华为正式发布“鸿蒙”操作系统并宣布开源。值此多事之秋,鸿蒙成功与否,在于其技术层面方便好用兼容,利益均沾;在于其符合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规则;以及在于其遵循的价值观。规则是信任的基础,价值观是信任的核心。
科学技术,既是往日超越社会纷争的主线,又是后现代分化之因,还是弥合分裂走向未来的源泉。科学,以及按科学方法所得到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学认识两条道路转折点“抽象的规定”是分化的共同出发点,是各条路径得以追根溯源,彼此理解和兼容的钥匙。科学活动所形成的精神和规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技术不仅是“用”,而且是“体”。科技,为其前沿中的“文明冲突”,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途。
未来趋势
由于各国在科技发展上所处的阶段不同,对科技的认识不一,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各异,利益纷争,以及文明冲突挥之不去,因而必将从不同角度持续影响科技发展的路径。公约数只是基础,如果没有“公倍数”的引领,各国科技的发展路径依然可能发生分裂。
开源一开始自由,未必永远自由。渗入了公司的利益,谷歌的Android可能是沾着蜜糖的诱饵;受到国家利益掌控,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长臂管辖”的一部分。
不计代价把是否实现“自主创新”作为单一或者最重要的目标,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便在贸易摩擦和断供背景下也是如此。自主创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手段,市场的作用更大。[15]“华为本来就开放思想,不打算走自力更生和封闭的道路。即使研究出来,也会采取‘1+1政策,购买别人的一部分器件。有一定弹性。我们渴望世界开放。前提是有实力,如果我们没有实力,别人说不开放,我们就死掉了”。[16]鸿蒙向世界开放。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的观点是,自主创新绝不应是自己创新。[17]
树欲静而风不止。全球化停滞不前,而逆全球化却甚嚣尘上。有人认为,今后可能是“半球化”,各国都不再享受全球化红利,大致形成美(美洲、英、澳、日)、欧(英、澳、日、南美),中(亚非拉、日韩),各据有半球(1/3)的产业链。
对于未来的科技路径,一种观点认为,假如将来出现两种以上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也就是相当于存在两个上帝,其结果有可能非常惨烈,战争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联合的可能性,其中的道理类似于两种一神教难以相容。[18]
科技与文明构成由物质到精神谱系的两端。这里的“两端”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科技之超越文明,进而为“文明的冲突”提供公约数,在于科技是所有文明在物质上的共同基础。在谱系的精神一端,如果“文明冲突”的各方执意而为,依然可能导致科技路经的分裂。
另一方面,科学精神与规范,IT的特点、互联网的开放、共享、赋能,意味着科技又处于谱系的精神层面;而“文明冲突”各方对金钱和权力,一言以蔽之,对各自利益的渴求,相对而言处于谱系的低端。对利益的追求既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路径分裂的源泉。
“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拥有同一个自然界。所有的技术产品,所有的科技黑箱共同构成了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人类是否会不得不接受一个分裂的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
科技从物质上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地基,在精神上提供人类彼此理解和兼容的明灯,人类需要不同文明的相向而行与融合。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及其发展路径研究”和“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19SJZDA126、19SZB-024)
注釋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https://mp.weixin.qq.com/s/6TMMtYEiu4QaX2xoi1TBpA.
[3]吕乃基:《论科技黑箱》,《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2期。
[4]朱颖:《全球化阴暗面——依赖关系武器化》,http://www.uzbcn.com/mon/keji/20190812/60662.html。
[5]路风:《自主创新与美国的负面教育》,https://mp.weixin.qq.com/s/tf8oU3nwvsuxTCvhaBpKmA。
[6]https://tech.ifeng.com/c/7pJP5PU6Sc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7]邢予青:《“中美脱钩”论折射了什么?》,http://www.uzbcn.com/mon/keji/20190730/60229.html。
[8]“大豆公约数”印证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9]https://www.docin.com/p-56109017.html
[10]《欧洲手机操作系统塞班的血与泪》,https://mp.weixin.qq.com/s/jiSbOZt8QHZzjU3oiMP2Cw。
[11]《“开源”的战争》,https://mp.weixin.qq.com/s/g2_kz9w7CY6c2Bik13R8hw。
[12]https://tech.ifeng.com/c/7pJP5PU6Sc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13]王志乐:《中国企业“全球化”四大挑战:做大之后如何做强?》,https://mp.weixin.qq.com/s/hN3fr1Pk0oSvinTpDn93JQ。
[14]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215712.
[15]https://mp.weixin.qq.com/s/rKI5GqN6xbz2VRULTTli_w.
[16]https://mp.weixin.qq.com/s/JIYtHs8ijo-aTXfrnDdCNw.
[17]《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自主创新绝不应是自己创新》,新浪网,2019年8月17日,https://tech.sina.com.cn/it/2019-08-17/doc-ihytcitm9850043.shtml。
[18]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
责 编/马冰莹
吕乃基,东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导,东南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主要著作有《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科学与文化的足迹》《科技知识论》等。
Is There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Scientific Frontiers?
Lv Naiji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showed signs of division, and the problem worsene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the trade war and technology war in recent year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ould no longer "leap-forward" or "surpass," but interact with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e can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split"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Internal" includes the influ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elf, especially the "black box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aslow's demand level; "external" means that globalization intensifies the international interest competition, involving the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ivilization levels. Interests,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values can help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o communicate at different leve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t only assist, but also lead. The spirit and norms formed by scientific activities are the common wealth of mankind,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mon divisor"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Keywords: fronti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ash of civilizations, development path, black box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on divi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