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新解的典范
——施蛰存《唐诗百话》读后
2019-03-12杨迎平
杨迎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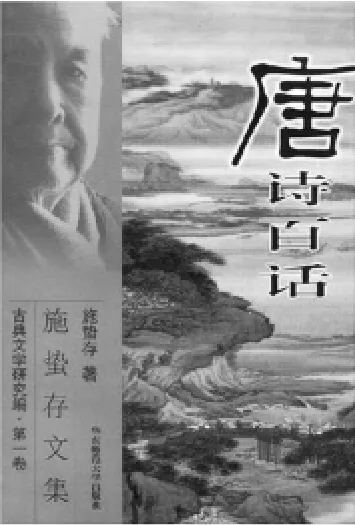
施蛰存历时八年撰著,于198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研究唐诗的专著《唐诗百话》。它不仅是施蛰存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最大成就,也是中国唐诗研究的突出成果。《唐诗百话》全书共一百篇,由五部分组成,前四部分是初、盛、中、晚唐诗话,重点选讲了七十多位诗人的近三百首诗,基本上反映了唐诗的全貌。第五部分是六篇专论:《唐女诗人》《六言诗》《联句诗》《唐人诗论鸟瞰》《唐诗绝句杂说》和《历代唐诗选本叙录》,对一些重要问题作了专门论述。
在传统诗话的基础上,《唐诗百话》做了大胆探索,在分析每一首诗时,都逐一列出历朝历代注家的评说,考证是非,鉴别真伪,然后阐述自己的新观点。黄裳说:“书出后佳誉如潮,连巴金都向我借了去读过。此书好处在新见层出,敢说自己的话,取传统的唐诗评论一一检讨,分期、作者、风格变迁、名篇解析,都有自己的见解,读之如遇一部崭新的唐人诗话。所见不必尽是,但确是一本崭新的文学评论。”①笔者以为,其“崭新”之处至少体现在下列诸方面。
一、裁断歧义,去伪存真
一开始写作时,施蛰存就查看各种唐诗注本,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从宋、元、明、清以来,就有许多距离极远的理解。不但是诗意的体会,各自不同,甚至对文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为了要核实情况,从语言文字中求得正确的含义,我又不得不先做些校勘、考证的工作”②。施蛰存仔细研究和辨读历代唐诗注本,考证唐诗的分期、诗歌的主题、各种名词术语乃至每首诗的字句,从而去伪存真、纠正谬误。
对唐代诗歌的分期,历来有多种分法,施蛰存肯定了明代高棅在其《唐诗品汇》中确立的四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分期说,但他不同意历代文学史家对唐诗四个时期盛衰的评价。明清以来,人们多认为盛唐诗代表着唐诗的最高成就,中唐是唐诗的由盛转衰期。施蛰存则认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在政治、经济方面不如盛唐,但没有唐诗的衰落现象(第565页)。胡适《白话文学史》阐述过类似观点:“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③在胡适的基础上,施蛰存进一步明确了中唐诗歌繁盛的事实:“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第565页)
经过认真的考证、辨析,施蛰存发现,历代文学史家对具体作品的误解、误读比比皆是。于是,他对书中选入的每个诗人的每篇作品都做了一番辨伪工作。如《唐诗百话》第44篇有女道士、女诗人李冶(字季兰)的《寄校书七兄》,第一联云:“无事乌程县,差池岁月余。”施蛰存说:“这首诗第一联是作者自述:住在乌程县里,虽然没有什么事,却已差不多有一年多了。”但后代人不了解唐人用词的习惯,就把“差池”改为“蹉跎”,从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到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都这样改,其实“蹉跎”与“差池”是古今字,“差”字加一个“足”旁,“池”字换成“足”旁,“也”与“它”是同一个字的异体写法。弄明白了这两个词的关系,就不会用“蹉跎”换“差池”了。施蛰存依唐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将其改正为“差池”(第312页)。再如《唐诗百话》第61篇选有刘禹锡的绝句《乌衣巷》,其中有两句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施蛰存查阅了《草堂诗话》《诗林广记》《唐诗绝句注释》《唐诗解》《唐诗别裁集》《岘傭说诗》《唐人绝句精华》《唐人七绝诗浅释》等多个选本,发现竟然没有一个解释是正确的,甚至有人将之理解为:“旧时王谢堂前燕”今天“飞入寻常百姓家”。施蛰存说:“旧时和现今,相差五百年,一群燕子,没有如此长的寿命。在诗的艺术方法上,‘旧时王谢堂前燕’是虚句,是诗人的想象。‘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实句,诗人写当今的现实。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去思考,那么‘王谢堂’和‘百姓家’的关系就可以获得正确的解释了。”(第432—437页)
除了纠正对诗句理解的错误外,施蛰存更多纠正的是对作品主题思想的误解。如《唐诗百话》第16篇选孟浩然的《临洞庭赠张丞相》,施蛰存认为唐汝询《唐诗解》的解释是错误的:“唐汝询首先肯定孟浩然不是要求仕的人……这样讲,已经弄错了孟浩然的思想情况。”(第109页)其实孟浩然很希望成进士,由此谋得一官半职,如果通读孟浩然的诗集,会看到他有许多求仕、求荐的诗句。“只是他胸怀高洁,不屑作不择手段的钻营。没有机会,也不介意。宁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要说他绝对不求名利,恐怕未必。”(第105页)另一个徐而庵则在《而庵说唐诗》里大骂唐汝询,施蛰存认为徐而庵的理解更是荒唐,“这位而庵先生一口咬定孟浩然是不要做官的人”(第110页)。其实此诗明显有羡慕别人得仕之情。“唐汝询是从小就双目失明的人,徐而庵评他的注解为‘真无目人语’,可谓刻毒。而他自己讲这首诗,比唐汝询更为不通,又何尝不是‘瞎说’?唐、徐两家都不知道此诗题下还有‘上张丞相’四字,也都没有从孟浩然全部诗集中去‘细循作者之思路’,仅仅就这四句诗中去穿凿典故,曲解诗意。至少,对这首诗的理解,他们两位都不免是‘门外汉’。”(第110页)再如《唐诗百话》第36篇选杜甫《新安吏》,施蛰存认为很多人对其主题的理解是错误的。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分析说:“此诗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恻隐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与仁之中,此岂寻常家数?”④浦起龙认为前半篇是作者要以恻隐之心感动皇帝,表现了诗人的仁,后半篇是他以责任心去鼓励兵士,表现了诗人的义。施蛰存说:“如果用这一讲法,这首诗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作品。前半篇对中男的怜悯成为虚伪的同情,其目的是劝诱他们去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卖命。所谓‘义行与仁之中’,这句话的意味就是用假惺惺的仁来实现阴险的义,这就符合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了。”此后,多数人用浦起龙的观点解释这首诗,自以为抬高了杜甫,其实是贬低了杜甫。施蛰存的理解是:“杜甫当时只是抒述自己爱莫能助的感情,不得已而只好喊出一声‘天地终无情’。”(第258页)他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观进行反思,认为“一味温柔敦厚的人,容易成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第325页)。施蛰存深入理解杜甫的思想情感、性格秉性和矛盾心理,从而正确地解释了诗的主题和作者的本意。
历代评论家为什么会误解诗人和误读作品,探究原因,施蛰存认为主观主义的“以意逆志”(第252页)是很危险的。施蛰存赞同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可是,以意逆志也不能完全从主观出发。必须先尽可能地明确这个作品的写作时期,作者的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把这个作品纳入一个比较近似的环境里”(第252页)。施蛰存认为:“一个词语,每一位诗人有他特定的用法;一个典故,每一位诗人有他自己的取义。”⑤只有设身处地去了解诗人的思想和秉性,才能正确理解诗意。
二、推源溯流,史论交融
《唐诗百话》仅仅百篇,入选的诗歌较为有限。历代选本多关注唐诗的经典化,施蛰存则更注重呈现唐诗的发展史。施蛰存认为,在唐朝,诗歌的各种体裁已经齐备,各种风格都已成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开头即说:“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⑥施蛰存站在诗歌史发展的高度,既关注诗歌内容对唐代政治、经济等时代变迁的反映,又关注诗歌作为独立文学体裁的内在艺术规律的演变轨迹。他不仅是在写唐诗发展史,更是在写中国古典诗的形式建构史,其选诗、评诗有一个思想内容以外的专注于诗歌艺术演变的形式史考量。看似在讲单个诗人、单篇作品,其实是超越了作家、作品而对整个唐诗的宏观把握,以小见大地展现唐诗的风貌,通过诗人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和社会风俗,推源溯流,梳理出唐诗发展、演变的线索,挖掘并论述各个诗人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做到史论交融。所以,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上,施蛰存不一定选择最优秀的诗人及其作品,但会选择具有文学史价值的诗人和诗作,从而使唐代的诗人成就、诗体发展得到全面而准确的展现。
比如初唐诗人沈佺期与宋之问,《唐诗百话》第4篇已经涉及他们的作品,第6篇又选了宋之问的《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第7篇选了沈佺期的《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施蛰存认为,唐代五、七言律诗的格式“,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两人奠定下来的。在初唐诗史中,他俩以‘沈宋’齐名”(第40页)。《唐诗百话》第17篇选了孟浩然三首五言律诗《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洛下送奚三还扬州》,都不是名篇,历代选本从来没有选过,宋元以来的诗话里甚至没有人提到过。施蛰存认为,在孟浩然的这几首诗里,有着开元时期五言律诗的各种篇法、句法、调声、对偶等多种形式,可以看到初、盛唐从五言古诗发展到五言律诗的脉络与轨迹。《唐诗百话》第26篇选了李颀的《渔父歌》,这首诗“既不同于六朝的五古,又还不是唐代的律诗,题目用‘歌’字,而诗体又不是歌行。从形式上看来,这首诗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第176页)。施蛰存之所以选这首“四不像”的诗,是因为《渔父歌》代表了盛唐五言古诗演变到五言排律的特殊形式,声调和句法都在五言古诗和律诗之间:一联中有粘缀处,但每一联都有失粘的字;声调不合律体,却有了调声的倾向,比较近于律诗,而不是古诗。这代表着古诗、律诗界限未清时期的形式。“盛唐以后,做古诗就不管平仄谐和,也不作对句;做律诗就严守格律,不许有一字失粘,于是古诗和律诗的界限清楚了。”(第178页)李颀《渔父歌》的文学史价值在这儿就呈现出来了。
施蛰存在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后面都总结性地撰有《初唐诗余话》《盛唐诗余话》《中唐诗余话》《晚唐诗余话》,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唐诗各个时期的形式演变以及唐诗内容对唐代历史变迁的反映。如在《盛唐诗余话》中,施蛰存说:“盛唐前期是李白诗‘飞扬跋扈’的时代,它们反映着玄宗李隆基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上升的气象。盛唐后期是杜甫‘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时代,他的诗反映着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的社会现实。”(第297页)由此可见,《唐诗百话》既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也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唐代史,闪耀着史学的瑰丽光彩。
三、人弃我取,避熟就生
如何从为数众多的唐诗中确定入选诗人诗作,《唐诗百话》坚持了两大原则:一是上文论述到的顾及诗史的全面,二是避免篇目与其他选本的重复。此前诸家唐诗选本,多选耳熟能详、在某种意义上可表现诗人最高艺术成就的篇目,可历代诗评家标准林立,加上立场、观点、认识的局限,唐诗中明珠暗投的诗章却也不少。这就为施蛰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即使是名家,他也能发掘出人们颇感陌生化的优秀诗作。
施蛰存说:“我现在另走一条路,人详我略,人弃我取。”⑦别人详细讲解的地方,他略讲;别人放弃不讲的作家、作品,他选讲;著名诗人诗作,他别辟蹊径换一个角度讲。施蛰存还避熟就生地选了一些人们陌生但有独特价值的作家、作品。如此选择,对不同的作家、作品来说,原因可能这样那样、不一而足,但其共同意义却是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人们的见识,刷新了唐诗面目,给唐诗赏析贯注了新鲜空气。
李白与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写了大量诗篇,李白诗约一千首,杜甫诗约一千四百首,历代选诗的人,常感到从他们的诗集中选几首代表作很不容易。施蛰存认为,《唐诗百话》不一定选他们最好的诗,但要选他们各种风格的诗,做到全面欣赏。对于李白,施蛰存在第30篇和第32篇选讲了《蜀道难》《将进酒》等著名诗篇,认为它们“文字通俗明白,没有晦涩费解的句子,这是李白最自然流畅的作品”(第223页),而且充分表现了李白的浪漫主义特色。但是,在第29篇,他又选了李白《古风》三首,认为其“不浮不荡,有深刻的感情,无穷的意趣”(第199页),“既不披游仙的外衣,也不作曲折隐约的比喻,它们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欣赏,这是李白诗的大众化倾向”(第202页)。施蛰存“人弃我取”地选择李白《古风》,是因为他认识了这些诗作的独特价值,“而一般人读李白诗,却喜爱他那些豪雄放逸的作品,殊不知这些作品,虽然才气焜耀,可是感情和思想都比较肤浅,而且没有含蓄,反而使比兴的意义,都被游仙的陈词滥调所掩盖了”(第199页)。李白的诗,施蛰存还选了《战城南》,施蛰存说:“《战城南》是李白几十首乐府诗中最浅显明白的……选李白诗的人,不很愿意选这一首,因为不够代表李白的豪放风格。”(第220—221页)而他认为,通过这个范本可以懂得古诗变为近体诗的演变过程。
对于杜甫这样一位大诗人,人们津津乐道他的《春望》《北征》和“三吏”“三别”,施蛰存则将视线放在他的五、七言律诗上,他说:“杜甫给律诗开辟了新的境界。他的律诗里出现了许多新颖的字法和句法,使唐代的律诗,无论在字句结构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两方面,都达到高度的发展。”而且“他自许晚年的诗,音律极为细密”,施蛰存选的七律《返照》和《登高》,“未必是杜甫的代表作。我之所以选这两首,企图从一些浅显易懂的作品中找一个‘诗细密’的典型”(第270—271页)。这两首诗的平仄、粘缀完全符合格律,没有一字失粘。通过杜甫的律诗可以看出,盛唐是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完成时期。
韩愈在继承先秦、两汉文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体,他攻击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和近体文的陈词滥调。“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将散文理论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用散文的句法、篇法写诗,做到“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于是,“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第406页)。陈文华说:“对他的诗,自北宋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以文为诗’这个问题,几乎是文学史上一段久争不决的公案。”⑧施蛰存却不回避这“不决的公案”,特别选了历代选本都不选的《落齿》。施蛰存说:“《落齿》诗从来没有人选取,也几乎没有人齿及。现在我选讲这首诗,作为‘以文为诗’的一个典型例子。”(第412页)《落齿》不做文字上的雕琢,像一篇很有趣味的散文,怪诞、风趣而且不失积极的人生态度。施蛰存认为:“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第406页)“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第414页)韩愈是“以文为诗”的始作俑者,之后的王安石、黄庭坚、苏轼正是步了他的后尘。其实,韩愈的这一特点,是对杜甫的继承,“形式是诗,精神却是一篇散文”(第575页)。当然,韩愈的诗本质上还是诗,它剥落了诗的形象思维等装饰,直接呈现了诗的本质。
四、着眼全篇,知人论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轻浮靡丽,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使诗的风气有所改变,但“摘句论诗”的批评方法却更盛。曹文彪说:“在唐代,无论是采用摘句批评的人数还是摘句所达到的水准,都远远超过了前此的魏晋南北朝时代。”⑨施蛰存说:“这一风气在文学批评上导致了一种极不好的倾向。即评论诗篇,不谈思想内容,不谈全篇的完整统一,而只摘取其一二‘奇章秀句’。”(第164页)他认为:“欣赏诗歌,要从全篇着眼,不要从一字一句中去求作者的用意。”(第43页)“我们每读一首诗,第一总得研求它的主题思想。”(第165页)如果仅对字、词、句津津乐道,就使欣赏对象破碎化,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批评家要深入历史的洪流,站在诗人的立场上去揣摩诗意,处在与诗人相同的位置去感受诗句的意境。
施蛰存说:“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盛唐诗风格的创造者,并不是他们遗留给我们的诗多至千余首,而是由于他们的诗在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方法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在过去许多诗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境界。”李白诗的新境界,是“他不甘心于搜索枯肠,句斟字酌”(第197页)。他用形象思维来表达豪迈、忧郁、苦闷、愤慨的情绪,从而突出了其作品的主题。杜甫似乎与李白不同,追求杰出的句法、章法,字字句句都要千锤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⑩,但“他比李白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社会的现象和人民的生活状况”(第197页)。可见,施蛰存评价李白、杜甫的伟大,首先看到的是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反映,其次才是艺术表现方法上的创造。施蛰存说:“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有一个成语,也可以说是文学批评术语,叫作‘知人论世’。要了解一个作家之为人,必须先讨论一下他所处的是个什么时世。”(第4页)王国维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⑪了解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生平处境,才能着眼全篇、提炼主题,进而理解作品的真正涵义。
施蛰存认为,“摘句论诗”的批评方法还会导致“一种虚伪的文学”(第165页)出现,“许多诗人先刻意苦吟,作得中二联,然后配上首尾,变成为只有佳句而不成佳篇的、没有真实情感的诗。他们只是为作诗而作诗了”(第295页)。如贾岛是一位刻苦吟诗的人,其《送无可上人》颈联云:“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为了这两句,他苦思了三年,他还为此写了一首绝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题李凝幽居》有脍炙人口的佳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但施蛰存却说:“《题李凝幽居》一诗,较多为选家取录,但是我以为它是这三首诗中最差的一首。这首诗每二联之间,都没有逻辑的关系。”《忆江上吴处士》有佳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然而整首诗也不佳。施蛰存认为,这三首诗总的看来都不是好诗,“往往是仅有佳句而无全篇的佳作”(第459—461页)。王世贞《艺苑卮言》亦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此是定论。岛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泪流……又:‘秋风吹渭水,明月满长安’,置之盛唐,不复可别。”⑫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中、晚唐人作诗,不少人用这种方法。刘贡父《中山诗话》对此提出异议:“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嘉,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者尔,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也。”⑬施蛰存说:“刘贡父反对摘句论诗,以为不能见到诗人雄材远思的人格。这意见是正确的。”(第473页)“宋元以后的诗话,很多的是摘句论诗,所以很少有高明的见解。”(第165页)
施蛰存也能体会到唐人“二句三年得”的辛苦,但他认为,即使是苦炼出来的字句,也要有行云流水、自然天成的效果。诗僧皎然在《诗式》中说:“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⑭这里说的是:作诗取境,必须苦思苦想得到奇句,但诗成之后,要让这奇句不显得突兀,不见苦思的痕迹,才是高手;有时佳句来了势不可挡,宛如天神相助。戴表元亦云:“无迹之迹,诗始神也。”⑮施蛰存认为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样一贯而下的流水对,可谓自然天成、“宛若神助”(第96页)。
五、精神分析,感觉主义
施蛰存的唐诗研究方法丰富多彩,他是一位现代主义批评家与新感觉派小说家,能够在唐诗评析中化用精神分析、感觉主义与意象批评等现代批评方法。
(一)精神分析
施蛰存赞同孟子的一句话:“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⑯施蛰存说:“对于一首诗的主题思想,我们也只有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求解……然后用自己的意去探索作者的志。”(第252页)这样做,似乎有些主观臆断,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可能会与作者的寓意失之交臂,因为有的诗“是作者确有寓意,但文字表面不很看得出来,读者也不容易体会作者的寓意”(第693页)。有时,他采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古代诗人的心理,别有一番情趣和意味。
(二)感觉主义
《唐诗百话》里选了李商隐的《锦瑟》和七绝四首。历代诗评家认为李商隐的诗不容易懂,不易懂的主要原因是用典多。施蛰存说:“在李商隐以前,诗人运用典故,不过偶尔用一二处,不会句句都用典故……但是,李商隐的诗,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即使都注明白了,诗意还是不易了解。”(第575—576页)如《锦瑟》,含义没有人能说明白。颔联和颈联并置了四个意象,相互没有关联,也没有逻辑脉络。宋代《许彦周诗话》大约是最早解释此诗的资料,许彦周记录赵深的讲法:“《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其弦数,其声有适怨清和。’”⑰认为“锦瑟”是乐器,中间两联乃描写适、怨、清、和四种音调;刘攽《中山诗话》说锦瑟是某贵人的爱姬,《唐诗纪事》说是令狐楚的妾;还有人说《锦瑟》是悼亡诗或者艳情诗……施蛰存认为,这些说法“也只是臆说,毫无根据”(第581页)。虽然人们都说李商隐的诗不易懂,但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白、杜甫、白居易诗的人更多。施蛰存说:“在唐诗中,李商隐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的社会意义,远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但我们可以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唐代诗人。”(第576页)
由于李商隐的诗难懂,所以人们都希望李商隐的诗能有详细的笺注,冯浩、程梦星、姚培谦等人进行过笺注、考释,考证出了李商隐诗中的典故,但是整首诗的含义还是不易明白。可见,李商隐是有意不让人们太明白。有人的诗,看诗题就能明白,李商隐的诗题有许多是《无题》《有感》《读史》,或者就用第一句诗的开头两个字作为诗题,如《锦瑟》《碧城》,等于无题。白居易作《新乐府》,唯恐读者不明白他的诗意,在诗题之下再加了一个副标题,如诗题《杜陵叟》下面有“伤农夫之困也”(第579页)。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大众化,如叶燮所说:“白居易诗,传为‘老妪可晓’。”⑱“李商隐恰恰相反,诗意已经朦胧得很,还不愿加一个说明性的题目,留有余地,让读者去感觉,而不是理解。”(第579页)
“让读者去感觉,而不是理解”是作为新感觉派小说家的施蛰存对李商隐朦胧、晦涩象征主义诗歌的看法。李商隐的朦胧、晦涩与一般古典诗歌的含蓄不同:一般古典诗歌虽然含蓄,但是可解的,李商隐却拒绝解释,他的诗诗意晦涩、诗题用“无题”,都可以看出其拒绝解释的态度。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好就好在不可解,好就好在朦胧、晦涩,不是浅显的“一读即意尽的诗”⑲。他说:“我们对于任何一首诗的了解,可以说皆尽于此‘仿佛得之’的境地。谁能够一百二十分地了解得一首诗呢。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⑳“对于李商隐的诗,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求解,冯浩也还不敢自信其无误。所以,我以为还是采取陶渊明的方法,‘不求甚解’为妙。”(第585页)王世贞说,诗就要在“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㉑。叶燮进一步说,作者不将诗歌内容说明白,“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㉒。李商隐追求的就是默会意象、如烟似幻的感觉。
施蛰存还说,大多数古人用典是明用,李商隐“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企图在他的诗中所显示的意义”(第576页)。李商隐这样用典,又增加了他诗歌的难解。施蛰存说他“近于象征主义”(第579页),他诗歌对比兴的运用,已经超越了传统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理解范围。李商隐的诗多用绮丽的辞藻写男女欢爱,“但在文字表面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与男欢女爱不相干的意义。这样,李商隐的艳体诗,或说情诗,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我们说他是用‘比兴’的创作方法来写这一类诗的”(第576页)。如七绝《闺情》:“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一看就觉得是一首独特的闺情诗。大多数闺情诗写妇女伤春怨别的情绪,这首诗写一个女人睡在丈夫身旁梦见与别人约会,丈夫却不得知。冯浩认为这首闺情诗写得太轻薄,太露骨,毫无寄托。其实,冯浩被李商隐蒙骗了,李商隐在诗题上标明是“闺情”,就不会是闺情,他一定隐藏着“严肃思想”。叶燮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㉓施蛰存对这首诗的感觉是:“有些人的思想、感情、行为,即使同在一起的人,或极其亲密的人,也不能了解,正如同床的丈夫还不知道妻子的思想、感情、行为一样。这是用有寄托的观点来解释这首诗,岂不是可以说是‘寄托深而措辞婉’呢?至少,这样一讲,它就不是一首轻薄的艳情诗。至于从这一寄托的意义去探索诗人所隐喻的具体动机,这就不可能求之更深了。”(第587页)象征主义将想表达但不愿直接表达的思想蒙上神秘的面纱,感觉主义与意象批评方法不是去揭开面纱,而是透过这面纱感觉其美妙。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诗的美妙是声、色之美,是和谐、铿锵之美,“尽管全诗的含义不甚可解,但就是这一联,已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使人击节心赏了……连意义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只因为有高度的声、色之美,也使读者不求甚解而仍能感到它是好诗”(第579页)。古人评诗多用考证,要求字字句句落到实处。李商隐的诗用考证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施蛰存欣赏朦胧、不求甚解、感觉美妙的现代解诗方法,更贴近李商隐。李商隐是最具现代性的古典诗人,施蛰存对李商隐诗歌的分析体现了现代诗学的意味。
施蛰存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学识渊博,能够触类旁通地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的方法去理解诗人的思想,将唐诗“气象之恢宏、神韵之超逸、意境之深远、格调之高雅”㉔的特性彰显出来。施蛰存更是一位现代派诗人、诗评家,注重诗歌的诗意、文学性和情感性,具有一个诗人的感性气质,《唐诗百话》因此成为诗人评诗的典范。同时,施蛰存是大学教师,他写作《唐诗百话》的初衷,是作为大学教学的唐诗串讲,所以有一个教材性质。为了让初入门的大学生方便学习,施蛰存细心地将书中提到的诗学名词、词语及成语编成索引附在书后,以便于学生和教师查阅。《唐诗百话》第100篇是《历代唐诗选本叙录》,将唐宋以来最重要的唐诗选集编列出来,以供研读唐诗者参考。可见,施蛰存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而且也传授了学习和研究的方法,更是树立了一种精益求精做学问的精神。
①黄裳:《忆施蛰存》,《夏日最后一朵玫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2.3 妊娠结局 研究组产妇胎膜早破、早产、剖宫产、胎儿窘迫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胎死宫内发生率略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②施蛰存:《唐诗百话·序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本文引文出自该书者,均随文括注页码。
③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
④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3页。
⑤⑦⑳施蛰存著,刘凌、刘效礼编《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页,第1103页,第468页。
⑥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⑧陈文华:《唐诗史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⑨曹文彪:《论诗歌摘句批评》,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⑩傅东华选注《杜甫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3页。
⑪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书林主编《王国维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61页。
⑫㉑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94页,第178页。
⑬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5页。
⑭皎然:《诗式》,《历代诗话》,第31页。
⑮《戴表元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⑯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35页。
⑰许顗:《许彦周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⑱㉒㉓叶燮:《原诗》,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第36页,第67页。
⑲施蛰存:《社中谈座》,载《现代》第3卷第5期,1933年9月。
㉔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香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