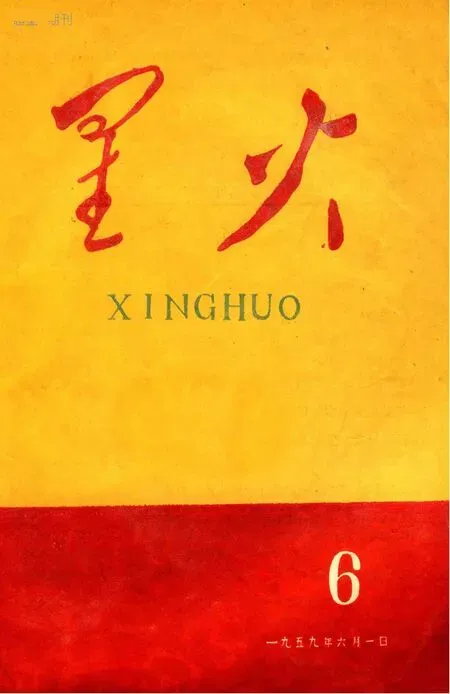阳台记
2019-03-11赖韵如
○赖韵如
1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租住在各式各样的房子里。
刚出来讨生活时,住在栎木庄,那是老城区边缘的返迁房,窗格子蜂窝一般敞开。
赣州老城区河套外的江边近年高楼汹涌,一批批的拆迁户搅动着城的漩涡。几乎每个拆迁户都补了几套小房子,他们将房子隔成小间,尽最大的效益装修好租出去。小间价格亲民,给出来闯荡的小年轻带来福音。
本来我是寄住堂哥家的,有天晚上我下班进门,发现气氛极其尴尬,原来堂哥要把我交的生活费退还给我,嫂子不乐意,吵起来了。我担心他们再次吵架,就出来自立门户。刚好新应聘的同事阿绿找人合租,我便主动搭伙,租住进栎木庄这个有客厅和两个不规则房间的顶层阁楼。
栎木葱茏应该是上世纪的事,栎木庄在秋风稀薄的早晨接纳了两名女子。
我们把双肩包和拉杆箱一放,心中驻扎良久的蓝图便一阵颤动。房间的天棚底板刷白了,依然掩盖不住砂浆的粗粝,隔着漫长的秋冬,我闻出溽暑的味道。天棚盖压在床尾半米高的位置,床头有个小窗,推开窗帘,旁边有个推拉门——外面竟然是一爿小小的阳台,跟客厅外的长条阳台连着,用布艺旧沙发隔开。长阳台另一头,房东用玻璃隔出一个简易厨房。从这往外看,可以俯瞰一截城墙,一截拐弯的贡江,甚至可以瞥见郁孤台的翘角。贡江在我和阿绿的眼眸里浩浩汤汤,奔走向前,冷不丁就隐进前方的楼群。尽管如此,这块方寸之地,也让我莫名感动。
炊具暂无,晚餐得去夜市摊解决。夜市摊设在古城墙下,沿着城墙摆了一溜——五金、干货、南杂、饰品、服装、古玩甚至香火寿衣应有尽有。最多的当属小吃摊,赣南的各色小吃都融汇于此,它以最大的便利和高性价比,满足了老城人民及城中村阵容强大的租户。
当藕粉色的晚霞从天边漫过来,吆喝声开始此起彼伏。我和阿绿从阳台探出身抽鼻子,防盗网外,各种味道穿越几百米空气后钻入我们鼻喉。我们趿拉着鞋下楼,宁都肉丸、兴国米粉鱼、赣南沙河粉、信丰芋饺、会昌珍珠粉、仙人草冻等轮番上阵,当嫩绿的葱和着醇厚的酱油辣椒撒下去,搁在我们心尖上的梦想也弥散开来。
遇到手头宽裕,我们就逛老肥的吆咪卤鹅。老肥把百年祖传的高汤浇上去,我们都来不及屁股点凳,便拎起鹅肉往嘴里送,鹅肉粑软松脆,骨髓香滑。阿绿嘬一口鹅汤,开始感慨胃的庞杂和伟大。
老肥喜欢看女人,尤其是阿绿这样凹凸有致的女人。他对着专注吃鹅的阿绿隔空抛了个眼拐,阿绿则用咂嘴回应他,这个浑不吝死老肥竟然还会不好意思。良久,老肥用勺子从汤锅里挖了一副鹅肝,扭着两瓣大臀过来,把鹅肝按进我们的大碗。
旁桌两个男孩问:我们也送鹅肝么?
潮头!小鬼切(吃)甚么鹅肝?老肥背心一撩,露出圆鼓鼓的肚皮回到摊前。
男孩们丢下一桌的鹅骨头扬长而去。一边走一边拖腔念:
肥牯子肥,挑大肥
挑到南门口,遇到一条蛇
吓得肥牯子打倒回
室友阿绿看着气鼓鼓的老肥偷笑。她总喜欢偷笑,大辫子一遮,半边脸挤弄出丰富的表情。她话不多,精简有力,像她紧致的腰肢。她偶尔来一两句冷笑话,旁人似乎要辅以延长线才get到点。沉静低眉时,隐约可感她眼神锐利,野心勃勃。
2
阿绿之前做过销售,我见过她套上工装的视频,胸膛饱满,眉眼端丽,接待客户时细腰一扭正步走,一副“圈内人”闯荡世界的样子。
阿绿为何离职她没说,反正现在和我一样万精油,做采编和策划。每天,我们骑着用一个月的工资换来的小毛驴在街巷间来回穿梭。
“老城区挖出古墓,巨大夜明珠惊煞全城!”“某某投资公司非法集资,上千市民千万投资血本无归”“某某地产,火爆开盘”“某某整形,来自韩国的蓝本”……当太阳照在赣江之上,我们便开始为这些打着感叹号的新闻与广告奔走,忙完纸质稿,又编电子版。阿绿比我耐劳,也更有头脑,奔走城区时还能揽到私活。当然,我们的工资在填完房租水电和三餐茶饭后,稍微搞点小动作就会捉襟见肘。
小姑是我在这个城市走得最近的血亲,她在开发区电子厂做磨具。我常钻进车间,看她打冲床,看她单手托举一框框原料放进碾斗。她边干活边和工友们高声说笑聊天,工友称她“大笑姑婆”。小姑笑起来才不像阿绿,她的笑声中气十足,天宽地广。遇上笑岔了气,小姑壮硕的双乳便跟着身体颤动。自从小姑离开了那个沉迷六合彩的丈夫,她的笑声更加响亮通透。
我们的阁楼置办齐厨具后,小姑便常来栎木庄颠锅,她说她喜欢这厨房,简直到了迷恋的地步,阳台厨房开放,透明,使人呼吸畅快!我就奇怪,大笑姑婆还有不畅快的时候。
为给我庆生,她挽着新男友来。小姑男友是高空作业装空调的,为表心意,他准备送我一台二手空调。男人晃着黝黑的膀子在租房里转圈,嘟囔着房东的精明,裤裆式的天棚,还隔出两间来出租。
小姑趁男人在里屋嘟囔时把我从玻璃厨房拽出来,衣服一掀,拉链一扯,牵出鲜红的内裤。原来她的内裤还缝了暗格,装了厚厚一沓钱。“骚气吧?这是保险裤,钱在这才安心。”她抽出几张递给我,眨眨眼。我惶恐地揣钱入兜。
小姑男友已坐在客厅,他没看见小姑给我钱,天知道他是否知晓小姑内裤的暗格。他高谈阔论时总带一句“伽妈地白”之类的赣普,伽妈地白这些拆迁户,伽妈地白读书读到牛百叶里去了……他就这样“白”到开饭。我和阿绿不接话,我们端起玻璃杯,眼神触碰后迅速移开,说老了一岁,喝酒喝酒!
3
接下来的寒冬,淘宝上的廉价家具和收纳盒慢慢填进房子。我们在天棚顶贴了壁纸,在墙壁上涂鸦,依着《老树画画》,手绘那个没有眼耳口鼻的草帽人,绘上春茶图,再添上蹩脚的打油诗。
开春时,我开始注意阳台对面那个绿色小土坡。挖掘机匍匐在堡坎上,像一头饱食酣睡的巨兽。我想拍下那个巨兽配条短视频,手指一推,朋友圈轰炸起来,溜娃的、秀恩爱的、喝酒泡吧旅行的,一波波照片蜂拥而来。我决定还是去绿坡走走。这一走不得了,我和阿绿开始来来回回跑,开启铲土挖泥种花养草模式。
漂泊的人处于随时离开的状态,器皿就不考究了,粗陶瓮、玻璃缸、塑料瓶,坛子罐子能盛上水土的,纷纷端上阳台及橱窗。随手撂几株苗或几粒种子进去,他们便兀自生长。藤蔓花草从不嫌弃,攀上了春天就蓬勃蓊郁。
太阳落岭的时候,菜蔬在铁锅里打个滚,砂锅一开,两盅清甜的汤就开始撒欢了,小圆木桌在小阳台一摆,愉悦的脑细胞醒过来。阿绿吞下一口醋萝卜,慢悠悠告知我第三棵豆苗长虫了。
果然如此,她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巡视一遍小花坛:阳台防盗网架上,百香果和丝瓜都已抽藤开了花;旁边的多肉肥嘟嘟的;碎木养的绿萝翠生生一片;铜钱草在水盆里擎起一顶顶绿盖;茉莉、鱼香草、紫苏、小葱幽香袅娜;太阳花和吊兰就像山里皮孩子,腰身健壮枝叶挺括……瞧上半天,碗里的饭菜也一扒拉一扒拉列队进了胃。
有一种草很奇怪,我们并没有洒下过任何种子,它却在水泥岩的青苔罅隙里挺起几株,借着春风衔来的泥土蔓延开来,小而肥厚的叶片长满了锯齿,趴在似草非草的苔花之上,天棚滴水弹射过来,它活泼泼迎风招展,顽强,突兀,悸动,毫无来头,挥之不去。
“那草叫落地生根,多像我们!”阿绿瞟一眼草,把一盅汤嘬得嗤嗤响。
阳台已融入了租客的灵性与气息,这真值得庆贺。那些徜徉在别处的梦想,在小阳台上得以补偿,日子,似乎也活色生香呢。
4
住在阁楼里,屁点大的地方实在不够我们折腾,盆盆罐罐堆起来时,我们的桌椅、衣架、鞋子、收纳盒等便被挤到角落了。
有一次,阿绿把一个顶帅气的男伴带来,他实在没法理解我们为何在本来逼仄的空间里,摆弄如此种类繁杂的草叶菜蔬。他点了根烟就走了,再也没来过。
楼下邻居举报有泥水滴落,房东老头便来视察警告。他指着那些拧巴生长的花草一脸鄙视:你们该住带花园露台的豪宅!他愤然离开。“个个都是乡巴佬,路边花草还没看够?”他混沌的喉音在楼道里横冲直撞。
说归说,听归听,我们才不理会呢。
不过,我确实开始憧憬有个属于自己的院落,在接通了地气的空间里,有属于自己的场地,不必担心没地方捣鼓花草,更不必操心搬家漂泊。
我也想念父亲的吊脚楼,那些岁月,父亲踮着高弓足,带着妻儿在吊脚楼卖百货,做裁缝。他的手艺在十里八乡都没得说。夜晚关了货铺,他便爬上吊脚楼,铺开案板,摊开一叠叠布匹,用尺子飞速打版,粉笔精确地划在各种布料上,裁缝剪纵横捭阖。我和弟弟趴在楼板上捣鼓录音机,磁带放进卡座,仓盒一关,传动轴悠悠地转起来,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飘出来,绵密袅娜,伴着父亲虎虎生风的裁剪声,光阴变得有声有色有样子。卡带了!弟弟掏出磁带,父亲只得停下手中的活,把指头塞进孔,磁带一圈圈归位……
许多年了,再没人需要父亲裁剪衣裳,父亲也跟着打工潮奔赴一座陌生的仓库。他得和我一样重新成长,我们从吊脚楼踏进城市时,卡壳卡带的事多如牛毛,身心似乎每天都被安排,被绑架。那些修身治国报效社会的豪言飘在年少的光阴谱系里,变成鸿蒙初辟的合声。
时不时有花叶蔫巴下去。晚上,月光粉嫩嫩铺展在阳台上,我赤脚出去,喷水壶洒下银白的弧线,我开始构建一个空间:那里阳光明丽,江水丰沛,风吹过庄稼,到竹木处歇一脚,接着撒丫子奔向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房屋。河边的场院,有吊脚楼,有父亲,有小妇人,似我非我。
5
有一些洪流,似乎是用怡然自乐无法掩盖和阻挡的。
夏日的金融风暴长驱直入,它在北上广深周旋良久,终究未放过赣南这样的三线城市。各种倒闭风失业潮传来,我们媒体行也越来越难适应市场,公司开始裁员,并承接各种项目,文化旅游、金融担保、地产房产、新闻出版,能挨上边的都接。我们的名片被打上繁复的头衔。
大boss带着大家跑业务,大部分时候都在酒桌上,我们被领头的女部长教导要大气喝酒,主动服务。我在首次端白酒杯后全身起疱疹进了医院,后来赴宴,总是焦虑得语无伦次。次数多了,我基本被打入冷宫,做各种端茶倒水主动服务的工作。
阿绿刚好相反,她拖着长辫子,乳房奔突,仪态万方。她微笑,仰头,喉头鼓动,伴着荤荤素素的段子,一杯杯白酒下肚。大boss说她有潜力,前途光明。那次一个地产界的老总在酒桌上非要室友叫一声“干爹”,阿绿用自罚白酒推诿。女部长过来小声劝阿绿,阿绿才嗲着嗓子唤了一声“干爹”,那老总微醺着,额头上恶狠狠的川字纹舒展开来。
那晚回来,室友阿绿趴在布沙发上吐了一地。她嘤嘤哭泣,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她揪了一把阳台的“落地生根”,抛掷出去。她跟我说起她改嫁的母亲,“家都没有多个爹算啥……要知道这桩谈成了我有10个点……”酒话断断续续,我无从安慰,只拿毯子重复包裹扭动的阿绿,裹住从不妥协和哭泣的姑娘。
阿绿能对付大场面。酒量好,酒胆雄,人俊还开得起玩笑,这是大家公认的。公司在接洽一家新能源公司入驻时,带上了阿绿,新媒体与新能源得以顺利对接。到签合同时,大boss吩咐阿绿单独接洽,她却执意要带上我。
我们进了包间,偌大的地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常来公司对接业务的小伙子,另一个是个儒雅的老头。老头面色红润,头发稀疏往一侧梳,形成边区支援中部的局势。
好在阿绿都熟悉,跟我说这是公司控股的大佬朱爷。朱爷静静地喝酒说话,说起自己如何一路驾驭生意场里的汹涌波涛与暗流。等冷盘上来,他开始谈论中日文化、民国美女、佛教,甚至说起哈代的《苔丝》以及意大利歌剧《塞尔维亚的理发师》,我们跟着话题辗转跳跃,疲于奔命。
在某个时刻,我们的确被这些话题和稳健的谈吐迷住了。朱爷抿一口酒,慨叹生命长度已定,宽度可以拓展,锦瑟年华就要多闯荡多体验。他们推杯换盏,我斟茶,一失手,一杯热茶浇在朱爷雪白的前襟上。他忽地站起来。
阿绿赶忙拉开我并不断哄朱爷,朱爷您大量,朱爷不生气,我的同伴笨手笨脚地帮朱爷擦拭前襟。
为了补偿我,那你就表演一下睡美人吧!朱爷皱缩的脸又笑开了,盯着墙上的古典画和画中的睡美人。
朱爷笑话,我哪敢跟睡美人媲美?
你今天比睡美人美。
阿绿缓步移至美人图下细看,良久,她在贵妃靠沙发上斜躺下来,雪白的右手腕枕于脑后,长发散开,灯光洒下来,凹凸有致的肢体散发出蓬勃的美感,她眉长入鬓,双眼紧闭,面若桃杏,这哪里是伸着脖子逛小吃摊的阿绿呢?她分明就是个睡美人。
朱爷摇晃着来回踱步。几分钟过去后,他踉跄着绕到阿绿的头部,伸手抚摸她绸缎般的长发。阿绿偏头对扯了一下。老头摩挲着,又让手伸向那胸前的隆起。就在肉体触碰的瞬间,阿绿张嘴咬住朱爷的手臂,朱爷骂咧着甩开,许是用力过大或酒劲上来,他一个趔趄顿倒在地。美人嗷叫着起来,我从未见一个女人如此狂怒,她抓起茶几上的打火机,“咔哒哒”对着朱爷头上的几撮毛点起火来。头发嗤嗤地响,老头一手抓住阿绿往美人图墙上撞,一手拼命护住寥寥无几的头发。焦糊味传来,我们匆匆离开。六月的街灯扑满了飞蛾,照见两个狼狈的影子。
6
项目自然功亏一篑。领导得知错失良机整天阴着脸,他逼迫整个部门集体加班,每天除了搞宣传,还瞎指挥造各种预算表和方案。
一个男同事电脑前安装了一个巨大enter键,据说是个减压神器,那个分离的回车键外形笨拙,跟他精巧的男儿身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快速敲好一些字,稍稍停顿,然后拳头扬起,青筋暴突,稳准地捶在回车键上。他间歇着、不顾一切地砸下去。格子间的许多心脏,也间歇着,被硬邦邦地捶上一记。
阿绿很快递交了辞呈,可一时半会走不了。她开始迟到早退,也不爱说话,回家便睡美人般地整日昏睡,每天在我弄好的饭菜里草草点两下筷子。
我怯懦着,还真鄙视现在的自己:不敢走,也不想干。深夜,我幽灵般点着电驴子穿过葱郁的红旗大道,绕着浮桥转圈,各种扭曲的眼睛让我无法招架,究竟是什么把人卷到生活的深处,将来我会滚到哪里去?
我还是滚回那张沙发。透过阳台婆娑的藤叶,我看见河对岸斑斓的灯火,那个水木丰盈的空间在细化:带阁楼的土房子挂着“春申遗风”的门匾,妇人在灶膛煨汤,探身和过往的邻里打招呼;山间的木梓树长茶包了,脐橙也开了白花;一些弃置的粗陶瓦罐都来了场院,睡莲飘萍在这些老家伙的怀里繁衍生息;谷雨来了,紫丁香、风雨兰这些天生乱序的花草在院墙下肆意妄为;村里人借鉴生态富硒园的经验,管理一群亢奋的茄子辣椒……那是一种让人倍感安心的生活机制,是生态和人心造就的心安。
实际上,我从小体质虚弱,在吊脚楼度过的童年已验应我不适合繁重的农活,按父辈的指点和期许,我拼命地走读书的路子冲出来。如今书好歹是读了几年,路冲得是七零八落。年幼时,我爱过美术和文学,碎片化的灵感就像飘忽的萤火虫,不知走过几个轮回,依然在暗夜里扑闪。
谁真的想回到农耕时代呢?它已从父辈们的肩膀上流过去,从我们的手指间推碾过去。互联网声像媒体爆炸的当下,农耕是逃避和落后的代名词。而今夜的阳台,默默地展开农业文明留下的美好画卷:那些长在骨子里的时令节气、春耕冬藏,那些点豆是豆、种瓜得瓜的辛劳与喜悦,那份藏在时光里的淡定和从容、自由和尊严。
阳台上的虚拟是喘息的载体,他们在我贫瘠的想象里日渐丰饶。
那段时间,我的幻景里偶尔也会出现归人,他们来自各个朝代。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清晰的脸。他们有时是行走江湖的侠客,有时是沉默勤谨的农夫。遇上身体不适,那个归人就是号脉精准、深谙百草及方剂的医者。有一次,高中时期那位白球衣学长竟然大汗淋漓进入我的场院……
7
又一顿晚餐在阳台,就着花草摇曳。
阿绿不知何时找了份家教,开始了漫长的考试生涯,她桌上摆着《消防安全案例分析》《会计CPA》之类的书籍。怯懦和梦幻终究不能细水长流度日,我也辞职了。
我们都开始不动声色地找新房子,找租友。
晚餐有一搭没一搭聊,我们谈起那位被点着了半脑袋头发的朱爷,绿女人啊,你也是天才,打蛇拿七寸,治人点要穴。我们笑得饭菜都喷出来,笑过后总是长久的沉默。
我们又捡起一些话题:亚丁稻城,那个被广告轰炸过的圣地,从没涉足却夸得天花乱坠的净土,如今组团游半价了;新区的房价在掉,有个公寓适合投资;一个设计方案被挟权力自重的女部长活活拖着;前男友结婚生子了,她还会想他;公司倒闭了,那个同事会到哪里去捶他的回车键呢;家里准备拆旧建新要寄钱回去。我们无话不聊,甚至聊起被冲撞得生疼的初夜……那些从不被人记挂的辛酸与过往,那些奔突的神经与高攀不起的梦想,化着庞杂的黑,在夜幕下密密铺开。
阿绿第二天不辞而别,我只听见一只沉重的拉杆箱轰隆隆碾过水泥走廊,笃定地向前磨损。
我留下来,住在裤裆式的天棚里投简历,在阳台浇花,我知道这片生发了无数幻想的阳台,过几天就要易主。天知道那些撩花撩草的小钢勺、小铲子、小喷瓶、陶瓷器皿会怎样,天知道我和端丽倔强的阿绿姑娘,将辗转漂流去往何方。
月光从城市的边缘撒下来,城市的呼吸声此起彼伏。绿植在阳台里随风摇摆,谢苗的菜蔬叶下,结着呆头呆脑的果子,落地生根又长出一片;几只小老鼠在暗处作作索索。也不知那些犄角旮旯里的生命,能否受到尘世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