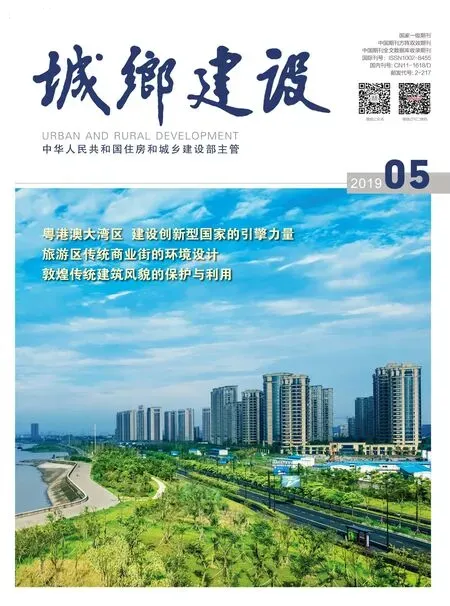湖南省美术馆的设计策略
2019-03-08胡世勇
■ 王 凡 胡世勇
在先秦两汉时期,湖南属楚国腹地,屈原的诗歌、马王堆出土的历史文物当中,都具有鲜明的“荆楚文化”特征。自南北朝以后,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区域。在此背景下,加之湘楚之地多达55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的影响,湖湘文化内容中的哲学、艺术、文学、宗教、民俗、建筑等方面均呈现出了鲜明的多元文化特征。因此,湖湘文化的特色无法一言蔽之,这就给美术馆设计的立意带来了挑战。

图1 夜景鸟瞰示意
然而换个角度思考,多元文化繁荣的背后实则折射出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湖湘学派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的态度,博采众长而不偏一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融合荆楚文化与儒家文化而自成一体,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由此可见,“开放”“包容”应该可以成为湖湘文化特色的关键词。
美术馆的创作思路中,建筑师希望将美术馆塑造为一种“双重根植”的建筑——即根植于区域的乡土文化,也根植于场地文脉。但对于区域文化的诠释,希望规避“煽情式的模仿”,摒弃对乡土建筑符号的简单堆砌和对空间形式的失真复刻,而试图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由于美术馆建筑的功能定位,使它与艺术品有着密切的联系,建筑师便将视角聚焦在湖湘艺术文化的层面。经过了细致的调研后,建筑师将切入点聚焦在了一种湖南本土惊艳的雕刻艺术——“菊花石雕刻”之上。

图2 一层平面
形式的文化追问:菊花石雕

图3 效果示意:东南侧(上),西南侧(中),东北侧(下)
菊花石,原产于湖南省浏阳县,呈青灰或褐色,因内有自然形成的白色菊花状结晶体而得名。花蕊部分是坚固的硅质燧石,花瓣由方解石晶体组成,存在于距今两亿七千万年的早二叠纪。菊花石的雕刻工艺最早起源于清朝乾隆五年(1740)前后,菊花石砚更是作为朝廷贡品,深受藏砚者青睐。“浏阳二杰”之一的谭嗣同就酷爱菊花石砚,曾留下“浏阳菊石,温而缜,野而文,复生谓己其影,名石菊影与庐,欲言其义不能”的赞叹。1915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工艺美术大师戴清升的菊花石雕作品荣获了“稀世珍品金奖”的殊荣,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至今还保存于联合国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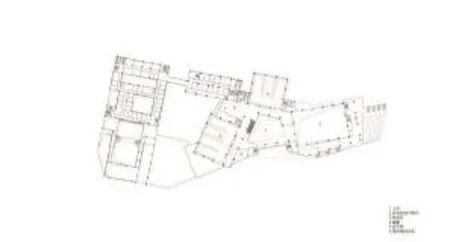
图4 二层平面

图5 三层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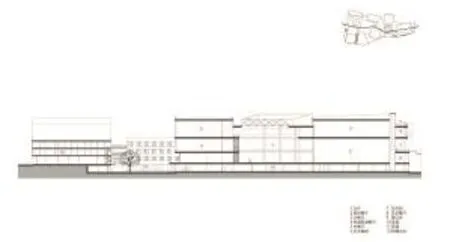
图6 剖面图

图7 立面

图8 分析集合
由此可见,菊花石雕刻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和清晰的地域辨识度,是一种可以代表湖南地方艺术的“乡土元素”。那么如何建立起建筑形态与菊花石雕之间的关联呢?将菊花石雕刻的图案肌理抽象为建筑表皮,或将建筑形体具象为菊花的形态——这类具象的模仿,或许是最容易迎合当下主流消费文化的通俗性、大众化的方式。然而,消费文化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本身就存在着巨大争议——对消费文化的一味迎合与妥协致使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诞生了一大批饱受社会诟病与舆论调侃的建筑——就是最为直观的例子。因此,应当避免线性思维的推导,而从更深的层面对这种“乡土元素”进行“再阐释”。
菊花石雕刻的工艺流程包含了采料、选料、寻花(开花)、造型设计(定题)、雕刻、打磨、上色、配座八道工序,建筑师撷取了其中自“寻花”到“上色”的五个与艺术创作最为相关的步骤进行研究,试图发掘传统工艺之于建筑创作的深层共性与参考价值。
(一)寻花
寻花也叫开花,是指在原石上进行开凿以找寻石菊晶簇,使内部的石菊形态逐渐显露出来的过程。放之于建筑创作之上,如果将美术馆的场地与其内部功能组团一并视为“原石”,那么建筑师要寻觅的“花”应当是何种元素呢?我可以理解,“石菊花”是菊花石雕刻匠心独具、与众不同之本,可以视作菊花石雕刻的灵魂。那么类比到建筑功能当中,决定了美术馆的功能定位,使其有别于其他的公共建筑的根本特征,便是其展览、展示功能。因此,以展厅部分作为美术馆形体的主要表现元素,在精神上便与“花”的内涵产生了高度契合。在对具体功能定量分析后,建筑师通过对陈展空间的组合与功能串联,整合出了三组“石菊花”组团。建筑师希望这些组团可以在立面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显露,能够被使用者观察与感知,从而为美术馆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形式逻辑和功能主义例证。
(二)定题:三湘四水
在寻花后,菊花石雕刻还需要结合石料大小、石菊的花型和分布确定恰当的主题。这个阶段的工艺特别强调“因材施艺”的原则。不同的母题产生出来的作品不尽相同。妙趣横生——有状物类作品,如菊花石雕刻泰斗戴清升先生的《秋菊傲霜》;也有叙事类的作品,如工艺美术大师陈继武创作的《桃花源记》。回到建筑创作当中,“因材施艺”的雕刻原则在这里与建筑设计当中的“因地制宜”的场地原则有着惊人的相似。美术馆的场地临近湘江,周边为空旷的未开发用地——这种现状导致了场地本身缺乏有效的制约条件,也使得建筑与场地的对话难以展开。

图9 材质比选方案
然而基地所处区位“两面环山,一面傍水”的景观资源,与其通透开阔的视野,给对话创造了另外一种可能。基地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景观资源可谓得天独厚——西可观金牛岭,北眺岳麓山、天马山、后湖,东北望湘江、橘子洲头。面对缺乏有效限定的场地现状,实现建筑与景观资源的对话便成了回应场地文脉的关键所在。通过对区域范围内景观节点的梳理,建筑师确定了西、北、东北方向的三条景观轴线,并将三组展厅组团的朝向与之对应,从而将周边的景观优势汇聚于场地之中。以三条轴线为逻辑派生出了建筑顶层东北向的望江台、艺术餐厅;北向观山赏湖的学术办公区以及西侧的景观挑台与美术馆附楼主入口空间。
如果说要赋予建筑一种雕刻的母题,那么三条线索的汇聚,可以让人联想到常用以指代湖南的“三湘四水”一词。三条景观轴线汇聚于三组石菊组团,暗喻三湘;在场地设计当中生成的四条放射型步道暗合四水。三湘四水,物华天宝,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喻;热土潇湘,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不负“惟楚有才、于斯为甚”的盛名——取题三湘四水,也是对湖湘文化的再次挖掘与提炼。
(三)雕刻/打磨
雕刻工艺名家田顺新曾经在解读戴清升先生的名作《石菊假山》时这样感慨:“形有洞、洞亦形。洞、形应为一体。对他们在造型过程中的专注,不能有丝毫怠慢和偏颇。这是一个资深雕刻家理应必备的技艺造诣之重。”从中可见,工艺大师们给予了雕刻艺术中的“虚”与“实”同等分量的关注。反观建筑,若将围合而成的室内空间视为“实”,那么半围合的院落与灰空间便为“虚”。注重灰空间的营造,模糊建筑内外的界限,建立一种开放的、具备亲和力的建筑场所,是对前文中所述湖湘文化“开放”、“包容”的形式回应;而对于院落空间的塑造也是对传统建筑形式与建筑文化的一种尊重。因此,建筑师怀着对工艺大师的敬意,将其看待虚与实的态度一并继承到建筑创作当中,对院落空间与灰空间的塑造上施以饱笔浓墨,最终形成了以外围灰空间,内部大小合院、边院穿插分布的场所形式。

图10 现场照片
(四)着色:水墨书画
在石雕接近完成的尾声,为使菊花石花型更加突出,同时也为保护石质,需对石雕进行上漆与打蜡。常见的着色以底石为黑,石菊为白;亦有赭石或深灰为底(图14)、花为白的配色。建筑师在美术馆主体选材时,曾经面对湖南本土的赭石色石材与黑色石材的抉择,二者都可以传达菊花石雕刻的神韵,选择黑色石材可与水墨书画的艺术脉络更为贴近,而本土石材则可以体现对当地文脉的尊重。
在与业主方漫长的方案调整沟通,权衡各方利弊后,最终落成的美术馆外立面选择了赭石色的配色方案。但为了保留和更好地实现原中标方案中采用的隐喻毛笔书画中行笔笔触的横向表皮肌理,建筑立面材质替换为了横向构件的开放式金属幕墙。三组展厅组团在立面上显露的部分延续了白色石材与竖向肌理,暗喻书画中巧施天功的留白,也象征艺术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