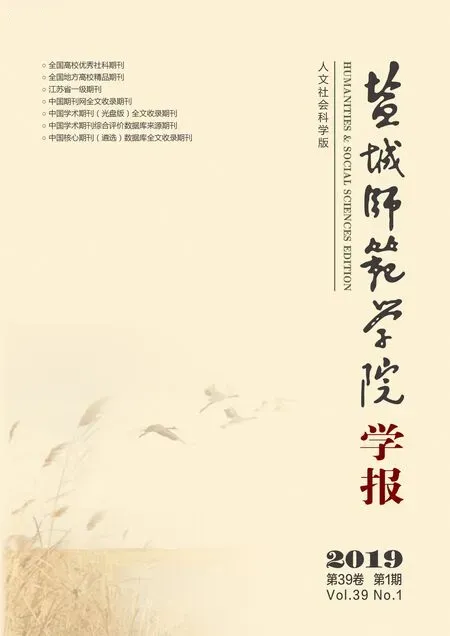民初文人“捧角”现象的新变及与士心世态的关系
2019-03-05薛超睿
薛超睿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戏曲是都市文化的产物,而明清社会的整体向俗,使士伶交往成为值得关注的症候,但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前者居于四民之首,后者则不入时流,故在正统道德观念看来,实在有干教化。而与男旦之间的同性相狎,更斥为伐性之斧,所以论者时常带着有色眼镜,凡属捧角之作,一概斥之“日渐颓唐,游戏笔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应当归纳、区别,分而论之,诚然,有一类钱色交易的勾当,喝花酒、打茶围,这些看官被戏称老斗、蔑片,而那些小角被贬为黑相公,为同行不齿;第二类是文人自命风雅,评选菊榜,编写花谱,对艺人的评判依据渐由台上色艺偏向台下风致[1]54,多带有暧昧的情愫和伤感的想象;第三类是朝中翰林京曹,借观戏而自遣,或以此夤缘官场、沟通消息,故往往重艺轻色[2]129。从艺人角度看,京剧创始人程长庚呼吁自律,不良风气稍歇。进入20世纪,田际云于1905年以精忠庙名义开办正乐学堂,规定凡非堂子私寓弟子,均可就学[3]111。民初又成立正乐育化会,并于1912年4月15日向北京外城巡警总厅递呈,以堂子私寓为乖人道,呼吁警厅查禁[4]1243。伶人开始自我救赎,追求进步,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士人,历经鼎革后沦为政治的失语者、文化的零余者,随着地位的此消彼长,“他者”视野渐趋拉平,由护花人转为知音,最终向现代性、专业性戏剧评论过渡。
一、民初文人“捧角”的几种形式
㈠梅兰芳旋风中的文人推手
1913年秋,梅兰芳经易顺鼎引荐,拜会当时在上海的樊增祥,并赠小影留念,樊见后惊叹“牡丹洛下君王后,蕙草江南士大夫”,遂作《梅郎曲》纪之[5]1803。樊与梅家乃世交,当年梅巧玲之景龢堂“陈设文雅,拟于世家,都中名士,皆以涉足龙门自豪;而巧玲亦以把臂凤毛为快,一时景和堂中,名士往来如过江之鲫,云门樊增祥其尤著者也”,巧玲“常为小诗,超逸不凡,士大夫益爱之,如樊山辈皆时茗会其家”。至梅二琐时“士大夫以爱巧玲者,移而以爱二琐,樊樊山、易实甫皆为其入幕宾”[6]320。梅兰芳乳名裙姊,拜于朱小芬门下后,署名兰芳,冠字畹华,年稚貌美“士大夫识巧玲、二琐者,无不推其爱于兰芳”[6]47。
梅先生赴沪演出,樊增祥等文界前辈极力揄扬,很快沪剧界刮起了“梅兰芳旋风”,前后三鼎甲时代造就的须生独尊格局,至此扭转,男旦“中兴”隐然可见(旦角第一次火爆,始于乾隆年间的魏长生),连伶界大王谭鑫培都自愧“我男不如梅兰芳”。梅兰芳的成功,自是出于天赋异禀与大胆出新,也与其性格谦讷,尚雅自重有关,“不习于酬接,迨精舍小聚二三文士相与瀹茗,则娓娓千言殊饶情致”[6]353。且他于同业不惟不相忮害,而是苦心爱才,引掖后进,树立了难得的君子之风,符合传统士人的评判准则,故受到他们的追捧,“梅兰芳初以美色为社会所惊叹,其后又竭力于艺事,今已昆乱新旧无所不精,其色之美已为社会所叹赏,今又益以艺之美,则此富于爱美思想之社会,其极端欢迎梅郎,乃为当然之事理”[6]65。如此,“兰芳在沪凡四十日,归京后声益噪”[6]50,初出茅庐,一炮走红。
㈡名旦古装戏中的文人加工
梅兰芳之《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天河配》[7]307《太真外传》,程砚秋之《红拂女》等经典古装戏,均由樊增祥、易顺鼎、罗瘿公等文坛名宿操刀润色,并通过评戏等方式,阐扬艺术,煞费苦心。姑举樊增祥评《天女散花为梅郎作》云:
三代威仪在于僧,僧家威仪今在伶。释迦佛出冠宝璎,袈裟镂金红于猩。天王甲胄状狰狞,金刚戴面黄蓝赪。应真十八各殊形,转珠闇诵莲华经。佛光如月晕几层,光中隐现垂天鹏。佛告伽蓝汝徂征,维摩示疾为众生。众病岂得独康宁,如红炉雪点始醒。自天雨花遍八紘,兹事惟有天女能。歘然绣幕一声莺,声如戛玉锵流铃。台上齐奏云和笙,侍人蜜香或双成。前引琉璃无尽灯,九华宫扇白鹭翎。此时天女降云軿,一枝玉蝶梅花馨。头上宝髻燕钗横,身上纤縠六铢轻。断红双脸长眉青,绛唇一点樊素樱。玉盘历落珍珠倾,引吭陈节亮且清。坐定伽蓝宣玉音,慈悲为女女心怦。爰呼花奴理行幐,维摩诘住毗耶城。飞天仙人下玉京,足不履地踏云行。满身珠珞隋苑萤,电光激射红素冰。两条绣带风泠泠,式歌且舞皆中程。圆如法轮转不停,浏漓浑脱眩目睛。分时两道彩虹明,合为一毬狮子擎。通身解数娇珑玲,节簇一一谐韶韺。少焉维摩讲净名,圣众趺坐侧耳听。华严楼阁弹指成,其上涌现双娉婷。天女索花花奴譍,风鬟雾鬓交相萦。此时曼歌鸾鸟鸣,此时软舞蛱蝶惊。飞花滚雪身手灵,千红万紫一篮盛。歌一句撒花一升,舞一遍撒花一坪。上头五采杰云棚,下界香雨沾衣缨。曲终翻倒甘露瓶,万花飞舞红蜻蜓。维摩与众俱安平,世界银色生光晶。将毋郎即玉女星,不然亦是许飞琼。公孙弟子不如卿,为此歌者或少陵[6]140。
作者已不满足于过去花榜式的品评,更关注剧情和技艺的精妙,这出戏的亮点是梅兰芳的飞天造型,以长绸取代水袖,糅合武戏做功,诗中着重刻画的就是这一新颖的“长绸舞”技法,为今人再现当时场景提供了生动素材。
㈢士伶生活的全面交错
文人不仅在艺术上支持艺人多出作品,出好作品,还全面融进艺人生活,这也是“士伶互动”中最颠覆传统的一面。艺人发起的公益活动,亲力亲为。1919年7月直皖战争后,梅兰芳等组织伶界书画慈善会,樊增祥特为其画竹题识“约数百字,大意备言京畿兵祸,及梅郎之勇于为善”。1923年春“伶界复发起演剧筹资,设立公会,建梨园新馆,梅兰芳复请樊增祥为撰楹联多幅。
艺人家的婚丧嫁娶,凡请必至。1918年上巳节,梅兰芳为祖母祝寿,樊增祥精心结撰寿序四屏,均精致工丽,俱见深致高情。1919年3月,尚小云结婚,樊上《贺新郎》道喜。1924年4月,程艳秋大婚,樊书二十余字长联。
伶人跟随文人学诗习字并不为奇,梅兰芳常向樊增祥等人讨教,尝得“草虫自拟张珩佩,松鼠还师恽铁箫”“天然风雅出苏扬,不独清歌动帝乡”等赞语。但文人拜入伶人门下,则亘古未有,而樊增祥就径称老辈名旦乔蕙兰、陈德霖为“师”,在当时引起舆论哗然“有人斯文惜扫地”[4]2,樊则不以为意。
二、民初“捧角”的士人心态与文化背景
㈠士伶关系的新变
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戏评杂志《立言画刊》,曾对民初捧角现象作如下酷评:
民十以前,在歌台捧角队中风头最健者为遗老,此辈或为达官显宦,或为才子诗人,彼时挂名差事甚多,类皆身兼数职,每月俸入颇丰,而又无所事事,于是流连歌场,大作其捧角运动。遗老本人虽不必然到处受人欢迎,而遗老之一管秃笔却具有伟大力量,所谓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是也。职是之故,名伶对于遗老不得不相当恭顺,而遗老对于名伶,亦各就其所好,力事游扬,各人算各人一笔账,其间关系微妙之极。
在此期间,一班风流遗老为数甚多,而最享盛名者,厥唯樊樊山、易实甫、罗瘿公三氏,若专以捧角而论,则三人中又当以罗瘿公氏为最得法,此三人者,几乎每日皆在戏场流连,樊易两公更喜在坤角队内走走。既然每日听戏,于是每日有诗,好此不疲,乐而忘返,有好甚者曾以此八字对联戏赠当时遗老诸公,可称恰切。
瘿公为人豪爽不羁,其诗格在三人中最为冲雅,既无樊山之试帖气息,亦不似石甫之故意求奇,即以捧角而论,樊易之成绩亦不逮远甚[8]398。
“就其所好,力事游扬”正是民初“士伶”关系的新变,从某种意义讲是旧社会秩序被打破的最突出的表现:由旧时的暧昧,逐渐光明正大,进而大张旗鼓,它得益于当时业已发达的媒体的宣传鼓励;艺人的明星化,使捧角者由护花人过渡到知音,他们逐渐隐退为情人、爱慕者、策划人与艺术指导的多重融合的身份;同时,公共空间促成了从主观爱慕到客观艺术标准的形成,捧角也要“民主化”,形成所谓集体分担责任的共识,有角大家一起捧[9]121。
捧角活动带有明显的游戏性质,是这些旧派文人在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中试图为自己重新定位的举动,在雅文化与游戏之间滑行,这点在易顺鼎身上尤为体现,他曾毫不避讳地说:“人不能无嗜好、无交游、无消遣,与其吸鸦片、赌博,毋宁狭斜游。盖游狭斜必多为交游起见、为消遣起见,而其嗜欲亦必因爱好美色而起,在嗜好中不能不谓为近清近雅。即因好淫而起,亦较吸鸦片与赌博之嗜好稍雅稍清矣。与其狭斜,毋宁看戏,盖看戏之嗜好,必在声色,不在货利可知,即好声色,亦非好淫可知。且尚有忠孝节义之观感其中,且亦以己之金钱与人而所费不多,不伤廉又不伤惠,好色而不淫,用财而不吝亦不费,在诸欲中可谓甚清甚雅,无害于人品者矣。”[4]773这种“离经叛道”之语,正是政治与文化失衡,士人整体道德感幻灭后的一种反讽。
㈡捧角者的心理动机
文人在捧角过程中,实乃自有寄托“全凭一部伶官传,陶写生平乐与哀”,如易顺鼎云“卅载春明感梦华,只今霜鬓客天涯。还倾桑海十行泪,来写优昙一朵花”,为伶可以哭,可以笑,甚至如癫如狂,行径荒唐,其心理结构其实是寻求一种寄托,当舞台上经过美化的明星的某种特质契合自己的内心需求时,就会很自然地将自我欲望投射到演员身上,渐变成一种背离现实原则的精神依赖。这是一种移情效果,明星只是这种欲求的代偿物[10]115。
当然,非理性的追捧,甚至会为自己喜欢的伶人辩护而攻击他人,堕入无聊的恶趣味,“棋劫兴亡谁管得,缓歌漫舞当中兴”,如易顺鼎卷入的鲜灵芝与刘喜奎之争:
一班莘莘学子,赳赳武夫,以及失意名流、浪漫政客,日以捧坤角为正事,揄扬褒贬之诗文刊满报章,此倾彼轧,酿成笔战,鲜刘一场恶仗,加入者近百人,大好报纸供若辈无聊之笔战,甚至树党立社,虚糜有用之精神,大不可惜哉![11]3
凡事过犹不及,不唯有玩物丧志之非,亦消解和偏离了知音本身的正当性,故难逃等诸下郐之讥。
有些捧角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民国二年喧闹一时的冯贾之争,一方是备受樊增祥、易顺鼎青睐的老派旦角贾碧云,一方是柳亚子等推重的新秀冯春航,一场本属梨园行内的争胜,因为支持者分列不同政治阵营,而上升为火药味益浓的“党争”,“犹是满清遗老,流连眷慕,发为歌咏,不少故国旧都之感,则虽谓贾党为官僚派之代表可也”[12]105,带有了明显的政治目的。
㈢捧角现象的文化背景
民初遗民文人观戏时的心态,颇值得玩味,一次荀慧生在《柳如是》中,对钱谦益多诋毁,樊增祥观之大怒“不终场而去,后作诗贻荀,结句云‘毕竟虞山才可爱,劝君休唱柳枝娘’,而语及荀之编剧,辄骂竖子,悒悒不释”。又一日樊增祥、林纾、罗瘿公等观程砚秋《汾河湾》,其中薛仁贵念白中有“倘若失节……将他杀死”句,林纾大骂“真混账”。这些虽为逸闻,而对那些前朝旧人而言,“失节”的梦魇,足以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
孟森先生有感于民初遗民的捧角热,谓之曰:
易代之际,倡优之风,往往极盛。其自命风雅者,又借沧桑之感,黍麦之悲,为之点染其间,以自文其荡靡之习。数人倡之,同时几遍和之,遂成为薄俗焉。由近日之事,追配明清间事,颇多相类。[13]89
处鼎革之际,发易代之悲,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由捧角亦可见一斑。
三、结语
我们讨论百年前热闹的捧角现象,有对当下粉丝文化的反思之义,作为都市亚文化的产物,两者都试图在对明星投射情感的同时,获得其他情感的慰藉与补偿,但区别在于,捧角群体都是文化水准、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较高的上流人群,即便政治权力丧失,但话语权力仍在,他们的评判标准在于艺术,对戏剧有雅化的提升。反观今天的粉丝,呈现低龄化、低俗化,只关注颜值、八卦。偶像追求高片酬、高曝光,不琢磨剧本、演技,久而久之,一切公共话语都趋向娱乐和庸俗,最终审美畸形,文化枯萎,这是极其可怕却又极易发生的。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捧角这一段文化史,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为当下整顿艺人队伍、规范观众行为的对策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