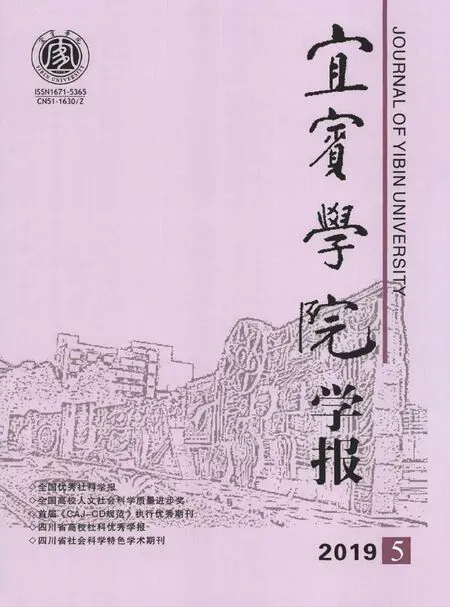论刑法中的公共场所
——以人际关系为补充标准
2019-03-05刘昱彤
刘昱彤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公共场所”在《刑法》中出现过多次并散见于分则不同章节中,是犯罪发生的时空条件之一,也作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和加重情节而存在。从《刑法》条文规定来看,涉及“公共场所”的罪名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但《刑法》中仅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中列举了“车站、码头……”等典型的公共场所,相关规定中也缺乏针对“公共场所”的实际可行的认定标准。随着社会变迁,“公共场所”的含义更加丰富,与“非公共场所”之间的界限更为模糊,实务中对非典型公共场所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需要对其进一步解释。
一、刑事审判对“公共场所”的认定情况
判决书中对“公共场所”的判断标准有以下几种:公共场所是指供不特定的多数人出入、停留、使用的场所。①公共场所应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大众的活动场所。②公共场所应具备三点要求:一是空间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二是人员的不特定和高流动性;三是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化。[1]
总结以上观点可以得出,“多数人”和“不特定性”是判断“公共场所”的主要标准,仅有“特定人”存在的场所通常不能认定为“公共场所”。从应然角度看,在满足人员数量的情况下,场所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是公共场所的形式标准,人的“不特定性”是公共场所的实质标准,具备了“开放性”和“流动性”也就意味着有资格进入该场所的人的“不特定性”。然而,“特定的多数人”存在的场所是否应完全排除在“公共场所”之外?“不特定性”的具体标准应如何确定?
为了解司法实践中对“公共场所”的考量因素,本文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筛选出对“公共场所”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的案例并分类进行了比较和总结,以期得出不同罪名对“公共场所”的不同要求和更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
(一)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法益是公众的生命健康,法益内容的公共性和重大性决定了“公共场所”的判断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判断的难点依然在于“特定的多数人”存在的场所中“特定性”的标准。
案例1:法院。被告人张某将灌满汽油的矿泉水瓶非法携带至法院执行局楼下,将汽油泼洒到车内及自己身上,后因被及时制止而未发生严重后果。辩护人认为,去法院的人基本上是办事打官司的即属于特定人员。进入法院执行局须经过严格的检查和登记。检方认为,案发地是执行局的院区,而不是法院办公楼内,进入法院第一道门并不需要检查登记,只有进入法院办公楼的人员须经过安检登记。进入法院的人数众多,属于不特定的对象。[2]法院认为,执行局院内属于可以让不特定人群出入的场所,应当属于相对开放的公共场所。事发时许多行人进入院内围观,这些人员为不特定对象,场所也具有相对的开放性,该场所应当认定为公共场所。张某构成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③
从案例1可以看出,“不特定性”是判断公共场所的重要标准,而对“不特定性”的判断主要根据进出该场所是否受到一定限制或经过一定手续。法院的观点是,不需经过安检登记即可进入的场所属于相对开放的公共场所,能够进入的人员即为“不特定”人员。那么,如果对出入场所的人员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登记和检查,是否就能使他们失去了“不特定”的特性成为“特定”人员,并且能使得该场所失去“公共”特性,得出该场所不属于公共场所的结论?要使进出场所的人员形成“特定性”,需满足何种程度的限制条件和检查手续,最终才能得到改变案件定性的后果?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思考。
案例2:学校。被告人萧某甲手持枪支进入某小学教学楼二楼一正在上课的教室。法院认为,被告人非法携带枪支进入正在上课的学校,危及校园安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携带枪支危及公共安全罪。④
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学校属于“公共场所”,但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学校内人员的“特定性”。中小学校通常仅供老师和学生进入,具有人员组成的“特定性”,按传统判断标准应当排除在“公共场所”之外。但是,学校的门禁管理很难保证达到严格的程度,不同学校、不同时期的门禁严格程度也相差甚远,存在有机会进入校园的“不特定人”。同时,学校人数众多,组成人员构成较为复杂,有“公共场所”的部分特征,但不属于典型的“公共场所”。
案例3:住宅楼电梯间。被告人纪某某携带枪支在某小区住宅楼电梯间向吸毒人员田某贩卖毒品。法院认为被告人纪某某非法携带枪支进入公共场所,危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行为构成非法携带枪支危及公共安全罪,与其所犯贩卖毒品罪数罪并罚。⑤
在案例3中,法院将住宅楼的电梯间认定为“公共场所”,但并没有考虑该住宅楼是否仅供“特定”人员使用。另外,如果有证据证明电梯间满足人员组成的“特定性”,是否能够影响对“公共场所”性质的判断?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保护的法益是公共秩序,该类犯罪中涉及“公共场所”的罪名成立的关键在于该场所能否形成“公共秩序”和行为能否造成场所中“公共秩序”的混乱。
案例4:学校。被告人张某某安排多人先后驾驶8台小汽车封堵县一中校门长达8小时,致使车辆无法出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致使工作和教学无法进行,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堵门行为已经造成了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但并未致使学校的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根据《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改判为寻衅滋事罪。⑥
案例4中封堵校门的行为最终定性为寻衅滋事罪中“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证明,堵塞校门的行为虽然仅能造成学校范围内秩序的混乱和进出校门的“相对特定”人员利益受损,同样可将其认定为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场所”。
案例5:政府办公场所。被告人王某多次到政府综合办公大楼等办公场所无故纠缠、谩骂办公人员并将公安出勤人员殴打致轻微伤。法院认为,区公务大厦不但是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也是人民群众办理事务的场所,系社会公众共同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应认定为公共场所,被告人王某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⑦
案例6:政府办公场所。被告人彭某甲在区政府机关大院上访,在办公场所吵闹、唱歌、裸奔。法院认为该行为扰乱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但公共场所应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大众的活动场所,政府机关大院是行政部门办公场所,不宜认定为“公共场所”,并未支持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⑧
案例5和案例6都发生在政府办公场所这一场景中,但最终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因在于案例5中的“公务大厦”面向公众开放,案例6中的“机关大院”仅供机关内部人员办公。
案例7:咖啡店后厨。被告人苌某在其工作的咖啡店厨房内持菜刀将吴某砍伤,又在厨房通往外面的消防通道内将张某砍伤。法院认为,本案发生于苌某工作的咖啡店后厨,是相对封闭的场所,行为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公共秩序,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构成故意伤害罪。⑨
案例7中,法院认为后厨不是“公共场所”的原因是后厨相对封闭。后厨与学校、政府内部办公区域类似,同样通常仅供工作人员即“特定多数人”使用,且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因而通常认为其不属于“公共场所”。但学校也属于存在“特定多数人”的场所却往往被认定为“公共场所”。该类场所中能够被认定为“公共场所”的因素有必要进一步思考。
(三)强奸、猥亵类犯罪
“在公共场所当众”是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加重处罚的情节。实务中教室、宿舍等场所能否被认定为该类犯罪中的“公共场所”,仍存在较大争议。
案例8:教室。被告人齐某在担任某小学班主任期间在学校办公室、教室、洗澡堂、集体宿舍等处多次对多位被害女童实施奸淫、猥亵行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认为本案符合“公共场所”“当众”:行为发生的集体宿舍供20人使用,具有相对涉众性和公开性,是公共场所;床铺缺少遮挡,行为能被他人感知,符合“当众”要求。⑩
案例9:宿舍。被告人王某某翻墙进入校园内女生宿舍猥亵多名女学生。法院认为,学生宿舍是供特定的人员即住在该宿舍的学生生活起居的固定场所,相对封闭、独立,不属公共场所。
指导性案例将教室和集体宿舍等认定为强奸、猥亵犯罪中的“公共场所”。此类场所具有供“不特定”未成年人活动的“不特定性”,也有除师生外其他人不得随意出入的“特定性”。但是,强奸、猥亵犯罪中有多人存在的教室被认定为“公共场所”已经成为共识,但同样具有“相对封闭性”,供“特定”人员活动的场所,宿舍是否属于“公共场所”仍存在争议。判断该类犯罪中“公共场所”的标准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四)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
扒窃构成盗窃罪必须要求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但不同于上述罪名,“公共场所”与盗窃罪所侵犯法益的关系并不密切,实务中却并未突出这一特点。
案例10:学校。被告人李某某在某小学开学时进入该校教学楼二楼某教室内对被害人实施扒窃。法院认为,对公共场所的界定应随着不同的时期、面向的群体和范围加以改变。本案因系学校报名时间,学校允许其他相关人员进入学校,此时学校成为公共场所,故李某某的行为符合“在公共场所扒窃”的特征。
案例10中法院认为是否构成“公共场所”的关键在于对该场所的进出管理是否严格。学校开学时期允许不特定人进入,因而成为“公共场所”,一般情况下并不构成“公共场所”。该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
二、从刑事审判中得出的结论和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案例的归纳不难发现,不同罪名对“公共场所”的要求不同。本文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对“不特定性”要求较低,供特定多数人使用的场所能够被认定为公共场所。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涉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和聚众斗殴罪时学校被认定为公共场所有一定困难,而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中学校基本能够被认定为公共场所,机关单位内部办公场所则很难被认定为公共场所。强奸和猥亵类犯罪对“不特定性”要求不高,有多人存在的教室能够被认定为公共场所而宿舍并不一定都不构成公共场所。扒窃行为的成立对公共场所的要求最低,范围最广。
(一)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刑法规定公共安全类犯罪的目的是保护“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利益,从而将个人利益抽象为社会利益予以保护。[3]687这意味着该类罪名重视量的“多数”认定,否则不能称其为保护“社会利益”。其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由于行为人携带物品的危险性,加之发生在公共场所,有可能会对多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直接的、有放大效应的危险。认定某场所是否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中的公共场所,应先判断其是否满足“多数”或者“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对“特定性”的要求相对较低。
因此,案例1中的法院执行局即使对出入人员进行了安检和登记,案例2中的学校即使装备了严格的门禁管理系统,由于其涉及“多数人”,如果在该场所内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仍应将其认定为公共场所。而案例3中如果该住宅楼电梯间仅供特定住户使用,如果住户的人数满足“多数”要求,也应认定为公共场所。
(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明文规定“公共场所”的罪名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根据罪名保护的法益不同,“公共场所”的成立有很大差异。
有观点认为,“公共场所”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场所是指车站、商场等人流量大、向全社会开放、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狭义的公共场所是指学校等仅允许特定多数人出入并从事特定活动的场所。与“公共场所”相对应,“公共秩序”也有广、狭义之分。[4]55
本文认同此观点,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场所”与其他罪名存在区别:
第一,从法条的规定内容来看,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公共场所”要求相对较低。按照体系解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规定“车站、码头……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其中“其他公共场所”的性质应与前述典型公共场所一致,对人员数量和“不特定性”要求很高,仅包括广义的“公共场所”。聚众斗殴罪规定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达到“社会秩序严重混乱”,该标准可根据《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断,即造成工作教学等无法进行、达到严重损失的程度;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要求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有观点认为,公共场所秩序是特殊形式的社会秩序,侵犯公共场所秩序必然侵犯社会秩序[5]。然而此处的“社会秩序”不能等同于法条规定的“社会秩序”,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成立不能直接以“社会秩序”混乱为标准,而应以“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为标准,应当包括狭义的“公共场所”。第二,寻衅滋事罪为了保护法益和处罚均衡存在,具有补充性。[6]例如,某行为发生在狭义的“公共场所”中,无法满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要求,但的确造成该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值得科处刑罚,则可以判断其能否构成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第三,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场所”仍然对人员数量和“特定性”存在一定要求,即要求场所内部能够形成“公共秩序”,否则不可能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
(三)强奸、猥亵类犯罪
强奸、猥亵犯罪中的“公共场所”与其他犯罪相比,更有必要进行扩张解释。
第一,强奸、猥亵犯罪中的“公共场所”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相比,对“不特定性”的要求较低。扰乱公共秩序类犯罪保护的法益主要是公共秩序,因而对“公共场所”的人员数量和特定性有一定程度的要求。而强奸、猥亵类犯罪因发生在公共场所加重刑罚的目的主要是保护被害人的性羞耻心,并不在于社会秩序混乱与否,从保护被害人层面考虑理应对“公共场所”予以扩张解释。将“特定的多数人”存在的教室解释为“公共场所”属于合理的扩大解释,既符合公民认知也未超出“公共场所”的最广含义。[7]
第二,要实现加重的法定刑要求“公共场所”和“当众”两个要素,“当众”理解为有现实的多数人在场,从而推定有多数人发现的可能性。[8]《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当众”认定体现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扩张解释。
(四)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
《盗窃司法解释》将“扒窃”定义为在“公共场所”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公共场所是扒窃的多发场所,但不能决定行为本质或者改变行为法益侵犯程度。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扒窃与普通盗窃罪相比并不能明显降低社会安全感,另外,扒窃中的“公共场所”与《刑法》中其他有“公共场所”规定的罪名不同,不能因发生在公共场所就加重不法内涵。扒窃与其他盗窃的区别在于未经允许侵入他人贴身范围的“贴身禁忌”。[9]例如,清洁人员进入仅供A使用的办公室窃取A身上的财物,应同样认定为“扒窃”。
因此,本文认为,对扒窃案件中“公共场所”的判断应进行最大化的扩张解释,无论是广义的公共场所,还是学校、机关单位内部办公场所等供特定多数人员出入的场所,抑或是单人办公室,也不必纠结于该场所的出入管理是否严格,只要行为人没有达到与被害人能够亲密接触的程度实施了盗窃行为均可认定为扒窃行为。
分析案例可以得出:“特定性”是判断公共场所的重要标准,实务中多通过门禁管理的严格程度判断。同样存在“特定多数人”的场所如学校、机关单位内部办公场所、宿舍、后厨等,“公共场所”的认定有较大区别。
但是,还有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第一,“特定性”的具体标准应如何确定,是否应按照门禁的严密程度来判断?第二,“特定的多数人”存在的场所如何能被认定为“公共场所”?第三,同样存在“特定”人员的场所,学校、后厨、政府内部办公区域的性质有何区别?教室和宿舍的性质有何区别?判断“公共场所”是否还有更确切的标准?
三、“公共场所”的判断规则——以人际关系为补充
实务中对“公共场所”通常的判断方法是门禁的严密程度,但该方法存在不确定性,也并未对不同罪名中的“公共场所”加以区别,造成“公共场所”的认定中存在较多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将人际关系理论引入“公共场所”的判断中。
(一)判断“公共场所”应考虑的标准
根据门禁的严密程度判断公共场所的“特定性”,会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因门禁的严密程度决定场所特定性的改变存在随意性。现实中很多场所要求仅供内部人员出入,但实际上由于管理缺陷、管理人员工作态度抑或是特殊活动举办等,其他人也有进出的可能。第二,门禁的设置情况有差别。有场所设置门禁仅供内部人员进入,但也有场所也供其他人员进入。例如,进入法院需要进行安检,但能进入的并不都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相当数量的当事人和律师等,如果认为经过了安检就具有了“特定性”并不合理。第三,“特定性”有性质上的区别和程度上的差异,不同罪名中对“特定性”的要求不同,以门禁为判断标准过于片面。例如,同样都设有门禁的场所,如学校和机关内部办公区,在寻衅滋事罪中被认定为公共场所的结论不同。
“公共场所”的界定应考虑“公共场所”得以存在的目的。《刑法》中规定“公共场所”有以下目的:第一,在公共场所实施犯罪会导致犯罪的危险性增加:一方面,场所中的人可能成为潜在犯罪对象,更有可能对更多人造成直接的现实的人身危险。即使没有造成切实的人身伤害,也容易增加场所中人员的恐惧感。第二,在公共场所实施犯罪会侵犯公民对社会治安和公共生活安宁有序的信赖感。公共场所通常被人们认为受到国家管理,是相对安全的场所。在公共场所中实施犯罪会侵犯公共秩序底线。在强奸猥亵类犯罪中会给被害人带来更大程度的受辱心理。第三,公共场所具有更高的制度化涉入程度,一般人处于公共场所时行为通常都会有所收敛。行为人选择在公共场所实施犯罪体现了更严重的主观恶性。
(二)判断“公共场所”应结合人际关系标准
在满足“多数人”条件下,对公共场所的判断应结合场所中的人际关系确定。特定性的判断标准之一是场所的封闭性与否,但特定性的本质在于场所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越亲密,场合控制的松紧程度越低,[10]行为的可接受程度越高。同时,人际关系越陌生,场合对行为的要求越高,行为对场合中其他人的影响越大。
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在差序格局中形成:每个人就像一颗石子落在水面上,形成的一圈圈波纹就代表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法律和道德没有统一标准,因判断对象与自己的关系不同会产生程度上的限缩。[11]同一犯罪行为对社会和对被害人造成的影响,会因行为发生时身处其中的人的亲疏远近而有所差异。人际距离的学说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人际关系的“参照系”。人类学家E.霍夫认为人际距离可分为:亲密距离(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个人距离(朋友之间)、社会距离(上下级、师生之间)和公众距离(陌生人之间)。[12]
将人际关系作为“公共场所”的补充认定规则,将对司法实务中有关“公共场所”的判断起到积极作用:第一,人际关系标准与公共场所的传统判断标准相协调。公共场所的判断与所能涉及的人数密不可分,在具体判断时人际距离的观点能与人员数量的判断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在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中,总是最靠近中心的同心圆面积最小,而越远离中心的同心圆面积越大。人际关系越松散越陌生,涉及的人数越多,对公共秩序的影响越大,人际关系越紧密,涉及的人数越少,对公共秩序的影响越小,最熟悉的人际关系存在于刑法意义上的“户”。第二,人际关系标准具有一定稳定性。相较于门禁的严密程度,人际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不会造成判断的随意性。第三,人际关系标准符合“特定性”的复杂程度要求。特定性原本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在涉及不同法益的罪名中应当有程度区别。第四,人际关系标准符合刑法规定“公共场所”的目的,有利于判断行为的法益侵犯程度。例如,性侵犯案件发生的场所不同会造成对被害人羞辱感的差异,扰乱公共秩序类案件发生在不同人际关系的场所中公共秩序受到影响的程度不同。
(三)以人际关系作为补充规则的具体适用
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学校、后厨、机关单位内部办公区域同为“特定的多数人”存在的场所,在“公共场所”的认定中存在差异,原因不仅在于三者的人数差别,也源于三种场所中人际关系的性质不同。虽然学校仅供师生进出,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有“特定性”,但学校内部成员是“不特定”的:学校中班级之间、年级之间、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相当一部分人员达不到与他人熟识,只能满足社会距离甚至是公众距离的程度,能够形成场所内部的“公共秩序”。相较于学校,机关单位内部办公人员之间和后厨同事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基本形成了长时间的合作关系,通常情况下大部分成员能达到熟识程度,人际距离通常应认为处于个人距离与社会距离之间,对内部成员不良行为的包容性较高。因此,同一起哄闹事行为在学校范围发生能影响学校的公共秩序,构成寻衅滋事罪,但在内部办公场所由于没有形成正式的公共场所秩序,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并不合理。
在强奸、猥亵类犯罪中,教室和宿舍同样供“不特定多数”人员活动,但在公共场所的认定上有很大区别。在此类案件中教室被认定为公共场所已经成为共识,但宿舍的性质存在一定争议,大部分宿舍被认定为不是公共场所,但在部分案例中集体宿舍也被认为是公共场所。教室、宿舍之间的性质有何差别?有观点认为,不特定性指成员之间具有不固定性:使用学生宿舍的人员具有固定性,使用教室的人员不具有固定性;因而学生宿舍则具有特定性,不是公共场所,教室具有不特定性,是公共场所。[13]
本文认为,“固定性”无法作为区分教室和宿舍性质的标准:根据普通中小学校的管理规定,同一时间内教室和宿舍的使用者都是基本不会变化的人员,人员组成都具有一定固定性。还有观点认为,宿舍具有“相对封闭”、“供他人生活”的特点,但该观点难以解释集体宿舍同样具备以上特点但仍被认为是公共场所的情况。
生活在同一宿舍中的成员通常人际关系更为亲密和熟悉,基本应处在个人距离,对被害人带来的羞耻感相对较弱。集体宿舍由于人数较多,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更弱,成员间的人际关系更类似于教室,接近社会距离。发生在教室和多人集体宿舍的性侵犯案件可能会造成更多相对陌生的人员参与或感受犯罪过程,对被害人造成更严重的受辱心理。
结语
《刑法》中不同罪名对“公共场所”的要求有所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要求人员数量满足“多数”或者“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对“特定性”的要求相对较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对人员数量和“不特定性”要求很高,聚众斗殴罪的要求较高即能达到“社会秩序严重混乱”,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公共场所”要求相对较低,要求场所内部能够形成“公共秩序”。强奸、猥亵犯罪应当“公共场所”进行扩张解释,对人员数量和不特定性要求较低。盗窃罪中的扒窃对“公共场所”的判断应进行最大化的扩张解释,对“公共场所”的要求最低,范围最广。
“公共场所”的本质在于处于其中的人的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对场所的“特定性”存在疑问时,有必要结合人际关系标准判断。
可能有观点认为,人际关系标准太过模糊,同样不利于判断公共场所的性质。本文认为,公共场所是一种模糊的场所,在刑法中“户”的范围之外的所有场所中都有可能存在,需要尽最大努力缩小“公共场所”与“户”之间的中间地带的范围,人际关系标准无疑对这一范围的缩小起到了一定作用。
注释:
①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梧刑一终字第38号刑事裁定书。
②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4)岳刑初字第369号刑事判决书。
③ 参见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3刑初224号刑事判决书。
④ 参见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
⑤ 参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刑初字第287号刑事判决书。
⑥ 参见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潭中刑终字第281号刑事判决书。
⑦ 参见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2015)菏牡刑初字第517号刑事判决书。
⑧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4)岳刑初字第369号刑事判决书。
⑨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2015)上刑初字第57号刑事判决书。
⑩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http://www.spp.gov.cn/spp/jczdal/201811/t20181118_3993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