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面对面
2019-03-04安刚
安刚
2018年底的一天,我有幸应曲博副教授之邀,去外交学院听了“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为该校师生做的讲座。
艾利森教授此次来华讲学,是为了配合他的近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文版(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发行,并出席在上海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研讨会”。
可以谈判确立“长和平”
已是耳熟能详,“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源自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就是指新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也必然做出回应,由此战争变得难以避免的历史规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崛起国古代雅典与守成国古代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0多年,最终斯巴达获胜,希腊由盛转衰。

格雷厄姆·艾利森
在讲座中,艾利森一如既往地介紹了他对有史以来16起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案例的分析,在那些案例中,12组最终滑向战争冲突,只有4组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说,我研究的终极命题是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方面,中美双方都知道必须避免战争,经济联系的紧密性既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也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中美注定一战”中的“注定”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两国竞争已不可避免,“旧日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The good old days has gone.),而且这种竞争的广泛性、特殊性和同体系性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我们该何去何从?”艾利森在他的《注定一战》中同样提出了这个在两国学界已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问题。艾利森想要扮演“结构现实主义”者的角色,主张华盛顿对中国的崛起不应只做“政治条件反射”,还要有战略思考,“先诊断后开方”。但他又说美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新的“中国战略”,而是应停下来认真反思——如果美国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美国的“战略”与当年英国、德国、俄国的领导人“梦游般”进入1914年时的幻想进行对比。
艾利森显然对美国的理性反思与调整不抱太大指望,也就拒绝彻底排除中美由竞争走向冲突的风险。艾利森谈及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风险:特朗普需要即刻可以兑现的经贸利益,但特朗普的身边人目标并不单纯,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即便谈出阶段性协议,也有可能受各种因素破坏出现反复从而长期化。中美正在东海、台海、南海同步开展军事上的竞赛,对哪个点上的近距离接触处理不慎都会引发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朝核问题是另一大风险,如果朝美谈判破裂,朝鲜重新走上发展核导能力的道路,美国对朝发起军事打击的概率将大为上升,中国很难置身事外。艾利森还注意到,政治合法性理念的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大“痛点”,他在答问时讲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后若干年决定两国竞争结果的可能并非中美在全球舞台上的表现,而是两国基于自身价值观解决各自国内问题、进行国家建设的实效,历史将根据中美各自的国内表现给出两国竞争的终极答案。
是否存在话语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在2012年前后正式进入中美关系话语体系的,围绕它的探讨已持续六年多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中美战略和现实利益摩擦的凸显,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表面化,两个全球性大国能否妥善处理彼此矛盾、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俨然成为两国高层与战略学界高度聚焦的命题。从这个角度讲,艾利森教授的学术贡献具有某种时代性的意义,无疑成了中美关系新语境的塑造者之一。
在我的工作记忆中,“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一经提出,得到了当时美国当政者的热心推广。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5月胡锦涛主席发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讲话时,正式提出了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而此前,自2005年首轮中美战略对话起,中方就一直在同美方探讨如何避免冲突对抗,共同努力发展出一种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多个场合回应时明显借用了“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思路,公开强调需要“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相遇的老问题寻找新答案”。同期,美方工作层和学术界也频繁提醒中方人士关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新概念”。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他的回忆录《战略对话》一书中对中美之间的这段互动有具体记述。
一个基于历史推演和未来假设且未经充分探究的话题堂而皇之地快速、大面积进入中美关系话语体系,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而这背后隐藏的,是不是也有中美围绕两国关系定义权、话语权的暗中较量?对此,中国国内已经出现了质疑,不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真相有不同的解读,也有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本身,包括“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互动模式”所做的界定,就是个陷阱——“艾利森陷阱”,一种将历史简单化、抽象化的话语陷阱。
我在讲座的答问环节向艾利森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中国学者认为,人们在争相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种“历史宿命论”的逻辑轨道,从而对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产生战略误判,您是否了解这种议论,是否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构成话语陷阱?艾利森插话询问了“话语陷阱”的含义,但由于现场采取了多人集中发问、演讲者统一作答的方式,他最终“忘记了”回应我的提问。
继续找寻大国相处的奥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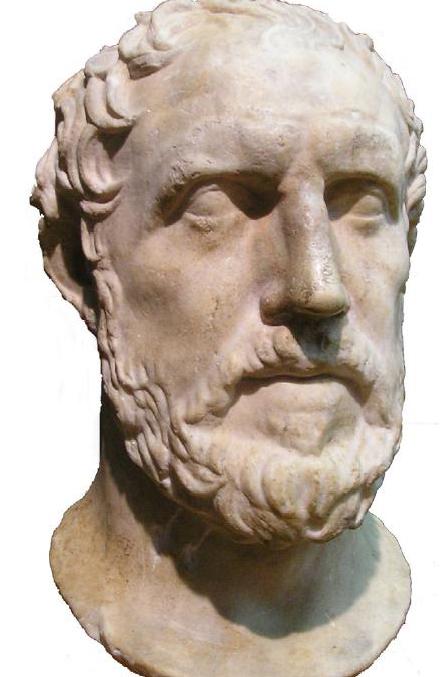
加拿大多伦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塑像
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都有机会亲眼目睹其所研究的课题揭晓最终答案,艾利森教授或许将是幸运的。正因为此,他不想停留在现有的分析水平上,而是急着搜集佐证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各种新观点、新论据,以便随时根据形势变化抛出续篇。今天的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两国交锋向各领域蔓延,一幅新型大国竞争的宏大图卷正在铺展开来,这为艾利森针对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处规律的观察和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现实参照,不过也迫使他承认“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对中美关系做出正确诊断的最佳时机”。艾利森认为两国的当务之急已不再是分析什么有利、什么不利了,而是要想方设法避免真的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他把这方面的思考集中到中美应如何在不启战端的前提下保住各自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对美方而言可能是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和在太平洋上的实际存在,对中方而言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安全。
艾利森说,中美是否“注定一战”,只有肯定和否定两个答案,“历史的例外”不会自然发生。如果继续按照老套路解决中美矛盾,将会重蹈历史覆辙。即便中美不会一战,双方也有必要重温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经济体的首要贸易伙伴,安全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中美通过彼此利益的重置催生亚洲新的结构性现实只是时间早晚的事。艾利森主张重新定义中美关系,通过谈判确立“长和平”。他说,潜在的“共识选单”是丰富的,可通过缔结条约或协议冻结在西太平洋的争端,确认国际水域中的“航行自由”,将网络攻击限制在商定的领域,禁止彼此用特定形式干扰对方内政等。
那天讲座结束后,还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内部研讨会。我谈了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重点讲了两点:一是“旧日的好时光”的确“一去不复返”了,但也有足够多的条件阻止“过去的恶时光”重新上演。中美关系恐怕正在形成新的常态,双方有必要探索出一套新的范式,为两国未来的相互行为共同划出底线和边界,并且厘清可以继续开展合作的领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二是中美双方都有必要形成某种形式的“自我克制”(self containment),而不是费尽心机谋求遏制或取代对方。这种“自我克制”应当包括审慎使用战略语汇,慎重做出结论性判断,克制采取針对对方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举措,以及积极管控危机风险,等等。
艾利森当场回应说,“自我克制”的提法有挖掘潜力,他要回去好好想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可以明确提出的新概念,有什么东西可以往里装。他还补充说,事情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坏,中美双方都知道底线在哪里。
不知有宋
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艾利森教授突然问,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定位到底是什么?我说,对学界而言,很难说对美国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定位,这与中美关系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有关,也与中国对美政策目标的多重性有关,在中方内部围绕到底怎么看美国也还存在一些分歧。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定位的话,可以说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认为美国既是对手又是伙伴,伙伴作用是在部分领域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现在战略对手的意味更强,伙伴的价值在下降、在收缩。将来很难说中美不会互为对手,但如果管理得当,绕开“修昔底德陷阱”,两国或许会成为“竞争性合作伙伴”(rivalry partner)。
艾利森教授听后又问,历史上中国对别的国家有过类似定位吗?苏联是不是?我说,苏联不太像,与中国关系好的时候是真好,中国外交政策“一边倒”,堪称战略盟友;关系坏的时候发展到相互备战,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敌手。中美互为对手是合情合理的,但对手不等于敌手,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但极易转成恶性的。中美要避免敌手化。然而两者界限很难把握,对手概念用多了自然会敌手化,如何把控竞争对双方执政者都提出很高要求。
艾利森接着问,那么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一种类似于“竞争性合作伙伴”的关系状态呢?我想了想,向艾利森教授介绍了中国北宋、南宋时期与辽金对峙的历史点滴,告诉他如果把中国古代不同民族政权并存比作一个相对封闭“国际体系”内的成员互动模式,中国1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或许可以为他理解中国战略文化提供一个案例。当时,两宋与北部强邻实力相当,各有优势,在战争冲突中各有胜负手,相互缔结“休战条约”,互遣使者,开展边境贸易,深度经济交融,甚至文明互鉴,形成较长时期的和平共存局面,但最终执政者错误的战略选择葬送了和平共存,也葬送了曾经互为对手的不同王朝。
聊到这儿,我从艾利森的反应中感觉他对中国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不知有宋,更不知辽金。这就成问题了。艾利森的实证研究几乎完全基于从古代斯巴达和雅典开始的西方文明进化史,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分析主要参考费正清、基辛格等人的西方经典著作,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先验分析,而中国正在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处的主角之一,不增加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艾利森恐怕难以准确推断和概括中国的行为方式。午餐中,我坦率地向艾利森教授表达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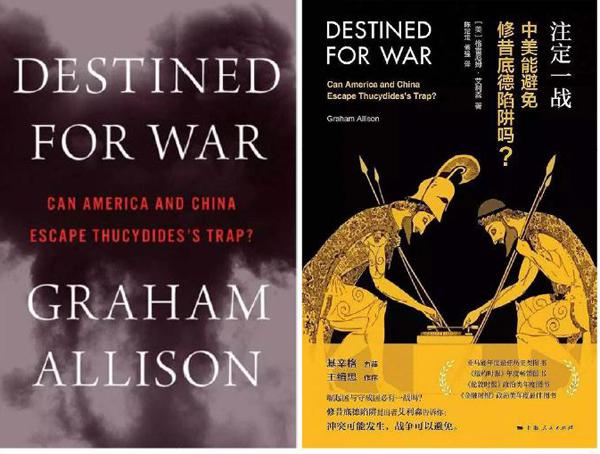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本封面。
在后来的联络中,艾利森教授希望我帮他搜集一些中国学者写的介绍两宋与辽金政权关系史方面的英文文章。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搜遍网络,我发现符合现代讲述习惯的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这方面英文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反映现代启示意义的。经请教中国的历史学者,我只好向艾利森教授推荐了《剑桥中国史·宋代史》《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史》以及《哈佛中国史·宋代卷》。这两套巨著尽管做到了相当客观,却仍是西方人主持编纂的。这件事再次表明,在世界叙事体系中,源自中国的资讯供给显然仍很不足,我们需要增加投入,这样才有能力保持自己逻辑思维的完整性,并且积极影响别人的逻辑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