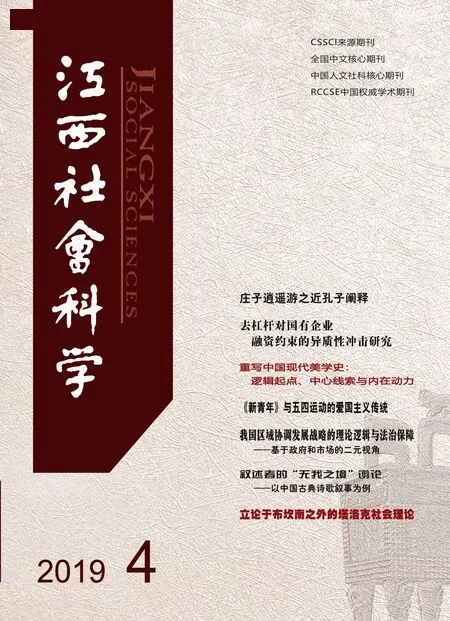立论于布坎南之外的塔洛克社会理论
2019-03-04
戈登·塔洛克一生热衷于思考,他涉猎广泛,其思想极具创造性,然而这份学术遗产的价值却被低估了。世人往往认为塔洛克的“经济人假设”只是补充了詹姆斯·布坎南的观点而已,他始终蜷缩在布坎南的阴影下。实际上二人的关系更像“发散的抛物线”:虽然他们都支持当代世界的自由主义,但是塔洛克的社会理论却与布坎南背道而驰。塔洛克立论于“巴别塔之西”,它不以社会和谐充当起点,而是始于社会不和谐,世人需要从矛盾和冲突中找到出路,这与布坎南立论于“伊甸园之东”可谓大相径庭。塔洛克似乎是经验主义者,他借助实际情况,分析框架依托冲突与演化;而布坎南擅长抽象分析,分析框架依托一致性和技术。
一、导 论
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思考,其思考涉及众多领域,并极具创造性。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的价值却被低估了。塔洛克的思想被人视作蜷缩在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宪法思想的阴影下,他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补充了布坎南的学术思想。与之相反,事实上塔洛克和布坎南的关系似乎是“发散的抛物线”,虽然他们都重视个人自由,但是分析却背道而驰。不同于布坎南,塔洛克从未概括过自己的研究,以致世人认为他只是凭借“经济人假设”简单地补充了布坎南的宪法政治经济学。
塔洛克在1970年后发表了众多不涉及布坎南的成果,然而它们似乎偏离了“经济人假设”的主题。[1]毋庸置疑,塔洛克研究世人应如何利用自身所面对的形势。步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后尘,塔洛克似乎是经验主义者。然而透过其著作却发现他并非理性选择论者,其作品聚焦于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永恒困境。任何社会都不乏那些竭尽所能利用自身所处情势的人,但是这并不能使其成为理性选择论者。塔洛克承认社会中充斥着各种源自互动的突发状况,其著作聚焦于人类在社会中的互动,绝非侧重理性选择。塔洛克远超布坎南所说的“天然的经济学家”[2](P9-19)。虽然理论是现成的,但是塔洛克从未加以概括,他的社会理论较之布坎南可谓差异显著。
塔洛克的著作学术价值极高,这集中体现在美国经济学会于1997年授予他“杰出学者奖”。此外,其他专业性学术团体也授予他荣誉头衔。与此同时,塔洛克的研究被大量引用。例如,他撰写的首篇研究寻租的论文[3]被引用超过4000次,研究有效率寻租的后续论文[4](P97-112)被引用超过3000次。更有甚者,阿特·卡登(Art Carden)和菲利普·马格内斯(Phillip Magness)强调“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塔洛克也应被授予诺贝尔奖”[5]。塔洛克的贡献受到广泛赞誉,但是他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依然被低估了。
笔者同塔洛克和布坎南交往已久,既撰写过有关布坎南的作品,又撰写过有关塔洛克的作品,还撰写过同时涉及他们两人的作品。②虽然塔洛克的社会理论见于其著作,然而本文的很多素材源自笔者同塔洛克的多次交谈。
二、塔洛克与布坎南:一卵双胎?
1947年,塔洛克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学位;1958年,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开启学术生涯。在此期间,他与布坎南商定了《同意的计算》一书[6]的基本原理。该书稿完成于1959—1960年,当时塔洛克就职于南卡罗莱纳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系。1962年,他回到弗吉尼亚大学任副教授。
1962年,《同意的计算》正式出版,它确立了布坎南作为经济理论学家的地位。此前十余年,他还在众多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实际上,布坎南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是“一个重要的进步”[7](P4),它涵盖了若干重要主题(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布坎南于196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7](P24-74),它提醒英语读者,大量涉及公共财政的意大利语文献只对意大利语读者开放。1958年,布坎南撰写的《公共债务的公共原则》一书[8]正式出版。该书在公共债务问题上同凯恩斯主义相左,这体现出众多意大利思想家的“非凯恩斯主义特质”。
与此同时,塔洛克却默默无闻。被授予法学学位后,他先后尝试了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涉及法律事务,但是塔洛克意识到它并不适合自己。随后,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九年,在此期间,塔洛克发表了三篇论文。第一篇[9]和第二篇[10]都与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合作,同年他还在《经济史评论》发文。[11]在开启博士后研究前,他将基于自己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经验所写成的书稿出示给布坎南,它最终以《官僚制的政治》[12]面世。随后,塔洛克在夏洛茨维尔获得了一年期研究员的职位,开始与布坎南共事。
《同意的计算》出版后,布坎南和塔洛克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合作撰写了数篇论文,这使得他们近乎“一卵双胎”的观感仿佛被坐实了。1963、1964年,布坎南和塔洛克以“非市场决策委员会”的名义,召集了由20位学者组成的学会。1966年,塔洛克创办了《非市场决策杂志》。1968年,该委员会更名为公共选择学会,随后塔洛克将杂志更名为《公共选择》。1967年,塔洛克转会至莱斯大学。1968年,布坎南从弗吉尼亚大学转会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于1969年加盟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与塔洛克和查尔斯·戈茨(Charles Goetz)共事。
共事之初,塔洛克与布坎南的密切关系集中体现在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初所进行的无政府研究上。其结晶是由塔洛克编辑出版的两本小册子——《无政府状态的理论探索》[13]、《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再探》[14],它们在出版上晚于由布坎南以及尼科斯·德夫莱特奥卢(Nicos Devletoglou)所写的《无政府的学术》一书[15]。虽然无政府研究是由布坎南和塔洛克完成的,但是却受益于布坎南和德夫莱特奥卢所进行的早期研究。布坎南和塔洛克分别为《同意的计算》撰写附录,相关附录表明他们的研究兴趣存在差异:前者关注政治哲学史,后者关注投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
三、塔洛克与布坎南:分歧乍现?
布坎南和塔洛克研究无政府问题的两部书稿都被提交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但是它们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布坎南的书稿被接受,即《自由的限度》一书[16];塔洛克却被拒稿,最终以《社会困境》[17]为名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对比两书,不难发现作者不再“一卵双胎”,他们越来越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布坎南和塔洛克都强调个人自由,并将政治行动视为一种理性行为。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却渐行渐远,这体现出两人不同的研究兴趣。
布坎南的社会理论基于如下假设,那就是存在一个宪法平衡点,它能够促成宪法共识。较之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布坎南认为不存在使社会收益最大化的点,这些点只能通过宪法上的讨价还价来获得。他假设存在一种点,这种点能够摆脱前宪法的无政府状态,并且社会问题集中在两方面。第一,找到这种点,并将它置于一个合适的宪法框架;第二,确保上述框架免受后宪法政治的侵蚀。因此,布坎南将国家视为政治——经济的均衡状态,这种均衡取决于宪法层面的讨价还价。
布坎南将“囚徒的困境”引入解释框架,以阐释具有自利性的人怎样才愿意生活在共同规则之下。为此,人类创造出政治权力以强制实施人们所认可的规则。实施规则的权力独立于服从这些规则的人,最终成为“利维坦”。由此,布坎南引出了《自由的限度》一书的副标题:在无政府和利维坦之间。他设想了两种现实选择:一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行动;二是将人置于某种规则下,这些规则由一个独立机构负责实施,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利维坦”。该设想被引入分析框架,期待宪法可以制约利维坦的行动。
我曾将布坎南形容为立论于“伊甸园之东”,它包含了若干意思。一者,立论于“伊甸园之东”需要某种起点,也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再理论化。现象不会存在于理论行为之前,这就好似在夏娃(Eve)恳求亚当(Adam)偷吃禁果之前,在伊甸园中不存在人类现象。最好的手段是特定的宪法安排,它能够制约利维坦的掠夺行为,这种分析属于比较静态研究。涉及生命的原始数据就在伊甸园中。伊甸园的产物是一种外因,它涉及不同数据,一道为生命创造新环境。在地理因素的制约下,存在多种方式使人们生活在一起。正如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一书中所说的,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多数人有可能将自我保护的权力转交给利维坦。
对布坎南来说,政治在有限范围内是有益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宪法或许能够制约政治。由此他揭示出一条主线,这与彼得·勃特克(Peter Boettke)[18]之后的主流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布坎南主张运用经济、法律和道德等手段,将政治削弱为一个消除点,只为必要的政治行为留下空间。上述观点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9]不同,后者强调保留政治在社会中的自主性。将政治弱化到近乎虚无的地步,这体现出宪政治理思想的理想自由观。政治被压制到近乎消失的地步,这种压制由经济来实现,公共产品理论揭示出政治对公民愿望的满足就好似生产者对消费者愿望的满足。契约理论揭示了政治在社会中的退场,而法律和道德将产生类似作用。世人能像布坎南那样认为自由宪政主义从未令政治彻底退场,并且得以延续的自由宪法引发了全社会的挑战。
塔洛克不同于布坎南,他在某些方面并未从相关理论的起点出发。塔洛克往往从一些实际点位出发;或者说,其立论基于媒体资源。虽然有时他也谈到均衡,然而较之布坎南,塔洛克并未将社会均衡理论化——后者认为社会和谐能够通过普遍的赞同来实现。在他看来,社会和谐是一种想象,它在历史上无先例可寻;而社会不和谐倒是常态。社会是一个竞技场,它充斥着层出不穷的内部斗争,其烈度从相对温和到群情鼎沸。在《社会困境》一书中,塔洛克将战争、革命以及政变视为某种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潜在现象。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满足于现状的人将会安于现状。但是还存在一些不满足于现状,并力图改变原有秩序的人。塔洛克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社会向善论者,他认为在生命中充斥着层出不穷的困境,并且大多数难以避免。
布坎南经常借助核心思想来推动研究。虽然将研究成果的片段以及上溯至1963年9月的大量谈话加以拼凑是有可能完成一项重要研究的,但是塔洛克并未这样做。在《风险、不确定和利润》[20]一书中,奈特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来分辨布坎南和塔洛克的研究方向。除两章介绍性内容外,该书分为两部分——分别涉及完全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奈特所说的完全竞争同当代经济学家所说的完全竞争极其相似——绝无可能在一人获益的情况下,而不使另一人受损。完全竞争需要一系列理论前提,在它们的约束下,社会内部所有可能的交易所得都将被剥夺。
完全竞争理论代表了一种演绎推理,它同乔治·波利亚(George Polya)所说的合情推理[21]构成鲜明对比。完全竞争是一种理想状态,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同于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奈特认为理想与现实之间虽然存在鸿沟,但是并不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加以弥合。恰恰相反,正是这一鸿沟激起了旨在对其加以缩小的举动,应该说这是有利的。同其他学者一样,布坎南和塔洛克都非常了解奈特的思想。他们在如何吸收奈特的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是都借鉴了相关思想。当布坎南将焦点从奈特所关注的市场转移到政治后,对他来说,奈特关于完全竞争的看法就成了一个宪法一致点。宪法行为与后宪法行为之间的鸿沟呼唤那些试图从交易中获益的联盟,而代价由这些联盟的外部人来承担。虽然布坎南立基于奈特对完全竞争的看法,但是他也秉持了奈特对不完全竞争的看法。相比之下,虽然塔洛克偶尔提及均衡,但是他坚决围绕过程立论。他认为现实是无定数的,因此难以达成普遍共识。
我曾指出塔洛克的理论源自“巴别塔之西”,这与布坎南从“伊甸园之东”立论构成鲜明对比。“巴别塔之西”意味着不将社会和谐作为起点,它始于社会不和,人们需要在社会矛盾中寻找出路。通过从中间情境展开分析,塔洛克的著作无不揭示出世人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巴别塔之西”的理论世界充斥着不和谐,通过宪法建设以重拾美好社会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通过明晰理性行为如何引发了战争与革命,这些启示将有助于接受社会向善论,而这也是人们期盼从经济分析中所获得的。我从未听闻塔洛克反对哈耶克(Hayek)的著名论断——有必要创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景来重拾自由主义的活力,并且我怀疑塔洛克是否反对哈耶克所表达的某种情绪以及这种情绪将足以改变现实。
四、塔洛克社会理论的提取
从“巴别塔之西”立论需要秉持社会关系的演化系统观,在社会关系中蕴含着大量的合作与冲突,这揭示出人类的困境,那就是很多人希望成为“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然而位子却很有限。塔洛克从未拒绝运用博弈论来研究问题,但是他对布坎南经常使用的“囚徒的困境”却很谨慎,理由接近于丹尼尔·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22]。
塔洛克肯定不会拒绝以下观点——如果生活允许的话,政治终将消失。然而他强烈质疑政治将会消失的观点,政治的消失预示将出现一个狮子与羔羊和谐共存的“和平王国”。塔洛克认为人类社会永远包含着冲突,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特征。在这一点上,塔洛克与施密特[19]较为接近,后者对政治的看法近似“敌友之分”。施密特的理论更适合国际关系领域,这与塔洛克在《社会困境》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不尽一致。换句话说,塔洛克的观点更适合国内政治。例如,税收和支出问题在西方将引发永无止境的冲突。[23]一次争吵有可能被暂时压制,然而新的争吵又接踵而至。“感觉良好的时代”有可能出现,此时在社会内部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共识。然而,威廉·瑞克(William Riker)认为这些好感觉将消失在涉及预算等问题的争吵声中。[24]
似乎塔洛克从未引用过施密特,并且施密特也并未出现在塔洛克精选的十卷本著作的索引当中。即便如此,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却相当接近。雷纳托·克里斯蒂(Renato Cristi)将施密特的观点形容为威权自由主义[25],埃克哈德·博辛格(Eckhard Bolsinger)将其视为政治现实主义[26]。上述看法不禁使人想起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对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n)政治思想的评价。[27]在此有必要回顾詹姆斯·F.斯蒂芬 (James F.Stephen)[28]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自由主义思想[29]的批判。施密特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解释为国家领导层难以抵制利益集团的掠夺行为。这一论断很好地体现在克里斯蒂所写的《卡尔·施密特与威权自由主义:强大的国家,自由的经济》[25]一书的副标题中。施密特认为,纯粹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维持自由制度。然而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弱国家,它难以抵制某些利益集团的掠夺。
塔洛克研究寻租问题的著作建立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具体来说少数人往往有能力集中获益,而多数人却因此受损,甚至在某些时候,损失超过了收益。长期以来,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承认利益相对一致的少数人在民主政体下拥有优势。假设存在一个包含1000人的政体,其中50人强烈关注某一事项,而另外950人却无所谓。这意味着950人可以通过掷硬币来决定如何投票,而偏好相对集中的50人将统一投票行为。在这种模式下,一个50人的群体将在80%的时间里达成目标,一个75人的群体将在99%的时间里达成目标。[30](P86-89)
如果在政治过程中涵盖了一系列具有相似偏好的事务,那么自由的宪法秩序将受损于贸易保护主义。而“一个强国家有利于抵制利益集团掠夺行为”的观点回避了相关问题。对这一点的阐释或许有助于解释在社会交往中,维持自由制度的难处。假设某国的公共财政包含一定的关税,这同引入所得税之前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共财政极其相似。世人似乎可以认为,适度的关税并不损害自由治理的原则。较低的关税似乎是一种合理手段,它能为政府提供财源。
低关税难以显著地改变通过市场交易所形成的商业模式。毋庸置疑,进口商品将更加昂贵,以致国内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进口商品。高低关税之间的临界点并不显著,它不会引发逃税行为(低关税不会引发走私,关税高于临界点将引发逃税行为)。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主过程”将产生足以引发走私等逃税行为的高关税。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假设关税使国内2/3的人需要购买的相关商品的价格上升了,并且关税的收益归入少数资源所有者囊中。[31]关税越高,越有可能引发走私,并催生出鼓励走私的新型商业模式。它还会导致政府的扩张,以侦查和起诉走私活动,毕竟走私破坏了私有财产以及自由契约等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随着关税由低到高,经济活动中的私人秩序逐渐让位于公共秩序,最终取代了私有财产以及自由契约作为经济交往原则的地位。由于国家难以抵制关税的上涨,以致公共秩序嵌入到私法领域之中,使政治在社会中进一步膨胀。塔洛克承认一纸宪法不可能抵制这一膨胀,只有当政治与社会彼此直面之时,这种抵制才有可能。
五、塔洛克社会理论的详述
通过梳理布坎南的作品,不难发现它们仿佛是一株成熟的橡树,这棵树脱胎于布坎南在第一篇论文[32]中就埋下的想法和灵感。在文中,他对比了公共财政研究的个人主义论以及在当时支配公共财政研究的有机论。布坎南的成就源于他最初的研究兴趣,那就是重构在“真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财政理论。虽然其他人对布坎南的研究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我坚信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阅读布坎南的著作,不难发现其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关联。然而对塔洛克这就显得难多了。塔洛克向我们充分展现了局部,但是他并未提炼出核心观点。根据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对思想家所做的刺猬和狐狸之分[33],上述学者当属狐狸。塔洛克探讨了众多主题,然而他并未明确核心观点,因此在广大读者的眼中他更像一只狐狸。此外,塔洛克在方法论上的优柔寡断更加重了上述印象。据我所知,《调查的组织》一书[34]对方法论的探讨仅限于第三章的最后三段。换句话说,塔洛克从未提炼出对各部分来说都较为适宜的综合性观点。这使我想起了柏林对托尔斯泰(Tolstoy)的评价——本质上他是一只狐狸,然而就思想来说,他是一只刺猬。我认为塔洛克本质上是一只刺猬,然而就思想来说他是一只富有活力的狐狸。
塔洛克更像一位种树人,而非造林者,这种感觉或许源自他在短短十年间从法学到外交学再到经济学的学术轨迹。一些人(包括塔本人)指出,塔洛克只是在法学院就读期间研读过由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所主讲的经济学课程。这话不尽然,塔洛克于1943年秋季学期研读该课程,但是尚未结课他就应征入伍。当塔洛克在退役后重返法学院之时,西蒙斯已经去世。虽然西蒙斯讲授了奈特所提倡的价格理论,但是塔洛克必定受到了案例研究方法的影响。案例法不关注争议点,它侧重于提炼贯穿于各种观点之间的一般原则。在学术成长的关键阶段,塔洛克更愿意像律师那样思考,这明显体现在《官僚制的政治》一书[12]中。在学术生涯中,塔洛克始终坚持以下逻辑,那就是从某些案例出发,逐步提炼一般原则。相比之下,虽然布坎南并未使用一般性的经济均衡理论,而是借鉴了奈特所主张的框架[20],但是布坎南的逻辑框架仍然显现出均衡理论的色彩。总之,布坎南的分析框架依托一致性和技术,塔洛克的分析框架依托冲突和演化。
如果询问100位知名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当他们听到布坎南这个名字的时候究竟想到了什么?毋庸置疑,他们的答复将涵盖从思想的个人主义脉络到围绕这一脉络的各种思想谱系。答者赞同既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当被问及对塔洛克的看法时,他们认为似乎看到了很多棵树,较之布坎南的“森林”,塔洛克提供了多元化的思想。
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强调,较之抽象的、普遍的原则,人们在本质上更关注个人利益。[35]莫斯卡的上述论断被其理论所佐证,那就是民主让少数人能够表达他们的观点以获取社会支持。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能够清晰地表达足以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共鸣的抽象原则,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思想家的身上。狐狸比刺猬更擅长表达具体观点,刺猬比狐狸更擅长抢占能够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位置。
《社会困境》一书有可能涵盖了《自由的限度》一书未能诠释的塔洛克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社会困境》一书阐释了塔洛克对社会秩序的大致看法,它同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极为接近。塔洛克借助实际情况,而布坎南擅长抽象分析。《社会困境》涵盖了塔洛克对战争与革命等问题的分析,但是他并未明确表达上述主题。该书是塔洛克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问题的例证,相关分析借鉴了“囚徒的困境”这一传统框架,它表明公共选择理论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而非国内政治经济问题。
塔洛克始终从法学理论展开研究。在《社会困境》以及其他涉及寻租、收入再分配、官僚制、犯罪、慈善等问题的著作中,塔洛克的分析视角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在现实世界中,由个人制定并推动行动计划。然而,这一分析视角并不聚焦于究竟能够达成何种普遍共识。即便塔洛克未曾详述,世人依然生活在他所说的“巴别塔之西”,而非“伊甸园之东”。塔洛克涉及“巴别塔”的作品为其社会理论提供了起点。所有被逐出“巴别塔”的人都很理性,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以及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
在塔洛克看来,政治是天命,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宿命。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敌友之分都难以逾越。在一篇几乎被人遗忘的论文中[36],塔洛克指出法庭的确有权力裁定某种行为是否符合宪法,但是法庭却不能由宪法来支配。换句话说,一纸宪法不会自行实施,只有人才能实施宪法。在塔洛克看来,除了在某些学者的笔下,否则压根不存在普遍共识。正如伯恩汉姆在《马基雅维利式》一书[27]的前两章中所说,在社会生活的沉浮中,只有朋友、敌人和斗争。伯恩汉姆在该书中对比了但丁(Dante)和马基雅维利。塔洛克的社会理论所涉及之人接近于伯恩汉姆在其著作中所涉及之人,例如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莫斯卡、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o Michels)以及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塔洛克在社会理论中的分析视角使他区别于布坎南,然而由于塔洛克未能全面阐述其社会理论,因此我认为这种差异被低估了。
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对柏拉图(Plato)在著作中提到的“他世”和“现世”思想家进行了区分。[37]在研究中,洛夫乔伊对那些影响学者思想的无意识心理习惯以及思维模式特别感兴趣。对“他世”思想家来说,经验世界不过是对想象中的那个美好世界的苍白反映而已。对“现世”思想家来说,虽然经验世界始终经历着由于人类及其思想之间的碰撞所导致的变化,但是经验世界就是一切。塔洛克的无意识心理习惯表明他是一位“现世”思想家,而布坎南明显是一位“他世”思想家。
同洛夫乔伊对思想的区分有关,理由和理性行为之间的区别属于形式和内容之分。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理性属于行为的形式。一切行动都是理性的,只因别无他选。塔洛克对此并不否认,但是他认为世界上的行为往往是实质性的、非正式的。理性能够被视为有目的的行动发生时的形式,然而这一形式不同于有目的的行动所指向的内容。理性行动假设认为人们试图以有效的或者并非无效的方式来行事。毫无疑问,该假设无例外,因为没有人故意将自己想干的事干砸。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都有日耳曼血统,也都迁出自己的出生地以追求梦想,前者从德国前往非洲,后者从奥地利前往德国。虽然他们行为的内容存在天壤之别,但是都符合理性行动的形式。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正式的理性行为将展现出人类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存在本质差异。私人秩序支配下的社会环境不同于公共秩序发挥显著影响的社会环境。根据市场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生产遵循成本函数,这些函数区分了不能实现的和能够实现的结果。低于成本生产是不可能的,然而产品高于成本是可能的。一旦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想知道经济学家缘何将成本定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临界点。就形式推理来说,答案是私人秩序下的财产权。在经理人员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组织模式下,管理者能够找到生产产品的低成本方式,并赚取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然而在公共秩序下,由于政治是商业活动的一种形式[38],因此剩余索取权要么消失,要么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都有成本,虽然形式相同,但是对二者来说,成本的实质含义却大相径庭。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强调,普通法判决符合经济效率[39];塔洛克明确反对上述观点[4](P97-112)[40][41]。塔洛克并未给“关注效率”打上错误的标签,他只是认为波斯纳未能回归相应的法制环境来论证其观点。至于塔洛克和波斯纳围绕普通法判决的经济效率之争,在此不妨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波斯纳曾为普通法法条作出注解——铁路部门只需要看护横穿铁路道口的行人,但是往往还需要看护沿铁轨游走的牲畜。波斯纳援引避免事故的比较成本来论证上述判断。他强调,人们凭直觉会同意行人在铁路道口留心火车的成本要低于火车留心行人的成本。相比之下,农场主在牲畜周围设置和维护栅栏的成本远高于铁路部门提醒火车司机留心在铁轨附近游走的牲畜的成本。
塔洛克注意到,和众多涉及效率的经济学论断一样,波斯纳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非经验性的。效率在竞争性均衡中的确是一种资产,然而在竞争性均衡之外,它尚未被定义。效率不能被直接感知,它是竞争性均衡中“帕累托效率”模型的某种结果。行人在铁路道口留心火车的成本真的低于火车司机留心行人的成本吗?如果横穿铁路道口对行人来说是最短距离的话,那么波斯纳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对某些行人来说,在铁路道口外穿行才是最短距离,如此就很难说哪种方式才是塔洛克所说的低成本方式。更有甚者,留心牲畜和留心行人可同时进行,一名留心牲畜的火车司机能够在无边际成本的情况下也留心行人。
统计决策理论存在一大问题,那就是一位女士声称她能说出一杯茶究竟是先放茶叶还是先放牛奶。[42]评判者应决定接受还是拒绝上述说法,并设法加以验证。在塔洛克的语境中,这等于询问该女士能否准确说出一杯茶是怎么来的。由于不存在独立来源的证据,以致根本就无法得出这种判断。作出判断的程序是存在的,并且这些程序在成本以及规避错误的能力上也大相径庭。除了准确性和成本,还有各种判断标准,并且标准越高往往意味着成本越高。例如这位女士喝过的茶越多,准确度就越高,成本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缺少能够得出“真理”的“上帝之眼”。
塔洛克对司法程序的成本以及准确性的分析适应这一决策理论。例如,波斯纳对比了普通法和竞争性市场机制,塔洛克对比了普通法和社会主义官僚制。在普通法系下,在代理人内部以及庭审律师之间都充斥着竞争。塔洛克强调普通法系类似一场军备竞赛,其均衡点或代价轻微,或代价高昂,然而普通法系往往导向代价高昂的均衡点。在此基础上,他倾向于由法官、而非律师来主宰一切的大陆法系(民法法系)。法官属于官僚,他们由税收、而非那些寻求服务的顾客来供养。此外,法律和政治深度纠缠,这是因为在所有法系中都充斥着公共秩序,而财产和契约等私法原则被淹没在各种政治需要之中。仲裁所涉及的私人秩序远多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它要求公务员具有执行判决的意愿。
六、结 语
同其他学者一样,塔洛克的学术遗产取决于后人根据前人的贡献所作出的评价。尽管我认为塔洛克注定被视作一只狐狸,而非一只刺猬,但是他却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众多值得思考的观点。虽然塔洛克的社会理论同布坎南背道而驰,但是他们都试图支持当代世界的自由主义。在塔洛克看来,政治是宿命,它并非局限在生活中的一隅,而是无处不在。塔洛克指出,较之让众人都赞同相应的宪法制度,或许在世人中存在对社会制度的反对之声更接近自由的本质。有组织的拳击将误导对宪政治理问题的解决。在拳击比赛中,裁判负责执行由昆斯伯里侯爵所制定的规则,拳手必须无条件服从。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昆斯伯里侯爵。在《美国宪法(1787)》即将颁布之际,一位女士问到我们究竟创建了一个怎样的政府,对此本杰明·富兰克林答道“一个共和国”。富兰克林承认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在1986年后同塔洛克有过几次深谈。从中不难发现,他对于未获诺贝尔奖始终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就推动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而言,自己的贡献与布坎南不相上下。塔洛克对寻租问题的研究似乎也应被授予诺贝尔奖,但是这也并未发生。他是一个既理智又古怪的人,这两种性格特质在他的身上经常相互冲突,这种怪脾气明显表现在他急于弥补自己所受的伤害。20世纪80年代末,塔洛克曾接受一名瑞典记者的电话采访。记者问他为何要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如此偏远的布莱克斯堡,塔洛克答道,当地优秀的经济学家比瑞典全国都多。从1963年9月与他相识的那天起,直到他去世,笔者看到这种怪脾气出现在一个最友好、最绅士的人身上。
注释:
①本文译自Richard E.Wagner撰写的论文“Gordon Tullock's Scholarly Legacy:Extracting It from Buchanan's Shadow”,原载于“The Independent Review”(《独立评论》,2018年第2期刊发),中译本已获作者授权在《江西社会科学》刊发,标题和摘要按中文习惯略作修改。
②时间上溯至1963年9月,从瓦格纳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伊始就与塔洛克和布坎南有了交集,并一直持续到两人去世为止(布坎南卒于2013年1月9日,塔洛克卒于2014年11月3日)。在弗吉尼亚大学同时做过塔洛克和布坎南学生的人当中,瓦格纳是唯一健在的;此外,先后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同塔洛克和布坎南二人共事过的人当中,瓦格纳也是唯一健在的。由瓦格纳所撰写的有关布坎南的作品,包括Richard E.Wagner,James M.Buchanan: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ist,Regulation,Vol.11,No.1,1987,pp.13-17等;有关塔洛克的作品,包括Richard E.Wagner,Finding Social Dilemma:West of Babel,Not East of Eden,Public Choice,Vol.135,No.1,2008,pp.55-66等;同时涉及他们两人的作品,包括Richard E.Wagner,The Calculus of Consent:A Wicksellian Retrospective,Public Choice,Vol.56,No.2,1988,pp.153-16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