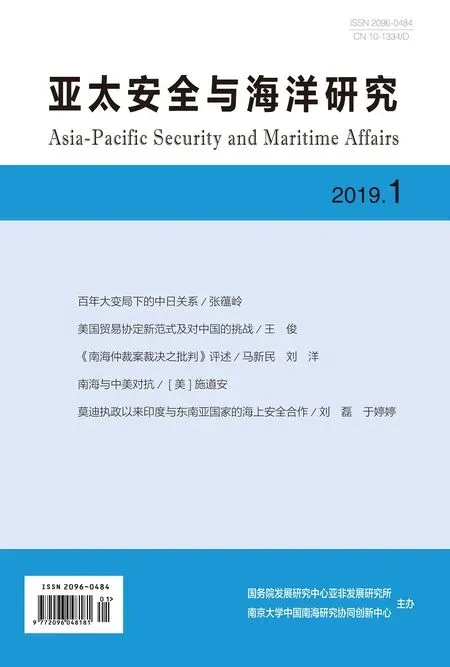资源安全视域下南海渔业纠纷探析
2019-03-04郑先武
赵 岚 郑先武
[内容提要]南海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依赖海洋资源,地缘政治深受海洋影响,渔业纠纷往往成为海洋资源争夺的重点。由渔业纠纷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冲突、国家对立,已成为关乎南海海域安全与稳定的突出议题。资源匮乏、民族情绪、领海争议等原因,推动南海相关国家对渔业纠纷进行安全化操作,激化南海渔业纠纷。在此背景下,协商建立渔业合作机制为南海资源安全治理提供了新平台。渔业合作机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将会不断弥补国家间的信任赤字、推动国家利益的聚合、加快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进程,而渔业合作机制也将成为综合安全治理的着力点。
近年来,随着亚洲各国海洋权益观念的空前提高,各国对于海洋资源争夺愈演愈烈。尤其是海底石油资源、渔业资源等海洋资源关系国计民生,成为国家间利益争夺的主战场,海上资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东南亚国家大多是沿海国家,地理位置依傍海洋,渔业捕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方面倚重海洋渔业资源。因此,南海渔业纠纷成为海洋资源争夺的核心议题,由渔业纠纷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冲突、国家对立,业已成为关乎东南亚安全与稳定的突出议题。由于争议方大多是世界上的渔业经济大国或区域实力强国,因而渔业资源争夺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当前的资源安全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资源安全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对国家主权和军事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水资源、石油、天然气等,或将其与国家治理失灵联系起来,或探讨因为资源争夺而爆发的国家间战争,或者是将资源安全与资源冲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注]参见:Kamila Proninska, “Resource War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4,2005, pp.29-44; Kent Hughes Butts, “Geopolitics of Resource Scarcity,” Penn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 No.2, 2015, pp.1-9; Jeffrey D. Wilson, “Resource Security: a New Motivation for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25, No.4, 2012, pp.429-453; Jeffrey D. Wilson, “Regionalising Resourc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the Challeng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9, No.2, 2015,pp.224-245;Travis Sharp, “Resource Conflic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eace Review: A Journal of Social Justice,Vol.19, 2007, pp.323-330; 张建新:《21世纪的国际能源安全问题》,《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曹云华:《东南亚国家的能源安全》,《当代亚太》2000年第9期。对于渔业冲突的研究,既有学术研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框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梳理,但较少有研究从安全化的角度对南海渔业纠纷进行详细的分析以及梳理其升级过程。[注]Alan Dupont and Christopher G. Baker, “East Asia’s Maritime Disputes: 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7, No.1, 2014, pp.79-98; Kuan-Hsiung Wang,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Fisheries Cooperation As a Resolu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4, 2001, pp.531-551; Eric Franckx, “Fishe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Centrifugal Or Centripetal Forc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 2012, pp.727-748; Anthony T. Charles, “Fishery Conflicts:A Unified Framework,” Marine Policy, Vol.16, 1992, pp.379-393; Elizabeth Bennett, Arthur Neiland, et al.,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ropical Fisheries:Evidence from Ghana,Bangladesh and the Caribbean,” Marine Policy, Vol.25, 2001, pp.365-376; Khondker Murshed-e-Jahan, Ben Belton, K .Kuperan Viswanatha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Coastal Fisheries Conflicts in Bangladesh,” Ocean &Coastal Management, Vol.92, 2014, pp.65-73; Hongzhou Zhang, “Fisheries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Evaluating the Options,” Marine Policy , Vol.89(2018) , pp.67-76;Robert Pomeroy , John Parks , et al. , “Fish wars-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Marine Policy, Vol.31, 2007, pp.645-656; N.D. Salayo, M. Ahmed, et al., “An Overview of Fisheries Conflict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Recommendations ,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WorldFish Center Quarterly, Vol.29, No.1/2, 2006, pp.11-20。因此,从安全化的角度对南海渔业纠纷进行探究,在中国同东盟国家积极推行“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的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注]参见鞠海龙:《南海渔业衰减相关问题研究》,《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李聆群:《南海渔业合作:来自地中海渔业合作的启示》,《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葛红亮、鞠海龙:《南中国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一、资源安全对地区安全再定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安全”的定义一直不很成熟,然而即使这种不成熟的“安全概念”也长期被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话语所主导。[注]参见郑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的重构》,《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第47页。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超级大国之间逐步实现核平衡,经济与环境威胁日益受到关注,安全的初始定义得以扩展,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开始向军事—政治之外扩展。[注]参见巴里·布赞:《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23页。1983年,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乌尔曼率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概念,将贫穷、疾病、资源冲突等内涵均纳入安全的范畴之中,强调非军事威胁在未来安全议题中的重要性。[注]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8, No.1, 1983, pp.129-153.随后,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世界范围内全球化的扩展,使“安全”的定义有所更新。包括恐怖主义、种族危机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并形成传统安全领域外的新安全挑战。
与传统安全相较,非传统安全因其丰富的议题以及模糊的边界而更加难以定义。但总的来说,仍然可以勾勒出其与传统安全之间的界限与区别:第一,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或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研究主要指向“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第二,传统安全研究的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安全互动,并把国家视为主要威胁,非传统安全着重研究“非国家行为体”所带来的安全挑战;第三,传统安全侧重安全议题中的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则研究的是“非军事安全”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第四,传统安全更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安全主体,而非传统安全则将“人”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注]参见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0页。
非传统安全研究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核心突破之一,在于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新的安全领域。因资源冲突而引发的安全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理查德·乌尔曼在其《重新定义安全》中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因为领土而爆发的冲突会减少,但由某些基本商品需求的增加而出现的供给不足可能会导致资源冲突更加激烈,这种冲突往往以公开的军事力量对抗为表现形式。”[注]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8, No.1, 1983, p.139.1982年以来,资源对国家内部冲突以及国家间冲突的爆发、延续和冲突烈度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注]Travis Sharp, “Resource Conflic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eace Review: A Journal of Social Justice, Vol.19, 2007, p.323.而渔业资源更是因其对于沿海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而成为海洋资源冲突的根源之一。
因此,本文首先指出渔业资源在资源安全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进而以东南亚渔业纠纷为切入点,采用领域和层次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对由渔业资源争夺而引起的冲突如何升级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存在性威胁”进行详细论述,进而说明资源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核心因素。
(一) 资源安全:更新安全的定义
资源是指一切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东西。[注]Kent Hughes Butts, “Geopolitics of Resource Scarcity,” Penn State Journal law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 2015, p.3.具体而言,“资源是指由人发现的、有用途和有价值的、出于自然或未被加工的状态的物质及其能量,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能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福利”[注]张元卓:《政治经济学大词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99—301页。。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正在面临迅速枯竭的风险,部分资源枯竭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可以承受的程度。对于关键性资源的供给争夺,在冷战结束后取代了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家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获取资源的居安思危,使得“资源安全”概念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新的关注点。资源安全被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供应自然资源的能力”[注]Jeffrey D. Wilson, “Regionalising Resourc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the Challeng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9, No.2, 2015, p.225.。资源短缺和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是引起全球资源冲突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而对资源安全的研究大多关注与国家安全、地区冲突之间的密切关系石油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
有史以来,因为资源利用相关的冲突甚至战争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命题。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及其阵营下进行的意识形态竞争几乎完全消失,各国不再以东西方的对立为主要关注点,追逐和保护稀缺资源成为国家的安全功能之一,这对于资源安全问题的中心化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由于资源的供给枯竭,政府则会设法最大程度地谋取有争议地区和近海的资源储藏,国家间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也如影随形。尤其是当资源的储存地被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分享、或资源位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以及近海经济区时,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的危险也会随之增加。[注]参见迈克尔·T·克莱尔:《资源战争:全球冲突新场景》,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1页。这种资源冲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在冲突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另一种尽管资源不是主导原因,但是在冲突中起到了催化作用。[注]Kamila Proninska, “Resource War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4, No.3, 2005, p.29.当矛盾无法调和,资源冲突会以国家对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或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争端的形式出现,并上升为地区性权力斗争。如1994年挪威和冰岛之间的“鳕鱼大战”,而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渔事摩擦的直接后果就是俄海军军舰几次向日本渔船开火并导致了两国间的外交抗议。[注]参见王逸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的国际关系》,《百科知识》1996年第6期,第4页。
从经济、资源和社会角度而言,渔业资源对南海周边国家至关重要。渔业资源是南海周边国家经济收入以及国民生计的重要来源之一。丰富的渔业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世界粮农组织所划定的世界主要渔区第36区以及37区的范围之内。[注]FAO划定的主要渔区第36区主要包括南海北部地区,37区涵盖了大部分南海区域。具体分区图参见:FAO, “Major Fishing Areas:Pacific, Northwest(Major Fishing Area 61)”, http://www.fao.org/fishery/area/Area61/en; “MAjor Fishing Areas: Pacific, Western Central(Major Fishing Area 71)”, http://www.fao.org/fishery/area/Area71/en[2018-08-10]。每年南海地区的捕鱼产量超过全球捕鱼量的10%[注]Hongzhou Zhang, “Fisheries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valuating the Options,” Marine Policy, Vol.89, 2018, p.68.,南海海域潜在渔获量为6.5×106吨至7×106吨。其中,水深500米以内浅海陆架区(含北部湾)水域内渔业资源最为丰富,潜在捕鱼量为5×105吨,占整个南海渔获量的80%以上。[注]参见鞠海龙:《南海渔业资源衰减相关问题研究》,《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第52页。而该地区也是中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渔业冲突与合作进行最为密切的地区。1970年后,随着各个国家逐渐建立起海洋专属经济区,南海渔业资源被人为分割,渔业纠纷开始变得更加频繁,暴力冲突也不断升级[注]Robert Pomeroy, John Parks, et al., “Fish Wars-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Marine Policy, Vol.31, 2007, p.646., 渔业资源分配与资源安全治理成为南海周边国家共同面对的海洋治理议题。
(二) 渔业纠纷:发展面临的困境
渔业冲突被定义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动机,在相同海域内对渔业资源的分配与获取产生的矛盾与纠纷。[注]Anthony T. Charles, “Fishery Conflicts: A Unified Framework,” Marine Policy, Vol.16, 1992, pp.379-393; Elizabeth Bennett, Arthur Neiland, Emilia Anang, et al.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ropical Fisheries: Evidence from Ghana, Bangladesh and the Caribbean,” Marine Policy, Vol.25, 2001, pp.365-376; Khondker Murshed-e-Jahan, Ben Belton, K .Kuperan Viswanatha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Coastal Fisheries Conflicts in Bangladesh,” Ocean &Coastal Management, Vol.92, 2014, pp.65-73.安东尼·查尔斯(Anthony T. Charles)将复杂的渔业冲突分为四种相互联系的类型:渔业管辖范围纠纷、管理机制问题、内部分配问题以及外部分配问题。在这些不同类型冲突的背后,是各种渔业行为体所追求的具有差异性的目标。分别以“资源保护”、“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为目标的行为构成了三种不同的范式。这三种相互冲突的范式共同组成了分析渔业纠纷议题的三角框架。[注]Anthony T. Charles, “Fishery Conflicts: A Unified Framework,” Marine Policy, Vol.16, 1992, pp.379-393.随后,伊丽莎白·班尼特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外界行为体在渔业纠纷中的作用,将渔业冲突更新为五种类型:第一种冲突指向“谁拥有渔业资源”,也就是指向在固定海域渔业资源的捕捞权;第二种冲突指向“渔业资源如何被控制”,也就是指向在资源管理机制中出现的冲突与纠纷,包括渔业资源分配问题以及渔业资源合作问题;第三种冲突指向“渔业资源使用者的关系”,例如手工业个体渔民与工业化捕鱼企业的关系;第四类冲突指向“同一生态环境中渔民与其他资源使用者之间的联系”,通常发生在渔民与同样依靠水资源而生存的从业者之间,由资源冲突而爆发的争端;第五类冲突指向“渔民与非渔业议题之间联系”,主要是指由于经济、政治变化等因素引起的冲突。[注]Robert Pomeroy, John Parks, et al., “Fish Wars-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Marine Policy, Vol.31, 2007, p.648.
南海渔业冲突已经成为南海冲突中的核心安全威胁之一。非法捕鱼频频发生,远洋捕捞与海盗问题相联系,周边国家海上民兵政策的推动都使得渔民的远洋捕鱼行动被赋予了更多政治性含义,而发生在争议海域的渔业冲突更是成为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宣示海上主权、展示国家实力的角斗场。以争夺渔业资源为本质的渔业纠纷被安全化为一场政治博弈,推动着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甚至成为大国战略对弈的新热点。[注]参见朱锋:《南海主权争议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效果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为例》,《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第12页。
二、多方驱动的渔业纠纷成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海上渔业纠纷逐渐增多,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大隐患。其中的原因,既包括资源衰退而引起的供求矛盾,也包括领海争议所引起的执法权冲突,而民族主义情绪的发酵也不断激化渔业纠纷。渔业资源对于东南亚国家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东南亚国家在海洋权益争夺中的重要利益诉求,而合作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地区合作难以有效进行。对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而言,渔业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关乎国计民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洋渔业资源的日益稀缺,使得东南亚国家已经将其视为本国海上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国家目标的驱动下,国家行为体更加倾向于采取有利于增加捕鱼产量和渔业收入的发展方式,这就造就了在资源相对有限海域中大量渔船被允许出海捕捞,渔业纠纷的发生不足为奇。[注]Meryl J. Williams, “Will New Multilateral Arrangements Help Southeast Asian States Solve Illegal Fish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5, No. 2, 2013, p.262.
(一) 难以平衡的供求矛盾
尽管渔业纠纷频发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南海周边国家渔业需求的大幅增长与渔业资源衰减之间的矛盾。渔业产品是世界食品领域贸易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预计有78%的海产品进入国际贸易竞争,而南海海域所在的西部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渔业产品出口地区。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渔业生产国。根据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的数据统计,东南亚国家的渔业总产量已经达到了4222万吨,其中远洋捕鱼量为1665万吨,占整个东南亚渔业产量的40%,世界海洋捕鱼总量的20%,其中南海海域的捕鱼总量占据半壁江山。与此同时,相较于水产养殖和内陆渔业捕捞而言,远洋捕鱼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海洋捕捞带来的经济效益占渔业捕捞产值的50%来自于远洋捕捞。[注]SEAFDEC, Southeast Asian State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17, Bangkok,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Development Center, August 2017, p.5, http://www.seafdec.org/download/southeast-asian-state-fisheries-aquaculture-2017/[2018-09-10]lbid.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海洋捕捞技术的不断发展,海洋渔业资源面临着严重枯竭的危机。沿海各国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在进行海洋渔业捕捞的过程中往往优先考虑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在过去的15年中,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捕鱼总量增长了将近60%,预计到2050年,东盟国家的渔业消费总量将达到4710万吨。[注]Chin Yee Chan, Nhuong Tran, et al., Fish to 2050 in the ASEAN Region, Penang, Malaysia: WorldFish and Washington DC, USA: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Working Paper: 2017-01, 2017, p.18, https://www.worldfishcenter.org/content/fish-2050-asean-region[2018-08-12].而长期的过度捕捞使得南海地区渔业资源产量逐渐减少。南海地区14%的鱼类种群被估计为按生物学不可持续的方式捕捞以及86%的鱼类种群被完全捕捞或低度捕捞。[注]FAO,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16, Rome: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16, p.51, www.fao.org/3/a-i5555e.pdf.[2018-12-27].目前,除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附近部分渔场及部分海域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外,东南亚其余海域传统渔场的渔业资源数量和质量相较20世纪中叶都呈现大幅度下降状态,南海近海海域几乎无鱼可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与资源衰竭并存的是过度捕鱼带来的社会问题,包括对于远洋渔船的过度投资以及由此引发的渔业从业者过剩、利润锐减,传统渔民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难以为继。[注]Robert S. Pomeroy, “Managing Overcapacity in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Southeast Asia,” Marine Policy, Vol.36, 2012, p.521.直面生存危机的近海渔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前往争议海域进行捕捞活动,而当前南海海域混乱的渔业管理体系以及国家间的政治斗争使得渔业冲突被不断扩大化。尤其是在南海争议海域以及专属经济区争议区,以经济效益为追求目标的海洋渔业资源竞争往往是“零和”性质的,对于有限的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一方捕鱼量的增多往往意味着另一方的减少。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以及渔业资源的减少,使得海洋捕鱼的竞争更加激烈,小户渔民难以适应这种竞争,跨境捕鱼、非法捕鱼事件频发,海洋渔业纠纷加剧。
(二)模棱两可的海洋划界
基于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近些年来海洋边界纠纷已使得不少东南亚地区国家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此,海洋划界争端尤其是发生在南海海域的海洋划界争议亦成为渔业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领海问题是海洋捕鱼的重要因素之一。渔业活动发生在特定的区域中,有权利进入相关海域是渔业捕捞活动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相对于鱼群来说,领海对于渔民而言更加实际。鱼群可以迁移,且有可能迁移至特定区域,因而对于渔业资源丰富的海域争夺更加激烈。[注]Maarten Bavinck, “Understanding Fisheries Conflicts in the South—A Legal Pluralist Perspective,”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Vol.18, 2005, pp.808-809.
1982年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目前处理海洋划界问题的主要国际法来源。这次以国际组织立法形式出现的 “海洋圈地运动”,将地球表面36%的海面变成了沿海国家的“内水”或管辖区,世界公海面积因此缩小了近1.3亿平方公里。[注]参见王逸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的国际关系》,《百科知识》1996年第6期,第4页。公约在第74条和第83条中要求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注]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网站, http://www.un.org/zh/law/sea/los/article5.shtml。《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一、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子)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卯)在第59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二、前项规定不妨碍法院经当事国同意本“公允及善良”原则裁判案件之权。参见《国际法院规约》,联合国网站, http://www.un.org/zh/documents/statute/chapter2.shtml[2018-10-03]。然而,在国际社会中对于海洋划界的原则分为“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和“公平原则”两种,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各国往往在谈判过程中采取对己方更有利的原则,从而使得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界标准难以达成一致。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实施的1994年,全世界海岸相向或者相邻国家之间共有420余条潜在边界,而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共有97条海洋边界。[注]参见王逸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的国际关系》,《世界知识》1996年第6期,第4页。特别是在专属经济区成为一种国际习惯法之后,南海各沿岸国家为了扩大在相关海域的生物资源及非生物资源纷纷提出了本国的专属经济区主张,这是南海争端发生的核心因素之一。[注]Kuan-Hsiung Wang,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Fisheries Cooperation As a Resolu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4, 2001, p.547.但各国主张的管辖区域往往发生重叠,因此海洋划界争端往往因此而发生。复杂的海洋环境使得东南亚地区各国渔民在未定海域与公共海域频频出现非法捕捞行为。
(三)举步维艰的生存危机
从社会经济向度出发,渔业冲突与海洋综合安全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是南海海域复杂环境中的一个缩影,渔业纠纷的不断激化与其经济特征息息相关。渔业经济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越强烈,国家安全化渔业纠纷的动因也会愈发明显。海洋渔业活动从属性上看有较强的经济目的,以盈利为目标,而东南亚渔民往往不得不面临资源衰减带来的生存危机;从运行方式上看,具有灵活性和跨境特征,单一国家在规范跨境渔业活动时往往力不从心。因而,往往与绑架、海盗、贩卖等多种海上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成为地区安全隐患。
对于南海周边国家而言,渔业经济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外汇收入。2014年全世界渔民和养殖渔民超过7538万,其中超过75%的人在亚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渔业生产国,有近376万海洋渔业从业人员。[注]参见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2017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年,第85页。就南海周边东南亚地区而言,有817万人从事海洋捕捞或养殖渔业活动。东南亚渔民数量众多,然而大多数渔民来自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菲律宾全国有超过87万渔民,其中超过85%的渔民从事远洋捕鱼。[注]SEAFDEC, Southeast Asian State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17, Bangkok, Thailand: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Development Center, August 2017, p.17, http://www.seafdec.org/download/southeast-asian-state-fisheries-aquaculture-2017/[2018-10-16].然而,菲律宾律宾却被称为是“渔民收入最低的渔业生产国”[注]参见陈思行:《渔民收入最低的渔业生产国:菲律宾》,《中国渔业报》2004年9月27日。。菲律宾渔民仍然是国家最贫困的群体,甚至被称为国内“穷人中的穷人”[注]Ding Cervantes, “Filipino Fisherfolk Among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The Philippine star, 19 February, 2012, http://www.philstar.com/agriculture/778532/filipino-fisherfolk-among-poorest-poor[2018-10-17].。在菲律宾南部,贫穷的渔民成为阿布沙耶夫集团等恐怖组织的潜在招募者,成为国家安全必须面对的社会危机。
渔业资源的减少以及现代化大型渔业公司在相关海域利用其先进的技术逐步在相关海域捕鱼业中占据垄断优势,渔民的生计更加困难。渔民及其所属渔业公司为了在经济活动中取得竞争优势,往往利用不完善的安全机制进行海上犯罪活动,推动了渔业纠纷的威胁升级。由于渔业资源匮乏,往往有一些传统渔民武装起来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船只上窃取现金等贵重物品以及渔业产品。[注]Sam Bateman, “Sea Piracy:Some Inconvenient Truths,” Maritime Security, Vol.2, 2010, p.15.在苏禄海附近常常发生针对捕捞拖网渔船进行的绑架抢劫活动。渔业公司雇佣他人在海上对竞争对手的渔船进行扣押,或绑架渔船至菲律宾令其以高额及价格赎回。[注]Karsten von Hoesslin,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 in Southeast Asia: Organized and Fluid”,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35, 2012, p.545.
(四)难以弥合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者看来,单个问题往往具有全局性的象征意义,即便是很小的妥协也会危及民族的立身之本。[注]参见归泳涛:《东亚民族主义勃兴与中国周边关系的转型》,《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2期,第78页。在应对南海渔业纠纷中,民族主义政策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出击,用民族主义政策为激进的海洋渔业政策正名,使其合法化、合理化。击毁渔船、保护弱势的捕鱼产业免受国外竞争,支持渔业生产者,是民族主义政策的典型应用。[注]参见连洁:《印尼与邻国海上捕鱼争端探析》,《国际研究参考》2018年第3期,第35页。印尼佐科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严厉的非法渔船打击政策,大量击毁外国渔船。从2014年起,印尼已经炸毁了488艘非法渔船,其中大部分是外国渔船。[注]Jakarta, “Indonesia sinks 125 foreign illegal fishing vessel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3 August, 2018, http://globalnation.inquirer.net/169224/indonesia-sinks-125-foreign-illegal-fishing-vessels[2018-12-28].其中,印尼在2015年国家独立日和民族复兴日当天,在多个港口同时炸毁多艘渔船,将打击非法渔船与民族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以展示政府决心和强硬的国家实力。2017年,有超过110条外国渔船被印尼击沉。[注]Prashanth Parameswaran, “Indonesia’s War on Illegal Fishing Continues With New Sinkings”, The Diplomat, November 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indonesias-war-on-illegal-fishing-continues-with-new-sinkings/[2018-11-18].
另一种是将争议海域渔业纠纷与国家领海安全相结合,利用领土民族主义争取海洋权益。作为民族的最终代理人,国家在应对外交事务中,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聚集力量,动员人民,从而保证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规避不良影响,从而摆脱由于竞争而带来的危机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利益是民族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注]参见王军:《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南海相关国家渔业纠纷中,渔民冲突、渔船冲突被赋予政治意义,民族主义情绪和领海争端发酵激化冲突等级,以至于使其上升成为一个“安全议题”。对于菲律宾、越南等在地区安全局势中相对被动的国家而言,一旦在争议海域渔业纠纷上进行妥协,可能意味着软弱可欺,即接受在海洋权益竞争中的不利形势。而这种消极信息的传递,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争议方在应对包括渔业纠纷在内的诸多外交争议时的政策选择。在国内政治精英的引导下、受偏颇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主导,相关国家在应对矛盾过程中难以形成战略信任,无法达成有效的协议,甚至会被民族主义情绪激化矛盾。
南海渔业的争端与开发是动态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注]参见徐小怡:《南海渔业资源争端的冲突分析》,《中国渔业经济》2014年第3期,第26页。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逐渐恶化的海洋环境以及相关国家矛盾的海洋政策,都是南海渔业争端中的重要变量。尽管民族情绪无法全面解释频频发生的渔业纠纷,然而却是愈演愈烈的海洋权益斗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民族主义在现代政治中所发挥的功能远远超出领土纷争、种族对抗的单一范畴。[注]参见梁雪村:《被“围攻”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国际秩序的道德贫瘠》,《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110页。对于民族尊严的渴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国家竞争中对其他国家的敏感,成为渔业纠纷“安全化”的工具。
三、动态变化的渔业安全进程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议题是行为体在实践中构建出来的。一旦某个议题被看作是一种“存在性威胁”,即使其并不具备迫切性,也可以通过安全行为体的言语行为而说服受众,使其获得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威胁的权力,从而上升为一种客观威胁。使用安全标签来说明议题不仅仅反映了一个问题是否是安全议题,同时也是一种政治选择,一种以特殊方式进行概念化的决定。[注]Ole Wa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On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5.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利·维夫认为,扩展安全概念的途径之一是将安全议程扩大到包括军事以外的更多威胁。[注]lbid., p.51.通过将某事定义为一种国际安全事务,可以使得这一议题获得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的优先地位,从而能够对这一被安全化的议题进行优先讨论。在安全化理论中,一个议题成为安全议题不再是以客观真实存在的外部威胁为前提,而是一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实践,安全的自我指涉性当之无愧地成为哥本哈根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观点。[注]Rita Floyd, Security and the Environment: Securitisation Theory and U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3.
南海渔业问题的不断激化过程是一个安全化过程,是一个从非政治化—政治化—安全化的发展过程。东南亚国家以及美日等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密切的域外国家,基于各种安全化逻辑对南海相关海域的渔业纠纷进行安全化操作,渔业冲突逐渐从非公共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从政治议题转变为安全议题,甚至被东南亚国家视为一种“存在性威胁”。中国作为南海渔业冲突的当事国,既是被“安全化”的主体,也在不断促进合作推动去安全化努力。
(一)渔业问题政治化:非法捕鱼导致地区冲突频发
20世纪60年代后,渔业纠纷在国家间竞相主张专属经济区的过程中上升为一个影响地区稳定的政治议题。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开始单方面将其自然管辖区扩展到200海里,将其称为“渔区”,其主要目的便是获取更多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海洋资源。[注]Daniel Yarrow Coulter,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Countdown to Calam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7, No. 4, 1996, p.378.尽管中国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应对冲突不断的南海问题,然而在复杂的南海资源冲突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划界争议的出现推动了东南亚各国对于渔业资源的争夺,使之逐渐上升为地区冲突。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此后在1960年和1973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各国终于在1982年达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了专属经济区的国际法地位。但是,对于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公约》规定“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加以解决,却未对海洋专属经济区进行明确划分。
与此同时,各个沿海国家陆续以国内法形式划分了捕鱼区,并通过发放捕捞许可证限制外国渔船进入海域。各自为营的划界方式,对于传统捕鱼区域的考虑不足,导致非法捕鱼状况频频出现,地区间纷争不断。1984年印尼关闭了外国渔船可进入的水域,1986年这项政策改为向外国渔船颁发准入许可证制度。但由于监管软弱,仍有大量外国渔船进入印尼专属经济区进行捕鱼活动。此后印尼陆续采取多种措施监管海外渔船捕鱼,成为政治议程中的一个棘手议题。
渔业问题逐渐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议题,其本质逐渐演变成为争端当事国之间的海洋主权博弈。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因渔业问题而产生的摩擦频频出现,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地区战争。1973年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上遭到了南越军舰的驱逐和抓捕,南越甚至炮击在海上作业的中国渔民,从而引发了1974年中越南海海战。自1985年起,平均每年有超过2000名泰国渔民进入马来西亚管辖范围内进行非法捕鱼活动,其中有近10%的渔民被抓捕。[注]Daniel Yarrow Coulter,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 Countdown to Calam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7, No. 4, 1996, p.383.
(二)渔业纠纷安全化:渔业纠纷进入地区安全议题
20世纪90年代后,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将应对渔业纠纷纳入国家重要政治议题当中,并逐渐引起更多国际行为体的关注。随着渔业纠纷的烈度不断升级,它已经不再是渔业资源开发上的矛盾,而逐渐演变成一个安全问题。安全化程度的升级,体现为国家在应对渔业纠纷时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流血事件频繁发生。
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正式生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直接和最深远的影响,就是它承认了沿海国对海洋资源享有管辖权,从而使这些资源成了沿海国的经济财产。[注]参见联合国新闻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介》,高之国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24页。这一时期,渔业纠纷发生的冲突数量和危机程度都远远超过此前的时期,冲突各方完全根据本国海洋利益主要是渔业利益的需要相互斗争。[注]参见王逸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的国际关系》,《百科知识》1996年第6期,第4页。1994年,越南在其领海抓捕了99名在越南进行跨境捕鱼的泰国渔民;1995年中国渔船被马来西亚海军舰艇撞击起火;2000年,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捕鱼的过程中遭到菲律宾海警围追和枪击,造成一人死亡。[注]参见李金明:《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将南海问题搬上国际政治的舞台,引起了更多域外国家的关注,包括渔业纠纷、领土争议在内的南海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日等域外国家纷纷呼吁东盟介入解决争端。1992年东盟外长会议开始关注南海问题。在1994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菲律宾、印尼等国纷纷提出有关南海问题的建议,并将南海问题写进会议公报。2002年,中国作为在南海问题中的一个主要行为体,同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声明“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注]ASEAN Secretariat,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nom Penh, 4 November 2002, http://asean.org/?static_post=declaration-on-the-conduct-of-parties-in-the-south-china-sea-2[2018-10-26].。宣言签署后的十年,东南亚国家基本保持克制态度,尽管国家间渔业纠纷仍时有发生,但基本上持续在可控的状态之下。
(三)安全化与去安全化进程: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
然而,2009年后,菲律宾、越南等国向联合国提交南海大陆架划分申请案,此后东南亚国家之间以及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划界问题上的争议不断扩大,南海渔业纠纷也随之不断恶化,跨境捕鱼被赋予更多民族主义情绪,渔业纠纷也采取更多强制性手段加以应对。这一时期,南海渔业纠纷与南海划界争议结合最为紧密,使其从国家间的双边问题恶化为多边参与的地区争端、从公共议题转变为一种安全威胁,乃至成为影响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威胁之一。而各国应对渔业纠纷而采取的措施也更加激烈和全面,各种暴力执法、武装对抗事件频频发生。国家激进的海洋政策与严峻的南海争端联系在一起,共同激化了渔业纠纷。
2011年中国与菲律宾由渔业纠纷而引发的海洋主权摩擦,在2012年达到高峰,中菲黄岩岛事件可谓“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海域作业时被突然出现的菲律宾军舰所堵截,随后中国渔民被菲律宾军人抓捕扣押。菲律宾等国对此态度十分强硬,使得纠纷迅速上升为国家间的主权斗争,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存在性威胁”。2013年台湾渔民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生冲突并导致一人死亡,以致台湾与菲律宾冻结了“外交关系”。[注]Jenny Gustafsson, “Asia is Trawling for a Deadly Fishing War”, Foreign Policy, 6 June,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6/16/asia-is-trawling-for-a-deadly-fishing-war/ [2018-12-28].
与此同时,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与跨境渔业行为的结合,迫使各国采取激进的措施打击非法跨境捕鱼。2014年,以建设 “海洋强国”为战略目标的印尼佐科政府,高调打击非法捕鱼行为,非法捕鱼成为印尼海洋安全的重点打击对象。正如印尼海洋与渔业部部长苏西·普吉亚斯图蒂(Susi Pudjiastuti)所言,对于印度尼西亚而言,将打击海洋非法捕鱼作为海洋安全的优先着力点,不仅仅在于非法捕鱼每年为印尼带来了超过数万亿印尼盾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非法渔船已经成为人口贩卖、毒品走私等海上违法行为的犯罪工具。[注]IOM,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Fishery Sector: The Benjina Case”, 15 March, 2015, https://indonesia.iom.int/human-trafficking-fishery-sector-benjina-case[2018-11-18].而频频发生的渔业冲突,也在南海周边国家营造了一个紧张的海洋危机感。
安全化理论认为,安全应当被认为是消极的,是作为常规政治处理问题的一种失败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注]参见朱宁:《安全化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3页。由于“安全化”选择所具有的“主体间”特性,安全化选择究竟是能够实现议题获得优先处理的施动目的,还是会因为激化矛盾而引起不必要的安全困境,目前也未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南海渔业纠纷而言,安全化操作对于国家而言已经激化了国家间的矛盾,而未能彻底解决渔业冲突。佐科政府上台以来,大力打击非法捕鱼,甚至在国庆日炮击外国渔船,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而近些年来,面对诸多国家的抵制和抗议,印度尼西亚的渔业政策逐渐温和。而中国与菲律宾关系也在逐渐回暖之中。2018年,中国与菲律宾共同发表声明,“南海问题不是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全部”,并升级两国关系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参见《中国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南海争议不是中菲关系的全部》,中国新闻网,2018年11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11-21/8682240.shtml[2018-11-18]。在可以预计的未来,推动渔业资源安全治理、对海上渔业纠纷进行去安全化努力,将成为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四、前路可期的资源安全治理
相较于国家间不断爆发的安全冲突并逐步激化军事竞争而言,加强安全治理的效用和地区安全合作更有利于规避国家间的信任赤字,更易推动区域安全。对于非传统安全议题频频出现的南海问题而言,强调多边性和综合性的安全治理则为处理南海安全争议提供了解决路径。具体而言,从加强渔业安全合作、削减渔业资源冲突的角度出发,以安全治理为渔业合作机制的建立本身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国家间在复杂的主权争议背景下难以达成信任,导致目前渔业合作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以捕捞技术交流和商业合作为主;另一方面,南海脆弱的生态环境令人担忧,渔业资源的衰竭迫使掀起“渔事战火”的国家不得不偃旗息鼓共同面对这一发展困境。协商建立渔业合作机制为东南亚资源安全治理提供了新平台。
(一)资源安全与安全治理
尽管治理尤其是全球治理的观念和目标早在19世纪后期已经出现,然而治理以及安全治理引入国际问题研究,则是在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研究逐渐凸显背景下逐渐形成的。相较于传统安全研究而言,非传统安全研究具有关注 “跨国家”的安全互动、注重“非国家行为体”、侧重非军事安全研究、强调人与社会安全等特征。[注]参见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第52页。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管制不同,安全治理在安全主体、安全体制、能力范畴有着不同的特征。如果说,管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刚性的制度设计,那么治理则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柔性的能力建构。[注]参见崔顺姬、余潇枫:《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建设的新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 第88页。
从安全主体而言,安全治理关注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私人机构等有序合作。较早将治理概念引入国际政治问题研究的詹姆斯·罗斯瑙(James N. Rosenau)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没有政府的治理”。他认为,相较于政府统治而言,治理具有在行为体和运行模式上更多的包容性,不依赖政府强制性的权威而通过共同目标驱使下所进行的一致行动而运行。[注]James N. Rosenau,”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最早提出“安全治理”概念的艾尔克·克拉曼认为,在安全领域中,不同层次的参与者构成了诸多共同体和联盟,这种由公共安全行为体和个人安全行为体进行的越来越多的合作,尽管有些支离破碎但是却更好地诠释治理概念的多行为体特征。[注]Elke Krahmann, “Secur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No.1, 2003, pp.10-11.
从安全体制而言,治理指的就是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层次中,无需统一权威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与合作。这种在安全领域中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变就是安全治理。[注]lbid., pp.5-13.从能力范畴而言,安全治理拓展并深化了安全领域。“安全”、“国家安全”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主权不被干涉或者领土不被侵犯,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国家整体的安全、国内社会的稳定状况、公民个体的安危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保持良好的平衡、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注]崔顺姬、余潇枫:《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建设的新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94页。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海上渔业资源冲突,已经成为一种多源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影响着地区安全。由于海上资源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资源衰退的事实,东南亚国家迫切需要通过维护资源安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南海周边各国由此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已经突破了其经济性、社会性与生态性特征,而与领土安全与国家主权交织,成为一种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多元性安全威胁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主体多样性和领域多向性、动因多源性与目标多重性、地缘多源性与空间多维性、手段多样性与过程多变性。[注]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就南海渔业资源冲突而言,渔业资源的短缺与资源需求的日益扩大是冲突升级的原因,与此同时海洋资源跨国家性的特征使得渔业纠纷与划界冲突等国家主权争议结合在一起,多元性的特征由此可见。从参与主体而言,包括渔民、大型渔业企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渔业安全议题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学者甚至将海洋渔民组织起来的民兵看作是国家在应对南海争议的第一道防线。[注]Hongzhou Zhang, Sam Bateman, “Fishing Militia, the Securitization of Fishery and the SCS Disput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39, No.2, 2017, p.291.就应对手段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渔业资源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通过国家立法、外交途径谋求更多的渔业资源利益。2011年,在菲律宾颁布的《国家安全政策(2011—2016)》中, 宣布要加大对于海上警备队的监控和巡逻能力,甚至将巡逻范围扩展到中菲存在海上纠纷的经济专属区。印度尼西亚近年来开展打击海上非法捕鱼行动已经为其与周边国家制造了诸多外交争议。
(二) 合作现状:域内外共同推动
随着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纷纷提出海洋专属经济区主张,海洋权益的相互重叠就成为东南亚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议题。在当前情况下,南海周边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不同的渔业安全问题。各个国家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应对不断恶化的渔业问题。国际社会以及以东盟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组织为了避免渔业纠纷,为推动地区合作做出不懈努力。联合国粮农组织将1948年通过APFIC协议形成的印度洋—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发展成亚洲及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以期能够促进亚洲各国在渔业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1967年,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EAFDEC)以自治政府间组织的形式成立,以 “推动和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共同行动,以确保在东南亚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为使命,容纳了包含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11个国家在内。199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以“确定制定和执行负责任的渔业资源保护、渔业管理和发展的国家政策的原则和标准”[注]FAO,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95, http://www.fao.org/3/a-v9878e.pdf[2018-11-05].为目标,约束90年代纷争的渔业资源争夺。
在亚洲地区,东盟成为推动地区渔业合作的主要驱动力。早在1983年,东盟农业和林业部长级会议完成了渔业合作协议的签署,共同商定商业性渔业合作的共同区域,并对地区性和国际性的渔业问题达成共识。[注]ASEAN Secretariat, “Ministerial Understanding On Fisheries Cooperation”, Singapore, 22 October 1983, http://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2012/Economic/AMAF/Agreements/ASEAN%20Ministerial %20Understanding%20On%20Fisheries%20Cooperation.pdf[2018-11-05]。这成为东盟渔业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04年第十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万象计划》以及《东盟优先领域一体化框架协议》,决定将包括渔业在内的11个领域放入优先考虑一体化的领域之中,为东盟渔业合作开辟了道路。[注]ASEAN Secretariat, “Vientiane Action Programme (VAP) 2004-2010”, Vientiane, Laos, 29 November 2004, http://www.asean.org/storage/images/archive/VAP-10th%20ASEAN%20Summit.pdf[2018-11-08].东盟成员国先后成立了东盟渔业协调组、东盟海洋与海洋环境工作组等多边合作组织,为推动地区渔业合作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东南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东南亚国家在应对渔业纠纷方面已经逐渐开始进行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现有的渔业合作仍处于基础阶段,冲突仍常常发生。南海海域仍然没有一个能够有效管理非法捕鱼和海洋渔业犯罪的排他性地区组织。亚洲及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因其广泛的目标和有限的行动,难以为渔业冲突提供仲裁。相较之下,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是当前情况下唯一能够对南海渔业活动进行研究的多边机构,但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对南海渔业行为的科学研究。
(三)资源安全治理:从渔业合作着手
在渔业方面缺乏地区性组织实体或者是多边协议,被看作是南海非法捕鱼、过度捕捞以及渔业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大多数多边机制都集中在捕鱼技术共享与养殖技术交流层面,对于因渔业纠纷而引发的冲突的解决机制不足;另一方面,现有的渔业合作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因为国家间难以形成共识而举步维艰,国家间在争议海域渔业资源上的重叠利益往往使得渔业合作收效甚微,南海海域并未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地区渔业管理机构(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注]Hongzhou Zhang, “Managing fishe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troubled waters,” East Asia Forum, 5 July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07/05/managing-fisheries-in-the-south-china-seas-troubled-waters/ [2018-11-18].在南海海域相关国家有意通过共同努力推动地区合作的基础上,在现有不完善的渔业合作基础上规范国家间的渔业合作行为以及建立合作机制是推动渔业纠纷“去安全化”的有效举措。具体而言,南海渔业合作机制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合作模式:
1.议题明确,机制灵活
缺乏一个明确的治理机制是南海渔业纠纷不断安全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将南海渔业纠纷议题明确纳入南海周边国家的协商议程之中,在“弱机制化”和“弱法律化”的合作基础上建立海洋合作机制,从而推动渔业纠纷“去安全化”进程,减少渔业纠纷在地区冲突中的影响。就现有合作机制而言,缺乏一个以应对南海渔业纠纷为主要议题的合作机制和地区组织,而渔业冲突的不断激化成为地区安全框架中的漏网之鱼。因而,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法框架下提供磋商氛围,搭建合作平台,以逐步实现渔业合作的机制化、系统化十分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起步阶段的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的主要功能,是为南海沿岸国之间提供沟通和协商平台,在坚实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法理基础上提供辅助性和建议性的意见和报告,而不必具有法律效应。[注]参见李聆群:《南海渔业合作:来自地中海渔业合作治理的启示》,《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9页。
2.方式灵活,多层次合作
渔业经济是南海周边国家的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维护渔业安全、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既是国家利益,同样也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国家行为体仍然是渔业治理机制的主要行为体。而随着渔业捕捞的规模日益扩大,渔业治理的方式也需要更加丰富和系统。从协商途径上来看,传统自上而下的渔业监管框架往往是国家通过签订多边条约的形式进行合作,而没有充分发挥渔民以及企业等渔业资源利用行动中个体行为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渔业部门作为资源的监管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而渔民则希望在监管下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在渔业治理中是理性的自私行为体。尽管在渔业资源的维护中,渔民与政府部门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维护渔业资源的持续性,然而在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机制中,渔民与政府却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似乎与管理者的目标完全背离。因此,渔业综合治理应该逐渐推动多方共赢的模式,将渔民以及渔业企业纳入渔业综合治理的行为体范畴中,分享权力、共同决策,灌输渔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促进渔业综合治理的可行性更强。
3.利用现有机制,发挥中国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8日。。随着南海形势明显降温趋稳,有关争议方回归到通过谈判磋商解决争议的正轨,国家间关系明显改善。2017年11月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峰会上,中国和东盟正式宣布将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的案文磋商。[注]参见《李克强在第12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11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10608.shtml[2018-11-18]。在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中国提出的“3+X合作框架”获得东盟赞赏。对南海渔业纠纷而言,可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而减少国家间渔业冲突的不信任感,共同建立合作机制。将渔业纠纷议题重新纳入“公共议题”范畴之中,而非通过采取“安全化”措施进行应对。
五、结 语
渔业资源既是国家冲突的诱发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推动地区资源安全合作。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资源引起的纠纷和争端,地区安全极有可能陷入一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如何在当前的国际社会的框架下对国家间发生的资源冲突做出相应的去安全化努力,越来越考验各国的外交应对能力。但渔业资源的合作、海上资源安全的治理道路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
渔业纠纷是近年来资源冲突的一个突出体现。因渔业资源而引发的冲突甚至战争已经成为地区安全需要面对的新议题。审视世界各地的渔业合作,也是一个在利益竞争中不断磋商、在谈判中互相妥协的过程。因此,应对南海渔业纠纷,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逐渐建立冲突应对机制和协商治理机制,为推动资源安全治理和地区和平稳定迈出坚实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