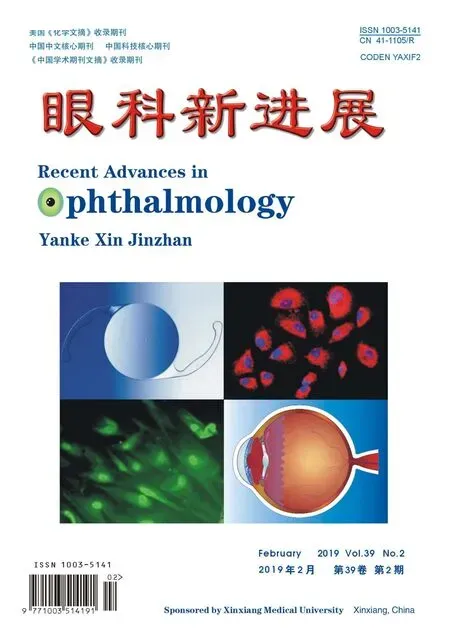儿童部分调节性内斜视术前戴镜时限对术后效果的影响
2019-02-27姜丹妮韩冬张佳欢裴天序赵琪
姜丹妮 韩冬 张佳欢 裴天序 赵琪
部分调节性内斜视在临床上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共同性内斜视,约占共同性内斜视的1/3[1]。导致其发病的因素包括调节因素和非调节因素[2],调节部分所致的斜视度需要配戴全矫镜来矫正,伴有弱视的患儿应在配戴全矫镜的前提下进行弱视治疗。临床研究表明,配戴全矫镜一段时间后患儿的斜视度明显减小,但非调节部分所致的残留斜视度仍需手术矫正。因为斜视严重影响患儿双眼视觉的发育,过晚手术会导致患儿术后双眼视觉难以重建[3],所以不可一味等待弱视治愈后再进行手术[4]。但是过早手术会导致非调节部分斜视角不稳定,术后一段时间出现外斜视的可能性较大[5]。究竟术前戴镜多久再进行手术较为合适呢?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为分析术前戴镜时限对患儿术后效果的影响,我们根据术前戴镜时限将就诊于我院的部分调节性内斜视患儿分为术前戴镜0.5 a和1.0 a两组,对两组患儿的术后效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找出合适的儿童部分调节性内斜视的手术时机。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来我院就诊的部分调节性内斜视患儿60例(120眼)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8例(56眼)、女32例(64眼),年龄3~11岁,平均6.2岁。入组标准:首先应用裂隙灯及前置镜对所有患儿进行眼前节及眼底检查以排除其他眼部疾病,患儿配戴全矫镜0.5 a或1.0 a后视近或视远斜视度减小,但不能完全消除,且残余内斜视度≥+10△。按术前戴镜时限分为A组30例60眼,B组30例60眼。A组患儿术前戴镜0.5 a且斜视度稳定,B组患儿术前戴镜1.0 a且斜视度稳定。
1.2方法
1.2.1术前准备(1)患眼用10 g·L-1阿托品眼用凝胶麻痹睫状肌后验光,均为远视或远视合并散光,伴有弱视者18例(32眼);(2)所有患儿均根据散瞳后验光结果配戴全矫镜进行矫正,伴有弱视者积极治疗弱视[6];(3)术前根据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并记录患儿的最佳矫正视力(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BCVA),采用三棱镜加遮盖法测量患儿裸眼及戴镜33 cm和5 m的斜视度,采用同视机及Titmus立体图分别测量患儿的远立体视功能和近立体视功能。
1.2.2手术设计以配戴全矫镜后残余斜视度为标准设计手术量。内斜度数<+20△的患儿采取单眼内直肌后徙术治疗;>+25△~+45△的患儿行双眼内直肌后徙术治疗,>+50△的患儿采用双眼内直肌后徙术联合单眼外直肌缩短术治疗[7]。本研究患儿中行非主导眼内直肌后徙术8例,双眼内直肌后徙术46例,双眼内直肌后徙联合非主导眼外直肌缩短手术6例。
1.2.3术后随访所有患儿随访均不少于0.5 a,复查时根据术后眼位变化调整眼镜度数,使眼位保持正位或内隐斜。术后0.5 a复查时检查患儿的BCVA、眼位、远立体视功能及近立体视功能。眼位正位:戴镜斜视角-8△~+8△;过矫:戴镜斜视角>-8△;欠矫:戴镜斜视角>+8△[8]。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术前、术后两组间BCVA比较及两组手术前后BCVA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术前、术后同视机及Titmus等相关结果比较采用交叉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验光及视力术前患眼等效球镜度数为+1.00~+7.00 D。术前BCVA≥0.9者25眼,其中A组13眼,B组12眼;0.6~0.8者68眼,其中A组33眼,B组35眼;≤0.5者27眼,其中A组14眼,B组13眼。术前两组BCVA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96)。0.5 a复查时,BCVA≥0.9者28眼,其中A组14眼,B组14眼;0.6~0.8者66眼,其中A组32眼,B组34眼;≤0.5者26眼,其中A组14眼,B组12眼。术后两组BCVA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70)。A、B两组术前与术后BCVA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267、0.406)。
2.2眼位术前眼位,裸眼33 cm:+25△~+120△,平均+53.25△;戴镜33 cm:+15△~+80△,平均+42.63△;裸眼5 m:+20△~+120△,平均+52.14△;戴镜5 m:+15△~+80△,平均+40.63△。裸眼33 cm与戴镜33 cm斜视度差平均为10.62△,裸眼5 m与戴镜5 m斜视度差平均为11.51△。术后0.5 a时,54例患儿眼位正位,正位率90.0%,其中A组26例(86.7%),B组28例(93.3%);1例过矫,过矫率1.7%,这1例为B组的患儿(3.3%);5例欠矫,欠矫率8.3%,其中A组4例(13.3%),B组1例(3.3%)。术后两组患儿眼位的正位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66)。
2.3远立体视功能术前同视机检查结果:A组无同时视及拥有一级视功能、二级视功能、三级视功能者分别为18例(60.0%)、 9例(30.0%)、 2例(6.7%)、 1例(3.3%);B组分别为18例(60.0%)、7例(23.3%)、3例(10.0%)、2例(6.7%)。术前两组间患儿各级视功能保留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84)。术后0.5 a复查时,无双眼视者15例(25.0%);拥有一级视功能、二级视功能、三级视功能者分别为5例(8.3%)、8例(13.3%)、32例(53.3%),合计有双眼视功能者45例(75.0%)。与术前比较,术后0.5 a双眼视功能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其中A组无同时视及拥有一级视功能、二级视功能、三级视功能者分别为10例(33.3%)、2例(6.7%)、4例(13.3%)、14例(46.7%);B组分别为5例(16.7%)、3例(10.0%)、4例(13.3%)、18例(60.0%)。术后两组间患儿各级视功能保留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6)。
2.4近立体视功能术前Titmus检查结果:A、B两组中拥有近立体视功能者均为3例(10.0%),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0.5 a复查时,拥有近立体视功能者共32例(53.3%)。与术前比较,术后近立体视功能显著提高,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6)。术后A、B两组拥有近立体视功能者分别为14例(46.7%)、18例(60.0%),组间拥有近立体视功能的比例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96)。
3 讨论
部分调节性内斜视是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共同性内斜视,多见于12岁以下的儿童[9],其发病年龄为1~3岁[10]。发病原因包括调节因素和非调节因素,调节因素多由不同程度的远视性屈光不正引起[11],而非调节因素包括解剖因素,先天性融合功能发育不全或是由于完全调节性内斜视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所致的内直肌功能过强[12]。对于调节部分所致的斜视度,我们需要给予10 g·L-1阿托品眼用凝胶充分散瞳后验光,然后配戴全矫镜矫正。全矫镜不仅可以较好地促进远视力的提高,治疗弱视,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去除调节因素以减弱斜视度对双眼视觉的影响[2]。戴镜一段时间后,对于戴镜不能矫正的非调节部分则需要进行手术矫正。
部分调节性内斜视不仅伴有远视性屈光不正,而且多伴有弱视,伴有弱视者需在戴全矫镜的同时积极治疗弱视[13]。但不应强求弱视治愈后再行手术矫治残余斜视。研究提示,当治疗弱视至双眼视力差距<2行且戴镜斜视度数稳定时应当尽早手术,术后患儿可继续积极治疗弱视[14]。若一味等待弱视治愈后再行手术矫治,则会错过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耽误双眼视功能的重建。
双眼视功能是人类在对外界环境认知中所形成的高级视功能,是指双眼同时使用的时候,视皮层对落在双眼视网膜黄斑区的物像进行识别并整合来自双眼的视觉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立体感的像的过程[15]。立体视是人类生后获得的,是在同时视和融合视的基础上建立的,拥有立体视的个体对三维空间有良好的认识,能够从事一些相对精细的操作,立体视也是双眼视功能的重要优势体现[16]。
儿童双眼视觉的发育是从2个月到9岁,在1~3岁内的某个时段双眼视觉的发育达到高峰[17],3岁之前为双眼视觉发育的敏感期,4~9岁为双眼视觉发育的成熟期。整个双眼视觉发育期内,任何异常的视觉经历,尤其是视轴不平行所引起的异常视网膜对应能够迫使双眼视觉发育暂停[18]。大量研究表明,手术能有效矫正残余斜视度,使双眼视轴平行,眼位稳定,从而建立正常的视网膜对应,促进双眼视功能恢复,建立远近立体视。有研究表明,在视觉发育敏感期内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是可逆的,及时去除这些不利因素,双眼视觉仍可继续发育,仍有较大的机会形成良好的立体视。所以一旦发现斜视应及早进行治疗,如果超过视觉敏感期再行治疗,其疗效明显不如在此时期内进行治疗者[19]。近些年临床研究表明,超过9岁的患儿术后也有很大一部分重新建立了双眼视,手术对其双眼视功能的恢复仍有积极的作用,双眼视觉的发育仍存在机会。因此对于大龄患儿,我们也要积极进行手术,术后积极配合双眼单视功能训练,不可轻易放弃,以期获得较好的双眼视功能,而手术时机的选择对于患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据文献报道,有的学者认为配戴全矫镜后残留的非调节部分应尽早行手术矫治,这对术后双眼视觉的恢复十分重要[20]。也有报道指出,由于发病后长期不行手术矫治,部分患儿发生内直肌纤维化,眼球外转受限,所以发病后长期的等待对患儿来说十分不利。另有学者认为,对于部分调节性内斜视患儿应给予充分的观察,待其斜视度数完全稳定后再行手术矫治其非调节部分。我们在本研究中试图找出一个恰当的术前保守治疗时间,针对术前戴镜时限对术后效果的影响展开研究,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有益指导。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戴镜0.5 a的患儿在术后0.5 a复查时,无同时视及拥有一级视功能、二级视功能、三级视功能者分别为10例、2例、4例、14例,拥有近立体视功能者14例;术前戴镜1.0 a的患儿在术后0.5 a复查时,无同时视及拥有一级视功能、二级视功能、三级视功能者分别为5例、3例、4例、18例,拥有近立体视功能者18例。术后两组间患儿各级远立体视功能保留率及近立体视功能保留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两者手术效果相同。因此,对于部分调节性内斜视的患儿来说,术前戴镜0.5 a即行手术矫正眼位可以达到尽早改善眼位及双眼视功能的目的,应该是我们首选的治疗方式,如果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而不能在戴镜0.5 a时手术,那么在戴镜1.0 a时手术亦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本研究中所有患儿均以戴全矫镜后残余戴镜斜视度为手术量。由于双眼内直肌后徙术所能矫正的有效斜视度约为+50△,所以对于斜视度数超过+50△的患儿,我们采取双眼内直肌后徙联合单眼外直肌缩短术治疗。对于手术量的设计,业界学者争论不一。因为手术量不仅取决于斜视度的大小,术中还应考虑肌肉的宽度和强度,肌肉附着点的位置等因素,这对术者的经验要求较高[21]。
术后戴镜检查患儿眼位,对于符合过矫诊断标准(>-8△)的患儿,适当减少远视度数重新配镜[22];对于符合欠矫诊断标标准(>+8△)的患儿,若其术后斜视角>+15△,需行二次手术进行矫正。由于本试验所有患儿术后斜视角均<+15△,所以对于这部分患儿,我们根据术后散瞳结果进行过矫配镜,随诊观察即可[23]。随着视觉发育,生理性远视逐年减少,眼位仍可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每 0.5 a 进行散瞳验光以了解患儿的屈光度变化,通过重新验配眼镜来保持眼位正位以及获得BCVA。对于术后眼位稳定但仍有弱视的患儿应继续积极治疗弱视。双眼视功能是评价斜视和弱视治疗效果的良好标准,对于部分调节性内斜视的患儿来说,矫正眼位、改善外观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双眼视觉的恢复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所以对于所有患儿,术后应积极进行双眼单视功能训练,促进双眼视功能的重建,使患儿获得良好的生活体验[24]。对于患儿家属,术前应告知手术仅矫正非调节部分,术后仍需戴镜矫正内斜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