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
2019-02-26赖一粟
赖一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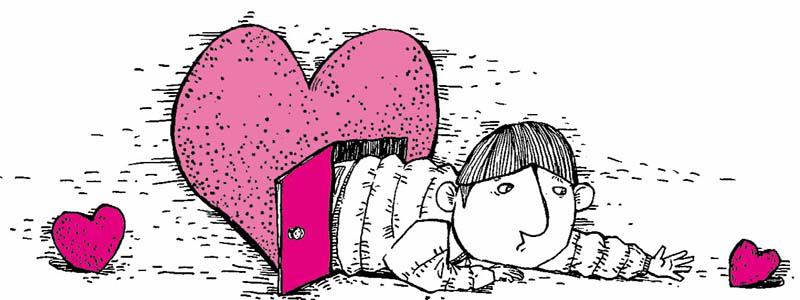
我8岁时,母亲给我生了一个弟弟。我从没有想过会有一个不熟悉的人出现在家里。但从某一天开始,整个家里都充满了弟弟的气息:他的声音,他的奶香味儿,占据了所有的房间,即便他不在时,也是如此。
每当父母问我对弟弟的到来有什么想法时,我都回答:“我不知道。”这并非是我刻意与弟弟疏远——事实就是如此。
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去父母或弟弟的房间。父母的房间里有一张很大的双人床,除此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而弟弟那间,堆满了积木和各种塑料玩具。被套总是蓝色的,经常更换,有着阳光的味道。吊灯是宇宙飞船式样,仿佛时刻引诱着一个小男孩去往某个未知的星球。我曾长时间打量过坐在玩具堆中的弟弟:粉嫩的肌肤、黑亮的眼睛,嘴巴微张,不断咕哝着。他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更得父母的欢心。
圣诞节那天,我将他装扮成鲁道夫。他起初不愿意,后来妥协了。当他撅着嘴唇,将涂了红颜料的鼻尖对着我时,我知道他其实并不开心。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残忍的胜利,原本的快乐变得隐隐约约。
有段时间,入睡前我总是强迫自己睁着眼睛,默背着白天的功课,或是想着别的事情,不让自己睡去。我害怕瞌睡迫近前松手坠落的感觉。慢慢地,我的入睡时间从11点变为12点,直至被无限推迟。隔壁房间传来轻微鼾声时,我便悄悄起身穿好外套,走到阳台上去。阳台的门被推开时会发出声响,我便用后背和左手抵着,小心翼翼地腾出右手来推。门外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好像近视的人摘掉了眼镜,眼前的一切变得温柔又宁静。天空中挂着干瘪的月亮,远处的霓虹灯尚未入眠。道路上空无一人,依稀可见一些烟蒂、废纸和酒瓶。日常的一切从我身上脱离,我将其理解为解脱。我在夜里起身去阳台,还有别的理由,那就是我害怕自己会走进弟弟房间,去伤害他。
起初,这个想法让我感到震惊和羞耻——我可以用枕头或被子闷死他。他一定会挣扎,扑腾着两只青蛙一般的小腿,但这是无用功。我的手带着快乐的痉挛与无知的勇气。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并不恨他,我只是见不得父母投向他的专注的眼神。
于是每天在天空依稀泛白前,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睡三四个小时。醒来之后,听到小家伙的汤勺叮当作响,我便如释重负地微笑。心中的负罪感与歉疚每天都在加深。
我一直都小心翼翼,但有一个晚上出了问题。有人在那里,是我关上阳台门时发现的。凌晨微白的光线映出他的轮廓。
是爸爸。他坐着,好像在抽烟。“你在干什么?”他问我。 “睡不着。”我只能这样回答。等待被质问,最好是一声低吼,他向来都这么做,带着某种绝对的权威与粗暴,这样我便可以飞快地跑回卧室。结果他说,睡不着很正常。然后,我们的对话在清晨的微光中默契地进行下去。我谈到学校里的事情,那些女孩,以及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最后说到了弟弟。我说我不是什么时候都很喜歡他——但说到这个似乎还不够,最终我并没有忍住。“我会杀了他。”最后我说。
“哦。”他大概是呼了一口气。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没有担忧,更没有敌意。他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有如火山底部岩浆一般被压制的愤怒、神经质的劝告、大呼小叫的恐吓。这是他第一次不以父亲的身份看我,仿佛他不是我和弟弟的父亲、妈妈的丈夫。那目光不带有审视意味,也没有观察我的意图。我想我以后和一个男人结婚时,父亲看我的眼神也一定不会有现在这般坦诚,使我感激。他没有刻意回避,也不说任何开导的话。我认为他是信任我——有些事情上一秒你还在为之担忧,下一秒它便过去了。这可能就是血缘的神奇。我看见他穿着白天的衣服,衬衣皱巴巴的,没有系领带,吸着烟。他早已不再看我,转而看着他那看起来很悲伤和粗笨的脚趾。我害怕他会再说些什么破坏了这个瞬间,但他没有。我猜测,他肯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他只说:“好了,早点睡觉。”躺回床上时,我以为自己肯定睡不着了,没想到却睡得又香又甜。
这之后,我时常想起那个夜晚。想着父亲为什么穿着白天的衣服,神情疲惫,吸着烟。无从得知。但在沉湎于没有答案的想法时,我总觉得父亲当时的做法是最正确的——没有任何的回应,恰恰是那时我最需要的。我需要的是轻描淡写,是遗忘。这拯救了我。我突然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和解的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