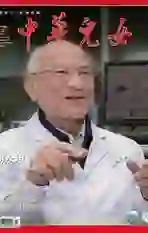八小时之外,人生如戏
2019-02-26梁伟
梁伟
当下的戏剧舞台上,活跃着这么一群人,戏剧成为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却不是他们的工作,也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他们不靠演戏挣钱,而是让戏剧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被称为——“非职业戏剧人”。
仅仅在北京,由“非职业戏剧人”组成的剧社就有几十家之多,在大大小小的剧组活跃着的非职业演员不计其数。他们中间有两鬓花白的老者,有刚刚读初中的少年,有公司白领,有律师,有医生……无一例外的是,在八小时之外,或是到了周末,他们就都成为了演员。这一群人在都市里过着从日常到剧场的“穿越”生活。借助舞台,有的人在此给自己找了片心灵的“栖息地”;有的人则希望在职场之外“解个闷”;还有的人则用一股纯粹而原始的“冲劲”去实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理想,试图去演绎另一种多姿多彩的悲喜人生。


放眼现在的世界剧场,通过表演触碰真实的尝试无处不在,无论是让普通人登上舞台,还是让他们在舞台上演绎自己的经历,甚至是让他们走出剧场进行表演,这一切都是不断模糊戏剧与生活的界限,构成了戏剧不断寻找与普通人生活联系的多种方式。其实,戏剧的意义终应该落在剧场之外,在剧场里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表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展露的一面——职业规范、社交礼仪层层遮掩下的自我,一个真真切切的自己。
戏剧作为高度综合的集体文艺生活,从来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内需。非职戏剧社的涌現,说明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要求更高了。非职业戏剧可以被称作是职业戏剧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职业戏剧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通过它培养了更多的戏剧观众。
“非职戏剧人热爱或喜欢戏剧,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却不以盈利为目的。这种健康理想的非职戏剧蕴含着质朴本源的戏剧精神,推广普及这种戏剧精神,或许可为现下一些过度娱乐的消费戏剧解解毒,防止剧场退化成低俗娱乐场所。”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杨乾武表示,“中国职业戏剧,尤其是国有主流戏剧,其门槛世界第一。但不是艺术门槛,而是技术、投资、票价等非艺术的门槛高不可攀。艺术门槛却一低再低,陷于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自我封闭,敝帚自珍。非职戏剧的目的正是打破职业戏剧的各种无谓门槛,广泛普及推广传播戏剧文化,吸引更多人参与戏剧活动,关注戏剧的现状。”
王蝉:“舞台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大学毕业之后,她开始担任中央广播艺术团导演,艺术团的孩子们叫她王老师;近年来,她多次担任央视、央广大型晚会的导演,集编、导、演于一身,演职人员称呼她王导;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话剧社的创始人,话剧社除了艺术团的孩子们之外,演员大多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这些人喊她“蝉哥”。
她,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优秀导演王蝉。近年来,她带着这么一群“非职业演员”演绎的《夜上浓妆》、《蝴蝶,飞吧!》在青年戏剧节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改编自作家史铁生同名小说《命若琴弦》的戏剧作品获得了著名戏剧评论家、翻译家童道明先生的高度认可;关爱孤独症儿童的公益作品《愿望树》走进了国家话剧院……
王蝉的作品充满了理性和痛苦的自我审视、热情而又绝望的寻找着生命中的“爱与温暖”。张扬、极致,旗帜鲜明的宣扬着女权主义,充满了对女性的悲悯与关怀,而既定的女人底色,让她的手笔细腻、敏感,所以她的作品爱憎分明又温暖人心。


时至今日,王蝉都清楚地记得儿时第一次和妈妈走进剧场看戏的情景。那时候,舞台上的一切对于她来说都是新奇的:人竟然可以从天而降,花儿骤然开放,甚至光束中飞舞的尘埃……这些神秘莫测的变幻燃起了她对舞台的好奇与兴奋感。
在梦想的指引下,她一直在努力前行,为了学习到更加专业的知识,她报考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传媒大学导演表演系攻读硕士学位。进入传媒大学学习后,王蝉的视野更加宽广。在一次参加国际大师的工作坊中,百老汇的演员、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的指导老师等杰出国际名家的出席,让王蝉深受震动:“那真是豁然开朗的一次交流,所有的眼界、格局都被打开。”
大学毕业之后,王蝉考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编稿子、做节目的忙碌生活。就在很多人以为她和舞台越来越远的时候,她开始担任中央广播艺术团导演。随后,酷爱戏剧的她与同事成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话剧社,除了艺术团的孩子们之外,还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组成。
“话剧社的主播们在台词处理上特别棒,有一些主播甚至之前是学表演的。”成员们身上的能量给了王蝉很大启示,“既然大家都喜欢,为什么不一起玩呢。”尽管所有人都不是专业演员,但大家都非常刻苦,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表演。
这些主播们来自各个频率的不同节目组,林溪、子文、陈亮来自中国之声,王驿、贾男来自中华之声,梅卿源来自音乐之声……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要把这样一群主播凑到一起进行排练着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很忙,主播们的直播压力是很大的,但是他们都是热爱表演的人,大家都会克服时间的难题,身心的疲惫,只要进入排练厅,大家的态度都是严肃而认真的”。王蝉说。
虽然主播们在节目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个性,但是在排练厅里,导演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王蝉笑着说“:可能是受到孙维世导演的影响,她工作中严格得不得了,但是演员们都很爱她。”在排练《命若琴弦》时,王蝉读了史铁生先生所有的著作,并要求演员们除了原著之外,还有几部作品必读。其中,原著中三弦琴的唱段其实并不是真实存在。王蝉便联系到三弦琴世家为唱词谱曲,要求对方看剧本,并为对方讲史铁生先生的故事。而她常常为了一场戏,会排练到深更半夜,一直在抠细节。往往在排练的时候,她是感觉不到辛苦的。王蝉说:而真正能站在舞台上的,都是极其热爱舞台的。能在这个时期遇到那些志同道合、那么纯粹的人,特别幸福!小时候问‘幸福是什么?现在不需要问,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幸福!”
从《一个人的战争》、《夜上浓妆》开始,王蝉便被贴上了女权标签。对此王蝉丝毫不介意,她希望通过女性更为细腻的视角为女性发声。她的作品探讨了外部生存环境对人的影响,手法多样,却细腻深刻。她的《蝴蝶,飞吧!》则是两种极端评价:剧结束,有的人泣不成声;有的人则觉得都是女人的事,没有多少感觉。王蝉用碎片化的时光处理,探讨女性背后不可承受之负荷;舞台风格则更加浪漫唯美。尽管朋友对她导戏风格的转变颇有不适,她还是坚持内心却并不盲目。她希望通过戏剧可以不断解放自己的思想,每一步都有提升。
带着主播们在郑州巡演的时候,剧场的侧台堆满了杂物。“我当时想,舞台是多么神圣的地方,有多少人为了登上舞台付出努力,怎么能这样呢!”身为导演的她便开始收拾侧台,剧场的工作人员面露尴尬,过来帮忙,被王蝉拒绝了。“大家都各有分工,布景装灯之类都忙到深夜,我正好有空,而且我很开心去干这件事情。把舞台收拾得很干净、舒服,我特别满足!也是那次经历才让明白我是如此深爱舞台!”
每次演出之前,看到观众慢慢入场、落座,王蝉便会问自己:在这90分钟里,可以给观众带来什么?给他们的孩子们留下怎样的记忆?“有了这些感悟,之后每次上台前,我会对演员说,你们要把它当成生命中最后一场演出。”
2014年8月,由北京市西城区公益文化传播中心出品、王蝉导演的公益舞台剧《愿望树》在国家话剧院免费公演五场,该剧改编自残障特教事业中的真实事件,讲述了一位培智学校老师克服重重困难,帮孩子们实现参观天安门的愿望的故事。为体验生活,王蝉走进了培智学校。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做游戏。一个孩子突然停下来盯着王蝉,她有些不知所措。大概停顿了几秒后,他笑着和王蝉招手:“你好!”那一刻,生活向她打开了另一扇门。她的思绪疼痛、感动而抽泣着,她愿意创作一部充满善意、正能量的作品。
她在《愿望树》的导演阐述中写到:“可能是职业的原因,特教老师们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像夜空的星星。而那些同样拥有梦想的孩子们,之所以被称作‘星星的孩子,我想正如同苍穹与星星。星星从未离去,只是黑夜到来时,才凸显它的光明!”
《愿望树》演出结束后,王蝉正在后台开会总结,听到工作人员说有观众很激动想要见她。王蝉在想“是有什么问题吗”?她走出门口发现有两家人在门口等着她。一位阿姨想要和她拍照,一位阿姨眼含着泪对王蝉说自己的孩子也是自闭症:“谢谢你花时间,排了这么一部戏。谢谢你!姑娘!”当时,王蝉内心酸涩:“阿姨,您比我伟大多了,您一直陪着孩子,我只是排了一部戏。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星星的孩子。”
多年来,王蝉在旅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看当地的戏,领略不同风格的戏剧让她在创作中更加开阔。“现在国外的剧院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游客。如果我们的城市发展到,游客每每到一个地方旅游,剧场成为一个地标,看戏成为旅行的一部分,这样更好!”她呼吁大家多关注小剧场:“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虽然王蝉的儿童剧在大剧场非常叫座,但她还是坚持在小剧场演出。

“小剧场非常锻炼导演的节奏感,而大剧场需要导演有很好的掌控力,是导演综合素质的体现。小剧场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创新的舞台,更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地方,留下了许多有质量的作品。虽然我有不少大剧场的经验,但我依然热爱小剧场!”
与朋友聊天,对方问王蝉:“如果没有恐惧,你会做什么?”当时这句话直指王蝉内心的困境,她身边不少当初一起做戏剧的青年同仁,正逐渐离开戏剧圈子,进入看似前景更加广阔的影视行业。毕竟,戏剧相对于影视,未来被赋予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虽然近两年,王蝉导演的《星期8》登陆院线,《七天大圣》也即将和观众见面,但她还是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没有恐惧,我会更愿意去做戏剧,对舞台的热爱让我更坚定地走下去。”
袁子航:梦想把素人变成戏精
“让八小时的工作,不再乏味,让第二职业的匆忙,不再束缚我们的肢体,脚步慢一些,让我们在工作之余,与快乐时光相拥,与天性解放深吻。在表演的舞台上,让梦想自由的奔放,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表演的权利。”五四青年戏剧联盟主席袁子航说。
在国内,很多“非职业戏剧人”都知道袁子航,因为他为太多普通人插上了梦想的翅膀,很难想象,袁子航也不是科班出身,高考填志愿时他报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物理系,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戏剧执着的爱,大学期间,他就在学校创办了戏剧社,排了四年的戏,依旧乐此不疲。在毕业择业之时,他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一个专业的话剧制作团队——戏逍堂。问其原因,就是戏逍堂的口号——“让生活有点戏”。在这个戏剧工厂里,跟随着戏逍堂的创始人关皓月,袁子航对于话剧这个行业,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理解。
在袁子航的身边,聚集了一批野心勃勃的戏剧狂人,做戏就是他们的狂人日记。他们了解戏剧,因为戏剧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戏剧没有限制:有爱情、喜剧、悬疑、武侠、经典;更有时尚,有流行,有娱乐,有思考。他们捕捉生活里出現的新东西,找到合适的、激起观众共鸣的视角呈现在大众面前,通过不懈的努力开辟一条戏剧工业化的道路。而在这其中,袁子航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对于戏剧也是无比的狂爱。
于是,在戏逍堂的支持下,袁子航和这群同样为戏剧执着的人成立了第三职业戏剧联盟。
一群五湖四海的朋友因为相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慢慢地,袁子航发现:这些知己能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从小就有舞台梦想的人,他们一直渴望走上舞台,但是因为家人的阻拦,或者一些其他原因,没有走上表演之路,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所以当工作满足家庭生活之后,再遇到接触舞台机会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拼命想抓住这个机会;一种是曾经并没有登台的梦想,但是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希望在工作之余,结交一群有艺术细胞的朋友,添加一种生活方式,高雅的、纯粹的、干净的氛围,然后大家通过努力,共同去完成一个目标,让自己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让自己的心情更加愉悦;一种是闲暇时间特别充裕,工作生活没有压力,年龄稍微大一些,他们想去挑战一下生命中的不可能,通过这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袁子航说:“我非常乐于和非职业演员一起工作,原因很简单,对于戏剧,他们非常虔诚。你说的每一句话,你说的每一个舞台呈现的细节,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的记住。可能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专业演员,所以会更加努力和认真。对于表演,是发自肺腑地爱,所以他们背台词会很快,也不会随意的更改。他们会一遍遍地去找寻人物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的状态,这样的专注让他们很容易代入到角色当中,可能舞台上会有口音,肢体不到位,表情不够丰富,但是他们却是极其真实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表演或许比职业演员还好看!”

在与这群非职业演员的合作中,袁子航常常被感动,在排练《一个白领的自我修养》的戏时,因为角色有十个人,这些演员白天都有本职工作,只能在下班和周末的时候集结到一起进行排练,很多人都是下班打卡飞奔到地铁,赶往排练现场,不少人都是一个面包排上三个小时,而在演出倒计时期间,排练常常到凌晨两三点,有车的人把没车的人送回家,基本上天也快亮了,新的工作日又开始了。可以说,戏剧把他们八小时工作之外的生活填的满满当当,完全没有娱乐生活和聚会时间,即使这样,所有的人也毫无怨言。
时至今日,袁子航接触到的非职业演员就有1600多人,而这其中,最后能登上舞台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这些人上不了舞台,不是因为他们的条件不够好,或者说我画了一条什么样的线,只能说,在某个角色上面,出现了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或者说所有一切都很合适,只有他的工作时间不允许,在演出的那段时间,他恰好有重大工作推脱不开,只能遗憾错过,还有一种就是喜欢在幕后服务的,他们的快乐不是站在舞台上,而是参与到戏剧的体验过程中。”
袁子航说:“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义是:把素人变成戏精!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我要去做表演老师,我只想在自己的作品中,有一个标签是素人。希望通过我的力量,让更多的普通人接触戏剧,走上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表演,评价演得不错!演得挺好!还挺厉害的!我就会特别欣慰。”
席雯: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或许,还是孩童的时候,席雯就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她在学校,唱歌跳舞一直是特长,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她想上艺校,家人极力反对,告诉她,等考大学的时候再讨论。而高中毕业,妈妈领着她去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面试,结果,面试结束,妈妈说,你还是考非艺术类大学吧!就这样,席雯考上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后,成了海南航空公司的一名员工,过起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在海南航空公司,一群喜欢话剧的员工成立了月心话剧社,席雯自然也是其中一员。虽然偶有排练,但是进剧场,上舞台是她没有想象到的。2012年,戏剧联盟和海航合作,排演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那时候的席雯被调离到集团内部的一个新公司,担任负责人,工作极其繁忙。但是在内网看到招募演员的信息之后,希雯特别激动,“我当时感觉这就是一个机会,不管工作多忙,我一定要去试试!”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希雯一击即中,成为郭晓丹的扮演者。接到电话的席雯感觉难以置信,认真准备着角色和台词。每天五点下班,她就从西五环赶到东三环的排练厅,周末也基本上都在排练,只要一有时间,她就琢磨自己扮演的角色。
席雯说:“郭晓丹的情感经历和我自己有些相似,当初试角色我挑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可以把内心向往的生活方式在剧中实现。这个角色对我来说,还是极具挑战性的,郭晓丹应该是一个十六岁左右天真浪漫的小女孩。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人物的年龄层,我一直找不到,感觉自己把青涩的初恋演绎成了黄昏恋。排练过程中,导演也运用多种手段,让我和有过演出经历的演员通过肢体的接触,去激发内心的情感。应该是经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磨合才慢慢找到那点感觉。”
排练之后,还是要通过舞台去检验的。在后台化妆的时候,席雯就极为紧张,想想自己很多朝夕相处的同事都在台下看着自己,她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她一出场是坐在椅子上,头上一个定点光,她要对着镜子化妆,席雯能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手一直在发抖,倘若她是站着的话,腿也一定是抖着的。
“完全记不住自己抖了多少场,直到有一天,她在戏里打了男主角一嘴巴的那场戏,一巴掌下去,感觉戏就到了一个高潮,我整个人的情绪全部爆发了,什么都不想,完全沉浸在角色和情绪中。那一刻,我找到了这个人物,从那之后,我认为自己对舞台的掌控能力要比之前好一些。至少更加收放自如了。”席雯说。
演出总有落幕的时候,在最后一场的演出中,她的表演把剧中其他演员都打动哭了,而在谢幕的时候,她泪流满面,感觉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也不过如此。而在演出之后,没有排练的日子里,让她感到莫名的空虚和失落。
幸运地是,因为在《有多少爱可以胡来》里的出色表演,让很多人记住了她。海航内部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她演了,戏剧联盟演出《与丘比特同谋》、《李晓红》也都找到了她。虽然排练耗时,费用很低,有的甚至没有任何酬劳,但是席雯依旧乐此不疲。
那时候,席雯参加了第三职业戏剧联盟几乎所有剧目的演出。联盟中流传着一个她的段子:席雯有三星期的年假,怎么休法,她先请示的不是老板也不是老公,而是联盟负责人,因为她休年假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这个假期多排几天戏;后来,她索性说:“要不我生个孩子吧,可以休7个月,这样一辈子的戏都排出来了。”
席雯说:“我的工作和演戏完全不矛盾,8小时工作之外,回家或许还要加班,在工作时间内全身心投入,把工作做好。等到排練演出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了,都在戏里!这就是一个角色的转换吧!梦想照亮生活,真的会带来不一样的色彩!曾经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舞台上实现不同的人生,和一群志同道合喜欢戏剧的朋友走到一起,让我的生活变得色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