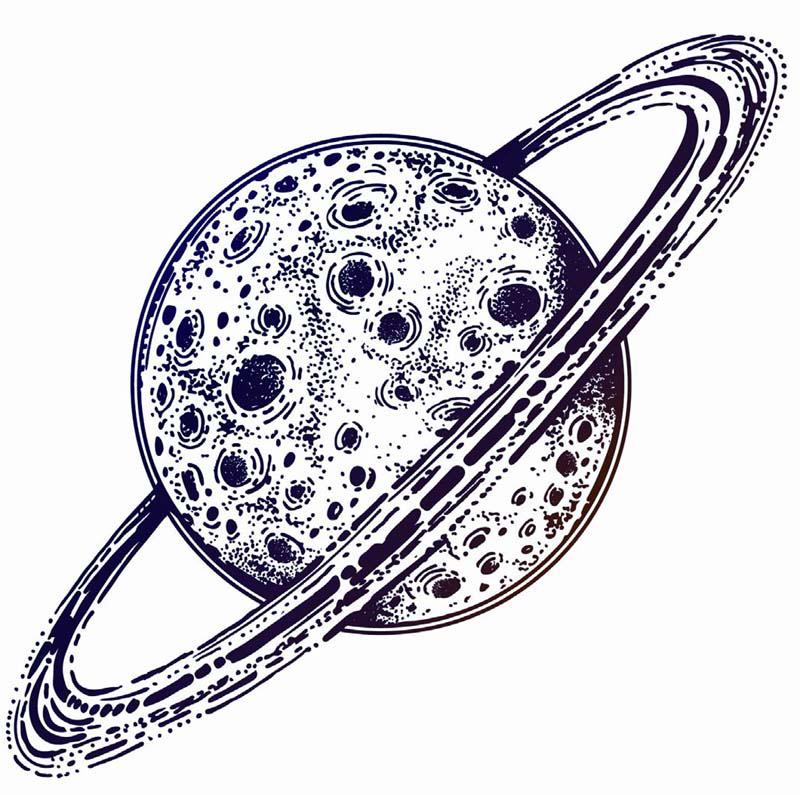人民为什么需要科幻
2019-02-24严锋
严锋

电影《流浪地球》取得的巨大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社会、技术、心理的动力。这些来自各方面的因素被一种文艺样式所整合,那就是科幻。很多年前,我关于刘慈欣说过一句话: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准。今天我仍然相信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需要补充修改了。更确切地说,科幻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刘慈欣与他的战友们响应了人民的呼唤,一起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准,并进一步推动了这股大潮。
科幻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神话
相对于源远流长的其他文艺样式,科幻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对来说是个新生事物,对于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科幻在上世纪初传入中国,从某种意义上,鲁迅也是中国科幻小说的先驱之一。他早在1903年就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对“科学小说”的启蒙意义寄予厚望,认为“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的《故事新编》,按照今天的定义,也是可以归入科幻的范畴的。可惜的是,科幻小说在五四以后道路曲折,命运多艰。科幻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启蒙的工具,但是在近现代史上,更迫切的任务是救亡。所以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科幻作品只有寥寥几种。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启蒙的科幻又被纳入议事日程,但是其工具性又凸显出来。“文革”后,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科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热潮,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人的作品备受欢迎。但是很快又出现了科幻到底是姓“文”还是姓“科”的争议,然后又被归入“精神污染”的行列,再度跌入低谷。经过90年代《科幻世界》的艰辛耕耘,新一代科幻作家的默默蓄力,到了新世纪,科幻重回人们的视线。这时的中国科幻,已经脱胎换骨,真正开始找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发力点,自己的意义所在。

科幻的力量在哪里,人民为什么需要科幻呢?其实人一直喜欢幻想,所以有神话、宗教、文学。但是人又不满足于幻想,渴望真实。人越来越理智成熟,从前的幻想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所以人一直在寻找幻想的新形式。在今天,这种新的幻想形态已经卓然成形,那就是科幻。从前人信神,现在人信科学,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能给人提供安慰和希望,但科学的安慰和希望比从前的神更加真实可信,从这个意义上,科学不但是现代的神,而且比旧神更加威力强大。科幻就是科学神话的最佳载体,或者说是旧神话与新科学的合体,将会越来越成为人类的主导性神话。
关于科幻的这个意义,刘慈欣早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SF教——论科幻小说对宇宙的描写》中就写到过。人是需要一些精神、安慰、寄托、超越的,这在科幻小说中可以体现为永生、穿越、精神上传、地球流浪……这听上去好像是又要回到旧神话的老路,其实是旧瓶里装了新酒,这就是科学。要知道科学在今天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神奇,比如超弦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有11个维度,电脑可以打败最优秀的人类棋手,全世界的很多实验室里科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开发长生不老药。一句话:科幻正在变得越来越现实,现实正在变得越来越科幻。在这个新的神话中,科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提供了信仰和希望的实证性基础。这也是刘慈欣和《流浪地球》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的核心密码。刘慈欣写的是硬科幻,他能把最疯狂的想象与最前沿的科学无缝对接,并用高密度的细节把这两大板块铆牢,这是他难以被别人复制的长项。
我很高兴中国科幻选择了刘慈欣,选择了更为坚硬的科幻类型,也很高兴中国观众在这个春节选择了《流浪地球》,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以想见:在这之后,一窝风跟进的从业人员会很多,他们未必能轻易超越刘慈欣已有的高度,但是如果能保留一些对科学和细节的尊重,我就很满意了。楼搭得越高,地基就越需要坚实。幻想飞得越远,支撑幻想的逻辑也需要越坚实。我们太需要希望了,也太需要科学了。
刘慈欣的“旧瓶子”里,其实装了很多新酒
2007年中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期间,在女诗人翟永明开办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著名科学史家江晓原教授之间有一场十分精彩的论辩。刘慈欣的旗帜很鲜明:“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全世界敢这样直接亮出底牌的人不多,在中国就更少。刘慈欣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可否运用某种芯片技术来控制人的思想,从而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面对灾难。江晓原则认为脑袋中植入芯片,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会摧毁人的自由意志,带来人性的泯灭。所以科学不是万能的,不是至高无上的,更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
其实类似的论辩在中国早就有了。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园作“人生观”的演讲,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而科学是客观的、分析的,所以无论科学怎么发达,都无法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此论一出,立刻遭到丁文江、陈独秀等人的迎头痛击,想那正是高举“赛先生”的时代,怎容得所谓“玄学鬼”的胡言乱语?从前看这段公案的时候,我对人单势弱的张君劢颇多同情,而对满口时代强势话语的丁、陈等人侧目以视。作为一个长期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人,我也本应毫不犹豫地站在江晓原教授的一边,对刘慈欣的科学主义倾向大加挞伐。但是,刘慈欣看似极端的“科学至上”和“唯技术主义”的旧瓶子里面,其实已经装了很多的新酒。
反讽式的情境,再融入一个对中国来说还未充分发展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其间的张力,我以为恰恰是刘慈欣小说爆发式流行背后不容忽视的重大动因。
刘慈欣所说的科学,是指一种更高级、更综合、更全面、更未来的科学。事实上,今日之科学,已非旧日之科学。近年来,随着脑科学、基因工程、进化心理学、量子物理学、宇宙学等尖端学科的进步,精神、人性、道德、信仰这些原先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艺术家的专属论题,正日益受到科学家的强烈关注。科学升级换代,带着强大的工具而来,会成为认识与解释世界的通用话语,乃至元话语吗?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传统的人文知识都在不断地分化消解,放弃全局性的视野,变得日益局部化。唯有科學,却开始呈现宏大叙事的渴望,或者说正在走向总体性。
我认为,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再度复兴,与这股强势的科学话语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刘慈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话语场域,启蒙式微之时,又恰逢科学强势之日,这种反讽式的情境,再融入一个对中国来说还未充分发展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其间的张力,我以为恰恰是刘慈欣小说爆发式流行背后不容忽视的重大动因。他站在一个难得的位置上,从科学的角度审视人文,用人文的形式诠释科学。他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主义,以惊人的冷静描写人类可能面临的空前的危机和灾难,提出了会被认为是极其残忍的各种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将理解他对人性的终极信念。
这是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年代,旧的信仰正在消亡,新的希望还在孕育之中。在所有人类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技术日益巨大的身影。科学既是问题的来源、问题的解释,也是问题的解决途径。这是一个吊诡的情境:人们越依赖科学、越相信科学,同时也就对科学越抱有敬畏和疑虑,也就越需要超越科学的视野,需要人文的关怀,但这种超越和关怀又越来越无法脱离科学而存在,依然必须与科学共生共存。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越来越需要科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