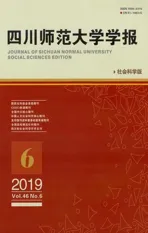人性、国家间道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2019-02-22罗华婷a戴永红
罗华婷a,戴永红
(四川大学 a.缅甸研究中心,b.南亚研究所 ,成都 610064)
当今世界早已成为“地球村”。地球村民之间能否和谐相处,可谓关涉每个地球人的重大问题。此间,大国关系具有决定性。但是,近些年来,尤其是特朗普当选以来,中美关系陷入危机。中美关系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中美,也是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针对此问题,习近平提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1)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而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要条件是建立国家间道义。所以,本文试图从国家间道义视角,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
一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现实主义国家关系及其困境
国家间是否能够产生道义?这在不同的理论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人性角度看,基于性私论,国家间道义则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但基于性善论,国家间道义是容易的。人性是什么,并无定论。中国和西方都不乏性善论,西方的性善论代表是康德。在西方现代转型和资本主义兴起后,谋求自己利益的自私被正当化了。经济人假设即人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成了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主流人性假设。但是,经济人只是假设,未必是真实。
在国家间关系中,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产生不同的理论。现实主义基于人性私,而理想主义则基于人性善,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就指出了这两种理论与对人性的假设直接相关。作为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作单纯的经济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理论鼻祖,摩根索明确指出了现实主义与人性的关系,“政治规律植根于人性”,“现实主义认为它最重要的观念——把利益确认为权力——是一个客观的范畴,是普遍有效的”;由于人性自私,所以,“追求权力既是国际政治的特殊因素,它和一切政治一样,也势必是强权政治学”。(3)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22、52页。结构现实主义代表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也认为,“国内政治是权威、管理和法律的领域,国际政治则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4)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大国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为霸主,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5)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因此,现实主义的各个流派都认定,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或曰强权政治。
按照摩根索所言,“一种政治理论必须经受理性与实践的双重检验”。(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17页。那么,现实主义能接受这双重检验吗?不能,它只能部分接受检验。如果完全依循现实主义,人类将面临重大的现实困境。因为每个国家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大国争夺霸权且欺辱小国,地球村便无法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无法建构。更糟糕的是,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一些国家尤其是大国掌握的毁灭能力迅速增强,人类很可能毁灭。冷兵器不可能毁灭人类,但如华尔兹所言,“核武器的绝对特性把有核世界与传统世界截然区别开来”(7)Kenneth N.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 1990, p.732.。而马克·W·赞奇则指出,“毁灭性也是国际结构的根本特征之一”。(8)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而目前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尤其值得警惕,人工智能失控,可能危及全人类。
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经济人假设跟当代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非常匹配。民族国家就是经济人,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具有明确的边界和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正是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式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经验基础。民族国家的弱点在于:民族国家犹如经济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国家间道义的空间,它很难摆脱“丛林法则”。
任何理论都只能有限地反映真实的世界,经济人假设、民族国家理论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人们一旦认为某个事件是什么状态,就很可能甚至只能按照该状态思考和行为。因而,一个局部真实的理论如果被视作唯一可能,它就会遮蔽其他可能,使人们沿着该理论思考和行为。如果人们认为人只能是经济人,就会把自私自利视作天经地义,沿着经济人思考和行为,因而无法避免“丛林法则”。其实,在国家层面,民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建构起来的,历史上还有诸多国家形式。既然如此,它就未必完全符合真实的世界。民族国家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最为匹配,但二者不能解释国家间道义的事实存在,犹如经济人假设不能解释道德或利他行为的事实存在。既然民族国家不能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我们就应该有勇气也有能力去修正现实主义理论。这种修正一旦形成一种新的理念,就有可能指引各国调整自己的思考和行为,以应对全球问题。
当今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间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应对了当代世界真实存在的重大问题。“高技术+全球化”所构成的“地球村”,已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危机与风险中独善其身。当代世界的许多风险如气候、环境、经济、犯罪、洗钱、核武器、生化武器、人工智能等都不能再以国家角度而必须以人类角度来考量。如果上述风险失控,整个人类都可能遭受重大甚至毁灭性损害。从积极角度讲,全球财富的增加应该但未必会实现共富;从消极角度讲,全球风险的增加不应该但却肯定会导致共损。因此,从积极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实现;从消极角度看,不论某些国家、组织和个人如何刻意筹谋,当爆发全球风险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成立。因此,为了规避共同的重大甚至毁灭性风险,人类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智,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培育国家间道义。
无论现实主义如何振振有词,它都无法解决人类面对的困境,因此,必须超越现实主义。
二 国家间道义超越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及历史案例
如何超越现实主义?有理论和经验两种可能路径。从理论上看,现实主义基于经济人假设,但经济人并未概括人性的全部真实情况,而只是假定的情况。即便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也承认,“真正的人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的复合体”。(9)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30页。这意味着,人性是复杂的,我们既可以在人性中发现自私(甚至邪恶),也可以发现无私与善良。正是人性的复杂性,使得人类具有各种可能性,而不会完全局限于现实主义。这为国家间道义提供了人性基础和可能。所以,如果在人性中注入道德因素,国家间道义就是可能的。从经验上看,历史上不乏国家间的道义行为。其实,从经验上来论证国家间道义的可能性,更有说服力,因为凡是经验存在的,就一定是理念或逻辑可能的;但理论或逻辑可能的,经验中未必存在。所以,下文准备通过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案例来论证国家间道义的可能性。
(一)国家间服从天下利益的案例
西周封建后,诸侯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但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还有独立的外交权,诸侯可以相互订立盟约;还拥有军队,有独立的军事权,“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10)贾公彦《周礼注疏·夏官》,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0页。周王室对诸侯国的制约本来就比较薄弱,加之春秋以降王室衰微,有些诸侯国日益壮大,王室对诸侯国尤其是大国的制约就更加薄弱了。但是,有些诸侯国却愿意超越自己的国家利益,服从天下利益,维护天下秩序。这些诸侯国其实已经不只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很难解释的。下面以齐桓公和晋文公为例说明。
齐桓公执政期间,他努力维护天下秩序。因公元前681年的北杏之会,宋国违背了盟约。于是,公元前680年(鲁庄公十四年),齐国联合陈、曹二国伐宋。在伐宋时,齐国“请师于周”。最终,齐国等与宋国媾和。其实,齐国等的力量远比宋国强,为什么还要请师于周呢?为了表示对周王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对天下秩序的维护。杜预注曰:“齐欲崇天子,故请师,假王命以示大顺”(1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公十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1页。,说的就是此意。接下来,齐国率领诸侯,抵抗楚国,达成召陵之盟,维护天下秩序(参见下文)。此间,虽齐国也有利益,但它绝非只为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天下利益与秩序,因为与楚国对抗,是要冒巨大风险的。此外,齐桓公多次组织诸侯会盟,商讨如何维护天下秩序。所以,孔子、孟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都很高。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2)邢昺《论语注疏·宪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1、2512页。而孟子则认为齐桓公为五霸之首,还专门记载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的盟辞(13)孙奭《孟子注疏·告子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59页。。这一盟辞既体现了齐桓公超越国家利益的天下胸怀,也体现了当时诸侯对民生、国家间互助等的关注,还体现了诸侯国的契约精神。
晋文公即位后,进行了勤王之役,即接纳、保卫逃难的周襄王。(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20页。此间虽然也有晋国的利益,但晋国也服从了天下利益。同样,晋文公抵抗楚国,也要冒巨大风险。例如,晋文公去世后的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晋国就大败于楚国。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齐桓晋文对天下利益的服从。如果两位霸主不主动出头担当天下责任,以两国的国力,完全可以自扫门前雪。虽然两位霸主也有自己的私利,但毕竟出头维护天下秩序,尤其是对抗楚国,是要冒巨大风险的。所以,可以说,两位霸主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服从于天下利益。当今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这样敢于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家。
(二)国家间和平协调冲突的案例
春秋时期,战争频仍,但诸侯国也尝试用会盟这种和平手段协调冲突。据统计,《左传》一共记载了745次战争,406次会盟。(15)邓曦泽《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3-573页。其中,有两次重要的会盟即召陵之盟和弭兵大会,突出地体现了先秦时期国家间协调冲突的实践与智慧。
春秋初期,被视作蛮夷的楚国日益强大,数度入侵中国(中原诸侯国)。公元前656年,为了抵御楚国入侵,齐桓公联合八国诸侯伐楚,进入楚国地界。楚国派使者质问诸侯联军为何进入楚国。管仲与楚使进行了言辞交锋,楚使承认了管仲的部分指控。接下来,楚国国君派大夫屈完跟诸侯谈判。齐桓公首先表达了和好的愿望,然后又以武力为后盾,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的回应则是有软有硬,“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于是,诸侯与楚国在昭陵结盟,互不侵犯。(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2-1793页。
晋文公去世后,晋楚进入拉锯争霸阶段,战争给交战各方造成大量的人财物力伤害。鲁国大夫众仲说:“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25页晋国韩宣子也指出:“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95页。连好战的楚国国君也认为:“止戈为武。”(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82页。反战观念使得各诸侯国可以坐下来谈判。在宋国大夫向戌的发起和联络下,晋楚等诸侯国进行了弭兵大会(公元前546年)。在谈判中,虽然晋楚两大诸侯国发生了许多分歧,但最终晋国对楚国作了让步,达成停战协议。弭兵大会后,截止春秋末,天下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召陵之盟和弭兵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大国也有妥协、让步和理性精神,也能以谈判的方式实现和平,因而,“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走出来的。
(三)国家间互助的案例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经常相互帮助(20)甄尽忠《先秦儒家社会救助思想析论》《先秦时期国家救助思想述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王星光《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王文涛《先秦至南北朝慈善救助的特点与发展》,《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范新可《先秦儒家典籍所见民间互助活动及其思想》,《华夏文化》2012年第3期。,这也是国家间道义的表现。西周封建之初,历任天子都很重视诸侯对王室的拱卫和诸侯之间的互助。王子朝的使者曾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2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14页。这是从祖宗法制层面规定了诸侯国之间应该相互救助。
案例2:晋国遇到了饥荒,要向秦国购米。当时,晋国内乱,晋惠公篡位,丧失民心,有人主张秦国借此机会攻打晋国,但秦穆公却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2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03页。不过,晋国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乏道义。次年(公元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求助,晋国居然不卖粮给秦国,以致于晋国内部对晋国忘恩负义的行为深表愤慨。第三年(公元前645年),秦国为报复晋国之不义,伐晋。由于秦国正义,故士气高涨;晋国不义,故士气不振,导致晋军数次战败,晋侯也被活捉。这个案例有三点典型意义。第一,秦国与晋国是两个相邻的大国,具有很强的竞争关系,但秦国仍有宽宏胸怀。第二,晋国的不义从反面表明,诸侯国互助是应然价值标准,如果违反了,很可能被惩罚。第三,尤其是,这个案例表明了一个国家可以选择道义,也可以选择不义。虽然道义不是必然的,至少是可能的。这意味着,道义具有人性基础,进而道义是可培育的。如果选择道义的行为者(包括国家、个体等)增多,就会形成越来越道义的环境,激励更多行为者选择道义,形成正向循环与加强,即螺旋式上升。正是这种人性可能和行为选择,使得人的行为不同于动物行为,具有超越价值。
案例3:诸侯达成的契约也明确规定和强调国家间互助(参见下文)。
上述案例均表明,国家间道义在事实上是经常出现的。
(四)国家间达成契约的案例
春秋时期,诸侯国举行了很多会盟,许多会盟的盟辞没有被记录和流传下来。但是,从流传下来的盟辞看,诸侯国之间有很强的道义关怀。并且有盟约与无盟约相比,前者对诸侯国行为有较为不错的约束力,诸侯国经常会执行盟约。这表明,中国并不乏契约精神(不过,秦汉以后,因中央集权,这种契约精神有所衰退)。(24)冯川《儒家思想的社会契约性质》,《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诸山《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孔子研究》2008年第2期;叶修成《论先秦“誓”体及其契约精神》,《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陈尚仁《盟约与结义——从春秋与〈三国〉谈起》,《浙江学刊》2003年第1期;王公山、马玉红《先秦盟誓的契约属性及其文化意蕴》,《学术界》2008年第6期;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樊鹤平《中国传统诚信思想探析》,《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3期。而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将这种契约精神进行现代转换与提升。
案例1:亳之盟。公元前562年,诸侯在亳这个地方结盟,其盟辞被记录下来了。其言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2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50页。从这个盟辞可知,诸侯国之间的道义关怀是多方面的,包括(遇到灾害时)不要囤积粮食(毋蕴年),不要垄断利益,不要庇护罪人,不要收留坏人,救济灾荒,平息祸乱,统一好恶(即建立统一价值标准和规则),辅助王室。
案例2:葵丘之盟。这是齐桓公主持的一场重要会盟。《左传》没有记载盟辞,但《孟子》对盟辞有所记载。(26)孙奭《孟子注疏·告子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59页。这次会盟不但表明诸侯国能达成契约,且契约关注的主题广泛。例如,第四条是建立权力运行规则。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规则太粗疏了,但有总比没有好,可谓巨大进步;第五条是对经济交往的规定,体现了“正德利用厚生”(2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46页。思想。
案例3:弭兵大会(参见上文)。这次会盟虽然没有留下具体的盟辞,但成果是很显著的,如晋楚双方停战,两诸侯国之间相互朝见。
[79][81] 郑先武:《区域间治理模式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115-116、116-118页。
当然,上述案例不能表明国家间道义是必然的。如此选择性地讨论国家间道义的案例及其蕴含的可能性,是要针对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遵循的是霍布斯意义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只有利益交换与争斗,没有道义存在的空间。但通过历史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国家间道义是可能的。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以及任何组织内部(包括家庭),都既存在现实主义因素,也存在道义因素。所以,无论现实主义还是道义,都不是单一存在,也不是必然的。至于国家之间以及任意行为者之间的交往究竟会导向现实主义还是道义,并无必然性,而是取决于行为者的选择。当然,影响行为者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世界、国家和各种组织,都应该积极培育促使行为者选择道义的因素。这不是本文的话题,不予讨论。
三 中国古代国家间道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借鉴作用
培育国家间道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多方面的资源和努力。由于人类行为深受历史的影响,所以,培育国家间道义,需要发掘历史中的有益资源。在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的国家间道义资源非常丰富。(28)余丽、李涛《中国国家间道义思想探本溯源——基于先秦诸子国家间道义思想的对比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阎学通、张旗编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3页。下面,本文将以中华文明为例,从理念改造、策略改进和措施保障三个方面探讨国家间道义资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作用。
(一)理念改造
对现代世界秩序进行道义理念改造的最重要思想资源为天下观念。
“天下”一词在先秦典籍中非常常见。本文无法对天下观念进行专题讨论(29)李扬帆《“天下”观念考》,《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而只需在本文视角下明白:天下观念的最重要含义是天下一家,天下利益是最高利益。这意味着两点,第一,普天之下,没有外人、敌人和陌生人,一切人都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或某个角色,都为天下共同利益而奋斗。这显然有助于处理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第二,诸侯国及包括个人在内的各类主体都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即不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而要服从天下利益。就历史实践看,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多民族错综复杂的交往之中,但它处理民族关系是比较成功的。许多曾与主体民族汉族相敌对的民族,如匈奴、鲜卑、西夏人、辽人、金人、蒙古族、满族等,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典型案例是,在汉朝对匈奴取得胜利后,对于没有逃跑的那部分匈奴人,既没有采取赶走的政策,更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而是采取了归化政策。同样,唐朝对北方诸民族也采取了同类政策。如果没有天下一家观念的影响,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总体上,中华民族呈现不断融合和扩大的趋势。可以比较的是,新加坡独立,并非自愿,而是在1965年被马来西亚联邦逐出的。这种情况在中华文明的天下一家观念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为了不至于美化中国传统文化,还得指出,中国传统国家间道义资源与现代世界国家间理论的改造是双向的,二者是互补的。现代国家间理论的优点是平等,缺点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天下观念的优点是不预设外人、敌人和陌生人,整个世界都可以纳入一个整体中,天下利益是最高利益,缺点是它是等级制的,即有中心、边缘的分别,或亲疏远近的区别。在周代,天下一家,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便是等级制的。所以当代世界塑造天下观念,需要剔除等级观念。那么,天下观念能否剔除等级因素呢?能。从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到今天的民族平等,我国已经实现了中华体系下的民族平等。这意味着,平等的天下秩序是可塑造和可推广的。
(二)策略改进
王道是重要的国家间道义资源,虽然它的适用范围不限于国家间,几乎适用于一切交往领域。在天下层次,如果没有王道,天下一家、天下和谐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王道可以视作策略或手段,而天下可视作目的。当然,将王道视作理念还是策略,要看具体语境,看它跟什么概念或理论构成关系。相对于天下一家,王道是策略,因为它更具体。
对王道最早的专题论述是《荀子·王霸》。在此文中,荀子区分了三种行为策略或方式:王道、霸道、亡道。荀子先说:“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30)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2页。这个“道”,跟《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3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1页。及日常所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是同一含义。王道,就是王的方式;霸道,就是霸的方式。所以,在策略层面理解王道,是妥当的。接下来,荀子分别论述了王道、霸道、亡道(3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2-203页。(引文从略)。大体可以说,西方的现实主义相当于霸道,理想主义相当于王道。但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主流观念是尊王贱霸的(33)参见:赵峰《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朱陈义利王霸之辩解读》,《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而西方主流却是现实主义。正是在推崇王道这一主流观念的驱动下,中国古代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有不少可称道的举措,如上文所举之例。在现代眼光看来,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也非尽善尽美,但从历史角度看,古代中国能日益兼容并蓄各个民族、多种文化,使中华民族不断扩大,成为唯一延续至今且不断壮大的古代文明。如果没有相对先进的理念和策略支持,很难相信中华文明会保持如此长久的领先和强大。
由于古代崇尚王道(策略),导致王道对君王、政府等构成一定程度的道义约束,这种约束又体现为行为方式、路径的选择。推崇王道,就必须少做自私自利、背信弃义的行为,多做符合公义、遵守信用的行为。后世儒家特别推崇成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天下(3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89页。之案例表明,王道事实上存在过,因而是可能的,可行的。但是,不要把王道理解为只讲道义不讲功利。其实,亡道是不讲道义和规则地追求非常狭隘的短期最大利益,霸道通过讲规则、重信用而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王道则是通过讲道义、利他人而谋求自己的长期的最大利益。从经济角度讲,王道特别看重共赢。我让你好,你也让我好。例如,在国内治理上,如孟子所言仁政,老百姓的生产能力增强,日子过好了,才能更好地纳税,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良性互动与日益扩大。商汤与周文王的具体事迹不可详考,但汉以后的事迹是比较清楚的。以对非汉族的接纳和融合为例,就短期看,非汉族来到汉族土地上,要分占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源,对汉族来说,短期是不利的,但长期看,却实现了汉族及整个中华民族的不断扩大和壮大。虽然不可否认中国的扩大也有征伐行为,但仅靠征伐,是不能解释汉族扩大以及多民族相处的总体和平、稳定与持续。当然,王道策略可以有许多具体表现,非本文所能穷尽。因此,旅居美国、深谙中美文化的著名学者汪荣祖先生就主张中国崛起当以王道取代美国式霸道。(35)汪荣祖、管永前《以王道取代霸道:中国崛起在世界上的角色——汪荣祖教授访谈录》,《国际汉学》2017年第3期。
(三)措施保障
除了理念和策略,国家间道义还需要体现在措施上。但措施恰恰是很难讨论的,一则因为它很具体、繁复,二则需要考虑具体应用场景,很难凭空拟定。这里准备从中国古代国家间交往中提取出几条可古为今用的措施。
第一,在经济上不以等价交换为刚性原则,适度让利。此点主要适用于大国和强国。加尔通说:“帝国的定义:是一个跨国界性、文化合法化、中心-边缘处于不平等交换状态的结构”(36)〔挪威〕约翰·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阮岳湘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而帝国占有交换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当今的美国尚不属于王道,只能算是霸道。在古代,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以及汉族政权与非汉族的交往(不包括民间交易),在经济上总体是吃亏或少利的。外国来朝贡,在经济上,中国所获甚少,付出甚多,但中国获得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情感等认同,这有助于边疆稳定。同时,长久以往,有助于中国的扩大与加强。
第二,援助,尤其是无偿援助。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说积累了许多经验。虽然当代世界也有国际援助,但是西方国家的援助常常有诸多附加条件,甚至很苛刻。而中国主张把经济援助与政治问题分开来,所以有许多无偿援助。无偿援助在经济上是最不划算的,但国家是由人构成的,也是由人决策的,它作为行为主体,也有情感,所以,无偿援助很可能产生超乎预期的政治、文化和情感收益,从而有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中国获得许多非洲国家的支持,与中国的无偿援助是分不开的。
第三,建立国际互助法。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援助,是作为义务被成文法(即会盟的盟辞)所规定的,虽然有时某些诸侯国执行得并不好。而在当代世界,国际援助仅仅是一种自愿。而且,一国对另一国的援助,国际组织对某国的援助,都介入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因而缺乏超越性。所以,我们今人完全可以向春秋时代学习,建立超越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义务性的国际互助法。援助越是无条件和无偿的,越有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建立国际互助基金。同国际互助法一样,国际互助基金将援助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区分开来,更有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融合。同时,鉴于第一点,此基金还可以进行国际补贴(与国内的转移支付、扶贫基金具有相似功能),即如果某穷国需要购买某些重要商品,但支付能力不足,该基金可以为它承担一部分。
或许有人会质疑上述措施有些理想主义。若从现实主义角度看,的确如此。但是,本文的立意就是要校正现实主义的偏颇,就是要赋予受经济人假设主导的国家间关系以道义因素。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自私的基因》中认为,因为人性是自私的,所以我们才要在人性中灌注爱和无私。他说:“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希望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的社会,那你就不能指望从生物的本性获得什么助益。让我们设法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吧!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我们自私的基因居心何在。因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去打乱它们的计划,而这是其他物种从来未能希望做到的。”(37)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通过比较中国春秋时期和古希腊(后者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代表文本),大体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国家间道义思想与实践资源要比古希腊多。古希腊的城邦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国先秦的高于诸侯或城邦的王室或“天下”观念,城邦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纽带。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可以看出,希腊城邦之间有同盟,小邦分别依附于大邦雅典和斯巴达,形成集团。这跟春秋时期小国依附于晋国、楚国而形成两大集团相当。但是,希腊城邦之间的互助行为非常有限,远不如春秋诸侯国之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没有记载城邦要和睦互助的制度性条文。可以说,中国的天下观念、王道策略及一些具体的道义措施,都非常有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天下一家”观念是古代生活的产物,具有宗法观念,这是需要剔除的。但是,“天下一家”观念中的国家间道义思想,却非常值得继承、发掘和发扬。由于交通、通讯等条件的落后,春秋时期要想实现国家间互助或进行一次会盟,成本远比今天高。既然彼时的国家间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国家间道义,当代人类没有理由冒着全球整体性风险而囿于民族国家利益,完全漠视国家间道义的事实存在与培养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