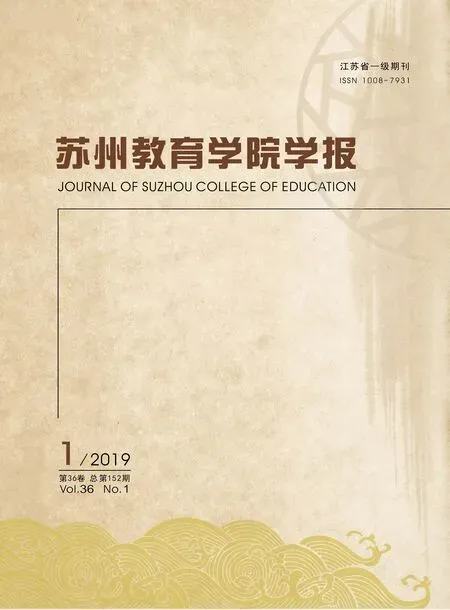陶渊明《答庞参军》二首系年辨正
2019-02-22刘奕
刘 奕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陶渊明《答庞参军》有四言、五言各一首,先引录于下:
答庞参军一首并序
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寻]阳见赠。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云胡以亲?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欢心孔洽,栋宇惟邻。伊余怀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一日不见,如何不思!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岂忘宴安,王事靡宁。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与江中。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1]26-27
答庞参军一首并序
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欵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唯旧,弱毫(夕)[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1]115
两首诗合起来看,五言一首在前,写于某个春天。据四言诗序“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以及诗中“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之句,庞是卫将军的参军,春天分别是因为他要去荆州的治所江陵。再据“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四句,可知大概当年冬天,庞参军奉使去京城,经过浔阳,陶公乃写了四言一首。
二诗是陶公晚年之作,五言诗序云:“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已说得很明白。那么两首诗具体作于哪年,旧有二说:清代陶澍认为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逯钦立则主张作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后人笺注陶诗,非陶即逯。今案:二说皆非。细核历史记载,这两首诗应写于元嘉二年(425)。
一
我们先引用陶澍、逯钦立两位学者之说,再一一辨正。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云:
时卫军将军王弘镇浔阳,宋文帝方为宜都王,以荆州刺史镇江陵,参军奉弘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有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称大藩也。四言五言,疑皆营阳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参军奉使之时,先赋诗为别,先生作此以答。四言则参军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诗以赠也。盖王弘兄弟王昙首、王华皆为宜都参佐,后皆以定策功贵显。营阳之废,王弘亦至建康与谋。时众欲立豫州,而徐羡之以宜都有符瑞,宜承大统。此必王弘兄弟先使参军往来京都,与徐、傅等深布诚款,故江陵符瑞得闻于中朝。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载耳。其后文帝讨徐、傅、谢三人之罪,而弘独蒙显宠,良有故矣。观四言末章云:“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此必先生阴察参军使都,当有异图,故以慎终保躬勖之。且序称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诗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迹、诇国之情具见,盖诗而史矣。此诗当作于营阳王景平元年。[2]102
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云:
而诗云: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岂忘晏安,王事靡宁云云,知庞为卫军,乃事荆州刺史。案:宋初以卫军为荆州者,仅谢晦一人,又《宋书·文帝纪》云:元嘉元年八月癸卯,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进号卫将军,知庞氏此春乃以抚军参军,赴江陵之任,渊明以五言诗送别。至冬则以卫军参军,衔命使都,渊明又有四言之赠遗也。……陶《考》谓二诗作于景平元年,时卫军将军王弘镇浔阳,宋文帝方为宜都王,以荆州刺史镇江陵。参军奉弘命使江陵,又奉宜都王之命使都,故曰:大藩有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称大藩也。又谓:乃王弘兄弟与徐傅等密谋废立之事,故使参军往来京都。钦立案:此说牵强,不足据。四言诗序,明言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云云,不得曲为之说。且谢晦镇江陵,已进封建平郡公,与大藩云者亦无不合。[3]
综合陶诗与陶、逯二氏之说,可知诗歌中的庞参军虽是个小人物,却牵涉到了政局的巨变之中。诗句看似平静,其实是时代风暴中暂时的安宁。让我们根据史书的记载,复原历史的场景,诗歌的写作时间自然就清楚了。
先选取一个时间节点:宋少帝景平二年(424)。该年八月文帝登基,改元元嘉,所以下半年的年号是元嘉元年。这一年中发生的大事是辅政大臣傅亮、徐羡之、谢晦等联络江州刺史王弘、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发动政变,废弑少帝刘义符及其二弟庐陵王刘义真,迎立刘裕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是为文帝。
回溯到永初三年(422)五月,武帝刘裕病笃,召太子义符而告诫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4]59檀道济是此时朝中第一名将,本来是负责建康城戍卫的护军将军,刘裕大概还是担心十七岁的太子驾驭不了他,也不妨有拱卫京师和牵制中枢的考虑,在病危时命檀道济“出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4]1342,去了广陵。而在本年正月癸丑,刘裕已做了更重要的人事安排:“以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刺史如故。抚军将军、江州刺史王弘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中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4]58少帝即位后的六月壬申,又任命傅亮为中书监。这时朝廷的格局如下:徐羡之负责尚书省、京畿扬州,等于宰相,傅亮负责中书省,等于副相。谢晦为领军将军,掌管禁卫军,宫廷护卫即由其负责。三人为辅政大臣[4]63。刘裕认为徐、傅二人出身低微,应该不会有异志,而谢晦数从征伐,长于谋略机变,而且是创建北府军的陈郡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未必可靠,所以建议少帝加以防范,让其离开中央。十七岁的少年天子此时并未亲政,对此显然无能为力。
王弘是王导曾孙,司徒王珣之子,刘裕举兵讨伐桓玄以来,一直备受亲信。自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起,王弘“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4]1313。此后到元嘉三年(426)征召入京任职为止,一直在江州刺史任上。这期间,宋武帝永初三年,王弘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元嘉元年,又进号车骑大将军[4]1313-1314。赴任江陵之前的庞参军,在浔阳时担任的是王弘的僚属。而更重要的荆州刺史,是少帝的三弟刘义隆。他在晋宋之际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并在永初元年(420),受封宜都王,进号镇西将军,时年十四岁[4]71。这就是少帝被弑前的内外格局。
完整的事件有两个阶段,一是景平二年直接的废立之事,二是事变各方的角力与最后摊牌,以元嘉三年(426)宋文帝诛杀顾命三大臣告终。第一阶段的经过大致如下:景平二年(424)春二月癸巳(初一),“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4]63。刘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素与谢晦等人不睦。徐羡之他们考虑到废立之后,义真为刘裕次子,法统上是新帝的最佳人选,“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4]1635-1636。说明最晚到该年正月,三大臣已经下定废立的决心,并有了行动计划。到了五月,徐、傅“讽王弘、檀道济求赴国讣。弘等来朝”[4]66,乙酉(廿五日)这天,一边假皇太后之令下了废帝为营阳王的诏书,另一边,事先安排好内应后,“道济、谢晦领兵居前,羡之等随后”[4]66,直入内廷,收玺绶,将少帝送回东宫,再迁去吴郡。到了六月癸丑(廿四日),三大臣再分别派人杀害了义符、义真兄弟俩[4]66、1638①案:《义真传》所记被杀之日为六月癸未,校勘记引《通鉴考异》指出,该年六月无癸未,应是癸丑之讹。其说是也。。七月,傅亮迎义隆于江陵,“甲戌(十五日),发江陵。八月丙申(初八日),车驾至京城。丁酉(初九日),谒初宁陵,还于中堂即皇帝位”[4]72,“大赦天下,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4]73。
不妨补充说明一下废帝的原因。从废帝的诏书看,少帝的罪过是骄奢淫逸,嬉游无度。裴子野在《宋略》中说,这是“高祖宠树”,缺少教育,“恣其嗜欲,群小兢进”,“居中择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5]395-396造成的。一个从小缺少管教的人,进入青春期,还一下子当了皇帝,其狂恣可想而知。但历代帝王,骄奢淫逸、嬉游无度不正是常态吗?其时权力基本在顾命三大臣手中,少帝除了玩乐,并没有更大的恶行,而且刘裕遗命徐、傅、谢辅政,正是要他们制约、引导少帝,怎么老师没当几天就换学生呢?所以王夫之对三人深致讥讽:
营阳王狎群小而耽嬉游,诚不可以君天下,然其立踰年耳,淫昵之党未固,狂荡之恶未宣,武帝托大臣以辅弼之任,夫岂不望其捡柙而规正之?乃范泰谏而羡之、亮、晦寂无一言。王诚终不可诲矣,顾命大臣苟尽忠夹辅以不底于大恶,亦未遽有必亡之势也。恶有甫受遗诏以辅之,旋相与密谋而遽欲弒之,抑取无过之庐陵而先凌蔑之。至于弒逆已成,乃左顾右眄,迎立宜都。处心如此,诚不可以人理测者。视枭獍之行如儿戏,视先君之子如孤豚,呜呼!至此极矣。[6]416
王夫之的切责极有道理,三大臣何至失心病狂至此。想来史书所载只是废立的托辞,实际恐怕是少帝成人在即,亲政有日,三臣贪恋权位,担心目前的权力格局发生不利于己的大变动,才妄行废立。魏晋以来,权臣欺负孤儿寡母已成惯例,刘裕自己又何尝不如是,政治生态败坏已久,才培养出徐、傅、谢一辈庸妄之徒。船山又云江东士人习于“党同幸免,廉耻隳,志趋下,国之无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风俗之陵夷坏之也”[6]417。论政治人才与政治生态的关系,以片言而得其要。
第二阶段:文帝即位后,其自己的阵营就开始了与前顾命大臣的权力斗争。张金龙在《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一书中指出:“宋文帝及其亲信很可能一开始就产生了除掉徐羡之等权臣的念头。惟其如此,宋文帝才能独掌大权,不再重蹈其兄被废杀的覆辙。也只有这样,宋文帝亲信琅琊王氏成员的政治利益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7]57此外,“消灭前顾命宰辅以彰显宋文帝对其行废弑之举的严惩,而他本人则可以免除承担篡夺皇位的责任。”[7]60双方进退拉锯的详情,张氏书中有详细考述,可参看,此处只记叙其关节之处,而不一一缕述[7]43-60。文帝即位之初,三大臣方面的人事布局是诸人皆进位、进号,徐羡之、傅亮继续中枢秉政,谢晦则出任荆州刺史,进号卫将军[4]73,且“京师精甲,多割赐之”[5]408。“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4]1476,是南朝除京畿扬州之外的第一雄镇,谢晦带着京师禁卫军的精锐出镇荆州,其意自然是要与中央的徐、傅呼应,继续维持内外军政大权。宋文帝与心腹王华、王昙首、到彦之等人谋划,逐渐掌握朝中军政之权,又分化拉拢了檀道济和王弘诸人。经过一年多紧密的准备,就向对方摊牌了。裴子野《宋略》记载:“(元嘉)三年(426)春正月丙寅(十六日),诏罪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三人,以废立杀戮事。”[5]411徐、傅在京,束手成擒。对谢晦,则“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上亲率六师西征”[4]74,至二月己卯(三十日),即擒获谢晦。至此,文帝基本完成了对政局的掌控。
二
梳理了事件的全过程之后,再看分别审察陶澍和逯钦立的二说得失。陶澍之说核心要点有二:王弘、刘义隆及其亲信在一开始就积极参与谋划了政变;而庞参军正是作为使者在浔阳、江陵、建康之间往来奔走。首先,这个“使者说”是很令人质疑的。陶渊明五言诗序说:“欵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且为别后相思之资。”[1]115诗则云:“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1]115短暂出使,陶公不会说您多珍重,再会不知何日这样的话,这显然是庞参军转赴异地为官,即将长别时的口吻。如果庞仅仅是奉使从浔阳到江陵,两地相隔不远,使毕即返,陶诗这样珍重惜别,未免过分小题大做,把写诗当成儿戏,太不合乎诗中情境。
《宋书·百官志》载,“卫将军”的军衔只能授予一个人[4]1224,景平元年(423),卫将军是王弘,陶澍把诗歌系年在这一年,那卫军参军就只能是王弘的僚属。这样的话,处处都让人觉得扞格难通。江陵到浔阳,路途不算远,王弘春天遣使江陵,自然应该很快回浔阳覆命,将江陵那边的态度与答复汇报主将,以便进一步的策划。怎么可能一直在江陵呆到冬天,转而作为刘义隆的使者出使建康呢?南朝时荆州是仅次于扬州的大州,州中官吏僚属向有数千人之多,刘义隆连一个可用的人都没有,非要留住王弘的参军大半年时间,然后为自己出使京师?古来没有这样的孤家寡人能登帝位者。再有,参与废立之事的一定是亲信心腹之人,庞参军能同时为王弘和刘义隆器重和任用,参与了篡位密谋,建立了卓著功勋,他一定有过人的才能,堪称人杰。这样的人物,在宋文帝刘义隆登基后,厚酬其功,高擢其位,大用特用才对,怎么反而重用的心腹亲信?但他并不是刘义隆的部下,何以反而声光黯淡,功名不显?这些都是很难解释的。
更重要的是,王弘与刘义隆方面,是否是政变的主谋,这在史书中找不到一点根据,反面的记载倒有很多。先看王弘与政变的关系。《宋书·王弘传》的记载是:“徐羡之等以废弒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4]1314这里的“非首谋”是史家为尊者讳的曲笔还是如实记载,可以得到证明。前已述及,政变的准备工作早在景平二年二月就开始了,《王弘传》载,五月,“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4]1314,政变紧接着就发生了。《宋书·少帝本纪》以及《建康实录》的记载与此相同,都是徐羡之等召王弘、檀道济入朝的,而非后两人主动请求入朝的,显然三大臣才是事件的策划者。《檀道济》传的记载更加清楚:
徐羡之将废庐陵王义真,以告道济,道济意不同,屡陈不可,不见纳。羡之等谋欲废立,讽道济入朝,既至,以谋告之。[4]1343
檀道济既不同意早先废庐陵王之举,政变的事,也是五月入朝之后才知道的。政变中,檀道济的重要性要高于王弘。不但因为檀是猛将,更因为他和兄长檀韶此前一直是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也就是禁卫军首领,在禁卫军中威望自然非常高。所以政变那天,檀道济、谢晦领兵在前,此乃二人分别是禁卫军的前首领和现首领之故。檀道济尚且入朝才与闻政变的消息,王弘又何能例外呢?
刘义隆方面又是否前知废立之事?应是不知情。《宋书·王华传》载:
太祖入奉大统,以少帝见害,疑不敢下。华建议曰:“羡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每生情多,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万无所虑。”太祖从之,留华总后任。[4]1676
《南史·到彦之传》云:
及文帝入奉大统,以徐羡之等新有簒虐,惧,欲使彦之领兵前驱。[8]又《宋书·王昙首传》载云:
太祖入奉大统,上及议者皆疑不敢下,昙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固劝,上犹未许。昙首又固陈,并言天人符应,上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带者数旬。[4]1679
以上记载完全一致,看不出有史臣因为涂饰篡改史实而常见的彼此不一的现象。根据记载,刘义隆听到两个哥哥被杀的消息,既忧虑更害怕,甚至不敢去建康即位。经过了他的三个心腹,也是荆州的三个最高级官员王华、王昙首和到彦之的再三劝告之后,勉强答应下来。不过,一开始他打算派到彦之率兵先行,即防备偷袭之意。后来东下的一路上,他命令属下荆州的文武官员和士卒严密护卫自己,不允许京城派来迎接的人员过分接近。甚至让中兵参军朱容子作贴身保护。刘义隆如果事先与三大臣密谋篡立,他该急不可耐东下才是,担惊受怕到这种地步,不是装得出来的。从宋文帝一生行事看,他也不是个会演戏的人。至于王华、王昙首,也没有可能事先参与谋划。第一,毕竟此时义隆已经十七岁,似乎没有必要瞒着他谋划这种惊天之事。第二,如王夫之所言:“当是时,华、昙首之流,年尚少,名位卑,不足以弹压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其效。”[6]416徐羡之等宰辅大臣没有理由绕开刘义隆单独与位望都还不够高的王华等人单独接洽。
再有一点,从政变发展进程上看不出荆州方面参与废立的可能性。前已述及,废少帝在五月二十五日,杀少帝和义真是在六月二十四日,迎立义隆则在七月十五日。从废帝到迎立,中间有四十多天的空白期。张金龙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指出:“表明刘宋朝廷决策集团并不是在宋少帝被废后立即做出了迎立刘义隆继任的决定,而是为此进行了长达一个月时间的商议,虽然现存文献并无蛛丝马迹可寻,但当时必定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可以确定,决策者在作出了迎立刘义隆的决定后,便将被黜为营阳王的少帝刘义符杀害。”[7]47张说极是。如果双方早就合谋了,何须拖延这么久,马上迎立宋文帝才对。
至于陶澍所推测的“时众欲立豫州,而徐羡之以宜都有符瑞,宜承大统。此必王弘兄弟先使参军往来京都,与徐、傅等深布诚款,故江陵符瑞得闻于中朝”[2]102,也与史实相悖。《宋书·王昙首传》记载:“景平中,有龙见西方,半天腾上,荫五彩云,京都远近聚观,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气。’”[4]1679祥瑞之事明明白白发生在京都,哪里来的“江陵符瑞得闻于中朝”一说?
总而言之,陶澍完全基于大胆想象,加上不小心的论证,给出了一个离奇的解释。他说:“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载耳。”[2]102如果这也可以为学者接受的话,那以后碰到任何疑难问题,我们都可以自由想象,任意解释,之后补上一句“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载耳”[2]102。此法可用于写历史小说,但不能用于考史。
下面再来看看逯钦立之说。他认为“元嘉元年八月癸卯,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进号卫将军,知庞氏此春乃以抚军参军,赴江陵之任,渊明以五言诗送别。至冬则以卫军参军,衔命使都,渊明又有四言之赠遗也”[3]这个时间线也明显有问题。《宋书·谢晦传》云:
寻转领军将军……少帝既废,司空徐羡之录诏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雝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诸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虑太祖至或用别人,故遽有此授。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节,依本位除授。晦虑不得去,甚忧惶,及发新亭,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寻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进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进封。又给鼓吹一部。[4]1348
谢晦本来是领军将军,废少帝之后,徐羡之任命为行抚军将军、荆州刺史,时在夏五月。到了文帝登基,才正式授予抚军将军、荆州刺史之职号,很快又进为卫将军,时在秋八月。那春天的时候,庞参军怎会去荆州做谢晦的抚军参军?元嘉元年即景平二年,这一年春荆州刺史还是刘义隆。如果庞参军这时去江陵任职,那应是义隆的僚属。到七月,就该在“府州文武严兵自卫”的行列中,随义隆东下,怎会放弃从龙的大好机会,又转投谢晦,返回荆州呢?
如果采用逯钦立之说,那么这位庞参军景平元年冬还是王弘的参军,景平元年春成了刘义隆的参军,到了该年冬又成了谢晦的参军。这太不可思议了。
正确的系年方式,是时间、地点、职官、人物各个要素要完全吻合才行。根据陶诗,可以确定的要素是地点在江陵,职官是卫将军。符合者自然是谢晦。至于时间,谢晦作为卫将军、荆州刺史,赴任在元嘉元年八月,被讨伐在元嘉三年(426)正月,其间有两个冬天,一个是元嘉元年冬,一个是元嘉二年冬。前面已经指出元年冬之悖谬处,那么合理的、毫无龃龉的系年只能是元嘉二年冬。也就是二年春,庞参军转任谢晦的卫军参军,陶渊明写了五言诗赠别。当年冬,庞受命使都,经过浔阳,再与陶渊明唱和,陶公乃有四言的《答庞参军》之作。
因为陶澍和逯钦立二位对四言诗中“大藩”一词有所争论,这里也稍加补充说明。陶说:“非宜都不得称大藩也。”[2]102逯则辩称:“谢晦镇江陵,已进封建平郡公,与大藩者亦无不合。”[3]两人的着眼点都是王侯身份才可以被称为“大藩”,这其实与魏晋南北朝人们的用法不相符合。刺史自魏晋以来常被尊称为“藩”,这是因为刺史辖地既广,兵将众多,又往往久于其任,具有较大自主性。如《三国志·蜀书·许靖传》称张津“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9]965。裴松之注:“子云名津,南阳人,为交州刺史。”[9]966是交州刺史可称为“藩”。而《梁书》卷二十七《明山宾传》有一明证,明山宾曾“出为持节、督缘淮诸军事、征远将军、北兖州刺史”[10]406,而昭明太子后来称“明祭酒虽出抚大藩,拥旄推毂,珥金拖紫,而恒事屡空”[10]406云云。“北兖州刺史”虽然重要,但地位远不如荆州刺史,也可以称为“大藩”,可见“大藩”就是对重要的刺史的尊称,未必需要其人为王、为侯。陶诗中的用例亦当如此理解,因此“大藩”只是当时习语,不能用作推测这个荆州刺史的身份的材料。
系年之后,再来反观陶诗。陶澍说:“观四言末章云:‘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此必先生阴察参军使都,当有异图,故以慎终保躬勖之。”[2]102陶渊明显然不可能具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居然能觉察到连史书都不曾记载的阴谋。但是陶澍的看法却提示我们,陶诗应该并非漫然赋别,而是另有深意。《宋书·蔡廓传》载蔡廓对傅亮说:“营阳在吴,宜厚加供奉。营阳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4]1572又对谢晦说:“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也。”[4]1572-1573可见眼明者已经看出三大臣命运堪忧,恐将难以幸免。作为旁观者的陶渊明呢?元嘉二年,文帝“声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装舟舰。傅亮与晦书曰:‘薄伐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忧惧者多。’……时朝廷处分异常,其谋颇泄”[4]1349。不知道陶公是否也听到什么风声。他告诫庞参军要“在始思终”,其典出《诗经·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11]这是很严重的警告了。谢晦聪明有余,器识不足,自速其死而已。庞君本自佳人,与我诗酒尔汝,延座促席,言说平生,何其安逸也。如今攀附势要,卷入政治的漩涡,需要该逆知政治的风险。今日洋洋得意,也许明天就会惶惶失志,何如我“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