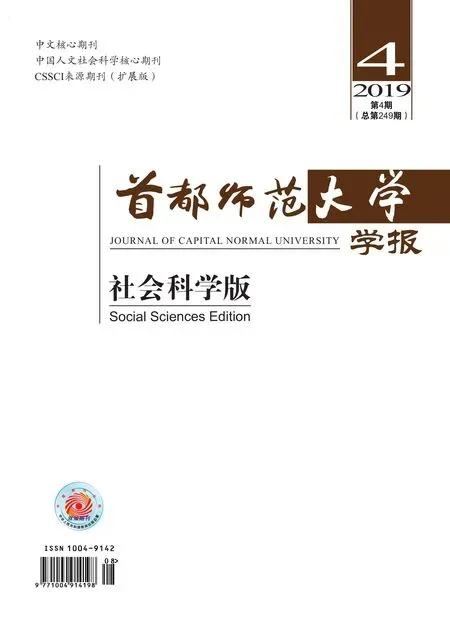日本“东洋史”三种模式及东洋史观批判
2019-02-22王向远
王向远
20世纪上半期整体崛起的日本“东洋史学”,研究东方(亚洲)史特别是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亚洲各民族关系史,是日本的东方学(时称“东洋学”)的一种重要分支,也是“中国史”(时称“支那史”)研究的自然扩展和延伸,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东方学家,如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高楠顺次郎、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滨田耕作、石田幹之助、鸟山喜一、羽田亨、宫崎市定等,他们的著述都有一定的文献学或思想史的价值,有一些在问世后不久就被译成中文出版发行,如藤田丰八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史从考》《西域研究》、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唐宋贸易港研究》、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康居粟特考》、宫崎市定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文明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下)等,都对中国的东方学界有相当的刺激和启发,对此学术史上已有公正客观的肯定与评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的“东洋学”总体上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时代的产物,既是个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国家主义的属性,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亚洲经略”的“国策”色彩。其中,桑原骘藏、白鸟库吉、宫崎市定三位最重要的东洋史学家的研究,形成了东洋史的“模式”,其“模式”包括了研究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历史描述的横向与纵向、研究对象的点线面及其相互关系等,亦即东洋史的基本方法与构架。因而,对三位东洋史学家的“模式”加以剖析,可以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日本东洋史学的国家主义属性有更清晰的了解。
一、桑原骘藏“民族盛衰-邦国兴旺”模式
桑原骘藏(1871-1931)的“东洋史”的学术观念与思想来自他的前辈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1894年,那珂通世、三宅米吉等博士最早建议在中学开设“东洋史”的课程。宫本正贯最早写出了东洋史教科书,接着是藤田丰八博士写出了《中等教育东洋史》。然后是市村瓒次郎将此前出版的《支那史要》(上下,1897年)改写缩减为《东洋史要》(上下)予以出版。接着,1898年,桑原骘藏推出了中等学校的教学用书《中等东洋史》(次年上海东文学社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译名《东洋史要》,王国维为译本作序)。可以说是日本最早形成了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的东洋史著作,影响甚大。《中等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为重心的,但是既然叫做“东洋史”,就不仅仅是研究中国,而是超出中国的范围,而延伸到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亚洲其他国家。从这一点上看,《中等东洋史》乃至日本的所有东洋史都是中国史研究的自然延伸和扩大,而东洋史的这种出发点与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桑原骘藏来奠定的。在他的《中等东洋史》出版五年后的1903年,那珂通世受文部省委托编写并出版的另一部教科书《东洋小史》,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历史分期上,在论述的范围上,都与《中等东洋史》有相同和相似之处,后来这也成为东洋史教科书及读物的一般通例。
冠于《中等东洋史》卷首的是那珂通世所写的序言《中等东洋史叙》,那珂通世这样说:“东洋诸国,尤其如皇国、支那、印度,在人类社会发达史上具有高度的文化,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我们皇国位于东洋的东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与东洋各国的关系都最为密切,国民应该具备关于东洋历史的盛衰沿革的明晰知识,故而在普通中学的历史学科中,在国史、西洋史之间,再加上东洋史。”(1)那珂通世:《中等東洋史叙》,《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东京:岩波书店昭和四十三年版,第3页。版本下同。同样的理解,也反映在桑原骘藏卷首“总论”中对“东洋史”所下的定义:“所谓东洋史,主要是阐明东方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并立,构成了世界史的一半。”(2)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17页。
这样的“东洋史-西洋史”的区分,以及东洋史加西洋史就是“世界史”的观点,直接承继了那珂通世的看法,也是当时日本史学界的共同看法。后来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又解释说:“东洋历史以支那为中心,叙说东洋诸国治乱兴废之大势。而此前的支那历史仅以历代兴亡为主,不叙说人种的盛衰消长。在东洋历史中,不仅要讲述东洋诸国的兴亡,还要涉及支那种、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等的盛衰消长。”(3)桑田六郎:《白鳥先生の追憶》,《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卷(月报10),东京:岩波书店昭和四十六年版,第1页。也就是说,“支那史”即中国史往往以中国历朝交替沿革为主线,而东洋史却是以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为主线,这是“东洋史”区别于作为国别史的“支那史”的关键之所在,也是东洋史的根本特征。
揭示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历史,是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撰述的基本宗旨。若对“民族盛衰、邦国兴亡”论再加以简化,那就是“民族、邦国”史;换言之,“东洋史”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而国家是民族的政治形态,故而归根到底是“民族”(及其原初形态“种族”)的历史,是民族关系史,即以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经纬的历史。在这里,国别史所关注的朝代更替、政权交接、官民关系、社会阶层、风俗沿革、天灾人祸等等,统统都退居其次了,或者只有在涉及民族、邦国及其关系的时候才被提到。
但是,对于一部有着著者特色的东洋史著作而言,不可能是对东方——亚洲——各民族、各国家及地区加以平均叙述的历史,而是有其重点和重心的。要撰写全面而又甄别轻重的东洋史,就要对东洋从地理上加以划分,为此桑原骘藏把亚洲分为五个部分,即东方亚细亚(东亚,范围是南至喜马拉雅山、西至帕米尔高原,北到阿尔泰三大山脉之间的地域范围),南方亚细亚(南亚)、中央亚细亚(中亚)、西方亚细亚(西亚)、北方亚细亚(北亚,阿尔泰山脉、阿拉尔海、里海以北之地,大致指俄罗斯所属西伯利亚一带)。他指出:“东洋史重点在东方亚细亚……南方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的沿革也要加以略述。至于北方亚细亚,因为气候严寒,人烟稀少,没有成为影响东方亚细亚大势的、具有重大干系的事件的舞台。而西方亚细亚,毋宁说他们与欧洲的大局势密不可分,因而出于东洋史的范围之外。”(4)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縂論》,《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17-18页。看来,桑原骘藏是把重点放在东亚、南亚和中亚(后来另一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则把西亚作为东洋史的重点),这也是桑原东洋史的一个特点。
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本着阐明东方亚洲“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之历史的原则,来构架其叙事结构。他把东洋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上古期”是“汉族膨胀的时代”(公元前221年之前);第二“中古期”是“汉族优势时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907年);第三“近古期”是“蒙古最盛时代”(公元907年至1644年);第四“近世期”是“欧人东渐时代”(公元1644年以降)。从这种东洋史的建构中就可以清楚看出桑原骘藏的历史观,那就是把以东亚为主要基盘、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东洋史,看作是此区域内不同民族此起彼伏、盛衰兴亡的历史。这种东洋史模式更多地是着眼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民族之本体;具体而言,更多地是着眼于汉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汉民族之本体。
我们需要关注桑原骘藏在这部全新架构的《中等东洋史》中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观念。从表面上看,书中对历史的记述,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是较为客观的,甚至涉及到日本历史的地方也尽力客观,如写到倭寇对朝鲜与中国东南沿海的掠夺骚扰,明确地说明了倭寇的劫掠性质,比起日本当代那些为倭寇翻案与美化的学者要尊重历史得多。但是尽管如此,桑原骘藏东洋史的主观思想还是显而易见的,他把东洋的历史叙述为“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历史,并且揭示出了历史盛衰的基本线索与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汉族”早在唐朝覆亡之后就走向衰落,接下来东洋舞台的主角是蒙古人。而中国的清代则是西方势力东渐的时代,也是满蒙民族衰败的时代,实际也就是中国(“支那”)衰败的时代。而导致中国衰败的原因,除了来自西方的“欧人东渐”之外,更有东亚最东端的日本的从东洋史边缘走向东洋史中心。《中等东洋史》最后一章一直写到当时。这一章描述了日本如何与中国(“清国”)冲突,日本如何收纳琉球、征伐台湾,如何为了朝鲜同“清国”开战,在战争中如何大败“清国”并签订“日中《马关条约》”,而日本如何在西方三国(俄国、意大利、法国)的干涉下,得到五千万两补偿金,而将中国的辽东半岛交出——时值公元1895年,全书至此戛然而止。就这样,整部《中等东洋史》从中国古代写起,揭示了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东方“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历史过程。作者从中国,写到了被欧洲人渗透的中亚,再写到被欧洲殖民的印度、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又落笔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作为,最后是日本在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冲突,在辽东半岛上与西方的冲突与妥协。整部《中等东洋史》,实际上就是讲述汉族及蒙古人治下的中国如何相继衰败衰落、欧洲势力如何东渐的历史,最后写到日本在此时开始走向东洋舞台的历史,寥寥数语,看似十分节制含蓄,但内在的逻辑非常清楚,不言而喻。
《中等东洋史》这样历史叙述的结构,在貌似客观、平静、公允的叙述中,暗含着他对古今东洋历史演变与走向的判断,其中心思想是中国衰败论、停滞论。对西方史学较为熟悉的桑原骘藏,在这一点的判断上显然受到了西方的东方学家的东方观,如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东方停滞论的影响,受到了19世纪西方社会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的影响,也受到了19世纪欧洲的文化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当时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思潮与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在日本将“亚洲经略”作为基本国策的时候,桑原骘藏及日本的东洋史学家当然很乐于接受西方的这些观点,并且作为其东洋史著述的基本思想。实际上,《中等东洋史》所要揭示的,就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早就衰落了,唐代以后东洋的历史主角不是汉族,而是蒙古族、满族。在这里,桑原骘藏显然混淆了种族、民族、国民、国家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作为一百年前的历史著作,我们不苛求作者对这些概念做严格的科学区分。但是,作为精通东洋史的桑原骘藏应该很清楚,“汉族”本身不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种族概念,汉族是在不断融合其它种族的基础上扩大的,汉族实际上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概念,无论是汉唐、还是汉唐之后的历代都是如此。所谓“蒙古最盛的时代”,实际上也是蒙古人逐渐被汉化的时代。即便从纯粹种族的意义上说,明代虽被桑原骘藏划分为“蒙古最盛的时代”,但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即被汉人推翻,推翻了元代的明朝却存续了二百七十多年,而且是东西方历史学家都公认的当时全世界最辽阔、最富有、最发达、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桑原骘藏把东洋史简化为汉族、蒙古族等种族此起彼伏、此强彼弱的时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此间种族的交融、民族的融合;没有看到中国历史的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代,实际上既是以“作为种族的汉族”,也是以“作为文化的汉族”为中心的历史。王朝的交替、统治者的更迭,不但没有撼动这一历史规律,反而不断强化这一规律。即便是作为一个种族的汉民族,它也一直都是发展的、演进的,有它稳定的、不变的一面,也有它变化发展的一面,因而很难说在“蒙古最盛的时代”汉民族就一蹶不振了,相反地,在那个时代汉民族文化却最大程度地显示了它的影响力同化力;很难说在“欧人东渐的时代”汉民族就退缩无为了,相反地,汉民族却在抗争中、在学习中更生和更新。在这个过程中,汉民族也突破了狭隘的血缘与种族,而不断发展和扩大。有当代学者用“滚雪球”做了形象的说明:“汉民族,这个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民族,也颇具雪的特性……她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摇篮,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那样,融合了许多民族,凝聚而形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5)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题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中等东洋史》中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东洋历史观,给人强烈的印象就是历史上汉族早就衰败了,“支那”文化早就衰朽僵化了。这一结论不仅是桑原骘藏的,也是同时和后来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支那史”学者,如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人共同的看法。因为按照这样的看法,到了20世纪,面临西方世界的挑战,中国国家虽大,但自身尚且不保,如何能领导亚洲抵抗西方。于是很多日本人自我感觉、或者坚信日本终于可以继之而起,能够成为东洋历史舞台的主角,来担当“保全支那”之责任了。几年后,这个观点在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日本的觉醒》中做了明确的表述与宣扬,而桑原骘藏等人的东洋史研究则为此做了铺垫。
二、白鸟库吉“南北对抗-东西交涉”模式
桑原骘藏以“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为主题的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模式,在同时代另一位东洋史大家白鸟库吉(1865-1942)那里有了进一步的发挥,那就是所谓“南北对抗-东西交涉”论。
“南北对抗”(又称“南北对立”)论是白鸟库吉在题为《戎狄对于汉民族的影响》(1901年)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来的。在这里,汉民族与北方各民族(戎狄)的关系是理解支那史的关键。他认为,位于汉族北面的主要有三个民族:位于东北满洲地区及西伯利亚一带的通古斯(包括女真、满族),位于长城以北地区的蒙古族,位于西北部的西域中亚地区的突厥族(其中包括匈奴、鲜卑、回鹘、吉尔吉斯等)。这三个北方民族的共同特点是野蛮、剽悍、尚武,打仗就是他们的本业,而且滥用武力,在文化上没有什么造就。但是,他们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凭借武力,对文明民族与国家加以攻击侵略,这对整个亚洲历史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白鸟库吉认为,要明白为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本来具有悠久文明的亚洲大陆各国,如今衰落到这种可悲可怜的地步,日本的东洋学应该从北方这些戎狄民族的研究中,从汉民族与这些民族的关系研究中,来寻找亚洲大陆荣枯盛衰的原因。
白鸟库吉认为,汉民族的民族性的形成与北方野蛮戎狄民族的入侵有很大关系。汉民族如今最根本的特性在于“保守固陋”,这种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汉民族要在戎狄的进攻破坏之下,想方设法不使自己的固有特性、固有文化传统——白鸟库吉谓之“国性”——丧失掉,千方百计对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否则就等于灭亡,于是久而久之,保守主义就成为汉民族文化、成为“国性”保护的一道铜墙铁壁。白鸟库吉认为儒教之所以成为汉民族的基本宗教,就在于儒教的价值取向是复古的、保守的。“因此之故,我断言汉民族保守的倾向是戎狄所造成的。”(6)白鳥庫吉:《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东京:岩波书店昭和四十五年版,第11页。版本下同。除了“保守固陋”之外,白鸟库吉认为,如今汉民族所具有的“尊大”习气,也是与戎狄的关系所造成的,因为戎狄没有什么文化,汉人一直瞧不起他们,而事实上戎狄一旦在武力上取得成功,并在汉民族的地盘上建立政权,但不久却在文化上被汉民族同化了,久之汉民族在文化上就有一种骄傲感,并养成了尊大习气;与此同时,“进取谦逊”之风全没有了。而现在当面对崭新的世界、崭新的近代文化的时候,汉民族仍然不改以往的“保守固陋”与“尊大”之习气,这样,它“与世界文明国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白鸟库吉不仅用“南北对抗”来解释汉民族性格与文化,而且推而广之,以此来解释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亚洲大陆的文化。他断言:“亚细亚文明古国落到了如今的这步田地,全都是由戎狄造成的。亚细亚人的思想总体上是保守的消极的,与戎狄也有重要的关系。” 在较晚发表的《古代支那和印度总说》(1937)一文中,对印度历史的分析也套用“南北对抗”论,并且进一步使用了“南北文武的对立”这样的表述,认为南方文化的精华是宗教,北方文化的代表是武力,并以此来论述印度宗教文化与北部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关系;还认为,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白鸟库吉称“回教”)也是起源于南方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文化,与北方突厥族的尚武文化对立统一。然而,正是南北方民族的这种文武对立与同化妥协,久之造成了亚洲大陆各民族的退化。“北方被南方同化,丧失了作为其长处的武勇;另一方面南方也因为不断地遭受北方的侵略蹂躏破坏而丧失了气力,使得原有的文明本身发生偏颇,逐渐变得固陋与老衰。”(7)白鸟库吉:《古代支那及びインド総説》,《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第104页。换言之,亚洲大陆各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互相对抗而又互相消耗、消磨的历史。
本来,“南”与“北”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也是所有研究学习历史的人所显而易见的。在日本,冈仓天心早在1894年就发表了题为《中国南北的区别》一文,指出:“关于长江以南、黄河以北的风俗习气差异,古人早有论说。”(8)冈仓天心:《中国南北的区别》,见蔡春华译《中国的美术及其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4-215页。桑原骘藏也曾在《历史上所见中国南方的开发》一文中指出:“支那自古以来就有南北之分,在风俗、人情、地理、物产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9)桑原骘藏:《歴史上より南支那観たる開發》,《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161页。这一点在日本学术界也是常识和定论。在这方面,白鸟库吉的“南北对抗”论没有新意可言,但是,他却在此基础上做了两件事情,就颇带有白鸟库吉独特的理论用心。
第一,就是将“南北对抗”论加以限定化、特殊化。白鸟库吉将“南北对抗”看做是亚洲大陆上各时代的普遍现象与共同规律,而唯独日本超于其外。在1904 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我国强盛的历史原因》中,白鸟库吉再次使用“南北对抗”的理论来解释亚洲大陆各民族均已衰败、而日本却能一枝独秀的原因。这个原因首先是地理上的:
我们再转眼来看日本国,就会发现其地理位置与它们完全不同,它们都是大陆国家,我们是岛国。国土处在温带,不像北方戎狄所居之地那样严寒,也不像南方文明发源地那样炎热。地势由北向南沿着大陆伸展,又不是与大陆完全处在隔绝的状态,同时也不会在接触中融入他们当中。隔着对马、朝鲜,可以窥伺大陆,从地形上看好像要把他们吞掉一般,又仿佛是在抱持着他们。总之,日本列岛在地理位置上是独立于大陆的,但同时也处在可以接受大陆影响的位置。这个岛国以往拥有怎样的历史,将来拥有怎样的历史,从地理上就可以说明一大半。(10)白鸟库吉:《我が國の强盛となり史的原因に就ついて》,《白鳥庫吉全集》第九卷,第164-165页。
在白鸟库吉看来,依靠这样的地理条件,日本没有受到大陆北方民族的入侵,也没有沾染中国人保守固陋的习气。他在19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在亚洲大陆,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不受北方民族的侵入与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超越于南北对抗之外,因而现在全都萎靡不振,但是,“在东面,只有一个国家未受北方民族影响,那就是日本。日本没有受到亚洲北方民族的影响,既有地理上的关系,当然也是由于日本民族的勇敢”,而将欲来入寇的蒙古人击退。(11)白鸟库吉:《世界に於ける日独の地位》,《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卷,第220页。而另一方面,日本对亚洲大陆又能取其精华,“北方勇武的气象、南方文物的精粹却又集于一身,亚细亚大陆美好的东西悉数汇集于日本国土,因而我国在与西洋文明接触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亚细亚唯一的文明国的资格”。(12)白鸟库吉:《我が國の强盛となり史的原因に就ついて》,《白鳥庫吉全集》第九卷,第169页。这样一来,白鸟库吉就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论证了自江户时代以来的那些“国学”家一直鼓吹的“日本优越”论与“日本特殊”论。
第二,将“南北对抗”加以推演和发挥,与上述的“限定化、特殊化”是相反的运动。白鸟库吉把他的“南北对抗论”加以推延和普遍化,使之不仅用来说明古代东洋史上的规律现象,也把它作为近代史上的一个规律现象。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1926)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写道:
这些年来我提出一个看法,认为东洋史的大势是由一个根本的事实所决定的,那就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也就是说,在古代是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南方势力,和统称北狄的那些北方势力,两者一兴一废、一弛一张,不断反复,带动周边势力的离合聚散,从而决定了东洋史的发展与面貌。而到了近代,又出现了作为南方势力的英国人,与作为北方势力的俄国人,使得南北对抗的局势仍然存续。所以我主张,远东的局势是由这两个因素的对立为中心所决定的。(13)白鸟库吉:《東洋史における南北の對立》,《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第69页。
这就等于把本来属于东洋的“南北对抗”问题也扩大到了西洋,把英国与俄国的关系看做南与北的关系,认为“南北对抗”是一种历史发展演变的“大势”,指出“这个大势不管时代推移、不拘民族的变化,都一直存在,并且扩大着其影响范围”。(14)白鸟库吉:《東洋史における南北の對立》,《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第75页。可见“南北对抗”论是白鸟库吉用来构架东洋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基本理论模型。
白鸟库吉将“南北对抗”论作为历史原理并加以普遍化,是对此前宣扬的“日本独一无二”的“特殊论”的一种调整与补充。在他看来,从东洋历史看,只有日本在亚洲各国中是个例外,因为日本历史上没有受到戎狄的祸害。“倘若我国也和朝鲜一样处在大陆的一端,那么必然遭受戎狄之害,绝不会有今天的一枝独秀。”(15)白鸟库吉:《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第14-15页。但是,放在世界上看,那就是无独有偶。他从西洋找到了一个用来说明日本的例子,那就是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岛国英国。“要问何以英国在欧洲最为强大?是因为英国是脱离了欧洲大陆的岛屿。当大陆上强有力的势力崛起之后,对英国也是鞭长莫及。相反,英国要接受大陆的文化并加以开发倒是很容易,而接受外国影响的弊端也减到最少,故而扬长避短。这就是如今英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16)白鸟库吉:《古代支那及インド総説》,《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第107页。然后他又用欧洲来比附亚洲,认为“欧洲的俄罗斯相当于亚洲的满洲,中欧相当于朝鲜,英国相当于日本”。这样一来,起码在地图上,日本与英国,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北方的野蛮与南方的文化,以及它们所形成的比照关系,就这样鲜明地勾勒出来了。白鸟库吉便有了“一石三鸟”之效:一是为当时日本与英国达成的同盟关系(“日英同盟”)找到了历史文化根据;二是把俄罗斯归为野蛮的北方戎狄民族的行列,显示了它的历史文化的落后野蛮性质,并把当时日本与俄国的对立,安上了一个东洋历史上“南北对立”的大背景;三是为日本在东洋的崛起、独大与“盟主”地位,找到了英国的榜样和旁证。
不仅如此,白鸟库吉还有第四个用意,那就是将“南北对抗”论,悄悄地演变、转换为“东西交涉”论(17)白鸟库吉:《東洋史における南北の對立》,《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第83-84页。。早在上述的《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的结尾处,“东西交涉论”就有了迹象,那里提到南北对抗往往会影响“位于南北对抗线上的东西方的小势力”。而到了《亚细亚史论》(1939)一文中,白鸟库吉便对此做出了明确论述:
在亚洲的南北对立的过程中,当北方与南方的势力相互均衡的时候,以及南方强大到能够压制北方的时候,北方的势力便向南方鞭长莫及的地带延伸。这从亚洲地理上看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对立常常会引起东西交涉。这是亚洲史上的经与纬的关系。假如在把握亚洲史上的南北方关系的时候,不同时把握东西方关系,那将是不充分的。(18)白鸟库吉:《アジア史論》,《白鸟庫吉全集》第八卷,第193-194页。
他举出的例子是,当匈奴与秦汉对立处在劣势时,便与东方的东胡联合,然后在西方进攻占据甘肃省西部的月支和乌孙。被攻击的月氏逃往天山,而进攻那里的塞种,塞种便逃往南方进入阿富汗斯坦南部,等等之类。看来,这种“东”与“西”的所谓“交涉”也是战争性的,只不过它们不是文明与野蛮、文与武之间的对抗,而是同种性质的民族之间的对抗,而且空间上是东方与西方之间,是横向性的。接着,白鸟库吉进一步把亚洲史上的这种“南北对抗-东西交涉”的历史现象加以规律化,把它适用于亚洲以外的欧洲。他认为:“这种南北对立引起东西交涉的现象,固然是亚洲史的一个特征,但这个西方不仅仅止于亚洲西部,一般也会波及欧洲的范围。故而亚洲内部的南北对立结果总会引起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交涉,从而使亚欧发生关系。”(19)白鸟库吉:《アジア史論》,《白鸟庫吉全集》第八卷,第194页。
这样一来,白鸟库吉就不仅用“南北对抗-东西交涉”来解释亚洲历史乃至欧亚的历史,而且也用来解释现实世界。“交涉”在日文中除了“交涉”的汉语本义外,还有谈判、交流、联系的意思,其性质是和平的、基本对等的。所谓“东西交涉”“东西交涉史”这类的词组概念,在当时和此后的日本学术界使用较多,指的就是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与交流。白鸟库吉使用“南北对抗-东西交涉”这个词组,包含着一种逻辑:凡是属于“南北”关系的,是侵略与被侵略、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也是非和平的对抗关系;凡是属于“东西”关系的就是“交涉”的关系。那么,在现在的欧洲,谁是“北方”呢,答案是“俄国”;谁是南方的代表呢,答案是“英国”。在亚洲,谁是北方呢,答案也是“俄国”;谁是南方的代表呢,答案是“日本”!于是白鸟库吉断言:“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亚洲发生的种种国际问题及其纷争,基本上都与亚洲范围内英国与俄国的南北对立有关。在这里对抗的民族不是亚洲民族而是欧洲民族,但从南北对抗这一点上看,与亚洲史上一贯的对抗形式是相同的。而且,英俄之间的对抗使得我们远东的日本也不能置之度外。日英同盟也好,日俄战争也罢,其原因与意义可能有多种,但基本的原因还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英国利用日本阻止俄国的南下。”(20)白鸟库吉:《アジア史論》,《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第198页。
白鸟库吉的最终目的,还在于用“南北对抗-东西交涉”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当时(七七事变时)的所作所为:
日本兼具亚洲北方民族的长处即“武”和南方民族长处即“文”。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卓越的国民,一旦得之时运,便可以展开划时代的伟大活动。日清战争后日本民族在大陆的发展,特别是这次的支那事变,就是最为显著的体现。唯有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民族向亚细亚大陆的发展,不是从北方进行的,而是从东方进行的。这是用“南北对立”不能加以解释的崭新现象。(21)白鸟库吉:《アジア史論》,《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第200页。
白鸟库吉最终要说明的是:日本与大陆的关系,不是“南北对抗”的关系,而是“东西交涉”的关系,不是侵略,而是平等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同样的,来自所谓“南方”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列强在近代史上对中国的侵略,英国、荷兰、法国对南亚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殖民统治,他都按下不提,因为按照他的“南北对抗-东西交涉”的模式,那都属于“交涉”,而不是对抗、侵略和被侵略。在这里,我们看到,白鸟库吉的“东洋史学”已经完全蜕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殖民侵略理论,已经堕落为一种反学术的强词夺理的强盗理论了。
三、宫崎市定“西起东至-终点文明”模式
白鸟库吉之后,对东洋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南-北”和“东-西”问题接着往下说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宫崎市定对白鸟库吉的“南北对抗”论,特别是对南方文化因北方侵入而衰败的理论不予首肯,他反倒认为北方民族的文化是“朴素主义”的,而南方民族的文化是“文明主义”的。在题为《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 年)小册子中,他提出了这两个概念,在该书序言里他解释道:
本书题为《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读者或许觉得这个书名很怪异。东洋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在中国。在中国这个文明的中心的周围分布着许多未开化的民族。焉知这些被视作野蛮的民族中,却保留着被文明人早已忘却了的一大优点。文明人有文明人的教养,朴素人有朴素人的训练;文明人善于思考,朴素人敏于行动;文明人是理智的,朴素人是意气的;文明人情绪缠绵,朴素人直接了当;文明人具有女性的阴柔,朴素人具有男性的刚强。更进一步说,文明人崇尚个人自由主义,朴素人囿于集体统制主义。总之,几乎在所有方面,两者之间都表现出了相互对立的特征。(22)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卷,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版本下同。
值得注意的是,宫崎市定没有把北方民族称为“野蛮民族”,而是用了“朴素主义”这样一个不无褒义色彩的词。而他所谓的“文明主义”也不是“文明”,似乎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明病”,接近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明”概念,即已处在保守、僵化、无创造性的死亡状态的文化,同时也受到了现代西方功能主义文明论的影响,即主张不对民族文化做“先进-落后”价值判断。宫崎市定在“朴素主义-文明主义”两者对立的理论前提下,既要解释东洋史上的民族冲突与交流的关系,更要论证的是作为东洋史之重心的中原(汉民族)民族的文明与国家为什么往往善始而不能善终的问题。
宫崎市定认为,北方民族对汉民族的影响,在“朴素主义”的意义上说是正面的、有益的,从这个角度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比白鸟库吉所秉持的来自现代西方的“文明-野蛮”二元论要来得高明。与白鸟库吉对北方民族作用的负面的、否定的估价正好相反,宫崎市定指出,汉民族文化衰退,表现为日益文明化,繁文缛节、安逸奢华、迷信保守,胆小怕事而又盲目自大,缺乏尚武精神和科学精神,这种情况到宋朝已经相当严重。汉民族王朝的覆灭,都是因为过度文明化所致,而外族的统治给汉民族注入了新鲜活力和朴素主义文化。他甚至认为:“在蒙古人统治的一百年间,中原人接受了朴素主义的锻炼……明王朝虽然内忧外患不断,但毕竟维持了三百年的天下,原因之一就是蒙古人朴素主义教育所赐。”而“三百年的历史让明朝步入了老龄。中原的文明社会,不得不再一次在以六万八旗为中坚的清朝的统治下接受朴素主义的锻炼”。(23)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卷,第121、123页。但是,满清治下的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国最终又陷入文明主义的泥淖——
所幸的是,与中原的文明社会相比,在东方世界还有一个朴素主义社会的存在,这就是日本……日本一方面有着古老的文明,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舍弃朴素主义的精神,这才是日本值得向世界夸耀的事实。日本精神绝不是建筑上或者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华丽,而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朴素主义精神……日本的朴素主义精神,表现为谦逊天真,善恶分明,因此对西方的科学文明有着惊人的判断力……以至于最终掌握了如何使文明生活和朴素主义相互协调的关键。(24)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卷,第126-127页。
在宫崎市定看来,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本质区别。按照这个逻辑,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是日本文明发展的条件;相反地,是日本不接受中国文明的影响,才保持了其独特的“朴素主义”本质。显然,这又是一种形式的日本特殊论,与上述白鸟库吉的日本特殊论表述有所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白鸟库吉是说日本由于没有受到北方野蛮民族的入侵,才保持了国体的连续性与特殊性;而宫崎市定是说,日本没有受到中国的中原汉民族的“文明主义”的熏染,才保持了难能可贵的“朴素主义精神”,并使日本能够吸收“西方的科学文明”,建成近代强大的国家与社会。联系到宫崎市定的这本《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出版的背景,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情况下,这种结论的“国策”性或日本国家主义的性质,就不言而喻了。
宫崎市定的“朴素主义-文明主义”论,一方面矫正了白鸟库吉的“南北对抗”论,另一方面又延伸和发展了白鸟库吉的“东西交涉”论,也同样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他在战争期间撰写、战后不久出版的《亚洲史概说》一书,在白鸟库吉的“东西交涉”论的基础上,初步提出文明起于西亚,最终到达最东端的日本并得到充分发展,简言之就是文明的“西起东至-文明终点”论。宫崎市定的学生砺波护在《亚洲史概说》1987年中公文库新版的“解说”中谈到,该书本来定题为《大东亚史概说》,是1942年日本文部省授意的,“‘大东亚史’指的就是当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文部省的远大目标就是在该书完成后,立即将其翻译为东亚各国语言,使共荣圈的各国民都阅读此书……按文部省的意思,‘大东亚史’涉及的地理范围就是缅甸以东,其内容就是试图把日本描述为拥有世界上最悠久历史的国家,日本就像扇子轴心一样处在东亚国家的中心位置。东亚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皇国文化从朝鲜、支那传到亚洲各地的过程”。(25)砺波护:《アジア史概説·解説》,东京:中央公论社中公文库,1987年版,第506页。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对官方的荒谬旨意做了妥协调整,由原来的“大东亚”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亚洲,由不着边际的“日本中心论”调整为“终点文明”的位置,但依然拖着日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尾巴。接着,宫崎市定发表《东洋史上的日本》(1958)的长文,既是对日本“朴素主义”论的延伸和发挥,也对《亚洲史概说》中的“西起东至-文明终点”论做进一步的阐释。
“西起东至”理论出发点是现代西方“文化传播主义”思想,即认为人类文明不是有多种起源,而只能从一个点上传播开去的,而这个点就是古代埃及,这是一种典型西方中心主义文明理论。宫崎市定在“亚洲史”的层面上,把人类文明的起点放在西亚的美索不达尼亚,而亚洲最东端的日本作为文明传播路线的终端。如此自西向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西交涉”的文明传播路径,而文明的载体就是青铜和铁。众所周知,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基本可以证实,西亚的美索不达尼亚在公元3000年前最先使用青铜,中国青铜文化是在公元前1000 年左右,铁器文化时代在公元前400 年左右,比西亚晚很多。但是,这种时差并不就能充分证明青铜文化和铁器文化是从西亚传到中国的,而至多只能是一种推测。宫崎市定也承认这只是推测,但他仍然很乐意接受传播主义,设想西亚的青铜和铁器先后东传,传到了印度、中国,然后又传至朝鲜,认为这两种文化几乎同时在公元前后传到日本,到达日本后,再往东是大海,没路可去了,于是就都留在了日本。这不仅直接促成了日本进入文明社会,而且还使得日本成为东洋世界乃至全世界的“文明的终点”。
这就是宫崎市定的文明“西起东至”和“文明终点”论。这种结论的做出虽然不是向壁虚构,但由于难以实证,更多地带有想象成分。正如宫崎市定所比喻的那样,从西亚发出的“文明之车”,装载着人类最早的文明,从西往东,不远万里一路驶来,最后到达日本的终点站。宫崎市定做出这个结论的目的,是要证明:“起源于西亚、印度,在中国因受到抵制而未能发展起来的文化,到了日本却开了花结了果。”(26)宫崎市定:《东洋史上的日本》,《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卷,第1336页。他接着举出的例子就是日本的表音文字的产生,说在西亚印度的表音文字最多使中国产生音韵学及反切法,但在日本却促使发明了假名文字。
“西起东至-终点文明”论,作为宫崎市定的东洋史、世界史理论建构的基础,目的无非是为了证明日本历史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不是白鸟库吉夸耀的那种与外界隔绝、不受外族侵扰的特殊性,而是一种把人类文明精华加以汇集、保存和发挥的特殊性。这种理论突破了中国影响日本论,把那些比中国更远的西亚、波斯、印度都拉过来,而中国仅仅是一个中介环节。因为中国处在中介位置,没有留住文明精华并加以发挥,只有日本做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冈仓天心在20世纪初提出的“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的论点,而宫崎市定的“西起东至-终点文明”论,则在半个世纪后,而且是在日本战败十几年后,与冈仓天心的论调遥相呼应。
宫崎市定的“朴素主义-文明主义”两种文化论,强调日本没有受到文明主义熏染而保留了朴素主义的特殊性,从而有别于中国等其它亚洲民族,这是强调日本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提出日本是东洋文明的汇集处,认为东洋文明起源于西亚,经过印度、中国而最终到达日本并集其大成,亦即“西起东至-文明终点”的东洋史观,这是强调日本的普遍性。两种史观相反相成,是说日本既是特殊的唯一优越的,又是最终的和集大成的。日本国家主义本质属性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