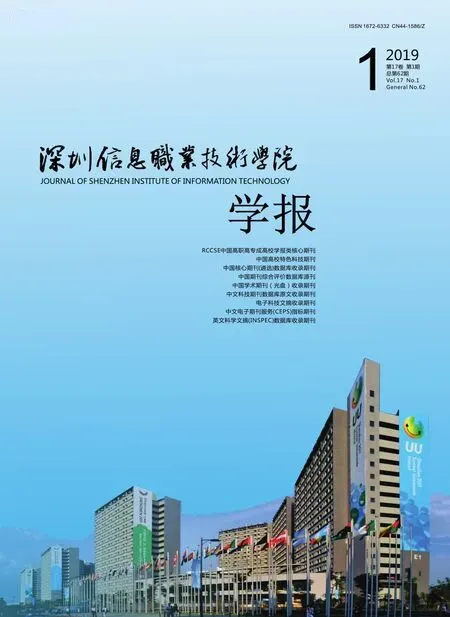大数据与“大思政”
2019-02-22傅鹤鸣
傅鹤鸣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谈到“大思政”,以往更多是在整体性哲学思维原则指导下,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思政工作教育理念,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组织机构、教师队伍与课程体系等方面的一体化与整合化,以期克服思政工作中不同机构、不同人员以及不同课程之间各自为阵的孤岛现象,构建同心同向的“三全”育人格局。以下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本性与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影响两方面来谈谈“大思政”育人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不确定性的知识本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从根本上讲属行为科学,即通过对学生行为的研究以期实现对学生行为的规范引导。现实工作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之所以显得异常艰难,从根本上讲这并不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关乎立德树人这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认识与判断,而是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知识本性。人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对于诸如什么是平面这样几何学知识的定义能迅速达成一致意见,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的定义却难以一致?同样是对定义的寻求,出现以上这种相反现象根本原因在哪?要弄清楚类似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几何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这就要求人们必须进一步还原出它们各自的知识本性。事实上,对于什么是平面这样几何学知识的寻求,其本性就是一种确定性的寻求,自然而然人们能获得一致性的看法。然而,对于关于人们行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的寻求,由于学生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与不确定性,属实践题材范畴,其本性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寻求,结果也就必然千差万别。
其实,对人类的不同活动进行归类整理,并交由不同的学科开展研究,由此形成不同的知识类型,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人类不同活动类型的知识论前提。从知识论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学之所以能独立门户,根本原因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题材采取了与科学研究本性完全不同的、独立的研究范式,并由此产生出了与科学知识本性上截然不同的实践型知识。这种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探究所形成的实践型知识与科学知识相比较,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达不到科学知识所具有的确定性(其实科学知识也并不具有大家所认为的那种确定性——即绝对确定性)。
显然,作为行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而言不是任何客观知识,当然也不是科学知识,而是某种他必须去做的东西。另外,科学的品质决定了人们必须在非常准确的意义上、而非粗略意义上使用科学知识这个词。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则完全不同,它只需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相匹配的粗略的确定性就合法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种实践的目的,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为了了解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为了培养有思想讲政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否则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将毫无意义。
二、不确定性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本性的确定性寻求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本性具有不确定性,那么对不确定性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本性进行确定性寻求是否可能?
在大数据时代,不确定性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本性的确定性寻求之所以可能,源自于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即以数据为本质的新一代革命性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有力推动,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将成为一种趋势。基于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性而生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必然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本质上讲,大数据可以将人(事实上是通过对人的行为数据处理来实现对人的数字化处理)进行数字化处理,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学生既不停留于作为教育活动的抽象对象上,也不停留于作为教育活动一般意义上的具体对象上,而是通过对教育活动对象——学生行为——背后的数据挖掘、数据收集、数据链接、数据沉淀、数据组接等数据处理方式来实现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准确判断与准确分析,从而解决过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非验证性问题,进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本性的确定性。
可见基于大数据而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可以转换成一种数据处理活动,即无疑可以做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精准定位、精准把脉、精准施教”,在科学的意义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千百年来想做而很难真正做到的“有的放矢、因材施教”教育教学理念。同时必须指明的是,尽管基于大数据技术条件下可以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革命性的转换(即从理念型转换成量化性),但其所达到的知识本性的确定性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或然性,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界限。事实上,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知识也达不到大家所期待的那种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只能对不确定性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本性进行确定性的寻求,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