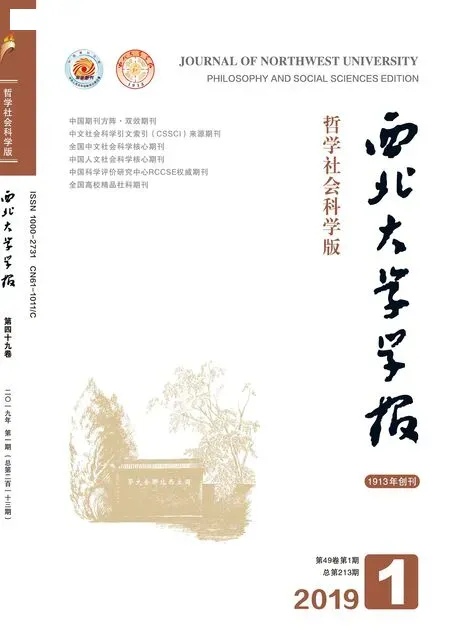“白尔尼—海涅论争”及其当代意义
2019-02-22张永清
张永清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众所周知,文学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理论、批评理论需要持续关注、反复探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历史境遇”进行某种“还原”就是对它们所蕴含的当代意义的变相“解蔽”,对其相关文学论争内核的某些“剥离”就是对现实难题的别样“解答”。尽管“白尔尼—海涅论争”在以往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深入的探究,但这一论争关涉到诸如作家的政治立场与其文学立场之间以及批评的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之间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一论争的重新审视或有助于理解与把握当代社会在类似问题上所展开的相关论争的症结所在,或有助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话语体系构建。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其一,“白尔尼—海涅论争”得以发生的时代状况、社会语境以及白尔尼、海涅两人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其二,“白尔尼—海涅论争”与之前的“歌德论战”之间的关联;其三,“白尔尼—海涅论争”的时限、起因、主要问题;其四,青年恩格斯、马克思、勃兰兑斯、梅林、卢卡奇、韦勒克等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论争所持的基本态度、理论立场;其五,这场论争的当代意义。
一
如果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所使用的术语来概括,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与亨利希·海涅(1797—1856)两人均生活在“双元革命”即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西欧社会剧变时期[注]路德维希·白尔尼(Ludwig Borne),在中文翻译中大体有四种译法:高中甫在勃兰兑斯的《青年德意志》中翻译为伯尔内;张玉书等在梅林《论文学》以及张玉书编《海涅研究:1987年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著作中翻译为别尔内;杨自伍在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中译为伯尔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为白尔尼。本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法。为了保持译名的统一,本文所引的其他相关译文全部改为白尔尼。。欧洲在1815年至1848年的短短三十多年间发生了三次大的革命浪潮: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革命(1820—1824),法国、比利时、波兰革命(1830—1834),1848年欧洲革命(仅有英国、俄国少数国家未被波及)。其中,尤以法国大革命、法国七月革命对这一时期的德意志社会影响巨大。
与英法等国相比,“革命年代”的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1806—1813年这一时期正是德意志争取民族解放的峥嵘岁月:耶拿惨败发生在1806年,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同胞书》也问世于1806年,1813年的莱比锡大捷则宣告反法军占领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正是在这一“革命年代”,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情被点燃、被激发;正是在这一“革命年代”,保守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社会思潮在德意志大地上竞相涌现。
德意志文学在这一“革命年代”又处在何种境地?在勃兰兑斯看来,“世纪交替期间的德国古典文学在题材和形式上都是仿古的。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在题材和形式上是效忠于中世纪的。两者都同周围现实保持着距离,同‘现时’,同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离得远远的;不管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文学流派,都没有直接想到自身要来一个变化。它们的理想不是飘浮在希腊的深蓝色的以太之中,就是荡漾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天空里”[1](P29)。勃兰兑斯所指的前者无疑以歌德、席勒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德国晚期浪漫派为代表。很显然,上述两种文学所表达的社会理想与新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它在德国浪漫派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到1805年时,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新保守主义已占优势。在法国和德意志,‘浪漫主义者’一词可说是18世纪90年代后期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幻想破灭的前左翼分子)所创造出来的反革命口号,这可以说明何以在这些国家当中,许多按现代标准应被看作明显的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传统上却被排除在这个类别之外”[2](P308)。
与上述两种“旧文学”截然有别的是,1806年之后的德意志文学呈现出与时代精神同步的新变,即涌现出了关注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精神状况、反奴役争自由的新文学,它们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新文学以反法军占领和入侵为主题,它以诗歌的形式表达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感。此种精神与情感无不体现在阿恩特(1769—1860)的《时代精神》、吕克特(1788—1866)的《顶盔带甲的十四行诗》、克尔纳(1791—1813)的《琴与剑》等诗作中,诚如勃兰兑斯所论,阿恩特“对法国的仇恨形成了固定观念,他一面创作一些雄伟壮烈的自由歌曲,同时和雅恩一起号召把德国的全部过去作为武器来反对异族统治者”[3](P277)。
但是,解放战争后,德意志的专制统治者并未兑现曾经对人民所作的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并未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与社会变革。随着神圣同盟于1815年的建立,随着卡尔斯巴德协议于1819年的实行,德意志的专制统治者试图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对自由思想进行全面禁锢,1815—1830年的德意志社会无可避免地陷入到了最为“苦闷”的历史时期。正是由于自由、公开地谈论政治、社会问题已然成为了奢望,人们就把希望转移到了文学、艺术、美学等领域,即以文学、美学的方式“介入”到时代的政治洪流与社会变革中,以此实现对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的严厉批判。比如,诗人沙米索(1781—1838)在《轮唱曲》中不无悲伤地写道:
这是沉重的时代苦难!
这是苦难的沉重时代!
这是时代的沉重苦难!
这是沉重、苦难的时代
再比如,诗人普拉滕(1796—1835)在《柏林国民歌》中表达了同样的愤懑之情:
啊!诗人,你该满意了,
这个世界并没有失去什么;
在这个地球上你早就知道,
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德国人更糟。[1](P17)
第二种新文学以“青年德意志”为代表,它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应运而生,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斐迪南·谷兹科(1811—1878)、鲁道夫·文巴尔克(1802—1872)、亨利希·劳伯(1806—1884)等。“青年德意志”形成了与之前的古典风格、浪漫风格迥然相异的“现代风格”:推崇希腊主义,提倡肉体解放;反对传统道德,主张妇女解放;崇尚自由主义,赞成立宪制[注]考虑到拙文《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对白尔尼、海涅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以及“青年德意志”的整体状况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概言之,白尔尼和海涅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他们不仅被视为1830年前新文学即文学反对派最杰出的代表,而且被看作1830年后文学反对派即“青年德意志”的先驱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海涅的文学地位了然于胸而不知白尔尼为何许人物,但白尔尼不仅被当时的青年恩格斯奉为“德国自由的旗手”与“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4](P451),而且被后来的勃兰兑斯等尊为“新德意志文学的第一个开路者”[1](P31)。此外,在当时的德意志,尽管人们把海涅与白尔尼并置,但始终把白尔尼置于海涅之前,这主要是因为白尔尼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都远甚于海涅。
二
“白尔尼—海涅论争”与当时的“歌德论战”等其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论争一样,它既是德意志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所发生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是文学从歌德所声称的“艺术时代”转向门采尔、白尔尼、海涅等所断言的“政治时代”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白尔尼与海涅在“歌德论战”中所持立场的某些差异早已为两人的相关论争埋下了伏笔,那么两人之间的“短兵相接”则是双方就“歌德论战”中所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所展开的正面交锋,因而十分有必要首先对“歌德论战”的相关情况作扼要描述与分析。
解放战争胜利后,歌德及其作品在德意志的命运出现了某种逆转,各方对其人其作所持的态度、立场及评判标准大相径庭乃至水火不容,由此引发了一场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歌德论战”。简言之,以齐默曼(1782—1835)、恩色(1785—1858)、舒巴特(1796—1861)、艾克曼(1792—1854)、伊默曼(1796—1840)、赫林(1798—1871)等为代表的赞美者认为,歌德是天才的艺术家,其地位无可撼动[5](P60);歌德的反对者则持如下三种批判立场:自由主义的政治——艺术批判;保守主义的道德——宗教批判;折衷派的艺术赞美——政治批判。
沃尔弗冈·门采尔(1798—1873)和白尔尼是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确如勃兰兑斯所言,“在政治上进步的青年中,已开始在探究歌德的政治信念,用当代标准对它作出评价,把歌德描绘成一个‘贵族’,他对人民毫无感情,实际上也没有天才”[1](P67)。
白尔尼之所以对歌德持严苛的批判立场,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在解放战争期间,歌德对法军的入侵无动于衷;歌德从未想过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救助陷入苦难的同胞,而是躲在艺术的象牙塔中。不过,与门采尔对歌德的全盘否定不同,白尔尼始终承认歌德是艺术天才,他将批判的边界一直严格限定在歌德本人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等方面。此外,即使门采尔与白尔尼对歌德的“围攻”都是典型的政治批判,但两人之间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白尔尼对歌德的攻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能与门采尔的攻击等量齐观。白尔尼的攻击不是恶毒的,更不是卑劣的。它们与其说是勾画出了歌德,不如说是描绘了作者自己,但有时它们却也触动了这位伟人性格中的伤口。尽管它们清楚地表明了白尔尼在才智方面的狭隘性,它们却也是他的性格的纯真的明证。这些攻击并不能减低人们对歌德的天才的崇拜。用白尔尼一八三○年错误的政治标准去衡量歌德,同用一八七○年错误的政治标准去衡量白尔尼本人一样,两者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若是这样的话,那人们今天就会给他打上恶劣的爱国者的印记,正如他对歌德所作的那样。白尔尼蔑视歌德,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他对歌德的无知,人们是能够理解的,而不必受他的愤恨的影响。人们能够充分珍视他文章中的狂暴的激情和才智的跳跃和闪现,同时也不忘记在他的散文的那沸腾和闪光的瀑布上面,是广袤深沉的平静的海洋,这海洋就是歌德。”[1](P74-75)
如果说白尔尼等是从政治观念上对歌德作出了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愤怒“指控”,那么普斯特库亨格兰佐(1793—1834)等则是从宗教—道德维度对歌德进行“戏仿”式批判。1821年,普斯特库亨在 “假冒”歌德之名出版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这部“仿作”中主要是从虔信主义的道德观点、宗教观点批判“异教徒”歌德。在保守主义者普斯特库亨看来,歌德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泛神主义”不仅会危及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且会败坏社会的道德风尚。此外,他还认为席勒远比歌德伟大。尽管这些“臆断”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一部分右翼分子的共鸣,但也遭到了左翼阵营的严厉批判。比如,青年马克思在1836年题为《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的讽刺短诗中就以诗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辛辣嘲讽:
据说歌德实在叫女人们讨厌,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给老太婆念。
他只知道描写人的本性,
却不用伦理道德来遮掩。
他本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
而后再根据教义写他的诗篇。
歌德有时也能想美妙的东西,
可惜他忘记说:“那本是上帝创造的。”
把歌德如此高高捧起,
这样的做法实在离奇,
他的整个动机多么卑鄙。
哪篇作品可用来宣扬教义?
请问他有什么真才实学,
好让农民和教师学到一些东西?[注]详见马克思:《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740页。此外,歌德(1749—1832)本人当时是如何看待来自“左翼”与“右翼”的共同批判?比如,歌德在1825年5月12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二十年来,世人争论席勒和我谁更伟大。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社会上毕竟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第158页,洪天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再比如,艾克曼于1830年3月14日问:“人们责备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参加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歌德作了如下回应:“我的好朋友,我们不谈这点吧!这个世界很荒谬,它不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人们得让它说话和自便。我没有仇恨,怎么会拿起武器呢?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碰上那次事件,那么我肯定不会是最差的人,可是我当时已年过六十啦。……由于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攻击我的品行。他们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时而说我沉溺于肉欲,时而说我不信基督教,现在又说我不爱祖国和同胞。你认识我已多年了,对我非常熟悉,总该认识到这些流言蜚语意味着什么。不过如果你想了解我所遭受的痛苦,请读一读我的《克塞尼恩》,从我的回击中你就会认识到人们试图轮流使我失去生活的乐趣。”(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第477—478页,洪天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再比如,作为“青年德意志”的青年恩格斯在这场论争中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他在1839年7月30日致中学同学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写道:“席勒是我们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这已是定论。他预感到,法国革命以后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而歌德甚至在七月革命以后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当事件已近在眼前以致他几乎不得不相信某种新事物正在到来时,他却走进内室,锁上了门,以求安逸。这十分有损歌德的形象;可是革命爆发时(1789法国大革命),歌德已四十岁了,已经是一个定型的人了,所以不能为此责备他。”[注]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不难看出,恩格斯以“年龄”论歌德的政治取向的做法明显受到了歌德本人以及文巴尔克《美学运动》一书相关观点的影响。此外,1847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歌德的“两重性”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与精辟的论断。
作为折衷派代表的海涅既不认同普斯特库亨等的道德批判也不认同白尔尼等的政治批判。海涅在《论浪漫派》中对上述两种批判立场作了如下概括:“正统教徒对这位异教徒十分恼火;他们深怕他影响人民,怕他通过笑吟吟的作品,通过最微不足道的短诗把他的世界观灌输给人民;他们把他看成十字架的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这些运动中的人物所以不满意歌德,当然绝不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对他的非难,已如前述,是他的语言产生不出结果,是通过他在德国传播了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使德国青年变得清静无为,而这种影响对于我们祖国的政治复兴是根本抵触的。因此这个淡漠的泛神论者便受到了相互冲突的各个方面的攻击;按照法国人的说法便是:极右派和极左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歌德。”[5](P55)不仅如此,海涅对自己的基本立场作了明确论述:“我颇不满意门采尔先生批评歌德时的粗暴态度,埋怨他缺乏敬畏之心。我觉得,歌德毕竟一直是我们文坛的君王,倘若要把批评的刀斧架在他的身上,不可缺少应有的礼貌……歌德作为诗人,我从未攻击过,我攻击的只是他这个人。我从未指责过他的作品。我从来也没能在他的作品里发现什么缺陷,不像有些批评家,戴着精工细磨的眼镜,甚至连月亮上的斑点也看见了,这些眼光锋利的先生们!他们当做斑点的东西,其实是花木繁茂的树林,银光闪烁的河流,巍峨高峻的山岭,风光明媚的峡谷啊。再没有比贬低歌德以抬高席勒更愚蠢的事了。其实他们对席勒也绝不是真心诚意。他们一向赞美席勒,就是为了贬低歌德。”[5](P56-57)不难看出,海涅试图从艺术家歌德与现实生活中的歌德两个向度对其人其作的矛盾性作合理解释,有意识地把艺术肯定与政治批判两者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艺术维度为歌德辩护。
以上所述表明,无论是以门采尔、白尔尼等为代表的“极左翼”还是以普斯特库亨等为代表的“极右翼”,他们或者以政治的或者以道德的观点对歌德其人其作展开片面批判。正因如此,极左与极右两大对立阵营才会得出歌德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远离人民等相似论断,才会得出席勒远比歌德伟大等相同结论。究竟如何准确把握伟大作家与其所处的革命时代、政治时代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正确理解伟大作家与同时代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当时也是现在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
如果说“歌德论战”主要发生在1810年代至1830年代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阵营间,那么“白尔尼—海涅论争”则主要发生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的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与“歌德论战”不同的是,“白尔尼—海涅论争”不仅发生在两人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双方当时的支持者之间。换言之,如果说“歌德论战”的各方主要是围绕歌德的政治观、宗教观等问题展开,那么“白尔尼—海涅论争”则是志同道合者之间而非陌路者之间就彼此的政治立场、道德立场、文学立场等问题所展开的“诘难”即文学革命者之间的“交互审视”,双方支持者随后也围绕这些“诘难”展开激烈交锋。
从时限看,白尔尼与海涅两者之间的直接论争大致发生在1833年至1837年间。问题在于,究竟是白尔尼还是海涅率先挑起这场纷争的,[注]两人之间的论争集中反映在白尔尼《评亨利希·海涅》(1840年)和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中两部德语著作中。因语言能力限制,笔者不能直接阅读德文文献,只能从所掌握的其他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尽可能地勾勒出双方所争论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判断。比如,勃兰兑斯认为是海涅率先在1833年的《法国现状》中中伤了白尔尼,由此引发了两人之间的纷争,“自从白尔尼对海涅的作品和他本人熟悉之后,他一直对海涅抱有好感。一些年来,他在谈起他时甚至是怀着热爱。他尊敬海涅作为一个诗人所取得的成就,他特别看重的是海涅是为世界解放而工作的一支伟大的力量。对人们在他面前传布的有关海涅的流言蜚语,他总是以一个伟大的天性所具有的那种冷酷加以驳斥。他毫无可卑的虚荣心,人们经常把他的名字与海涅的名字相提并论,并把两人的才华和能力加以仔细地比较;当这种比较差不多总是有利于他时,他毫不在意。但是海涅在《法国现状》中伤害了他,他在阅读时感到极为不快。在《巴黎书简》的最后一卷里,他发泄了这种不快,虽说并不激烈尖刻,但确实用的是一种讥诮讽刺的形式;海涅成了这种讽刺的对象,并在为数不少的读者的眼里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品格的人”[1](P98)。不过,梅林则持与勃兰兑斯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梅林看来,七月革命前的白尔尼与海涅已被视为德国解放斗争中的狄俄斯库里即希腊神话中的孪生兄弟,两人关系尽管不密切但十分友好[注]梅林在《海涅评传》中指出:1827年11月,海涅在去慕尼黑的途中,在卡塞尔拜访了格林兄弟,在法兰克福拜访了白尔尼。详见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 译,第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是白尔尼在七月革命后主动挑起事端:海涅的《法国状况》“这本书使白尔尼找到了一个契由,来罗织造谣诬陷之词,把海涅套在里面达数年之久。……随着七月革命的爆发,当代的现实问题显得更加具体,两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势必立刻变得截然不同……政治和社会的矛盾越趋尖锐,海涅和白尔尼就越发疏远,那么今天一切材料俱在,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白尔尼是以最刻毒、最可恶的方式挑起这场争论的,而且多半是背着海涅搞的”[6](P175-177)。
本文无意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追问,这是由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首先引起争端而在于两人因何而争执,在于两人的争执为何能够演变为双方信徒乃至不同阵营之间的争斗乃至攻讦?从政治观、世界观、道德观、文学观、人格等诸多方面看,与白尔尼的“纯粹”“清澈”“如一”相比,海涅则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混沌”“多变”。比如,白尔尼在政治观上始终秉持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同一思想立场,而海涅则摇摆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这三种不同思想立场之间[注]与白尔尼性格的“单一”“坚定”“果敢”相比,海涅体现出了某种“复杂”“怯懦”“摇摆”。比如,海涅自己为了更好的生活,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但对作出同样改变的埃杜阿特·冈斯(1798—1839)进行责难。再比如,为了在慕尼黑大学谋取教职而与专制政府妥协;拟在巴黎办德文报而与普鲁士当局妥协。。总体而言,两人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看待诗人在政治上的不彻底性、摇摆性,如何看待诗人世界观的复杂性、矛盾性,如何看待文学与革命、艺术与现实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以今日的眼光看,海涅无疑是具有强烈政治倾向与批判意识的诗人,在政治上已十分激进了。但正如勃兰兑斯所论,由于作为政治家而非艺术家的海涅总是在贵族分子与民主革命者之间摇摆不定才导致白尔尼在《巴黎书简》中对其予以批判:“海涅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不彻底的,是软弱的。……海涅说,在他努力于博得民主主义者的好感时,德国的耶稣会——贵族党诽谤他,因为他勇敢地反对了专制主义;而为了取悦于贵族主义者,他同时又说,他顶撞了雅各宾主义,是一个极好的保王主义者,并且一直是一个有君主主义思想的人。”[1](P109)“白尔尼的愤怒的本质是在于他认为海涅这个人对党派观念不关心。 ……在我们今天, 说艺术本身就是它自己的目的, 这已是一句得到公认和多余的废话了。 而在那个时代, 人们却都相信这样的思想, 认为艺术应当服务于一种生活目的。 在当时德国的诗歌作品里, 不管它是具有较高价值还是只有较低的价值, 我们都能从中觉察到, 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促使作者拿起笔来。 甚至像海涅这样倾向性强烈的诗人, 比起同时代人(如白尔尼)中那些思想激进的人, 也只能说是倾向性不强的。 他们在反对他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虽然这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但却没有品格。’ 海涅在《阿塔·特洛尔》里对这句话进行了无情的嘲弄。”[1](P195)
在对白尔尼与海涅两人直接论争的问题实质作简要分析之后,我们再审视来自右翼与左翼尤其是双方信徒之间对这一论争所持的政治态度与思想立场。
右翼阵营对两人的关系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判断。比如,爱德华·迈尔在《声讨路德维希·白尔尼——置真理、正义和荣誉于不顾的巴黎书信者》(1831)的诽谤性文章中就把“‘白尔尼,海涅及其同伙’相提并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白尔尼是个犹太人,正如海涅和萨菲尔一样,是否经过基督教的洗礼,这点是无关紧要的……’”[7](P324)再比如,阿达尔贝特·封·博恩施泰特在1835年10月27日致奥地利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白尔尼和海涅生活在不共戴天的敌对情绪之中。后者在谈到前者时,除了最肮脏的称呼外再没有别的词汇了,妒忌是相互仇恨的主要原因。白尔尼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人,毫无疑问都更有价值……海涅和白尔尼从不交谈、从不见面,从不互相问候,说他们在一起工作,真是无稽之谈。”[7](P324)
左翼阵营对两人论争的认识也经历了前后不同的变化。谷兹科在《当代文学史稿》(1836)中坚称:白尔尼与海涅“共同倾向于一幅他们所梦想的自由图景……白尔尼,这个被德意志的鹰吞噬心肝的人,不是普罗米修斯。海涅是普罗米修斯,因为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诅咒诸神。白尔尼过于片面,而海涅则缺乏公正”[7](P325)。不难看出,这时的谷兹科把海涅置于白尔尼之上。
但是,随着白尔尼1837年的离世,更由于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的问世,左翼阵营对白尔尼的讴歌与对海涅的抨击就成了这场论争的显著特点。赫尔曼·马格拉夫在《德国当前的文学和文化时代》(1839)中对白尔尼与海涅两人的性格特质做了如下评判:“德国式的坚定性和抵抗能力在人们的个性中越来越不存在了……白尔尼还有一些,甚至还拥有一种性格的大部分内容,海涅却极少有首尾一致的沉稳性格,如果不说有些人的性格正在于没有性格的话……一个像白尔尼这样合乎道德的人,这个不妥协的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是不可能长时间和法国环形大道上的英雄海涅相处的……海涅很可能会认为,白尔尼在监视他所走的每一步,并把他的蠢行一笔一笔地记上黑账。”[7](P326)
1840年的谷兹科改变了他此前的判断,把白尔尼置于海涅之上:“白尔尼的最后著作使他在我们眼里表现得从来没有过的高尚和完美。当他写完最后一本小书离开人世的时候,甚至于他的敌人也喜欢上了他。而海涅先生的最后著作(即纪念白尔尼的文章)则向我们显示了完全陷在道德瓦解中的他。白尔尼不是诗人,他像预言家那样写作。海涅先生佯作诗人,却像一个流氓那样写作。白尔尼并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在信念的烈火中他钢铁般的性格锻炼得更为坚强。海涅先生遨游在谎言的大海之中。必将逐渐被蒸发到自负的‘金色虚无’中去。白尔尼与生者论战,与死者和解。海涅先生惧怕生者,只有等他们死后,才与之(如白尔尼)斗争。”[7](P326)
白尔尼去世后的第十年即1847年, 伯特·普鲁茨在《德国当代文学讲座》中对两人的自由观做出了高下立判的结论: “海涅想争得自由, 是为了享受它, 而白尔尼是要给人民争得自由。 海涅是吉伦特派分子, 白尔尼则属于山岳派, 海涅是梅菲斯托, 永远的怀疑者, 白尔尼是浮士德, 永远的奋斗者。 海涅身患时代的疾病, 如同可伯的流行痛疡一样。 而白尔尼, 在成千上万的病人中他是唯一健康的人。”[7](P327)
梅林在《海涅评传》(1911)中以希腊神话中的狄俄斯库里孪生兄弟来比喻白尔尼和海涅之间的关系, 此种比喻不仅被格·冯贝格在《论狄俄斯库里接受模式——关于对海涅和白尔尼的接受历史》一文(1987)中所沿用而且被他视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比较研究方法。 在冯贝格看来, “整个公众对1840年海涅发表的纪念白尔尼的文章报以强烈愤慨,其原因在于一种旧的、 对海涅适用良久的接受模式, 这就是‘与白尔尼类比’的模式。 通过这篇纪念文章, 海涅本人使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自己。 ……这里也以另外一种方式证实了作为一种接受模式通常具有的属性。 首先他们两人是相互联系的, 其次他们又是互相对抗的。 海涅的对手们得意洋洋, 因为海涅的卑劣行径已经公开化, 甚至他的朋友也认为他这样做极为过火。 但是, 海涅的那篇最终使两人之间的对比公开化的纪念白尔尼的文章1840年发表之前很久, 即从二十年代以来, 这种狄俄斯库里模式, 也称为‘敌对的兄弟’的模式, 已经被人们运用了。”[7](P323)
四
法国七月革命后,海涅与白尔尼都自愿流亡到巴黎这一革命之都,以便近距离观察革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革命之子”。海涅在1830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话语,犹如闪亮的投枪,嗖嗖地直飞九天云霄,击中那些潜入至圣至神之地的虔诚的伪善者。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6](P173)白尔尼写就了在德国各地影响巨大的六卷本《巴黎书简》,“特别是这部书的第一卷达到了他作为作家所能达到的顶峰”[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在1832年5月的汉姆巴赫宫集会上,白尔尼被奉为“德国自由的捍卫者”。。由于鼓动革命,该书一出版就在普鲁士等邦国被查禁。客观而言,就两人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看,白尔尼远在海涅之上,但就此后的文学影响力而言,海涅则远在白尔尼之上;白尔尼在当时赢得的多是赞誉而海涅得到的多是“批判”,与此相反,海涅在后来的岁月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礼赞而白尔尼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批评”。本文接下来将选取青年恩格斯、马克思等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及观点并按照时间先后对论争所关涉到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与探讨。
在“白尔尼—海涅论争”中,青年恩格斯坚定地站在了白尔尼一边。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青年恩格斯的心目中,白尔尼若是“天神”那么海涅则是“凡人”。白尔尼的人格特质以及《戏剧丛谈》《巴黎书简》等论著无疑在青年恩格斯从文学政治到哲学政治再到社会政治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独特的作用[注]详见拙文《青年恩格斯思想视域中的白尔尼因素》(载《复旦学报》2018年第4期),本文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青年恩格斯是激进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还未完全接受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更不是共产主义者。。青年恩格斯在《评亚历山大·容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1842)一文中写道:“这种争吵在海涅论述白尔尼的书中达到了顶点,而到了使人厌恶的庸俗程度。……海涅评论白尔尼的书是历来最不像样的德文书。”[8](P453-454)
与青年恩格斯相反,马克思则坚定地站在了海涅一边[注]马克思和燕妮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同年底,马克思与海涅在巴黎相识并成为好友。1844年9月22日,海涅从汉堡给巴黎的马克思写信,希望能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部分内容在巴黎的《前进报》上刊出,同时请马克思写一个引言。梅林认为,“海涅确实同马克思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海涅的讽刺诗达到了一种使之在世界文学中永远具有突出地位的高度,这里肯定也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具体见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译,第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846年4月5日左右,马克思自布鲁塞尔致信客居巴黎的海涅:“前几天,我偶然发现一本诽谤您的渺小作品——白尔尼遗留下来的书信集。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我决不会想到白尔尼会这样愚蠢,狭隘和无聊。而谷兹科的后记等等更是贫乏的拙劣之作!我将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写一篇详细的评论介绍您评白尔尼的那本书。基督教德意志的蠢驴们对待您这本书的这种粗暴态度在文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少见的而德国的任何时期粗暴的例子却是屡见不鲜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一评论。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为好友海涅的遭遇而鸣不平。
与以上两人的各自选择不同,勃兰兑斯(1842—1927)在《青年德意志》(1894)中努力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性立场。他的相关阐释都是在尽力调和白尔尼与海涅之间业已存在的思想差异,“提到高度上看,这是以对真理的尊重为一方,以对形式与艺术的崇敬为另一方相互之间的冲突”[1](P99)。
不过,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在《纪念海涅》(1906)、《海涅评传》(1911)等文中打破了勃兰兑斯的“平衡”,想从根本上为海涅“正名”。梅林指出:“人们之所以对海涅没有作出公允的评价,原因是海涅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一无二的、无法比拟的地位这一事实。在一个世纪里依次更迭的三大世界观,其色彩和形式在海涅的作品里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艺术形象里得到了完整的统一,像这样的诗人我们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在他身上这三种世界观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而是同时表现出来的,如果只从其中的一个观点,即只从浪漫主义,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海涅,就会觉得他身上充满了缺陷和矛盾”[6](P141-142)。梅林认为,对海涅的作品“不是从政治倾向上,而是从历史的美学角度——用资产阶级观点办不到,但用无产阶级观点则可以做到——来加以解释,就是给德国工人阶级的绝妙的礼物”[6](P144)。因此,由梅林的对比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白尔尼是一个诚实的、但却是颇为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典型……海涅则不同,他具有一种更为细致、更为丰富的气质,只要不把自己抛弃,他是绝不会抛弃歌德和黑格尔的,他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如饥似渴地扑向社会主义学说,把它当作精神生活的新源泉。……我们可以原谅白尔尼,因为他根本不理解海涅。”[6](P176-177)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与梅林的观点相仿。他在《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1935)一文中指出,由于青年恩格斯对白尔尼过于尊崇、对海涅过于贬抑,由此导致他对两人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在卢卡奇看来,青年恩格斯“这时候对浪漫派的批判,从本质上说,还没有超过白尔尼和‘青年德意志派’的水平。因为他片面地赞成白尔尼,并且对海涅抱有成见,所以他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青年恩格斯的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使他一般地能够合理、公正地判断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唯一的例外是对海涅的判断,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白尔尼认为海涅‘背叛’了民主,这种偏见决定了恩格斯对海涅的判断。恩格斯的这种态度转变得比较晚,一直到他在英国逗留期间,也就是当海涅由于与马克思有了友好交往,态度更加激进,而恩格斯对此有了印象的时候。……青年恩格斯的社会见解的局限性,在文学领域内,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白尔尼所作的过甚其词的评价上。甚至当他由于深入研究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脱离‘青年德意志派’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对白尔尼的崇拜”[9](P4-6)。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梅林与卢卡奇主要是从内容层面来论证海涅比白尔尼更深刻,那么形式主义者韦勒克则主要是从艺术的独立性层面来肯定海涅。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1955)中毫不犹豫地把海涅置于白尔尼之上,“白尔尼,偏激的报章作家和随笔家,是一位心直口快的道学先生和开明的教条主义者。……海涅通常和他并称,但是两人相去霄壤。白尔尼后期曾攻击海涅。海涅始终是一位诗人,他始终未曾失去对艺术本质的把握”[10](P256-258)。“海涅批评的真正重要性,倒是在于他理论立场上出人意表的含混态度。……海涅在理论上谴责的只是倾向诗,而维护着艺术的自主性。‘艺术不应像侍从一般,为宗教或政治服务;艺术本身即为其终极目的,正如世界便是其自身目的。’……他多次毫不置疑地否认艺术的独立性。他称赞‘青年德意志’作家,他们‘不想把生活与写作区别开来,他们不想使政治脱离学术,艺术,宗教,他们同时是艺术家,护民官,传道士’。面对当代作家,海涅大多是用思想意识的准绳来进行评判。”[10](P261-262)
此外,国内也有个别学者表达了对这一论争所持的基本立场。比如,张玉书在《战士海涅》一文中认为:“白尔尼被认为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反对白尔尼就伤害了一大批人。海涅和他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极左、反对偏激的斗争,然而这点连恩格斯也不能谅解。”[11](P447)
冯贝格认为,“海涅—白尔尼”“这种模式是2500年来欧洲思想史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方法……十九世纪初,在有关海涅和白尔尼两人的接受问题上,公众中出现了这样一种需求,它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艺术时代的终结’,也产生了反对这一消极观点的积极主张。”[7](P330-331)
五
尽管“白尔尼—海涅论争”这一事件本身已成为了历史,但论争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与细究。
首先, 我们怎样才能正确看待“白尔尼现象”与“海涅现象”? 历史的吊诡之处不在于白尔尼与海涅俩人的座次被调换, 不在于前者走进了历史而后者走出了历史, 而在于两者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血与火的时代, 白尔尼们坚毅果敢地担当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他们真诚地把文学视为时代生活的镜子, 把文学视为改变社会的有效手段。 从这个意义讲, 他们及其作品只属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时代的命运就是他们自身及其作品的命运。 “在当时站在前列的作家中, 几乎没有一个人像路德维希·白尔尼那样被置之一旁不加理睬的了。 他写的题材都已陈旧, 只有那些对作家的人品性格感到兴趣的人才去读他的那些篇幅不长、 用报纸社论或书信形式写出的散文作品, 这只是为了了解他的表现形式或是了解他在处理那些题材时的精神状态。……他那种温暖着同代人的火一般的思想, 现在看来就如同用长矛去攻打堡垒和宫殿的唐吉诃德的热情一样。 然而, 他为德意志民族新铁器时代的钢铁建筑的产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的火把矿砂冶炼成铁水, 社会的新的箭矢就是从中锻制而成的。”[1](P38-39)
经过岁月洗礼后,一方面海涅们在政治等方面的缺陷会程度不一地被淡化,另一方面他们巨大的艺术才能则会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肯定,他们的作品会成为跨越时代的艺术丰碑。“一个时代有着数量众多的作家,然而,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在他们中间却只有极少数人还能拥有读者,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在不可胜数的作品中,也只有个别的作品还被读者所接受。”[1](P33)
其次,“白尔尼—海涅论争”其实关系到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学批评的政治之维与审美之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说歌德本人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持审美优先立场,那么白尔尼则持明确的政治优先立场,海涅则摇摆于两者之间。
歌德在1832年3月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一个诗人一旦想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他就必须献身于一个政党;一旦加人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无偏见的总揽能力告别,把目光短浅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你知道我一般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工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鄙薄地拒绝干预党派之争。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你注意看吧,作为政治家的乌兰德终会把作为诗人的乌兰德吃光。当议会议员,整天在摩擦和激动中过活,这对诗人的温柔性格是不相宜的。他的歌声将会停止,而这是很可惜的。”[12](P593-594)
与此相反,白尔尼的文学写作及其批评属于典型的政治写作与批评。“白尔尼缺少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思想,他公开承认这一点。……人们因白尔尼对德国的命运悲剧采取激烈的敌对态度而十分赞赏他;在那个时代,这种悲剧在德国舞台上泛滥成灾,愚弄着人们的感情;但人们很容易看到,他的反对并不是从审美观点出发对这些作品所进行的批评,他是从道德的或宗教的角度出发去批评的。”[1](P62-63)
如果艺术家是诗人歌德的自我身份认同,如果革命家是剧评家白尔尼的自我身份认同,那么革命者—贵族则是诗人海涅的双重身份。换言之,强调艺术有其目的,强调艺术有其独立性,强调政治诗必须有诗意,这是海涅与歌德的共同之处,同时也是他们与白尔尼的最大不同;歌德有意疏离政治、自觉远离革命,海涅则积极介入政治、主动投身革命,这是歌德与海涅和白尔尼两人的最大不同。客观而言,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固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最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样式之一”[13](P133),但审美批评、形式批评同样是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样式之一。回溯历史,深刻思想与优美形式的完美融合是所有作家的写作理想,但这样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家的文学写作要么偏向思想方面要么偏向形式方面。同理,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很难做到既是政治的又是审美的,这里固然有个人才能、个人选择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时代自身的要求所致。比如,青年恩格斯针对普拉滕认为自己理智的产物就是诗这一观点作了如下评论:他将更加远离歌德,“他的思想也日益接近于白尔尼……他的思想和性格在这些歌词里比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更有力和更突出地代替了诗意。……凡是向着普拉滕提出其他要求的人,对这些波兰之歌是不会感到满意的,然而,凡是抱着这些期望拿到这本书的人,在感到书中缺少诗的芳香的同时,却会由于在崇高性格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许多有巨大影响的高尚思想,以及在序文中恰如其分地表达的‘伟大的热情’,而得到充分的补偿”[8](P104-105)。总之,无论是政治批评还是审美批评,都应从时代生活面临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始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做不到批评的政治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有机融合时可以有偏重但不能有偏废。
再次, 文学批评应始终恪守批评的边界与限度。 无可讳言, 海涅无论在1820年代与普拉滕的论争中还是在1840年《评路德维希·白尔尼》的著作中确有人身攻击之举,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注]具体见梅林:《海涅评传》《论文学》,张玉书等译,第171、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第217—2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真正的文学批评是求真、 求善、 求美的, 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追名逐利, 才会谋取话语权; 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真诚的、 真挚的、 真实的思想对话与情感交流,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或恶意诽谤或阿谀奉承他人及其作品;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理解的、 同情的批评, 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居高临下地无情宣判。 青年恩格斯的批评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他在《现代文学生活》(1840)一文中指出: “无论批评有多么大的摧毁量力, 我们相信, 仅有批评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8](P126)“倍克是个诗人, 在对他提出批评, 甚至提出最严厉而公正的指责时, 也应当顾及他未来的创作。 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应当受到这种尊重。”[8](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