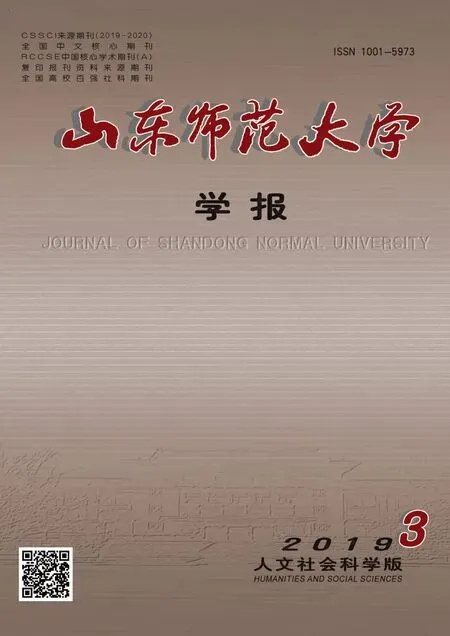人生遭际与诗风转变
——以西晋诗人刘琨为例*①
2019-02-22张爱波
张爱波
( 山东交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250357 )
在历史上,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处于内战纷争、外族入侵、生灵涂炭之际,本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然而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的反抗反思中,往往最能产生极其伟大的作品,唤起人们的共鸣和神圣感,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文学史现象。如屈原放逐在外而创作的《离骚》、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等等,都是诗人在家国蒙难时所创作出的千古绝唱。其中,西晋著名爱国诗人刘琨及其诗作也是典型代表之一。刘琨前期是文坛风流名士,作品注重艺术创作技法完善和个人情感抒发,后期经过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融入社会生活,深刻体验到民族荣辱和家国兴衰,从而超越名士风流的“个人化体验”,进入末世英雄的“社会化体验”。这种地位和生活的巨变,使刘琨的内心经历了巨大的侮辱和难以言状的痛楚。他后期的诗作,或感叹身世,或眷恋往昔,或托物言情,或直抒胸臆,把一个末路英雄的民族情、亡国恨表现得凄戾悲壮而极具感染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
刘琨早年颇具名士风流,根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所载,刘琨生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71年),卒于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公元318年)。《晋书·刘琨传》:
琨少得俊朗之目,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
西晋时期士族制度确立,西晋初期颁布的户调式包括按官品荫族、荫客和占田,其中特别是荫族特权,确定了士之为族,士族的名称也在此时开始出现。[注]对于士族的形成时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认为,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但是我们认为:对于这个称谓,在两汉史中无明载,士与宗族的结合比较符合本文中所谓的“世族”,因为余英时文中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势族世族的概念而通用之,所以这种观点本文没有采用。本文观点参考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文中还举了史例加以佐证,较为符合客观史实。同时,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士族的世袭特权,从而促使士族制度在西晋初中期形成、发展起来,并对这个时期的清谈任诞的士风产生了很大影响。年轻的刘琨正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善于交游且富有文采,参与权戚贾谧为首的“二十四友”文人集团,与当时石崇、陆机、潘岳等士族名士交游唱和,“少得俊朗之目”,以“雄豪著名”,“文咏颇为当时所许”,传有“洛中奕奕,庆孙越石”[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29页。的美誉,这些都使刘琨名声大增,仕途也屡屡升迁。
刘琨交游名士,但与石崇等人热衷于清谈任诞不尽相同,他胸怀大志,豪侠气盛,更重志士。刘琨26岁初任司隶从事,与祖逖结识,史称祖逖“性豁荡,不修仪检”,为人慷慨任侠,与刘琨意气相投,二人“情好绸缪,共被同寝”,闻鸡起舞,相约报国,“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注]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4页。。不久,“二十四友”文人集团溃散,“八王之乱”开始,刘琨分别征战效力于赵王伦、齐王冏、范阳王虓、东海王越等人帐下,备受诸王的赏识任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年仅35岁的刘琨封广武侯,拜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可谓权高位重,显赫一时。也就是说,在刘琨35岁以前,他的生活是游历权贵之间颇得盛誉,周旋征战于诸王之间而获得高官,因此,刘琨的前半生是风流名士和政坛明星。
从永嘉元年往后,刘琨奉命独保晋阳,开始了抵御异族入侵的战斗。这一年,既是西晋王朝在异族入侵下风雨飘摇的开始,也是刘琨由一个风流名士真正转变为民族英雄的的转折点。这个战乱的时代赋予了刘琨辉煌腾达的前半生,也把悲壮与责任留给了他的后半生。
刘琨的后半生是充满坎坷和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产生的一个原因来自于无可挽回的晋末乱世。西晋王朝经过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诸王混战,内耗严重,民生凋敝,整个国家实力已经完全无法抵御匈奴的进军了。这在刘琨前后上的表章中可以看出:
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注]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0页。
在赴并州上任的路上,刘琨目睹战争惨状。到达壶口关一带,他看到因为战争人民流离失所,十不存二,更有灾民鬻妻卖子,生离死别,白骨横野,惨不忍睹。虽然西晋朝廷接受了刘琨的请求,拨予粮物,但是这相对于当时民生凋敝、僵尸蔽地的残酷现实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从京城享乐的环境中走出,刘琨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非常清楚这种极端不利的战争形势。
刘琨怀着以死报国的决心坚持孤军奋战。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刘琨上请求北伐之表曰:
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枭,臣无归志,庶凭陛下威灵,使微意获展,然后陨首谢国,没而无恨。[注]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4页。
西晋东北八州,石勒已经占领七个,只剩并州城。这时的并州,经历了战乱、饥馑,人户不到两万,荆棘成林,豺狼满道,仅为一座空城。刘琨任并州刺史后,一边要与并州的匈奴等少数民族展开激烈的争夺,一边又要与东部的王浚进行较量。在这种条件下,刘琨一面安抚百姓,招徕流民,一面加强军事防御,抗击流寇。但其内心,却已经作出了“陨首谢国”的准备。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词·刘中山集》中云:“……夫汉贼不灭,诸葛出师,二圣未还,武穆鞠旅,二臣忠贞,表悬天壤。上下其间,中有越石……”[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3页。他将刘琨与三国诸葛亮、宋代岳飞相比,三人所处时代不同,但是为家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是一脉贯通、异代相承的。
刘琨的人生悲剧性还源于其个性的原因。史称“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注]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0页。,这种“颇浮夸”在西晋承平时代对他早年的辉煌有过很大帮助,但在充斥着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却是为害非浅的。刘琨有两次重大失败都与其个性浮夸有关。《晋书·刘琨传》记载其中一次曰:
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河南徐润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贵势,琨甚爱之,署为晋阳令。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注]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1页。
刘琨善于怀抚,但是短于控御,名士意气,只能一时聚友,却不适合并肩为战,因此其部队“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刘琨不善用人,还表现在他不纳良谏,难辨忠奸。河南人徐润因精通音律,刘琨非常喜欢他,就任命他为晋阳县令。但“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奋威将军令狐盛数次进谏罢免徐润,刘琨不听忠言,反而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杀掉令狐盛,致使令狐盛子令狐泥叛归刘聪。上党、太原二郡郡守叛归刘聪,刘琨实力大损,不得不放弃晋阳根据地。后来刘琨又因为不听良谏,一意孤行深入乐平,中了石勒的埋伏,只好归依鲜卑段匹磾,最终为段所害,身死异域。
纵观刘琨的时代和他的一生,异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刘琨挺身而出,一脱风流名士的超然洒脱,举起抗击外虏的大旗,无奈生不逢时,他所处的晋朝风雨飘摇,无力相济,他所坚守的晋阳,三面受敌,孤城难支;他投奔段匹石单,段却听信谗言,反手相残,这一切都使刘琨壮志难酬,他只能长叹“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不仅是报国无望的痛惜,更是其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的真实写照。
二、悲壮诗风的思想艺术感染力
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使刘琨诗歌体现出一种与当时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历数西晋著名诗人,刘琨没有被列入“张潘左陆”之中,这当然不是刘勰的疏漏,而是刘勰已经完全意识到其创作风格与西晋诗坛“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风格不同。在《才略篇》中,刘勰指出:“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注]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5页。关于刘琨特殊人生遭际之下形成的诗歌风格,钟嵘《诗品》、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陈延杰《诗品注》、刘熙载《艺概》等都对此有专门评论,其中以刘熙载《艺概》评论最为贴切:
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注]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4页。。
刘琨诗歌具有壮美的特点,但在其“壮”中更多的是夹杂着一种“悲”的情绪,这种“悲”正来自于他从风流名士历经家国之恨而成为末路英雄的悯世悲情。
统观刘琨诗作,其前期较少而且大多散失,后期仅存数篇,《隋书·经籍志》有《刘琨集》9卷,别集12卷。《旧唐书·经籍志》及《宋史·艺文志》只存集10卷。而清《四库全书》已不见著录。今所传者,只有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所辑的《刘中山集》。其《题辞》云:“晋刘司空集十卷,在宋时已多缺误,今日欲睹全书,未可得也。”[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43页。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刘琨诗4首:《扶风歌》“朝发广莫门”、《扶风歌》“南山石嵬嵬”、《答卢谌诗》《重赠卢谌诗》。其中《扶风歌》“南山石嵬嵬”借南山松树之口抒发被砍伐雕琢之苦,并无多大深意。因此,能体现刘琨悲壮诗风的主要有《扶风歌》“朝发广莫门”、《答卢谌诗》《重赠卢谌诗》3篇诗作,这些作品体现着刘琨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末路的人生际遇。
(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真正能代表刘琨悲壮诗风、体现忧国忧民爱国情怀的当属《扶风歌》“朝发广莫门”,此诗作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刘琨从洛阳出发到并州上任刺史的路上。西晋后期外戚专政,引发“八王之乱”,司马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中。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匈奴刘渊首先起兵造反,西北各族也纷纷起兵,中国北方进入“五胡乱华”时期。连年战争,使原本安居乐业的人民国破家亡,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刘琨目睹此景,毅然放弃了早期风流名士的清谈任诞,从黄老与世无争,走上儒家济世救民、立志报国的道路。《扶风歌》就创作于此时:“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废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四《杂歌谣辞》一题中作《扶风歌》9首,实际上是四句一解,凡九解,当为一篇,关于此歌的写作背景,陈沆论述较为详细:
集中扶风歌九首。盖以两韵为一首,即乐府四句一解之例也。……考永嘉元年。以琨为并州刺史,……即此诗所咏也。[注]陈沆:《诗比兴笺》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页。
这首诗集中描述行军途中所见山河破碎的悲惨景象,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这些是通过景物描写、抒情和议论等各种手法体现出来的,如诗中“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等一系列景物描写,生动地体现了行军途中人迹全无、鸟兽横行的凄惨情景,为全诗笼罩了一片悲郁的气氛。而满怀离别之苦的诗人面对如此惨状,心中更是无限悲愤,“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此种直接抒发情感的诗句不断地来回咏唱,反复出现,不断把诗歌推向悲伤的氛围之中。在诗歌的结尾,他直接议论,以李陵自况,表达出对将来前途的无限忧虑。整首诗歌始终笼罩在“悲”的氛围中,但却“悲”而不“哀”,在其以大开大合的手笔描述山岳宫阙中,在其慷慨激昂、拍案长啸的自我形象刻画中,我们都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股悲壮之气纵横诗间。王钟陵曾经这样评价此诗:“《扶风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小而言之,它是刘琨在新的生活经历中诗风转变的结晶,因了这种转变,刘琨方才获得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大而言之,这是历史开始进入‘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之际,中国诗歌所发出的第一声沉重凄戾的哀音!”[注]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53页。这个评价从个人人生遭际到历史战乱纷争的角度出发,充分肯定了刘琨《扶风歌》的文学意义和文学史意义,可谓千古会意、历史认同之语,也揭示出刘琨及其诗歌不泯众俗、流传后世的原因所在。
(二)英雄末路的人生遭际
建兴三年(公元316年)十一月,刘曜围攻长安,愍帝开城纳降。因攻打石勒失败,刘琨穷蹙难守,不得不率领残众,前往幽州投奔段匹石单。段是鲜卑族首领,起初很推崇刘琨。二人曾结为婚姻,并歃血同盟,约为兄弟,以图后举。但后来段匹磾听信其弟谗言,囚禁刘琨,最后矫旨将其杀害。“出师未捷身先死”,一代英雄末路于此,让人不胜唏嘘。卢谌为琨姨甥,曾是他的故僚,当时任段匹磾别驾,据《晋书·卢谌传》云:
琨为司空,以谌为主簿,转从事中郎。琨妻即谌之从母,既加亲爱,又重其才地。建兴末,随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领幽州,取谌为别驾。[注]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9页。
刘琨、卢谌二人相契,又同依附段匹磾,此时的刘琨将人生遭际融入诗歌,与卢谌往来赠答,抒发英雄末路的悲壮之情,《答卢谌诗》和《重赠卢谌》即是此时之作。
《答卢谌诗》为四言八章,诗歌的一、二章首先以“火燎神州,洪流华域”之句展示了天翻地覆的乱世之景,笔力恢弘,纵横开合。第三、四章以沉痛的笔触叙述了自己和卢谌在战乱中父母被害、家族覆亡的惨痛。其后的五、六、七、八章表达了卢谌之去己而为段匹磾的别驾的不舍和欣慰,其中“茂彼春林,瘁此秋棘”一句既表达了自己对于卢谌之去的不舍,同时也为卢谌托身得所而欣慰,并鼓励卢谌戮力王室、“竭心公朝”。整首诗从时代的大处着笔,落实到个人的英雄末路的人生遭际,而在宣泄时代个人之痛后,又能重整心情,荡开眼光,在激励卢谌的过程中也不断激励自己,整首诗贯穿着一股悲而复壮的情绪。王夫之盛赞此诗“结构奇绝,神龙得云”[注]《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一四)《古诗选评》,长沙:岳麓出版社,1992年,第601页。,正得越石运神笔抒悲壮情怀之妙。
《重赠卢谌》是刘琨的绝笔之作,也是最能代表刘琨诗歌风格的作品。《晋书·刘琨传》记载刘琨为段匹磾所拘杀害之前,自知必死,但神色怡如,写了《重赠卢谌》一诗:“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茍能隆二伯,安问党与雠?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刘琨少年得志,半生戎马,期望如太公望、邓禹、陈平、张良、狐偃、管仲等人,得遇明主,建立永世功业。然而,时运多舛,内有八王乱政,外有五胡乱华,中原帝国大势已去,倏忽之间“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使命尚未实现,杀戮已到眼前。“西狩”“获麟”,指鲁哀公西狩猎获麟之事,诗人借用此典,既感慨自己功败垂成,更抒发了一片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诗歌结尾以秋风摧落花实、狭路翻车架、马惊折木辕等一连串的比喻,表达了人生终有一死,但功业未成却身陷囹圄、家国难报的悲愤苍凉。最后一句“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可谓“诗眼”,千回百转之后,诗人只能面对今日英雄末路的悲愤遭际,将一生豪情壮志消磨其中,化为绕指之坚刚。明代王世贞曰:“余每览刘司空‘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未尝不掩卷酸鼻也。”[注]罗仲鼎:《艺苑卮言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123页。这种阅读感受正揭示了历代读者对刘琨诗歌英雄末路的同情共感,而刘琨在感怀自己功业未成时依然不忘鼓励卢谌继续报效国家,于英雄末路之中却不泯爱国情怀,这也正是他的诗歌最感人之悲壮风格所在!
三、刘琨诗风转变所体现的普遍意义
刘琨诗歌悲壮诗风的转变与成功流传,主要源于他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风流名士的学习交游是其作为个体的文学艺术积累,后期的战乱则激发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促生了其悲壮诗风的转变形成,在诗歌艺术上把个人文学体验升华为社会精神共鸣,从而具有了普遍的文学史意义。
(一)从个体角度来看,诗人只有深入社会民生才能保持不竭的创作源泉
诗人只有走向社会底层,切身体验民生疾苦,才能有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此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刘琨在《答卢谌诗并书》中明确地表达了在面对现实时自己思想的转变: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塊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1页。
刘琨少年时崇尚老庄,爱慕阮籍,不问人事,尽情潇洒。这时的刘琨,不过是一个名士子弟,毫无文学建树,空有清誉之名。历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兵荒马乱之后,他目睹身受了人民的苦难、家国的衰亡,这种体验使他倍感痛苦,坐行之间一刻难忘。他完全脱离了为文造文的矫情造作,悲愤的心情可能未及讲究遣词造句,但却句句深沉,汩汩而出,正面现实,直指人心,进入了我手写我心的创作境界。《扶风歌》《答卢谌诗并书》《重赠卢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云:
刘琨……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注]章太炎:《国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35页。
章太炎明确指出刘琨诗歌之气“抗浮云”“比金石”的悲壮之风,正来源于他把自己的痛苦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联系一起,与《诗经·国风》中对人民生活的关注与同情可以相提并论,都充分体现了诗人从社会现实中汲取不竭创作源泉的艺术规律,这个解读是很深刻的。
(二)从社会角度来看,只有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作品才能被社会所认可
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是对现实的艺术化再现,诗歌创作只有走出小我的感受,拥抱社会大我才能完成艺术创作的升华,也只有与时代相关的作品才更具有普遍意义。在西晋一代,诗坛群星闪耀,涌现了张载、陆机、潘岳、左思、刘琨等“太康群英”,更有“二十四友”交游唱和,但是随着历史发展,这些人的作品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脍炙人口的更是少之又少。刘琨和与他时代相近的左思、郭璞的诗歌之所以广泛流传,其原因就在于其充满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愿望。左思一生报国无门,虽然没有为国征战,但其《咏史诗》系列塑造了一位国有战事则驰骋疆场,以绝世之才能谈笑定乾坤,而功成以后长揖归田庐的理想人物,并以此自况自励。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而论现实,通过飘渺的仙境构筑宏大的诗境,将对家国的忧虑和自身处境的悲慨融入其中,凝聚成极具张力的时代诗歌艺术特色。他们的诗歌内容具有时代普遍意义,诗歌艺术风格或清壮、或悲壮,都与刘琨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而得到社会认可接受而广为流传。
(三)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伟大的作品无不具有传承发展的文学史意义
抒发个人情感之作和庙堂之作虽然也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但是真正伟大的诗歌作品大多具有承上启下传承发展的文学史意义。钟嵘《诗品》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注]钟嵘:《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页。
从文学史来看,西晋诗歌上承建安风骨的气韵和力量,下接东晋玄言诗谈玄论理,在唐前诗歌史上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随着士族制度的确立,清淡任诞风气的形成,西晋诗风逐渐脱离了建安风骨,更倾向于华丽辞藻和铺张对偶,形成了轻绮华靡的诗风,内容主要是交游唱和拟古乐府诗,更有四言诗,追求庙堂气,缺乏深沉的个人感情和博大的家国情怀。青年刘琨混迹“二十四友”,沉迷“金谷”交游,诗歌创作毫无建树。经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后,刘琨有了与建安诗人和后代的边塞诗人共同的战场经历,他的思想在战争中得到历练和升华,诗风巨变而为悲壮之风,一跃当时轻绮之气,直追建安风骨。其《扶风歌》悲风、涧水、浮云、归鸟所共同构建的战场惨状与曹操《蒿里》《七哀诗》异代相通。无论是曹操的“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还是刘琨的“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读之皆令人涕下。而英雄末路的刘琨,对时不我待、功业难酬的感慨,不正是暮年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拔槊独舞的场景再现?可以说,刘琨以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悲壮的诗风继承了建安风骨,成为转移时代风气的诗人。刘琨“左手弯繁弱弓,右手挥龙泉剑”的慷慨激昂的诗人气质还对后世盛唐边塞诗产生了启迪影响,唐代诗人如高适《蓟门行》、王昌龄《塞下曲》、刘弯《出塞曲》等名作中,无不饱含家国情怀,感情真挚,激昂悲壮,直抒胸臆。陆游在《夜中偶怀故人孤独景略》中云:“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正是对刘琨及其诗歌所具有的时代传承与感召力的极高评价。
总之,刘琨诗歌风格是悲壮的。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他的人生遭际导致了其诗风巨变。他在并州孤独战斗十数年,血与火的考验涤荡了他的浮华任性,生与死的博弈强大了他的内心。从一个士族子弟成长为一个真正能够驰骋疆场的英雄人物,刘琨对于西晋中后期这个战乱悲怆的时代有着最为深刻的感受,他的诗歌所抒发的那种源于现实的爱国情怀和悲壮气概,体现出一种英雄的末路之悲。这种悽戾之词与悲壮之风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更对后世盛唐边塞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为历代所敬仰,体现了艺术创作根植于现实的普遍意义。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社会,中国的文士多缺少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正是历代尤其爱重刘琨其人其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