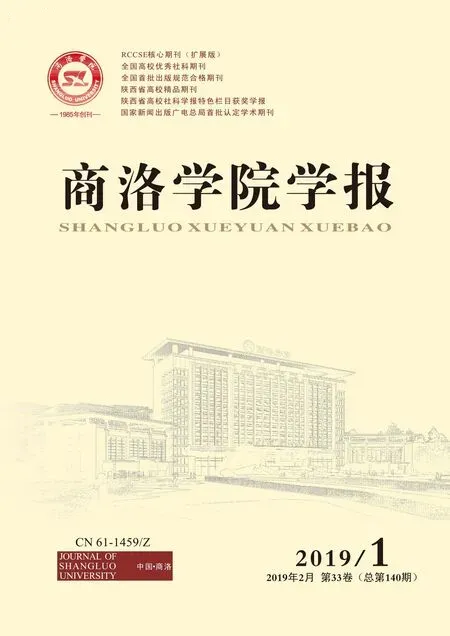徐大椿《洄溪道情》研究
2019-02-21武明慧
武明慧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道情,是道教徒在宣传教义和募斋化缘时所演唱的一种含有特殊意义的道歌,言辞浅白、通俗易懂,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用渔鼓和简板伴奏,集抒情、叙事为一体的民间说唱。道情最迟在南宋时期形成,至元代发展大盛。清代道情发展受到时调小曲挑战,生命力下降。郑振铎[1]认为,清代道情衰微,当时有三位作家扭转了这个局面,激起了道情的复兴。这三位便是“复活了这个体裁”的郑燮、徐大椿和金农。
当前学界对徐大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医学成就方面,徐氏的文学成就尚未引起关注,研究成果寥寥。仅有的几篇针对《洄溪道情》的研究论文,主要探讨的是其思想内容。陈泳超[2]重点论述了徐大椿以道情为诗文的追求及对以生活感慨入诗的表现;车振华[3]则认为《洄溪道情》不仅扩大了道情的题材,更是以儒家警世教化思想为主,半为警世之谈,半写闲游之乐;钟微等[4]认为《洄溪道情》中除古来多见的醒世游闲之作外,还增添讽谏时事、悼亡亲友、恭贺赠送、游览书画等大量内容,实为半儒半道之作。此外,黄莹[5]从戏剧戏曲的角度,对徐大椿的曲学生涯、曲论思路和制曲追求进行了整体观照。本文旨在分析《洄溪道情》在曲调、题材和内容方面对以往道情的继承与发展,在比较中明确其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
一、徐大椿与《洄溪道情》的创制
文学创作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道情发展亦如此。如果说元朝的统治为道情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那么清朝则恰好相反。为清除异类,清朝统治者极力干预曲词的创作和演唱,从作曲到唱曲,甚至对民众听曲也严查力堵,这直接造成了清初散曲的式微。至清中叶,道情发展情况稍有好转,徐大椿、郑燮、金农三人交相辉映,为道情发展史上一道鲜活亮丽的风景线。
(一)《洄溪道情》与徐大椿的家学渊源
徐大椿,字灵胎,初名大椿,后更名为大业,自号洄溪,江苏吴江松陵镇人。徐大椿是一位医文俱通的大家。他性情通敏、喜善豪辩,天文地理、周乐古音、星经地志等无一不通,曾考取秀才入太学,后常往来于吴淞、震泽等地,行医济世。徐大椿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一身无人可比的医术,《清史稿》中就载有其多部医稿。作为医者,徐大椿主要以医学典籍闻名四里;作为曲学家,主要以《乐府传声》著称于世。《洄溪道情》是他唯一遗留的文学作品,体现了其精妙的曲学才情。
《洄溪道情》最早的版本为乾隆十三年(1748)丰草亭原刻本,附于《乐府传声》之后,此版本的内容不甚完整,只有现今流传的前14首,多为警世之谈与闲游之乐。道光四年(1824),大椿孙徐培重刻乃祖《乐府传声》《洄溪道情》,在内容上多出了庆吊赠别类作品。任中敏《曲谐》所录《洄溪道情》,共有“自序”一篇并道情39首。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皆言《洄溪道情》共38首,但未列细目,详情不得而知。
按徐大椿所言,《洄溪道情》所作“半为警世之谈,半写闲游之乐”。前者指第1首至第9首,即《劝孝歌》《劝葬亲》《劝争产》《读书乐》《戒酒歌》《戒赌博》《时光叹》《时文叹》《行医叹》;后者指第10首至第14首,即《邱园乐》《隐居乐》《泛舟乐》《游山乐》《田家乐》5首。这14首为道情本格,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与道情一脉相承。从第15首起,全为题画酬赠、祭吊、寿文之类,大大扩展了道情的内容范围,真正体现了徐氏道情的文学史意义。
徐大椿出生于书香望族。曾祖父为好学之士,学识广博,见闻丰富。祖父徐釚是清初著名的词人和词论家,徐大椿最早接触曲学即来自于祖父的影响。徐釚一生交游半天下,以文字交结四方之士,与朱彝尊、潘耒、尤侗等人关系亲厚,因而徐大椿在年少时就结识了许多文坛大家。通过学习交流,大椿对曲学乐音有了自己的独特见识,并开始创作道情。正是由于对声乐的熟悉,徐大椿对古乐的遗失深表遗憾,决意推本求源,作道情以恢复古乐。
如果说祖父对徐大椿创作的影响在于曲体和声腔方面的话,那么母亲对他的影响则重点体现在创作内容上。徐母丁氏天资聪颖,学识丰富,文采斐然,文化素养甚高。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徐大椿对周乐唐诗非常了解,对人情世故有着独到的见识,对母亲也应当有着极大的恭敬与尊重,所以他的娱亲诗中有众多古诗名篇,并阐明了自己创作的直接原因——娱母。
我曾为娱我哀,谱得周乐唐诗入管弦。先慈年高目瞽,无以为欢。因将《关雎》《鹿鸣》等篇及唐人名句,按宫定谱,令童吹唱,以娱晚境。[6]7
与普通劳动妇女不同,徐母博学多才,平日除操持家中事务以外,还常帮助亲朋四邻解决日常琐事,劝勉教诲他人。徐母常借词曲诲人、醒悟人心,不论是非争执还是家庭纷争,都能合理处置,其词曲动人,以至有人流泪深悔。这种以词诲人的方式,近似道情说道劝世的意味。此外,徐母还常以韵语入词,词句中满含其深沉炽热的情感,更以变调入谱,这种劝说方式对徐大椿道情的创新意识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洄溪道情》的创作观念
1.展现世情
《洄溪道情》多写警世之谈与闲游之乐,加以庆吊赠别类作品。徐大椿因家庭环境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始终坚持儒家济世救人的原则,不仅在行医时身体力行,而且在文化精神上也毫不退缩,虽不走功名入仕之路,但济世之心未泯。有感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大椿鄙薄时文,常沉浸在经学之中,多以儒家的道德教育和处世之道入诗,浅处立说,用俚俗的语言表现世情。
儒家强调五伦,重视道德教养,徐大椿也在作品中劝勉世人重视孝亲。整部作品以《劝孝歌》开篇,告诫世人要关爱、侍奉父母,以孝为先。儒家伦理体系中“悌”紧随“孝”后,兄弟间相处应和睦友好,所以作品继以《劝争产》,强调兄弟间应和睦友好,虽是道德说教,却不流于空洞:“争天地,终日喧。锦江山,不要钱;人生何苦把家园恋。”[6]2这并非枯燥乏味的伦理解说,而是以人情度之,不显得刻板。此外,许多人一生汲汲名利,终日企盼入仕做官,期望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做人上人。八股取士发展到清代,弊端日益暴露,严重禁锢了文人才情,众多文人起而攻之。徐大椿更是在道情中揭露了这一现实,叹惋时文对文人身心的毒害。虽然他的《时文叹》流传不广,但用语浅显生动,常被当时文人借用:“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似泥。”[6]4面对这种情形,徐大椿表示,对每个个体而言,人生不过百年,倏忽一瞬,要戒赌、戒酒,升华自身;人生应当尽力追求快乐,抛却烦恼、算计,万勿留恋身外之物。
徐大椿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作品全力表现世情,上至儒家伦理,下至隐居闲游,涵盖世间百事,包罗万象,为道情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风貌。
2.自比狂生
文章是个人性情的最好观照。“狂”是徐大椿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他也用这个字来概括自己的个性。徐大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人,其祖父徐釚“少颖悟绝人”,非常人可比,而徐大椿虽不似祖父般天性聪颖,却性情狂放、豪宕不拘,其特立独行的任情狂傲之气与祖父一脉相承。
在行医中,徐大椿胆识过人,让许多医家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他都敢于开具药方,并对自己的药方充满自信。遇到怀疑处方、不敢喝药的病人,徐大椿以强逼迫,并提前声明,若有差池,伤则赡养一生,死则甘愿抵命,近乎狂医。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医术有着极大的把握,没人敢说出这种话来。高明的医术为徐大椿提供了狂傲的资本,医术上的“狂”又被他带到文学之中:
君赋性端凝,笃诚谨懿,我天生顽鲁,狂放粗豪。(《祭顾碧筠》)[6]17
况我半世相随,一朝永诀,落落狂生。(《吊何小山先生》)[6]15
又怕人笑我狂纵,只得向灵前默诵,洒泪满西风。(《祭潘文虎先生》)[6]14
这种“落落狂生”的性格伴随了徐大椿的一生。其实,纵观徐大椿作品及生平琐事,他很少有极放纵的行为,“事亲孝,与人忠”,见义必为,很是厚道,亲朋好友也甚少有人说他狂放,在知音面前更是谦逊有礼。作品中徐大椿不止一次自我贬低,他将自己比“朴鲁寒儒”“樗材散弃”,在《哭沈果堂先生》中更称自己为“野马”,因此我们可以猜测,徐大椿之所以用“狂生”这个词来评价自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嘲。他想济世安身,但现实却不给他这个机会,自己孤身一人,无力改变,所以他探研易理,信奉道教,乐在其中,乐于放任自己的这一个性。
徐大椿把自身这种狂傲的性格全面细致地融入了作品中,他是顽者狂生,又是不得意的失落者,在写作道情时,唯心而作,任心尽兴。
二、《洄溪道情》对传统道情的继承与创新
道情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然而一旦进入世俗视野,它却会开辟出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文人们汲取道家清虚无为的思想,不断地进行道情创作,表达自己的出世情怀。明清时期,道教世俗化进程日益加剧,写作道情的文人也逐渐增多,道情慢慢脱离道教思想的藩篱,越来越向世俗的思想情趣倾斜。
(一)《洄溪道情》对传统道情思想的继承
1.避世思想
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始终面临艰难的仕与隐的选择问题——是通过科举居庙堂之高?还是退居山林处江湖之远?古往今来,企图科举入仕、功成名就者有之,渴望隐逸山林、幽居闲适者亦有之。受传统道教和中国隐逸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文人在自身创作时都对避世思想有所推崇。
散曲文学“其精神构成的轴心是避世思想和玩世哲学”,“而前者则又是后者的前提和内核”[7]。与散曲类似,道情也多以隐居闲适等为主题,有着浓厚的避世观念,不论是道情还是散曲,避世一直都是其表现的重要主题。
大椿的祖父徐釚生值明清易代,他和多数前朝遗老一样拒绝与新王朝合作。后来康熙帝为安抚和网罗各地文人学子,召试鸿博,徐釚无奈入征,但最终辞官隐退。徐父养浩同样选择隐居,终生不仕。这种避世家风深深地影响了徐大椿,他出身于这样一个隐士门第,不愿上京应试求官也是极自然的事,因此他不满科举制度,厌弃时文,渴望归居田园,观江山沧海、驾轻舟远帆。他在《洄溪道情》本格后五首中有着强烈的表达,在其中构造了一个无忧无虑、无荣无辱、潇洒放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朝来不怕晨鸡唤,直睡到红日三竿”(《邱园乐》)[6]7的潇洒之人,也有“东西往来无拘系,琴书宝玩凭缘寄”(《泛舟乐》)[6]21的泛舟隐者,更有“到山中,便是仙,万树松风,百道飞泉”(《游山乐》)[6]6;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不但可以“绳床铺草,土壁涂泥……笋皮为帽,荷叶裁衣”(《隐居乐》)[6]15,亦可以“买碎鱼一碗,挑野菜几般,暖出三壶白酒,吃到夜静更阑”(《邱园乐》)[6]7。在这里,徐大椿向往的是禅宗世界里所呈现出的幽静,悠然自得,不需考虑俗尘杂事,逍遥适性,那里没有神仙皇帝,没有宫苑亭台,不必争名夺利,不必勾心斗角。与传统佛道劝诫说理不同,在徐大椿的笔下,这种自给自足、淡泊寡欲的日子才是人人应当艳羡的生活。这种思想融入大椿心境,让他自然以老庄哲学为核心,融和儒释思想,进而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特质。
“清风吹我尘心断。不知今夕是何年。遥望着牧竖樵夫洗足清泉。与他言,竟不晓得唐宋明元。”(《游山乐》)[6]6此作风格与《桃花源记》相似。其《田家乐》又与陶渊明的农家之乐相仿,风格迥似《归去来兮辞》:
一顷良田,十亩桑园。两只耕牛,一对农船。柳杏桃梅,篱间岸间。鸡犬猪羊,栏边树边。看了蚕收起丝绵,穿得来花样鲜,浑身软。过了黄梅把青苗插遍,到得那稻花香日,又正是明月团圆。收成好,满场米谷,柴草接连天。手拥着炉,背负着暄,抱女呼男,擦背挨肩。宰一只鸡肥,捉几个鱼鲜,白米饭如霜似雪,吃得来喜地欢天。完粮日到城中买一面逢逢社鼓,只等贺新年。[6]6
篇首几个量词的使用简单直观,自然超尘,淳美平淡散逸在字里行间。田家土地平坦,房屋整齐,良田桑园美景如画,村落里鸡犬相闻,人们养蚕插秧耕种劳作,闲情静怡。被桃柳环绕的农家小院更令人如痴如醉,一丝惬意的美妙不由从心底升起,月隐阳来,又一次叩开美好之门,寻到了树丛里素净的一枝花,看见了白云飘曳的一份闲,抱香而舞,拥静而眠。这里的每个人都成了有着清梦而无忧的人,穿行在其间,这种生活仿佛可以超越人间所有黑暗和苦难。
《洄溪道情》里反映的避世思想承继了传统文学中的离尘绝俗,构建了自身避世的精神内核,把叹世隐居与乐道慕仙融为一体,作品虽有发展,但依旧延续了传统道情的避世思想。
2.警世思想
古人常借写作抒发内心情怀,唯心发声,嬉笑怒骂等不平之音皆在文章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讽刺的手法多被用于感时伤世之作,一旦宣泄,常使人醍醐灌顶。古人的骂世手段高超绝伦,又颇为讲究艺术表现,所以他们的警世之文往往如敲醒灵魂的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洄溪道情》中有不少警世之作,具体表现的是以儒家传统观念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和处世之道。任中敏认为此类道情“非等闲俚唱可比,自足另成一派[8]29。”
徐大椿在《洄溪道情·序》中直接指出警世之谈是他创作道情的宗旨之一,他把“警世之谈”纳入题材范围,始终用现实的眼光观察世界,立意也多针砭时弊,《时文叹》为其典型代表。明清时期痛斥八股时文和科举取士弊端的作品很多,但都重在说理,较为雅驯,徐大椿的作品则以浅显通俗、明白晓畅的语言开头,全是嘲骂,尖酸刻薄,严厉地抨击了科举取士的社会现实,整首作品完全表达了作者胸中不可抑制的愤世嫉俗之情:“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似泥,国家本为求贤计,谁知变了欺人技。看了半部讲章,记了三十拟题,状元塞在荷包里。”[6]4由于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偏爱,徐大椿鄙弃这种模式化、规范化的时文,运用正反对比的手法,揭露了才不如银的社会现实,语言明白晓畅。这篇作品也因此受到很多文人的喜欢,此后多部诗人作品集中均有收录。
除不满朝廷科举外,徐大椿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市井民间,百姓的言行举止、医者农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了他批评指正的对象。如《劝孝歌》:“你想身从何来?即使捐生报答,也只当欠债还钱。”作者用“欠债还钱”比喻行孝,这种说法相较于儒家宣扬的“五伦”而言不可谓“不孝”,但却正是这种直指实情的敢想敢说,让他的作品充满浩然之气,给人当头棒喝。
警世之作一般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徐大椿更是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警世道情谐谑辛辣,反讽嘲弄,篇篇气脉相通,一气呵成。《戒酒歌》张口便骂:“造酒的是魔君,把米麦高粱,烂做了这样醃羶醞!”更在其中快言快语地明确指明:“敬亲朋必灌死方为快,争意气便醉杀也无论。”对喝酒、敬酒、灌酒等行为语带嘲弄,讥诮直讽,鞭辟入里。更有《行医叹》对世人学医应当保持本心进行警示劝谏:
叹无聊,便学医。唉!人命关天,此事难知。救人心,作不得谋生计。不读方书半卷,只记药味几枚。无论臌膈风劳,伤寒疟痢,一般的望闻问切,说是谈非。要入世投机,只打听近日行医。相得是何方何味,试一试偶尔得效,倒觉稀奇。试得不灵,更弄得无主意。若还死了,只说道药不错,病难医。绝多少单男独女,送多少高年父母,折多少少壮夫妻。不但分毫无罪,还要药本酬仪。问你居心何忍!王法虽不及,天理实难欺!若果有救世真心,还望你读书明理。做不来,宁可改业营生,免得阴诛冥击![6]18
3.劝世思想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混乱,礼教松弛,很多有志于匡正风俗的文士开始大量写作道情,宣扬劝善思想,明白晓畅,娓娓道来。清代范祖述在《杭俗遗风》中记载当时杭州的情形:“道情以渔鼓简板为用,所唱多劝世文。大家小户多不兴,惟街书有之。”[9]虽然此处说的是杭州地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情在民间传播的特点和内容。
由于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社会自古重视伦理教育,“孝”在家庭伦理中更是居于首要地位。徐大椿创作道情时劝“孝”必不可少,他在开篇《劝孝歌》中就大力宣扬孝道伦理:
五伦中,孝最先。两个爹娘,又是残年。便百顺千依,也容易周旋,为甚不好好地随他愿!譬如你诈人的财物,到来生也要做猪变犬。你想身从何来?即使捐生报答,也只当欠债还钱,哪里有动不动将他变面!你道他做事糊涂,说话欹偏,要晓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个婴年,定然是颠颠倒倒,倒倒颠颠。想当初你也将哭作笑,将笑作哭,做爹娘的为甚不把你轻抛轻贱?也只为爱极生怜,到今朝换你个千埋百怨。想到其间,便铁石肝肠,怕你不心回意转![6]4
在这里,徐大椿仿佛是一位邻家老者,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苦口婆心地对世人进行劝说。他指出,孝道的基本内涵是“亲亲”,就是对父母养、顺、敬。作品以“孝”开始,从人的性情讲开,婴童颠颠倒倒、将哭作笑,青年人从婴年度过,而老人的性情又回到婴年,全文以佛家轮回思想警世,敦促大众以孝亲为先,浅处立说,劝勉世人。
徐大椿认为“孝”不止体现在子辈对父辈的敬爱侍奉,还表现在能够让逝去的亲人入土为安,其《劝葬亲》云:“劝世人只须得省衣节食,早早的送你爹娘入土,这就是造福之门。”葬亲类作品难以表现,一般少有人作,大椿却毫无顾忌,大力劝勉世人不能听信风水先生一派胡言,不仅要“孝”生者,更要“孝”逝者,惟有此行为之人方能受到社会尊重,才不失为君子。
此外,徐大椿的劝世思想还体现在其更强调自我的人生升华方面,要戒赌、戒酒、戒争产。他认为人生不长久,赌博嗜酒、烦恼算计都是对人生的荒废,锦绣乾坤就在自然之间,美与艺术就蕴藏在日常之中,人生不是一味的行乐。《时光叹》就劝人珍视光阴,少些算计:“劝世人且快活几时饶人一步,不要等那钟鸣漏尽懊悔凄惶。”[6]8
劝世道情的创作主要源于“劝善”观念,明清时期的劝善运动把它推向高潮。明清时代的文人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动,陆续思考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以扶世教、救颓俗为己任,他们的创作继承了劝世思想,并贯穿其中,成为清代道情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
(二)《洄溪道情》对传统道情的创新
徐大椿用道情代替传统诗文,把它作为自己的专用体裁,劝世警俗、酬赠知音,从俗通雅。正是在这种致用的雅俗之间,道情曲体迎来新变,题材得到极大发展,为文人创作道情提供了成熟的范式,具有深刻的典范意义。
1.成曲调之一家
道情一般由曲调和词两部分构成,可做表演弹唱,然发展至清代曲音大多失传,往往有词无声。在清代道情的诸多创作者中,徐大椿创作的道情最具特色,他不仅关注道情辞的发展,更致力于探本穷流,恢复道情曲音。《道情序》直接表现了徐氏重视曲调的观念:
以声布辞,以词发声,悉一心之神理,遥接古人已坠之绪。若古人果如此,则此音自我续之;若古人不如此,则此音自我创之。无论其续与创,要之,律吕顺,宫商协,丝竹和,可以适志,可以动人,即成曲调之一家。[10]521由此可知徐大椿以“遥接古人已坠之绪”为己任,写作道情时本着承继古音、协调宫商的态度,无拘无束地试验着创作出一种自由的新诗体。
徐大椿受家世影响,曲学素养很高,对道情之曲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对声乐的熟悉,徐大椿对“声”有着独特的认识,把它看作曲体之至高至妙者,并认为古人之音多有失传,而道情曲已完全断绝。他感慨于古乐的遗失,因而推本求源,改造北曲仙吕入双调并推广其音,采用道情古调表现曲情,这也成为他创作《洄溪道情》的曲论基础。
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对传统小道并不重视,仅有南曲比较盛行,徐大椿却把北曲作为乐道典范,极力推崇。徐大椿认为,宫调从古人分宫立调开始就有了固定的模式,即使失传,但只要依循旧例,按照已有的规律稍加变通,就可以重新恢复。宫调是从古至今音乐艺术发展因素中变化较少的一类,不同的宫调有不同的风格,黄钟调唱情时富贵缠绵,南吕调唱情则感叹悲伤。《洄溪道情》以仙吕宫和双调入词,根据《中原音韵》和《太和正音谱·词林须知》可知,仙吕宫清新绵邈,双调健捷激袅。现在虽然无法确定徐大椿具体使用的是哪些曲牌,但就文字部分看,作品多道情本色语,通俗质朴,明白晓畅,两种宫调里蕴含的曲情明显对应《洄溪道情》里的内容。
除此之外,对于曲的创作,徐大椿也做出了相应发展,反复要求能够感动人心,强调自身对道情的创作非知音不作。其《寿沈井南》云:
自余广道情之体,一切诗文,悉以道情代之。然构此颇不易,必情境音词,处处动人,方有道气,故非知音不作。[6]10
传统作者作曲时均按词谱曲,但大椿却另辟蹊径,因曲填词。他认为对道情内容的强调是其次的,而道情之音最为绝妙,词起辅助作用,只是为了让大众深入理解曲所传达的意蕴才需要填词。因而《洄溪道情》的序言中几乎没有“词”的出现。大椿强调曲音的重要,完全是为了推动道情的发展。道情以渔鼓、简板固定节奏,北曲衬字较多,演奏时为完美承接只设置了底板,不似南曲曲牌有固定的格式,可使道情曲调自由变化,达到“声境一开,愈转而愈不穷”[10]521的效果。
遗憾的是,徐大椿在声乐上的创新改造虽然展现了其独树一帜的曲学才华,但《洄溪道情》中他最为得意的曲调却仅仅剩下不可歌的文字,而他对古乐的恢复也一定程度上将道情禁锢在了文人的案头,这或许也是他的道情并未在民间得到得到发展的原因。
2.显微曲折,无所不畅
徐大椿的道情不仅在声腔音律方面做出了创新,而且对文本的内容与形式都有一定的发展。《洄溪道情》中除去“警示之谈”和“闲游之乐”,其余几乎所有题材都用道情来写。题画、酬赠、凭吊、祭文、寿文等用诗文来写难度不大,只要做到整饬严密、端庄谨肃就可以了,但若用道情就需要写出其绝尘脱俗的“道气”。因而在传统文学中并没有人选择用道情来写作此类作品。徐大椿自己曾在《吊何小山先生》中说:“凡哀死祭吊之作,自《离骚》、四言而外,一切诗词歌曲,无体不全,而独无道情。”[6]15他对自己能够拓宽道情题材应当也是感到颇为自豪的。
徐大椿结合儒家仁义与道家无为,以道教的教理教义及理想境界入诗,洋洋洒洒,竭力表现道家的逍遥洒脱,表达了自身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以及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具有独特浪漫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倾向。
相对道情本格的作品,大椿道情中的庆吊、赠别、题画、寿文、祭文作品可以说是徐大椿在内容上的创新。与庄子一样,大椿对亲人离世表现得十分旷达,在三子燝亡故后他不像世人那样悲痛嚎哭,而是只惋惜自己失去了一位青年道友:“恨只恨,又失了一个青年道友,教谁人伴我度残生?”(《哭亡三子燝》)[6]15或许是因为清代统治者对文学创作控制严密,稍有不慎就会得罪,造成许多作者在创作中不敢面对现实,所以才用题画酬赠等形式,如此可信马由缰,比较自由,以致这种“借题发挥”在当时形成一种风尚。这些题画、祭文等作品用道情难以表达,向来少有人作,但徐大椿却巧妙地为其注入了一丝“道气”:
只愿得天公怜我,放我在闲田地,享用些闲滋味,直闲到东溟水浅,西山石烂,南极星移。 (《六十自寿》)[6]11
莫笑我逍遥闲散,也只为百岁光阴有限。你不要锄熟了亡经佚史,抛荒了越水吴山。 (《赠曹慈山》)[6]8
道情本格作品中表现的说教劝世意味明显,但庆吊、赠别类作品所表现的“道气”也不遑多让,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大椿认为,道情的“道气”除了音词情境之外,更要加入自身性情,以及与亲朋好友相识相知的情感,所以在作品中常会看到多具有道家色彩的人物:有最爱清幽、鹤发朱颜的席士俊;有温文尔雅、敬友谦恭的丁三母舅;有年已七十,仍赤子情肠的老友更有逍遥散仙……这些人简单纯真、品格高洁,身心不为外物所累,追求逍遥洒脱,似欲乘长风的道者。徐大椿周围不仅有心忧天下的白衣方又将,不畏权贵、一心为民的顾碧筠,读书不为功名的何寓庸,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的沈果堂;还有以古乐唐诗侑酒的陈圣泉,礼乐宗师禽味经,品望清隆的蒋迪甫,皓首穷经的曹慈山,崇经复古的韩云开,善于品鉴的何小山……这些本应为记人记事的文章,大椿却把他们全入于道情,或作书画题赠,或作寿文、祭文。这类作品在大椿《洄溪道情》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按创作时间来看,徐大椿1743年在写作道情本格时,已经创作《题翁霁堂三十三山堂图》和《寿韩开云先生九十》,足见其在道情创作之始就产生了创新意识。
3.句式自由不受限
除在内容方面有所创新外,徐大椿在道情曲的形式上也作出了一定创新。《洄溪道情》曲多者五十余句,少者只有十余句,短有三字,长有十余字,平仄运用也无太大讲究。徐大椿主张不论是何种体裁,每首曲子的创作都应拥有自身特有的结构句法,这种结构句法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只有在不改变曲牌的前提下,作品字句多寡方可依时而变,自由不受限。
《洄溪道情》中道情本格的十四首形式上固定整齐、简明清晰,大多作品以三、三句式起调,无有特殊;庆吊赠别类作品与道情本格略有不同,多以四字或五字起调,其中有十六篇以四字起,七篇以五字起,而有八篇以四、四、四、四起句。这种艺术风格明显承继古人所作,与《诗经》颇具相似之处。如《祭顾碧筠》“同林四鸟,饮啄相招。三鸟云逝,哀鸣嗷嗷”[6]17,不但借用了典故,还运用了“兴”的艺术手法,以同林四鸟为喻,将自己、顾碧筠与何家兄弟比为离别之人,四鸟本形影不离,然意外失去同伴,鸟儿低飞哀鸣,辗转徘徊,情感强烈而执着,四人之间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此外,作品还多处运用典故,如“所其无逸,稼穑艰难”(《题山庄耕读图》)出自《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提篮采药非他意,只为无粮代采薇”(《题何师之采药图》)典出《诗经·采薇》。
大椿的道情基本如此:虽为单支小曲,篇幅较小令稍长,文辞质朴,浅显明畅,多谕人以理,广泛流传于小家庭院和茶楼酒肆之中。
徐大椿利用自身不可多得的曲学才情在道情创作中扩大了道情题材,“完全摆脱词曲的形式和规律,在试验着一种新诗体。”[11]题画酬赠类道情作品在元、明两代罕见,清代以徐大椿为代表发展空前繁荣,文辞显微曲折、无所不畅、通俗真切,声韵流荡生动,毫无故作典雅之弊。任中敏在《散曲概论》中说:“今世但知郑板桥有其词,而不知徐灵胎实定其制。”[8]345赵义山更是认为道情“可惜灵胎谥后,再无人继其绝响。”[12]
三、结语
道情发展至清代由徐大椿发扬光大,地位几乎可与诗词争席。作为一名曲学家,徐大椿幼年时期便受到祖父和母亲的极大影响,深厚的家学渊源为他提供了思想基础,使他的整个创作活动得以不断展开,并完成了重要著作——《洄溪道情》。在道情创作中,徐大椿坚持展现市井风俗、人情天性,他情深气盛,敢想敢言,常常自比狂生,同时继承了以往文人创作道情的避世、警世和劝世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他摆脱了传统道情词曲的限制,对道情曲体探本穷流,在扩大传统道情题材的同时,也为其形式发展带来了新变。徐大椿常怀宗经法古之心,却非处处创新求异,与板桥、金农诸人一起复活道情体裁,引领了清代道情的发展。从对后世的影响看,《洄溪道情》在道情史上的作用是开拓性的,它向人们展示了一部曲情独特而又成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