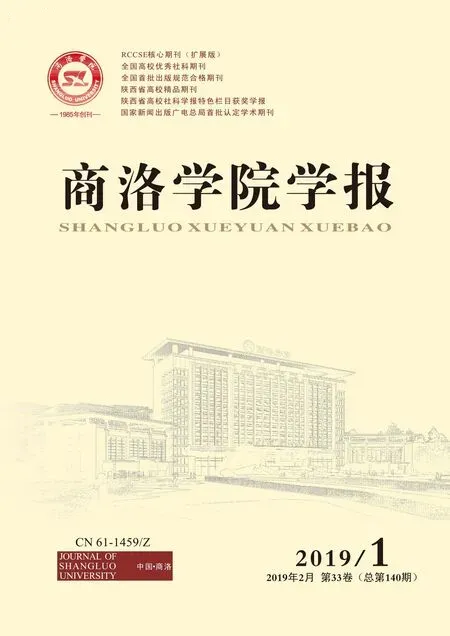《梁四公记》对“商山四皓”之典的重构
2019-02-21金晓琳
金晓琳
(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000)
《梁四公记》是初唐时期六朝志怪小说向唐传奇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作品,今只存《梁四公》《五色石》《震泽洞》三节。《梁四公》以闯、杰、、仉督四公为线索,内容涉及丰富的异域博物及奇珍异宝,将独立的故事单元串联为一个故事内核展开叙述;《五色石》和《震泽洞》则通过山人献石、龙女献龙珠的事件,展现了杰公善识宝物之能。关于《梁四公记》的记载,最先见于唐人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国朝燕公(张说)《梁四公传》”[1]。《新唐书·艺文志》杂传类著录卢诜《四公记》一卷,注云“一作梁载言”[2]。《宋史·艺文志》作“梁载言梁四公记一卷”[3]。可见,《梁四公记》的作者在史籍目录中存在不同的记载,目前仍无法确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唐代小说史研究的著作开始对《梁四公记》给予关注。李宗为在《传奇产生前的唐人小说》中认为《梁四公记》非张说所著,其内容荒诞,文字也较芜杂,不像是当时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名相张说所为,并根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引证的内容,认为是唐高宗时临淄方士田通所撰,盛唐后的方士附会为张说,以此来抬高身价[4];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对《梁四公记》的著录、作者、佚文及内容情节做了介绍,认为顾况较梁载言、张说时代较近,且以顾说为准[5];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进一步对《梁四公记》的著者问题进行考辨,认为顾况《戴氏〈广异记〉序》的记载确实无疑,而托名田通、梁载言是张说故弄玄虚,是张说得田通旧文加以润色而成的[6]145-150;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对《梁四公记》的内容、故事情节、艺术描写、作者等相关问题做了概述,认为《梁四公记》在内容上继承《博物志》的传统,艺术上采用短篇连缀成长篇的形式,为传奇的发展积累了创作经验[7]。李鹏飞认为《梁四公记》反映了初盛唐时代军事政治形势的演变以及作者张说个人的思想情感与人生经历,通过对素材的溯源、分析作者具体的创作手法,将其视为熔铸史实与传说、现实与幻想于一炉的典型的小说文本,体现了唐代前期作家有意为小说的意识[8]。上述关于《梁四公记》的研究,集中于对作者的考证和传奇的内容、情节等方面,而对其文化内涵及意义的探析却较少涉及。本文将结合《史记》文本中关于“商山四皓”的记载,对比分析《梁四公记》中梁四公与商山四皓的继承、延展关系,进而探讨《梁四公记》传奇在故事内核、人物形象、小说创作观念等方面对“商山四皓”之典的重构。
一、《梁四公记》四公与“商山四皓”形象之变
“商山四皓”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留侯世家》:
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9]2044-2045
《留侯世家》中关于东园公等四人的记载是“商山四皓”典故的原始出处。《史记》中关于“商山四皓”,仅有其年长,因在位者轻蔑、怠慢贤士而逃匿山中不为汉臣的简单记载,至于其形象则是“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9]2045。司马贞在索引中则进一步交代了四公的具体姓名:“四人,四皓也,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9]2045《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求聘四皓”条据颜师古注云:“四皓须眉皓白,故谓之四皓。”[10]697颜师古注的依据是《留侯世家》中“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形象细节描写。由此可知,“商山四皓”之形貌特征从始至终即是如此。
现存的《梁四公记》佚文主要见于《太平广记》卷八十一《梁四公》(三千多字),卷四百一十八《五色石》(二百三十四字)、《震泽洞》(一千三百多字)。后二篇下皆注“出《梁四公记》”。宋代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赵彦卫《云麓漫钞》、庞元英《文昌杂录》三部文献中也记载了一段内容大致相近的异文,应为《梁四公记》的开篇。
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了梁代大通中四公来朝,武帝问及三教九流和前朝旧事,四公皆对答如流之事,突出了全朝竟无识梁四公者,惟昭明太子萧统识之,四公便欣然依附萧统的情节,其中又有关于四公年龄、面貌的描写,如《六朝事迹编类仪贤堂》:“大通中有四人来,年七十余,鹑衣蹑履,行丐经年,无人知者。帝召入仪贤堂……帝问三教九流及《汉书》事……举朝无识者,惟昭明太子识而礼重之,四人喜揖昭明如旧交,时目之为四公子。”[11]《云麓漫钞卷六》中又有一段近似于《六朝事迹类编》中对梁四公的描写,其四人在大通中年入梁,“貌可七十,鹑衣蹑履,入丹阳郡建康里,行乞经年,无人知……帝问三教九流及汉朝旧事,了如目前。问其姓名,一人曰姓名闯,一人曰姓名杰,一人曰姓名,一人曰姓仉名督。合朝无识者,惟昭明太子识之。四人喜,揖昭明如旧交,目为四公子。”[12]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亦记载:“梁四公子:一人姓名闯,孙原人。一人姓名杰,天齐人。一人姓名,浩人。一人曰姓仉名督,无阮人。昭明太子曰:‘ 出扬雄蜀记,闯出公羊传;出世本,字亦作简,出三齐记,杰出竹书纪年;出索纬陇西人物志,出世本及广雅;仉出太乙符, 出史记。孙原,僰山名。浩 ,洮湟之间二水名。五阮,雁门也。’”[13]它补充说明了四公姓氏、人氏及出处。
李剑国认为:“以上除四公姓名皆不见《广记》引文中,亦是此记佚文。”[6]148此三段佚文中对四公年龄、面貌均有相似的记载,其中《梁四公记》中关于四公“年七十余”“知三教九流之事而无人知者”“惟昭明太子礼而遇之”等情节又与“商山四皓”在《史记》中的记载极为相似。《梁四公记》中,梁朝宫廷诸王、儒士中唯一得到正面描绘的是昭明太子萧统,前引两段佚文中关于四公“合朝无识者,惟昭明太子识之”“四人喜,揖昭明为旧交”的情节使人联想到《史记留侯世家》中“太子为书,卑辞候礼,迎此四人”“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等语,则四公与四皓在人主的选择上,同归附于对自己礼遇有加的太子。四公与四皓同样年长而博闻强识,不仅在形象与智谋上相同,且同时都作为整体出现。而在《梁四公记》中,则着重突出了四公各自所长,并对其所长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其中,梁四公“行乞经年”的人生际遇也与商山四皓不同,四皓作为高贤隐逸之人,其形象素来高洁,而四公却颇显落寂。
二、《梁四公记》对“商山四皓”江山之助的延展
《梁四公记》通过梁武帝时期的四位异人,将各个具有独立性的故事串联起来,所述四公之事,内容完整,情节颇为曲折。“商山四皓”高尚贤能、智谋出众的佐王之才则在《梁四公记》中得到了细致的叙述。梁四公都是博才识广的能人,闯能够卜筮识物,知晓礼仪并且能预知后事,杰能辨明异域方物,仉督则擅长应对礼宾问答、精通儒道及梵语释说。《梁四公记》传奇中描写的四公各有所长,人物性格各异,均是作者有意识地对人物进行的塑造,从而将独立单一的故事串联成一个博才多识的整体,而在博闻强识的整体形象中又见其个性分明。前引《留侯世家》中关于四皓的记载,未详其人其事,只叙述了四皓归附太子刘盈,得到了刘邦对太子的信任,认为他根基稳固、深得人臣民心,最终放弃了易储之念。但在《梁四公记》中,四公不再是串联在一起的形象整体,而是各有侧重,闯明卜筮、知礼仪、杰识博物、仉督擅应对。在现存佚文中,唯杰公之事最为称奇,情节最为完整,物类也最为丰富,传奇中所涉及的异域方物、珍奇异兽、珍珠宝玉皆光怪陆离、神异非常,具有志怪小说广征博物之质。
三、从梁四公与“商山四皓”之不同反观小说作者创作观念
班固《汉书·张良传》沿袭了《史记·留侯世家》的记载,但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对“商山四皓”作出了道德评价:“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10]3058将四人与郑子真、严君平并列,成为抑制贪婪之风、劝勉良好风俗的典范。《法言·重黎》云:“或问‘贤’。曰:‘为人所不能。’‘请人’。曰:‘颜渊、黔娄、四皓、韦玄。 ’”[14]扬雄将四皓列入“为人所不能”的“贤”之列。在后世的援引中,四皓皆以其贤称名于世。如《后汉书·郑玄传》记载灵帝末年,党锢之禁解除后,郑玄拒绝接受何进、袁隗的征辟,而深得国相孔融敬重。孔融列举汉世被冠以“公”之称谓的有名之士:“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15]可见,四皓亦并列在“公者仁德之正号”内。《晋书·殷仲堪传》记载桓玄持“隐以保生”之论以质疑四皓羽翼太子之事,殷仲堪则认为“若夫四公者,养志岩阿,道高天下,秦网虽虐,游之而莫惧,汉祖虽雄,请之而弗顾,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应,事同宾客之礼,言无是非之对,孝惠以之获安,莫由报其德,如意以之定藩,无所容其怨”[16]。四皓本于仁义之道出山,以宾客之礼对待汉惠帝,问答不涉及是非之论,汉惠帝的太子之位因而得以巩固。四皓为发扬仁义之道而出山,是保有国家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古今圣贤共同珍惜的,与踏入仕途做臣子的人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可见,历代史籍逐渐以“贤能”“仁德”等表征四皓之事,并将其固化为特定的称谓。后代也不乏对四皓事迹真实性的质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山四皓”的形象被不断建构和符号化,四皓也成为贤德高隐的表征和典范,备受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推崇。
《梁四公记》中的四公形象不仅在发挥江山之助的作用方面比商山四皓更为具体,且善卜筮、熟识异域方物,已非典型的儒者形象,且传奇文本中除了昭明太子之外,对诸王儒士均无正面、积极的描写。四公在人生价值的选择上,用其禀赋之异能积极辅佐统治者。如文中藩国向梁朝进贡,满朝王公儒士竟无一人识之,唯有杰公能辨其物,令在座之人叹服;被誉为“博学赡文当朝第一”的北魏使者崔敏与督公谈论三教之理,督公所学无所不窥,辩才敏捷,崔敏为督公所沮,后竟病死。传奇中以杰公之事最详、博物之质最明。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对扶桑、拂林、炎洲、漆海等地各处风土物产了然于胸,梁朝君臣将信将疑,“朝廷闻其言,拊掌笑谑,以为诳妄”。扶桑使者至梁,杰公“识使者祖父伯叔兄弟”,识别“赍火浣布三端”原料差异,道出胡商之玻黎镜乃色界天王之宝,异域方物与杰公之言一一印证。《五色石》中又记载杰公能识上界化生龙之石,告帝命人琢之为瓯,以盛御膳,其食香美殊常;《震泽洞》中,又述杰公能够预知龙宫藏宝机密,制作制龙石遣人至龙宫取宝,辨别珠宝特性。
可见,四公不以商山四皓“道济天下之溺”的儒家理想为念,相反,他们对异域方物、卜筮神异之事颇为关注,也不以朝廷“拊掌笑谑,以为诳妄”[17]的轻视态度为意,反以掌握特异之才而独拔于士人之上,自处于世。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认为《梁四公记》“虽然偶然涉及儒释道三教,但主导思想已然是道教思想,卜筮释卦、陈述方外遐域所贡奇珍异宝的特性,或派人到龙宫取回珠宝,基本上是道教文化的特性”[18]。诚然,在《梁四公记》中,四公并非以儒士著称于世,反而擅占卜、熟知异域博物,四公的形象更接近于方术之士,而非儒士。就此反观《梁四公记》的撰者问题,李宗为在《唐人传奇》中对《梁四公记》的作者问题进行考辨,他根据陈振孙的论述,结合篇中关于占卜释老、轻视朝中儒生的内容,进而判断此书是高宗时期临淄的方士田通所撰,盛唐后又为方士附会张说以此抬高身价,但因顾况距张说年代相近,所记较为可信,姑且署名张说撰[4]。结合四公特擅博物、精通神异的特征来看,此论有其合理性,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顾况的《戴氏〈广异记〉序》亦有其真实性。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进一步对《梁四公记》的著者问题进行考辨,根据《戴氏〈广异记〉序》,李剑国认为确为张说撰无疑,至于题“田通、梁载言云云,疑乃张说故弄狡狯,正犹李公佐之撰《古岳渎经》然;若张言不诬,则系张说得田通旧文而重加润色以行世。俗人不察,见卷末有梁载言,遂定为梁作。”[6]146李剑国之论调和二说,尤为允当,不妨将《梁四公记》视为张说得田通旧文而重加润色以行世之作,反映了博物尚奇的创作观念。
《梁四公记》投射在梁代的现实之上,其中涉及的人物及事件都与此时相关。如传奇中言及的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遣使献方物等事件,在《梁书·诸夷列传》中皆有记载。盘盘国“天监二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19]789;丹丹国“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19]794;高昌国“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19]811。这也体现了传奇或以梁武之盛托喻初唐之兴,反映了传奇作者以史为参照、力图神异、崇尚博物的创作观念。
四、结语
《梁四公记》以“商山四皓”为原型,旁征博引、志异尚奇,丰富了传奇中人物与情节的完整性。虽然传奇中关于人物形象的描写仍然较为简略,但仍可看出,梁四公在商山四皓这一典型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梁四公辅君之助的作用,凸显了梁四公的博闻强识。“商山四皓”作为圣贤之人,实践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儒家政治理想。梁四公与商山四皓同为世之高贤,商山四皓是典型的致君尧舜的儒者形象,而梁四公却是在南朝方士盛行的现实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的游方之士的形象。不同于兼济天下的儒者,四公的形象与作用更倾向于精通术数的方士,寄托着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也体现出唐代志人传奇博物志奇、有意为之的创作观念。作者对商山四皓形象与特性的重构,体现了作者的创作观念并非以独尊儒术、强调教化为主,而是以熟识异方、博物志异为尚的创作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