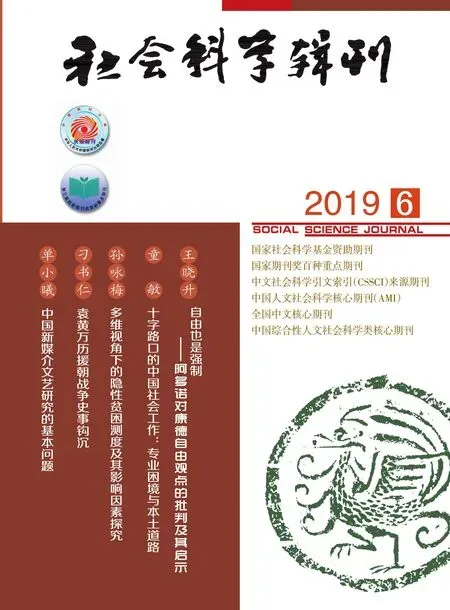袁黄万历援朝战争史事钩沉
2019-02-18刁书仁
刁 书 仁
袁黃,嘉靖十二年(1533〕生,字坤仪,号了凡,明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①袁黄,《明史》无传,关于其生卒年众说纷纭,较为可靠的史料为《了凡四训》及清彭绍升著《居士传》中《袁了凡先生传》。其生卒年,本文采用章宏伟《袁了凡生卒年考》文。幼年丧父,遵母命弃学习医。后偶遇知占卜的孔先生,算其“明年当补诸生,后以贡生为知县”〔1〕,遂弃医应科考,嘉靖四十五年(1566〕为贡生。隆庆三年(1569〕遇云谷大师,受其指点顿悟,始积德行善,命运始有转变。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出任宝坻知县,万历二十年(1592),擢兵部职方司主事。
时值壬辰之役爆发,日本侵朝,朝鲜深受兵难,向明乞师救援。袁黄以为“渡鸭江,适朝鲜,奋武海邦,立功绝域,匪男子之壮游,实夙生之业债未了也”〔2〕,是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之机,遂主动请缨入朝作战。同年八月,得到明廷允准。〔3〕袁黄以军前赞画入朝抗倭,如朝鲜文献所载:“兵部主事袁黄,同心协赞,誓死穷寇。”〔4〕
袁黄学有所宗。早年师从阳明,后学王畿(龙溪),笃奉阳明心学,又深受唐顺之禅宗影响。他曾论及道学感叹道:“今朱子之学已大行于世,如日月当天,独陆氏之学,世儒皆排之……而阳明先生亦为一世宗仰,邹吉士风采可重,惜未究其所施耳。”〔5〕其对陆王之学的体认由此可见一斑。袁黄所奉掺杂着禅学的阳明心学,在国内无人不晓,即使在域外朝鲜也大肆宣扬。据李朝官书《宣祖实录》载:袁黄“尝命题以朱、陆之学,试文于我国人。我国人无他言,但答曰:‘我国但知有程、朱之学’ 云。厥后寄书于其师赵公,自夸曰:‘吾道学大肆于外国’ 云,可见其人之浮妄”〔6〕。可见时为援军赞画的袁黄希望与朝鲜士人通过讨论改变朝鲜以程朱理学为宗的指向,然而宗奉程朱理学的朝鲜士人对其所宣扬的阳明心学是格格不入的,并由此引发一场论辩。
后袁黄因“冒功请赏”事件,与北兵统帅李如松发生矛盾,适逢“癸巳京察”,卷入明廷内争而被罢官革职。《了凡四训》为袁黄晚年削籍还乡之作。万历三十四(1606〕年逝世,享年 74岁。明熹宗即位后,追叙其援朝征日之功,赠尚宝司少卿。
学界对袁黄研究多有成果问世。对其生平事迹,有酒井忠夫的《袁了凡传》①参见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0 年。,特别是章宏伟对其生卒年考订详实,补充了酒井氏研究之不足;②章氏依据袁黄父袁仁所著《嘉禾记》《新筑半村居记》与袁黄著《两行斋集》等文献,认为袁黄生于嘉靖十二年(1533),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享年 74 岁。参见章宏伟:《袁了凡生卒年考》,《中国道教》2007 年第 2 期。对其仕宦政绩,有郑克晟、张献忠等关于袁黄任宝坻知县期间的研究;③参见郑克晟:《袁黄与明代的宝坻水田》,《天津农业科学》1982 年5 期;张献忠、崔文明:《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以袁黄 〈宝坻政书〉 为中心》,《史学集刊》2018 年第4 期。其学术思想近年引起学界的关注,先后有王卫平、张献忠、南炳文、冯贤亮、何孝荣等人的研究。然而于袁黄抗倭援朝的经历,由于中国史料阙如,仅见两篇论文有所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检索李朝官私文献,拟对袁黄万历援朝战争期间在朝鲜的史事加以梳理,以补袁黄研究之不足。
一、以军前赞画入朝参战
如前所述,有关袁黄在援朝抗倭的经历,中国史料阙如,而朝鲜文献则保留一些这方面的史事,可补袁黄研究的不足。万历壬辰战争是关乎前近代东亚政局走向的重大事件,国内外学界对其多有研究。不过,笔者重点梳理袁黄援朝史事。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二日,丰臣秀吉投入约十五六万兵力,大小舰艇700 余艘,渡过对马海峡后,突袭釜山朝鲜守军。釜山沦陷后,20 天攻破王京,60 天占领平壤。日军所经之处,朝鲜军队望风而逃。〔7〕朝鲜承平日久,毫无抵抗能力,只好向明朝乞求救援。史载:“请援之使,络绎于路。”〔8〕作为东亚共主的神宗皇帝,仅派3000 明军入援,结果遭遇日军伏击,几乎全军覆灭 〔9〕,这才引起明廷君臣的高度重视。八月,明廷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10〕。应昌受命,奏称:“辽左、天津皆畿辅要害,承平日久,军务废弛,乞赐专敕便宜行事,及请发钱粮、制造器炮,以本部主事袁黄、刘黄裳随行赞画。”神宗下旨:“经略关系重大,应昌忠勇任事,督抚官毋得阻挠,将领以下一听节制,违者以军法行。”〔11〕时任职方司主事的袁黄被应昌举荐,由原六品官,特赐四品,随军参赞。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袁黄受命赞画后,便积极参与援军战前诸务的准备。九月,他奉命前往天津、山海关等处,会同地方官,布置备倭事宜。他经过实地调查,认为兵力调配、军械粮饷等尚未准备充足,仓猝入朝作战,对战事不利。时为赞画的袁黄很可能向宋应昌建议推迟入朝进攻日军的时间,但未被采纳。这从宋应昌给他的回信中可得到印证。④如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五日,宋应昌写给袁黄信中有如下语:“第今日事势有难一一尽如吾辈意者,各兵老弱未经练习,且马多于步,不佞尝窃忧之。但中国目下可恃者,惟倭性畏寒一节。而欲调换则动有牵制,欲操练则又稽时日,故不得不果时决意进剿。如再延缓,指日春和,我兵战阵未必闲习,而倭奴得志,咎将谁归?”见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5 与袁赞画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93 页。十一月二十七日,辽东都司张三畏于义州与宣祖的对话中也反映了援军粮饷筹措不足问题。据朝鲜文献记载:
上幸龙湾馆,接见辽东都司张三畏。上曰:“皇上既降敕,许发十万兵,小邦日夜企待,未知师期的在何时?”都司曰:“宋侍郞已到辽东,兵马不久当出。但所忧者,贵国粮刍不敷,故先遣俺检视。我还,兵即发矣。”上曰:“一路粮刍,粗已措办。而南寇不耐寒,此正剿灭之时。若过了数月,则虽有天兵十万,事无可及矣。”都司曰:“中原恃辽东以为固,辽东恃贵国以为藩蔽,唇亡则齿寒,岂可纵倭寇而不讨,见贵国之急而不救乎?”〔12〕
可见,朝鲜濒临国破家亡,急切指望明援军击败日军,勇于担当的明军将领只好在粮饷不足的状况下入朝参战。袁黄作为赞画,对主将充其量仅有建议权,只能服从宋应星、李如松在粮饷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冬季发动对日军作战的命令。①据《李朝宣祖实录》,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癸卯条载:李朝吏曹判书李山甫驰启中言及,在辽阳拜李如松时,如松曾言:“所领兵马十万,而见来者四万余,待彼齐到,恐失天时,四万足以平倭。”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 年,第 587 页。
袁黄渡江入朝后,仍念念不忘赞画援军粮饷。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六日袁黄入朝,朝鲜国王在龙湾馆迎接。交谈中,袁黄谈及援军粮饷筹措问题。据《李朝实录》记载:
袁黄曰:“天朝为贵国发大兵,若到安(州)、定(州〕绝粮退军则奈何?”上曰:“各站皆遣官支候,似无不足之忧。恐或军卒暮到,不及分给也。今闻下教,当更加申饬。”袁黄曰:“炮车无牛,尚滞途中,大军虽进,将何为乎?”上曰:“当更差官督运。”〔13〕
时朝鲜沦陷日军之手,对朝鲜而言,粮饷供给并无十分把握,而国王一心企盼早日击败日军,只是不负责任的应承而已。
为赢得援朝战争的胜利,袁黄与刘黄裳共同向朝鲜军民发布战前动员令。正月七日,他们以“大明钦差经略防海御倭军务兵部”的名义发布咨文。指出:“我大明皇帝,念尔二百年来恪守臣节,不惜万金之费,命将徂征。尔国中岂无宗戚,受重寄而忠愤熏心;岂无县官,守地方而慷慨委命;岂无忠臣,怀主忧臣辱之念;岂无义土,萌捐躯报国之思。”号召朝鲜军民“宜乘天威震迭,速招集义兵,各提一旅之师,共申九伐之志。今倭夷逞强,其势必亡,尔国虽微,其势必兴”。进而阐释必胜的理由:以天道论有三:日本来侵,“逆天而行,虽强亦弱,一也”;倭性畏寒,“立春后,尚有二三十日,寒气未消,天时可乘,二也”;“尔国君臣,俱聚此城,晨起望气,郁郁葱葱如练如盖,旺气在我,势必恢复,三也”。以人事论有四:“我大国雄兵,如虎如熊,无敌大炮,一发千步,彼不量力,当成齑粉,一也”;经略宋应昌、提督如松“二职,素仗忠贞,同心协赞,誓灭此贼,以报天子,合两国之师,驱此穷鬼,如振落耳,二也”;“关伯强暴,上劫制其主,下虐使其众,天欲亡之,实假手于我,三也”;朝鲜国王“举动安详,手姿俊伟,势必中兴”,尔国“请兵天朝,诚意恳恻,泪下如注,庶几申包胥泣楚之意,君臣若此,岂终沦困,以顺讨逆,何功不成,四也”。咨文最后号召朝鲜军民:“须速传示各道臣民,义兵已起者,便为前进,未起者速为招集,或协力以挫其威武,或迭出以分其势,或邀其惰归,或断其饷道,诸所机宜,皆听自便。”〔14〕朝鲜士大夫赵庆男对此评论道:“激发劝谕,逐条开说,明白恳切,凡有人心,孰不感动?”〔15〕如上所述,尽管袁黄并非赞同立即对日作战,但并不固执己见,而是恪守赞画职责,予以贯彻执行。
与此同时,袁黄对入朝明军发布禁约,严肃军纪。袁黄获悉:援军中“无知之辈,乱打厨人,争先夺食,不成模样”,为严肃军纪,发布禁约文告:“朝鲜兵燹之余,人民乱离,天兵远来,专为救恤,往来官军,恃势侵凌,毁夺器械,以此驿夫苦累逃遁,致令公差忍饿,稽迟军务,两属未便。今后不许打夺饭食,不许抢掠财畜,不许殴辱官长,犯者依令处置。”〔16〕整肃军纪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应当指出的是,明朝援军违犯军纪,固然与明中叶以降边防日益废弛,军纪随之涣散有关,但援军不能及时得到粮饷供应恐怕也是事实。
“平壤大捷”后,随即发生“冒功请赏”事件,袁黄前往军中迅速平息。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统兵三万,渡鸭绿江,翌年正月初六日扺平壤城下,令部分将领围城,初八日早,如松“焚香卜日,传食三军讫,与三营将领,分统各该军兵”向占据平壤的日军发起猛攻,九日,攻下平壤城。〔17〕“平壤大捷”是明军入朝抗倭首战大捷,理应论功行赏,令人匪思的是,明廷却未论功行赏。其原因是李如松北军“冒功请赏”,引发南北军矛盾,从而招致科道官的弹劾。史载山东都御史周维翰、吏科给事中杨廷兰等上疏言:“李如松平壤之役,所斩首级,半皆朝鲜之民,焚溺万余,尽皆朝鲜之民。”〔18〕对于李如松斩杀朝鲜之民首级冒功的做法,李朝君臣强烈不满。朝鲜国王接见接伴使知中枢府事李德馨、平安道监司李元翼、左承旨洪进时,君臣对话中曾言及此事:
德馨曰:“前奏闻,以提督活出我国人之事陈之,若是则斩朝鲜人头之事,庶可发明矣。”上曰:“向义鞑子或见我国之人,必斩首削发云,然耶?如此之事,提督岂能尽知之?”元翼曰:“然。无人处见之,则必斩而献之。吏民及城中男女往来之人,斩头断发者亦多矣。”上曰:“如此之事,南将亦知其由乎?”元翼曰:“北军之所斩,南军必指而为斩朝鲜人之头也。”〔19〕
由于李如松斩杀朝鲜之民首级冒功的错误做法,引发了南北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冲突〔20〕,此事进一步发酵,严重地影响了援军的形象。
袁黄赶赴军中了解了真相后,质问李如松“老爷何为如此之事乎?”如松勃然大怒,挥臂叱责袁黄:“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袁黄针锋相对:“此是公论。”待双方冷静下来后,都各作让步,“黄谢以所闻之误,则北将亦叩头谢罪”,事态总算得以平息。〔21〕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后来事态的发展竟出乎袁黄意料之外,他被卷入了明廷内部的纷争。
正月二十三日,宣祖接见明廷派往朝鲜的天使黄应旸、吴宗道、俞俊彦等。交谈中,黄应旸言:“提督辽东人,分辨皂白,只喜杀戮,故俺赍免死帖万余道,专为活民而来。愚氓虽或畏死附贼,而如非向道者,则俺皆给帖安接,许还其本业。”〔22〕可见,如果无人上疏弹劾李如松冒功领赏,明廷绝不会颁发免死帖的。此事朝鲜很快获悉。二月二十日,宣祖与群臣议政时,曾云:“意外,提督被参,我国不幸,事适如此奈何?”知中枢府事李德馨也附和言:“以天下大将,既受重任,中原岂有轻论之理? 提督亦受天下之重任,又岂有中途弃归之理乎?”可见,此时朝鲜已确知李如松冒功请赏事被弹劾。接下来,李德馨又言:“与其手下人(李如松——引者〕相语,则提督见家书,多有不喜之色云,谓曰:‘吾之事为功为罪,未可知也。’”〔23〕如松平壤之役立功,反倒怕受惩,足以说明已被弹劾。问题是何人举报的呢?对此,平安道监司李元翼曾听到袁黄属下私议:“主事(袁黄——引者〕同年二百余人,布在台阁,此言必闻之,闻之,则大事必生。”接着君臣又有如下对话:元翼云:“且主事,以书遗骆尚志(南军将领——引者〕曰:‘凡论功之事,俱书而送之,皆以公等为首功,以报朝廷,公等将有大功。宋侍郎亦已知之。’”宣祖颇为赞同地回答:“此等争功之事,姑舍之。如此之事,古亦然矣。以公言之,南兵之功为首耶?抑北兵为首耶?”〔24〕从以上君臣所言推断,如松被弹劾缘于袁黄举报的可能性很大。但检索中外文献未发现袁黄上疏弹劾如松的直接证据,朝鲜君臣在谈论时也未提及袁黄,倒是云:“似闻宋侍郞即奏本于朝廷,故论劾云。”〔25〕如前所述,宋应昌出任经略,万历皇帝授予他“将领以下一听节制,违者以军法行”〔26〕之大权,但作为提督援军的如松显然其无权处置,只能借弹劾的方式打压他的气焰。宋应昌为浙江仁和人,与南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入朝后将南军视为嫡系,自然形成与北军及提督如松的矛盾。而袁黄也是南方籍,为应昌属下,诸多因素促使他站在以应昌为代表的南军系。这就注定了袁黄与以如松为代表的北军系发生矛盾,为后来被如松弹劾埋下隐患。
碧蹄馆之战后,袁黄又施用间计成功地解救朝鲜二王子,收回汉城。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四日,李如松所部“碧蹄之败,死伤甚众”,随后,日军将领清正“合阵于京城,贼势益盛,提督因此,不敢为再举之计”〔27〕。但王都汉城还在日军之手,无论如何,收复汉城乃是援军当务之急。为此,袁黄提出以谍战取代兵战的良策,得到允准。朝鲜获知后,领议政崔兴源即刻求见袁黄,请求解救二王子。《宣祖实录》详载如下:
臣到袁主事下处,告曰“本国二王子,时在咸镜道倭贼中,若大人差人飞檄,付送贼中,则庶有生还之理,敌方欲仰渎此意。而适闻大人差冯相公(冯仲缨——引者〕等往咸镜道云,此实机会。望大人作檄文,以付冯公之行。”主事即取笔砚作札付后,仍招前差三十人于前,问之曰:“汝等之中,有能入于咸镜道贼中,传此札付,图还二王子,则我即报兵部,为世袭指挥。”有二人应募曰:“小的愿往,但俱不识字,欲得一识字者同往。”主事曰:“汝二人应募,识字者,汝可拣了。”主事且曰:“本国北道,有一万兵云,故我差冯、金(金相——引者〕二人,领管下兵三十人同往,向导之人,须以惯知道里者定送。”〔28〕
引文中提及的冯仲缨、金相二人为袁黄属下。因被掠咸镜道“倭贼中”的宣祖二子,为国之根本,故身为领议政的崔兴源亲赴袁黄下榻处求助。由于袁黄巧施用间计不仅解救了二王子,还成功收复汉城。这原本是可喜可庆大功一件,但意想不到的是反倒给袁黄惹来了麻烦。问题是冯仲缨等用计使日军撤离汉城已是奇迹,却偏偏劫掠日军散兵游勇首级,邀功请赏。而事先并不知袁黄施用间计的刘黄裳获得内情后,十分恼怒,“忌黄收功,责其通倭结好”。为平息刘黄裳被瞒的怒气,袁黄只好分与其部分日军首级,以消其气。李如松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揭仲缨卖倭宵遁,论以军法,并揭袁黄罪。袁遂削籍。”〔29〕朝鲜文献也载:“北道斩倭之事,皆是刘员外、袁主事管下之人。”〔30〕显然如松因从中未得到好处,故而强加袁黄属下冯仲缨“卖倭”的罪名,借机弹劾袁黄,以此达到报复的目的。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首级是袁黄为己邀功请赏,还是用作其他?梳理朝鲜文献,此问题基本得到答案。三月二十六日,宣祖于备边司堂上与群臣议政,谈到援军将领,君臣有如下品评:
(兵曹参判〕沈忠谦曰:“华人好处甚多,而亦有不足观处。袁主事执沈喜寿(李朝问安使——引者〕手,入卧内,愿得首级新鲜者云矣。”上曰:“予专不闻也。”(同副承旨〕李好闵曰:“沈喜寿问安于袁主事,主事入帐内,求首级甚恳,且曰:‘非但我也,经略之意亦如此。’ 云。沈喜寿曰:‘大司马(宋应昌——引者〕以皇朝重臣,总兹戎重,官非不高,功即己功,岂肯为此。’ 云,则答曰:‘是何迂也。大司马岂不欲升职?且有不文不武两子, 岂不欲得首级乎?’”上曰:“此乃冯(冯仲缨——引者〕之事,无乃讹传为袁之言耶?”〔31〕
由上述君臣对话可得出如下判断,袁黄原得日军首级并非为己邀功请赏,而是受宋应昌之托,为其邀功,即应昌希冀借东征战事立功受奖,为他“不文不武两子”谋取官位。换言之,冯仲缨、金相截杀日军应是袁黄授意,以此满足上司的某种需要。可见,宋应昌假借袁黄之口营私舞弊是可以坐实的,至于刘黄裳参与分赃说明他与宋应昌并无二致。令人惋惜的是袁黄因此事被李如松弹劾,随即卷入京察之争,最终成为明廷党争的牺牲品。〔32〕
二、“贬朱褒王”论在朝鲜的反应
袁黄在学术上宗奉心学,在国内早已颇有名气,入朝后亦大肆宣扬“贬朱褒王”论,试图改变程朱理学在朝鲜思想界的正统地位,引起朝鲜士大夫的反感,进而又卷入明廷党争中,招致政治层面的打击,其学术倾向成为革职罢官的助推器。
如前所述,明朝文献中,几乎看不到明朝士大夫要求朝鲜改变宗奉程朱学之类的记录,而朝鲜文献中却有大量的记载。袁黄在战事之余不忘讲学论道。他与朝鲜士大夫论学,试图改变朝鲜尊朱的学术指向。有关袁黄与朝鲜士大夫的讨论,柳成龙(1542—1607〕有如下记载:
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万历丙戌进士……性好佛道,持身如山僧。尝与我国议政崔兴源语曰:“中国昔时皆宗朱元晦,近来渐不宗朱矣。”兴源曰:“朱子无间然矣。”主事頩然不悦。翌日,移咨举《四书注疏》,逐节非毁之。〔33〕
朝鲜儒者林宗七(1781—1859〕在其《屯坞集》卷 8《杂识篇》中记载更详:
皇明兵部主事袁黄以赞画军谋东来。袁之学术邪僻,左道惑众,专主禅陆,力排程朱。以一书送示行朝诸公,题曰:“为阐明学术事:自程朱之说行,而孔孟之道不复明于天下,天下贸贸焉,聋瞽久矣。我明兴,理学大畅,揭千古不传之秘,尽扫宋儒支离之习。”云云。因摘示朱子四书集注十余条,其末曰:“吾辈今日工夫,只学无求无著便是圣人,至简至易。较之朱说,孰是孰非云云。”中朝之学如此,极为寒心,天下岂能久安耶。行朝诸公欲力辨之,而畏其相激,有违于讨贼,当逊辞以答,而难于措辞,共推先生(成牛溪——引者〕起草。〔34〕
上述记载鲜明地表达了袁黄“贬朱褒王”的立场,显然以崔兴源为首的宗奉程朱理学的朝鲜士大夫是不予认同的,基于“欲力辨之,而畏其相激,有违于讨贼”的考量,退避三舍“逊辞以答”。然而,对于袁黄的“异端邪说”,朝鲜士大夫是绝不会使其在朝鲜有土壤的,所以“共推”朝鲜大儒成牛溪撰文驳难。因此,成牛溪(1535—1598〕遂撰有《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黄书》,其文如下:
小邦僻在遐远,学本通方,常仰中国书籍以为口耳之资。伏遇皇朝颁赐《五经四书大全》,表章先儒之说,列于学官,颁行天下。小邦之人,无不诵习而服行,以为此说之外,无他道理也。今兹小邦不夭,妖贼椓丧,老爷合下受命来讨,赞画军谋,军旅之外,旁及讲学之事,谆谆开导,牖以小邦迷昧之失,揭示前古不传之秘,甚盛举也。第缘某等末学肤浅,思虑荒芜,其何能言下领悟,发微诣极,以仰承老爷之至恩乎。今者邦国垂亡,上下皇皇,凡在陪臣,久困行间,平日所知,失亡殆尽,不得绎旧闻,以求正于有道,伏愿老爷俯鉴微悰,哀而怜之,讲学之事,请俟他日。〔35〕
作为朝鲜思想界的大儒,成牛溪的应答十分巧妙。面对“上国”入朝的军前赞画试图改变朝鲜信奉程朱的立场,既要固守朝鲜宗朱的立场,又要给足袁黄的面子。他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回应袁黄,认为朝鲜宗奉程朱,是遵依“皇朝颁赐《五经四书大全》”而来,言外之意这种遵依是不可改变的。同时,又巧妙地示意袁黄,朝鲜面临外寇侵凌,已陷于亡国灭种的境地,此时讨论学术不合时宜,而作为援军赞画此时辩论学术更是不得要领,“讲学之事,请俟他日”。袁黄见成牛溪答书,“嘉赏不复言”〔36〕。对此,朝鲜儒者林宗七评价成牛溪答书:“盖袁之意,欲以其说行之东方,而先生答辞虽逊,意思严而正,辞语婉而直,有以挫折其陂邪之锋,使不敢复肆鼓篁。”〔37〕
对于袁黄“贬朱褒王”的言论,朝鲜士人有诸多载录。如李廷龟(1564—1635〕《月沙先生集》中载:
天朝主事袁黄以赞画来,贻书论学,其言主陆氏而绌程朱,行朝诸宰难其答,请先生(成牛溪——引者〕草报。略曰:“小邦之人,皆诵习皇朝所颁经书传注,及性理诸书,以为此说之外,无他道理。”袁见之嘉叹,不复言。〔38〕
金尚宪(1570—1652〕在《清阴先生集》中载:
天朝主事袁黄以赞画来。贻书论学,专主鹅湖而绌洛闽,彼素亢倨,诸公不欲拂其意,而难为辞。属先生答云:“小邦诵习皇朝所颁经书传注及性理诸书,以为此外无他道理也。”袁不能复难。〔39〕
南克宽(1689—1714〕在《梦呓集坤》中也载:
李贽之出,风俗一变,猖狂无忌惮之言,皆自此人当为罪首。是固气机之变衰虚幻,非人力也。然其论皆昧于“制乎外,所以养其中”一句,必以发而直遂为第一义。今夫涂之人,见列肆之贝,其不欲攫而归也者,鲜矣。循此辈之论,必攫而后可也,岂不悖哉。牛溪跋袁黄之书曰:“世衰妖兴,一至于此。”断之确矣。〔40〕
以上所引袁黄“贬朱褒王”论在朝鲜的反应,内容大同小异,皆对袁黄之论持反对态度。表明朝鲜士人秉持程朱理学的立场。不容否认的是,袁黄之论在朝鲜士人中也多少引起些共鸣。其中以朝鲜大儒朴世堂为代表。朴世堂(1629—1703),曾著有《中庸思辨录》《论语思辨录》,书中对朱子学多有质疑,引起朝鲜士人的批判,如南有容(1698—1773〕曰:“朴世堂敢以朱子为可毁也,批注为可改。割裂章句,颠倒义例,其乱经悖常,真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也。又丑辱先正臣宋时烈,至比乱政大夫。”〔41〕结果在 75 岁高龄时,遭削夺官爵。〔42〕
对于袁黄“贬朱褒王”的言论,朝鲜君臣也有过专门的讨论。据《宣祖实录》记载:
(左相尹〕斗寿曰:“袁主事,非朱子之学,而宗阳明,尝贻书论学,答以微辞,而主事通书于其友曰:‘我来朝鲜论学,人有感悟涕泣。’ 云云,甚可哂也。”上曰:“此亦予所未闻之事也。”(同副承旨〕李好闵曰:“在定州时,所往复答辞,实玩弄也。”(兵曹参判沈〕忠谦曰:“其答辞云:‘我国蒙皇朝之恩,只知有四书五经,而干戈之际,旧业沦亡’ 云云,意不露而中含讥讽矣。”上曰:“其人非寻常底人,观给事中弹文,可知其人也。”(兵曹判书〕李恒福曰:“平时则不得志,而有才智,故受任以来也。”上曰:“著书亦多,分明非庸人也,渠之为人,心术不明而然也。今所谓感泣云者,全未闻也。”〔43〕
可见,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朝鲜,袁黄之论显然也得不到官僚士大夫的认同,相比之下,宣祖的评价还算公允。
三、援朝有功反倒成为党争牺牲品
万历二十一年是明京察之年。是年正月,大学士王锡爵归省还朝,重新出任首辅。为打压内阁,以吏部尚书孙为首的吏部官员借京察将诸多王锡爵的内阁亲信罢黜,但因树敌过多,遭致言官弹劾。科道官弹章中以“虞淳熙入吏部为私,复及主事袁黄、郎中杨于庭”〔44〕。这其中,虞淳熙为吏部郎中,吏部尚书孙同乡,袁黄身份特殊是首辅王锡爵的门生。如前所述,袁黄宗奉心学,不仅在国内颇有名声,入朝鲜后亦大肆宣扬其说,自然引起明廷程朱理学信奉者忌恨,进而招致政治上的打击。朝鲜文献载“言官劾其左道惑众,革职回籍”〔45〕是最好的辅证。王锡爵为袁黄座主,言官执意将其门生作为弹劾对象,身为首辅的他,生怕袁黄的学术“异端”给自己带来麻烦,关键时刻未能为袁黄争辩。吏部为力保虞淳熙、杨于庭,牺牲了袁黄,同意将其革职。但袁黄在朝鲜多有功绩,吏部不敢擅自做主,将球踢给皇帝。结果科道官上疏加以反对,建议罢黜虞、杨,以从公论,至于袁黄“候征倭事毕议处”〔46〕。孙再度为虞、杨力辩,惹怒圣上,被惩俸三月,将虞淳熙、杨于庭、袁黄等罢职或降级。〔47〕可见袁黄在这场京察政争中,成为了牺牲品。
袁黄而被弹劾罢职还与背负宋应昌“和议”的罪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壬辰战争爆发时,大明帝国已步入晚明,如同大厦将倾,尤其刚结束一场平叛大战,国库捉襟见肘,已不具备入朝鲜作战的条件。但在前近代东亚封贡体制下,作为东亚“共主”的明朝基于对属国朝鲜履行“扶危藩”责任担当,不得不出兵救援。所以援朝战争伊始,明廷内就一直存在战与和两种意见的争执。碧蹄馆之战失利后,议和之议便提到日程。收复汉城后中日间和议终未达成。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屡遭科道官的弹劾,他本人也因此锒铛入狱。〔48〕作为石星的忠实执行者,朝鲜战场的最高统帅宋应昌自然成为言官弹劾的对象。礼部主客清吏司提督会同馆主事洪启睿上奏弹劾宋应昌云:
宋应昌诚惶诚恐,以为背负议和封贡罪名太大,即上疏辩解,推卸责任。据其《经略复国要编》卷 14《辨明心迹疏》载:
臣于未复王京以前,臣实未曾题请封贡也。倭在王京乞款,臣始言之。然臣止是请封,未曾请贡。但沈惟敬至辽阳时,赞画主事袁黄曾言,倭中人有指封贡为和亲说话。臣与赞画刘黄裳大骇,面折其非。袁黄不悦,逐条陈征倭有十不利之说。此二十二年十二月初间事也。〔50〕
这里应指出的是,宋应昌惧怕承担议和责任尚可理解,但其将倡议议和的责任推卸给赞画袁黄就不能不令人费解了。必须承认袁黄也是主张议和的。对此,朝鲜文献多有记载。如朝鲜右议政沈喜寿就曾说过:“今此议和,袁主事主之。”〔51〕朝鲜国王李也言:袁黄“著书亦多,分明非庸人也……渠之学术虽如此,成事则可,而其人主和,误我国事矣”〔52〕。问题是袁黄仅仅是个赞画,他对朝鲜战局和战与否充其量仅有参谋权,毫无决策权。而决策议和的是得到内阁支持的兵部尚书石星及经略宋应昌。宋应昌为援军最高长官,李如松以下受其节制。整个平壤战事中,宋应昌一直在辽东,直到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这位“足不践朝鲜地方”的经略才渡江到朝鲜,朝鲜深知“侍郞出来,和战决矣”〔53〕。至于宋应昌与石星的关系,朝鲜认为“石尚书与宋应昌为一体”〔54〕。碧蹄馆之役失利后,就连反对议和的提督李如松也改变了态度。正如平安道观察使李元翼所说:“提督军中,一闻和议之成,莫不喜悦,欢声如雷”,“非但人人皆喜,提督亦甚喜”〔55〕。可见,议和是整个东征军都赞成的,作为赞画的袁黄何罪之有?如果说袁黄有罪的话,充其量是石星、宋应昌等议和决策者的忠实执行者。而宋应昌作为援军最高统帅为洗刷自己,将主和的责任推给袁黄,其人格之低劣令人发指。可怜这位在东征战场立有战功、本应受到嘉奖的袁黄,非但未得尺寸之赏,反倒成为明廷党争的牺牲品,被无情地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