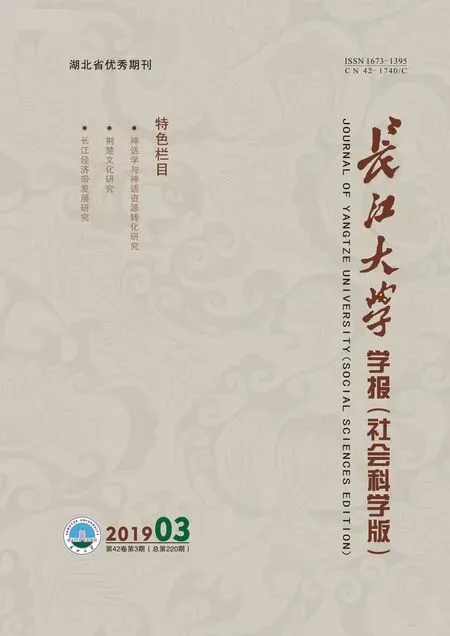西曲与南朝宫廷风尚
2019-02-15刘砚群
刘砚群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的西曲,是流行于南朝社会的乐府民歌。其以哀婉缠绵的格调,对南朝社会的市井生活情爱进行了或明或隐的大胆描写,体现了南朝社会市民阶层情爱意识的觉醒和人性自由,也实现了对先秦乐教“制乐以治心”“制乐以化民”的超越。[1]但西曲的“情爱”中心主题,缺乏更全面更广泛的对现实生活苦难的抒写,从根本上违背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P361),和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3](P596)的优良写实传统,以及历代创设乐府以“觇风于盛衰”“鉴微于兴废”[4](P226)的政教宗旨和功利目的。西曲“尚情”风貌与乐府宗旨和目的吊诡的真正原因值得思考。本文旨在探讨西曲之流行,及其入乐府与南朝宫廷沉湎享乐风尚和世俗化审美趋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嗜好声色的宫廷沉湎
《宋书·乐志》说:“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5](P549)相较于汉乐府而言,吴哥杂曲在乐府的数量上只是“稍有增广”,显然是让史家颇感遗憾的事情。言为心声的民歌,是作为社会生活实践中个体的人在群体关系中对社会生活和人生体验最广泛、最自由、最真诚也最本质的情感抒发,正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各言其情”[2](P361)。根源于基本生活本相的民歌,理应涉及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世态人情有最直接最广泛的表达,但以西曲和吴声为代表的南朝乐府民歌,在乐府中只是“稍有增广”,在主题和题材上却表现出孪生同胞一样的惊人相似性,即“内容单调,几纯为男女相悦之情,画眉注口之事,绮罗香泽之态”[6](P304)。这或固然与西曲和吴声产生的水性地理环境和市井生活相关,除此而外,也是南朝社会沉湎享乐的社会心理和嗜好声乐的生活风尚的主观选择的必然结果。
“南朝乃一声色社会。”[6](P200)这是萧涤非先生对整个南朝社会生活状态的破的之论。“迨晋室东渡,中原沦于异族,南朝文物,号为最盛。然以风土民情,既大异于汉,加以当时佛教思想之流行,儒家礼教之崩溃,政治之黑暗,生活之奢靡,于是吴楚新声,乃大放厥彩,其体制则率多短章,其风格则儇佻而绮丽,其歌咏之对象,则不外男女相思,虽曰民歌,然实皆都市生活之写真,非所谓两汉田野之制作也。于时文人所作,大抵亦如此。乐府至是,几乎与社会完全脱离关系,而仅为少数有闲阶级陶情悦耳之艳曲。”[6](P25~26)在经历了汉末社会风云变幻的生命意识启蒙和魏晋玄学的自由思想洗礼之后,基于感性生命意识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到了南朝社会,因缺乏从个体感性到社会理性的升华,即缺乏个体对社会历史责任的道义担当和社会事功的主观追求,已然从魏晋之际的“重性情”转向了南朝人的“纵声情”,特别是在儒学式微、思想解放、儒道玄佛融通并进的大背景下,在东晋以来的门阀政治的深刻影响下,文人的政治生活选择更是从魏晋之际基于对生存的焦虑所作出的对政治的被迫疏离,在经历两晋的疏宕风流后,转变为南朝士大夫的主动远离放弃,建安慷慨悲凉的气骨风神,正始言近旨远的批判意识,甚至东晋体玄悟道的思辨精神,到南朝时,已渐趋纤弱以至于荡然无存。逃避了社会责任,远离了底层民众的苦难,南朝人凭借着自己的声乐修养或文学才华,沉湎在对世俗生活情感的浪漫主义审美愉悦里,纵情享受着俗世的感性快乐,也极大地释放着人的感性生命的本真性情。诚如王运熙先生所言:“六朝是一个大纷乱的时代。空前残酷的民族战争,频繁篡夺的政治局面,放浪无为的老庄思想,这些因素凑合起来,使得当时的贵族们眼中地感到了生命的无常,从而尽量趋向于消极的目前享乐。”[7](P14)
南朝“全社会皆崇尚声色伎乐”[8](P186)。据《太平御览》卷569引裴子野《宋略》载:“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又李延寿《南史·良吏传序》所记:“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元嘉)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粧。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9] (P1696)南朝人对自然生命的感发,纵情声色,嗜好歌舞,完全形成了一种自宫廷至民间的自上而下的柔靡风气。有关南朝宫廷享乐淫逸的记载,于史册俯拾皆是,如(刘宋)沈勃“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酣放纵,无复剂限”[5](P1687),杜幼文“所往贪横,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5](P1722),范晔“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5](P1829),徐湛之“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5](P1844),沈庆之“妓妾数十人,并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意欢愉,非朝贺不出门”[5](P2003),齐武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10](P1063),等等。仅从这些文献的记载,就不难感受到南朝社会不论文臣武将、君主臣僚、朝野后宫对声色的普遍好尚与沉湎,一度到了蓄养男妓、攀比争风甚至亲属乱伦的腐靡地步。前文所列徐湛之所蓄千余门生即为男宠,杜幼文则因为嗜好声乐引起废帝“不平”而直接导致了被杀,“(废)帝微行夜出,辄在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5](P1829)。这个前废帝刘子业也算是个极品皇帝了,不但和自己的同母姐姐山阴公主、亲姑母新莱公主乱伦,更是为“淫悠过度”的山阴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9](P71),以满足其在私生活上追求男女平等的私欲。此后又有齐郁林王为文安王皇后“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9](P331)的效仿之举。在生活荒乐淫侈这一点上,刘宋父子两任皇帝真可谓不相上下,把东晋以来的纵情享乐之风的延绪余波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据《宋书·后妃列传》载:“太后居显阳殿。上(宋孝武帝)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5](P1287)刘骏的蒸母丑行,即便是在相对放纵的南朝社会,也导致了民间喧然,只不过宫闱事秘,不得不讳。又《宋书·刘义宣传》:“世祖闺庭无礼,与义宣诸女淫乱,义宣因此发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举兵。”[5](P1800)又《南史》:“殷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也。丽色巧笑。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宠冠后宫。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9](P323)君临天下,刑于四方的皇帝和生母私通,和堂妹(据《南史》一说)缠绵,可见南朝宫廷的声色淫侈的感官享乐到了何其普遍和混乱的地步。就连梁武帝都认为社会风气的败坏,“夫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世之浇淳,恒由此作”[10](P15)。南朝宫廷纵情声色,“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5](P1990)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也就不难理解到了陈代“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社会现实。针对这“上慢下暴,淫侈竞驰。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弩爵,贿货公行……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堤绣是袭。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10](P15)的状况,梁武帝认为整个社会的声色沉湎严重到了“弊国伤和”的程度,要“自非可以奉集盛,修级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庭备御妾之数,大予绝郑卫之音”,并请从自己开始,“菲食薄衣”,以期“人务退食,竞存约己,移风易俗”[10](P15),并下诏放遣宫女:“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後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给廪食。”[10](P35)带头行俭,以为表率,放遣宫女,以戒逸乐,梁武帝决心可谓坚定,气势可谓浩大,可从历史效果看,实则没有根本改变世风时俗,个中原因,足以让人深味了。
可见对于声色嗜好、恣肆淫侈的习气,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们不是没有觉察,忧虑之臣不是没有献策,朝廷也不是没有采取办法,只不过政策只见于诏令文书,声色使人忘情,世风成易改难,欲罢不能而已。据史载,早在刘宋时期,就有了关于伎乐的禁令,但无人遵循,前文所引《宋略》“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的文献之后,尚有“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之辞,“莫为禁令”,可见禁令是有的,但只限于文件而已,并没有落实到日常生活中。齐武帝箫赜在永明七年(489年)也曾诏令禁止侈靡婚风:“晚俗浮丽,历兹永久,每思惩革,而民未知禁。乃闻同牢之费,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11 ](P56~57)可终究未能移风易俗。
如果说思想的转变导致了南朝人嗜好声色的生活选择,那“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偏安江南的统治者提供了享乐腐化的物质基础”[12](P172)。即便是帝祚短命的南朝,也曾出现过元嘉之治和永明之治的盛世景象:“江南之为国盛矣……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5](P1540)这是《宋书》里沈约对南朝人生活富足的描绘,可以感受得到出于言表的溢美之情。“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装,桃花绿水之间,秋风春月之下,盖以百数。”[11](P913)这是《南齐书》里箫子显眼中的南朝人的世俗生活图景。江南的烟雨、经济的富庶与都市的繁盛,使南朝统治者沉湎于对此刻生命的享受之中。
南朝以水为脉发达的商业文明,产生了诸如荆州和扬州这样繁荣的港口城市(“荆、扬州,户口半天下”[5](P1738)),也孕育了西曲以哀婉感伤为主的繁复的商旅码头情结,如《估客乐》《三洲歌》《那河滩》等。都市码头不仅是商业的繁华之地,也是贵族巨贾的集居之所,更是物质消费和文化交流的交汇中心。这里一方面是各级贵族富商大贾的声色享受之处,同时也是民间乐舞艺人为谋生的寓居之所。迎来送往,相思离别,牵挂怨念,往往一水贯穿。“《西曲》中多商人歌。”[13](P28)繁荣商贸是西曲产生的土壤,也是西曲吟诵的情感对象。商人为利而动风波不定,而又衣冠奢华出入繁华之所,梦绕富贵之乡,风流影响到南朝社会生活的深处,无疑也刺激了全社会的享乐欲望。更值得注意的是,南朝的宫廷贵族,相当一部分本身有商贾身份,或有深刻的商旅记忆,这对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审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嗜好声色的沉湎生活态度,经济繁荣带来的充足的物质享乐保证和精神刺激,以及商旅生活的深刻记忆,使南朝宫廷对西曲的哀感特质和浪漫情怀葆有强烈的主观喜好选择,而西曲的流行丰富了南朝的宫廷享乐,也促成了审美趣味的趋俗化转变。
二、世俗化的审美趋向
南朝社会对声色的沉湎,必然带来审美趣味的世俗化转变。整个南朝偏安江南,以水为脉的市井生活,养成了南朝人柔情的水性人格和以柔为美的审美趣味,经济的繁荣和思想观念的转变,陶养了南朝人追求世俗生活的享乐思想。西曲和吴声正是在此土壤中得以滋养并繁荣,而又以其浅俗鲜丽的语言、明媚巧妙的表达、浪漫炽烈的情爱、缠绵哀伤的格调、谐隐双关的意味,逐渐受到南朝宫廷的喜爱。加之南朝诸朝统治者,多出身寒门行伍,对于民间的流行俗乐,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感,是以吴声、西曲先后盛行于南朝上层社会中,尤其是郎情妾意、“歌词多浮哇不典正”的西曲,其感伤的情爱基调,与传统的雅乐和旧的清商乐相比,更能缱绻摇曳人情,从审美趣味和娱乐性上看,更能引发人的生命之思、悲情之美,也最为南朝宫廷所好尚,最终导致了“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5](P553),以及“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14](P288)的局面。据《南齐书·萧惠基传》:“自宋大明(孝武帝年号)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12](P811)《南齐书·王僧虔传》:“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11](P594),“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11](P595)。史书载记,均可参证其时风貌。
南朝宫廷对新声的好尚,渗透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喜听能唱,甚至直接参与创作。据《旧唐书·音乐志》:“宋、梁世,荆、雍为南方重镇,皆皇子为之牧,江左辞咏,莫不称之,以为乐土。”[15](P1066)虽为牧主一镇,实为享乐一方,于斯可以探知其中本柢。《宋书·范晔传》载:“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宋文帝)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5](P1820)这是一幕极具戏剧性的情景:文帝欲闻精弹琵琶的范晔奏新声,几番微讽旁敲侧击,一个明知上旨却仍装聋作哑,最终还是文帝放下架子乘着宴饮欢适直接请求,一个才漫不经心且奏且和。上层社会对新声的喜好之情由是可见一斑。又《南史·王俭传》载:“(齐高)帝后幸华林宴集,使群臣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9](P593)君臣相娱,一时竟尊卑莫顾。南朝宫廷对西曲新声的嗜好,无疑刺激了西曲的流传和对上层宫廷生活的进一步渗透,直接影响了宫廷审美趣味的世俗化。
如果说对西曲新声的喜听乐唱只是宫廷声色生活趋俗的一种表现,加速了西曲的流传的话,那么创制新曲则表明,南朝宫廷贵族已然投身到新曲的具体生产创作中了。换句话说,南朝宫廷生活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对整个西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宋书·乐志》:“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夜飞哥曲》,并列于乐官,歌词多俘哇,不典正。”[5](P552)沈约对西曲曲词“浮哇不典正”的批评,只能说明沈约的审美趋向可能比较正统尚雅,毕竟自西晋以来的浮华风气已经由来已久了,风气所及,大化流行,能免其俗也着实希贵不易。
郭茂倩《乐府诗集》现存的33曲(佚《黄缨》1曲)146首(不含拟作)西曲中,明确表明创作者宫廷文人身份且有故实的有7曲45首,约占全部西曲的三分之一,若算上有归属无故实的作品,那就更多了。其具体曲目及曲数大略如下。臧质的《石城乐》(5首)。《唐书·乐志》曰:“《石城乐》者,宋臧质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质尝为竟陵郡,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暢,因作此曲。”[16](P689)刘义庆的《乌夜啼》(8首)。《唐书·乐志》曰:“《乌夜啼》者,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於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庆大惧,伎妾夜闻乌夜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16](P690)齐武帝的《估客乐》(1首,另释宝月4首)。《古今乐录》曰:“《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於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鍮石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黄裤,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16](P699)刘诞的《襄阳乐》(9首)。《古今乐录》曰:“《襄阳乐》者,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始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仍为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歌谣,因而作之。”[17](P703)梁武帝的《襄阳蹋铜蹄》(3首,另沈约3首)。《隋书·乐志》曰:“梁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蹄,谓金蹄,为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16](P708)刘铄的《寿阳乐》(9首)。《古今乐录》曰:“《寿阳乐》者,宋南平穆王为豫州所作也。……按其歌辞,盖叙伤别望归之思。”[16](P719)沈攸之的《西乌夜飞》(5首)。《古今乐录》曰:“《西乌夜飞》者,宋元徽五年,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以歌。”[16](P722)其中的这两位作者身份尤需引起注意,那就是齐武帝和梁武帝。这个齐武帝,就是前文提到颁过诏禁过奢的那位南朝第二代皇帝,可在对待西曲新声的态度上,他不但喜欢西曲创制西曲,还命宝月和尚为之谱曲,完成后更是在水上进行表演游观。五城的舟帆犹在目前浮现,篙榜者的歌声尚在耳畔回响,相比于其他宫廷权贵而言,他可谓过而无不及了。梁武帝也非等闲,也曾经带头行俭戒奢放遣宫女,但在“天监十一年,武帝于乐寿殿道义竟留十大德法师设乐,敕人人有问,引经奉答”,共论商人歌《三洲歌》,法云谓“古辞过质”,“应欢会而有别离,啼将别可改为欢将乐”,“歌和云: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旁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16](P707)把西曲和讲经打包,共论“天乐绝妙”,是乐坛奇景,也可谓天下创举了。齐、梁二代正是西曲最为流行的时候。如前文所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好尚选择,是可以直接作为宫廷及市井生活的影向标的,齐梁社会对西曲的态度由此可以觇测,南朝宫廷审美趋向的世俗化也得到了最强有力的体现。
要之,西曲在乐府中呈现的“尚情”风貌,是南朝宫廷耽乐风尚和世俗化审美意趣的主观选择的必然结果,南朝宫廷嗜好声乐、沉湎享乐的生活风尚和世俗化审美趋向,造成了西曲的实际面貌与乐府“观风俗,知薄厚”“觇风于盛衰”“鉴微于兴废”宗旨的吊诡,西曲也正是从世俗情爱层面反映了南朝社会沉缅声乐享乐的宫廷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