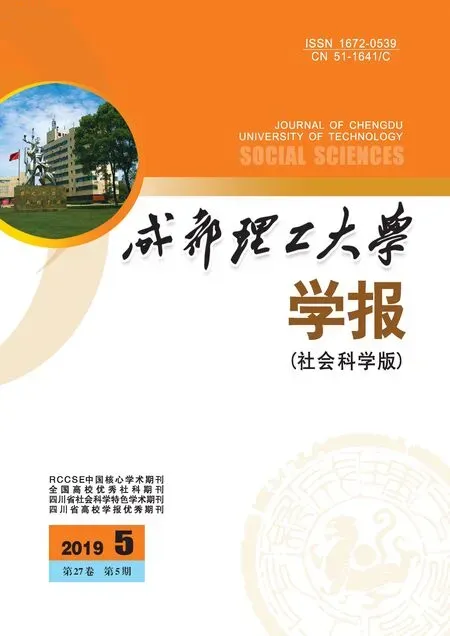评《永徽律》“化外人相犯”条
2019-02-15陈若愚
陈若愚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50)
“化外人相犯”又称化外人有犯,据唐高宗时期所编纂的《永徽律》记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1)“化外人相犯”条因其开放包容的特性而广受赞誉,甚至被称为“最优美的条文”[1]。“化外人相犯”条基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法律背景而产生,它与其他相关制度一道,解决了法条适用对象及案件范围的问题,并受到了化外人士的好评。这一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制度并未被一直沿用下去,但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一、“化外人相犯”条的产生背景
(一)政治背景
在谈及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时,我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元朝和清朝。而比起完全由汉族所建立的汉朝、明朝等,唐朝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李唐政权的建立者和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这种联系也影响着唐朝的对外政策。
尽管唐室自称来自陇西狄道,但李氏曾长期于武川镇戍守边疆,还曾使用过“大野氏”作为姓。由此观之,李氏先祖就算不属于北方民族系统,也与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族人独孤信的四女。唐太宗的母亲窦氏,其母系为宇文一族,而宇文是鲜卑大姓,故窦氏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同样也带有鲜卑血统(2)。从李渊到李治,唐朝的前三任皇帝皆由带有鲜卑血统的女子所生,再结合李氏先祖的渊源,我们不难发现李唐的掌权者或多或少与少数民族有关联。
这一特殊性最直观的表现,就体现在唐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上。唐太宗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其施政纲领也正是如此。(3)这种思想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唐初的边防较为松散,中央政府以羁縻府州和册封制度进行管理。“化外人相犯”条作为唐朝的涉外立法,也是基于这种特殊思想而产生的。
(二)经济背景
每条法规的产生,都有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化外人相犯”条也是如此,唐朝频繁的对外经济往来为该条的出现及适用提供了可能。
唐朝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在原有基础上更为便利,其中有唐朝主动修建的,也有周边政权修建的,如北方民族修建的参天可汗道[2]。据贾耽的《皇华四达记》记载,当时对外的主要交通干道有七条之多。这些干道四通八达,既可抵达朝鲜半岛,又可通向西域诸国,还可经帕米尔高原及天山至中亚西亚,甚至能远达欧洲(4)。
由于相对便利的交通,大批异族人从路上丝绸之路来到唐朝,他们怀着外交、学习、贸易等不同目的,在长安和洛阳聚居。据德宗时期鸿胪寺记载,光是各国使者及人质就已有四千余人,而经商者更是数倍于此。随着交往的深入,商业往来不再仅限于众所周知的茶叶、丝绸、香料,而是触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长安甚至出现了胡人的饼子铺。
同时,唐朝的海上贸易也十分繁荣,这里以扬州和广州为例。在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扬州的经济飞速发展,而运河使扬州真正受益,则是唐朝的事。此时的扬州商贾云集,已成为一座国际贸易城市,在此下锚的外国商船来自多个国家,近有新罗、日本等国,远有波斯、阿拉伯等国。在唐朝中后期,定居扬州的商人已多达数千人;而广州的对外贸易更胜扬州。唐僧鉴真从扬州出发渡海,却被风暴刮至广州。在那里,他看到了“从婆罗门、昆仑(南海诸国)来的商船,满载着堆积如山的香药和珍宝停泊在港内,此外还有从狮子国、大石国、白蛮、赤蛮(东南亚诸国)等来的很多商船”[3]。
(三)法律背景
“化外人相犯”的有关规定最早出现在《永徽律》中,其中化外一词,也是于唐律首见书证[4],但这并不代表“化外人相犯”条就与之前的法律全无关系。
唐朝建立后,在法律方面首先废除了隋炀帝时期的大业律令,重新回到了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令体制中。唐高祖发布了以《开皇律》为范本的《武德律》,之后进行了数次修改。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修改法律,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形成了《贞观律》。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李绩等人修《永徽律》,《永徽律》于次年(651年)九月完成,“化外人相犯”条就在其中。鉴于对法律的理解没有一个权威标准,唐高宗还在永徽三年(653年)召集法律水平较高的大臣对《永徽律》进行逐条解释,撰《律疏》共三十卷,与《永徽律》合为《永徽律疏》。
唐高祖时期皇上选择恢复开皇旧制,即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隋文帝的关中本位政策,而否定了隋炀帝的江南本位政策。这一政策使得唐朝把军事政治主轴定位于长安。在这里,唐朝与北方民族互动更多,而基于李唐政权的特殊性及政治经济需要,统治者更倾向于对异族人采取一种怀柔政策。对开皇律令的继承,可以说是为“化外人相犯”条奠定了基调。之后的《贞观律》,在承袭这一基调的同时,又在唐太宗的明确要求下,具备了宽简、平允、统一的原则。因此,在后来的“化外人相犯”条中,我们不难看出条文对这些法律原则的体现。
二、“化外人相犯”条的适用
(一)适用对象
“化外人相犯”条不到三十个字,但其中的关键词却耐人寻味。在讨论其具体适用范围时,“化外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字眼。究竟何为化外人?这一问题在学界探讨颇多。有的学者认为,化外人并不是指国内的少数民族,而是指外国人,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化外人除了外国人,也包括少数民族。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采取后一种理解更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1.“国”的概念
其实,《永徽律疏》第六卷名例第四条对化外人一词已有了详细的描述。律疏将化外人定义为别有君王的番夷国家的国人,同时还注明这类国家的风俗法度与唐朝有所不同(5),如高句丽和百济就属于蕃夷国家。
那么,北方少数民族算不算蕃夷之国呢,国的概念又是如何界定的呢?在传统观念中,说到少数民族,我们会想起突厥、鲜卑、匈奴等民族,而提到国家,则会想到高句丽、安息、大秦(罗马)。其实,那些少数民族也是成立过自己的国家的,如突厥成立过突厥第一汗国、突厥第二汗国,铁勒部的回鹘也建立过回鹘汗国。与高句丽等国相比,他们也有着独立的政治体系。那么,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区分北方少数民族和蕃夷之国呢?一方面,我们以农耕和游牧进行区分,另一方面,我们以距离感及臣服度进行区分。而事实上,唐王朝也是这么做的,唐朝对于距离近、臣服度较高的游牧民族,多采用相对严格的羁縻措施进行管控,对于距离远、独立性强的农耕部族,则以册封为主。但这并不绝对,如高句丽灭亡后唐朝也在朝鲜半岛设置过羁縻府州。
不论羁縻还是册封,都更多是一种名义上的管控,而非实际管控。事实已经证明,我们认为只算是少数民族的部落,其中部分与高丽百济一样,有着自己的君王和法度风俗的。因而认为少数民族不算国,从而不适用“化外人相犯”条的观念是有所疏漏的。
2.外国人的概念
时至今日,外国人是指不具有内国国籍之人。有观点认为化外人指的就是外国人,而实际上“外国人”(6)一词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5]。有了外国人一词,为什么还要用化外人呢?答案就是二者并不等同。外国人当然属于化外人,但化外人除了外国人,还包括异族人,即少数民族。今天的外国人主要是从国籍上加以区别,然而唐朝并没有国籍这个概念,所以唐朝的外国人更偏向于地域上的概念。化外人则具有更强的概括性,它从多方面进行区分。《唐律释文》的解释便是一个例证,释文认为东夷与西戎之人有相犯情节时,应当以中华的法令判决[6],这里的东夷与西戎,显然是把异族人算在化外人的范围内。
3.化外人的概念
化外人中的“化”,在中国古代含有教化礼仪之意,汉代学者郑玄进行了如下注解:“教谓礼仪,政谓刑禁。”[7]可见在我国古代,教化的作用就是移风俗、通礼仪。同时礼、法又是紧密结合的,对于民众,国家首先施以教化,而对于礼教所不能化者,则以法律迫使其遵循统治者所推行的教化。化外之地,即中原的法令与教化无法传达的地方。外国毫无疑问是化外之地,那以羁縻形式管控的地区算不算呢?在古汉语中,羁和縻都是用于控制牛马的工具,从这个解释看,设立羁縻府州的目的在于便利中央管理边远地区。但实际上这种管理的掌控力度并不大,有实权的刺史或都督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而唐朝只能设立都护府监领。羁縻府州的人民不必向唐朝纳贡赋税,也不入唐朝编户,其首领享有独立的权力。当地首领以原有方式处理内政,唐朝无权干涉,唐朝的教化及法令自然也就无法在这里施行。由此看来,羁縻府州的少数民族是属于化外人范畴的。
化外人从教化的角度对适用对象进行了区分,同时它也从地域角度进行了区分。化外人这个词在《唐律疏议》中出现了不止一次,它在《唐律疏议》第八十八条的《卫禁》中也有登场(7)。在该条文中,化内化外与边关也产生了一定联系。此处的化内与化外,带有以边关为分界而产生的境内与境外的含义。
化外人有着高度的概括性和灵活性,它以教化区分为主,以地域区分为辅。立法者在订立“化外人相犯”而不是外国人相犯时,展现了高超的立法技巧,因为“化外”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概念。帝国的疆域边界在不断变化,原本的化外人也可能变成化内,如那一万多因战败而被迁入长安的突厥人,他们的后代就会慢慢被汉化。甚至就连外国也会变化,在修订律疏时被当作例子的高句丽和百济,不就在武则天时代被灭国了吗?由此观之,化外人是一个带有时代性的词汇,它给出了大致的指引,但究竟什么是化内、什么是化外还需结合当时的情况。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化外人不仅指异国人,还包括未被汉化的异族人。
(二)相关制度
1.译语人制度
“化外人相犯”条因其所蕴含的包容和人性,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学界也存在不同声音,认为这一制度难以操作,司法官无法听懂外国语言,也不通晓外国法律,从而无法裁判。这一观点有其道理,但在实践中“化外人相犯”条并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唐朝还有其他的制度配合其实施,例如译语人制度和接下来要提到的蕃长制度。
译语人是专门负责翻译异族异国语言文字的人,我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外事管理机构和翻译职称[8],此后秦朝设立典客,北魏设立译令史,译语人制度经过历代发展直至唐朝,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
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语人在法律诉讼中的身影。在新疆阿斯塔那210号墓出土的《唐贞观二十三年杜崇礼等辩辞为绫价事》残卷,记载了杜崇礼在高昌县与少数民族交易的过程中,因货物价格的问题而被官府勘问。该残卷可辨识的部分仅有七行,但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行是专门为译语人签字画押而设计的,这说明了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译语人确确实实参与到了裁判过程中来,为双方沟通提供了帮助。相比前一卷文献的有所缺失,《麟德二年五月高昌县勘问张玄逸失盗事案卷》则记载了更多的信息。在该残卷中,案件当事人春香是一名奴婢,但因她是突厥人,不通汉语,于是官府派出译语人翟浮知为其翻译。在出土的文献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译语人翟浮知的名字,还能够看到他画押的指节痕迹。在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中,有这样一起行政案件:一队中亚商队前往中原进行贸易,但没有唐朝颁发的出入关卡的凭证,便被唐西州地方官府查问。因语言不通,由译语人翟那你潘为商队作出辩词[9]。从以上三篇文献残卷看来,译语人制度较好地扫清了语言障碍,因而“化外人相犯”的施行并不会因语言不通而受阻。
此外,唐朝为了明确译语人的法律责任,还有相应的法条进行规制。《永徽律》卷二十五对“证不言情及译诈伪”作出了规定,其规定译语人若是不如实翻译或作伪证,则与犯人同罪。在之后的《唐律疏议》中,法条又对译语人犯罪的量刑细节进行了规制,还补充了议、请、减的适用情形(8)。唐律之所以加以立法并详细说明,主要是为了规范译语人的行为,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唐律的公平公正。
2.蕃长制度
唐朝年间,在重要的沿海贸易城市会有大量外商聚集,久而久之形成了外商聚集区,也就是蕃坊。蕃坊的首领称蕃长,由外商推举并由唐朝皇帝审批任命。蕃长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化外人相犯”条的实施。
说到唐朝的蕃坊,一般指在广州一带形成的波斯穆斯林蕃坊。但蕃坊并不仅仅在广州附近出现,其他沿海地区也有蕃坊存在。登州楚州一带是唐朝对新罗的交通口岸,在此也出现了新罗人聚居的新罗蕃坊。蕃坊的管理机构称蕃长司,设蕃长一名主持管理坊内事务。蕃长所处理的内部事务,其中也包括部分法律事务。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为欲裁决广府回教徒之争议,由支那皇帝简选一回教徒。”[10]7这一段文字是唐朝任命广州穆斯林蕃长时苏莱曼所记,这说明唐朝赋予了蕃长一定的司法权。但这种司法权是受到限制的,首先蕃长只能在广府行使,其次还必须是回教徒之间的争议,即回教徒与汉人,回教徒和其他异族异国人的争议蕃长是无权审理的。这一制度一方面保护了唐朝的司法主权,防止了蕃长滥用权力;另一方面,由知晓回教法律的蕃长来裁判,也解决了异类相犯时唐朝司法人员不熟悉异族法的问题。唐律规定的“化外人相犯”条是由唐朝政府依据唐律断案,而蕃长制度有些特殊,它是由唐政府授权蕃长,让蕃长“依其俗法断之”。让通晓本族法律的人司法,无疑能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在实践中,这种蕃长制度和“化外人相犯”条相结合的模式颇具成效,《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长官行使职权,所作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及其他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真主经典的,同时也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10]7
(三)效果评价
社会实践中确实出现了“化外人相犯”的情况,唐朝才制定了法律以期调整。那么,调整的结果如何呢?从现有资料来看,“化外人相犯”条的施行效果应当说是令人满意的。
这种良好的效果首先表现在它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上。从前文所列举的种种案例来看,不论是在长安、洛阳、广州这样的大都市,还是在敦煌高昌这样的偏远地区,“化外人相犯”条都切实解决了涉及化外人的法律问题。其次,通过化外人对这一制度的称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施行深得人心。对于其中的同类相犯以本俗法裁判,外商从中体会到了唐朝对民族习惯的尊重,他们的感受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也有所记载:“故商人来此者,皆颂声载道也。”对于异类相犯按唐律断处,唐律也因其本身的公正合理而使化外人心服。曾有阿拉伯商人回忆唐朝的债权法律制度,并作出了如下评论:“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方法,放债人与借债人之间的矛盾总是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10]18-19
但这种良好的执行效果是依赖于唐朝强盛的国力,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为衰弱,“化外人相犯”条的实际效果也大打折扣。前文曾提到一案例,即京兆尹拘捕了杀人的回鹘人,唐代宗却不予处罚。而同年九月,又有回鹘人刺伤市民,官吏将其关押。回鹘首领赤心竟然砍伤狱卒,劫走囚犯,唐代宗亦不追究(9)。伤人、杀人、劫囚,都是唐律中有明确规定的犯罪,此时犯案的回鹘人按“化外人相犯”条应以唐律论处,为什么唐代宗却不予追究呢?原来,回鹘在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立下大功,战后有大量回鹘人留在长安,他们自恃功高肆意妄为,甚至普通回鹘人就敢强抢长安令邵说的马匹,而唐朝方面却无可奈何。为了不触怒回鹘一方,唐代宗对于回鹘人的违法乱纪行为只能一再宽恕。此时,由于国力问题,唐律的威慑力和尊严不复以往,“化外人相犯”条的执行效果也大不如前。
三、“化外人相犯”条的变迁
(一)宋代的化外人
宋朝的《宋刑统》对《唐律疏议》没有太大改动,有关化外人的规定也基本沿袭了唐朝的“化外人相犯”条。但在具体操作中,宋朝“化外人相犯”的处理有了变动。据宋人朱彧所著的《萍州可谈》记载:“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挞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蕃人不衣裈裤,喜地坐,以杖臀为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11]文献表明,蕃人犯了罪,首先由地方政府查明案情,案情较轻的由蕃长处理,徒刑以上的犯罪则交由宋朝政府处理。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唐朝单一的属人或属地,宋朝的规定更为详细。不论案情如何,首先都要送交宋朝政府,这可以说是属地主义的一种强化。而这种属地主义强化的趋势,在宋朝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汪大猷传》记载:“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大猷则有言:‘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12]9552相似的案例还有王焕之知广州时,有蕃客杀奴,市舶使认为该“送其长杖笞”,即由蕃长惩罚,但王焕之不同意,认为要“论如法”,即以宋律论处[12]8773。这两个案例都是司法者对属地主义的贯彻,在宋朝,对化外人的处理原则已由唐代的属地属人并用,慢慢向属地主义转变。其实这一转变并不难理解,唐代的华夷观是四海一家,而宋朝则前后与辽、金、蒙古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交战,此时民族矛盾激化了华夷有别的思想,宋朝的化外人政策也自然向属地主义不断倾斜。
(二)明清的化外人
比起宋朝的向属地主义倾斜,明朝则是在化外人问题上彻底采取了属地主义(10)。在明朝,不论是化外还是化内、同类还是异类,法律明文规定案犯皆以大明律拟断。我们在评价这一制度时,要考虑到明朝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已有了较大的改变。明朝是汉族推翻蒙古族的元朝后所建立的,而蒙古族统治者对汉族施行种族歧视制度,这自然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矛盾突出。明朝立法者华夷之别的观念甚至比宋朝更突出,当然不可能采用唐朝有关“化外人相犯”的规定。此外,如果采用同类相犯依其本俗法,那么,对于元朝灭亡后大量滞留在中原的蒙古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间的冲突要用元朝的旧法调整,这对明朝统治者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们确立了严格的属地主义。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在开放性和包容性上不如唐朝,但明朝的属地主义在当时确实是更有利于社会稳定的[13]。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基于行为人的特殊身份,皇帝会选择让行为人的本族首领处理,例如这种情况会在异族使节犯法时发生(11)。
清朝对化外人的处理继承了明朝的规定(12),也采用了属地主义。但清朝不似明朝那么严格,随后又出台了一些变通的政策,如在雍正三年规定隶属理藩院管理的人仍然适用原定蒙古法律。之后又有《回疆则例》《苗例》等民族政策问世,给予了少数民族法律上的特殊照顾。这一方面是基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现实,另一方面也和清朝统治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有关。但遗憾的是,由于后期清朝国力衰弱,这种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属地主义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对于外国人侵害中国人的案件,当地政府往往并不积极追究,而是由当事人双方私了。之后出现的领事裁判,更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极大损害。
从清末属地主义的难以贯彻,联想到唐代宗时期唐朝对回鹘人的无可奈何,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涉外法律而言,国力就是法律执行的保障。当国家强大了,外国人才会服从法律,而在国力不济时,再美好的法条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1)参见:《唐律疏议》第六卷名例第四条。
(2)欧阳修所撰写的《新唐书》中记载:其先魏拓跋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
(3)唐太宗曾在贞观年间表示:“自古以来皆贵中华,贱夷狄,唯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同时其施政思想为: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4)《皇华四达记》对干道记载如下:一曰营州入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5)“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6)“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
(7)“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疋加一等,十五疋加役流。”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1982年创刊,月刊,每月25日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欢迎向当地邮局订阅。2019年定价12.00元,全年144.00元。本刊邮发代号:4-347。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国外代号:RM5892。编辑部地址:上海市柳州路 615号 1号楼。邮政编码:200233。网址为 http://xyyl.cbpt.cnki.net。电话:021-64511836。 E-mail: xyylc_tougao@126.com。
(8)“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 其后律疏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证不言情,谓应议、请、减,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并据众证定罪,证人不吐情实,遂令罪有增减;及传译番人之语,令其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谓减所出入罪二等。译人与同罪,若夷人承徒一年,译人云承徒二年,即译人得所加一年徒坐;或夷人承流,译者云徒二年,即译者得所减二年徒之类。”
(9)有回鹘人白昼刺伤市民腹部,竟至大肠流出,官吏拘系之于监狱。回鹘酋长赤心冲入狱中,砍伤狱吏,劫囚而去,唐代宗亦不令追究。
(10)《大明律·名例》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11)《明英宗实录》记载:“瓦刺使臣卯夫刺等庆成宴毕,出长安门左门与女真使臣喧呼忿争,夺卫士兵械殴伤之。事闻,上曰:‘夷狄素无礼义,不可以醉饱之故责之,宜谕虏王自治。’”
(12)《大清律例》记载:“凡化外来降之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