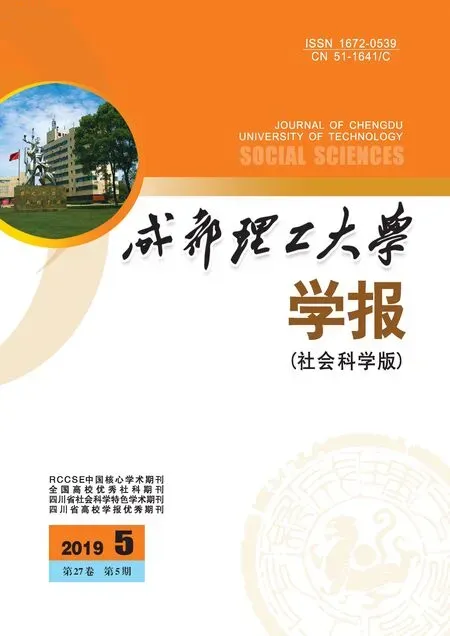文学批评的危机常态
——对1932—1933年“文艺批评危机”的一种解读
2019-02-15康建伟
康建伟
(甘肃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兰州 730070)
一、引言
茅盾晚年回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几篇关于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时,提到了“30年代初文艺批评的危机”:“记得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顷,曾出现过所谓文艺批评的‘危机’,作家们和批评家们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所谓‘危机’,是指一九二八年以来盛行的那种文艺批评不时兴了,曾经目为‘权威’的,被发现是建筑在错误基础上的,于是遭到了‘清算’。‘第三种人’又乘机‘崛起’,把文艺批评中的这些过失归咎于党对文艺的领导,以艺术保护者的身份出现,指责革命文艺,提出所谓‘文艺自由’的口号……健全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尚未建立起来,批评家们尚未完全摆脱旧的习惯……总之,通过与‘第三种人’的这场论争,也暴露了左翼文艺批评界的贫弱,和引来了作家对批评家的意见。”[1]539
这里所提到“一九二八年以来盛行的那种文艺批评”指蒋光慈、钱杏邨等提倡的革命文学批评模式,而“旧的习惯”主要指1930年11月苏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消极影响,“茅盾回忆所指出的文艺批评界的‘危机’和‘贫弱’,正是‘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消极影响未消除之前的必然现象”[2]119。这种危机,具体表现为“每每是‘从大处落墨’的宽泛论断,什么‘没有把握时代精神’,‘无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没有写出新时代的英雄’等等,缺少具体评论。也很少听到对作家创作的甘苦表示体恤的”[1]539。
概而言之,这一危机主要指革命文学批评模式遭到清算,“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消极影响,“健全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尚未建立起来”,文学批评界缺少正确的主导思想引领批评走向。具体而言,一是评论空泛,缺少细读文本的具体评论;二是作家和批评家关系紧张,批评家对作家创作甘苦缺少体恤。前者涉及批评技巧,后者涉及对创作的理解。
二、批评家的反批评
就批评技巧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批评家茅盾的反批评来剖析这一现象。茅盾首先是以编辑、评论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虽然后来自我定位为作家而业余兼职评论,“我这个作家而在业余写写评论的人,就不敢效法这些专业评论者,只想做一点平凡的工作”[1]540,但终其一生,他对文学批评从未放弃。通过分析这样一个批评家反驳其他批评家对其著作的批评,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春蚕》发表后,文坛瞩目,一大批评论家纷纷撰文评论。罗浮的《评〈春蚕〉》认为阶级意识淡漠。茅盾辩之为这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者评论文艺作品时常有的看法,他们不知道农民觉醒过程之漫长。朱明在《茅盾的〈春蚕〉》中认为这篇小说缺点有三:一是作品硬凑一个老通宝典型,缺少现实性。二是没有反映与时代的关系,三是未能探究恐慌的原因,流于表面化。茅盾认为,上海郊区农民的生活,并非因为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才觉醒。丁宁批评在《春蚕》到《秋收》间缺少必要的过程,没有描写出这一过程中的高利贷、加捐、增卡、小商人的没落等,茅盾极不赞同。凤吾指责茅盾第一没有描写出革命的契机,第二走向机械唯物论。对此,茅盾只能客气一番,不做申辩,迫于革命要求而选择沉默,背后的矛盾显而易见[1]532-536。
通过上述评论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评论多半拘泥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革命性,从社会科学眼光着眼,弱化或忽视了对作品艺术性的探求。正因为如此,茅盾对从艺术角度进行批评的文章格外看重。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有篇署名为“言”的评论:“茅盾君为当今最努力之小说家。所作无长短,莫不刻意经营,于描写技巧上最见匠心……旨意可谓广泛;然茅盾君笔下曾无一语空洞,惟以全力描绘乡民劳作之奋力艰苦;既以象真,亦见收获之难,以为后文物价惨跌之陪衬。其写工作之紧张,一再以‘连日连夜无休息的大决战’‘奋斗’字样称之。”特别提到《春蚕》篇中写“窝种”之情形,认为 “可谓刻画入微”[3]。此篇评论最为看重《春蚕》的是旨意虽广,却无一语空洞,刻画入微。茅盾通过文笔断定“言”就是吴宓,在众多评论中,茅盾独钟情于这篇评论,认为“也是从技巧着眼,但看得相当仔细”[1]540。虽然后来有研究者指出此“言”乃朱自清的笔名[4],但由此也可见茅盾对吴宓的深刻印象,以及对从技巧着眼的批评的认同。
之所以茅盾断言此文乃吴宓所作,是因为在此之前《子夜》发表后,与茅盾向来不睦的吴宓却出人意料地发表文章,大为赞赏。吴宓认为《子夜》一是结构最佳,“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二是个性鲜明,环境描写相得益彰,“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三是笔势姿肆,文字口语化,“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委宛多姿,殊为难能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学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学”[5]。20年代茅盾领衔的文学研究会发起对学衡派的论战,茅盾发表《写实主义之流弊》,专文驳斥吴宓将写实小说同黑幕小说和“礼拜六派”小说相提并论,认为吴宓对欧洲写实主义小说并没有全面的研究,且对托尔斯泰毫无所知[6]。吴宓后来在其自编年谱里也特意将此事记录[7],可见触动之深。虽然出于政治立场、艺术理想的分歧,茅盾晚年依旧认为“吴宓还是吴宓,他评小说只从技巧着眼,他评《子夜》亦复如此”。但是他也很诚恳地道出,“在《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1]514-516吴宓还是吴宓,志不同道不合,但在对《子夜》的众多评论之中,茅盾认为吴宓的分析最是深得文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述,这种个人文学批评理想与集团政治实践的落差,不仅凸现在茅盾身上,我们几乎可以从所有的左翼文论家身上看到这种痕迹。这种悖论性的存在仿佛成为纠缠于左翼理论家身上的一个幽灵,挥之不去。
三、 危机的漫延
茅盾所提危机也是针对批评家与创作者的不和,茅盾后来还发表了《作家与批评家》《批评家的神通》《批评家的种种》《批评家辨》等文章,纵论批评家,但目的如其自道:“谋求文艺批评工作的改进和作家与批评家的团结。”这其实已经引出了危机的另一方面——作者与创作,茅盾虽然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学批评的危机,但其指向已经暗含了其他两个方面的危机,创作的危机与理论的危机。不过,创作的危机与批评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而理论的危机则是隐而不明的。这样一种关于“危机”的讨论是当时左倾刊物很喜欢的一个论题。
1932年1月,丁玲主编的《北斗》发起了“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讨论,除丁玲外,鲁迅、郁达夫、茅盾、戴望舒、叶圣陶等22位应征者参与了讨论。丁玲认为:“在这个大变动的形势面前,左翼作家不但要带头而且要团结广大作家去反映已经变动的时代,迎接更大的变动,创作不能再‘不振’了!”[8]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通过这样一种话题,其目的在于引起注意,达到团结的目的,原因及出路也是暗含于发起者的问题之中的,不可能找到终极之论。“最终,这场讨论理念地设计了一套左翼文学的规则与标准,却难以在实践中创作符合标准的范本。”[9]
1933年,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大型《文学》杂志发起“文坛往何处去”的讨论。茅盾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其实这个杂志的幕后主编便是茅盾,他引出当时更为迫切的三个话题:首先是“用什么话”的问题;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又其次,“旧形式利用”的问题。在他看来,“文艺理论上的基本问题例如‘文艺自由’的问题,自然需要热烈的讨论,但是像上面所举的具体问题则关系于文坛的进展很大,也应当注意讨论。”[10]458-459“文坛往何处”,这样一个关于方向性的问题,极富政治色彩,与其关联的命题大概就是“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政治话语。问题的提出不免让人揣测其背后隐藏的答案,茅盾似乎也在等待着理想答案的出现。然而,从他引出的三个问题来看,分别涉及语言、题材、形式,却是小处着眼,从技巧着眼,并未讨论政治问题。经历了文学研究会时期的论争,1926年的沉潜、思考,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革命文学论争,进入30年代的茅盾,基本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虽然批评思想有所转变,但茅盾身上那种宏观着眼把脉时代,并力图导向批评动向,极重社会功利作用的个人气质却是深入骨髓的。当他在1932年提出这一问题时,是明显针对文坛现状,隐含并期待着某种答案的。
1934年,郑伯奇的一篇《伟大的作品底要求》引起《春光》杂志社发起“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产生”的征文讨论。郁达夫、艾思奇、高荒(胡风)、夏征农、徐愁庸等十五位作家应征作文。同时,《申报·自由谈》《文学》等杂志也参与讨论,但讨论结果,正如茅盾评论,“综合这十五篇文章的内容,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一)环境不好;(二)作家不争气。”[11]显然,这样的答案完全不能令人满意,问题依然还是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论争,充满浓烈的政治斗争色彩,“从政治化角度看问题,是30年代文学论争最基本的也是最显著的特征”[12]。表现在文坛上,便是“集团化”倾向与公式主义,以及社会科学的思路[13-14]。纯然的关于文学技巧的交锋并不多,这些论争,只是以文学为平台各自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其实均可归属于政治批评。论者有时会认为创作的危机源于批评的危机,而批评的危机源于创作的危机,这似乎是一个首尾相接难以摆脱的怪圈,仿佛狗逐其尾,自我循环。
四、“结果是没有结果”
综观20世纪30年代前期关于批评、创作、理论的讨论,我们发现,首先,它们代表了不同政治诉求的阵营对于主导话语权的争夺。根据政治倾向,大革命以后逐渐形成左翼批评、“京派”批评、民族主义批评三大板块。在三方角逐中,左翼理论家为了获得主导话语权,在这些讨论中往往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先行设计带有倾向性的话题,这样一来论题本身就指向了预设的答案。每抛出一个论题,辅之以相应作家的积极参与,摇旗呐喊,一时成为话题焦点,类似话题营销一般,短时间内达到吸人眼球的目的。同时再以大批左倾文章轮番轰炸,占据舆论制高点。即便应者寥寥,讨论未果,左翼理论家们也会再次设计相应话题,引导舆论焦点,努力掌控主导话语权。
其次,左翼理论阵营自身也有一个校正与纯化的过程。从 “为人生”思潮、革命文学、新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创作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后到《讲话》的确定,终于趋向一体化,直到第四次文代会再转向宽泛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反复的摸索、校正以及纯化,使得左翼批评理论配合政权的夺取与建设。有论者认为茅盾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1919—1981)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17—1979)[15]轨迹大致重合,这种重合,不仅体现在起始时段的相对一致,间隔时间(62年)的完全相同上面,更体现在茅盾所代表的批评模式,几经修正,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可以“通过茅盾个人的同化与顺应,窥见‘主流意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与逻辑演绎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历史进程”[16]。
最后,我们也能窥见,30年代关于危机的讨论,其实是一个连类而及的话题,文学批评的危机,同时指向创作的危机,背后也隐含着理论的危机。落实到茅盾个人身上,趋向左翼主流的理论认同与个人对于技巧性批评文字的情感认同就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表征为30年代文论悖论化的存在。
关于危机的话题一再被提及,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议。但当我们仔细检点历次关于“危机”的讨论结果时,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些讨论最终不免不了了之,讨论不能说毫无价值可言,但很难说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于这些危机的讨论,鲁迅的评价是:“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17]同样,茅盾在《文坛往何处去》中认为,“我们这文坛上有许多问题曾经提了出来,曾经有过论战,可是都不曾有满意的结束。”[10]458这一话题延续至今,且不说西方理论界从“上帝死了”,“人之死”再到“作者之死”的死亡旅程,“好像‘死了’也已经死了”[18]。单就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先生为《批评家》创刊号撰文“文艺批评的危机与反思”[19],90年代曹顺庆提出了“文学理论失语症”[20],后来,又有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引起的讨论[21]。既然“结果是没有结果”,可为何理论家、批评家乐此不疲,执念于此呢?
30年代关于文论危机的话题表达了一种对终极性答案的渴望,带有浓厚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建构时启蒙现代性的表征。刘禾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22],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后发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更加强调启蒙现代性而非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非理性反思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中顺应于启蒙现代性。正如王晓明的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我们在欧洲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看到的情形明显不同:它先有理论的倡导,后有创作的实践:不是后起的理论给已经存在的作品命名,而是理论先提出作家再按照这些规范去创作……我简直想说,它是一种理智的预先设计的产物了。”[23]这种提问方式,恰恰是中国现代文论的初始状态,对它的批评还需考察历史语境,表以同情之理解。
危机话题的反复提出,恰恰体现了理论的特点。“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24]这种内在的反思性,使得文学理论与批评界时时以自身作为解剖对象,每一次危机话题的提出,虽然我们难求终极性的答案,但我们也不能否定讨论所激发的思想碰撞,产生了一些有意义的命题,甚至成为理论的增长点,创造了学术史上又一个“学案”。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正是在不断的面临危机与解构危机中存在的。
当然,危机的解构并不意味着危机的解决,反倒更像一次研究范式的转型。回顾历次讨论,我们不言自明地将之视为“危机”,然后一再固执地寻找答案,我们是否需要反思这是又一“危机”,还是又一“契机”。“哲学是以真理的名义考察何为真理的反思性实践……哲学最初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哲学关注的是事物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的知识。”[25]借鉴这一思路,关于危机的答案的追寻,表现了对知识的渴望,而理论作为一种反思性实践,则更应该关注于这种知识的形成。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正如前引鲁迅的评论一般:“结果是没有结果”,引用库恩的观点,那便是“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26]。似乎“危机”反倒成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一种“常态”,既然答案屡寻不至,换一个角度,我们不妨将这种危机状态视为文学批评的常态存在,即文学批评的“危机常态”。在这一张力结构中,因为“常态”,文学批评必须每天直面挑战,承担风险;因为“危机”,文学批评必须保持其学科活力与理论的再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