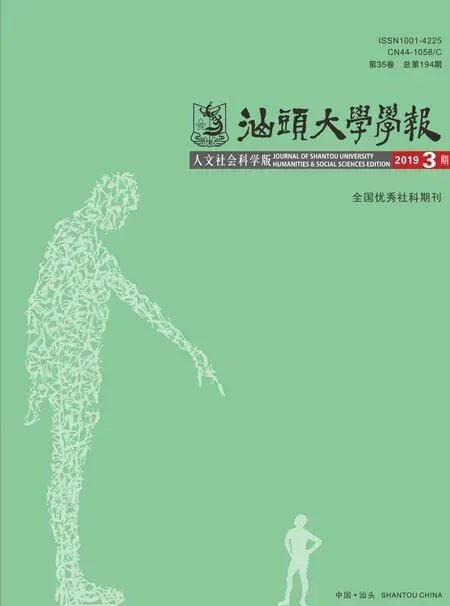诗歌、自然与翻译
——顾彬等诗人创作谈①
2019-02-11李影媚
李影媚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一、诗歌与自然山水
顾彬:舒婷,人家说《致橡树》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首诗。但它很难翻译成德文,我翻译你的作品不少,但这一篇,我没有翻译。如果我记得对的话,你把橡树和爱联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好像这种橡树是一种象征,是国家吗?那么自然山水与政治,与国家、爱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舒婷:首先,要说一下,我去年收到汕头大学诗歌节的邀请,没有来,是害怕你会问我哲学问题,对我来说,我很怕深奥的理论。但今年诗歌节的主题很好、很明确,对“诗歌与自然山水”这个问题,我深有感触。因为我是一个本能的诗人,我写东西都是根据本能。与其说故乡,不如说原乡,我的原乡就是一个海岛。我们世世代代都住在小岛上,我们鼓浪屿是一个植物非常茂盛的地方,它的阳光、大海、建筑,都对我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我以前的诗歌作品中,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花草树。作为一个诗人,我经常不喜欢说一朵花开在什么上。我不要说一朵花,我要说这朵花是什么花,因为不同花的形状、颜色、气味,呈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我也不要说一颗大树、也不要说一颗大鸟从头上飞过。我一定要去找这颗树是什么树。所以,自然山水对我写作的影响非常大。近几年,中国也有一个热门话题,叫做“作家地”,探讨一个作家所处的生态、环境对一个作家写作的影响。我蛮认可这种影响说。如果我离开我的小岛,可能我的写作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而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当年在DAAD②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简称DAAD,最早成立于1925年,代表德国231所高校和128个大学生团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教育交流机构之一。DAAD的经费由德国政府提供,是德国文化和高等教育政策的对外执行机构。舒婷1996年受DAAD邀请赴德国进行一年文化交流。杨炼、北岛、顾城和翟永明等诗人也曾受DAAD之邀,赴德交流。的时候,在柏林一年写了20多首诗。柏林的冬天,白天很短,夜晚很长,早上10点天才亮,下午3点时候已经暮色苍茫,4点已经万家灯火。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就花很多时间去看书和写作。那时候写作的状态、题材、风格包括气味,都和我在厦门写作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年诗歌节提出的诗歌与自然山水这个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强大的人可能自己就可以造出一个环境,但对于一些人,比如我,环境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的写作对环境的依赖,这点毋庸置疑。
顾彬:你为什么在柏林写了20多首诗呢?和柏林有关系吗?
舒婷:当然,它们肯定和柏林有关系。柏林和我们厦门太不一样了,正是这种不一样,让我不断有创作的冲动。另外,那里的冬天,特别短,像我刚刚说了,还很压抑,我只能窝在房子里写诗了。
顾彬:我没有注意到我们柏林的冬天。可是我们的夏天不是很美吗?柏林墙在湖水里头,那里有它很特别的历史。
杨炼:这也是我在柏林的原因之一。柏林是整个欧洲历史地层,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后冷战、全球化以及现在世界矛盾的集中地,是欧洲历史考古学的标本。所以如果你住在柏林,你历史的根会一层一层地扎进去。这个和中国文化有很多连接和对话的关系,所以在那里写作没有问题。
顾彬:杨炼,你说过,诗歌是我们唯一还是最后的故乡,那自然山水不是我们唯一还是最后的故乡吗?
杨炼:关于这次诗歌节的主题,我同意舒婷的说法,很好,我认为是我到汕头大学以来最好的一次①2018年汕头大学诗歌节的主题为“诗·自然·生态”。汕头大学诗歌节,由汕头大学文学院主办,始于2013年,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历届诗歌节的主题分别为:“根植土地,点燃心灵”(2013年首场)、“长诗的长夜”(2013年第二场)、“短诗的短夜”(2014年)、“爱 &情”(2015年)、“我们的存在”(2016 年)、“诗与哲学”(2017年)。从 2013年开始,已邀请将近20位诗人来到汕头大学朗诵诗歌,并进行各种诗歌交流活动。曾出席过汕头大学诗歌节的诗人:北岛(中国)、沃瑟·拜丽耶(瑞典)、添姆·利尔本(加拿大)、奥尔维多·加西亚·巴尔德斯(西班牙)和蓝蓝(中国)、欧阳江河(中国)、潇潇(中国)、王家新(中国)、杨炼(中国)、王小妮(中国)、郭金牛(中国)、郑愁予(中国)、陈黎(中国)、罗智成(中国台湾)、张依萍(马来西亚)、翟永明(中国)、陈育虹(中国台湾)、池凌云(中国)、李亚伟(中国)、George O’Connel(l美国)、顾彬(德国)、西川(中国)、多多(中国)、韩东(中国)、冯晏(中国)、徐贞敏Jam(i美国)、舒婷(中国)、袁绍珊(中国澳门)、唐晓渡(中国)、MingDi明迪(美国)、姚风(中国澳门)。杨炼和顾彬先生是汕头大学客座教授,每年都参与汕头大学诗歌节。。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笼而统之的话题,其实它也是人的一种处境。这个山水也好,自然也好,环境也好,在这些词汇里,都包含着非常清楚的问号,而且这些问号已经内含了负面的、否定的回答。那么,我为这个题目翻遍了我的《周年之雪》②《周年之雪——杨炼集1982-2014》,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我没找到一首比较正面的、优美的、描写山水的诗。因为实际上经过这些历史记录之后,中国也好,甚至包括外国也好,这种表面的古典式的山水自然,实际上基本不存在了或者说是虚假的存在。自然在欧洲看起来似乎还比较美好,比如美国,但它是和垃圾运到第三世界、军火出卖到沙特阿拉伯等等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这些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完全是来自于内心、内在自然的毁灭。我们内心的垃圾比外面的垃圾肮脏、恶臭得多。对于老顾说的诗歌故乡或者精神故乡,实际上,我们唯一还能往回找一点内在自然的可能性,是诗歌,因为不仅是指诗歌这个话题,包括诗歌瞄准语言本身这样一个创造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散文或者戏剧,使用比较现成的语言。诗歌是钉住语言,非要找出语言独一无二、非他不可的表达方式,所以它是以创造语言本身来开拓或者保护人的感受和思想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比语言更深,它是一种语言的根。另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比较理想主义地对诗歌说这句话——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故乡。
顾彬:你刚刚说,诗歌比语言还深刻,这是什么意思?
杨炼:因为诗歌可以不停地寻找那个非他不可、独一无二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我们内心感受的要求之中,现成语言是不够的。当诗歌出现那些陈词滥调的时候,作为诗人,我们首先感到非常不满意,因此诗歌永远面对着创造性这一点,诗歌思维以突破现成的语言表述方式作为目标。如果我们说中文和德文,或者阿德尼斯说他的阿拉伯语,等等,我们可能互相听不懂。但是如果我们把世界上各种不同诗人的诗,以某种方式看穿它表面的语言,进入到诗人的世界,感受人生、然后整理自己的思想,从中找到创作、创造的能量,那么这个诗歌思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不同。把一首诗拿过来,我们可以立刻知道,这个是什么层次的诗,什么质量的诗。在这一点上,诗歌在思维、在更深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互相理解。
顾彬:这就是说明你对诗歌的作用还是非常乐观的,对吗?
杨炼:恰恰这个乐观是因为彻底的悲观,因为它什么作用也没有。
顾彬:那么小姚,你原来是北京人,你去了澳门后有写作吗?这些写作和山水有关系吗?
姚风:很多时候,我介绍说我是澳门诗人。其实,我是假冒的,货真价实的澳门诗人是袁绍珊。①由于诗歌主题关于“自然”,袁绍珊用了对于她感觉最自然的语言,即她的母语粤语,进行朗诵。唐晓渡也用他的方言江苏扬州话朗诵了他的诗歌《访韩诗笺之一次止于腹稿的发言》。详见2018汕头大学诗歌节视频http://mp.weixin.qq.com/s/q3x10vWTmasq3QQbQhlewQ我这么多年是“乡音未改鬓毛衰”。我1994年去的澳门。我学的是葡萄牙语,当时澳门政府需要一些会讲葡萄牙语的人,我就去了。但这么多年以来,我写作的主题基本还是和内地相关。当然我的诗歌很多和北方有关系,因为那是我的成长记忆。至于山水诗,我没有用过这个概念,也没有生态诗的概念。但我对山水、自然、风光,都会关注。可以说,我对山水比较敏感。我写过一首诗,叫《德里加海滩》,名字是我虚构的。我觉得我们对自然的伤害太深了,只是自然无法用语言表达。可能有时候它会用海啸、地震来发泄它的愤怒。但我们依旧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所以,杨炼老兄说得非常正确,敬畏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首先要清除我们内心的垃圾。说到故乡,其实没有故乡。杨炼拿的是英国护照,但是住在柏林;我是北京人,住在澳门;明迪住在洛杉矶;顾彬您现在号称是中国的北方人。我觉得可能在全球化的今日,“故乡”这个词,我们要重新去解读它。
顾彬:我们可爱的唐晓渡,他80年代说过一句话:生活最深刻的危机是翻译。但对我来说,在翻译的时候,我会安静下来,我是另外一个人。那么我们写诗,我们也把自然山水变成我们可能需要的。从六朝来看,自然山水对于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贵族,是一种安慰。那么我想问你,你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之一,那你写诗的灵感从哪里来?
唐晓渡:您刚刚说的写诗灵感,和翻译有关系。我为什么做翻译呢?其实是内心某种焦虑的产物,反正这个情绪本身肯定不是什么正面的,比如快乐很少能成为我的灵感资源。这次诗歌节的题目很好,让我想到我在1993年歌德学院做过的一次关于中德诗人的交流。我记得一个东德诗人问我,你们中国有生态诗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生态诗”这个概念。我说,好像没有。他问,这是为什么?当时东德已经有了生态诗。当然,我不知道如何评价,不知道先有或者后有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我在想,也许我们中国诗人更关注人文生态吧。因为讲生态诗,它总是自然地和自然生态有关系。我对杨炼刚刚说的,深有感慨。比如说,我插过队,和山水贴得很近,但我很少从山水中得到写诗灵感。当然,它有时候会让你进入一种状态。可是,我的诗歌表达的,应该更多的是内在自然。外在的自然好像对我这代人,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已经永远失去了。也许不是“永远”,谁说得定呢?因为我还能活够几十年,也可能会回归。其实,对于老顾您刚刚说的六朝山水诗,当时诗人写山水,也不是非常直接的、目的式的、现实意义的关系。最早可以溯源至“玄理诗”。中国人和山水之间的那种自发关系,也就是完全自然意义上的那一种,我认为,没有。最初贵族写山水,他们更多的是将山水诗作为一种心灵慰藉,是一种避世、谋求安放心灵的方法。但有意思的是,它的文化背景,即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的看法,和诗又是同构的。我觉得在世界上,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文化最高的文化形态。这个自然不仅仅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外在自然,其实也包括我们内在的自然,叫“大德”。《文心雕龙》里面讲到,诗是大德,可以和天地并肩,它本身内涵了一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六朝时期,在本体意义上,诗歌就已经和自然有互相包容的关系。西方诗歌似乎与自然没有这种关系。所以,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都成熟得特别早。对于我来说,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构成了生态这个词的两面。但是我们当代人,很难在那个意义上,再写那个意义上的山水诗。诗也许能够向它的源头追溯,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中国最早的自然观、诗歌观,在追溯过程中,可以通过语言,试图重新探讨有机整体的可能性。至于外在的自然历史进程,不好说。
顾彬:我想请杨炼谈谈内在的自然。
杨炼:其实晓渡已经提到了。我觉得老顾设计这个题目比较重要、也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可以借此探讨中国和欧洲对自然不同的传统或者态度。从生命死亡来定类,中国原来是道教,后来是佛教,是一种轮回式的理解。而欧洲的宗教从原罪开始。其实,中西方宗教思想的基础来源于不同的启示。简单地说,欧洲的思想启示是动物,一只动物死去之后,不再回来。但东方的思想启示是植物,也就是大自然。因为植物在同一颗树上,一岁一枯荣,冬天叶落干枯,第二年春天发芽,同一棵树是可以复生的,所以对于中国人、东方人,启示是轮回的。中国的诗歌从《诗经》开始,哪怕到了屈原,大自然对于哲学思考的作用,其实永远是作为一种灵感和启示。而在西方,不一样。普罗旺斯有一座山,叫作Mont Ventoux。彼得拉克,文艺复兴时期写十四行诗的意大利诗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写下了欧洲第一首纯粹的山水诗。彼得拉克和但丁是14世纪的,和我们《诗经》的时代比起来,那是差了几个千年。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篇小散文的结尾是:他第一次看见了这座山。以前的欧洲都是通过人、通过神看自然。风景画都是在背后的,前面都是神或者人,风景从来没有以主角身份出现,在诗歌方面也一样。对于中国传统来说,六朝的贵族文化已经发展得很充分,那时候,山水诗是生命的一个寄托。关于“看见”,彼得拉克第一次看见了山,而中国人早早地就看见了山水。这个不一定是今天的话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残酷的处境。就像唐晓渡、姚风提到的山水被毁灭的这样一个命运。其实,山水的命运和人的命运是一回事。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山水。没有多少人能像舒婷一样住在那么美好的鼓浪屿,被花香鸟语包围着。“看见”非常关键,这个是一个诗歌命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命题。
顾彬:小袁,我们年轻的诗人,你有什么看法呢?
袁绍珊:说实在的,中学时候,我最讨厌读山水散文,特别是欧阳修的。虽然写得很美,但我们在澳门长大的这代人没有看过这样的风景,根本对不上号,而我们不仅被要求背那些山水散文,还要考试。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对风景描写没有兴趣。我比较关注内在的事情。当然,后来因为到处去旅行,我慢慢觉得我看见了很多不同地方的美景,在这种看见的过程中,就会去思考、去内化,我和它的关系是什么。虽然以前很少写关于自然山水的诗,但自然生态现在已经成为我最近这几年比较重要的创作命题。除了我个人的原因,也有我们所处的语境因素,所谓的生态诗、田园诗,这几年在港澳台差不多是一个显学了,因为它和本土的关系密切。澳门因为地少,经常填海。在港珠澳大桥筹建的时候,我收到很多电邮,比如香港很多环保团体问我,“作为一个诗人,你对这个议题、对这种填海工程,有什么看法”。在写作过程中,会有很多声音不断地追问你,诗人对于环境的角色是什么,仅仅是描述吗?对于我而言,诗人,不仅仅满足于描述美。由于台风“天鸽”以及港珠澳大桥的修建对诸如中华白海豚等生态链的影响,我们这辈澳门诗人,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是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像古代那些山水诗表达什么精神寄托和个人志向,更多的是与人有关,可是这个人不是个人,而是众人。
康富贵:自然山水,比如说,石头,在你们的诗歌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杨炼:举个例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和鸟是比较抽象的,但是通过汉字的具体、具象把这个抽象的东西变成可以感觉的东西。这是中文的好处,但不一定是中国人思维的好处。总的来说,中国的思维比较抽象。舒婷刚刚说的,我觉得比较重要,她还是想要去找到,到底是什么样的花,到底是哪种味道。这和我们刚刚说的“看见”,其实,“听见”“闻见”也一样,都是感觉的具体化、气质化。从诗歌来讲,应该回到,你想从语言里头写出什么样的对于某一个山的感受,或者在诗歌里建造某一座怎样的山,等等。总之,要落到具体的实处,这是一个从诗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方式。我小时候生长在颐和园附近,因为那时候没有很多高楼,每次抬起头来,眼前就是北京西山的那个轮廓线。后来当我1997年放弃了在颐和园附近的房子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书装进车子里,也是在冬天暮色苍茫中,车开的时候,我回头又看见了西山的轮廓。我当时还想着:这是最后一眼看见眼前这座山了。后来没想到,去年,我到周口店参加一个活动,突然就在西山边上,我又看到了这座西山,我以为永远告别的、回不去的这样的一座山,感触良多,最后写了一首诗,叫做《和我一起长大的山》,就在小册子①汕头大学2018年诗歌集,收录了杨炼、舒婷、唐晓渡、明迪、姚风、袁绍珊以及包括李影媚在内的汕大师生的诗歌作品,由汕头大学文学院主编、康富贵设计。里。因为我的海外漂泊经历,不是任何一座山,而是,就是这座山,跟我有这种深刻的感情,所以我写“美丽石子都在找回家的路”,是“都在找回家的路”,而不是“都在回家的路上”,如此类的这种感觉,像“火石一敲”。小时候,我爬香山去找那种有点像水晶一样的石头,叫火石。乍一敲,它在黑暗里头,就有了火星。结果我在这首诗中写到,“火石一敲,心里的洁白”,不是外面的洁白,“心里的洁白/一一再造我的亲人”,不是活在那儿,是“再造”。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非那座山不可,就像刚刚舒婷说的那样,她的“本地”对她非常重要。因为对本地的爱,你才知道失去本地的痛。当然,我们应该是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这种痛,但是对于本地,感觉更痛。所以我没写别的地方的山,因为西山这座山对于我来说,才是独一无二的。
唐晓渡:以前,中国的画家讲“胸中山水”,不是说你去照着画、去模仿山水。那是什么意思呢?从艺术创造的角度讲,你胸中的山水是真正的山水。从外在的角度讲,山水不只是山水,山水是道。这个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包括它的整个运行演变。今天我们谈的自然环保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书写对象。古人从来不会说,我写一个山水诗,是我们后人给它做这样的分类。如果我仅仅把石头看成是石头,就像顾彬说的,它谈不上什么道。山水,如石头,有一种内在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是和我们息息相通的。所以,中国传统的绘画和建筑的布局,都充分考虑到道的一种存在方式,考虑到生命的彼此呼应、照应。我们现在的建筑行业也会讨论这些,但基本都停留在技艺性层面。有时候我就在想,山水也好,自然也好,可能现在更多时候,它都在启示,在说话。可惜我们现在眼里只有市场、效率,只有财富的积累,完全听不见、看不见自然山水。但是自然总会突然给你一个警示,一个启示,一个召唤。
李影媚:我想请问舒婷老师一个问题。舒婷老师的成名作是在鼓浪屿所作,但那时候的鼓浪屿已经是几十年前的鼓浪屿了。经过城市化的发展,鼓浪屿现在充满着商业化气息。关于这样的变化,对于诗人的创作而言,现在鼓浪屿对您还有当初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吗?
舒婷:首先,我特别爱我的家乡。现在,我有时候也很感慨,小时候的我可以蹲下来半天,看墙角的一朵花还有下雨天透明的小水洼。那时候,我们家的木棉还是全岛最高最大的,可惜在莫兰蒂台风的那一年,它的腰被折断了。木棉其实是一个热带植物,生长在南方。但我也像南方很多作家一样,非常向往北方那种非常伟岸的、强壮的、耐风雪的树。于是,我把橡树作为一个象征。实际上,木棉和橡树永远不可能生长在一起。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觉得这两个意象是能够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不可能。所以,对于我的读者,我非常抱歉。我当时写《致橡树》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不可能性。虽然现在的鼓浪屿已经被商业化,但我还是能每天看到我的海,我很喜欢阳光在海面上不同时期的变化。有时候,我听到别人讲,我也很悲哀,觉得自己胸无大志,就愿意呆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有很多次,我都可以移居到国外去。然而,我每次都回来。这是因为我实在是胸无大志,我就是爱我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不管我的家乡变成什么样,我还是爱它。
杨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二、诗歌与语言翻译
刘倩兰:我想请问各位诗人,读诗需要智商吗?我在看一些诗歌文本的时候,我好像很难进入到文本当中。我比较享受的是,诗人们用他独特的嗓音和节奏感把诗歌朗诵出来的过程。但是除了这个过程,我收获不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感动,但过后就忘记了。所以写诗肯定需要灵感和智商,那读诗是不是也需要灵感和智商呢?
唐晓渡:对于读诗这个事,你不能有太强烈的要从里面读出什么来的想法。那样去读诗,你可能很吃力,另外一个可能是,如你所感受的,没有什么收获。你就是要放松。你问要不要智商,干什么事,不需要智商呢?我觉得,就阅读来说,也许情商更重要。阅读是一种对话,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要进入到里面去。所谓创造性阅读,是你要成为阅读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对象。说一下我自己的经验,一开始,我也一样。比如,我知道艾利略的《荒原》很重要,在上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时候,老师也说《荒原》是现代主义里程碑的作品,结果一读,我根本读不进去。那时候,是1979年,现代派作品已经出来了。当你读不进去的时候,就放下来吧。最后,随着你的阅历,包括你阅读的经历、世事的经历,你可能突然就进去了。你进去以后,不仅仅是进入它的文本。当然,最主要进入你自己。
顾彬:小唐,你说得太棒了。我也说一下。杨炼会同意我的说法,声音是节奏,也是内容。对于诗歌,首先要听诗的声音,再听它的节奏,最后再看内容。姚风和杨炼都是北方人,他们朗诵的声音和你们南方人不一样,他们朗诵得很棒。
陈乙宁:老师们好。我想问,翻译是不是都是一种误读呢?王小波曾经说过,最好的中文是翻译家创造的。可是我有时候读诗集,比如之前我读安娜·阿赫玛托娃诗集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她。可能因为我读的是译本,就像刚刚那位学生说的一样,我也看不懂。
顾彬:看不懂是次要的,关键是声音和节奏。
陈乙宁:但是我也没有听到,所以我想就这个诗歌翻译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诗人。
姚风:误读是存在的。但不是所有的翻译都是误读。另外,误读,有美好的误读,也有把一首诗全部毁掉的误读。关于“诗歌翻译是一种创造”这种说法,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意。但是,创造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看你怎么创造;还有,是谁在创造。比如顾彬老师翻译,他就可以去创造。不是每个翻译家或者译者都有足够的敏感度和能力根据对两种语言的把握去创造。所以我们提到诗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创造背后的这些因素,就是谁来翻译,如何翻译,这两点很重要。
杨炼:从广义来说,不仅仅是读翻译作品,所有的阅读都是一种译者翻译。当你读中国古诗的时候,当你读现代诗的时候,当你和诗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实际上都在一种距离之中阅读,你并不能直接知道诗人究竟在说什么。其实你都在想象,通过一种语言,创造自己的想象,想象一个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说你直接知道诗人说什么,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在中文之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两者之间,就是你和诗人,或者你和一个译文之间,这个距离其实在创造一个第三者,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中英诗人翻译①诗人杨炼活跃于国际文化、文学界,经常参与并组织不同文化之间诗人的交流和对话。杨炼和赫伯特主编的《大海的第三岸——中英诗人互译诗选》于2013年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国际对话和译诗集《仲夏灯之夜塔》是九卷本《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第九卷,收录了杨炼历年来与国际作家的对话(《唯一的母语》),和其翻译的世界各国诗人之作(《仲夏灯之夜塔》),也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一直在推进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不是简单地,通过翻译家来阅读,诗人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和别种语言的诗人的交流和对话。因此,我们中英诗人、中德诗人之间,都在做这种诗人之间的对话。而这种对话的基础就是德国的瓦尔特本雅明说的一句话:“翻译是第三种语言”,不是原文,也不是简单的译文,而是原文和译文共同创造的第三种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同意王小波说的“现代汉语是翻译体创造的”这类观点。现代汉语同时也是在古典文学、文化之间互相创造的。所以,我们现在处于各种创造的焦点上,在这个意义上,你就是那个第三种语言。
明迪:其实刚刚提了三个问题。最后那个问题,声音。实际上,不需要那个人去朗读,你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就能感觉那个诗里面有一种节奏、一种声音。这是不需要听的,通过看,也可以感觉得到。其实不仅仅是译本,任何诗都有它内在的声音。读一首诗,感觉到它内在的声音,和你听到那个诗人的朗诵声音,一样重要。另外,你提到误读。误读不仅仅是读翻译的时候,像杨炼刚刚所说的,你在读母语,也会有误读。还有,翻译。可能每个做翻译的人都有不同的翻译方式。有的人尽量去理解,理解消化完了之后,用自己的语言去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再创造。还有一种是模仿式的,模仿作者的声音、节奏、语气、语调、用词,一切都去模仿。“我”就躲在作者的背后了,你根本看不见译者。你看到的、你感觉到的,全部是那个原作者,这样的翻译也需要花很多功夫。另外就是所谓的翻译体。如果一个人不花很多时间,那你看到的版本就可能是翻译初稿,“翻译体”很严重。需要花很多时间,反复修改,把“翻译体”去掉,然后尽量既本土化,也保留那个译者的意志,另外一种语言的意志。那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句式。但是句式又很容易变成翻译体。其实做翻译的人最害怕翻译体出现。当然,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需要译者去克服。但如果读者你感觉到了翻译体,也还是有一点点好处,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接触另外一种语言。比如,最早的汉语,广东话,比较接近古代汉语。但现在,现代汉语的句式、用词、节奏,一切都变了。现代汉语发展到现在,一部分也有翻译体的功劳。所以翻译体并不都是一个坏事。它也可以改变一种语言,给它带来一种新的生命。
袁绍珊:按照我的个人经验,我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性。所以在翻译当中,我和我的译者交流的时候,我都会比较希望尽可能地保留诗歌的音乐性。我不是很在乎我的诗歌是不是一字一句地被翻译出来。作为一位作者,我觉得诗写出来之后,“作者”已死,剩下来的就是,交给读者去处理、去再创造。所以我的译者不需要一字一句地把我的诗歌搬到另外一个语言那边去。对于我来说,他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诗歌本身就没有必要有标准答案。即使是其他文学作品,我也觉得没有唯一的译本。这也就是为什么诗歌值得一直被讨论和翻译。
舒婷:我很同意绍珊说的“作者已死”这个观点。对于我来说,我的诗歌写出来之后,那首诗歌就已经脱离于我,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坚持不朗诵自己的诗歌而交给其他人去朗诵的原因。很惊喜的是,我看到不同朗诵者在朗诵时候的不同可能性,当然,也有让我感觉自己不被理解的朗诵,但我不会有什么特别伤心的想法,因为那首诗歌被我写出来,它就已经属于大家的了。
顾彬:同学们提出来的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你们别认为是我翻译唐晓渡、舒婷和杨炼,是我的语言把他们三位的中文翻译成德文。杨炼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翻译不是一个译者与一个作者的对话,是两种语言的对话。那么杨炼最近让我累死了。他老是写你们听不懂、看不懂的诗歌,让我翻译,不对,不是让我翻译,让我的语言翻译,我可以,我没问题。
杨炼:所以你的语言死了,人还活着。
李影媚:顾彬老师提出一个对于我来说比较有趣的观点。他说,在翻译过程中,母语才是他最大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平时的观念中,可能外语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姚风老师,您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姚风:我个人感觉是,当你掌握了比如说英文或者其他语言,也就是你对这种语言的理解和把握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用其他语言去翻译这个国家的诗人作品,那么你的译入语非常关键。在翻译的时候,如果译入语是你的母语,那么母语绝对是决定性因素。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学者或者教授的翻译,在准确度上,没有问题。但是从我们的母语角度来看,它离作为一首诗的标准还有差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原文的一首诗翻译成译文的一首诗,很多时候是因为译者的母语还不够好,而且还不是不够好的问题。比如说你的中文很好,但如果缺少诗人的敏感、节奏和音乐性,那你这时候也很难去翻译一首诗歌。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译入语的把握,在翻译当中,可以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比重。译入语①有时候译入语直接是母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杨炼: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好像看的是翻译,实际上,里边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它是译者和这个原文诗歌②杨炼强调译者和原文诗歌的对话并不一定是译者与原文诗歌作者的对话。之间的一种非常深刻的对话,也就是说原文诗歌里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译者在道德意义上必须去回答。否则的话,这就不是翻译。或者有些是贬低,有些是拔高。老顾翻译我的诗歌作品的时候,他会很累。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诗歌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抒情诗,在观念上,它其实是对当代诗歌,至少我自己希望,是一种大的挑战。它不是简单地写一首,两首,五千首,一样的诗,而是一首不一样的诗。这个观念实质上是对我们当代文学的要求。同时,这个观念还必须找到它最恰当的形式和最好的声音、最好的声音能量。这都是诗歌最内在的要求。而译者不仅是面对一些词,而且能够面对这些词背后的诗歌要求,那么这个译者才是够格的。同时,我翻译英文或者德文诗歌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像老顾所说的,这个作者能让我恨,但是最后是让我爱。而舒婷的诗,大家为什么现在还会那么喜欢呢?我觉得她的诗里边,也是在那个时候很难得的,有非常出色的音乐性,可能大家没太注意到。实质上到现在,舒婷的诗歌还在你心里回响着,是因为它有音乐性③顾彬也认同杨炼所说的“舒婷诗歌的音乐性”。。而这个音乐性,在当代诗歌,尤其是用所谓意象诗歌之后,很多时候是被忽略掉的,或者说实在的,诗人不够格。那么在这个时候,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比如老顾,他的工作就太轻松了,因为他只要把一些词堆上去就完了④顾彬在首发于2019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的文章《翻译是创造世界也创造自己》中写到:“最近杨炼与他的妻子友友告诉我,翻译没有什么,用一本词典把几个字混在一起,就可以了。”这篇文章于2019年3月5日被转载于微信公众号“北外全球史”。杨炼于2019年3月6日在其微信朋友圈转发并称赞该文,但同时质疑顾彬在文中谈到他与友友关于翻译态度的表述。顾彬对杨炼关于翻译态度的误解应该源于此次诗歌研讨会的这句话。。但他翻译有音乐性的诗歌的时候,对不起,你必须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老顾翻译我的诗歌的时候,他的难度不得了。当我们和英国诗人做互相翻译的时候,我之后赫然地发现,他们把他们翻译我的诗,都收在了他们新出版的诗集里,这就像老顾说过的要把我写进了德国文学史。
顾彬:这是你的要求。
杨炼:对,这是我的要求,也是你的成功,而且本来就是应该的。因为这样一种译文的作品在被翻译的文学里边,是不存在的。既是挑战性,又增加了非常多的新内容。所以我们之前都只是把翻译和原文分开,是不对的。⑤顾彬认同杨炼的这些说法。说实在的,我们中国当代中文诗人,受到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的很大影响,其实我自己受到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过分。但是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根本就失去了洛尔迦原来的音乐性。因为洛尔迦原来对押韵、节奏等等,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伟大的戴望舒的翻译把他的音乐性完全关在了国门之外,所以我们读到的是三手洛尔迦。
顾彬:多谢小李的问题。时间很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