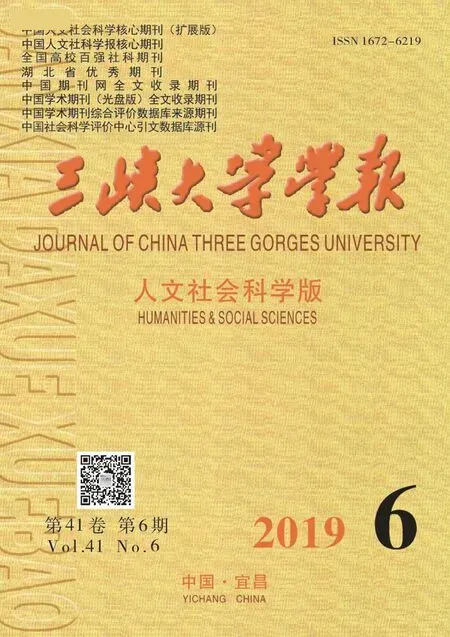论晚宋“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对立
2019-02-11邓莹辉田丽萍
邓莹辉, 田丽萍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宋代是古代文学全面兴盛的时代,也是诗歌发展嬗变的重要阶段。自此开始中国古典诗歌明确分为二途:唐诗主情,以韵胜;宋诗尚理,以意胜。宋诗强调义理,其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宋代儒学的复兴,尤其是以程朱为核心的理学的发展繁荣及其官学化。四库馆臣在《击壤集提要》中有云:“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於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1]1322针对唐代盛行以自然山水为描写对象的风月诗,宋人提倡有思想深度的“学者之诗”。而作为从诸派争锋到一家独尊的宋代理学,其诗学批评理论存在着更为明确的学理化倾向,他们不仅认为唐诗太过肤浅,鄙薄其为“不知道”者,而且对当世“专于适情”的“诗人之诗”更是多所批评,转而大力提倡“学者之诗”“儒者之诗”。
晚宋时期(1208—1279),随着理学官方化地位的逐渐凝定,及其对文学创作领域更广泛深入的渗透,肇始于北宋、形成于南宋前期的关于“学者之诗”“儒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争论,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作为诗学批评概念,“学者之诗”在宋季文人诗学批评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其内涵较之南宋中期以前也更加丰富。这些概念的提出和确立,是宋代学者对于诗歌创作“既有文学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2]。因此,追寻宋代“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概念的形成过程,描绘宋季“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从冲突对立到逐步走向融合的真实图景,可以为认识宋代诗学思想的发展嬗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划疆立界的历史性考察
天水一朝以文学而著称于世的文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继承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精神,强调“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文学观念,而理学家则更是将其推向极端。在诗歌创作领域,北宋中后期出现的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道学之诗”与晚唐派、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诗人之诗”“文人之诗”几至于水火不容,判若云泥。理学家视文学家的创作为“闲言语”,认为“作诗妨道”。其极端诗学观因其学术的民间地位和诗歌成就的制约,对当时诗坛所产生的影响毕竟有限。而到了南宋中后期,随着理学理论的系统化,特别是在理学逐步官方化的历史语境中,一方面,朝廷君臣通力合作,皇权以自己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科举手段,对追求文辞之美的纯文学严加限制,直接规范文学朝着义理化道路推进,如有“文章天子”之称的宋理宗于宝庆二年(1226年)“手谕知贡举、礼部尚书程珌等曰:‘国家三岁取士,试于南宫,盖公卿大夫由此其选,事至重也。……卿等宜协心尽虑,精考切择。夫文辞浮靡者,必非伟厚之器;议论诡激者,必无平正之用。去取之际,其务审此。’”[3]241正统大臣亦积极进言,如绍定二年(1229年)“臣寮言:‘近年文气委苶,请申饬胄监师儒之官,专于训导,使之通习经传,考订义理,课试抡选,须合体格,去浮华穿凿之弊。’”[3]259另一方面,理学家们充分利用其学术优势和逐渐取得的政治权力,以风雅主导者自居,在二程“作文害道”“作诗妨志”诗学观念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诗歌必须阐发“人伦义理”的理学诗教观念,标榜自己所为是“学者之诗”,以此最大限度地挤压纯粹诗人之诗的生存空间,并通过编纂标准文本(如《文章正宗》《濂洛风雅》等)的方式,试图引导诗歌沿着理学所规定的路径向前发展。
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能够从理论上完整而且明确地将诗歌划分为“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者之诗”等不同类型的是清代诗学批评家。如生活于雍正、乾隆年间的诗人程晋芳(1718—1784)在其《望溪集后》中有云:“夫诗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4]嘉庆、道光时的著名诗人陈文述(1771—1843)在其《顾竹峤诗叙》中亦曰:“有诗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5]这种划分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清代学者对传统诗学批评理论的重大贡献。但追根溯源,这种源自对诗歌进行文学类型的批评早在唐宋时期便已展开,并在两宋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就。
“诗人之诗”概念的提出要远远早于“学者之诗”,而且“诗人之诗”乃是从“诗人之赋”这一赋学批评概念转化而来的。根据现存诗学史料可以看出,早在西汉晚期,辞赋大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就提出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概念:“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6]其对赋体文学的概括,在中国古代文类批评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受此启发,唐代诗学批评家开始对诗歌进行文学类型分析,将诗歌划分为“诗人之诗”与“词人之诗”两种类型:“诗有二家:一曰有诗人之诗,二曰有词人之诗。诗人之诗雅而正,词人之诗才而辩。”[7]宋代诗学批评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并与“诗人之诗”形成尖锐对立,进行更加深入的诗学理论探讨。所不同的是,唐人眼中“雅而正”的“诗人之诗”属于传统诗学体系中的“名门正派”,而“才而辩”的“词人之诗”则是等而下之的变体,其“正”与“变”暗含着高与低之分;而在宋代作家视野里,“诗人之诗”则是偏于感性而“不知道”的纯文学,与“肇自典谟,本之经术”的“学人之诗”相比,其价值要大打折扣,爰及宋末,这种扬此贬彼的意识体现得更为明显。
学界普遍认为,最早正面提出“学人之诗”概念,并与“诗人之诗”加以对比讨论的学者,应该是南宋中期著名的理学家、有“东南三贤”之称的张栻(字敬夫,号南轩)。据元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记载:“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张栻)。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8]张栻认为“诗人之诗”太过专注于语言、格律等形式技巧,而内容上显得非常浅薄,缺乏内涵;“学者之诗”正好相反,表面看起来朴实无华,但经得起仔细咀嚼,如品陈酿,滋味绵长。而张栻所谓“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划分的理论根据当源于北宋小程子的有关说法。程颐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9]程颐推崇的是研讨六经大“道”、关注道德性命、从总体上探究儒家经典的内容和精神实质的“义理之学”,对文章(诗文歌赋)、训诂(对经典字句进行解释和考订)、异端(佛道思想)加以贬斥。与张栻限于诗歌创作不同,小程子是从宏观层面阐述道与文的关系,是其重道轻文诗学观念的体现。应该说明的是,南宋中期以前,诗坛存在的主要是“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的对立,它们分别代表着“唐音”和“宋调”,是宋代作家争夺诗歌话语权、建立新的诗坛秩序的体现,其主流便是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形成了“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的宋代诗歌特征。而张栻所提倡的“学者之诗”仅仅作为“文人之诗”的羽翼或支流而存在,其诗坛地位并未获得充分体现。这一状况直到南宋晚期才获得极大改变。
随着宋季理宗一朝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因缘际会,肇始于南宋中期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争论,开始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展开,并逐步形成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诗坛两大营垒。以“永嘉四灵”“江湖派”为代表的“诗人之诗”和以理学家为主体的“学者之诗”两军对垒、其他诗人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共同构成宋季诗坛“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大家缺席”[10]的奇特景象。
南宋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和“江湖诗祸”的影响,纯粹诗人被排除在权力场域之外,其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而“诗人之诗”作为文化资本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完全被边缘化。对此,理宗朝名臣江万里在《嬾真小集序》中颇有感慨地说:“诗本高人逸士为之,使王公大人见为屈膝者。而近所见类猥甚,不能于科举者必曰诗。往往持以走谒门户,是反屈膝于王公大人不暇。曾不若俯焉科举之文,犹是出其上远甚”[11];宋末戴表元云:“近世汴梁江浙诸公,既不以名取人,诗事几废。人不攻诗不害为通儒。……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12]但物极必反,诗人地位的下降反倒激发了他们的作诗热情,创作出与士大夫文人截然不同诗风的作品。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代表的诗人群体被视为既是宋季诗歌创作的主体,亦是“诗人之诗”的典范。作为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大多不事科举,追求林泉高致,以纯粹诗人自居,从生活方式、作诗原则和审美理想上与庙堂文人和儒家学者之间划上一条颇为清晰的界限。徐照与徐玑、翁卷、赵师秀号为“永嘉四灵”,不满江西诗人的资书以为诗,倡导捐书以为诗,主张向晚唐诗人学习,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山水小景和闲情野趣,倡导清瘦野逸、平淡冲和的诗歌风格,而江湖诗派亦追随四灵诗人的诗学理念。
宋季文人士大夫则崇尚道学,在诗学观念上强调“学者之诗”甚至“儒者之诗”,作诗大抵疏通畅达,切近事理,务为有用之言,不屑为藻缋之词,故不以文采见长。其上者如叶适诗歌“晚尤高远。……其间与少陵争衡者非一,而义理尤过之。”[13]魏了翁“所作醇正有法,而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1]1391,“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诗其文皆如语录。然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1]1386其下者则如刘克庄所批评的那样:“本朝文治虽盛,诸老先生率崇性理,卑艺文,朱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氏意,水心叶氏又谓洛学兴而文字坏。”[14]125在晚宋,“学者之诗”几乎等同于语录讲义之押韵的“义理诗”,极大地压缩了诗歌的表现空间,降低了诗歌本来应该具备的审美价值。
二、“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特征差异
欲明确“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不同,首先须弄清楚何为宋人眼中的“诗人”和“学者”。可以看一则刘克庄相关论述:“诗必与诗人评之。今世言某人贵名揭日月,直声塞穹壤,是名节人也;某人性理际天渊,源派传濂洛,是学问人也;某人窥姚、姒,逮《庄》《骚》,摘屈、宋,熏班、马,是文章人也;某人万里外建侯,某人立谈取卿相,是功名人也。此数项人者,其门挥汗成雨,士群趋焉,诗人亦携诗往焉。然主人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深浅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处。”[15]25他于此区分了诗人、学问人(学者)、文章人(文人)、功名人(官僚)等身份,虽然学者、文人、官僚都写诗,但与“诗人”却显然不同,“诗人”当是特指某一类人物。宋末元初遗民诗人郑思肖在其《中兴集自序》中将平生往来唱和交流的人分为“名相”“阃臣”“名臣”“道学”“诗人”等[16],同样也将“诗人”和“学者(道学)”分别列出。由此可以看出,在晚宋历史语境中,“诗人”特指那些没有或不屑于仕进而以游士为身份特征的、专擅诗歌创作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而“学者”则指那些强调“道问学,尊德性”、阐扬道德义理的士大夫文人,特别是程朱理学一派人物。
整个宋代始终弥漫着一种重学轻文的氛围,文人特别重视“学”,所谓“以才学为诗”就是在诗歌创作中强调儒家义理的呈现,体现浓厚的道德意识和学术精神。通观宋代,大凡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文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学者型的作家,而不像唐代文人那样以纯粹诗人引以为傲。因此,当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赠王介甫》)来称许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年轻的王安石时,被赞美者则对此回应“它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这一回答显示了王安石的儒者或学人追求。这种态度同样在南宋理学家身上得到体现,如被视为理学家中最能作诗的朱熹便不愿以诗人自居。据《鹤林玉露》甲编卷六记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熹与焉。文公不乐。”[17]我们可以透过刘克庄的一段论述考察宋代诗人逐渐边缘化的状况:“本朝文治过唐远甚,经义词赋之士悉尊宠用事,惟诗人遇合者少。内而公卿,外而强大诸侯,穷贵极富,致士满门,类多抵掌谈功名、飞笔作笺记者,未尝容一诗人也。”[14]79到宋季理学官方化的时代,这种轻“诗人”而重“学者”的意识进一步强化,掌握政治、学术和诗学话语权的庙堂文人普遍存在“贵理学而贱诗人”的思想倾向,宋季诗界提倡“学者之诗”,既是理学家长期以来主张“本于经术”、以诗阐道创作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传统儒家诗学注重功利的突出反映。而江湖文人似乎“自甘堕落”,常常以“诗人”自居,自觉与文人士大夫划清界限,在自己设定的诗歌圈子里“寻欢作乐”而怡然自得。自我身份的认定也基本确立了各自诗歌所要表现的疆域,从而形成了“诗人之诗”和“学者之诗”的特征差异。
关于“诗人之诗”和“学者之诗”的区别,前引张栻有关“诗人之诗”和“学者之诗”的论述已经有了基本判断,他认为诗人之诗“不禁咀嚼”,而“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宋季诗学家刘克庄、郑思肖等对此亦做过颇有价值的探讨,认为诗人与文人、学者、官僚各有所长,诗歌创作有其内在的创作原则与规范,诗人试图与不懂诗法的文人、学者、官僚谈诗,无疑是对牛弹琴,不得要领。这一论述虽然不够具体深入,但一定程度指出了“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的差异。而清代学者对此的认识显然更深一步:
昔之论诗者曰: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余谓……学人以材富,诗人以韵格标胜。”[18]
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19]
有学人之诗,……有诗人之诗。駢花俪叶、妃白偶青,獭祭心劳,鹤声偷巧。弓衣而织白傅,团扇而画放翁。既锢阏其性灵,徒求工于章句,此诗人之诗也。……若夫学人之诗,上薄风骚,根极理要,采经史子集之菁华,味兴观群怨之旨趣,必有为而作,无不典之辞,庶几司空表圣所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者乎?”[20]
这些论述不仅清楚地把古典诗歌分为“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以及“才人之诗”等类型,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归纳出每一类型诗歌的特点。当然,明清批评者多以客观公允的态度看待不同类型的诗歌,并无明显褒贬轩轾,而理学影响下的宋季诗学则表现出明确的取舍和倾向性。根据前人的相关论述并结合宋季诗歌的创作实践,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晚宋“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一些基本特征。
“诗人之诗”在题材上少关注世事、忧念时局,而多品题风月、往来酬唱祝颂之作,取材十分狭窄;形式上“斤斤于格律,屑屑于字句”[21]多写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专注于字句声律;语言上常常好为苦吟,“专以炼句为工,而句法又以炼字为要。”[1]1390体现出字句尖新的语言特点;风格上主张野逸清瘦,清空隽雅,其高者不失雅音,其下者则显卑靡。其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之《芳兰轩集》所言:“盖四灵之诗,虽镂心鉥肾,刻意雕琢;而取迳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1]1389
“学者之诗”则体现出明显不同于“诗人之诗”的特点。从作者来说,创作者要涵养道德,奠定深厚的儒学根柢;就内容而言,学者之诗要弘扬伦理道德,抒写性情义理,探究兴衰之乱之由,即钱谦益所谓“肇自典谟,本与经术”;形式上不求工拙,不讲究格律、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语言上要洗去铅华,厚重质实,风格上追求明白淳实,自然平淡。晚宋学者提倡“所为文章,淳古质直,不事藻饰,而自然畅达”[1]1389的诗歌境界。
三、关于宋季诗坛两种对立诗学思想的反思
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在论述南宋诗歌时说:“诗至南宋而宗派之说起,宗黄庭坚者号‘西江派’,宗邵雍者号‘濂洛派’,一变而为‘江湖派’,再变而为‘四灵派’,生硬浅陋,盖弊极而不可复焉。”[22]学界基本认同这一判断,问题是宋季诗坛究竟是“诗人之诗”占上风,还是“学者之诗”在主宰?这实在是一个难有完美答案的疑问。表面上看,借助叶适的《四灵诗选》、陈起的《江湖集》(前、后集)等的刊刻发行,“诗人之诗”在诗坛上一时风光无限,但实际上这种影响多局限于江湖民间,而在庙堂精英阶层则依然流行着“学者之诗”,特别是在理学官方化的宋季,士大夫文人自然强调诗歌的义理化,即便江湖诗人也多有“攀附濂洛”者,以至于造成“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15]78的“盛况”。
宋代诗歌自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开始,便具有议论化、学理化的倾向,“文人之诗”逐步取代以“晚唐派”“西昆派”为代表的“诗人之诗”。到南宋后期,随着理学思想体系的确立和学术界、政治上独尊地位的获得,重教化、明义理的“学者之诗”在正统的庙堂文学中无疑居于统治地位,在这方面,理学家的诗歌表现得最为明显。自北宋以来,濂洛学派始终强调“以学为诗”,而他们所谓“学”,“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善学者本之以经,参之以史,所以明理而达诸用也。”[23]理学家利用诗歌探讨天理、人欲、情与性、诚与妄等道德义理问题。
主于明理的“学者之诗”在正统的庙堂文学中无疑居于统治地位,但专在适情的“诗人之诗”却在江湖民间则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不仅与士大夫文学并驾齐驱、占据了南宋后期诗坛的半壁江山,甚至被认为“广义上的江湖诗人几乎代表了南宋中后期诗坛的整个动向”[24]。而这一地位的取得,自然有赖于江湖诗人的创作成就,但当时文坛宗主叶适的称赏推扬更是居功至伟。叶适亲自选其诗五百首编成《四灵诗选》,由杭州书商陈起刊刻,于是风行一时,所谓“水心先生既啧啧叹赏之,于是四灵天下莫不闻”[25]随着四灵诗人的声名远播,影从云集,桴鼓相应,“天下皆知四灵之为晚唐,而巨公亦或学之。……刘潜夫初亦学四灵,……同时有赵庚仲白,亦可出入四灵小器。”[26]遂成一堪与江西诗派相争锋的诗派,诗人众多,声势浩大,不仅在晚宋时期鼎盛一时。而且流风及于有元一代:“近时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27]应该说,宋诗发展到南宋中后期,在江西诗派一家兴盛、“文人之诗”“学者之诗”占据诗坛主流的情况下,“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的横空出世,“摆脱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28]他们补偏救弊,标榜新的审美风尚,关注诗艺,回归语言精致、声律和谐的传统,于矫正江西诗派之偏颇、规正诗歌的健康发展是有很大意义和历史功绩的。但是,以四灵诗人和江湖诗派为代表的“诗人之诗”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问题。其主要体现,一是取径太狭,立志不高。“四灵,倡唐诗者也,……然具眼犹以为未尽者,盖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贾也。学者闯其阃奥,辟而广之,犹惧其失,乃尖纤浅易,相煽成风,万喙一声,牢不可破,曰‘此四灵体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坏,不复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29]二是雕琢太甚,运思清苦。“四灵诗薄弱,其锻炼处露斧凿痕。所取者气味清纯,不害诗品耳。不及唐人远矣。”“四灵气味似诗,然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馁弱。”[26]其它如思想蕴含不深刻、艺术表现不浑厚开阔等,都极大限制了“诗人之诗”的历史成就和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多以“以纤佻为雅隽”“油腔滑调”“冗沓琐碎”“寒酸纤琐”“委琐”“鄙俚不堪入目”“蔬笋气重”等否定性的语言对晚宋江湖诗歌加以批评,也一定程度说明宋季诗歌走向全面衰落的窘况。
总体看来,晚宋“诗人之诗”和“学者之诗”各擅胜场,如“诗人之诗”对诗艺的精研,“学者之诗”对哲思的探究,在各自领域对诗歌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有意义的深度开拓。但是这些只是注重“小结裹”而缺乏“大判断”的局部调整,而两种诗歌的尖锐对立带来的是诗学观念的越来越偏激,而随着官方意识强势介入文学,“学者之诗”不断收编越来越孱弱的“诗人之诗”队伍,最终结果便是“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14]92繁华过后是沧桑,宋季诗歌走向“弊极”似乎成为一种“命中注定”,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