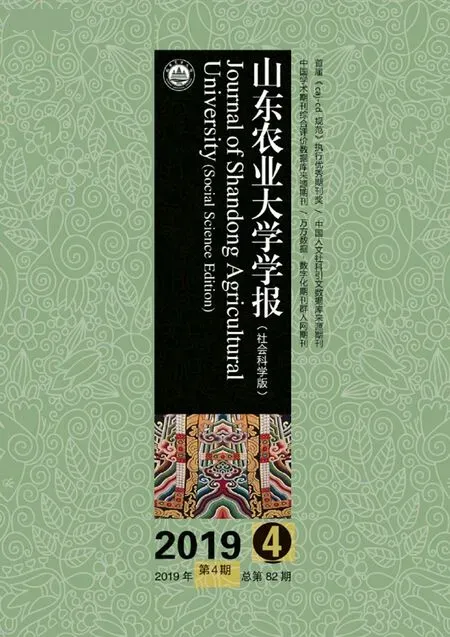论莫言小说中的“儿童之死”
2019-02-10□李阳
□李 阳
[内容提要]莫言小说中多有对儿童死亡现象的叙写,其“儿童之死”寄寓着不同的主题内涵,可归纳为三类:审视战争与反思历史的殉葬悲歌主题、质疑权力异化的痼疾的亲情之殇主题,以及表达道德失落忧思的消费语境批判主题。莫言以自己独特“儿童+死亡”模式,完成了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死亡是生命个体不可逃脱的必然趋归,也是每一个人心底难以言说的彼岸情结。死亡作为正常的自然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呈现,这点正如学者殷国明所说:“艺术的起源不仅联结着一个阳光普照的白天,而且深深扎根于无边无际的黑夜——死亡。”[1]与死亡相反,儿童则往往是新生与希望的代言人,他们年轻,充满活力,朝气蓬勃,象征着美好与未来,离死亡很遥远。当儿童与死亡相勾连时,往往意味着是一种非正常事件,暗示了社会的某种症候。事实上,文学作品中出现儿童死亡在不同历史时期表达不同的主题,如鲁迅《明天》里的宝儿因救治不当而夭折、《祝福》中阿毛被狼叼走,作家以此批判彼时腐朽的社会体制及动荡的现实,揭示人性中的愚昧和黑暗。在“十七年”时期文学中“儿童之死”的叙述,则表达个体为民族国家牺牲、奉献的主题,如《苦菜花》里母亲为保守八路军的秘密,女儿嫚子被折磨致死。莫言的小说亦不乏“儿童之死”的叙述,但他书写“儿童之死”与上述时期的“儿童之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隐喻与题旨内涵,对其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莫言小说的特质。
一、殉葬悲歌:审视战争与反思历史
人类经历了无数战争,战争给人带来的最直接的毁灭性打击就是死亡,死亡作为一个特殊的意义单位承载着人类对战争的记忆。因此,许多作家往往通过书写战争的死亡事件,来表达对战争的态度。它们或反思战争的痛苦,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以西班牙内部战争为背景,讲述流着相同的血、有着相同信仰的双方剑拔弩张、兵刃相向的悲剧;或论证战争的合法性,揭露敌方的凶残,如“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书写战争的死亡,要么是表征胜利的快慰,要么是表达着激起更大战争勇气。
其实,任何战争对人类而言,都是杀戮与劫难,正如学者王富仁所说“战争文学离不开战争,但战争文学不能仅仅是对战争历史的摹写,它更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作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而不是对战争中的任何一方或某个历史事件的是与非的反思。战争本身是人类的一种灾难,无论对于失败一方还是胜利一方,战争带给他们的都是灾难。”[2]
莫言的小说则正是表现出对战争的审视态度,他通常在小说中通过“儿童死亡”事件的叙述,展示战争对儿童的摧残和毁灭、审视战争的惭愧和对生命早逝的惋惜。他有意识地回避战争的崇高感,通过儿童群体的死亡切入战争并凸显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不仅仅将战争中的残暴杀戮所暴露的人性之恶进行无情的揭示,而且关注到战争意外对儿童生命无声无息的剥夺,试图在这样的编纂中构筑出历史的另一种解读层面,设法呼吁人们对战争的反思。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我”母亲未出嫁时遇上了日本人包围村庄,外祖父母为了保护母亲和小舅舅,将他们藏在枯井里,可自己却再也没有回来。母亲有幸等到余占鳌父子的解救,但小舅舅因多日水米未进已经饿死了。普通父母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在战争面前任谁也做不到万无一失,这就是战争的无情与残酷。类似遭遇的还有小姑姑香官。香官是余占鳌与恋儿的女儿,日本人洗劫村庄时,六个穿着金黄色军装的日本士兵畜生般侮辱了恋儿,并残忍地用刺刀挑起小姑姑又使其狠狠摔到地上,导致其最终死亡。另外还有《丰乳肥臀》中三姐上官领弟与孙不言之子大哑和二哑在国共内战期间被天上盘旋轰鸣的飞机炸死。战争的硝烟使得成人的生命都如草芥一般,何况尚未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的儿童。在这些作品中,战争导致的新鲜生命的流逝而非战争性质,是作家关注的焦点,生命的本体意义成为评价尺度之一。
海登·怀特曾描述历史叙事为:“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3]也就是说,过去的事件本身并非一定存在意义,而是需要通过叙述者撷取更符合个人和社会审美、符合当下意识形态的材料,进行真实事件和虚构故事之间的编纂,运用隐喻式的技巧使文本中的事件产生意义。同样,“儿童之死”是莫言反思历史的隐喻手段,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之恶进行反思。英国学者吉登斯将现代化进程比作一匹马力巨大又失去控制的引擎,意在指出其运行的进程陷入无可估量的风险之中,而造成风险的原因之一即操控的失误。正如他在著作《现代性的后果》里说:“任何抽象体系,不论它设计的如何尽善尽美,也不会按人们所假设的那样完美的运作。”[4]从根本上而言,莫言以“儿童死亡”为利器,所要展现的正是对历史进程中的操作失误的审视与辨析。《丰乳肥臀》中,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主、也是后来的抗日别动大队司令司马库的女儿司马凤和司马凰姐妹俩死于土改大会上,徐瞎子上台控诉地主恶霸司马库的压榨行为,主张杀其女儿;另一部分人看穿徐瞎子公报私仇的本质,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现场陷入了一半赞同一半反对的尴尬境地。但是领导张生为了尽快树立共产党在民众中间的威望,将母亲的坚决反对视而不见,武断地选择一味地以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秘密派人射杀司马库的两个女儿。同时作为孩子亲属的鲁立人将上级命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牺牲伦理和道德为代价保持自己的政治正确。至此,帮助深受压迫的农民翻身做主的利于人民的社会变革,竟然在盲目的具体实施中变质成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莫言以此向历史上曾发生的国家伦理野蛮侵入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提出质疑,以此呼吁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到了八十年代,国家为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矛盾,颁布计划生育政策,并定为基本国策。于是出现《蛙》一书中,被誉为“送子娘娘”的姑姑迅速转化为执行政策的急先锋,亲手结束了两千八百小生命。事实上,莫言在全文的描述中并未直指计划生育制度,而是借助姑姑晚年的忏悔替代对政策的指控。姑姑始终背负强烈的道德谴责,为了赎罪,姑姑嫁给了捏泥人的手工艺人郝大手,对泥娃娃吊唁,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在这里,即是莫言借文中姑姑之口展示自己对生命的敬畏,揭露生育制度中人文主义的缺失和执行中的偏颇,它超越了国家与个人狭隘的对立模式,是对整个历史进程中个体伦理与国家政策执行间的矛盾与困境融入具有厚度的反思。
总而言之,莫言通过“儿童之死”的书写,一方面批判战争的罪恶,召唤人性的复苏;另一方面质询和反思了历史境遇中的种种生存症候,具有开阔的历史反思的视野,并非简单的止步于社会文化批判,而是不断回望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生存境况,探寻生存困境突围,构筑具有现实意义的审美生存关怀。
二、亲情之殇:质疑权力异化的痼疾
巴雷特认为:“西方人已经变成了三重(自然界、与其他人、与自己)异化的人。”[5]萨特认为,真正可怕与恐怖的地方不是有神论的地狱,真正可怕与令人恐怖的是因“别人”造成的“异己现象”。如果“别人”干涉与剥夺了自己的自由,那么“我”就陷入了真正的地狱。“异化”,从本源意义上追溯,源于德文,意为疏远化或冷淡化,而在拉丁文中,又表示出卖和转让的意思。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异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阶段的不同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如费尔巴哈从唯物论出发,强调神是人的自我异化,只有消灭旧的宗教,才能消除异化、实现人的本质,从而建立充满理性和爱的新宗教。黑格尔则从唯心论出发,认为先有理念,理念异化为自然,而后产生了人,人具有自我意识,也就是精神回到了自身,提出精神异化的概念。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概念,认为异化的根源蕴藏在经济关系中,人与社会的全面异化首先是从劳动异化开始的,并且归纳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三个方面的异化。尽管解读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异化的本质是“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人格趋于分裂。”[6]在莫言小说中“儿童之死”的根源之一就是政治权力对人造成的异化以及在这种环境中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丧失。
在莫言的笔下,政治权力呈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乡村政治权力,新政权的初步建立、僵化愚昧的封建宗法观念、刁钻狡黠的人性欲望,三者共同形成了一套专制性权力结构。在这种异化的现实下,基层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不似《白鹿原》中以宗法为基础的乡规制约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交换与尊卑意识。基层干部作为中国权力制度中的最底层,控制着内部利益分配与基层建设管理,俨然成了外强中干的“土皇帝”。短篇小说《枯河》中,大篇幅描写父母对小虎子的暴打致使身心俱创的小虎子落入冰窟窿自杀,但施暴之因却是来自“干部”的权势。小虎家被划归为中上农,这是一个具有“暧昧性”的身份:表现的好就有可能和贫农雇农团结,表现不好则会被打成富农永世不得翻身,至于具体的评判标准,自然是村里的领导干部说了算,也正因此,小虎一家人都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相反,村支书是村子里的权势代表,拥有着全村唯一的瓦房,院子里砌着很宽的甬道,有一道影壁墙,还立着两辆自行车,车圈上的镀镍一闪一闪的。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公平正义、仁爱慈祥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封建专制的卑劣无耻、蛮横无忌的嘴脸,他当众嘲弄小虎子,拧着他的耳朵,当着许多人的面问:小虎,一条狗几条腿?基层政权在他手里已经面目全非。小说中多次出现对权势的隐喻,如:“村中央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把顶梢插进迷蒙的气体里,挺拔的树干如同伞柄,气体如伞如笠,也如华盖如毒蘑菇。村庄里的所有树木都瑟缩着,不敢超过白杨树的高度……白杨树把全村的树都给盖住了,犹如鹤立鸡群”,[7]这里的白杨树和其他树木的正是象征着权力极度膨胀的非常态社会中当权者与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地位差距。
权力下人们的异化,即个体存在的意义价值丧失,是“儿童之死”的直接原因。《枯河》里的父母在权势中被异化,他在潜意识中将权力同日常生存联系在一起,生命就等同于求生的本能需求。当村支书嘲弄小虎时,身为父亲的反应却是认为书记愿意逗他,说明跟自己一家合得来,是心里有自己,俨然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当代运用;小虎从树上摔下来砸到书记的女儿小珍,书记对小虎拳脚相加,这时的父亲跪着哀求书记,通过语言上的竭力贬低儿子来求取饶恕;回到家后,父亲三次将小虎拎起来摔到地上,并在大儿子的帮助下用沾了盐水的麻绳抽打在小虎子赤裸的身上,直到打人者气喘吁吁。父亲是一位别无所长、事事隐忍的农民,他唯一做错的就是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一块地,正因如此他的成分定格到了中农,并且这个身份符号也像噩梦一样继续影响着他的后代。这种情况下,他面对着怒不可遏的书记,面对着自己儿子尽管不是有意犯下的大错,他能做的就只有通过毒打自己的孩子以躲避更大的灾祸,实属艰难时势下一个父亲的无奈之举。而小虎的哥哥在熟悉事情始末后的反应却是愤怒地给母亲说:“砸死算了,留着也是一个祸害,本来我今年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子全完了”,在哥哥的眼中,小虎子葬送了自己当兵的前途和改善全家命运的希望。母亲埋怨父亲土改前不合时宜的买地行为,哥哥甚至埋怨嫁给中农父亲的母亲,对出身和未来的绝望使得这个青年看不见出路。事实上,小虎并非村里人眼中“少个心眼”的孩子,他身体素质好、有高超的攀树技巧,他珍惜与小珍的友情,为了满足她的要求不顾家人的警告爬上白杨树,他是有童真童趣的活生生的孩子。小虎的格格不入在于他是一个自闭型儿童,沉默寡言,他的种种奇怪行为,包括回答狗有三条腿、在父亲毒打时骂“狗屎”以及最后离家出走投向死亡,实际上是对异化状态的无言反抗,这是他作为一个儿童,面对权势以及被权势异化的社会做出的最决绝的反抗姿态。
如果说《枯河》是“奴在身”,它表明“在权威性质的文化与行为面前,人身上体现更多的是机械化服从的局限性”[8],那么《普通话》就是另一种权力异化模式:“奴在心”。柿子沟人对外面来的讲普通话的人充满敬意,但对于自己村子里学说普通话的人则是极端鄙夷。当中专毕业生小扁放弃吃商品粮的大好前程,回乡教书、倡导普通话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学生小青是推广普通话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普通话使用的衷心爱好者,这样一个小姑娘竟然喝农药自杀了,并且留下了一首表示不愿学普通话的诗。也正因为小青的死,停止了全县中小学推广普通话的活动,一腔热血的小扁也发疯了。权力之间的角逐外化为使用何种语言:柿子沟的土话还是普通话。前者代表的是闭塞落后、所有人都如同井底之蛙般服从于村长的权威;后者则如同小扁所说,“普通话不仅仅是说话的腔调,还是人的身份、尊严。”它象征着开放与现代文明,是唤起村民们个体意识与自我选择权力的一把钥匙。村子里流传的“荞麦地里打死人”的笑话、嫉妒心理作怪的高大有的万般阻挠无一不是已经异化的人对真正的自我的拒绝与排斥。正如刘再复所说:“最残暴的‘吃人’莫过于自食,自食以自己为吃的对象,陷入自我毁灭,它是更深层次上的‘吃人’。”[9]小青同小虎子一样,“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反而成为了其他人眼中不正常的异类分子,他们似是在铁屋子里的觉醒者,却又无能为力,母亲的嘲骂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小青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自杀的孩子。这种自主性的丧失不仅仅在于外在不合理的权力束缚,更侧重于人将这种不合理的束缚内在化,异化的习惯沉积于自身,并且化为自觉的行动,摧残自己的同时还要摧残未被异化的儿童,最终成为麻木无知的木偶。
不论是“奴在身”还是“奴在心”,莫言所写的这一类的“儿童之死”也正是聚焦权力文化痼疾带来的异化生存症候。权力的极度膨胀成为笼罩在人周围的高气压,造成的弊端不止体现在权势之下所褫夺的物质利益,更在于对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扭曲与变形。普通民众习惯于对权力低眉顺从与顶礼膜拜,自我抗争意识与个体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就被消解,从而由有血气有思想的人变成了同鲁迅笔下一样的看客。他们当稳了奴隶,在权势者的表演中找到了快感,也反过来增强了权势者的气焰。一言以蔽之,亲情之殇下的悲剧就是一场人被权力异化而不自知,又盲从于压迫自己的权力的悲剧。它表达对恨与丑的高度焦虑,以及对权力导致的异化下儿童成长艰辛的永久悲悯。
三、消费的切片:道德失落的忧思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以迅猛的态势进入到了一个全新转型的商品经济时代,“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经济上商品具有政治话语的权力,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新神话;文化上全面张扬欲望。”[10]有社会学家直接称其为“后物欲时代”。经济领域的这一方沃土,滋养了消费主义文化,消费至上的观点漫漶全球,消费成为一切社会分类的基础。不言而喻,消费主义席卷中国,击垮传统价值观念和情感导向,重构了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莫言作品中这一时代的儿童的死亡,就如同一面凸透镜将消费与享乐主义下的中国社会的所有不足尽数放大、展现在人们面前出来。
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通常有两点:一是商品化逻辑。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物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此时物品即商品,消费者购买商品在于利用其使用价值。而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认为,物品成为商品的必要条件并非在于它的有用性,而是与符号系统内部的相互差异和等级秩序相联系,物品首先要成为符号。也就是说,物品的有用性消费开始让位于符号消费,消费就成为了一种操作符号的行为,以此来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地位。《酒国》主要描写了国家侦查员丁钩儿来到酒国执行关于红烧婴儿事件的调查。酒国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欲望之都,这里的上流官员热衷于食用一道“婴儿宴”,起初该菜品是由猪肉、莲藕等原料制作成婴儿的模样,但是后来竟然真的杀小孩子来满足人们的消费,从普通家庭用男孩卖钱、烹饪学院教授并制作到酒席上享用,婴儿宴在酒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出售、制作加工以及经营消费的合法过程。这里的吃人并非因为食物短缺的不得以为之,而是消费主义发展到极端的残忍表现,官员和暴发户们以食用婴儿为荣,通过这种符号消费来给自己定位、彰显自身。二是欲望化逻辑。正如费瑟斯通说道的:“遵循享乐主义、追求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11]于是,在消费文化的欲望释放观念下,越来越多的人持这种观点:欲望的满足就是幸福,而只有尽可能多的占有财富才能满足源源不断的欲望,也就能达到最终的幸福,因而人们在赚钱—消费过程中找到了归属感。看似合情合理,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消费社会,其实就是欲望化生存的社会,驱动消费社会前进的不是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换言之,对于消费享乐欲望的极力推崇实际上是将人陷入受欲望支配的境地,一切人类活动都将以满足无限的欲望为起点和终点。《四十一炮》中,小说明确指向市场经济的生存语境,以村长老兰为首的屠宰村,通过贩卖注入化学防腐剂的生肉,以此攫取不义之财。莫言敏锐的察觉到因社会语境发生的巨大转变带来的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欲望把持下道德失落等现实存在的弊端,这也是儿童走向死亡命运的原因。
社会学家曹锦清曾说:“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既不在官方手中,也不在知识分子手中,而在先富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即通过享受与攀比形成的消费标准与消费方式中。”[12]先富者是这一时代的弄潮儿,他们高度物质化、消费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社会各个层面蔓延,而消费主义的放纵欲望、追求享乐的行为,往往是同非道德联系在一起。传统伦理上的程朱理学告诫我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新中国建立后强调舍小我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可以看出,欲望一直被视为道德上的“恶”被鄙视的。而进入消费社会,不仅宏观上,欲望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微观上,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也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首要标准,这种情况下,欲望的巨大转变直接冲击人们对欲望的看法与判断。首先,功利性、物质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迅速取代了传统的非功利性观念,成为新时代的主导。《四十一炮》中经济体制改革前的屠宰村是一个祥和安宁、以种地为生的传统村落,虽然物质生活相对贫瘠,但打谷场经常传来欢声笑语;改革后,村子成了专业屠宰村,并且村民在金钱刺激下开始卖黑心注水肉。顺应时代潮流的老兰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的农民企业家,明面上向世人承诺不卖注水肉,暗地里拉拢官员、威胁记者,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用尽手腕。《酒国》里父母生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卖钱,丈夫拿到钱欣喜地仿佛刚刚卖的只是家里的牲畜;知识殿堂的高等学校将剖杀婴儿设置为课程,不仅教师有专门的科学术语,就连学生们也听得非常认真,似乎他们用于宰杀的只是普通的教学模具。其次,身体欲望解禁,传统道德伦理受到挑战。在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欲望的禁忌与负罪感被一扫而尽,性被物化为商品,使得道德模糊化。罗小通的母亲杨玉珍,一位勤俭自强的农村妇女,遭到父亲的背叛后母亲立志要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没有丈夫自己能过得更好。父亲五年之后带着私生女还乡,母亲虽然有埋怨,但最后还是接纳了父女俩。老兰肉联厂成立,母亲被任命为财务主任,面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逐渐失去了自我,不仅成为了麻将桌上的常客,甚至同老兰保持着暧昧的情人关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伦理道德体系的全线崩溃,强烈的物欲追求使人和动物毫无分别。最后,消费至上打破传统人际关系格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匮乏。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的乡土文明中,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如同一粒石子,将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水波纹就是中国乡土传统的社会关系,即“差序格局”。但是在转型时期,人情淡漠与信任危机成了人们普遍的精神困境。在老兰妻子的葬礼上,杨玉珍与老兰的不正当关系被人当众揭露,罗通在愤怒与羞愧中杀死杨玉珍,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罗小通从此家破人亡,只有他和妹妹相依为命,而妹妹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不久后死于食物中毒。妹妹的死亡揭示了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片面追求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欲望追逐和道德失落。
儿童之殇书写,正是莫言以其前瞻性的敏锐感受审视从欲望禁锢到欲望释放这一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的生存悖论。正如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的结尾中强调的:“消费是关于当代社会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13]通过消费社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消费享乐主义带来的弊端,它们是不可阻止而且也不应该完全阻止的,但根据“儿童之死”的悲剧做一些必要的反思是作者的初衷,更是当下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四、结语
虽然只是在描写死亡,甚至可以说“儿童之死”只是莫言千万文本中的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故事情节,但莫言的视野显然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借助“儿童之死”,莫言聚焦的是对逝去儿童生命的同情与悲悯,展现作家的人文关怀;是借助儿童这一弱势群体进行对社会痼疾的暴露与批判,表达对现实秩序、历史本质的追问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