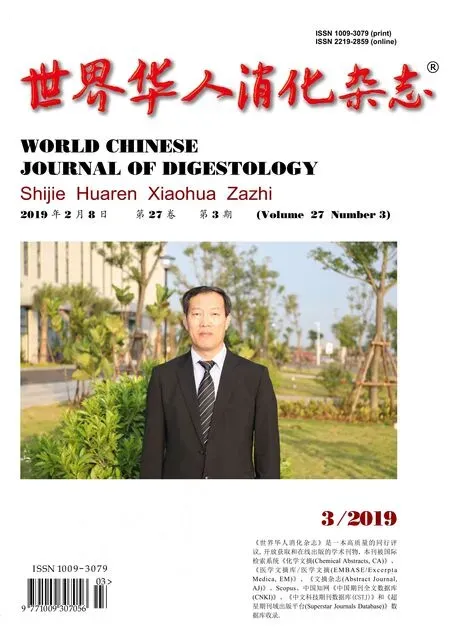肠道菌群对炎症性肠病诊断的研究进展
2019-02-09曹莞婷范一宏
曹莞婷,范一宏,吕 宾
曹莞婷,范一宏,吕宾,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 浙江省杭州市 310006
核心提要: 肠道菌群的结构及功能变化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发病机制中的关键环节,并随IBD疾病进展变化.肠道菌群预测模型在IBD诊断上具有较高特异度和敏感度.基于IBD肠道菌群特征性变化,联合多项检查,有助于 IBD鉴别诊断、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及明确肠外表现.
0 引言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由免疫、遗传、环境三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的消化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疾病,目前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及未定型肠炎(indeterminate colitis,IC).虽然IBD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是肠道微生物(Enteric Microorganism)在IBD的发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已达共识,IBD患者肠道微生态(intestinal microecology)失衡,诱导异常免疫反应,破坏肠道稳态,最终致使肠黏膜屏障完整性缺失,临床上主要症状为腹痛、腹泻、黏液血便等,部分患者伴消瘦、贫血等.临床研究认为临床表现结合内镜下表现、影像学及病理学结果,并排除其他肠道疾病后,有助于IBD诊断,但是仍缺乏金标准.血清生物标记物的介入为IBD诊断提供了新依据,其中以联合检测pANCA和ASCA最为常用,但因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不高,限制了临床诊断价值[1].近年来,针对肠道微生物的研究已从疾病与肠道微生态相关性分析向因果关系及机制探讨迈进,多项科学前沿报道肠道微生物可作为疾病诊断的新型标记物.本文拟综述近年来肠道菌群在IBD诊断方面的研究进展.
1 IBD患者肠道微生物特征性变化
肠道微生态改变是IBD病变特征之一.通过宏基因组测序对人体肠道微生物的研究证实99%的微生物基因来自于细菌,可分为共生菌及致病菌,当共生菌与致病菌动态平衡遭到破坏即诱发肠道菌群失衡[2].超过大约90%的人由四大类菌群组成,其中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占主导,另有变形菌门及放线菌门.相对于健康人群及其他功能性胃肠道疾病,IBD患者中肠道微生态失衡更为严重,伴随菌群多样性及丰度下降、菌群结构的改变、不稳定的菌群等情况.目前一致性认为IBD患者肠道菌群组成变化以厚壁菌门减少和变形菌门增加为主,而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的变化尚未达成共识,其中IBD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与厚壁菌门中的柔嫩梭菌属变化密切相关[3].同时对比IBD患者和非IBD患者粪便菌群研究发现拟杆菌目、瘤胃球菌科、梭菌目、类丹毒菌科、双歧杆菌科提示IBD患病呈低风险,肠杆菌科、毛螺菌科、普氏菌属提示IBD患病呈高风险[4].除肠道共生菌整体性变化外,部分致病菌感染亦是IBD疾病触发及病情演变的关键因素.相较于其他致病菌,IBD患者最常见艰难梭菌感染,长期感染艰难梭菌的IBD患者,其疾病进程更迅速且病情发展更严重.活动性IBD除艰难梭菌感染外,重叠其他肠道细菌性感染率有3.6%(2%-9%),弯曲杆菌、黏附侵袭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鸟分歧杆菌亚种副结核等致病菌在IBD患者的肠道活检组织、粪便样本中有很高的阳性检出率[5].虽然肠道真菌在肠道微生物群中比例较小,但是在IBD患者中真菌群落相较于健康人群结构发生变化,多样性增加,肠黏膜定植密度升高[6].研究将IBD患者粪便微生物群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发现,前者担子菌门与子囊菌门的比例增加,并伴促炎真菌白色念珠菌丰度增加及抗炎真菌酵母菌丰度减少[7].肠道病毒数量为细菌的10倍[8],最为重要的是噬菌体,它具有严格的宿主特异性,以活菌为宿主,同时赋予宿主菌生物学性状的遗传物质.临床研究发现相对于健康人群,IBD患者中有尾噬菌体目丰度增加,其中与IBD存在相关性的主要为乳球菌属噬菌体、乳杆菌属噬菌体、梭菌属噬菌体、肠球菌属噬菌体及链球菌属噬菌体[9].另一项研究证实IBD患者柔嫩梭菌群少于健康人,其中4种柔嫩梭菌群相关噬菌体在IBD患者中丰度增加,并可能进一步减少IBD体内的柔嫩梭菌群[10].事实上基于噬菌体对细菌的依存性,未来针对IBD相关特异性噬菌体的研究可以聚焦于IBD特征性变化的肠道细菌分类群中,充分利用基因组测序等技术对微生物群测序菌株的原发性噬菌体进行检测,进一步完善肠道病毒宏基因组的研究.
2 IBD鉴别诊断与肠道菌群
2.1 IBD与功能性肠病鉴别 排除其他肠道疾病是IBD诊断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当遇到非典型临床表现的IBD患者,鉴别诊断更为重要.误诊容易导致IBD诊断延迟,影响IBD及时治疗.IBD需要鉴别功能性肠病,尤其是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stem,IBS).肠镜检查是鉴别的重要依据之一,但作为侵入性检查方式,一般不作高频使用.定期监测血沉、C反应蛋白及粪钙卫蛋白常作为IBS患者筛查IBD的工具.尽管如此,每年仍有约10%的IBD患者被误诊为肠易激综合征,其中3%的患者误诊时间长达5年甚至更久[11].IBS和IBD的鉴别难点在于临床症状重叠,IBD患者前驱期可出现IBS样症状并维持数年.研究表明,即使在缓解期,实验室及肠镜检查无炎症表现,仍有59.7%的CD患者和36.8%UC患者并发IBS样症状[12].肠道微生态失衡是IBS和IBD的共性特征,而肠道微生物群的个性变化可能成为IBD和IBS鉴别的新工具.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患者存在粪便菌群失衡,与健康人群比较,IBS-D主要改变是菌群丰度减少,而不是菌群多样性下降,其中以厚壁菌门丰度减少和拟杆菌门丰度增加为特征[13].另一项针对IBS-D患者和UC患者的黏膜相关菌群差异性研究发现,IBS-D和UC的共性特征是黏膜相关细菌总数及大肠杆菌、梭菌属、拟杆菌属数量显著上升,而UC患者菌群的特征性变化是黏膜细菌总数多于IBS-D患者伴乳杆菌属的丰度下降;同时IBS-D与UC的黏膜相关细菌定植不同,前者定植于黏膜表面及附近的黏蛋白层中,而后者的大肠杆菌、拟杆菌属定植于固有层[14].相较于IBS,IBD肠道菌群紊乱更为严重,除菌群丰度变化,并存在菌群多样性改变,此外由于IBD病变部位突破黏膜层,部分肠道菌群定植部位更深,常位于黏膜层以下.
2.2 IBD与器质性肠病鉴别 除功能性肠病外,IBD需与器质性肠病鉴别.(1)结直肠癌(colon rectum cancer,CRC)是IBD病情进展中常见肠道并发症,可能与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有关.IBD患者结直肠癌发生始于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指上皮异乎常态的改变,可分为无不典型增生、疑似不典型增生、低级别不典型增生和高度不典型增生.其中疑似不典型增生是鉴别的关键点,它可分为两类,一是与炎症相关的再生变化,二是上皮的不典型增生.而要区分这两种病变,通常采取积极的药物治疗以控制炎症以及内镜监测.长期内镜涉及患者依从性问题,对不可见的不典型增生检出率较低.近年来基于结直肠癌的肠道微生物研究发现,菌群可能是结直肠癌潜在的诊断标记物.Dai等[15]发现脆弱拟杆菌、具核梭杆菌、不解糖卟啉单胞菌、微小小单胞菌、中间普雷沃菌、芬氏别样杆菌、食氨基酸热厌氧弧菌等7个菌种在CRC中富集,可区分CRC患者和健康对照,AUC为0.80(结合临床信息可提升至0.88).Xie等[16]研究发现结直肠腺瘤、早期CRC、晚期CRC患者的具核梭杆菌相对丰度逐步显著上升,利用具核梭杆菌作为标记物,在CRC诊断方面比粪便隐血、癌胚抗原等检测方法更为有效.因此将菌群标记物与内镜监测、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结合有助于提高临床CRC诊断能力.(2)肠结核(Intestinal Tuberculosis,ITB)和CD的临床和内镜症状存在较大的重叠,缺乏相对特异的指标鉴别这两种疾病[17].CD和ITB均可出现肉芽肿,前者为非干酪样,后者为干酪样肉芽肿和抗酸杆菌染色阳性,但是内镜下活检发现肉芽肿的几率较低.虽然结核杆菌培养、抗体检测和结核杆菌DNA检测等血清学检查虽然特异性较高,但是敏感性差,仅20%-50%的结核杆菌感染者可呈阳性反应.ITB中肠道菌群失衡已得到证实,Luo等[18]研究发现TB患者粪便菌群中厚壁菌门的普氏菌属和毛螺菌属较健康人群显著降低.另有两项小样本临床研究检测CD和ITB患者粪便菌群,结果证实 CD和ITB患者均存在肠道菌群紊乱,相较于CD患者,ITB患者粪便拟杆菌显著增多伴大肠杆菌显著减少[19,20].提示拟杆菌和大肠杆菌数量变化可能对二者具有鉴别诊断价值,但尚缺乏定量指标.事实上,将肠道菌群特征性变化与临床、内镜及病理相结合,可能有助于ITB和CD的鉴别诊断.
2.3 CD与UC鉴别 明确IBD诊断后,需进行CD和UC的鉴别.相较于UC,CD的内镜表现更为多样性,同一病变肠段中可有多种病变形式存在,早期病变类似于UC,可能有弥漫性糜烂、出血、浅表溃疡,因此当早期CD病变局限于结肠时,与UC鉴别困难,极易误诊.但随病变进展,CD内镜特征性表现: 纵行溃疡、鹅卵石样增生、管腔狭窄等均会出现.在IBD病变早期鉴别CD和UC,有利于控制病情进展,但由于缺乏金标准,需要将内镜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相结合,而实验室检查中的血清和粪便是研究重点.血清学检查中发现两种新的抗肠道微生物抗体anti-L和anti-C,它们可用于IBD诊断的评估,联合ASCA和pANCAs有助于区分CD和UC[21].抗肠道微生物抗体的变化是CD和UC肠道微生态失衡的间接证据,而粪便检测可以更为直观的了解患者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种类和数量.Pascal等[22]研究共纳入四个国家(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和德国)的2045个非IBD和IBD粪便样品,发现CD患者较UC患者肠道菌群失衡更严重,存在菌群多样性下降、菌群结构不稳定及8种不同的菌群标记物(柔嫩梭菌群、消化链球菌科、Anaerostipes、甲烷短杆菌、柯林斯菌属、梭杆菌属、Christensenellaceae和埃希氏杆菌属,最后两种在克罗恩患者中观察到最多)三大特征,基于上述特征诊断鉴别CD和UC,灵敏度达80%,特异度分别达91%.Zhou等[23]研究同样基于肠道菌群建立IBD诊断预测模型,对CD和UC患者的预测准确率分别为87.5%和79.1%.
3 IBD疾病严重程度与肠道菌群
内镜监测是评估IBD疾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但是具有侵入性,因此合理应用非侵入性的生物标记物辅助疾病严重程度评估是近年来研究重点.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IBD患者肠道菌群结构转变,多样性下降,伴有特征性菌群丰度变化[24].基于不同疾病严重程度分层体系,IBD患者肠道菌群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性.
3.1 CD疾病活动度分层与肠道菌群 CDAI评分倾向于评估CD患者过去7 d内排便、腹痛、腹泻等临床症状,是近期疾病活动度的重要指标.Schaffler等[25]检测分析26例CD患者的肠黏膜组织微生物群发现缓解期患者(0<CDAI<220)的菌群相对相似并且由拟杆菌属(>40%)主导,而活动期患者(CDAI>220)的菌群以嗜糖假单胞菌属(25%)和黄杆菌属(13%)为主导而拟杆菌属(4%)相对丰度较低.提示不同的CDAI水平存在特征性菌群,而肠道黏膜菌群主要结构特征性转变表明CD的疾病活动度发生变化.粪便菌群结构变化同样可以用来区分活动期和缓解期CD患者.Zhou等[23]应用CDAI对CD患者粪便菌群分层,发现轻度活动者粪便中链球菌属丰度增加,中重度活动者粪便中变形菌门、肠球菌科丰度增加同时伴有瘤胃球菌科、梭菌目丰度降低.粪便微生物群主要代表肠腔内的共生菌,并不等同于肠黏膜上的微生物群.Danyta等[26]研究重复收集71例CD患者粪便样品,并依据生化及临床参数将粪便样品分为缓解期和活动期,应用50个差异分类单元(OTUs)组合建立预测模型,证实能够准确预测73%的缓解期和79%的活动期样本,AUC为0.82,灵敏度达0.79,特异性达0.79;深入研究发现Alistipes杆菌、普拉梭菌、卵形拟杆菌及单形拟杆菌与缓解期样品相关,而脆弱拟杆菌与活动期样品相关.
3.2 UC疾病活动度分层与肠道菌群 UC蒙特利尔临床分型根据大便次数、血便、体温、血红蛋白、血沉将疾病严重程度分为缓解期、轻度、中度、重度.Zhou等[23]依据蒙特利尔临床分析对UC患者粪便菌群分层,轻度患者中拟杆菌纲和假单胞菌科,中度患者链球菌属丰度增加,重度患者变形菌门和芽孢杆菌纲丰度增加.Machiels等[27]研究从细菌代谢物探讨UC微生态失调,结果提示产丁酸盐相关菌群罗氏菌属和普拉梭菌在UC患者中丰度下降,且与疾病活动度呈负相关.Fukuda等[28]研究基于个体OTUs中的肠道微生物整体特征设定判别值(Ds),共纳入149人,按活动期UC、缓解期UC、有亲缘关系的健康者、非亲缘关系健康者分别分为组1、2、3、4,Ds大小为组1>组2>组3>组4,并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推断低Ds值预示稳定缓解,高Ds值与UC疾病活动度相关,揭示肠道菌群种类和UC的病情进展密切相关.该项研究以判别分数作为生物标记物鉴别UC的疾病活动度,相对于依赖肠道微生物差异性变化的鉴别体系而言,本研究聚焦于肠道微生物整体性改变,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
3.3 CD疾病行为与肠道菌群 与UC不同的是,CD患者在肠道病变进展中更容易出现穿透、狭窄、瘘管等疾病行为,提示疾病行为是CD疾病严重程度评估的重要环节.CD蒙特利尔分型纳入疾病行为分型,即定义无穿透无狭窄为B1、狭窄为B2、穿透为B3、瘘管为P,应用该分型对成人CD患者粪便菌群分层研究发现,CD-B2患者肠杆菌科及假单胞菌科丰度增加,CD-B3患者气单胞菌科丰度增加,CD-P患者肠杆菌科及假单胞菌科丰度增加[23].儿童CD患者的疾病进展相对于成人更快,疾病亚型迅速发展为复杂的疾病行为,如肠梗阻、肠穿透、肠狭窄、瘘管等[28,29].针对新发儿童CD患者粪便菌群研究发现罗氏菌属、瘤胃球菌属与狭窄行为相关,柯林斯菌属与穿透行为相关,韦荣氏菌属在回肠中增加[30].
3.4 粪钙卫蛋白与肠道菌群 探讨肠道菌群与IBD病变相关的生物标记物的关系也可以间接反映IBD的疾病严重程度.粪钙卫蛋白作为非侵入性的生物标记物可以反应肠道炎症,临床上常用来监测IBD疾病活动度.Kolho等[31]前瞻性研究共纳入68例IBD儿童患者,发现粪钙卫蛋白表达水平逐渐提高,粪便微生物也随之而变,主要与总体微生物丰度、产丁酸盐菌群丰度及革兰氏阳性菌(梭菌属Ⅳ及ⅪVa)丰度下降相关;同时证实一组由9种不同细菌分类群组成的生物标记物可以预测IBD的钙卫蛋白水平,ROC曲线下面积AUC = 0.85,说明该组生物标记物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31].
4 IBD肠外表现与肠道菌群
4.1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PSC)是慢性胆汁淤积性疾病,胆汁在体内存在肝肠循环,肠-肝轴与PSC的发病密切相关.60%至80%的PSC患者存在IBD,伴随的结肠疾病通常被归类为UC,但也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表型,被称为PSC-IBD[32-34].相对于健康人群,PSC患者韦荣氏球菌属丰度更高[35].与单纯IBD患者比较,PSC-IBD患者中与胆汁酸相关的特异性微生物群种类及数量变化显著,肠道菌群中瘤胃球菌属与梭杆菌属丰度显著增加[36].无论IBD病变进展如何,在PSC患者中罗氏菌属、肠球菌属、链球菌属、韦荣氏球菌属及其他三个属丰度增加,Adlercreutzia属及普氏菌属丰度降低,而UC患者中Akkermansia属、Butyricicoccus属和梭菌属及罗氏菌属丰度降低,提示上述菌群标记物可明显区分IBD表型中的PSC-IBD和UC[37].
4.2 脊柱关节炎 脊柱关节炎(Spondyloarthritis,SpA)是一组慢性炎症性风湿性疾病,SpA与IBD的临床发病存在相关性.对SpA患者的长期队列研究发现,部分患者肠道活检存在慢性炎症,其中6.5%的SpA患者在5年内发展为临床明显的IBD[38].30%的IBD患者出现关节病变,如外周关节炎,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强直性脊柱炎[39].IBD与SpA之间存在显著的疾病重叠,极有可能与肠道微生态失衡相关[40].与类风湿性关节炎(RA)及健康人群对照,SpA患者粪便菌群中瘤胃球菌属丰度增加了2-3倍,且与有IBD病史的患者的疾病活动度呈正相关[41].部分伴有SpA的CD患者肠道菌群中存在一种特定的大肠杆菌(AIEC E.coli2A),进一步实验研究证实这种大肠杆菌驱动全身性TH17免疫异常并恶化结肠炎和关节炎的发展[42].
4.3 葡萄膜炎 葡萄膜炎在IBD患者中的发病率为0.5%-3%,是IBD患者最常见的眼病,在UC患者中,葡萄膜炎常累及双侧,发病隐匿并且持久[43].葡萄膜炎的临床常见症状为眼痛、畏光、视力模糊和头痛.眼睛是炎症性疾病常发部位,肠道微生物可介导免疫炎症反应的发生,推测肠道微生态失调可能与眼部炎症相关.实验研究发现在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小鼠中,口服抗生素改变微生物群导致葡萄膜炎严重程度降低,而肠道共生微生物群抗原的信号通过刺激视网膜特异性T细胞触发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证实了肠道微生物组在葡萄膜炎发病机制中的重要性[44,45].Huan等[46]对急性前葡萄膜炎(acute anterior uveiti,AAU)患者粪便菌群检测发现与健康对照组多样性显著不同,同时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在AAU患者中,罗氏菌属等8个属减少,仅韦荣氏球菌属增加.
4.4 代谢性骨病 IBD患者的代谢性骨病主要与低骨密度相关,常合并骨质减少和骨质疏松,而骨胳系统长期受累容易增加骨折风险.IBD患者骨质异常的危险因素主要有糖皮质激素、年龄、吸烟、运动减少、以及营养不良等,而上述危险因素与肠道微生物改变有关[47].实验研究证实肠道微生物与骨密度产生密切相关[48,49].IBD肠道微生态失衡,激活异常免疫系统,促进炎症反应,增强破骨细胞因子表达,减少钙、维生素D、维生素K等营养物质吸收,最终导致骨质流失及骨量减少[50,51].临床研究证实骨质疏松患者与健康人群在门、科、种分类水平的部分肠道菌群含量存在差异,其中芽单胞菌门、绿弯菌门、酸杆菌门、芽单胞菌科、丛毛单胞菌、厌氧绳菌科、毛螺菌及优杆菌等肠道菌群在骨质疏松患者中所占比例要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52].但IBD合并代谢性骨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特征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
5 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内镜检查、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是诊断IBD的重要辅助诊断,但是由于IBD临床症状不典型、病变发展多样化,延迟诊断、错误诊断仍频频发生,寻求新型生物标记物以便早期准确诊断IBD是研究的重点.众所周知,肠道菌群已被证实是IBD的重要病因病机,目前多项临床研究证实肠道菌群与IBD病程的关联,将肠道菌群与临床症状、内镜表现、影像学、血清学等联合应用,或有助于IBD鉴别诊断、疾病严重程度评估及肠外表现等并发症诊断,提高发病初期诊断的准确率,使患者采取及时治疗以延缓病情进展.但是肠道菌群在IBD诊断中尚存部分难点有待进一步研究.应用肠道菌群鉴别IBD与结直肠癌、肠结核、肠淋巴瘤等其它器质性疾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IBD病程长,不排除进展为结直肠癌、肠淋巴瘤或合并结核感染,在这些复杂情况下,IBD肠道菌群的特征又是如何?目前临床研究重在寻找与IBD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特征性肠道菌群标记物,而事实上IBD疾病严重程度是一个动态的病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肠道微生物标记物动态变化如何?肠道微生物不仅与肠道疾病相关,而且参与诱导肠外疾病的发病及其进展,已有研究表明IBD肠外表现与肠道微生态变化密切相关,该如何应用肠道菌群将IBD特有的肠外表现和肠外疾病相鉴别?同时目前针对肠道菌群的临床研究大多为观察性研究,部分研究结果显示的特征性菌群标记物未经大样本验证,缺乏大数据支持,其敏感度和特异度仍有待考查.另有部分研究显示基于肠道菌群建立的预测模型对IBD诊断的特异度和灵敏度较高,但是该模型部分存在缺陷,首先,微生物模型的建立受研究者主观因素影响,对不同的临床研究缺乏应用普适性,其次在建立微生物模型的过程中,受试者年龄、性别、地域、饮食、生活习惯等基线资料对肠道微生物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该模型的精准性易受多重因素影响,建模时应该严格控制变量.因此,肠道菌群要成为IBD诊断性生物标记物尚需大量试验性研究证实,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结合宏基因组测序、代谢组学等检测技术以便更好地鉴定出IBD的菌群生物标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