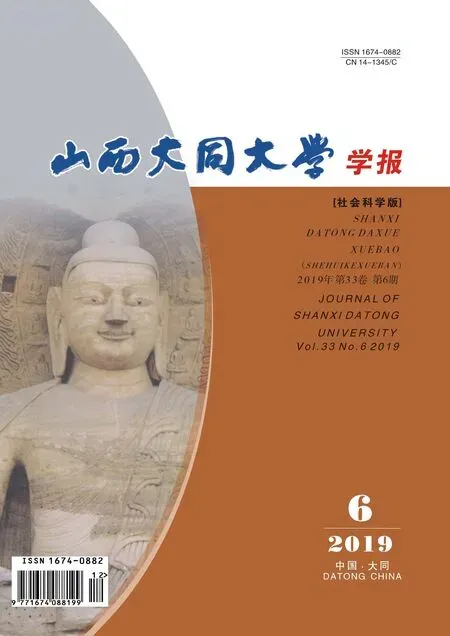辩证把握命题知识谱系生成
2019-02-09王列生
王列生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命题知识递进延展为命题知识谱系,是谱系生成内驱动力与外驱合力的复杂知识后果,作为常规科学的知识谱系学,更多地从弹性演化特征与张力形态分析去给予事态描述,这显然是知识形而上学内在追问之外的现象事态把握方式。无论弹性事态还是张力事态,象征叙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命题知识的谱系生成,其实不过是扩容和拓殖的基本演化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诸如“阐释循环”一类的语境反应,有时会使我们不同程度地,对命题知识客观性、延展性以及关联性产生怀疑,但在更加宏大的人类知识史审视视野与价值判断位置,则一定会有主体知识自觉与选择自律的总体知识学进展,一种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人的知识解放。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每一主客互动关联场域,知识发生与认识主体的关联性存在有效确证,从来都是入场者命题建构与命题博弈所形成的命题知识成果,使其凸显从而得以知识本体价值实现。对此,无论狄尔泰“功能性”定位的“只有当它们把这种参照结合到它们那些命题中去的时候,它们对于实在来说才是有效的……这些无论可能多么抽象的命题才会对于实在呈现出它们各自的有效性”,[1]还是波普尔“效果化”描述的“进化之树是从共同的树干产生越来越多的分支而生长起来的。它象像一个家谱:共同的树干由我们共同的单细胞祖先即所有生物的祖先结构……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些生长着的进化之树与我们成长着的知识的结构相比较,那么我们发现,人类知识的成长之树有完全不同的结构”,[2]抑或库恩“虚拟态”猜想的“构造某个基本科学知识的梗概”,①都是从不同叙事角度为命题、命题知识和命题知识谱系的常态状况与变态状况,提供了必然性以及可能性的学理预设。
基于这样的预设,命题知识的谱系性实在,无论处于常态还是处于变态,都是客观已然知识成果,并成为此后或然知识诉求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它是孔子知识论“述而后作”思想中,“述”作为“作”的合法性前提的现代语境表达方式,而“述”在这里可以指涉特定命题知识演绎史和全部命题知识建构史的可言说性与言说限制性,意即一切悖离命题知识谱系的命题性随机言说或者断章臆造,必然会在真值率衰减过程中成为语言游戏而非知识陈述,甚至沦落为“妄说”、“讹说”乃至“伪说”。人们在知识活动现场所时时遭遇的伪命题或显或隐的侵扰,其所产生的根源既驳杂且繁多,但缺乏命题知识谱系的严格规约,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值得引以为患的因由。
在列维——斯特劳斯“总谱”知识观念仅仅获得理论上的预设合法性的同时,我们必须站在肯定的知识观念立场,充分意识到“边际总谱”或者“知识域谱系框架”的现实合法性,并坚信人类在命题知识中的既往知识行为,及其未来一切更加复杂形态的知识创新,无不以这一现实合法性作为其显性事态抑或隐性事态的基本规则或基本维度。因此,在弹性作用与张力作用躯动下的命题知识谱系,实际上就成为一个“历时性秩序”与“共时性秩序”高度统一的有机编序整体。
其历时性秩序,既有线性因沿的一面亦有弹性替代的一面。线性因沿使遭遇问题诉求命题的入场涉身者,在其寻找参照物、处置方案或更加深度进入的真相追问过程中,既能在“沿波讨源”中,逆向窥望其所意欲窥望乃至有必要窥望的原来如此命题指涉,也能在“渐行渐远”中,顺向通向其所意欲通达并且有能力通达的后来如此命题繁衍。
于案例举证意义上,前者有如当代美学史家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对亚理士多德“模仿说”命题定位的逆向溯源,从而窥望到模仿命题根源于几何学观念的先在土壤。即所谓“‘模仿’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后来亚理士多德例说的某种针对步幅的奇怪东西,还包括单位强度间隔、言说的构成单位以及价值和行动的单位。所有这一切,能用作计算的基础,而且在每一个案中,我们依此首先通过确定一个测值或单位大小来决定各自的大小,进而决定穷尽总体大小的单位大小量值”,②而这显然会从极具模仿说命题异质性的前命题知识角度,深化我们对文艺学知识域亚理士多德模仿说命题的所指目标与语义重心移位。至于后者,则德里达的“延异”学说及其阐释过程中的丰富资料填充,择其一即可获得直接经验的清晰效果。例如古希腊命题定位的“逻各斯主义”或者说“逻各斯中心主义”,就知识异化为“在历史和存在之外,逻各斯什么都不是,因为它就是话语,就是无限的推论性而非实显的无限性;因为它就是意义。不过,意义的非实在性或者说意义的观念性曾经被现象学当作其自我的前提来发现……而这个逻各斯正是在其自身中投射并言说自身的大写的意义”。[3]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承认德里达“延异”说也能成为学理合法命题,并且承认其作为命题知识建构具有知识学史的广泛有效性,那么很显然,任何命题知识的顺向线性“敞开”,都会呈现为递进性和多元性所带来的延异后果,从而在后置语境不断产生具有源远流长的知识演化效果,或者说命题知识增长后果。
与此具有同步发生时值的是“弹性替代”,一种真值率变化情况极为复杂且具标志性变化的命题置换、迭加抑或新的创建。但问题是,无论真值率变化情况多么复杂,抑或命题置换、迭加和新的创建具有多大的革命性变化,哪怕处在黑格尔否定逻辑结构或波普尔知识批判路线的某个否定性知识点,其知识学发生关系,至少在知识谱系学语境,仍然将其视为“历时性秩序”变化的构成要素以及构成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不同知识域所有存量命题知识,或者对特定命题知识的亲缘关系集合、繁衍与延异状态,实际上都必须在时间线性维系上,给予历时性秩序审视、把握和统辖,并且这直接就是命题知识谱系的一种基本存在特质。
事实上,无论现代知识谱系学对知识形而上学的激进批判,还是东西方传统谱系观念在知识实践中的绵远坚持,“历时性秩序”作为基本存在特质始终体现得较为充分,而不充分甚至往往被漠视的是命题知识谱系的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基本存在特质,那就是“共时性秩序”。
如果说命题知识谱系的历时性秩序可以被描述为“谱系纵深”的话,那么共时性秩序则似乎可以象征叙事为“谱系横截”,也就是将其理解为任意时间线性位置,命题知识谱系的在场亲缘关系整体结构。在场横截的亲缘知识命题之间,存在另外一种知识存在维度的叠合事态,即关系结构的空间存在维度。譬如“在地全球化”知识语境中的“怀乡范式”(nostalgic paradigm)命题,及其本质上的“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是一种互相交叉的诊断……是制度化的社会论——在全球扩散的(而且有时是强制性强加的)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预期,包括认同独特性这种预期的制度化——的一个组成部分”,[4]与“地方性知识”语境中的“原始幻象”(primitive fantansy),及其内在诉求的“艺术家作为民族志……显著差异的自动编码本身就是一种清晰的身份,他性的自动编码是外部性。长期以来,这种编码使边缘性(marginality)文化政治成为可能”。③其命题知识叙事的语旨重心就在于空间存在取向,而给予命题知识间的关联性处置,同样也取决于这种空间存在取向的强制维系。毫无疑问,这种维系并不具有知识谱系学的秩序意义,尽管它们作为命题知识,共在于相同的自然时间场域以及此在空间界面。因此,知识谱系学意义上的“谱系横截”及其所凸显抑或隐存的“共时性秩序”,虽然具有横向空间特性,但其所维系及其对这种维系予以空间拓值和展现的命题知识结构,还在于特定时间节点的功能支撑及其这种支撑的横向空间覆盖。基于此,“谱系横截”对命题知识空间散布的有效捕获与学理统辖,关键在于只有此时的此在空间内那些具有知识亲缘关系和知识逻辑关系的命题知识,才能成为具有共时性秩序的知识谱系学命题知识对象,才能将这些空间散布的对象,在共时维度建构起特定功能诉求的知识谱系。
就知识亲缘关系而言,意味着给定时间的空间横截面上,不同时空定位的某些命题之间,具有源流生成和影响驱动的直接关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不以同质性抑或异质性存在程度决定其亲缘程度。一个很值得讨论但全球知识界却尚未给予足够学理聚焦的案例就是,刚刚过去的跨世纪前后二十年,全球知识界在不同的知识域或者价值维度,基于不同的地缘空间背景,洋洋洒洒先后出现的诸如东方主义文化命题、后殖民文化命题、文明冲突命题、文化帝国主义命题、文化安全命题、文化软实力命题乃至文化输出命题等等,④如果我们细探其究而非登高远眺,就会发现这些命题,不仅与各民族既往知识谱系没有亲缘传承关系,而且与人类学意义的文化理论知识生成要素没有逻辑功能链接。既然如此,由此形成的谱系横截作为命题知识谱系中极具标志意义的弹性现象,何以能在横截面的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现场效应很强且具在场横截特征的命题知识谱系呢?其直接亲缘关系的亲缘基因就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世界冷战格局及其所衍生出的“文化冷战”,作为知识基因裂变和新的畸变基因核与基因突等,产生出空间分布状的横截在场命题知识谱系,而且是“直接亲缘结构谱系”。无论是“文明冲突命题”拟置者,现场事态放大的“相比之下,断层线战争根据定义,是在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在断层线战争中,A1 集团与B1 集团作战,他们双方都试图扩大战争,并动员本文明的亲缘集团A2、A3、A4 和B2、B3、B4 给予支持,而那些集团将认同于他们正在作战的亲缘集团”,[5]还是“东方主义命题”想像的地域及其隐性价值诉求的“东方是用来圈定东方的舞台。这一舞台将出现这样的人物:其作用是表述他们所属的更大的整体”,[6]诸如此类,都是“文化冷战”的基因繁衍后果,皆莫不亲缘于诸如“1948年,《国家安全指南》(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授权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文化战略,以削弱苏联的‘和平攻势’,因此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很快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帝国较量中最重要的项目和机构之一”。[7]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量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以外的其它发达国家,在特定时域都深度卷入并且普遍焦虑于这一具有“共时性秩序”限制的命题知识谱系横截界面,并由此再生其不同立场特征与不同情绪面貌的诸多自议命题言说。
这些言说,其中就包括很多共时性秩序的特定命题知识谱系化叙事。譬如乌吉·吉布逊(Mark Gibson)的《文化与实力:文化研究史》,及其基于本然事态敏锐洞察到的诸如:“如果就‘极权主义’(totalism)的起源而言——一个一般性且到处蔓延渗透的实力概念——那可以追溯至新的社会运动和冷战,这一命题经常与该领域的‘美国化’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8]或者穆斯塔法·卡马尔帕什(Mustapha Kamal Pasha)基于衍生社会后果评估时,所意识到的所谓:“总之,为了减少伊斯兰社会进程对全球化的影响,无论形态还是内容,在伊斯兰文化圈内误读了其实例化”,[9]就都属于所议谱系横截内的命题知识言说,而且是以直接亲缘关系为维系的共时性场域言说行为。如果我们以类似的案例审视姿态,去展开人类知识史或不同知识域指向的遍扫视野,穷究特定知识命题及其命题知识谱系在共时性秩序中的语境状况,就不难发现,几乎在任何一个谱系横截位置,类似的直接亲缘关系命题知识谱系都会比比皆是,只不过当人们的知识言说处在“闲谈”位置时,通常会在无知性遮蔽或无惧性撒泼中视而不见罢了。
就知识逻辑关系而言,意味着给定时间的空间横截面上,不同时空定位的某些命题之间,在没有直接亲缘维系的知识生成条件下,非家族相似地以功能逻辑可换算结构,支撑起可以命题知识编序的间接逻辑关系在场谱系语域。如果以宏观知识命题作为此在的讨论案例,最具指涉意义的莫过于“轴心时代”作为“谱系横截”的描述案例,而且不难发现道德知识域“善”命题非互约性谱系结构生成。这种生成在空间分割并且缺乏亲缘关系生成机遇的条件下,同样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知识史遍扫视野立场,确立此在命题建构抑或知识言说行为合法化与有效性的必然前置条件。⑤正是基于这样的前置条件,我们由此可以在逻辑结构的功能支撑下给予谱系化关联关系建构,例如以并列结构编序出诸如季札善论辩证的“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10]孔丘善论主张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1]苏格拉底善论分析的“善者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原因,不是坏的事物的原因”,[12]世尊善论唱偈的“是故当殖德,愿念于后世,人所作功德,后世且待人”,[13]诸如此类,可以编序出一长串异质阐释取向但命题靶向趋同结构的共时性秩序谱系横截。
当然,我们同样能够按别的逻辑关系来进行类似的谱系知识建构,例如将如上所例命题空间范围,压缩至先秦中国的轴心场域一隅,就可以在李月冉、孔丘、墨翟和商鞅的非互约亲缘共同在场中,编序出基于对立因果关系或者说命题共识内在语义紧张的逻辑结构关系,而这样的逻辑结构关系所建构起的谱系横截,同样是共时性秩序命题知识谱系的一种特定存在形态。对略滞其后的荀卿而言,无论是其自身命题拟置的诸如“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直,合于善也”,[14](P327)或者场域遍扫视野知识评价的“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德,慎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4](P290)甚至不屑孔门一脉知识有效性苛求的“然而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14](P72)都是以立场分异中同质性与异质性彼此因果对立而生作为其“谱系横截”依据的,并且其支撑点更多着力于知识逻辑关系而非知识亲缘关系。
尽管运用谱系切分工具进行形态分析之际,我们可以而且也常常会基于单一维度给予操作,由此而清晰地描述出诸如“历时性知识轶序”与“共时性知识秩序”的命题知识形态分存状态,或者基于“知识亲缘关系”与“知识逻辑关系”不同谱系建构原则来予以事态描述,但在绝对多数知识现场,涉身者所经验的知识存在状态具有“去分存化”的混存特征,而这也就要求涉身主体保持对命题知识谱系分析性进入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基于谱系整体观的统辖姿态,否则就极有可能因执于一端,而在谱系识别以及进一步的命题知识操作过程中,出现“所指”意义滑移,或者知识工具功能错位而丧失阐证有效性或知识行为合法性。当韩非面对先在与此在知识场域之际,其命题知识嵌位语境,即使最粗线条描述,也复杂事态地显形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⑥从其显形方式不难看出,既融合了知识亲缘关系,亦融合了知识逻辑关系,也就是以谱系混存的审视姿态去处置现场事态的“谱系横截”。
与此类似,在二十世纪知识场域关于时间存在命题的横截谱系界面,我们既可以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界面,知识亲缘关系地寻找到影响线索与语义指涉,诸如乔治·伽莫夫、拉尔夫·阿尔夫·阿尔弗和罗伯特·赫尔曼的所谓“核合成理”,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所谓“热平衡微波辐射”理论,弗里德曼的所谓“临界密度模型理论”,乃至薛定谔的所谓“微观尺度时间演化理论”等等。诸如此类都是热力学和大爆炸理论知识基因可编序系列的时间起源命题方式,并且霍金式地求同归纳为“这就会导致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定义很好的热力学和宇宙学的时间箭头”,[15]或者史蒂文·温伯格更加技术化陈述方式地定位于“‘膨胀特征时间’大致为宇宙规模扩大1%所需时间长度的100 倍。更准确地说,任何时期的膨胀特征时间都是那个时期哈勃‘常数’的倒数”。[16]
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现代社会科学界面,基于逻辑结构关系地阅读到另外一些时间存在命题指涉,诸如海德格尔“时间现象学”知识维度的所谓“在这样一种当前化中到时的东西就是时间”,[17]或者乔治斯·古尔维奇“时间社会学”知识维度的所谓“社会时间是总体社会现象运动集中与发散的时间,不管这种总体社会现象是全球的、群体的还是微观社会的,以及它们是否被表达在社会结构之中。总体社会现象既产生社会时间又是社会时间的产物”,⑦抑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文化学”知识维度的所谓“今天时间是一种速度功能,显然只有按照它的速率或速度本身才能理解:仿佛旧的柏格森关于量度和生命的对应,即时钟时间和生命时间的对应,已经与虚假的永恒性或滞缓的持久性一起消失”。[18]尽管类似的二十世纪时间存在命题知识,十分复杂地散布于知识亲缘关系与知识逻辑关系不同显形特征的分存位置,但是却都以共同入场的知识姿态成为二十世纪所指命题场域建构的功能知识点,并进而在知识谱系学框架及其支撑原则作用下完形其“谱系横截”建构。对任何意欲涉身这一特定命题知识谱系横截面者而言,其阈值限度与谱系密度的占有状况,将直接制约其知识身份价值及知识工具使用的有效性程度。
总而言之,辨证地把握命题知识谱系生成,是确立谱系活性并进而确立这一知识范式客观存在价值的唯一正确选择。
注释:
①托马斯·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引自伊姆雷·拉卡托斯与艾兰·马斯格雷夫合著:《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P20。
②Stephen Gaukroger,The Genealogy of knowledge:Analytical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7,Aldershot,P.26.对此作比较性演化理解,有必要关联阅读亚理士多德的“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亚理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P.3)。与此同时,实际上还应该逆向思考柏拉图此前已经有所命题指涉挪移的本体论摹仿命题定位,因为这一命题挪位是此后亚理士多德文艺学知识域命题知识建构的支撑杠杆。
③霍尔福斯特:《艺术家作为民族志者?》,引自乔治·E·马尔库斯、弗雷德·R·迈尔斯编:《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359。
④这里的非穷尽性例举,并非按某种谱系标准进行的命题编序,往往有交叉与非均衡性,其有效的知识功能谱系建构,有待对此有兴趣并深谙知识背景者的专门运作。
⑤英国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一般性地意识到:“轴心时代的人们都发现,富于同情的伦理规范卓有成效。 这一时期创造出的所有伟大的思想传统一致认同博爱和仁慈的极端重要性”(凯伦·阿姆斯朗:《轴心时代》,孙艳燕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P5)
⑥《韩非子·显学》。郭沫若认为“韩非在先秦诸子中为最后起,他的思想中摄收有各家的成分,无论是作为亲人而坦怀地顺受,或作为敌人而无情地逆击”(《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P382),只是看到了现场的命题知识复杂性及其对涉身者影响的多元性,却不能从知识谱系学的工具有效运用中将现场事态清晰化,所以其所获得的先秦知识场域描述后果就只可能是粗线条状态,而这显然有待先秦知识谱系建构者的后继发力,否则就会一直混杂下去而不能清晰而有效地完整把握。
⑦乔治斯·古尔维奇:《社会时间的多样性》,引自约翰·哈萨德编:《时间社会学》,朱红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