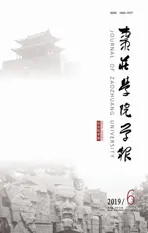从“三味书屋”的阐释史看“救救孩子”的命题
2019-01-29张梅
张梅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 271365)
“三味书屋”是鲁迅幼年读书的地方。鲁迅自1892年2月进“三味书屋”读书,一直到1898年5月离开绍兴,除了短暂的去舅舅家避祸,鲁迅的少年时期主要在“三味书屋”度过。1926年鲁迅把这段生活写成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文章自1956年起被编入中学课本,“三味书屋”随之名闻天下。“三味书屋”在被一代又一代人包括亲历者鲁迅,阅读、记忆和阐释中,被赋予太多的文化想象和社会记忆,其意义被不断叠加和重构。这固然源自于历史文化语境的改变,具体而言就是儿童教育观的变化。鲁迅对儿童教育困境有个经典表述:“救救孩子”。“五四”前后,鲁迅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进儿童教育。鲁迅显然认为“立人”从儿童实施最为有效。1911年鲁迅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就是私塾叙事。1912年鲁迅去教育部任职后,积极组织全国儿童艺术品展览会,发表《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拟播美术意见书》《<儿歌六首>注文》《维持小学之意见》(周作人拟稿,鲁迅修改)等文章,翻译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儿童之好奇心》《社会教育与趣味》和高岛平三郎《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儿童研究文章。而这时期也正是周作人儿童本位论思想的形成时期。兄弟之间频繁的思想交流也促使鲁迅儿童教育观逐渐成熟。1918年鲁迅在对文化礼教吃人性震惊发现的基础上,喊出了“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然而通过对“三味书屋”100多年阐释史的考察,我们悲哀地发现鲁迅“救救孩子”的世纪命题仍然横亘在眼前。那么这100年来,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命题?为解决这个命题做了哪些努力?又遭遇什么新困境?
一、晚清民国时期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这样描述他的私塾生活: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提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1](P289~291)
由此可见,鲁迅的“三味书屋”生活主要是“只读书”,但也有“只读书”枯燥生活中偷来的乐趣。正因如此,鲁迅的私塾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心理阴影。而且在鲁迅家道中落、频遭众人冷遇之时,寿镜吾先生也曾援手相助。鲁迅一生都很敬重寿镜吾先生,并与其一家都保持着密切往来。
但是在《怀旧》中,小主人公“吾”的私塾生活却如牢狱一般痛苦压抑。夏夜“吾”仍被塾师“秃先生”拘禁在书房里读书,不准玩乐、听故事,不准嬉戏、跳跃。以至于“吾”极其厌倦这种生活,希望自己或者先生生病,甚至盼望先生死掉。文中的“秃先生”被作者漫画成了丑角一样的人物,可笑可恶可憎。王富仁认为“秃先生”是个巧滑善变、投机钻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附庸文人。[2](P272)尽管《怀旧》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同样使用童年视角,同样是写私塾(《怀旧》中的家塾也属于私塾的一种),但由于塾师的差异让学童的主观感受截然不同。
为什么私塾生活在鲁迅的散文和小说中会如此不同?
很显然,鲁迅对私塾制度的抨击和对自己塾师的怀念是两码事。在《怀旧》中,鲁迅采用文化批判的启蒙立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则属于个人化的追忆。就像鲁迅一面为孝子,一面却激烈抨击封建家长制对儿童身心的摧残一样,都是基于不同文化身份的表现。
鲁迅《怀旧》影射辛亥革命,但写的最精彩的是私塾夜课。王富仁是这样评价《怀旧》的不足之处的:“我认为关于书塾夜课的描写多少有游离全文之感。就其本身而言,这段描写相当精彩,简直可称之为生花妙笔。但放在全文中,却觉与小说的中心内容扣得不紧”[3](P275)。《怀旧》开头的私塾夜课的确与后来的内容关系不大,但鲁迅却把它放在文首,而且写得相当精彩,以至于喧宾夺主。多年以后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提起这篇小说,说题目和笔名都忘了,单单记得“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3](P93)。可见,私塾是鲁迅审视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自隋唐科举制通行以来,读书就成为入仕的唯一渠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社会共识。文人中举前漫长的读书过程是必备的成本投入。为了求得利益的最大化,人们总是尽可能压缩这个读书过程。越多越快地背书就成为私塾教育中超越一切的宗旨。如何做到越多越快?那就是剥夺孩子一切玩乐、休息、甚至睡觉的时间。蒋梦麟曾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拜天”。“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了之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4](P21~22)如何处理孩子各种反抗情绪呢?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体罚!何其芳说体罚的“名目很多,最普通的是罚跪、打手心、打屁股、敲脑袋、揪耳朵。最普通的工具是先生的手和竹板子。……在旧日的家庭里,体罚就是一种教育。至于私塾先生,有许多是以严酷出名的,几乎越会打学生便越有人聘请”。[5](P176~177)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继续催化私塾教育的负面性。梁启超在《论幼学》对晚清私塾教育以科举为旨归的急功近利和混乱无序提出了尖锐批评。[6](P210~212)在强劲的废科举、兴新学的社会思潮推动下,私塾成为知识阶层声讨的对象。1906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使私塾作为科举制的基层组织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也抹去了私塾在传播文化方面的正面价值。这是一个新的价值重构的时期。
因而晚清民国文人倾向于建构一个个黑暗私塾故事。钱玄同幼年便因为偷看《桃花扇》被打,致使额头上留下永久的疤痕[7](P105~112)。而顾颉刚则在先生责打的威逼下成了口吃。[8](P8)陈独秀、郭沫若、沈从文、丰子恺、何其芳、赵元任等都提到私塾中种种触目惊心的体罚。据周作人回忆距离“三味书屋”不远的广思堂体罚就骇人听闻[9](P84)。而且小便还要“撒尿签”“三味书屋”撒尿是完全自由的。“三味书屋”开明人道的教学方式的确是个案。周作人猜测《怀旧》中的“秃先生”很有可能就是广思堂做馆的先生,或者把很多塾师集合而成的一个庸俗恶劣的典型。[9](P217~218)那么《怀旧》中的私塾和“三味书屋”真的没有本质区别吗?
周作人曾说:“有人讲鲁迅的故事,把这两件事团作一起,原因一般是由于不明白从前书房的区别,但是把人品迥不相同的两位先生当做一个人,未免对于三味书屋的老先生很是失敬了”。[9](P216)其实,把两种书房混为一谈恰恰不是周作人认为人们不懂家塾和私塾的区别,而是两者没有本质区别。两种书房看似有人性和非人性之别,但教学内容是一致的,都是紧紧围绕四书五经的读背展开。没有对儿童心理的关注,没有故事、没有娱乐,也不鼓励思考。寿先生的方正、质朴并没有改变“只读书”的教育模式。寿先生不过用相对人性化的方式使死背书的教育机制得以顺畅运行。因而两位塾师的教学模式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程度差别而已。
此外,两者的混同还源于黑暗私塾故事的社会记忆。这种社会记忆始于晚清五四以来文人的建构,私塾常被叙述成压制、摧残孩子身心的强权符号。寿先生的“三味书屋”只属于鲁迅的个体记忆。哈布瓦赫关于社会记忆的理论中有一个中心论点:“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就算是隐秘的个人回忆也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始终离不开社会性这个基础”。[10](P23)也就是说,社会对某种文化现象的记忆不是以个体化方式保存下来的,它不是个体记忆简单相加的总和,是通过个体记忆相互交织、作用,并通过某种复杂的生产机制才形成的。作为个体无法向社会记忆添加任何东西,也无法决定它的性质和走向,个体记忆只是集体记忆的一个回声而已。这就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往往忽略寿先生的方正、质朴,只记住了他和秃先生类似的刻板教学模式。
总之,寿先生虽然人品中正、学识渊博,但改变不了私塾教育机制本身的致命痼疾。因而在建国前,私塾常被表述成破坏童年幸福的黑手和阻碍民族发展的力量。[11](P68~75)“三味书屋”这样相对人道的私塾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就连亲历者鲁迅也在《怀旧》中把它艺术化为一个黑暗的象征。民国文人在这个时期只完成了对私塾负面性的指认。虽然周氏兄弟倡导“儿童本位”,并各自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上海的儿童》《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和《儿童的文学》《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等文章中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方案,但随之而来的革命和战争很快遮蔽了“救救孩子”的命题。因而“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仅仅实现了对私塾这种教育机构的颠覆,这只是外在的社会变革,没有从根本撼动旧有儿童教育观的“吃人”性。
二、十七年到文革时期
1950年教育部就明确指出,私塾在性质上属于封建教育的残留物,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相违背,因此,各地教育机关“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解决儿童就学问题的程度,来管制和改造当地的私塾,最后使它们不可能存在”。[12]私塾在新的意义框架下被定义成落后腐朽的典型。虽然私塾在清末民初已经备受批判,但基层教育机构的不完善使它仍有存在空间。建国后的“管制和改造”使之成为众人合力共歼之的对象,私塾很快在全国范围内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1956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编入中学教材,相关的学术研究、语文教学研究多起来。但“救救孩子”作为思想命题的丰富性复杂性却被大幅度简化。比如1956年的《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二册教学参考书》明确指出此文的主题为:“作者通过童年生活的回忆,批判了封建教育对儿童的束缚和损害,肯定儿童身心应得到正常发展”。这就为今后如何阐释此文定下基调。同年的学术研究文章也指出“‘朝花夕拾’首先从多方面揭露了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扼杀与摧残,并描绘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形象。”“在封建主义者看来,一个儿童应当被教养成读死书、做对课的工具。三味书屋中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的种种活动显示了封建教育跟人的天性的对立性。”[13](P64~74)建国后阶级论的文艺观使塾师和学童二元对立更趋极端化。
随后的文革时期,有关的评论文章更彰显其斗争的锋芒。比如《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4年第3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分析》(《鲁迅研究》1974年创刊号)、《一篇批判封建教育的战斗散文——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新教育》1975年第8期)、《冲破封建教育牢笼的时代强音——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武汉文艺》1976年第4期)、《试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两个问题》(《语文战线》1976年第4期)等等文章充分演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特色。其中以李何林1974年发表的评论文章对后来影响最大,他说:
本篇的中心思想是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用乐园似的百草园生活来和阴森、冷酷、枯燥、陈腐的三味书屋相对比,一个是多么适合儿童心理,表现了儿童的广阔的生活乐趣;一个是多么妨碍儿童身心的发展。……通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生动的对比,通过对这位老先生一面教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一面自己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地欣赏无聊文章的描写……说明了他是一个体现孔孟之道的、不学无术的典型腐儒。[14](P489~490)
此文具有典型的文革文风和逻辑。由于李何林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地位,“这一观点成为一段时期内众多研究者公认的观点。所以在全国通用语文教材第一册中的这一课的课后题也是围绕这一主题而设置的”。[15](P479)其实,李何林的观点能长期影响着人们对“三味书屋”的看法,不是他的观点多么雄辩深刻,而是他的观点恰好是当时斗争逻辑的经典表述。鲁迅饱含深情的童年回忆被解读成一篇对封建教育无情抨击的战斗檄文,鲁迅一跃成为批判“先生”的文化斗士。“三味书屋”也成了对小鲁迅美好童年的一种戕害。
这种对“三味书屋”的阐释属于“贴标签”似的批评,对私塾教育的个案“三味书屋”没有分析、没有辨别、没有内在的思想建设,仍然纠缠于外在的、有形的枷锁。而且在文革盛行的斗争逻辑下,作为“革命小将”的儿童并没有实现人格独立,而是进一步被抽象化为革命的符号,沦为政治化斗争的工具。过去的私塾教育把儿童规训成恭顺懦弱的羔羊,那么文革教育则把儿童训练成张牙舞爪的鹰犬。“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不但没有深化,反而被重重遮蔽。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三味书屋”的阐释首先进行的是拨乱反正。陈根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二题》(《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第11期)、张硕城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思想不再批判房间教育制度》(《语文月刊》1983年第5期)等文章都对李何林的观点提出质疑。
关于“三味书屋”的主题探讨一直持续到21世纪。李怡在2009年撰文说过去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视为抨击‘封建教育压抑摧残儿童’的控诉书……其实,这大概是没有读出鲁迅在文中那无所不在的情趣来”。“一个有腊梅可折,有蝉蜕可寻的所在”,先生“读书的痴迷也是这样的可爱”。因而李怡认为“鲁迅的陶然是明显的”[16](P103~108)。王富仁在批判过去观点的同时,对教育和教师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教育是由教师对学生实施的,但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却不取决于教师和学生。“而是取决于一个时代 、一个社会对教育和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运用”。[17](P30~50)王富仁直接拨开表象,抽离出本质:三味书屋代表的私塾确实压制人性,但这不能由先生负责,这是科举文化中实用理性决定的。
当文革的喧嚣早已逝去,对文革的声讨也不再热闹。当我们的国家在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慢慢崛起,当下中国进入到一个“深刻的身份焦虑”期。因为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我们试图挣脱西方的价值参照体系,但是“何谓中国”呢?化解这种身份焦虑的一种方式是“寻根”,在对历史的回望中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然后勾勒未来。
在民间,努力摆脱西方框架的焦虑具体化为对国学的追捧。旧时私塾里儿童读的《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百家姓》《论语》等书籍是常销书,也一直是书店的热销书。当然未必有多少儿童真正爱读。很多家长自己不读书,但也要买几本《三字经》《论语》,或者唐诗宋词之类的书给孩子看。在社会上“读经热”此起彼伏,似乎现代社会的传统衰落、道德失衡都是不读经书的缘故。另外,人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也让一些教育人士或家长开始尝试体制外教学,而私塾便是体制外教学经常采用的教学模式。
在学界,许多论者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持“成长说”:“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都是鲁迅成长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存在用一个打倒另一个的价值取向。杨义就强调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重大的精神转型,并指出“只有百草园、没有三味书屋的鲁迅,是难以想象的,百草园根本无法铸造成思想和文学巨匠的鲁迅”。[18](P1~17)宋剑华在2014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差不多都有过同鲁迅一样的‘塾学’训练,因此他们才会博古通今令我们这些后人望尘莫及”。[19](P22~32)宋剑华和杨义都肯定“三味书屋”的正面价值,指出私塾塑造了像鲁迅这样的一代文学巨匠,并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南怀瑾的观点更激进,他直接走上了弘扬私塾文化的道路。他说:“如所周知,在这个时代几十年来很多对国家社会有建树的人物,无论在党政、军事或文化教育、工商各界出人头地的,他的学识基础的深度,都是由于旧制小学和依照旧式读书的教育成果”。[20](P112)正因为南怀瑾怀着文化传承面临断层的深深忧患,他成为“儿童读经”的积极倡导人。他说儿童读经可以“一劳永逸,由儿童时代背诵的‘经’‘史’和中国文化等基本的典籍以后,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年摇头摆尾装进去,经过咀嚼融化以后,现在只要带上一支粉笔,就可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要,并不太过外行,更不会有‘空白’之感,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年的父母师长,保守地硬性要我们如此读书”[20](P120)。
这番对私塾的肯定很可能让建构出黑暗私塾故事的民国文人们始料未及的。小鲁迅当年在“三味书屋”只读书的枯燥被置换成“文学巨匠”的辉煌。儿童完全不解其意地“死背书,背死书”也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但是,当我们肯定私塾教育和读经对传承国学的重要性时,儿童又一次被抽象化为一种隐喻符号,负载着成人关于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的想象。鲁迅“救救孩子”的命题以某种荒诞的方式再次返回原点。
钱理群曾在2008年说鲁迅的“三味书屋”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性,不能不有惊心动魄之感”。钱理群认为这个“惊心动魄”来源于今天的学校教育,还没有走出“三味书屋”的“只要读书”的教育模式,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以至今天校园里连“三味书屋”里那位“读书入神”的先生的身影,也已经很少见到了[21](P57~62)。
钱理群揭示的儿童教育的困境真是“惊心动魄”。我们曾经以为现在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尽情享受过去的儿童在梦里也想象不到的极其丰富的物质生活,沐浴着祖父辈的万千宠爱,徜徉在各种玩具和新媒介创造的奇幻世界里。但是儿童并没实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因为虽有花样玩法但他们没有时间,他们的生活被各种作业、考试、比赛、辅导班、兴趣班所占满。正如周作人所说:孩子“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那些高喊“救救孩子”的人不过“看见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嚷着要把‘它’救了出来,照自己的意思来炸了吃”。100年来人们在努力践行鲁迅“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原来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吃孩子”?!这种痛彻发现真是细思极恐。因而周作人质疑拯救者本身的合理性,他说:“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说救救孩子”。[22](P729)这其实让“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陷入到荒诞的悖论中。吃过人的成人如何有资格拯救没吃过人的孩子?
这种悖论并非当下独有,但却在当前表现最突出最尖锐。成人只有遵循“狂人”的大声疾呼“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23](P453),这样才能救出自己,救出孩子。不然,我们的孩子连“三味书屋”里的小朋友的童年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