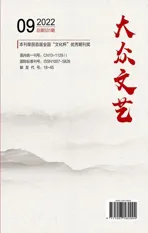莫言小说中巫术叙事的三种解读
2019-01-28江南大学人文学院214122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14122)
根据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观点,巫术是原始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起点,它蕴藏着原初民的一切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的密码,所有的民间文化都可溯源至巫术。莫言的小说充满社情民俗、宗教图腾、野史戏演等的元素,这些叙事元素通常展现一种浓郁的巫术色彩,成为其中无法忽略的一类叙事内容。因此,本文聚焦莫言小说中的巫术叙事,从莫言对原始思维的溯源、悲剧意识、救赎情怀三方面展开论述,力图把握其小说的深层内涵。
一、民间立场上原始思维的溯源
巫术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是还未完全开化,俗尚鬼神的旧高密乡父老乡亲们最主要的精神寄托。莫言小说中的巫术叙事是昔时邻里乡亲生活状态的恰切描述,对于民间百姓或迷信、或无知、或恐惧等的心绪的再现,也是丰赡民间文化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对于闪烁着原始思维之光的民间巫术活动的一种源溯和敬畏之情的表达。
莫言小说中关于民间巫术的描写比比皆是,如《檀香刑》中眉娘对县令钱丁一见钟情后,突发相思病,久病不愈,便寻神婆吕大娘(民间巫师)。吕大娘先让她用白绸包住两条正在交配的蛇,用蛇交配后留在白绸上的血去引诱钱丁,后来又说喝了心上人的粪便可去心火,治相思。再如:《生死疲劳》中,许宝作为前朝太监,没了男根,本着吃什么补什么的传统说法,到处寻找雄性动物的生殖器给自己当下酒菜。黄合作知道蓝解放出轨庞春苗后,便咬破手指,在树干上写血书:“离开他!”以此来威胁和宣战第三者。谨遵“相似律”和“触染律”的巫术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它同民间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属于完全野生的、民间的非物质文化。写巫术活动是莫言文学立场始终在民间的最好印证。正是巫术叙事才让莫言的民间故事显得真实与丰满。小说中淳朴的高密父老,往往在遇到人生不如意时,就会采取巫术的手段来克服劫难。民间百姓热衷于巫术,源于他们相信心灵感应。在科学的光芒还未普洒的乡野山间,百姓选择相信实际毫无关系的两种事物,可以在冥冥之中确立一种不可言说的联系。所以,眉娘和吕大娘认为动物间的交配和人类的男欢女爱有着关联,来自意中人肉体的分泌物可以成为一解相思的良药;许宝选择相信人类生殖器和动物生殖器是同一种事物,顺势模拟的做法可以让自己重获新生;合作写血书则是采用了最原始的诅咒方法,血与灵的相连,让春苗成为被诅咒的对象,她希望春苗可以受到来自巫术对其灵魂的不断震慑与鞭挞。巫术精神和朴素的顺势模拟思维可以说是未接受启蒙的民间百姓的一切内在精神的基础和核心,所以莫言将巫文化纳入其小说创作的重点之一,将其视作民间文化的“根”。巫术活动所暗含的原始思维的野性与张力,同莫言始终追求的生命力的野性与勃发具有一致性。
二、返魅背后的悲剧意识
即使新时期后,学界重新发现巫术的价值并赋之以极高的历史文化地位,也不能否认的是巫术“伪科学”的本质。莫言有意识地引入各种各样的巫文化素材,使其小说时常笼罩在一片巫术文化的神秘氛围里,其小说的返魅色彩可见一斑。然而莫言作为一个有着极高文学艺术造诣的“当代文豪”,对于巫文化也绝不仅仅满足于纸间的再现和深沉的回望。巫术叙事的背后,还蕴藏有一种浓烈的悲剧感。
《檀香刑》中孙丙和他的两员“虎将”分别扮成岳飞、孙悟空和猪悟能,企图利用“模仿”来摄取“偶像”的灵魂,进而达到“神灵附体”的效果。可巫术骗得了愚昧的乡邻,也无法改变他们依旧是乌合之众的事实。孙丙带领百姓作战前大摆祭坛、念咒语、设禁忌,俨然一副巫术作法的派头。按照民间信仰“禁忌的规定是为了预防死亡”,可纵使有法术的庇佑,德国军队的子弹也照样让百姓们伤亡惨重。这场民间与外来侵略者的战役是近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博弈,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之间的矛盾性。莫言对于该战役从头至尾的叙述,由神秘返魅的巫术开始,到惨烈祛魅的现代战争结束。叙述伊始还令读者对孙丙等一众乡亲拜天祭地的行为而感到可笑,等到结尾就只能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惨剧而哑然失声。正如法国哲学家韦博的文森所说:“悲剧是把欢乐的开端引向悲伤的结局。”莫言内心的悲剧意识,让他给了这场巫术的闹剧一个悲剧的结局。莫言对于民间巫文化所怀有的悲剧意识绝不仅限于对民族劣根性的批驳以及人种改良的妄言,希望借巫术叙事发现人性的幽微和唤起大众的怜悯才是他的真正用意。小说《檀香刑》中,莫言给予了刽子手赵甲以较多的笔墨来突出他职业的特殊性和神秘性。小说多次写到赵甲行刑前具有仪式感的巫术祭拜活动,如杀鸡不见血,鸡血涂脸以及邢前戒腥荤等。杀人如麻、冷血残酷是赵甲性格的一个侧面,是由刽子手的职业枷锁赋予他的,除此之外,赵甲作为人也有着人性方面的内容。比如,邢前祭拜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传统,更是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告慰。赵甲对于祭拜仪式的重视和小甲的轻视形成对比。赵甲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有所忌惮,所以才会慎重行事,而小甲作为一个失去理智的“非人”,他无法体会行刑时和行刑后的快感与痛感对行刑者本人身心的反噬,才会有恃无恐。对于深信迷信的封建人来说,刽子手有着极大的职业风险,他们是冤魂的债主。赵甲作为一个正常人,因为职业和历史的原因,把自己变成了非人,本身就是一出悲剧,而莫言对其的巫术描写,加强了他的悲剧感。在悲剧效果的考察范围内,用巫术叙事来寄托作家内心的悲剧意识符合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悲剧最高的表现形式,即在强烈的恐惧过后体现一种更为久远的悲悯感。或许这也是莫言所要追求的悲剧意识的最准确表达。
三、人文精神观照下的救赎情怀
《金枝》所述,巫术之所以被发现、创造并且信仰,源于原始人对于把握一切未知的自然的渴望。巫术祈雨、求丰产、求胜利等,即使最终成功应验,也仅是一种偶合现象。巫术的起源与传承,寄喻了整个民族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于苦难人生的救赎。本雅明曾谈到:“世界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一部救赎史。”莫言极强的文学使命意识和清晰的历史责任感造就了他大部分小说同中国历史之间的互文本性。莫言小说的历史倾向必然导致了他对于救赎道路的抉择,而巫术叙事则成为了他救赎主题的一大载体。
《生死疲劳》中黄互助神发救人和《蛙》中姑姑退休捏泥娃娃是莫言救赎情怀表现较为明显的两段巫术叙事。小说中,黄互助的头发犹如一种神物,不能剪,否则血流不止。“凡是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都有几分不寻常”。这样的情节安排虽然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但若以巫术的原理和思维来验证就合情合理了。原始人一般认为头发里寄住着人的灵魂,以头发救人,是按照触染原则,将这个人的蓬勃的生气通过头发注入另一个奄奄一息的生命的过程,从而使得两个生命体都得到永生。黄互助的神发先后出现在“神发救治小三活命”、“蓝解放切指试发”及“世纪婴儿”三章,一次次的大显神威,乃至大头儿蓝千岁的血友病竟靠此长发续命,“发在儿活,发亡儿死。”至此蓝千岁的生命将永远和黄互助的头发纠缠在一起。互助的神发对蓝千岁形成救赎,让小说最后散发出人性的温暖和救赎的情怀。《蛙》中的姑姑,出于对前半生所犯罪孽的忏悔,在退休后便开始捏泥娃娃,她捏的每一个泥娃娃都是在为曾经经由她迫害至死的无辜生命叫魂。人文关怀是身为知识分子的莫言所固有的,这种固有的精神同巫术原本的精神暗合形成了小说中强烈的救赎情怀。
莫言曾表示:“我必须承认少时听过的鬼怪故事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它影响了我感受世界的方式。”莫言作为一个胸怀格局的“大家”,面对中国传统巫文化的题材,总是可以做出恰如其分的安排与选择,让其小说既免于平淡,但也并非充满猎奇,既不锋芒毕露,也不欲盖弥彰,既不肆意歪曲,也不刻意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