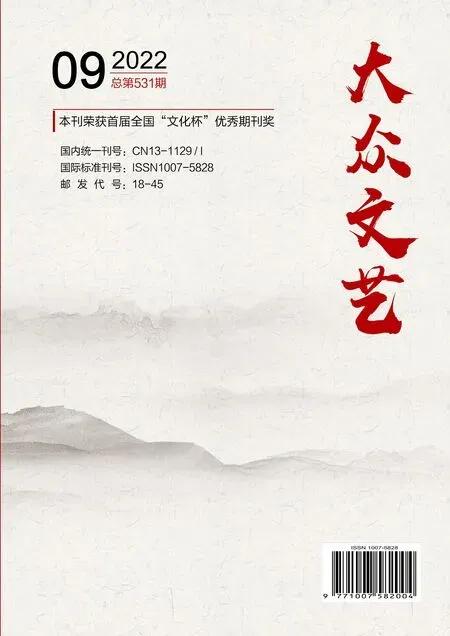荒诞书写下的真实原欲
——浅析阎连科《日光流年》
2019-01-28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430000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430000)
阎连科是现代文坛中的一位重量级的小说家,他的军营和平系列小说,瑶沟系列小说,耙耧系列小说都在当代文学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小说主题内涵是多元的,乡土、死亡、平民、怀旧、苦难、荒诞等等。同时他又有自己的小说理论著作:《发现小说》,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荒诞叙事下的真实被他自己总结为“神实主义”1的写法,涉及到这种写法的小说有许多,譬如《炸裂志》、获“卡夫卡文学奖”小说《受活》、《日光流年》、《丁庄梦》、《四书》等等。笔者选择了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日光流年》,试图探讨它在荒诞的外壳下隐藏着怎样的“内真实”2。《日光流年》选取了耙耧山脉中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作为书写对象,与阎连科其他耙耧山脉的小说设定相同。作品同样延续了人的“残疾”主题,展现了患喉堵症的几代农民的生活。而正是因为与世隔绝,很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染的三姓村保持了“人”的原始性,其中无伪装,原始的欲望才得以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结合小说具体的文本,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真实原欲显露的方式,内容以及意义。
一、荒诞:小说的外壳
首先是小说荒诞的主题和背景。小说分为四个篇章,更替了四代村长,前后跨越了一百多年,围绕的始终只有一个中心:活着。不同于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中表现的精神层面上的“活”,《日光流年》中的“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寿的延长。第一章《注释天意》以年轻的司马蓝兄弟丈量坟地开篇,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三姓村人“活不过四十岁”的死亡噩梦,这样“为死而活”的压力彻底改变了三姓村人,使得他们从生存观念到实际行动,都截然不同于常人。只有四十年甚至不到四十年的短命人生,让三姓村人始终苦苦挣扎。但种下这样的“果”的“因”在哪呢?《日光流年》对此有两处注释,一处说明从外迁徙而来的三姓村人初始是家畜兴旺,几代之后开始缩短寿命,直到今天的三十来岁;另一处则解释曾有考察队来勘察此地的水土,发现是因为生态环境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导致了如此特殊的现象。这两处注释将三姓村的悲惨故事铺垫得真实并且顺理成章,但实际上这些注释也是作者阎连科自己编造出来的,企图制造一种以假乱真的文本设定,没有任何现实依据。小说中多次提到三姓村是县政府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村庄”,与他的许多小说中涉及到的村庄相同,实际上这种说法正恰恰说明了这个村庄是世界上“找不到的一个村庄”。这就让围绕着“活不过四十岁”的挣扎为主题的《日光流年》从根本上成为一个荒诞的,虚拟的故事。
其次,小说的情节中也处处充满荒诞。村中人为了筹钱,男人卖皮,女人卖肉。三姓村附近的城里有一个教火院,收留因烧伤来植皮的病人。村里的男人们从几代之前就来这里卖皮赚钱,以几寸几钱来恒定价格。实际上医院的确有植皮手术,但实际在病理上病人只能在患处植入自己身上其他部位的皮肤。村人包括村长司马蓝从十几岁就来卖过皮,痊愈了就再卖,其复原能力夸张到超乎现实。女人卖肉本也是一件普通的事,但故事中讲到每家每户都要为修水渠出钱出力,走到一些寡妇家里,无钱无力,登记的是“寡妇婶 卖淫二十天”3,显得荒谬又有些可笑。
再次是一些不合常理的细节。比如杜岩得了喉病预感死期不远,自己躺进了棺材里,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撬开棺材发现他还活着,经过村人的悉心照料在棺材中又活了一年多;村人去坟上祭拜,死去的人还能坐在坟头上与亲人说话拥抱,替他们擦去泪水;司马笑笑当村长时,村里遭遇蝗虫灾害,村人靠乌鸦肉才活下去,乌鸦肉又是由死去的人的尸体吸引而来;杜菊吊死在司马笑笑坟前,身子都变硬了,却还是自己活了过来;司马蓝干瘦的媳妇杜竹翠生孩子就像倒豆子一样简单……此类小细节贯穿了整个小说,与情节、背景、主题共同构造了小说外在故事的荒诞性。
二、真实:小说对原欲的凸显
作者阎连科在他的《发现小说》中说:“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4用“神实主义”来概括他某些小说的写法。《日光流年》正是其中的一部。所以那些荒谬的外在情节内里有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关乎到人的精神与灵魂。在三姓村人几代人的奋斗史中,显露出触目的,强烈的原始欲望。
一为生存。这一欲望的展现是非常明显的。三姓村人的寿命仅仅是普通人的三分之一,人生的所有历程在他们的生命中都被压缩:十几岁出头已经可以说是青年,二十几岁已经是壮年,三十几岁就算得上村中的“老人”了。如此扭曲的认知来自于近在咫尺的死亡经验太过频繁地发生,司马蓝常常“弄不明白村人,为啥儿活着活着就死了。”5而“和那死了的人年龄相仿的大人们,埋了死者,坐在山坡上的日光里,望着面前的一堆黄土,谁都不言不语。”6。这些可怕的经验让多活几十年成为他们心灵深处最大的追求。因此三姓村四代村长毕生的使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的方法去延长村人的寿命:生育、种油菜花、换土、引水。这些手段有的十分荒唐,期间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甚至还没有预期地付出了残疾,死亡的代价,但村人一想到这样做可以活过四十岁,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小说对灵隐渠终于通水时人们的反应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有杜姓的人家”7,“便从自家后院墙上跳出来,把那土坯院墙跳塌了”8,“有一个人女人为了立马看到流来的水,把裤子穿反了。”9,“男人们只管放着鞭炮,只管吹着响器,只管莫名地把拳头挥在半空中,莫名地一句接着一句骂:‘我日他祖宗——水来啦!’”10。等到发现水根本不能喝时,只剩下久久的“木呆一片”11,杜流与司马虎相继自尽。生存下去的渴求支撑村人四代之久,也许在司马蓝死后,下一代人依然会飞蛾扑火般去继续寻求长寿之路,这是一个美丽又可怕的循环,只要生欲不灭,就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二为权力。对权力的渴望远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就存在,并非是文明社会的专有物,短寿也同样不能减灭三姓村人对权力的争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种欲望更加强烈。三姓村中有着两种权力系统,分别来自内部和外部,在小说中的代表就是村长以及在乡公所做事的杜岩杜柏父子。权力的根本来源就是村人的观念。村长是传统的自有的,而乡政府带来的权力是新兴的,村人的盲目尊崇促成了这种新的力量的形成,但实际上还是来自本土的内部权力占上风。在三姓村,当了村长几乎就可以“为所欲为”,小说中司马蓝是渴望权力的典型,当村长的愿望几乎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深深扎根在心里,杜柏则将妹妹嫁给司马蓝来分有这种权力。村长们通过延年益寿的承诺来稳固自己的权力,同时承诺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因此他们常常盲目地牺牲村人的其他利益来保证长寿的举措顺利实行,但为了活的坚持却总是制造更多的死亡。比如村长司马笑笑为了在蝗灾中保住油菜花田让蝗虫们啃咬玉米田,结果接着来临的饥荒饿死了村中的许多人;在挖掘灵隐渠的时候炸药炸死了很多年轻男人,也造成了许多人的伤残;为了让外来劳动力留在三姓村换土,将黄花闺女,稍有姿色的少妇送给卢主任;为了多生孩子,村长找男人们谈话让他们晚上回去和妻子行房。作者在讲述那些死亡的时候,有意强调了“不是由于喉病”而死,更是令村长用强权换来的坚持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小说中司马蓝最后选择了回到蓝四十的床上和她一起死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权力欲望的消解,同时也带来了反思。
三是性欲。阎连科对性欲有一种特殊的描写——在传统的感觉,视觉的角度之外,还加入了嗅觉、听觉的描写,发生过性的房间往往有一股“奶腥气”12。小说第五卷写到村里孩子们断奶的情节,正在断奶期的他们对与奶水有关的一切有一种非凡的敏感性,能闻到“半腥半甜的羊水味”13,多余的奶水是“浅红的气息”14,实际上是通感描写的“血的腥气息”,与性的气息相关。第五卷还写到在杜桑时代,男人们努力回去与妻子生孩子的当晚,司马蓝领着成群的孩子村中一家一家地“听墙角”,听了无数对夫妇性爱时发出的各种细碎的响声。天真无邪的孩童与性的关联凸显了性欲的本能性,原始性。这是一个充满着奇异想象的情节,通过这种方式来描写性,正是阎连科的独特之处。对性欲满足的强调还在于三姓村人普遍提早的结婚年龄,男人们往往十几岁就可以开始和媳妇“合铺”15,父母也会很早就为孩子张罗婚事,以弥补未来缩短的几十年。村长们凭借自己的身份,在正妻之外,还会和村中其他女子发生关系,司马蓝在儿时也多次想象他将蓝四十和杜竹翠同时娶回家,成亲后仍然和蓝四十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本是为了借茅草包裹母亲的尸体,却和邻村的寡妇做爱。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司马蓝的妻子杜竹翠,为了满足性欲甚至可以答应让丈夫和蓝四十同居。在性方面,他们很少尝试去约束自己,在做爱时他们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原动力,似乎对死亡的恐惧或多或少能通过性欲的餍足得到缓解。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人们通过种种手段来追求这些原始欲望的实现,而其中的思路同样是原始的,生理的。杜桑为了增加人口便让村里的女人拼了命地生孩子;司马笑笑企图通过吃油菜来清洗村人的肠胃;而蓝百岁则更大费周章地换土,想要种出健康的食物;甚至赚取钱财的方法也不例外,在小说中虽有提到村人出外做一些小生意赚钱,但只能获得非常低微的利润,最后似乎都不了了之。村中主要的经济收入还是来自于男人卖皮,女人卖淫,二者实际上都是出卖肉体,赚来的钱或用来娶妻,或用来修渠延寿。司马蓝为了自己多活几岁,也为了继续当村长,竟然带着女儿一起去求蓝四十到九都做人肉生意,而在蓝四十自己感到羞耻时,村人却当她是救世主,对她投以尊敬的目光;村里的许多男人不仅自己一再卖皮,卖到大腿上的皮肤粗糙得像树皮一样,还将自己几岁的孩子带进割皮的手术室,好让他们今后有勇气来卖。这大概是因为“作为本能欲望的显现或交换工具,身体是“劳苦人”生存的唯一依据”16吧,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三姓村人用身体奏出了一曲又一曲哀歌。
三、困境:求而不得带来的苦难
“内真实是人的灵魂与意识的真实。外真实是人的行为与事物的真实。”17《日光流年》看似写的是一个小小村庄的荒诞故事,但正是因为它不注重人的行为与事物是否真实,它能够突破现实主义的局限,跨越地域和种族,讲述一个有关全人类的心灵困境。
在四代人之后,三姓村能否摆脱死亡噩梦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日光流年》成了一个在苦难中无法得到救赎的故事,充斥着深深的压抑。即使小说采取一种“索源体”18的结构方法,最后以司马蓝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来结束,似乎回到生的起点是一个不算太坏的结局,但村人们的痛苦并不能因此消解。比短命更难摆脱的是人们心头的重压,一种积压了多年之后愈发强烈的恐惧。正是这些恐惧刺激了人们不断地努力,每一代人流过血之后,下一代人就换一种方式重新来过,在每一代村长和村民的血泪中,生育、种油菜花、换土、引水这几种政策都在不断地克服困难中实现了,然而在这之后人们仍然在三十几岁,甚至更早患上了喉病。每一次失败都将生的希望减少一点,在将一条臭水引到村里之后,村人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如同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许多小说一样,荒谬的情节恰恰反映了人类心灵深处不可言说的东西。卡夫卡小说中人变成甲虫,k永远进不了那个城堡;约瑟夫·海勒小说中不知从何处来的第二十一条军规;塞缪尔·贝克特描写的有一群等待戈多的人……它们用一些超现实的情节表现现代人的迷惑,痛苦和无可奈何。人人心中都充满了欲望,无论是生存的,性的,权力的,亦或是现代社会中财富的,事业的,名誉的,但真正能让欲望最终得到满足的人少之又少,得到的人也不代表永恒的满足,那么如同三姓村人心头的恐惧与挣扎一样,他们的心中同样有着求而不得的困境,有着那么一些经过了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依然抓不住的东西。但这一困境究竟要如何摆脱,作者却没有给出解决方案,这也正是《日光流年》让无数读者阅读之后沉浸在三姓村人的苦难与悲惨中久久无法释怀的原因,小说中的哭泣和绝望与读者心中某些东西遥相呼应,产生了持久的共鸣。在这一点上《日光流年》具有跨越时代和种族的恒久价值。
四、结语
《日光流年》所暴露出的正是人们都具有却羞于直接承认的欲望,小村庄的无根可溯也让读者不易对号入座,更容易去接受其中的赤裸和直白,从而进一步去认识自我,表达作为“人”所本有的原始欲望,同时能够开始思考欲望实现的困境问题,在思考中或许能给出自己的答案,完成对作品内涵的延伸和再创造。
注释:
1.阎连科.《发现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2.阎连科.《发现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
3.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4.阎连科.《发现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5.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398页.
6.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398页.
7.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233页.
8.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9.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10.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11.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12.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406页.
13.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459页.
14.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459页.
15.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16.林玮.《论阎连科小说的身体叙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第165页.
17.阎连科.《发现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
18.李小玲.《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11》[J].《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