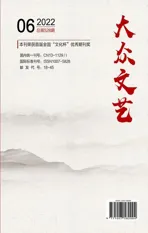论纪录片《我的诗篇》的诗意再现
2019-01-27浙江师范大学321000
(浙江师范大学 321000)
一、画面再现
在《我的诗篇》中,诗歌文本与影像文本相互作用,影像画面再现诗歌内容。例如诗歌《吊带裙》:“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聚集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亲赴一种安静的爱情/ 然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褶皱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从诗学意义上,这是一首现实主义诗歌,诗人通过细腻的内心,由手中认真对待的物品联想它可能发生的境况,连衣裙代指“姑娘”,渴望享用爱,也代指诗人本身,则更有给予爱的双层意蕴;“等待风吹”的美好与“唯一的你”的珍视,组成诗人生命与爱情的价值意象,与读者达成移情。
在镜头下,诗歌语言转化为视听语言,画面再现是纪录片诗歌再现的第一步,也是最直观的一步。在《吊带裙》诗歌作为画外音出现之前,镜头是一轮明月,交代时间,联系前后影片,这个镜头奠定了空间基调。当镜头转至邬霞,我们可知,在车间的夜晚,邬霞仍在加班工作,而月光静谧又温柔。邬霞在车间做着熨衣的本职工作,镜头跟随着她温柔的动作,从“肩带”熨到“腰身”熨到“裙裾”,镜头 没有任何技巧修饰,却因其质朴而显出生命的活力与本真的灵动。镜头切到大场景,是封闭杂乱的车间,诗的甜蜜与现实的贫瘠对比出主人公灵魂的自由,以及无法忽视的现实困境。
画面再现的手法平实质朴,镜头跟随诗歌的字眼,实拍诗人生存环境,展现诗人的创作背景。介绍性陈述的旁白说到:“邬霞的父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又不愿再拖累家人,不久前曾有过两次轻生之举。”面对父亲,邬霞于是创作了《家》,写到:“爸,生活有多艰难,就有多珍贵/我们的小屋就是暴风雨中宁静的鸟巢“;面对自己,邬霞创作了《爬山虎》“我一定会昂起我的脑袋,向着阳光生长,/像工厂灰墙上地爬山虎。“同时,她的心声与创作动力,在纪录片中以采访自白交代,“我觉得我要像那个石缝里面的草啊花啊什么的,就算是有一块石头压着我,我也一定要倔强地推开那块石头。要昂起我的脑袋,向着阳光生长”;“我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我觉得诗歌最能抵达人的灵魂。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诗歌,能感受到美好。”
二、情节再现
《我的诗篇》以纪录2015年年初的工人诗歌朗诵会为叙事主线,每朗诵一篇,镜头则引以诗歌声诗歌、作诗人及其群体。据采访,秦晓宇导演在编排《跪着的讨薪者》这篇诗时,朝阳门附近地下通道有100多名农民工讨薪不成夜宿于此,他们的神情就如诗中所写“我们失意的得意的疲惫的幸福的/散乱的无助的孤独的……表情/我们来自村屯坳组我们聪明的/笨拙的我们胆怯的懦弱的……”一个名词一张面孔,词与脸剪辑步调一直,节奏沉缓、平和、有力,更显人数众多与民众愤懑张力。导演请工人们读诗,工人们齐齐跪在地上,用各地的方言大声念出“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与诗句“我们跪在地下通道举着一块硬纸牌/上面笨拙地写着’给我们血汗钱’/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如出一辙。导演在这一段落中记录工人们集体发声的历史一刻,用诗歌朗诵穿插期间,以情景安排再现诗歌,讨薪工人们与讨薪诗的契合令人震撼;诗之精神真实与纪录片之形式真实巧妙结合,得以使文本呈现精神,而影像给予精神实体。
三、写意再现
《我的诗篇》在以影像阐释诗歌时,其空镜头表达缺少前奏铺垫,诗句意象剪辑刻意,缺少潜在逻辑与意韵的连贯,从而在写意层面缺少与诗本体的意境共鸣。例如,爆破工陈年喜《炸裂志》“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打发”与“借此”用力轻巧,却在“五千米深处”、厚厚“岩层”下思考责任重大的“中年”,一种张力被拉开了,压抑之深之沉,忍耐,憋着渴望冲破一切的强烈意念;读完整诗回看,“炸裂”是诗眼,“我”“炸裂”的不仅是岩层,更是人生,一个人到中年,依然被束缚无掌控的人生。而纪录片怎么处理的呢?画面仅仅是工人和矿洞,于是“炸裂”一词出现时,画面转为忽然的爆破场面与爆破同期声,非常刻板生硬,折损诗义。私以为,诗歌读到”炸裂”一词时,所配画面如果是一群工人从黑暗的矿洞洞,忽然间,蜂拥而出,见一片光明蓝天,是否更见诗之蕴涵与影像魅力呢?相比之下,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中拍摄余秀华去看雪,因患有脑瘫疾病而身体状况不佳,她走路时的模样一瘸一拐。镜头下,摇摇晃晃的人影走远,是人文关怀的注视;镜头转至空镜,雪纷纷落下,旷白、洁净、缓慢,观者则思绪停留,悲天悯人的诗意心境顿生,诗人诗情的写意再现得以淋漓,甚至烘托出了观者诗情,产生移情效果。
在文字艺术转化为影像艺术的过程中,诗歌的诗艺结构,文学文本间通过词语间、上下句之间的,以意象的勾连与冲突所营造的诗意想像,艺术再创造为影像文本的结构时,体现为一种二次解读、一种再阐释,其中诗意想像的诗艺内蕴流失与否、表达精准与否,则考验导演与剪辑导演的影像艺术表达力度。诚然,《我的诗篇》由于写意再现与情节再现的处理较为平叙朴直,对于其中诗歌诗艺的表达是欠缺的,而作为一部对社会阶层底层工人的生活境况、心灵状态的直接呈现,画面纪实记录,直面当代现实,为一群生活贫困而才华横溢的打工诗人发声,一股清流,涓涓而粼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