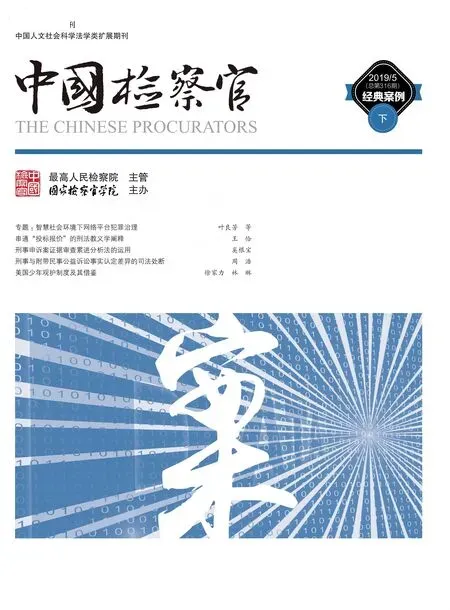网络平台犯罪及其治理对策
2019-01-26/文
● /文
在信息社会中,网络平台处于核心地位,信息社会活动高度依赖网络平台,网络平台是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网络平台相关犯罪随之迅速衍生,给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从前面两篇文章的相关犯罪学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网络平台相关犯罪与网络平台的运作模式紧密相关,有效治理网络平台犯罪,应以网络平台为抓手,落实网络平台的协助管理义务,强化国家管理机关的信息网络空间治权和用户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畅通网络平台与管理机关在违法犯罪数据上的联通,同时打造有利于遏制网络平台犯罪的信息网络社会环境。
一、网络平台犯罪的基本类型
网络平台是信息技术应用于商业社会之后的产物。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新的商业模式的发明,新的应用领域的出现,都有可能造就与以往不同的新型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新的网络社会生态中,已产生多种类型的网络平台相关犯罪。
(一)网络平台自身实施的犯罪
网络平台,作为提供网络空间服务的新型主体,自身实施犯罪同样严重,不仅可以实施网络化的传统犯罪,如曾经出现过的QQ平台中的以Q币为筹码的棋牌赌博,还可以实施新型的网络犯罪,如快播公司的共同传播淫秽信息。网络平台自身实施的犯罪有两种方式:一是由网络平台独自实施的犯罪,表现为作为犯形式的单独犯;二是由网络平台与其他犯罪主体共同实施的犯罪,或者由网络平台对他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升级”形成的犯罪,如快播视频网络平台对他人提供的违法内容信息进行深度编辑、整理,借助网络平台提供的网络空间广泛传播形成的犯罪。
(二)网络平台客观上起帮助作用的犯罪
具有网络技术和工具是网络犯罪的关键条件,除了国家以外,网络平台拥有最强的提供技术、程序等工具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被网络平台使用者用于实施犯罪,网络平台客观上起了帮助作用。相比其他发挥帮助作用的犯罪主体,网络平台拥有技术、资金、用户群等不可比拟的优势,特别是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自动信息处理、低成本、高效便捷的特性,造就了“一人服务人人、人人服务于一人”的社会行为样态,使网络平台环境下的犯罪具有了传统物态环境下所不具有的作用广度和深度。网络平台的这种特殊帮助作用对其新犯罪能力的获得,无疑是关键的。一般而言,网络平台实施客观上起帮助作用的犯罪,涉及两类:一类是普通的帮助犯罪,即网络平台的帮助行为对犯罪实行者侵害法益仅起辅助性作用,实践中这种帮助行为易与正常的业务活动相混淆,网络平台的主观罪过乃是犯罪成立的关键要件;另一类则是起主要作用的帮助犯罪,网络空间中某些犯罪的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远超实行行为的危害性,如网络打码服务平台,这类犯罪在性质上具有帮助行为的性质,网络平台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帮助能力,是其他下游犯罪得以实施的关键,因此具有独立的社会危害性。
(三)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犯罪
信息社会的良性治理离不开网络平台的协助,需要网络平台切实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网络平台,作为信息社会生态环境的主要创建者、网络活动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与包括违法犯罪在内的平台服务接受者呈共生互利的关系,有责任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目前信息发达国家普遍对网络平台设立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我国包括《网络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内的法律规范也对网络平台规定了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违法犯罪监管以及协助执法等义务。在我国,网络平台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犯罪虽然没有司法判例,但客观上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如百度付费搜索竞价排名案、斗鱼直播平台乱象案等。
二、网络平台犯罪的治理模式及不足
(一)网络平台犯罪治理模式演进
网络平台犯罪需要进行有效治理,而当前的犯罪治理模式仍是传统的条块管理模式,以属地管理、管理物态对象和分行业管理为基础。首先,根据网络平台从事的行业确定具体的管理机关,特别是行政管理机关,如网络金融平台由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金融部门监管,网络出行平台由交通部门监管,网络直播平台由文化部门监管等;然后,由具体负责管理的管理机关,以行政地域为界对网络平台相关违法犯罪进行管理或执法。
在信息社会环境下,网络平台已不同于传统的管理对象,自身已形成封闭的生态系统,传统的条块管理模式不适应网络平台的运作方式,不利于社会管理机关掌握网络平台上的违法犯罪数据,实际上导致管理机关对信息网络空间治权的流失,而这无疑增加网络平台非法利用用户个人信息实施犯罪的可能。
具体而言,网络平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累积了大量的用户和海量的用户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管理数据,将相互依赖的服务提供方和服务接受方聚集在一起,“网络平台的特点在于始终存在两方主体,一方提供各种不同的技术架构以提供信息服务;另一方在该架构内使用该种服务,”[1]但随着服务提供方技术的不断进步,服务接受方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平台容易形成封闭的生态系统。
(二)网络平台犯罪治理模式的不足
在上述情形下,以条块管理模式治理网络平台犯罪的不足愈发明显,网络平台犯罪治理呈现出一些问题:
1.国家的信息网络空间治权流失。在面对跨地域、全领域和信息态的网络平台经济活动时,条块管理模式遇到了低管理维度管不了高维度经营活动的困境。当前网络平台普遍具有封闭式运营和全领域扩张的特征,部分网络平台几乎成为信息网络空间中的“封闭性藩国”,管理机关难以探知其经营活动,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监管,在我国社会全面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下,如果不提升国家对网络平台的管理维度,国家对信息网络空间的治权流失情况将更加严重。
2.用户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不足,加剧了网络平台利用用户个人信息实施犯罪的可能。网络平台自身实施的犯罪以及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犯罪,往往与利用用户个人信息有紧密关系。虽然《网络安全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对保护用户个人信息起积极作用,但刑法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不足。例如,虽然《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此罪不能规制网络平台非法利用用户个人信息的不法行为,尽管前置法对此类不法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但对网络平台而言,只是增加了一些经营成本,根本起不到阻止违法犯罪的作用。
3.网络平台与管理机关在违法犯罪管理数据上联通不畅,不利于发现和防控网络平台中的违法犯罪。由于网络平台形成了封闭的生态系统,只有网络平台,才能第一时间掌握网络空间内他人实施网络活动的数据,实时发现违法犯罪活动并能采取有效控制措施。而网络平台与办案机关在违法犯罪管理数据上联通不畅,办案机关不能及时调取相关数据、调查网络平台上的不法行为,也不能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犯罪,甚至是案发后的调查取证都有一定的困难,如外地公安机关要调查淘宝网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去阿里巴巴公司调取涉案数据就存在困难。如果没有强制性法律措施要求网络平台及时提供违法犯罪管理数据,那么在紧急事态下执法机关也就无法强制网络平台实时提供司法协助,如滴滴司机故意杀人而滴滴出行平台未能及时提供协助就是很好的例证。与此同时,网络平台若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不仅会导致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大,犯罪黑数也会升高。
三、网络平台犯罪的治理对策
治理网络平台犯罪,应以控制力理论为治理根据,从网络平台控制法益侵害事实的程度上落实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同时,强化管理机关的信息网络空间治权和用户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畅通网络平台与管理机关在违法犯罪管理数据上的联通,完善对网络平台犯罪的治理。
(一)消极的事后惩罚对策
对网络平台犯罪予以刑事处罚,是事后的对策,通过对网络平台犯罪活动的消极评价,会起到一般预防和公正惩罚的作用。控制力理论可作为这一消极对策适用的理论依据。所谓控制力理论是侵权法学中的一种责任理论,是指包括网络平台在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取决于对侵权事实的控制程度,借鉴到网络刑法中,可根据网络平台对法益侵害事实的控制程度,来追究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
对于网络平台自身实施的犯罪,网络平台对法益侵害事实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属于主导控制法益侵害事实的情形。此情形下网络平台完全基于自身意志实施犯罪,控制法益侵害事实的程度最强,应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
对于网络平台客观上起帮助作用的犯罪,网络平台不属于单独的犯罪主体,而是和其他主体共同参与控制法益侵害事实,其控制法益侵害事实的程度较前者弱,刑事责任程度较前者轻。但是,如果是其起决定作用的,应以独立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只起辅助作用的,应按帮助犯处罚。
对于网络平台负有管理义务、有管控能力,未采取改正措施,未有效履行义务,导致法益侵害事实发生的,依法对法益侵害事实负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是履行义务超过其能力的,说明网络平台缺乏管控法益侵害事实的能力,阻却其刑事责任。
控制力理论不仅能反映网络平台不同犯罪行为控制法益侵害事实的程度,也能反映网络平台基于不同犯罪类型的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
1.有利于惩治网络平台犯罪。网络平台不仅是网络空间的提供者,更是网络空间的直接管理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被视为连接互联网的当然看门人,其毫无争议地处于过滤和制止互联网中非法和不良内容传播的最佳位置。”[2]网络平台“不再是纯粹的商业活动经营者。因而,在法律上都兼具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安全管理者双重主体形象。”[3]以控制力理论作为网络平台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能及时反映网络平台对网络空间出现的不法行为的管控程度,确定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程度,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2.有利于预防网络平台犯罪。在网络空间中,网络平台不仅自身可以实施犯罪,他人也可以利用网络空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依据控制力理论确定刑事责任,能提示网络平台管理好网络空间,将后者违法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为了预防损害的发生,应当由形成危险或风险的一方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些人更加接近损害发生的源头,由他们来承担责任更有利于损害的预防。”[4]
3.有利于降低防控网络平台犯罪的管理成本。以网络平台为中心治理犯罪,不仅有利于规制网络平台自身的不法行为,也有利于降低管控其他各类相关违法犯罪的司法成本。
(二)积极的管控对策
除了依法追究网络平台犯罪的刑事责任,进行事后的一般预防,还应进行积极管控,打开网络平台构筑的封闭社会生态,实现对网络平台犯罪的有效治理。
1.强化管理机关的信息网络空间治权。关键是要提升对网络平台管理的维度,建议在国家网络与信息化办公室体系下成立实质性掌控社会管理各部门、各行各业数据的大数据局,打通信息社会空间中部门、行业之间的数据流通壁垒。通过大数据局管控好网络平台的数据,对于各地发生的网络平台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由当地管理机关依法律程序向当地大数据局申请调取,各类数据分布式存储和集中调用。只有握住信息网络空间治权,才能更好地发挥管理机关治理犯罪的效能。
2.加强用户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是信息社会环境下的战略资产,对国家、社会和网络平台都具有关键价值,关于用户个人信息的利用和保护,应当平衡用户个人、网络平台和社会管理三方面的利益。应在确保用户个人的人身安全、重大财产安全等重要权益的基础上,在有利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前提下并经用户同意后,网络平台才能收集、提供和利用个人信息。对于网络平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利用、滥用用户个人信息开展业务的情形,除了从法律、行政法规方面完善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外,网络平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利用用户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应纳入《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制范围。
3.畅通网络平台与管理机关在违法犯罪管理数据上的联通。首先,要提高有关网络平台违法犯罪监管和协助执法等义务的规范效力层级。当前网络平台的违法犯罪监管和协助执法的义务大多规定在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必要提升这类义务的规范效力层级。其次,要明确网络平台未履行违法犯罪监管和协助执法等义务的处置措施,规定强制性法律措施要求网络平台及时提供违法犯罪的涉案数据,在紧急事态下网络平台未实时向管理机关提供司法协助的,应及时依法处罚。
注释:
[1]Volker Haug,Grundwissen Internetrecht,3.Aufl.,Stuttgart:Kohlhammer,2016,S.159.
[2]See Lilian Edwards and Charlotte Waelde,Online Intermediaries and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https://www.era.lib.ed.ac.uk/bitstream/handle/1842/2305/wipo-onlineintermediaries.pdf?sequence=1&isAllowed=y.
[3]梁根林:《传统犯罪网络化:归责障碍、刑法应对与教义限缩》,《法学》2017年第2期。
[4]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