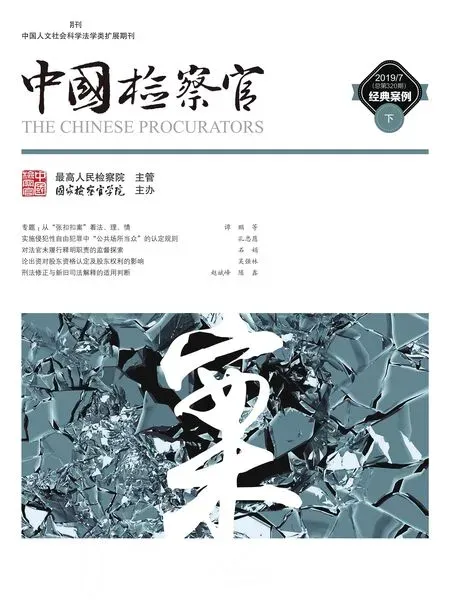为他人办理手机贷款后删除贷款信息并转移资金的行为认定
2019-01-26张建兵邱楠
●张建兵 邱楠 张 涛/文
一、基本案情
2017年以来,郭某某、倪某某租用南通市通州区某酒店房间作为办公室,从事贷款业务。2018年2月,被害人黄某某经人介绍来到郭某某、倪某某办公室,要求该二人为其办理手机贷款业务。郭某某、倪某某利用黄某某急于用钱的心理,取得黄某某信任,待黄某某告知其银行卡密码、支付宝密码等相关信息后,从黄某某农业银行手机APP软件中贷款,贷款成功后将黄某某手机中银行发送的贷款成功等信息删除,对黄某某谎称该贷款已被其他网贷扣除,并将资金转移至郭某某银行卡以及通过POS机虚拟购物方式套现。郭某某、倪某某采用上述方法共实施作案两起,取得黄某某人民币6999元,后予均分。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郭某某、倪某某在为他人办理手机贷款后,删除贷款信息,谎称贷款已被其他网贷扣除并转移资金,该二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郭某某、倪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因为诈骗罪是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而在“自由意志”支配下自愿处分财产的行为,其本质在于被害人自愿处分财产,财产占有关系的变化需要被害人的积极协助。诈骗罪强调通过骗取被害人的处分即交付,进而取得财产。[1]本案中,郭某某、倪某某取得黄某某信任,在黄某某自愿交出银行卡密码及支付宝密码后,为其办理手机贷款业务,后删除贷款信息并转移贷出资金。郭某某、倪某某的财产转移行为需要黄某某加以协助,本质上属于骗取黄某某的处分而取得财产,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郭某某、倪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因为盗窃罪是违背财产占有人的意思,以平和手段转移财产占有的行为,财产占有关系的变化无须被害人的协助,完全由盗窃行为的实施者自行完成,即强调直接从他人占有下取得财物,不用对方处分即交付。本案中,被害人黄某某并没有将郭某某、倪某某通过手机网贷为其贷出的资金交付给该二人占有的意愿,而郭某某、倪某某删除贷款信息并转移贷出资金的行为,违背了黄某某合法占有的意志,直接从黄某某占有下取得了资金,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构成盗窃罪。
三、评析意见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利用手机APP软件进行网络贷款等行为日益常见,也给一些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司法实践中,类似本案为他人办理手机贷款后删除贷款信息,谎称贷款已被其他网贷扣除并转移资金的行为时有发生,该类行为涉及到互联网支付这一新型支付方式,如何准确定罪处理,应予充分重视。就本案而言,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即郭某某、倪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具体分析如下:
(一)郭某某、倪某某删除手机贷款信息的行为导致黄某某产生认识错误,进而骗取黄某某的处分而取得财产
一般认为,诈骗罪(既遂)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或继续维持)认错误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获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2]实践中,取得财产的犯罪分为: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犯罪与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财产的犯罪。盗窃罪属于前者,诈骗罪属于后者,该二罪的关键区别在于:受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被害人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并未因此而处分财产的,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被害人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是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地位时,其帮助转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也不构成诈骗罪。针对一个财产损失而言,诈骗罪与盗窃罪处于这样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不存在同一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3]有无处分行为,划定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被害人处分财物时是诈骗罪,被害人没有处分财物时是盗窃罪。正确理解和认定“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所在。行为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进而骗取被害人的处分而取得财产,致使被害人产生财产损失,即可构成诈骗罪。
本案中,郭某某、倪某某以帮助被害人黄某某办理手机贷款业务为由,取得黄某某信任,待黄某某主动告知其银行卡密码、支付宝密码等信息后,从黄某某农业银行手机APP软件中贷款,贷款成功后又将黄某某手机中银行发送的成功贷款等信息删除,并对黄某某谎称该贷款已被其他网贷扣除。该删除贷款信息、慌称贷款已经扣除的欺骗行为,导致黄某某产生已获银行贷款的错误认识,进而错误处分其财产,导致资金转移给郭某某、倪某某,同时黄某某自身也受到损失。因而,郭某某、倪某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构成诈骗罪既遂。值得注意的是,财产处分行为不限于积极的举动,或者说“处分行为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不应在民法意义上理解,而是包括了被害人的一切作为、忍受和不作为”。[4]不作为的处分行为典型表现形式为,由于受欺骗而不行使“请求权”。[5]此外,欺骗他人放弃财物,而后自己拾得该财物的场合,属于他人即被害人在错误状态下自愿处分财物的行为,因而构成诈骗罪。[6]本案中,表面上被害人黄某某并未主动将财产所有权交付给郭某某、倪某某,但是黄某某的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其必须主动将财产交付给他人,也包括了黄某某的不作为,即其因受欺骗而放弃行使对已通过手机贷款贷出资金的“请求权”;[7]而且郭某某、倪某某欺骗黄某某放弃财产,而后自己取得该财产,属于黄某某在在错误认识下自愿处分其财产,因而郭某某、倪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二)郭某某、倪某某在作案过程中与黄某某沟通交往,而且介入了黄某某的中间行为
司法实践中,在移动互联网支付等新型支付场合,一般可以通过考察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实施手段或实行行为,进而厘清两罪之间的界限。
一方面,盗窃罪和诈骗罪在手段上的不同,体现在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沟通交往形态上的不同。行为人采取“排除沟通”的方式直接获得对方财产的,构成盗窃罪;存在“沟通交往”的情况下间接获得对方财产的,构成诈骗罪。诈骗罪的成立需以行为人和被害人发生沟通交往为前提,如未发生沟通交往,被害人就不可能产生认识错误,也就不满足诈骗的条件。只有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就“财产决策事项”发生了意思互动,才能认定被害人“合意”将财物移转出去。行为人利用虚假信息使被害人似乎“自愿”地转移了财产,该种行为威胁到了财产的流转秩序,因而刑法将其导致的“被害人同意”一律认定为无效,行为人必须对其行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8]本案中,被害人黄某某系具有意识理解能力的成年人,郭某某、倪某某非法获得黄某某财产的关键手段,是删除贷款信息并谎称贷出资金已被其他网贷扣除,进而导致黄某某产生认识错误而处分其财产。在此过程中,郭某某、倪某某与黄某某之间显然就“财产决策事项”进行了较为密切的沟通交往,倪某某、郭某某利用虚假信息获得黄某某的“同意”应当认定为无效,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另一方面,盗窃罪和诈骗罪在手段上的不同,还体现在是否介入了被害人的中间行为。实践中,该中间行为体现为被害人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这也是认定诈骗罪的关键要素。处分行为指被害人一方能够直接地造成财产减少的任何举止形态,必须是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害的“直接”原因,即被害人的财产损害必须“直接”产生于处分行为。[9]而在盗窃罪中,行为人不经对方同意直接拿走对方财产,在行为人的行为和财产取得之间,不存在被害人的中间行为。本案中,郭某某、倪某某删除贷款信息并对被害人黄某某谎称已贷出资金被其他网贷扣除,导致黄某某的错误处分行为,进而取得黄某某的资金,并非不经被害人黄某某同意而直接取得其资金,其中插入了黄某某的财产处分这一关键性“中间行为”。因而,倪某某、郭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盗窃罪。
综上,本案中倪某某、郭某某在为黄某某成功办理手机贷款后,删除贷款信息,谎称贷款已被其他网贷扣除,导致黄某某产生认识错误,进而骗取黄某某的处分而取得财产,而且在作案过程中与黄某某沟通交往,期间又介入了黄某某的“中间行为”,因而该二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注释:
[1] 参见黎宏:《刑法学各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31页。
[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0页。
[3] 参见张明楷:《三角诈骗的类型》,《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
[4] 参见张明楷:《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
[5] 同前注[4]。
[6] 同前注[1] ,第329页。
[7] 此处的“请求权”表现为黄某某对已通过手机贷款贷出资金的债权,即请求银行依法支付相应贷款资金的权利。
[8] 参见蔡桂生:《新型支付方式下诈骗与盗窃的界限》,《法学》2018年第1期。
[9] 同前注[2] ,第10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