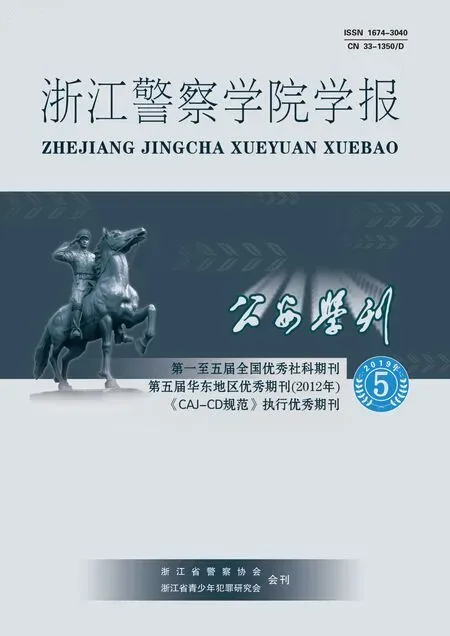不是“切除”而是“治愈”
——“枫桥经验”的隐喻学阐释进路及对中国法治的启示
2019-01-26余韵洁
余韵洁
(重庆大学,重庆400044)
一、引 言
“枫桥经验”是中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的兴起,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划分组成集合的敌对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来予以打击、管制、监督和改造,而对“四类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便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①毛泽东主席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场面向7000人的大会上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②但事实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和平运动,尤其在初期,斗打、乱捕甚至乱杀的过激方式占据了主流,充斥着血腥和暴力,从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扩展为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再到斗打“四类分子”的直系亲属,③斗打的范围、斗打的程度都无异于一场“赶尽杀绝”的激进政治运动,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本质与初衷。两年后的1963年,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说理斗争”的方式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崭露头角,④与武力制服阶级敌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枫桥群众利用感化、说理的温和方式顺利改造了“四类分子”,成为不流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标杆。此后,诸暨县枫桥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实践上升成为闻名遐迩的“枫桥经验”,其主要精神被总结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⑤
“枫桥经验”诞生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斗争大背景下,其卓越品质体现为,以阶级之内的方式解决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用对待“人民”的方式对待“敌人”,孕育了否定阶级斗争的萌芽,具有了平等对待所有人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本文试图通过隐喻学的方法,对“枫桥经验”的核心与本质作出阐释,以把握和进一步理解“枫桥经验”中的创新之所在,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稳定提供启发、赋予灵感,并给未来法治的深入推进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二、身体政治学隐喻坐标构建
隐喻,作为一种与明喻相对应的修辞方式,是人们认识、理解、解释复杂社会现象与事物并进行运用的思维方式。⑥同时,与明喻中本体——喻体之间具有表面相似性的特征不同,隐喻中本体——喻体之间是一种隐晦实质性的映射关系,质言之,“隐喻就是一种类比”,⑦在理论和学术研究范围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和平解决阶级斗争——可以通过隐喻学的理论获得一种新的认知进路。同时,由于阶级斗争的起源主要来自于身体政治学隐喻,本文将以此建立坐标中心(鉴于篇幅受限,只选择西方的这一国家机体论作为讨论背景),阐释“枫桥经验”核心内容对此隐喻基点的暗合与突破。
(一)身体政治学隐喻的西方源起
在基督教浸入西方的整个历史中,教会与国家之间相互渗透、彼此影响,无论是礼仪、法学、哲学还是人文主义领域,都制造出了各种混合状态的事物。例如,世俗世界的领导者(国王)在加冕的时候,要像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教宗)一样被授予一枚戒指,“到最后,神职人员有了一副皇帝的样貌,而国王则带上了一种教士的调子”。⑧又如,基督教徒出于福音性的圣爱而殉道的做法,通过人文主义者的手,转换成了领土性君主国家的人为了“祖国的爱”而献身的爱国主义行动。⑨政治体的构成也毫不例外,从西方中世纪至18世纪,神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借用基督教神学中的“基督奥秘身体”发展出了世俗对应物——“国家神秘身体”(即国体),⑩以此巩固世俗主权的统一性、延续性、永久性,就好像永恒的基督圣体一般。
“基督身体”的隐喻来源于新约圣经中圣保罗的机体论概念,“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哥林多前书》12∶12,12∶27,6∶15)。“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以弗所书》4∶4,4∶16,4∶25,5∶30)。按照圣经中所说,基督乃“基督身体”的头部,各个器官、肢节都在头部的主导下发挥作用,以维持整个身体的稳固存在。
到了中世纪中后期,教会以“基督身体”为模板,发展出了“基督奥秘之体”的政治体涵义用语,在这里,由基督教社会所有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信徒所构成的教会成为了“基督奥秘”这个集体性的、社会性的、法人性的有机体的身体,“基督奥秘”的头仍是基督,其可见的头则是基督在世俗间的代理人——罗马教宗。阿奎那认为:“正如整个教会被认为是一个奥秘之体,因为她与人的自然身体类似,也因为其活动的多样性符合肢体的多样性,因此基督被称为教会的‘头’……。”教宗卜尼法斯八世认为:“罗马教会的合众政治体‘体现为一个奥秘的身体,基督是她的头,而基督以上帝为头’。”
教会将“基督奥秘之体”政治化的过程深刻影响了世俗政治体的构建。毋庸讳言,这种“基督教政体”机体性结构原理正为新兴的领土世俗性国家所需,并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现代国家政治形态。13世纪开始,机体论的概念便从教会转移至了世俗国家,并赋予了其与教会相似的某种超自然性的价值属性,“国家奥秘之体”得以产生。一方面,“国家奥秘之体”是由头和许多肢体构成的无形的、合众性的、与各个有形自然体相区分的拟制体,君主是“国家奥秘之体”的头,“国家奥秘之体”是君主的身体。1536年,由英格兰高等民事法院(Common Bench)审理的Willion v. Berkley一案中,索斯科特法官在论辩中写道:“国王有两个职能,因为他有两个身体,其一是自然之体,由自然的肢体构成……另一个是政治之体,其肢体就是他的臣民,他和他的臣民一同构成了这个合众体。”13世纪晚期的比利时哲学家戈弗雷认为:“依照自然本性,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是神秘身体的一个器官。”英国的约翰·福蒂斯鸠爵士写道:“正如人的身体由胚胎发育而来,受一个头的管治,王国也是从人中生长而出的,作为一个奥秘之体而存在,由一个人来做头来统治。”另一方面,“国家奥秘之体”比拟“基督奥秘之体”(即教会)属灵的超自然基础,创设了世俗政治体得以存在并且永恒存在的神秘性基础——正义性、道德性与政治性,人们依照这样的德性和伦理性组合构成国家政治体。正如卢卡斯·德·佩纳在论述合众体原理时所说:“人们在属灵上加入属灵的身体,有基督为其头……人们也是在道德与政治上加入国家,即一个以君主为其头的身体。”
至此,以基督为头部的“基督身体”和以教会为头部的“基督奥秘之体”为摹本,世俗领土君主国最终发展出了以君主为头部的“国家奥秘之体”(又称“国家身体”“国体”),这种国家机体论概念不但促成了政治性国家的生成,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还极大地影响了关乎世俗政治体存续的“国家身体”中头部与身体的关系(主权者与国家的关系)、肢体与身体的关系(臣民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神经脉络与身体的作用关系(法律的作用),而正是这些关系从理论上深刻影响了阶级斗争的形成、走向以及实质意义。
(二)以身体政治学隐喻为基点的阶级斗争
1.头部的地位与作用
以机体论概念建立起来的国家身体中,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肢体是为身体服务的,支持身体、服从身体是其题中之义。不但如此,与同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头部相比,肢体的重要性也要位居其下,不但要依照自然理性听从头部指挥、侍奉头部,必要的时候还要为了头部做出牺牲。因为头部是身体的大脑、中枢神经、灵魂之所在,斩去作为国家身体的头,无异于斩去统一于身体的灵魂,灵魂破裂或者消失,整个身体也将不复存在。1628年英国主教劳德对国家身体的阐释足以说明灵魂对身体的重要性:“正如在一个人身体中,灵将所有器官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灵魂破裂,成员则四分五裂。教会亦然,国家亦然。”因此,头部毁灭,作为其结果,各个肢体也将毁灭自身,相当于整个身体毁灭。
在“国家身体”中,作为头部的是君主或国王,而社会各个阶层遍布头部以外,成为身体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一方面,这些肢体或器官的任务是执行头部大脑发出的行动指令,同时也要对抗一切攻击头部的行为,阻挡一切有害物或无用物。萨尔兹伯利的约翰在《论政府原理》中写道:“国家的头部是君主……心脏是议会……法官和地方主政官是耳朵、眼睛和嘴;官员和士兵是手……两足对应的是农民。”两个多世纪以后,法国人比赞继续论道:“贵族和骑士是政治体的手臂,普通臣民为胃腹、腿和足。”“王国的头就是国王……王国的任何一部分攻击国王,就是攻击头,并威胁整个身体,最后也是毁灭他自己。”另一方面,肢体、器官对于身体的作用也在于服从、支持以及保护,任何背反身体的行为都无异于自我毁灭,亦即肢体器官的任何自我攻击也等同于冒犯国家,比如,自杀也构成叛国。第一,公民为了保卫“国家身体”而贡献个人的财产(纳税)、外出征战、甚至牺牲生命都是国家机体论的自然延伸。1214年,自布汶战役开始,法国的王家军队的一部分便来自于普通公民集合,由这些法兰西政治体上的“肢体”来捍卫祖国安危,同时,另一些“肢体”——教会的教士——也要以其他一些方式如负担战争的经济开销来完成保卫法国奥秘之体的任务。事实上,每一个居住于法兰西这个以所谓“道德和伦理”之永恒价值建立起来的国家身体之中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下等人——都有奋力保卫身体的责任。第二,在国家机体论观点下,自杀者会因为这个最为私人的行为而触犯重罪,因为其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伤害了国家的安危,使得国家损失了健康。来自英国的法学家埃德蒙·普洛登在其编纂的《判例报告》中记录一个衡量自杀行为法律性质的经典案例——Hales v. Petit案,首席法官戴尔勋爵认为自杀是三重犯罪:“自杀者犯了重罪,不仅因为他的行为有悖自然、冒犯了上帝,而且也冒犯了国王,导致国王丧失了一名臣民,他作为头就丧失了他的一个奥秘的肢体。”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机体合众体概论下,不支持、服从身体的任何肢体器官都被视为腐化、堕落、丑陋的一部分,是与整个身体格格不入、不相协调的,必须要被“切除”。1296年,一位法国王室的法学家在一本匿名小册子中宣称:“那些拒绝服从整体,拒绝支持自己身体的无用、半瘫痪的肢体,乃是腐化堕落的器官,无论他是教士还是俗众、贵族亦或是平民,如果他拒绝为他的头或身体——即我主君王和王国——提供帮助,他们就证明他们自己是不顺服的器官,是无用、半瘫痪的肢体。”而对于这种如同断肢、有害于身体健康的部位,身体政治学论者皆认为应当“切除”,“如果为了全身的健康(整个身体的利益),我们说一个手或一只脚——就像国家的公民,必须要被切除。”
2.阶级斗争的隐喻:谁是头部
以身体政治学为坐标原点,阶级斗争的隐喻是决定谁为“国家身体”的头部,谁控制“国家身体”的灵魂和理性,谁主导“国家身体”的行为方式。头部虽然只是“国家身体”的一部分,但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了头部,只剩下躯干和没有生命的四肢,这哪是身体?并且,身体政治学中,头部必须是唯一的,排斥多个头部的存在,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而是一个怪物。无论是霍布斯还是博丹的国家主权理论,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机体论构造。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在一个有主权者存在的王国中如果又另有一个最高权力者存在,这本身就是个分裂的王国……每个臣民不可能要服从两个统治主……。”博丹在《主权论》中指出,主权(头部)不可分割,君主或是贵族或是民主只能占据其一,不存在两个或多个头部并存的混合政体。
在“国家身体”中,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被喻为身体各个部位的器官,各司其职。但由于头部的重要性和唯一性,诞生了争夺“国家身体”头部的阶级斗争,即谁成为头部,谁就是主权者,谁就是“国家身体”的灵魂之所在。
3.敌人的隐喻:腐化堕落的肢体
国家政治体由“一个身体、一个头部、一个灵魂”三位一体的身体理论打造而成,并对外表现为一个健康、统一、协调的整体。就如自然身体的手、足、器官、关节等都只能听从于头部的大脑而统一运动一样,国家整体、各个阶层、每个人也只能听从于主权者的命令而进行行动,在国家中,主权者的思想即为大众人的行动指南,违背其思想就会导致如身体紊乱一般的社会动荡。当国家的主权者确立之后,“国家身体”便拥有了唯一的头部,身体的思想、身体的理性、身体的良心都由头部所主宰。质言之,头部大脑的思想统辖躯干肢体的思想,这是身体政治学中“身体灵魂只有一个”的理论延伸。主权者,在现代国家中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贵族、还可以是民主(议会),成为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思想、信仰的源泉。正如萨尔兹伯利的约翰所言:“如果国王安然无恙,所有人都是一个头脑;如果国王死去,信仰则破裂。”
因此,不听从主权者指挥、不服从主权者思想、不支持主权者理性的敌人便成为了“国家身体”中腐化堕落的肢体,其存在危害了统一的身体机能,为了保全整体,无能为力,只能切除掉。“切除”意味着,那些不服从国家政权的敌人只能被消灭。
三、“枫桥经验”的隐喻学阐释进路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行进程中,枫桥地区的干部群众独树一帜的地方便是脱离了传统的对敌斗争方式。即使在中央制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大方针前提下,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区分敌我、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上。这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捕、判、杀等激烈的运动方式盛行,因为敌人的归宿应当是灭亡。而枫桥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浙江省委工作队发动的“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中,一致同意后者,并且在之后的社教运动中也积极贯彻了这一“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文斗理念。本部分内容将从身体隐喻学理论出发,揭示“枫桥经验”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精华之所在。
(一)抛弃阶级斗争:身体大于头部
在“国家身体”的构造理论中,主权者是国家的头部,国家是主权者的身体。这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头部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历史上,头部重要的观点直接映射为“君主主权”的政治形态,而身体重要的观点后来演变为“议会主权”的政治形态。事实上,头部重要的观点有可能导出头部可以吞没整个“国家身体”的结论,就好像中世纪教会政治中的教皇派所言的:“基督的奥秘之体,就在头所在的地方,那就是,教皇所在之处。”这种实质将肢体与头部完全等同的理论会导致不受限制的君主绝对主义,明显不符合国家机体论中身体应当大于器官的概念,因为头部也只不过是身体的一部分,属于身体的一个器官而已。16世纪,亨利八世对咨议会所说的话中明显表达了这个含义:“……当朕处在议会中的时候,王家等次是最高的,在其中,朕是头,而你们是肢体,联合并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政治之体。”上文提到的Willion v. Berkley一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含义:“另一个身体是一个政治体,其上的肢体就是他的臣民,他和他的臣民一同构成了这个合众体……他与他们连结在一起,他们也与他连结,他是头。他们是肢体……。”其实,机体论的“国家身体”概念中并没有发展出国王与基督一样具有“两个身体”的观念。也就是说,世俗君主作为“国家身体”的头部并不构成一个拟制的“独立身体”,他的身体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自然之身。鉴于机体论中强大的头部与肢体之间的统一协调理论,头部与肢体之间必须相互区别而又彼此牵连,头部根本不能吞并身体,因而,“君主大于个别的公民,但小于其全体”的区分肢体与头部、身体大于头部、整体大于部分的机体概念得以胜出。这标志着头部和身体是相互依赖的,正如君主在一些方面是至高无上的,作为政治体的“国家身体”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同样如此。
而阶级斗争在身体政治隐喻中的实质意义即为争夺并确立“国家身体”的头部。没有了头部,成何身体?但同样,没有了肢体、躯干,又成何身体?头部统领肢体在内的整个身体,但并不意味着头部能够替代或者吞并其他身体部位,因为每个部位对于身体来说都具有不同的价值。实质上,在身体政治学中,虽然强调“国家身体”的统一性,同时也强调“国家身体”的机能协调性,包括头部在内的任何肢体器官都只是身体的一部分,都只能在相应的位置发挥作用,共同为身体的健康运转发挥合力。阶级斗争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划分为主权者(人民)和被主权者(敌人),对于敌人要打击殆尽,这实质是将头部的地位置于身体之上——为了头部的利益要舍弃身体的某些机能,是将“国家身体”肢解的另一种方式。“枫桥经验”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破除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用所谓阶级之内的方式解决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用对待“人民”的方式对待“敌人”,孕育了抛弃阶级斗争的萌芽,是将整个“国家身体”的机能利益置于“各个身体部位”局部利益之上的考量和突破。因而,无论是在国家政权夺取、巩固的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中,还是在国家政权已经稳固的今天,“枫桥经验”弥足珍贵的核心意义都无异于在昭示国家政治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头部,还是身体四肢,亦或是其他器官,你们都与整个共同体一脉相承,同呼吸、共命运。
(二)以人为本:不是“切除”而是“治愈”
国家犹如身体的政治理念中,那些拒绝支持国家和主权者的人就好像自然身体中一个半瘫痪的肢体或不顺服的器官,是被认为与整个身体机能相排斥、格格不入的无用的一部分,必须要被“切除”。这一身体政治传统深刻地造就了近代“整体大于部分”“主权高于人权”的国家主义理论以及现代国家中对司法机关的性质与职能定位。
“保全整体,牺牲个体”是机体论中“身体大于部分”理念在近现代国家中的极度滥用,其构成了一种膨胀的国家主义或国家理性。这意味着,国家在紧急状态下甚至任何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了国家利益剥夺公民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被喻为连接自然身体各器官、各肢体于一身的“神经和肌腱”的世俗化结果——国家法律——同时也变成了低于国家理性的存在。质言之,在国家理性的主导下,法律的最高目的是维护国家整体、增进公共福祉,而不是维护整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基于此,西方历史上的英国就曾经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从14世纪开始,英国的国家理性开始膨胀,直至17世纪到达顶峰,由此爆发了议会与国家之间的争战。在此期间还诞生了臭名昭著的“剥夺公民权利法案”(Bill of Attainder)。这项法案于1542年1月29日由亨利八世在国会通过,导致了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被处决。剥夺公权(Attainder)这个词最早在英国历史中的隐喻是“污血”,起源于身体政治学中的“腐朽溃烂的身体一部分”,在国家政治体中演变为犯有重罪或叛国罪的罪犯本人,同时,与身体中腐化有毒的部分应当被“切除”一样,重罪者、叛国者也必须被处死。并且,这些罪犯不享有任何公民权利,不享有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将由对应的司法外程序进行处置,即议会通过即时立法、事后立法和审判绕过了专门的司法程序来剥夺掉这些罪犯的公民权利(以生命权为首,还包括财产权、世袭贵族头衔的权利等)。在英国这段时期的历史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斯特拉福德伯爵案(Strafford trial)——生动地揭示了身体政治学对“剥夺公民权利法案”的影响。在对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即第一任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审判中,圣约翰先生在论证应当剥夺公民权利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中这样说道,“议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身体,她囊括了从国王到乞丐的一切”,因此,“为了维护整体,(议会这一政治身体)对其本身以及身体上下每个部分都享有任意的权力。(议会)既是医生也是病人:一方面,如果身体有恙,为了自我治愈,她有权切开静脉,让污血排出;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分感染病毒并腐烂了,为了保全其余部分,她有权将其切除掉”。其实,在自然身体中,腐化有毒的一部分实质上也确保了机体免受进一步被入侵的危险,从这一程度上讲,其并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也应当是增强机体免疫性的有益的一部分。在处理这一有益的感染腐烂部分时,作为身体机体首先应当是治疗她,尽力使她痊愈,而不是一味地切除,因为这一部分在被切除掉的同时,身体本身也失去了对自己有益的一部分。政治身体如果可以类推自然身体的话,不是“切除”而是“治愈”才是对整体实质有益的进路,更何况,自然机体论真的可以一成不变地套用到国家身体论中吗?在国家身体论中,我们更应当关注到,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同国家一样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同样是在身体政治理念的影响下,以审判机关为首的国家机器被喻为“刀把子”。以我国为例,从新中国成立起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刀把子”一直都是人民法院的隐喻,常见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诸多司法文件之中,具有非常持久的生命力。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1958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司法工作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反革命,这不是说把什么案件都看作是反革命案件,但只要有敌人,我们同敌人的斗争就是尖锐的。司法干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死刑要不要?我们是从来不说废除,但要少用。死刑好比是刀子,我们武器库里保存这把刀子,必要时才拿出来用它。”而彭真在1979年《实现四化一定要有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讲话中也指出:“公、检、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是党和人民的刀把子,根本任务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有论者认为,“刀把子”对人民法院的隐喻来源于其本身的原始含义与司法权的属性与功能的契合,例如:“‘刀把子’原是把握道具的部分,可引申为对司法权的掌控”、“‘刀把子’为人人可用的器物,由此联想到司法的大众化特征”、“‘刀把子’系不祥之器,容易衍生出厌讼的社会心理”,但这种论点实际上只停留在了对“刀把子”的表层理解,其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家机体论构造。按照身体政治理论,国家的其他部位不顺服头部、不支持头部甚至还要对头部发起攻击,性质完全等同于不听从国家灵魂的指挥、破坏统一的身体机能,是倾向于毁灭整个身体的最终意图,而这些部位便是“国家身体”中腐化堕落的肢体部位(国家的敌人),应当予以“切除”(消灭)。切除自然身体的腐烂部位需要相应的刀具,而消灭“国家身体”的敌人需要国家机器,刀具对应于国家机器。在中国的相关语境中,刀具具体对应为“刀把子”,国家机器具体对应为人民法院,这同时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刀把子”的“把子”即握持部位由国家头部(人民)所掌握,另一方面,“刀把子”的“刀锋”部位是指向敌人、砍向敌人、消灭敌人的。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标语口号下进行治国,这种过分区分敌我、极度强调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范式,使得法律完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司法机关也纯粹沦为贯彻“切除”思维的“刀把子”。殊不知,“刀把子”的运用也是有利有弊的,运用得好,可以消除“国家身体”中无可医治的腐烂部位,运用不好,便是伤害“国家身体”的统一机能,使得其损失了原生于身体的一部分。事实上,极端阶级斗争的有害之处在于,将“国家身体”割裂为“头部”与“头部以外”的部分,消灭“头部以外”的原属于身体的部分其实是以“头部”取代整个身体的体现,这从国家机体论中“身体应当大于头部或器官”的概念来看,也是不可取的。
如前所述,传统的“打、捕、杀”对敌斗争、阶级斗争方式在国家机体论隐喻中代表着一种被“国家身体”全面否认的“切除”模式,而枫桥地区干部群众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说理斗争”温和方式和平化解阶级矛盾的经验,则是一种全力拯救身体各个部位的“治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式机体论照搬运用于国家政体中的症结,具有了更为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所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一方面,“枫桥经验”中的“治愈”手段意味着阶级之间的矛盾等同于阶级之内的纠纷,都被视为整个国家机体的疾病,要想国家机体得到最为完全的康复,这些疾病都需要对症下药,进行及时、有效、全面的治疗,或清除脓液或矫正畸形,如果每次都挥舞着“刀把子”切除这些病灶,“国家身体”上势必留下一个又一个的创伤,长此以往,对国家整体的机能性、协调性、健康性都是不可挽回的打击;另一方面,“枫桥经验”中的“治愈”手段超越了旧式的机体论,表现为清楚地区分了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的本质不同,即肢体、器官不但体现为“国家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为每一个鲜活、独立、与众不同的生命个体,代表了法治基石的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的意义呼之欲出。
四、余论:对中国法治的启示
从身体政治隐喻学的阐释进路中,本文揭示了“枫桥经验”创新精神的基础性价值,这种价值体现为对身体隐喻基点的的暗合与突破。一方面,国家机体论构造中,头部、躯干、肢体、器官都是“国家身体”的一部分,彼此分离而又相互依赖,谁都不能吞并谁,并且,“国家身体”作为整体比任何身体部位都要重要,因而身体比头部重要;“枫桥经验”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用对待“人民”的方式对待“敌人”,孕育了抛弃阶级斗争的萌芽,破除了阶级斗争——头部最重要与争夺头部——的思维定势,将整个“国家身体”的机能利益置于“各个身体部位”局部利益之上,是对“身体大于头部”机体论的暗合。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国家机体论构造中,“身体大于头部”“身体大于肢体”“整体大于部分”是基本原则,但极度滥用也会造成绝对的“国家身体主义”,就像不受限制的君主(头部)绝对主义在现代国家会导致君主的专制,从而导致大部分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不受限制的国家(身体)绝对主义在民主国家中也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进而少数人、个别人的权利同样无法得到保障。“枫桥经验”将阶级之间的矛盾等同于阶级之内的纠纷,一视同仁进行解决,不但具有反对以人的身份划分行为性质(反对区分敌我)的平等自由的思想,同时还具有反对以暴力、血腥的激烈手段消灭敌人(反对“切除”手段)而以感化、说理的温和方式改造敌人(提倡“治愈”手段)的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的思想,区分了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的本质不同,杜绝了国家机体论的滥用,是对旧式机体论原则的超越以及突破。
迄今,中国的法治建设一直偏向于“整体大于部分”的国家主义,这固然有出于对特定国家历史、文化、伦理等情况的特殊考量,但“枫桥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国家处于比较混乱、不稳定的时期,体现了个人自由主义的温和有理的“治愈”手段也远比激烈残暴的“切除”手段在社会治理方面付出的成本更小、取得的效果更好。转向如今和平稳定倡导和谐社会的新时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更应当回归至个人权利本身,在既有的国家主义法治元素的思维中更多地融入个人主义的元素,更多地维护和保障作为社会共同体而不只是国家政治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尊严、财产以及自由,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首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之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任务;直至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仍然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当下以及未来需要实现的“中国梦”。和谐为何屡屡被提及,重要性何在?和谐,意味着彻底否定了区分敌我的阶级斗争,意味着反对以保全整体为由牺牲个体,这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法治的理想维度,即法律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法律的最高目的从保护人民转向为保护所有人。事实上,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理想法治不仅是立法形式层面的“去阶级性”,更是诉讼程序、司法制度层面实质性的“去阶级性”,而理想法治的实现程度又集中体现于国家对于罪犯(无论是轻罪还是重罪、政治性罪或非政治性罪)所秉持的理念和所采取的措施。因为,侵害了法益(国家利益)的罪犯是给“国家身体”造成损害的一部分,其形式上等同于“阶级性”国家政治体中的敌人,而按照身体政治论所言,敌人属于腐化堕落的肢体是必须要被“切除”的。如果在“去阶级性”的国家政治体中,罪犯与敌人的最终结局相同或相似,那么两者实质相同,即这些罪犯在“去阶级性”的国家政治体中替代“阶级性”国家政治体中的敌人“复活”了,“去阶级性”成为一纸空言。如前所述,“枫桥经验”的宝贵价值在于抛弃阶级斗争,坚持以人为本,现代法治的核心同样在此,即实质是“去阶级性”、保护人权。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要体现每个人皆平等,都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进而,秉持着“枫桥经验”所示的法治价值,刑事诉讼法的真正目的也彰显出来,其并不是为了控诉犯罪、追求事实真相的制度构造,而是保护人权、预防犯罪的制度构造。现代社会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区分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分也能够简单论证前述观点。一方面,如果说,刑法的目的是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免遭损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秩序,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恰恰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免遭侵害,从而维护人类的基本尊严与自由。质言之,刑法所保护的损害是个人可能对国家造成的,而刑事诉讼法所保护的侵害则是国家可能对个人造成的,可以说,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刑事诉讼法绝不是贯彻执行刑法的程序法。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相比,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律对于追求事实真相是毫无优势可言的,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真实的目的,那么社会科学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换言之,社会科学的优势并不是“求真”而是“求善”,在面对善恶的价值判断面前,甚至可以过滤或抛弃真实。美国学者赫伯特·帕克在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模式中,将刑事诉讼程序比喻为一场障碍赛,这意味着在以人文本、保护人权的理念下,刑事诉讼是一场遍布一个又一个障碍阻止被告人被判有罪的单向跨栏赛,当国家无法通过自身力量跨越法律设置的障碍时,那么比赛就终止,绝不能再回头重新赛跑。
综上,“枫桥经验”的隐喻学阐释进路表明,对于“国家身体”中腐朽堕落的肢体、器官(不听从主权者指挥、不服从主权者思想、不支持主权者理性的敌人),应当竭力“治愈”而不是一味“切除”(和平说服而不是打击消灭)。相应,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应当吸取“枫桥经验”这一精华之所在,真正消除法律以及司法中的“阶级性”,回归个人权利本身,在既有的国家主义法治元素的思维中更多地融入个人主义的元素,更多地维护和保障作为社会共同体而不只是国家政治体的每一成员的生命、尊严、财产以及自由。罪犯享有人权、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同时,刑罚的功能也转向为矫正、预防以及规范犯罪。
注释:
①金伯中:《论“枫桥经验”的时代特征和人本思想》,《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第12页。
②赵义:《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③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④1963年,时任公安部领导的谢富治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下,将浙江农村枫桥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口头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服”“四类分子”的做法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当即表态:“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⑤参见前引③,吴锦良文,第43页。
⑥刘风景:《法律隐喻的原理与方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24-125页。
⑦[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⑧[德]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5页。
⑨参见前引⑧,康托洛维茨书,第348-366页。
⑩佀化强:《国体的起源、构造和选择:中西暗合与差异》,《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