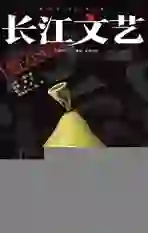小说二题
2019-01-25赵大河
赵大河
夜半敲门声
按: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审查死囚,看到这些要被处死的人,心生怜悯,下旨放其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来年秋天返回长安就死。第二年秋,头年所释放的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带领的情况下,都按期归来,无一人逃亡……
哐!半夜,他们被惊醒。黑暗中,接生婆罗小女攥着丈夫蔡葫芦的手,谛听着门口的动静。什么声音?敲门声,风,还是别的,比如狐狸的打闹?他们不能确定。
可是,接下来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寂静。他们不敢翻身,怕弄出声响。
对罗小女来说,半夜有人敲门,已经习以为常了。毕竟生孩子这事,谁也说不准时辰,说生就生,十万火急,敲门声通常急促紧密迫切,让人心惊肉跳,决不会只敲一声。
罗小女从17岁开始接生。她是误打误撞干上这一行的。她是老大,下边有10个弟妹。母亲还不肯罢休,又挺起了大肚子,又要生产。叫接生婆已来不及,母亲让她接生。我不会,她说。你能行,母亲说。母亲教她一步一步怎么做,她竟然成功了。从此,她一发不可收,一干就是30年,接生的孩子有多少,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也许不是敲门,蔡葫芦说。他心疼老婆,想让她多睡会儿。他是个木匠,他打制过很多家具,但自己家却找不到一件他打制的家具。这样说吧,他们家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全都是破烂。都是别人不用的,他捡回来修修补补继续用。他喜好旧家具。他说旧的物件有温度有感情。门也是旧的,两扇门的材质都不一样。听声音就知道你敲的是哪一扇门。刚才的声音是从右边这扇门发出的。左边那扇门的声音干硬清脆,右边这扇门则低沉圆润。他刚说罢,即做出修正:是敲门。
罗小女已坐起来,开始窸窸窣窣穿衣服,显然她的判断也是有人敲门。她甚至嗅到了外面人的气息。
谁?
我。
她问的声音很大,可回答的声音却很小,她有些气恼。
“我”是谁?
李大头。
李大头是罗小女娘家那个庄上的,李庄,他老婆是该生了。
作孽啊!罗小女叹息一声。李大头的老婆怀的不是李大头的孩子,而是那个冒牌货的。李大头出外七年,音讯全无。另一个男人冒充李大头,住进她家里,砍柴、种地、喂牲口,睡他老婆。李大头回来时,他老婆怀孕四五个月,已经显怀了。
当初,新婚不久,李大头说出去做生意,一走就是好几年,没有一点儿音信,大家都以为他死在外头了。李大头的老婆叫春香,姿色平平,一个人艰难度日。李大头有个叔叔叫李有财,想赶走春香,侵占李大头的家产。恰在这时,李大头回来了。他比走时个子高了一些,脸上也多了一道疤。他是李大头吗?看着不像啊。但他说他就是李大头。他能说出邻居们的名字,还有他和邻居们以前经历的一些事。比如他说他和李虎进山采药迷了路,见到一个小屋,他们想在那儿过夜,小屋的主人将他们赶走,走到半路,李虎想返回去把那家伙杀了,他将李虎劝住。李虎说,没错,我是想杀了那家伙,太可恶了。他又说许三强下河洗澡溺水,是他看到,下去将许三强捞上来,上来时许三强已经翻白眼了,他把许三强放到牛背上,赶着牛在沙滩上转圈,颠,把许三强肚里的水颠出来,又转了几圈,许三强才活过来。许三强说,要不是你,我就没命了。他又说和小飞有一天在树林里看到一个女吊死鬼,两个人都吓得大病一场。小飞说,别说了别说了,吓死人。不是李大头,他怎能知道这些。关键是,春香并不怀疑他是李大头。人家的女人都不怀疑,其他人有什么好怀疑的。李有财一直不信这个侄儿,说他不是李大头,他要是李大头,我把头揪下来当球踢。可是,没人听他的。再说了,他有私心,大伙都知道,就更不能信他了。
罗小女回娘家时,见过这个李大头。李大头管她喊姑。她说,你是谁?疤脸说,我是李大头啊,您不认识我了,我还是您接生的。她“噢”了一声,大头啊,变了,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她心里嘀咕,一个人怎么能变化这么大呢。春香与疤脸同床共枕,春香都没怀疑,她更不应该怀疑了。她好不容易说服自己,疤脸就是李大头。砰,一个瘸子从天上掉下来,说他才是李大头,那个疤脸是冒牌货。疤脸不甘示弱,说瘸子是冒牌货,他是真的。
这下热闹了,疤脸、瘸子都说自己是李大头,都说对方是冒牌货。疤脸拉过春香,你对他说,我是真的,让他滚!瘸子拉住春香,你说,到底谁是真的?春香哭着躲进屋里。
报官,报官!李大头的叔叔李有财说。
众人簇拥着疤脸和瘸子来到县府,求县太爷公断。这个案子轰动了整个县。衙门前人山人海,都想看看县太爷如何斷案。卖烙饼和吹糖人的凑过来做生意,生意兴隆。县太爷姓骆,骆知县。他说,这真是一大奇观,拍案惊奇!公开审理。疤脸和瘸子各说各理,都振振有词。李大头是独子,父母已下世,最亲近的人就是他叔李有财。李有财很肯定地说,瘸子是真,疤脸是假。邻居私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谁也不愿作证。最后李大头的老婆春香被带到堂上。骆知县说,事关生死,你必须说实话,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疤脸盯着她肚子,意思是看在肚子里孩子的份上,你也不能说我是假的。他相信春香不会指认他是假的。如果春香指认他,就等于说春香明明知道他是假的,还和他生活这么长时间,她要么是耐不住寂寞,要么是别有用心。如果这样,她的名声就毁了。瘸子眼巴巴地看着春香,像是在乞求。春香很犹豫。她不愿指认,只说求老爷明断。骆知县哪肯放过她,让她必须指认。他不相信一个女人会分不清哪个是丈夫,哪个不是。春香指着瘸子,她没敢看疤脸。骆知县问,他是真是假?春香说,真的。疤脸哈哈大笑。不待动刑,他就爽快地承认他是冒牌货。后来,他被判了死刑。
罗小女摸索着穿衣服。蔡葫芦爬起来点亮油灯,剪去灯花,屋里亮堂起来。不用点灯就行,罗小女说。她不慌不忙穿好衣服。无论来人再急,她不急。一是年龄大了,不比年轻时麻利,二是她清楚孕妇喊天喊地,终究会等着她的,生孩子哪那么容易。
罗小女拍一下蔡葫芦,你睡吧。她端上小油灯,撩开帘子,来到当堂。她将油灯放小桌上,去打开门。门外的黑影闯进来,带来一股冷风,差点将油灯吹熄。灯焰拼命挣扎,屋里黑影幢幢。尽管如此,罗小女还是看到来人脸上的疤。她吃了一惊。这哪是李大头,这是疤脸,冒牌李大头。她很快镇定下来,心想,疤脸被判死刑,应该已被砍头……想到这里,她打个寒战,莫非真有鬼。
她盯着疤脸问,你是人是鬼?
疤脸说,我是人,没吓着您吧?
她说,鬼我也不怕。
她问他刚才为什么说他是李大头,他说,说真名怕她不知道。她说,是啊,说李大头我知道,你说疤脸我更知道。她猜想他是越狱出来的。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找她。报恩,她于他无恩。报仇,她于他无仇。
罗小女看疤脸手上没刀,也没棒子、锤子之类的东西。他两手空空。不像是来找她麻烦的。他的声音也没有杀气。
葫芦已悄悄起床,手中拎着棒槌,站在门帘后,随时准备保护罗小女。罗小女说,你去睡吧,没事。
葫芦撩开门帘。疤脸看到他手中提着棒槌,不自觉地后退半步。
疤脸说,我来求您一件事。
罗小女说,你胆子真大,还敢回来,不怕瘸子杀了你?
疤脸说,我不怕死。
罗小女说,是,怕死的人不会那样胆大妄为。她指的是疤脸冒充别人丈夫,和别人老婆过日子。
疤脸说他不后悔。
后悔也没用,罗小女说。
我想求您件事,疤脸说。
你走吧,你没来过,我也没见过你,我不会帮你,我不想成为包庇犯。
姑,您误会了,我不让您包庇我,我也不需要,我是放出来的,不是逃出来的。
放出来的?罗小女不信,判了死刑能轻易放出来,哼!
我真是放出来的,疤脸说,皇帝开恩,将我们这批死刑犯全部放出来,让我们与家人团聚一年,明年秋天回去就刑。
有这事?
千真万确!
不怕我报官?罗小女说罢就后悔了,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
不怕。
像你的性格,罗小女不无讽刺地说。这家伙死都不怕,还怕你报官。他诡计多端,你得提防着点。
姑,我想求您件事,他说。
你不用叫我姑,我不是你姑。羅小女不想与一个逃犯(或者如他所说是特赦的死刑犯)有任何瓜葛,她说,你别求我,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你走吧,我就当你没来过,我不会报官。
您必须得帮我,只有您能帮我,疤脸说。
帮你什么?罗小女想将他赶快打发走,免得夜长梦多。她可不想惹麻烦。
救救孩子,他说。
救救孩子?罗小女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要救那个孽种,他的亲骨肉。瘸子不会留着那孽种,那是耻辱的象征。因为那个孽种,瘸子没少揍春香。不用猜,就知道瘸子不会留下那个孽种。那个孽种的归宿只有一个:鬼沟。
鬼沟是个弃婴的地方,包括活婴和死婴。那个地方野草疯长,阴森恐怖。夏天,即使中午,也少有人敢走鬼沟边那条小路。夜晚,即使打赌,从那儿走一趟给二斗麦子,也没人敢走。秋天一如夏天。冬天,草木枯萎,鬼沟不那么阴森,但恐怖依旧。有人看到成群的婴儿在枯草上跳来跳去玩耍,仿佛没有重量一般。还有人从那儿走被“鬼剃头”。回到家发现头发没了,从此成了秃子。春天的鬼沟据说最为安静,只有草生长的声音。但从那儿走也要小心,一声突如其来的婴儿啼哭便能将你吓个半死。另外,还有道德问题:如果弃婴是活的,你救还是不救?
救救孩子吧!疤脸突然给罗小女跪下。他动作幅度太大,灯焰随之摇晃一下,墙上黑影乱舞。他说他家三代单传,就这一点儿骨血,她若不救,他家就绝后了。
不知是真是假,这种说辞谁都会编。罗小女甚至有点厌恶,一个大男人给她跪下,让她有精神负担,帮他吧,凭什么!不帮他,受此大礼,似乎道义上说不过去。
起来,快起来!罗小女拽他,拽不动。她生气了,呵斥道,跪什么跪,起来说!
疤脸不起。他说他没有钱,他什么也给不了罗小女,但他求罗小女救救这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
我怎么救?罗小女说,瘸子要把他溺死,或者塞尿罐里淹死,我能拦得住吗?
您会有办法的,疤脸说,您一定有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只管接生。
您一定要救救他,您会有办法的,我给您磕头了。
疤脸咚咚咚给罗小女磕三个响头。罗小女没拦他,磕就磕吧,看来不答应他,这事就没完。她叹息一声。
我试试看吧,救了救不了,我可说不准。
必须救了!
疤脸声音不大,但里边透出的那股狠劲,让人不寒而栗。
罗小女说,你威胁我?
疤脸说,救不了会死人的。
屋里一下子静得出奇,彼此能听到呼吸声。这个跪着的男人,可能不小心,可能也是故意地,展示出积蓄在心中的那股可怕的力量。
疤脸补充道,我不会伤害您。言下之意,他会伤害别人,比如瘸子,或者春香。完全有可能。
罗小女相信这个男人为了一个婴儿会杀人。胆大妄为的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她接生这么多年,知道弃婴是普遍现象。每想到经她手出生的婴儿最后去了鬼沟,她就心里难受。狠心的男女为了一时快活,不顾后果,忍受十月怀胎和分娩之疼,最后两人合谋或一方强势,总之丢弃了亲骨肉。这件事,他们都背着她干,怕被她骂。没有不透风的墙,事后她都会听说,但听说了又怎样,无非一声叹息。她的心早结茧了。
罗小女现在清楚她无法置身事外,否则,“会死人的。”
她不想看到任何人死,也不想看到婴儿死,这就决定她必须做点什么。做什么呢?她会问瘸子和春香,婴儿要留着吗?当妈的一般都心软,当爹的却不同,瘸子会说,不留。不留就好办,她会说,我把婴儿带走,帮你们扔掉。瘸子会让她代劳吗?不,我自己来,瘸子若这样说,并把婴儿塞进尿罐里,她怎么办?赶快拉住,别,别,真是罪孽,死在屋里,冤魂不散,会有晦气。那就拿到外边,瘸子说。你留下照顾老婆,我帮你,她可以这样说,尽管她从未干过这样的事。瘸子会把婴儿交给她吗?你没必要让冤魂缠上,她可以这样吓唬瘸子。至于她,她不怕鬼魂。她会把婴儿扔进鬼沟。瘸子说,我把他溺死,你再带走。不,你的手不要沾血,沾血不好。瘸子会坚持吗?多半不会。如果一开始瘸子就要把婴儿留下,她怎么办?她说,你真要留下?瘸子说,真要留下。如果,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并不等于瘸子真要养这个婴儿,更有可能是瘸子不想让她插手,瘸子要自己处置这个孽种。还有一种可能,瘸子那方面不行。他结婚后没能让老婆怀孕,是其一,其二,正享受鱼水之欢,突然外出做生意,一走七年,也值得怀疑。这样,就麻烦了,他真有可能留下这个孽种。你能说,这是个孽种,扔了算了。瘸子可能会说干吗扔了,养着,我要让他叫我爹,我要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她怎么办?骂他,一个大男人,折磨一个无辜的婴儿,算什么能耐。管用吗?管用吗?管用吗?
罗小女让疤脸起来,她说她答应他,救他的亲骨肉。
蔡葫芦说,多管闲事。
罗小女说,不关你的事,你去睡吧。
黑暗中传来脚步声,一轻一重,渐渐走近。
是瘸子,疤脸说,春香要生了。
你快躲起来,别让他看见你。罗小女指指里间,蔡葫芦闪身,让出一条缝,疤脸进去。
脚步声越来越近,果真是瘸子。瘸子没想到门是开着的,屋里亮着灯,罗小女在等着他。
贞 操
完事之后,他看到床单上斑斑血迹像怒放的梅花:鲜艳,润泽,生机勃勃。血,仅仅是血吗?仅仅是女人的贞操吗?仅仅是命运吗?它还是千年来的黑暗咒语,还是沉淀于习俗的原始力量,这是族群意志的隐秘象征。
赤身裸体的马洛怔怔看着状如北斗七星般的几滴血,再也说不出话来。几个月来蓄积在躯体内的情感,突然爆发,跪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同样赤裸的李莹怕冷似的缩在墙角,像一团白光。她早已泪水涟涟,只是咬着嘴唇没有发出声音罢了。
馬洛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心中百感交集,难以言表。昨天他还心灰意冷,身陷地狱,突然间,美人从天而降,将他带入天堂。他来长安寻找李莹已经整整四十二天,毫无收获。他甚至不确定李莹是不是在长安。他之所以在长安寻找,是因为别的地方更不确定。除了长安,还能到哪儿去寻找呢?天下太大了。即使碰运气,也只能在长安碰,而不是去别的地方。昨天,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客栈,没有吃饭,倒床上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已是夜晚。李莹站在他面前。不是做梦。真真切切,就是李莹。尽管看不清楚,准确地说,他只看到一个影子,但他知道,眼前的女人就是李莹。他能嗅到她的气息,听到她的呼吸。借着窗外清冷微弱的光,他稍稍看到她模糊的轮廓。他从床上坐起来,伸出手臂抱住她。她的身子在抖。他揽住她的腰,把头埋进她衣服里。衣服粗糙的纹理摩擦着他的脸鼻子嘴唇下巴。她呼吸时肚腹起伏,像温柔的波浪。多么安静啊!他愿就这样抱着她直到永远。死在她怀里,他也心甘情愿。时间停滞了。她抱住他的头轻轻抚摸。这一刻,就是天地合,他们被压为齑粉,他也没有遗憾。他和她在一起,足矣。她松开他的手,开始脱衣服,他也脱衣服。她那样白,皮肤放光,照亮夜晚,照亮她自己。她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抱她入怀,将她放倒床上……
完事之后,月光照进来。马洛看到床单上状如北斗七星的处女之血,深感震惊。不,他宁愿没看这血,宁愿她不是处女。那样,她的罪还会小一些,他还能原谅自己一二。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这超出他的想象,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马洛号啕大哭,李莹默默流泪,到此时,他们还一句话都没说。沉默之中,往事汹涌。八个月来,命运天翻地覆,李莹从他的未婚妻变成杀人犯,他,良心备受煎熬。
八个月前,他和李莹定亲。他,见过李莹,她是一道明亮绚烂的光。他期待着和这道光结合,让这道光照亮他的生活。结婚的日子已经定下来,只等如梭的日月运行得快些再快些,好早点迎来大喜的日子。等待是甜蜜的痛苦,是芳香的焦虑,直到有一天,闫三说了那番话,一切都改变了。
闫三对一群朋友说,李莹是我的,以前是,以后还是,你们谁也别想打她的主意。
有人起哄,什么叫“以前是”啊,你给我们说说。
是啊,给我们说说,众人附和。
“以前是”就是“已经是”,她已经是我的人啦。
什么叫她已经是你的人啦,我们不懂。
就是说,我把她睡了,她把第一次给了我。
大伙说他吹牛,李莹不是那样的人。
闫三于是说出时间地点和细节,并对天发誓,句句为真,绝无半点虚言,如果他撒谎,不得好死。他说李莹私处有一颗玉米大的黑痣,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她。
谁会去问这样的事。
几个朋友皆感惊愕。他们都知道李莹已和马洛定亲。有些事既不能做,也不能说。做了,也不能说。没做,更不能说。
闫三,你摊上大事了。
闫三,你死定了。
闫三,你个傻瓜!
闫三的话传到了马洛耳朵里,马洛不相信闫三所言。他找闫三质问:你说的是真是假?
是真。
何以见得?
你可以去问李莹。
马洛把闫三揍了一顿。闫三没有还手。闫三说他该挨揍,马洛揍他是对的。他对朋友说,这揍挨得值。
马洛把亲退了。
他没有去问李莹,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莹已经声名狼藉。他不会要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一辈子不娶,他也不会要这样的女人。
他恨闫三。他恨李莹。他也恨自己,为什么没早点结婚。退婚容易,但从内心里割舍对这个女人的爱却不容易。李莹是一束光。他很清楚,他对这束光有多么迷恋。没有这束光,他今后的生活会多么暗淡啊!这辈子完了。没什么指望了。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女人来代替李莹,无论哪个女人,无论她多么漂亮,无论她多么芳香,她都不可能放光芒。那光芒来自骨头,穿越肌肉,透过皮肤,柔和得像棉絮。她,李莹,永远地带走了他的幸福。他,闫三,成为他在世上最恨的人。他想杀了闫三,只是他还有父母兄弟姐妹,他也不能成为杀人犯。
李莹对父母说,如果闫三家差人来提亲,你们就答应下来。
闫三是个无赖,她父亲说。
除了闫三,我还能嫁给谁,谁会要我?李莹说。
父亲叹息一声,没再说什么。母亲转过脸去,偷偷落泪。
李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被父母宠着爱着。突然间,她成了让家人蒙羞的人。因为她,家人出门抬不起头来。李莹说,我没做对不起你们的事。父亲听到,没吭声。母亲听到,也没吭声。李莹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怎么看这件事。他们只是沉默。沉默就是他们的态度。沉默里面包含了太多不可言说的东西:羞辱、无奈、失望、愤怒、冷酷、麻木、忍耐、窒息、死亡、寂静等等。她能朦朦胧胧感受到一些。她的心紧缩着。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不管她是如何变得声名狼藉,不管她有无过错。不管她是死是活,没有哪个家庭需要,没有哪个家庭愿意容留。她是多余的。她应该消失,快把这盆脏水泼出去。
闫三家差媒人来提亲,李莹父母没提什么条件就答应下来。大家心照不宣。中间环节比如合八字,定亲,看日子等等都省了,直接结婚。
闫三喜出望外,他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总该有点波折吧,可是没有。挨那顿揍不算什么,那是意料之内的事。
白日梦不过如此。
闫三与马洛比,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才没才,可是娶到李莹的是他而非马洛。凭什么?简单,造谣中伤,让女人名誉扫地,受点皮肉之苦,厚着脸皮求婚,如此而已。
成亲这天。尘埃落定,一切再无变化。闫三多喝几杯,得意忘形,对他那帮朋友说,咋样,我没吹牛逼吧,我说李莹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也是我的……哼,我看上的女人……
这帮朋友毫不掩饰他们的羡慕嫉妒恨。
上次说闫三,你摊上大事了的朋友,这次说,闫三,狗日的,艳福不浅啊!
上次说闫三,你死定了的朋友,这次说,闫三,你中,我看看你蹦蹦能日天。
上次说闫三,你个傻瓜的朋友,这次说,闫三,你牛,我们才是傻瓜。
闫三哈哈大笑,拍着胸脯,对这帮朋友说:你们看上哪个女人,给老子说,老子帮你弄到手。
闫三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进洞房,扑通,给李莹跪下,抱住李莹的腿,求李莹原谅。原谅什么?原谅我造谣。造什么谣?我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你是我的人,以前是,以后更是。还有呢?还有……还有,我说你那儿有颗黑痣。有吗?闫三嘿嘿笑笑,我胡说的,胡说的……
“胡说的”是闫三留在世上最后的话语,之后即是鼾声,再之后……
第二天,人们发现闫三死在床上。他的死法当时叫“千斤坠”。只有自杀的人偶尔会用这种方法,即,绳子一端绑床帮上,在脖上绕一圈,打一个扣,另一端拴一块土坯,自杀者猛地拉紧绳扣,推下土坯,土坯的重量使绳扣瞬间抽紧,即使自杀者后悔他也无能为力,救不了自己。还没听说有人用这种方法杀人的。
马洛痛苦得撞墙,头上撞出鸡蛋大的包。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能和李莹在一起。可是为了家族的名声,他不能娶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进门。他把李莹推给了混蛋闫三。他做得对吗?他,对吗?他不能确定。他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苦思冥想,想不出个所以然。屋子像坟墓,他像死人,至少这一天,李莹结婚这一天,他是一个死人。
第二天,李莹杀夫的消息传来,马洛无比震惊。他如同被闪电击中一般,呆若木鸡。他的血液冻结了。稍后,他的血液燃烧了。一个念头陡然升起来,他跳起来立即行动:去救李莹!
马洛满血复活。他跑到县衙去为李莹脱罪。他说闫三是他杀的,该受惩罚的是他,而非李莹。
縣官问:你怎么杀的?
他说:怎么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是我杀的。
你砍了几刀?
我不记得了。
慌乱中,我哪记得砍了几刀。
凶器在哪里?
扔到河里了。
血衣呢?
也扔河里了。
大胆刁民,敢欺诳本县,拖下去,打二十大板。
马洛被拖下去时,还兀自争辩,人是他杀的,他愿抵罪。他不知道,他早已着了知县的道儿。闫三死于“千斤坠”,而非刀砍。知县问他砍了几刀是诈他。他挨了二十大板之后,知县才告诉他实情。他仍坚称人是他杀的。他说,闫三虽非我杀,但因我而死,我不退婚,李莹不会嫁给闫三,李莹不嫁给闫三,就不会杀闫三,归根结底,闫三死于我手。知县不听他的歪理,将他赶出县衙。
马洛没能救得了李莹。他的努力非常可笑地失败了。他像个小丑。他想替李莹顶罪,失败了。他想被列为共犯,失败了。李莹被判死刑,他无能为力。我能干什么?他发现他干不了什么。除了祈祷,他什么也做不了。祈祷有用吗?他不确定。但愿有用。
奇迹发生了。皇帝放出所有死囚,令其回家与亲人团聚一年。
马洛等了一个月,没见李莹回来。他动身前往长安寻找。李莹为什么不回家?她害怕什么?长安好大啊!朱雀大街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还有许多胡人。他站在大街上,深吸一口气,他相信李莹就在长安。寻找吧。每一条大街,每一个小巷,每一个作坊,每一个店铺,每一个酒肆,每一个茶馆,每一个乐坊,每一个饭铺,每一个客栈……他都要走到,都要问到。四十二天。他将长安梳了一遍。希望。失望。希望。失望……他疲惫不堪。
回到客栈,和衣躺倒床上,朦朦胧胧他有过一丝怀疑:也许李莹不在长安。随即,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要相信奇迹,要相信奇迹。信则有,不信则无。李莹就在长安。他能嗅到她的气息。她在这儿。她在这儿……他睁开眼,李莹就在面前。黑暗中,一个会发光的女人。她是李莹。她只能是李莹。这不是梦。不是梦。他伸出手,触碰到一个比云还柔软的身体。他将她抱入怀中……
完事之后。面对床单上状如北斗七星的处女之血,马洛跪下,号啕大哭。李莹缩在墙角,默默流泪。
马洛哭了一阵后,拉过被子盖住李莹,抱着李莹又哭了好一阵。眼泪将被子打湿一大片。马洛说,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我是个懦夫,胆小鬼……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我是个傻瓜……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应该我去杀人,我去杀闫三……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应该我去坐牢,应该我去就刑……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我羞愧难当……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我生不如死。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你做了我该做的事……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你了不起……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说,请受我一拜……李莹不让他说。马洛跪下给李莹磕了三个响头。
早上,马洛醒来,李莹不见了。他上上下下寻找,一点儿踪影都没有。他问老板可否见一个漂亮女人出去,老板摇头。昨天夜里见一个女人进来吗?老板摇头。莫非南柯一梦?马洛跑回房间,揭开被子,床单上状如北斗七星的几滴血迹赫然在目。
选自《四川文学》2018年第10期
原刊责编 杨易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