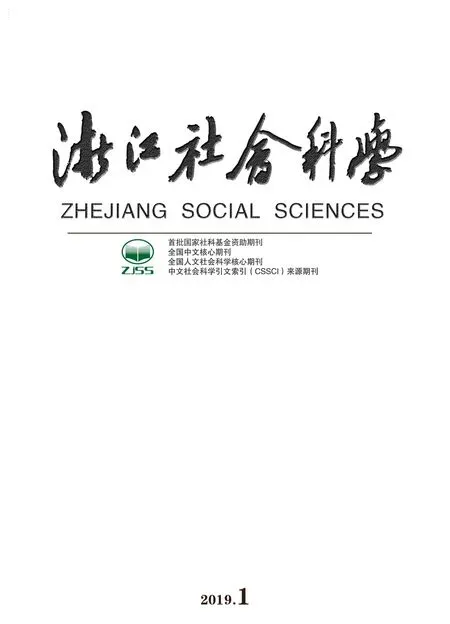农业与村庄的关系:一个新议题*
2019-01-24刘诗梦
□ 王 萍 刘诗梦
内容提要 农业与村庄的关系这一古老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经常性的困惑”,是必须要加以解释的命题。随着农业产业的衰败与边缘化、农业政策的工业偏好与城市偏好以及农业政治意识形态的日趋式微,村庄“农业去中心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与“去农业化”几乎同时出现的则是农村经济的“后农业式”发展,包括村庄工业化发展、零售、服务业发展,即农业的后生产性,也包括乡村空心化、边缘化等村庄的衰败趋势。农业去中心化以及多样化的村庄发展类型均说明传统的农业与村庄关系正在发生巨变,需进一步评估这种变迁对村庄转型带来的复杂影响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
一直以来,农业与村庄的关系似乎是一个不用过多说明的问题。因为农业一直是区分乡村特性的重要指标,是村庄最重要的景观部分,村庄的核心就是农业经济的存在。也即,对于农村来说,农业是初始的、第一性的东西,没有农业也就没有农村。①但是,近二、三十年的发展经验不断提醒我们,农业与村庄的关系并不是如此简单明晰,可以用一句话讲清楚的问题。这个看似基本的问题,在经验上会遭遇这么几个刺激:第一,农业对部分村庄来说可以不是第一性的,甚至是几近消失的产业,比如工业化村庄,旅游型村庄,都市里的村庄;第二,农业并不一定与村庄重叠,比如都市农业区,市民农业;第三,国家对待农业与农村态度的矛盾性,即一方面从GDP角度出发,国家重点发展的是非农产业,或直接鼓励农村走非农化道路;另一方面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在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因而可以说,农业与村庄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经常性的困惑”,是必须要加以解释的命题。
一、农业与村庄的关系
梳理来看,从波兰尼关于市场的“嵌入”与“脱嵌”,以及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社会等概念入手,结合大转型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农业与村庄之间的复杂关系变迁。在十九世纪之前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及其经济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嵌入”在整体社会关系之中的,波兰尼甚至认为“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都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②不过自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自由放任、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也逐渐被打破了,这一过程体现被波兰尼形容为“脱嵌”的市场如脱缰的野马,开始脱离乃至凌驾于社会之上,村庄当然也不例外。这一从“嵌入”到“脱嵌”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当市场“嵌入”在社会之中时,零星的市场尽管存在,却是从属于社会的。然而随着市场从社会中“脱嵌”,社会的运转反而受市场的支配,社会也就演变成了 “市场社会”,并呈现混乱甚至解体的危险。市场由“嵌入”到“脱嵌”的过程,也是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社会的演化过程。从波兰尼的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进入近代之后,每一个村庄几乎都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产生的直接后果那就是类似于市场与社会、农业与村庄的关系也经历了互嵌、脱嵌的过程。
第一、农业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产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类型。③村庄是人类聚落发展中的一种低级形式,人们主要以农业为主,所以又称为农村。可以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农业与村庄的关系非常密切,甚或常常有人把农村简单看成是纯粹经营农业的地方,认为农村就等同于农业,农村人就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这个时期农业和村庄是互为嵌入的,村庄的性质表现为生产性和生活性的重合,即村庄就是农业生产,因为只有村庄才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条件,从自给自足到互惠互利都需要村庄作为保障;农业就是村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是重合的,生活就是围绕农业生产展开的,村庄同时是生活性的,是熟人社会关系中的,村庄熟人社会关系为村民提供了进行生产生活的社会支持。因此,在这种农业与村庄紧密相连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还表现在:农业尽管作为一种产业,担负着提供粮食的重任,但该阶段的农业生产主要并不是遵循市场经济的效率、利润原则,而是以生存共同体的互惠、互助为核心。农业与村庄的互嵌或者说农业村庄则说明了,农业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既以村庄作为一种地域基础,同时也把村庄生活编织进生产领域,使得村庄的生产和生活行为交织在一起。
第二、农业商品化之后,村庄与农业互嵌格局逐步解体,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外部庞大的市场需求,其生产和销售行为逐步脱离村庄。农业逐步市场化,这意味着农业可以从村庄中“脱嵌”出来,这一过程表现在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的市场发展,导致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开始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不必再与农业捆绑在一起,而是可以自由地迁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农业市场化需要农业技术为支撑,进行集约式发展,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农业产量是过去的几倍、几十倍,这就导致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农业成为极小一部分为了粮食经营性生产而规模化的人所依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不少农村土地闲置、农业经济活动的十分零散、甚至农业仅仅成为留守女性和老人就业的主战场,从而使得村庄成为一个“被遗弃的世界”。村庄不再是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的生产性单位,也不再扮演着熟人社会的角色,换句话说,村庄不再是可以为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的社会支持单位。村庄与农业互为需要的关系慢慢消解了,农业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部门,从这意义上讲,村庄转型的本质甚至可以简化为村庄的“去农业化”。具体来说,农业与村庄脱嵌式发展,既呈现为农业沦为一种村庄人的日常生活的补充性生活方式,比如城市型村庄,这类村庄本身已经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几乎没有耕地,村庄人已经不是农业人,基层政府实际上是把它当成城市来建设。不过这些逐步被纳入市民序列的村庄人,仍旧在小区里或者周边种菜,阳台上养鸡;再比如我国不少城郊村或超级村庄,农业并没有完全退出,而是与工业经济比重相比,农业的比重很微弱,但是农业在社区经济中却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作用。④
第三、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村庄变迁的经验来看,村庄转型是从传统农业社区向现代居住社区的转变,是一个社会内在多样化的进步过程,也是一个功能不断分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行动慢慢地从地域化情景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脱域化”发展。⑤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土地以及农业产业的整体“城市取向”,人们的农业生产行为、消费行为慢慢地与村庄分离开来。一方面,农业生产行为与农业商业行为的分离。大多数人的农业生产行为主要在村庄实现,但除了少部分维持生存的农产品生产之外。大部分商品化农业的销售、消费行为均在村庄之外。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村庄生活的人,其消费行为也逐渐与村庄脱离开来,这也是农业与村庄脱嵌的另一深刻内涵。
从国内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农业与农村的分离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流的、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些趋势不仅在发达国家乡村变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近二十年类似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也开始加入这一行列。这种变迁导致了一系列的“现代追问”:农业是否是农村?农村什么时候是农村?⑥村庄在什么意义上是农村?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把与现代化同步发生的主流趋势概括为村庄的“去农业化”。进一步分析的话,“去农业化”进程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业的“去中心化”发展,包括农业产业的边缘化,包括农业就业比例,农业整体收入,农业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比例都在下降;农业政策的工业偏好与城市偏好;农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趋减。另一类就是农村经济的“后农业式”发展,包括村庄工业化发展、零售、服务业发展,即农业的后生产性功能逐步凸显。村庄的替代性发展模式往往被概括为乡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乡村商品化等。
二、村庄“农业去中心化”的发生机制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生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进一步说,在工业化时代以后,农业总是处于市场经济的边缘。⑦这不仅表现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农业所占份额的大幅度减少,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农业与农村关系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巨变,如今的“农村”不再等同于“农业”。或者更干脆的说,农业在农村的中心地位已经改变了,农业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中已经逐渐“去中心化”。概括起来看,支撑起村庄的“农业去中心化”发展的机制主要有:农业产业的衰败与边缘化、农业政策的工业偏好与城市偏好以及农业政治意识形态的日趋式微。
(一)农业产业的衰败与边缘化
资本主义农业变迁的主要表现就是农业产业转型,主要是指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现代农业的追求是用工业化方式、新技术来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投入大、周期长、自然风险大等弊端,发展高效、集约型的农业产业。农业的工业化趋势,即农业产品不再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甚至可以脱离自然条件,成为工业化的产品。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改进,⑧这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这也使农业摆脱了仅够维持生存线的生产地位。这些变化长期被视为“乡村发展”的核心。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速中,尽管农业革命的动力、方式与进程与发达国家的不同,⑩但这场农业革命对农村转型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实现了粮食增产增收,但另一方面却直接导致了农业日益危险化。从全球范围来看,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一个趋势,即随着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农业非但没有出现兴盛的局面,相反,各国现代化进程无不展示农业产业日趋衰败的景象。这种衰败表现在农业三大要素资源的持续流失以及由此导致更深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变化,如农业老龄化和女性化。
第一、农业衰败的直观呈现就是农业就业人口、农村土地、资本这三大要素持续不断的流失。总体来看,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及其集约化发展,直接导致农业就业人口比例的下降。当然,这不仅包括农业直接就业人口的减少,而且间接的就业,包括与农业有关的零售、服务,农业辅助产业。而且,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非单一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出,而是包括农村土地、资本在内的农业生产三要素都流出,并进而导致农业的衰败。这也就意味着,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多的收益。⑪由于农业整体收入不断下降,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发生了巨大了改变,产生了没有农业的村庄、一个农场企业就是一个村庄、农业消费型发展等各种复杂的情况。
不仅如此,从微观来看,农业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比例都在下降。越来越多的经验说明,农村家庭经济收入构成中农业比例的下降,而来自其他产业的比例则逐步上升,例如国内外相当多研究注意到家庭外出人口汇款行为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⑫农业家庭在农业花费上日益降低,比如农民在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上的花费在家庭支出中的份额日益减少;我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情况则是,留在农业或者保持农业生产的农民多数不再是为了农业利润,而是为了避免城市工作的不稳定而做出的退路性选择,因此普遍的对农业生产不用心。例如那些城市打工机会较多的农村,基本上是根据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来做出农业的生产抉择:譬如,因玉米劳动投入较低而选择耕种玉米,凭此达到接近于进城打工的每劳动日的收入,而放弃其他的经营可能。在这种种植模式之下,农业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活动,等于是打工的副业,自然不会很用心耕种,更不会积极创新经营。⑬而且,这种情况是当前的“半工半耕”制度下相当普遍的现象。
第二,农业就业人口的边缘化,集中体现为农业的老龄化、女性化等发展形态。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农业人口大量流出,向城镇集聚逐渐产生了一些副产品,即老人农业⑭与女性农业。2011年中国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在重庆举行的“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上谈到,目前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农农民年龄已接近60岁,“老人农业”现象已成为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难题。⑮2012中国农村经济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多个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比例高达85%,外出务工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的仅占8.9%。由此来看,所谓“老人农业”,指农业劳动力以老人为主,因为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土地大多由他们年老的父母耕种。⑯对此,一部分人认为当前普遍存在的“老人种田”的合理性在于,老人种田维持了低廉的粮食价格、低廉的养老成本,以及低廉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在微观层面上维持了低成本与较高质量的农村家庭生活,在宏观层面上支撑起中国制造业优势。⑰但大部分人都悲观地认为这种状况很难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另一个结构性特点是,男性率先从农业中流动出去,大量女性滞留在农村。女性成为事实上农村常住人口的多数,主要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催生了一种新现象,即农业女性化。⑱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农户中农业从业人员总数为34246.4万人,其中女性高达18205.1万人,比例为53.16%。全国31个省(市、区)中,女性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男性的有24个,占总数77.4%。⑲农业女性化的原因被认为是农业比较效益低,土地、户籍制度结构的约束和限制⑳等诸多因素导致的。而且,这种现象是对农业常态分布的过分偏离,会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潜在问题。
这两类情况则说明农村家庭城市打工经济的兴起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了农业在家庭经济中的位置,并影响到农业发展本身。而这是否真的如黄宗智所认为的,说明中国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经济单位的强韧生命力,以及其所包含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廉价的妇女化和老龄化农业生产,要比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㉑
(二)农业政策的工业偏好与城市偏好
可以说,任何一国农业的盛衰,都可以在有关政策安排中找到根本性原因。㉒普遍观点也都认为中国农村改革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甚或可以说,在农村经济变迁中,市场绝不是单独起作用,在很多时候,政府仍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㉓因此,农业政策本质上体现着国家对待农业、农村的态度,比如五十年代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在农业工业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追求农业效率的同时出现了多功能农业的追求,㉔这意味着农业至少可以成为回归到区域经济的食品供应链中。20世纪80年代面对国际农场危机,欧盟和美国继续对农业实行较高的保护,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选择让农民直接暴露在全球市场威力中。㉕总体来看,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大幅度减少,实现了向经济调控、规制者角色的转换。而近十年来我国农业政策总体上偏向资本主义式企业(龙头企业),但同时也透出相当实在的社会公正倾向。㉖但是,由于我国农业政策的择定扭曲,必然产生持续性的偏差问题。㉗
第一、工业化模式下农业的角色和功能。传统时期,农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进入现代之后,农业在国家中的角色和地位则表现得非常复杂。一方面,农业作为一个传统产业,其对经济发展、人们就业以及福利供给方面的贡献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农业作为一个基础产业,其在人类生存、生态保护、社会安全以及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却不可忽视。作为农业大国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强调农业所发挥的提供资源等传统的功能之外,尤为重视农业所发挥的安置就业、稳定社会的政治功能。这一点在很多国家的农业规制中均可发现,比如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大米供给已经过剩,但迫于农民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粮食管理制度成为了出于政治需要而维持高米价的机制。㉘从我国现有农业政策来看,则是集中体现了国家干预特征,它强调对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提高的重要性,重视利用国家资源建设现代农业,采用宏观调控政策实现农业生产的协调和农场品市场的稳定。与此同时,在农民增收政策中,政府则强调市场就业、非农收入比重和水平提高对于农民增收的重要性。㉙>也就是说,在适当允许市场力量进入农业生产过程以外,目前国家干预仍然是我国农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在农民收入增加这块,则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这种情况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主导调控农业产业发展是因为农业作为一种基础产业,经济效率与政治安全同等重要。
尽管从各种说法上看,对农业重要性的强调已经到了言尽其辞,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基于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容易受自然力的影响,农产品特别是主要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以及需求收入弹性小等诸多产业自身因素,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安排,通常表现为“剪刀差”政策,即政府通过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㉚>长期使农业处于持续被挤榨的处境中。与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转换和农业自我发展的要求明显不足叠加在一起,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剥夺农业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㉛
第二、城市中心主义下的边缘化农村(农业)发展策略。西方经济理念对城市偏好政策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种范式:第一是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来解释,第二认为农业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歧视,是因为城市阶层在政治上具有过大的影响力。㉜工业化发展改变了城乡之间平衡的关系状态,一方面,城乡二元异质性逐渐明显,二元结构固化成型;另一方面农村(农业)逐渐沦为城市经济、社会、政治的附属品抑或边缘地带。而且,在相对固化的二元结构下城乡居民对政策安排的约束权数或影响力相差悬殊,市民作为已经从特定的政策安排中获益的集团,必然会以其政治资源的控制力和较强的行动能力千方百计抑制政府矫正农村政策偏差的冲动,从而使得相关政策的调控继续保持在以城市为中心的规则框架内,构不成实质性的变革。在这种城市经济、社会中心主义政策作用下,农村的边缘化发展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事实上的农业政策目标就成为了保护非农阶层和非农集团的利益。㉝
(三)农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趋减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地理学的研究中没有被认真地对待。㉞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体系,通常是社会特权群体发展出来并保持的。㉟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以及它的变动性,导致在资本主义中社会关系的再生,导致空间和社会结构意义上的不平等。农业经济发展对意识形态会发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小农自然经济时期,对土地、农业的依赖会形成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封闭及其自私等;对家庭、家族的依赖导致一个“传统指导型”社会;对男性家长的依赖,会形成社会人群的依附心理;在特殊的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㊱
通常,农业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对农业职业的认同感、农村精英的衡量标准、农民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等。㊲自现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在农民、农村形象塑造上,一直处于落后、蒙昧,需要被启蒙的对象;在价值取向上,乡村话语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而出现。由于农民与农村的“他者化”、“失语”,乡村话语始终无法在社会中正确地建立起来并播洒其意义,更别说在整个社会话语系统中占有优势。㊳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社会主要从金钱、消费的角度来看待农业职业,也就是说如果农业不赚钱或者赚得很少,那么这个产业就不是社会主流的选择;同样的,如何衡量农村社会的精英,也以非农业的工商业收入为主要指标体系,“老板”、“生意人”是农村精英的同义词;现代化话语分析在解释社会生活构建中以及对意识形态分析来说,都很重要。在农村政策和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拥有话语权的人绝非地道的农民,而是一些拥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较多的“准农民”或者干脆直接就是“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村庄俨然成为一个被市场控制、驾驭的社会,面临着解体崩溃的危险。
三、“后农业”村庄的发展趋势
和Murdoch一样,本文强调农村变迁研究的网络维度,即从纵向、横向交织的网络式维度来思考农村经济、社会变迁问题。㊴这要求:一方面,把农村放置在全球-地方的关系上,综合地来把握其变迁的趋势。我们会发现粮食价格体系的全球波动,大量农产品的出口与部分农产品的进口同时存在,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传统农业方式复兴等复杂的问题。另一方面,把农村放置在国家-社会关系上,把握农村变迁中的国家规制、社会自我运动力量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农村发展的多样化路径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村庄发展彼此之间还有某些关联,具有内在链接性。
整理英文文献时浮现的一个明显现象便是,国外乡村性的讨论有多个版本,包括农业的、工业化经济发展的、社会剥夺者的保护、荒野保护区。这些表述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移植在乡村的使用上,比如葛兰西解释了二十世纪法西斯的意大利,是如何把国家主义和乡村主义用于政治学的修辞;Howkins发现了英国乡村田园诗的政治性重新发现;Weiner讨论了英国和美国的乡村田园诗文化和经济意义,是作为与工业化进程相反的进程而被动员的。㊵可以说,经济体制变迁对每个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差异也是必然的。本研究强调农村“去农业化”变迁趋势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化,而零零碎碎的讨论将被概括为村庄的“后农业”发展。与“去农业化”几乎同时出现的则是农村经济的“后农业式”发展,包括村庄工业化发展、零售、服务业发展,即农业的后生产性。对诸如此类的替代性乡村发展模式,已有研究往往简单地概括为乡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乡村商品化,同时也包括乡村空心化、乡村边缘化等等说辞。
(一)“后农业”村庄的内涵
“后农业”发展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主要表示农业与村庄分离之后的一种过渡状态,其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乡村发展路径。这种说法隐含地强调一种趋势,那就是农村经济、社会景观中农业的衰退,取而代之出现的则是农村工业化,零售、服务业发展甚或商品化等不同于传统农业景观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乡村研究的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研究范式主要从农业的生产-后生产概念中引申出来。所谓农业的 “后生产”,Evans等人在整理相关研究基础上认为“后生产”有五个主要特征:从重视农产品的数量到重视农产品的质量;农业多样性的增加与非农就业的增加;通过对农业环境的关注降低单位投入并提高农业可持续性耕作;农业生产形式的多样化;政府支持下的环境规制与重构。㊶Wilson等人总结出农业后生产阶段的六个指标,即从注重农业政策调整到重视乡村发展;重视有机农业技术;反都市中产阶级价值观与环境态度的兴起;环境非政府组织得以参与决策的制定;从事多元经营;由农业生产转为对地方的消费(把农业活动看作生活消费方式)。㊷Ilbery等认为后生产主义的特征为降低土地利用强度、分散化农地利用及农业的多样化。㊸而Halfacree推论后现代乡村的到来,把乡村变成了一个符号,而且符号乡村要先于作为一个物质空间的乡村。Murdoch和Pratt把这些称之为“后农村的”,他们的方式主要关注乡村的学术话语如何采用明显的现代方式,这样他们把乡村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开来,通过这样的话语表达中的权力,如何参与乡村的非自反性的构建。他们认为如果这种忽视他者的话语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结构,那么后现代的社会学就必须产生”。这种方式会把注意力限定在权力上,即特定的行动者把他们的乡村性强加在其他人上。像Halfacree一样,他们也把乡村看成是从属于乡村的社会产品的一个物质的空间,即使指出在培养“城市”或者其他地方中,“乡村”还有不同的方式。
比较来看,我们所提的“后农业”村庄概念内涵要大大超出“后生产”农业概念,强调的是村庄经济“去农业”变迁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从类型上讲一定是多样的,包括欧洲所谓的现代生活压力下的农村,衰退的农村、边缘化的农村,或者我国更为直接的工业村庄、城郊村、空心村、旅游型村庄类型等。
(二)典型类型
国内外对村庄类型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比较流行,如已有的实体乡村和建构乡村以及用“分化的村庄”参数来定义、发展出来的某些理想的典型类型,如家长制村庄、竞争性村庄、保护性村庄和代理人村庄。欧洲的乡村地区主要有三种类型:现代生活压力下的农村地区,主要指离城市中心比较近、人口密度比较高,经济环境比较好,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多样化突出。这些地方的农业比较现代、集约。受到“现代回到自然运动”的影响比较大,土地往往用于第一或者第二居住地,用作旅游或者休闲活动;衰退的农村,这类型的村庄农业活动相对比较多,且往往有自然和结构的缺陷。人口持续地从农村到城市转移,未充分就业,家庭收入低和公共私人服务的持续衰落。边缘性的农村地区,主要表现为村庄去人口化和经济脆弱性,经济多样化非常有限,基础设施发展缺乏,建造昂贵。㊹对比来看,国内对村庄类型的讨论集中以一些指标体系来做划分,比如以非农化的方式与水平可以把中国村庄分成城村、镇村、工业村和农业村。㊺以地方(place)作为界定村庄的主要类型时,可以发现村庄既可能是一个传统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行政的地方,一个集体的地方。㊻以村庄行动者为依据,村庄可分成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㊼
我们无意建构一种新的村庄类型学,而是强调农村经济变迁带来农村社会的复杂化,特别是市场化侵入之后,村庄已经无力解决其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包括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与安全等。这说明农业与村庄日益脱嵌,必然推动村庄变迁与转型。而这反过来突出了村庄共同体在市场入侵之后,是无能为力还是主动回应,对此我们在最后部分的讨论中会涉及。这场正向的市场化运动中,因农业与村庄剥离性发展导致的,可以观察到的发展类型有:部分村庄现代化程度颇高,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走向了乡村工业化的道路;部分村庄则由于农业人口、资金的外流,日益成为空心村;部分村庄则通过农业商品化,发展村庄休闲产业,成为旅游型村庄。
首先,工业化村庄或者说非农社会经济区的特点是村庄内农业几近消失,经济来源完全以工业收入为主,而且这类村庄往往被赋予很强的社会主义特色,具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对于工业扎根村庄并且成长为一种新的非农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折晓叶、陈婴婴的《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作者把在村庄发展起来的工业以及非农经济概括为一种 “社区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类型说明:第一,非农经济在村庄的成长,需要有深厚的乡土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这种经济类型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第二,社区经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内部的经济调节机制,具有农村居民自治的性质并仍以村社区为其基本的利益边界。㊽该类型的“后农业村庄”充分说明了:第一,明确了现代化进程中村社区的未来前景远没有人们曾经设想的那么暗淡,或者说至少承认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是有存在的意义,是有未来的。第二,“超级村庄”研究显示的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某些倾向,提醒我们注意一些问题,比如乡土社会内源性发展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能人”的作用问题、乡村重建社区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多种所有制下解决问题的趋同性、社区实践中的合作问题、新的地方中心-非行政性镇的可能性以及“有增长无发展”的难题。
其次,消费型村庄是因农业景观的保护,进一步商品化而产生的一种村庄类型。在后生产乡村中,大多数资本积累都是通过乡村地区的商品化来实现的,也就是乡村环境的开发是为了满足或者创造当前的需求或者消费。㊾有意思的是,商品化同样也可用于乡村边缘性的开发,即因为远离城市的边缘性自然风景、人文景观而使得乡村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比如欧洲大量的乡村因为他们的边缘地位而成为有吸引力的地区,这意味着与此相关的边缘性行为可以在这些乡村经历中集中体现。有意思的是这些地区因为早期的没有城市化(偏远的位置、高海拔和没有耕地),现在反而可以转变成资产。这种村庄发展的类型偏离了经典经济学们对农村现代化的想象力,创造性地把村庄的“传统”、“落后”、“农业”等转变为村庄消费转型的卖点,从而来推动村庄实现自我价值、自我发展。
再次,空心村特指我国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村庄类型。对此,从土地利用的情况看,空心村就是村庄面积盲目扩大,新住宅多向村外发展,村庄内部出现了大面积的空闲宅基地的一种特殊结构布局的村庄。当然,主要归结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地方经济发展出现的“剪刀差”,从而导致的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状况。㊿这种村庄形态也是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从而造成的村庄内部建设用地闲置,是一种异化的聚落空间形态。51简言之,农村空心化是指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原宅基地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不良演化过程。52村庄空心化,一方面说明宏观工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抽取,导致村庄内部人力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围绕传统农业生产聚集起来的村庄功能逐步丧失,农业不再发挥凝集村庄人口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空心化的关键在于“失农业”之后,村庄的居住功能日益凋零,外部的尤其是政府的村庄发展规划、公共服务供给等缺失,加之村庄内部的尤其是传统的社区成员凝集机制的丢失。
当然,不少研究者强调季节性村庄(即农民主要从事非农工作,但季节性的回到农村从事短期性的农业劳动)以及准通勤村庄(即农民主要在中心镇或者小城市工作,仍居住村庄,每天乘车往返于家庭与工作单位之间)等诸多复杂的村庄类型也均被纳入“后农业村庄”的类型。不过,限于篇幅和能力,笔者在此就不展开论述。
农业“去中心化”以及多样化的村庄发展类型的出现均说明传统的农业与村庄关系正在发生巨变,或者说农业与村庄的关系问题已经慢慢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困惑”。当然,我们的工作不能停留在对“后农业”趋势以及典型类型的描述层面,而是需进一步评估这种看似不可阻挡的洪流对村庄转型带来的复杂影响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
注释:
① 许经勇:《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农业、农村与农村经济》,《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②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③ 李成贵:《中国农业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④ 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⑤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6页。
⑥ Friedland,H.,“Agriculture and Rurality:Beginning the“Final Separation”?”,Rural Sociology,2002,67(3),350~371.
⑦ 山口重克:《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⑧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也有不同,黄宗智概括为主要的两种类型,英国的古典模式和东亚模式或绿色革命。前者是通过畜力使用来节省劳动力和提高劳均产出,后者是依赖化肥和科学选种。
⑨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6月版,第12页。
⑩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与发达国家的农业革命不同,中国表现为隐性农业革命,其动力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是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上升的变化。
⑪ 温铁军,杨殿闯:《中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及化解机制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8期。
⑫ Hill,B., “Farm Household Incomes:Perception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9,15(3),345~358.
⑬ 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2006年第10期。
⑭ 山口重克:《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83页。
⑮ “老人农业”现象成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现实难题,新华网,2011年7月11日。
⑯ 程必定:《中国的两类“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8期。
⑰ 桂华:《中国农业生产现状及其发展选择》,载《中国市场》2011年第33期。
⑱ 张凤华:《乡村转型、角色变迁与女性崛起——我国农村女性角色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⑲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⑳ 刘筱红、姚德超:《农业女性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㉑ 黄宗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人们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3月。
㉒ 李成贵:《中国农业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㉓ 王晓毅:《国家、市场与村庄-对村庄集体经济的一种解释》,《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农村组织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㉔ Ilberty,B.,1998,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In:Ilbery,B.et al.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Longman.Harlow.
㉕ Share,P.,Campbell,H.,and Lawrence,G.,1991.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structuring of Rural Regions: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In Family Farming: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pp.1~23,Alston,M.et al.Keypapers No.2,Centre for Rural Social Research,Wagga Wagga,Australia.
㉖ 黄宗智:《中国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㉗ 李成贵:《中国农业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 15~16页。
㉘ 山口重克:《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㉙ 郁建兴、高翔:《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㉚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㉛ 李成贵:《中国农业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㉜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㉝ 邓大才:《试论农业政策的非农偏好及矫正思路》,《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㉞ Pratt,C.,“Discourses of Rurality :Loose Talk or Social Struggle?”,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6,12(1),69~78.
㉟ Langton,P.,Kammerer,D.,Practicing Sociology in the Community,2005,Pearson:53.
㊱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版2011年,第 30~34 页。
㊲ Marsden,T.et al.,Constructing the Countryside,London,1993,UCL Press.123~138.
㊳ 贺艳:《传媒中的 “他者”:浅析乡村话语边缘化现象》,《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㊴ Murdoch,J.,“Networks—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0,16(4),407~419.
㊵ G.J.Lewis,G.,Maund,D.,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A Framework for Analysis”,Human Geography,1976,58(1),17~27.
㊶ Evans,N.,Morris,C.,Winter,M.,“Conceptualizing Agriculture:A Critique of Post-productivism as the New Orthodox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2,26(3),313~332.
㊷ Wilson,G.,Rigg,J., “Post-productivist Agri-cultural Regimes and the South:Discordant Concepts”,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3,27(5),605~631.
㊸ Ilbery,B.,Bowler,I.,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London,Longman,1998,57~84.
㊹ Bengs,C.,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Europe.in:Collections of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x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n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2004,255.
㊺ 卢福营,刘成斌等:《非农化与农村社会分屠——十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㊻ 王斯福:《什么是村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㊼ 罗兴佐:《社会行动单位与村庄类型划分》,《甘肃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
㊽ 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㊾ Bengs,C.,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Europe.in:Collections of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x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n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2004,255.
㊿ 张昭:《关于河北省空心村治理的理论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第4期。
51 张军英:《空心村改造的规划设计探索——以安徽省巢湖地区空心村改造为例》,《建筑学报》1999年第11期。与此类似的看法有:空心村是在我国特有的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因此,空心村是在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条件下由迅速发展的村庄建设与落后的规划管理体制的矛盾所引起的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进一步参见薛力《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城市规划》2001年第6期)
52 刘彦随等:《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