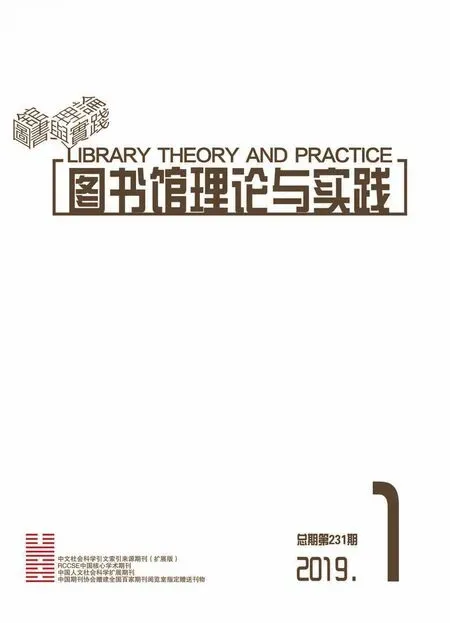口述历史后期成果的评价问题
2019-01-21全根先
全根先
(国家图书馆)
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史学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史学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口述史学理论、开展方法与项目成果的介绍,对于口述历史后期成果的评价问题却少有问津。然而,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如果缺乏一个切实可靠的评价标准,很难成为体系严谨、发展成熟的一门学科,从而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因此,笔者认为,对口述历史后期成果的评价问题进行探讨,势在必行,意义重大。至于评价标准的建立,当然不能脱离口述历史的基本特色。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1]口述历史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主要从口述历史访谈、口述文稿处理、口述史成果的艺术呈现、文献收集与工作卷宗等方面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1 口述历史访谈
口述历史访谈可以说是口述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口述历史后期成果评价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对于所有口述历史项目而言都是相同的。不过,由于口述历史访谈的对象不同、目的不同,故对其成果的评价不能“一刀切”,要根据访谈目的而区别对待。口述历史的对象与口述历史的目的,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口述历史的目的决定了口述历史的对象,而口述历史的对象反过来又会对口述历史的目的产生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口述历史项目的启动,要在确定口述历史目的前提下进行;而口述历史对象的选定,无论其对象是群体还是个人,都会对口述历史目的之实现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决定口述历史项目的最终成果。
同时,口述历史与单纯以文字形式书写历史的方式不同。口述历史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或者说,口述历史本质上就是多人参与的历史记录与书写方式。口述历史项目的关键人物,姑且不论其影像文献的艺术展示,至少有两人,即采访者与受访者;口述历史的内容是由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决定的,项目的成败与成果的展示,就内容而论,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互动的结果。正如左玉河先生所说:“作为研究者的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受访的历史当事人不仅处于研究对象的客体地位,也不仅是历史研究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研究的参与者,同样是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双重主体是口述历史研究的突出特性。”[2]
口述历史的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口述历史的创作。然而,他们在口述历史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又是不同的,其中采访者对于口述历史的创作尤为重要。首先,采访者与受访者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一个是主动者,一个是被动者;其次,采访者对于访谈内容起引导甚至主导作用,直接决定了口述历史的最后成果;最后,作为口述历史创作的一方,受访者一般都是由采访者选定的。同时,作为口述历史的采访者,能否充分发挥其主动性,遵守口述历史访谈的学术规范,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准备、访谈问题设计,在访谈过程中是否能娴熟运用访谈技巧,对于访谈记录能否进行高水平整理,并与受访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访谈内容,这些都是影响口述历史后期成果的重要因素。
真实性是口述历史的灵魂。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当然不能脱离受访者的个人记忆,又不能完全依赖受访者的个人记忆。有学者指出,记忆并不只是单纯地再现过去,它还“拥有忘却和写入两方面”。[3]所谓“忘却和写入”,实际上决定了记忆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与完整的再现,而总是有所选择、有所损益的。口述历史是否真实,这是决定口述历史的必要性、可信度的核心问题,也是评价口述历史后期成果的根本标准。换句话说,只有具备真实性的口述历史成果,才有进行评价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由于社会与个人原因,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总会面临各种挑战。① 来自社会的挑战,主要是指在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记忆可能被有意篡改,只能被部分地甚至片面地加以展现。著名戏剧批评家、作家夏衍先生说:“电影是阶级斗争中最犀利的思想武器。”[4]实际上,岂止是电影,几乎所有领域都可能出现类似问题,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社会集体记忆遭到篡改。② 来自个人的挑战,既有受访者记忆衰退的自然因素,又有其当时的心境、情绪、动机,以及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与对采访者的信任度等因素。但尽管如此,在口述历史后期成果评价中,真实性仍然是评价的根本标准。
对于口述历史后期成果评价而言,项目本身的意义与受访者选择是否得当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口述历史采访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与物力,项目是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至关重要。就是说,要考察这个项目所涉及内容对历史发展是否产生过重大影响、有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开展口述史采访的目的,就是要搜集现有文献资料所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历史资料,或者能够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丰富已有的文献资料,拓展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果项目不符合以上条件,不论这个项目实施过程如何尽力、费了多大功夫,都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口述历史项目。与此同时,在口述历史项目选定以后,受访者的选择也非常重要。笔者认为,理想的受访者应当是口述历史项目的亲历者、见证者,具有清晰的历史回忆和良好的表达能力,并且是这一项目的积极支持者。
就口述访谈的过程而言,访谈前准备是否足够充分也是后期成果评价中的重要内容。访谈准备是否充分,可以通过访谈成果加以判断。成功的口述史采访,必然会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采访提纲,通过访谈提纲,可以看出采访者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程度、对于受访者是否有深入的了解、是否具备项目所涉及的相关知识。采访者对受访者了解得越多,越容易提出针对性的问题,调动受访者的积极性,从而挖掘保存在受访者脑海中的历史记忆。同时,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交流情况,访谈中是否达到了此次采访的主要目的,挖掘到已有文献所没有的历史信息,受访者讲述的信息是否完整、足够深入。不论访谈过程如何,内容新颖、完整、深入是在后期成果评价中占据第一位的因素。
总之,一个成功的口述历史访谈,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交流充分,内容可信,发掘深入,生动具体,富于个性,能够弥补已有文献之不足,从而形成新的历史文献。
2 口述文稿整理
口述历史与一般学者撰写的历史著作不同,它不是个人创作成果,而是由采访者与受访者通过对话共同完成的。由于是口头交谈,必然会掺杂许多不符合文字书写常态的表现形式,甚至出现政治、学术问题,因此,对于口述文稿进行整理是口述历史项目的重要工作环节。口述文稿的质量高低,既受前期口述访谈内容制约,又与口述文稿整理有关。就前期访谈内容而言,采访者与受访者的文化修养与性格习惯,以及他们之者的互动与博弈,对于口述文稿质量会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口述文稿整理者(不论是采访者、受访者,还是第三者)能否进行高水平的文字处理,对于口述文稿的质量高低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口述文稿整理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和规范。首先,必须将音频资料转录成文字,如果是以少数民族语言或外语进行的口述访谈,还应转录为对应文字的速记稿(无对应文字除外),同时转译为汉语。速记稿中,需保留访谈时间、地点、采访者、受访者的信息介绍,并与口述内容逐句对应,不做任何润色与修饰。在此基础上,整理者根据文稿内容进行大致切分,组成若干章节,拟定相应标题,形成主题明确、逻辑合理的口述文稿。这是口述文稿的基本框架。由于口述访谈目的与对象各不相同,口述文稿篇幅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口述文稿的最终呈现形式,大致不外乎书稿与文章两种,不论是哪种形式,口述文稿的整理者都应对口述访谈内容进行合乎逻辑的结构编排。
对口述文稿进行结构编排后,就要对文稿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处理。这是一件非常细致、费时的工作,需要注意许多问题:一是要保持口述内容的真实与话语风格;二是要使口述文稿的语句通顺,纠正错别字,具有可读性;三是要对访谈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专业术语等专有名词进行逐一核对与适当注释,以免发生学术性错误;四是酌情删除受访者习惯使用的无实际意义的口头语,使文稿更为简洁通顺;五是要根据访谈时的具体语境对语义不完整的句子加以补充,并用括号的形式标明;六是根据书稿或文章的出版(或发表)要求,选择质量较高的照片进行配图。虽然口述文稿的具体形态丰富多样,整理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然而,笔者认为,在口述文稿整理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历史事实与文献资料的考证与核实。
根据笔者经验,在口述访谈中,记忆错误的事情屡有发生,不可不审慎处理。例如,一位学者提到江苏省淮安市西汉名将韩信祠里的一副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与韩信的生平事迹:韩信屡建奇功,被封为淮阴侯。刘邦当了皇帝,猜疑韩信,韩信知道后密谋造反,被韩信一个门客的兄弟举报;吕后知道后,便与萧何商量,引诱韩信到长乐宫中,将他斩首;萧何发现韩信要逃跑,于是月下追韩信,并秘告吕后,把韩信给杀了。这段叙述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是在韩信拜大将前。接着,他又讲,韩信投军之前,家中贫困,食不果腹,差点饿死,是一位洗衣的妇人把他接到家中,他在妇人处吃住十多天,才保住生命。这个记忆也有误,因为韩信在“漂母”处“蹭食”,不是十多天,而是几十天。这两件事,在司马迁《史记·淮阴侯韩信列传》中均有记载。又如,一位学者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彭陆罗杨”①事件,说是批判这几位老帅。事实上,他们都不是1955年授予军衔的共和国元帅。对于这样的问题,口述文稿整理时必须注意。
口述内容不符合逻辑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某位非遗传承人在谈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时,追溯该项目的历史:汪近圣是越国公汪华的后裔,汪氏家族为了不跟李世民发生战争引起战乱,归顺唐,汪华被封为越国公;汪华生有九子,徽州汪姓就是他的后代;发展到清雍正年间,制墨大家有汪近圣,他是我们家祖上,他应该是第84世,我们是第90世。这个世系,如果不加推算,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然而稍加推算就会发现:如果汪华是第一代,传承人本人是第90代,那么,差不多是15年左右一代;如果汪近圣是第84世,传承人本人是第90世,那么,两代人之间相隔差不多是40年!无论是何种算法,传承人的口述必定有误。
在口述文稿整理中,我们既要尊重受访者,又要对其口述内容进行分析与核准。例如,某位传承人在口述过程中,引用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由于传承人记忆有误,说成:“(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勤奋,零点五是天赋”。又如,某位学者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关于“红专辩论”与“工具论”时提到:有些人说,“我就是工具”,可是我挺反感,因为马克思说过:“工人是不会说话的工具”,我说:“共产党是挽救人民的,他怎么会把人民当成‘不会说话的工具呢’?所以,我就是想不通。”[5]按:口述者提到马克思说“工人是不会说话的工具”,此处记忆有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最残酷的”。[6]7771他还提到,“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6]249如此看来,马克思原话不是像口述者所说:“工人是不会说话的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可能是套用古罗马作家马可·铁伦提乌斯·瓦罗在《农业论》中的一段话。瓦罗将奴隶比喻为“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犁是“无声的工具”。②
同时,在口述文稿整理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纠正文稿中的学术问题,还要关注文稿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口述文稿出现政治问题情况并非鲜见。
总之,在口述文稿整理过程中,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对于口述文稿整理质量进行评价,要从篇章结构、学术、政治与文字处理等方面进行考量,严格检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3 口述历史成果的艺术呈现
口述历史与单纯以文本形式书写的历史作品不同,口述历史作品的创作,除了采访者与受访者,还有摄像、录音、剪辑等多人参与;其成果展示方式,除了口述文稿,还有视频与音频形式,根据采访目的、采访条件、设备情况,口述历史的展示形态各不相同。如何合理地安排访谈环境,如采光、访谈人坐位、摄像机分配,以及摄录技术标准等,均为口述史采访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后期成果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而言,为了尽量避免引起受访人的不适与紧张,拍摄中应尽量使用自然光,如自然光照不理想,再考虑全部或部分使用灯光。在采访人的座位安排上,以采访者与受访者坐高相仿、视线相对为佳。
至于摄影机分配,如仅有一台摄影机,没有摄影师,摄影机应主要拍摄受访者;有摄影师的情况下,应在采访者提问时,拍摄两个人。景别为中近景,构图原则为人物主体在画面中央稍微偏左或偏右的位置,视线应与偏移方向相反。如有两台摄影机,则可考虑两种情况:一是如访谈采用类似对话形式,即受访者与采访者语量相仿,一台拍摄受访者,一台拍摄采访者。两台摄影机都应位于采访者——受访者轴线的同侧。景别为中近景,采访者在画面中的位置应与受访者相对,视线也相对。二是如访谈以受访者为主,采访者仅负责提问,无过多交谈,两台摄影机均可拍摄受访者,摄影机位置位于采访者旁边或身后,一台拍摄中景、一台拍摄近景,两者构图原则相同。如有三台摄影机,则可以安排其中两台拍摄受访者,一台拍摄采访者,构图原则相同。③
口述采访完成以后,除了对口述文稿进行整理以外,对于音频、视频资料的处理(即素材整理)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而最终的呈现形式,大体可以分为文献片和综述片两类。
所谓文献片,就是在不省减口述采访基本内容情况下,对采访所得音频、视频资料,根据口述历史访谈的时间顺序,以次为单位,根据口述史文稿剪辑成片。文献片应最大限度地保存访谈内容,去除中间休息、噪音打断等与口述内容无关部分,将不同机位拍摄的画面剪辑在一起。需要注意的是,受访者提出不予公布的部分,其画面要加黑色字幕题版,隐去声音,并添加“此处根据受访者意愿,隐去××分钟内容”字样。文献片要求结构合理,叙述流畅、完整,声音清晰,画面美观。
所谓综述片,是在文献片制作完成的基础上,对口述采访成果进行提炼,选择其精彩部分,进行概括性展示。一般来说,综述片可以不拘泥于采访者的对话形式,将受访者的生活场景、历史资料、工作状态等音频或视频内容嵌入其中,运用蒙太奇手法制作,可以进行调色、调光、配音、配乐、特效、解说等艺术化处理,影片需要设计基本包装,片头、片尾、字幕标准,要有一定的艺术水准。让观众在了解口述者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怀、事业发展、口述采访内容的同时,有一种美的享受,得到精神升华。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文献片还是综述片,影片中的字幕都非常重要。正是通过这些字幕,才能正确传递口述访谈的基本信息,体现口述访谈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字幕必须正确无误。根据笔者经验,口述历史影片中字幕错误现象屡见不鲜。此外,字幕文字要求清晰、准确,视频分辨率为1920×1080。字幕位置须贴合内安全框左下角,字幕版式需左对齐,字体为黑色,并设置字间距,每屏字幕不超过14个字。如果访谈是少数民族语言(且有对应文字)或外语,需有双字幕。如果受访者在叙述中记忆有偏差或是发生口误等,应加以修订,并在其后加括号注明。
对于口述历史作品的音频质量,要求清晰、完整。由于采访环境或访者身体状况等原因,有时在采访中会受到噪声干扰,甚至因某些突发情况而被迫临时中断。此时,采访团队就要保证受访者叙述的清晰可辨以及内容的连贯和完整,这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在参加文化部2015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后期成果评估验收时,接触到许多传承人口述历史的文献片(包括口述片、项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和综述片,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影片都存在较大的问题,既有项目执行团队对于执行项目理解不深造成的问题,又有项目执行团队总体艺术水准不够的问题,林林总总,千差万别。尽管存在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就是在对口述历史项目后期成果进行评估时,应当重视其艺术化展示及对视频、音频作品进行评价。通过口述历史成果的艺术化展示,可以进一步传播口述历史研究成果,激发和带动人们从事口述历史创作的热情,推动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4 文献收集与工作卷宗
4.1 文献收集
口述历史采访,本质上是要从受访者那里获取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以补充或填补已有文献资料的不足。为了有效地进行口述历史访谈,采访者必须作充分的文献资料准备,主要是收集有关受访者的各种信息与资料。实践证明,对受访者的充分了解,有利于采访者与受访者的沟通与联络感情,是做好口述历史采访的必要环节。同时,口述历史采访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口述史料,还应尽量收集相关历史文献,与口述访谈史料进行互证、核实和辨伪。如果条件允许,采访者还应注意收集与访谈内容有关的文献与物品,如受访者的日记、家谱、相册、奖章、奖状、证书、手稿、笔记、纪念品,以及磁带、音频、视频资料等,丰富口述历史访谈成果,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对于那些受访者未赠予原件的文献资料,应当尽可能数字化。
需要说明的是,采访者在向受访者征集文献资料时,还存在著作权问题,应当妥善处理。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说:“将口述历史狭隘地界定为只适用于大型档案收藏是不对的,但是访谈者做口述历史必须按照口述历史的标准,并且应该承担法律、伦理和方法上的责任,包括将其访谈提供其他研究者验证或进一步运用的责任。”[7]在国内,口述史界著作权纠纷事件也时有发生。这就为口述历史工作者敲响了警钟,要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当然,尽管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口述历史的采访者还是应当尽量收集与受访者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往往可以弥补口述访谈之不足。
对于口述历史项目的文献收集情况,也可拟定一定的评价标准。根据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为文化部非物质文化司起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收集文献情况评价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文献价值,能全面反映传承人及非遗项目各方面的特点及信息,种类丰富、全面,数量多,且能合理地解决版权问题;二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文献价值,能较全面地反映传承人及非遗项目各方面的特点及信息,数量较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版权问题;三是史料价值、文献价值一般,仅能反映传承人及非遗项目的部分特点及信息,种类单一,数量较少,未能解决版权问题。以上标准,虽然是针对非遗传承人的记忆项目,但其他口述历史项目也可作为参考。
4.2 工作卷宗
口述史采访费时费力,完整地记录口述史采访过程、形成系统而完整的工作卷宗非常重要。根据采访目的与采访对象的不同,工作卷宗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在口述史采访过程中,已基本形成相对成熟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规范,在项目结束以后,整理成一份比较系统、全面的工作卷宗,以便长久保存。一般来说,口述历史项目结束以后,其工作卷宗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法律类文件,包括采访者伦理声明,受访者伦理声明,采访团队成员保密协议,文献采集、收藏与使用协议(特指通过口述历史采访所得之新形成文献),文献收集与使用协议,著作权授权书等;二是工作过程类文件,包括受访者基本信息表、工作团队成员基本信息表、拍摄日志、场记单等;三是工作成果类文件,包括收集文献目录、提交资料清单、元数据表单、口述史文稿等。
对口述历史项目后期成果进行评价,自然也包括对其工作卷宗评价,基本要求是:法律类文件要求完整有效,不能出现空缺、信息不全、存在疑问、信息不正确等情况;工作过程文件,要求能完整地记录工作信息,实事求是地反映工作过程;工作成果类文件,要求记录完整、全面、条理清楚,能真实反映项目实施情况,不能出现遗漏、空缺或错误。
当然,口述历史后期成果的评价,还可进一步延伸至项目成果和所有文献的保存和整理,甚至包括项目成果的开发利用。由于篇幅所限,相关内容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注释]
① 彭陆罗杨,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
② 关于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犁是“无声的工具”原文核准,笔者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张文喜教授帮助,谨致谢意。
③ 参见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内部资料).2016:28-29.